政治·社会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847 |
| 颗粒名称: | 政治·社会 |
| 分类号: | D675.7 |
| 页数: | 14 |
| 页码: | 99-112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漳浦县的政治、社会情况,内容包括解放前的漳浦警察、漳浦的禁烟禁毒。 |
| 关键词: | 漳浦县 社会问题 政治 |
内容
解放前的漳浦警察
·李松辉·
漳浦有警察始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5年)镇压白扇会起义之后。(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本来镇压“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开始悔悟到必须“维新”,在西安行在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宣布“维新”。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巡警部。光绪三十二年漳浦发生白扇会起义,烧毁县城英国基督教堂,捣毁甘林法国天主教堂,镇压白扇会起义后,漳浦按照“各省官制通则”改革政制,改原来负责缉捕、监狱事务的典史满人达明亚为警务长,改原来“捕快”十多名为巡警)。知县卢元璋奉令向“有匪各乡”(有人参加白扇会起义的乡村)派款赔偿英法教会(协议赔银四万六千四百元,摊派至六万四千元),派县丞朱映青为总办,警务长达明亚为助办。催收这次赔款是漳浦有史以来第一批警察的首次任务,催征孔急,曾开枪击毙梅林秀才陈实卿之母。
辛亥革命后,福建省设警察厅。北洋阀统治时期,漳浦重要集镇曾设警察所,所长由县知事卖放,警察由所长招收流氓充任,人数很少。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漳浦县设立公安局,局长杨子保。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受破坏,县公安局撤销,成立“剿共保安大队”,翁必达(猪母)任大队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成立公安局,设于麦市街烈女祠,林化龙任局长,警察三十多人,身着黑色制服,手执警棍,在街上巡逻。不久撤销。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开始设警察,在省保安处设警务科,县政府设警佐,在各区区署指定一个区员兼巡官,负责警察工作。省设警官训练所,开始训练第一批警察骨于。全省各县分二期设立警察,漳浦为第一期建警县份,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开始设警察机构。
福建初建警时是将原来各县的民政、区政人员调到省警察训练所施加训练后派为警官任用,然后由这些警官在县里成立警察训练班,招收高小毕业以上学历者加以训练,派充警士。后来才由省警官训练所招收高中毕业以上学历者入所训练,毕业后派充警官。我是原来已经在省公务人员训练所毕业派任区员,调到省警官训练所受训后再派回区署当区员兼巡官的福建省第一批警官。后来区成立警察所,脱离区署,独立行使警察职权。由于当时公务员必须回避原籍,我自任巡官至升级任县警察局长,都在云霄、南靖、长泰、诏安等邻县工作,抗战胜利后不再执行回避原籍的规定,才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从诏安调回漳浦任警察局长。但在漳浦任警官的多数是我在警官训练所时的同学,只有少数是中央警校毕业生,所以我对漳浦县的警察工作知之甚详,这里从漳浦1937年开始设警察至1949年9月解放的漳浦警察情况作一个概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省派闽候人张昭鼐来任漳浦县政府警佐,从属于民政科。10月,警察工作从民政科分离出来,成立警佐办公室,省先派张昭鼐来任警佐一个月,后改派冯德(四川人)来任,下设科员、办事员各一人,初由民政科调任,后由省派警官训练所毕业学员充任。年末,成立城区警察所(址在西街李家祠),由警佐冯德兼所长,省派林纯如为督察员,程瑛、黄瑞文、江子民、张怀三、丘大波为巡官,王振华为侦缉组长,叶民懋等为探员,张瑞祥、陈远光、沈光伟、陈瑞彬等为警长。同时,成立警察训练班,冯德兼班主任,以这几个巡官为区队长、教官。第一期招考录取53人,施加半年训练,于翌年5月结业,派充警士,第二期37人于9月毕业,派充警士。并由省第三警察训练所(设在漳州)派来毕业学员多人来漳浦任警士。在各区区署所在地的旧镇、佛昙、石榴坂、官浔各成立警察分驻所,各由一名巡官负责。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城区警察所升格为县警察所。翌年3月,警佐办公室与县警察所合并为县警察局,原警佐兼所长冯德改为局长。局址在南街城隍庙。旧镇、杜浔、佛昙、石榴坂、官浔等区警察分驻所一律升级为区警察所,派任所长。县警察局侦缉组(先后由王振华、李慕韩、杨清滣唇任组长)开级为侦缉队。全县官警增加到一百多人。抗战时期,省保安司令部在县设防空监视哨,由警察局长监督指导。县警察局并曾组织训练义勇警察45名及义勇警察消防队30名,服装由地方筹款制发,武器及器械用警察局拨用,派警长张瑞祥、沈光伟分任队长,事过3年,因队员不可缓服兵役而解散。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时期),针对靖和浦边区及梁山周围共产党游击队,在象牙庄和盘陀设立直属派出所,后撤销,改成立象牙庄派出所。警察配合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对革命根据地的“清剿”,迫使蔡国等叛变革命,向警察局“自新”。警察局令叛徒们带路,袭击中共漳浦县委临时驻地虎空岩。中共漳浦县委委员吴庭坚力战牺牲,县委书记张太西及交通员蔡火弹尽被捕。国民党警察局长冯德因功晋升漳浦县长。蔡国加入警察局侦缉队为探警(后开除,解放后上山为匪被镇压)冯德升任县长后,省派皮励吾(江西萍乡人)来接任警察局长,继续配合第二十师和漳浦县保安队进攻革命根据地。警察和保安队占据原中共漳浦县委驻地下楼村为反共据点,派民工建碉堡,强迫壮丁守望,对村民严厉管制。实行移民并村,强迫小村并入大村,龙潭、后井等自然村被剿到“无社”,溪内村被移民于磁窑村,墓后村和长埔村被移民于下楼村。警察和保安队多次进行搜山,对拒不移民并村的村民肆意胁迫,乘机抢劫、强奸。人民恨之入骨,革命传单骂他们为“下楼警犬”。
在皮励吾之后继位漳浦县警察局长的有:林学占,长乐人。许淑溪,仙游人。吴凌汉,平和人。黄丽川,晋江人。杨崇德,潮州人(旧镇警察所所长,暂代局长一个多月)。张怀三,云霄人。翁化清,本县人,原军事科长,调来暂代。以后,将我从诏安调来接任。
1946年,省政府设立调查室以加强反共活动。各专员公署及各县县政府都设立特种会报秘书室。规定由县长、县政府主任秘书、特种会报秘书、军事科长、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组成“党政特种会报”,每月召开秘密会议一次,对共产党嫌疑分子不必审判定罪,只要“特种会报”会议通过,便可由军事科命令自卫队以“中途脱逃,乱枪击毙”处理。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戡乱建国”政策指导下的一种毒辣作为,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乱枪”之下,其时我在诏安,不知漳浦这种秘密举动详情。1948年7月26、28两天,县城发生反对警察局长张怀三的大风潮。这是由“吃评价”而引起。因为抗日战争期间物价猛涨,县长召集各机关会议,成立物资管制处,分期召集各机关代表集议,对各种重要物资进行“评价”,以图限制物价,但物资既缺,通货又无限度膨胀,“限价”无效,只有由县物资管制处发给公务员、军警以一定数量的“评价”(低于市价十多倍)食油、猪肉凭条,分别由油商和屠宰户购买,油商由油业同业公会分摊各油车(榨花生油的作坊)负担差价,油车将差价损失计入成本;猪肉由屠宰同业公会集议转嫁负担于养猪户,规定每售一头生猪给屠宰户,应扣4市斤不计价,以弥补屠宰户供应“评价”猪肉的损失。抗战胜利后,“评价”停办,而物价猛涨比抗战时更利害,自卫队和警察以“吃评价”为理由,随意向屠宰户以极低的价钱(无标准)强购猪肉,甚至对农民挑入城出售的蔬菜和柴草也要“吃评价”,扰商害民,经地方人士向县长郑有泰反映,要求制止。郑县长召集县参议会、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分团部等首长会议,决定从本县所特有的“米谷出口捐”中拨款补给自卫队和警察副食费,禁止“吃评价”。自卫队大部份派驻海口,自抗战以来,每条渔船“讨海”回来,必交上一条大鱼,已成惯例,抗战胜利后,渔民仍不敢废止那不成文法,所以保安队对在县城禁止“吃评价”比较没有意见。而县城警察不服“禁吃评价”决定,由警察局行政科长林保成带两名警士出面强买“评价”猪肉,谢屠户说“县政府规定,不能再吃评价了”,林保成就诬指谢屠户卖瘟猪肉,谢屠户与之理论,被打倒在地。一时间市场上群众议论纷纷。屠宰公会常务理事陈浯江向县参议会副议长陈则蔡反映情况,要求为民请命。陈则蔡到县政府向郑县长转报,郑县长即与陈同到“县前”市场,当众讲话,表示要惩办肇事警察,劝市场上商贩照常营业。郑县长是广东高要县人,说普通话,由陈则蔡翻译。警察迁怒于陈则蔡,出动多人,到陈家将其强制到市场上,当众向警察道歉。事后,陈到县参议会告诉情况,即由议长杨拔萃以电话集合省参议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地方人士郭祖柴等,一齐到县政府,要求郑县长召警察局长张怀三到县政府讨论此事。警察误以为张怀三到县政府后被软禁,由林保成率一群警察全副武装,包围县政府,将轻机枪对准县政府大门,要挟释放张怀三。郑县长令自卫队在县政府大门架起轻机枪,防止警察冲入。一时剑拔驽张,形势紧张。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抗议警察的不法行径。杨拔萃、陈则蔡、柯汉扬、陈秀夔等各以电话通知与其有关系的乡镇长,调动乡村武装群众三千多人,对包围县政府的警察进行包围,高呼“打倒张怀三、高志道(警察局督察长)、林保成”口号,满城风雨。郑县长打电话报告正在漳州视察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及漳州专员公署。专员公署派保安副司令汤涛到漳浦调查处理。在漳浦县国民党“党、团、参”三巨头强烈要求下,刘主席即下令将漳浦县警察局长张怀三、督察长高志道、行政科长林保成撤职,限日出境,调军事科长翁化清暂代警察局长。不久,调我回漳浦接任局长。
县警察局原设有督察室和行政、司法二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扩大编制,改股为科,增设总务科,由局长兼总务科长。原缉队改为刑事警察队。我于1948年调回漳浦任职后,县警察局的组织已较具有现代警察机关的规模,局本部有督察室(设督察长,相当于幕僚长)、行政科、司法科各有科长、科员。局以下有城区、旧镇、佛昙、杜浔、官浔、石榴坂6个区警察所,各设所长1人。另有事警察队,1949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令县,从原属县政府军事科管理的三个自卫中队中调出一个中队改编为保安警察中队,隶属警察局建制,改编时中队长潘赐福,官兵62名。至此,县警察局有官警130人及保警官兵62人。共192人。此外,警察局长兼负责监督省保安司令部在县政府设立的无线电台,省保安司令部发给密码本及电报纸供警察局长使用。
有一个时期,由于侦缉队只有队长1人,探员2人,探警8人,省令物色本地人组织义务警察,协助搜集情报,协助侦破案件,后来,由于义务警察成份复杂,勾结流氓地痞,包烟(吸毒)、包赌、欺压、勒索之事时有发生,我接任漳浦警察局长后,宣布撤除义务警察。
按警察服装条例,每年可发两套,但因县财政困难,有的年份只发一套。官警每人可配发短枪(驳壳或左轮)一支,但子弹甚少,只得自己补充,有的配带无弹的短枪,有的见习警士未受过训练,无战斗力,佩无弹手枪聊以吓唬老百姓而已。
警察对刑事案件负有侦破责任,但对漳浦一件枪杀要案,本来是容易侦破的,却因为凶手是身居县自卫总队长的军统分子陈思明所指使,不予破案。案发生在1948年8月的一天午夜,地点在三青团漳浦分团部(向姚寿租用的许官巷边大院)后楼,分团干事长陈秀夔的宿舍。起因在陈秀夔与陈思明(两家都是金塘乡敦柄村地主)争夺金塘乡势力范围,陈思明指使其弟陈思聪(时任警察局探警),伙同林铁、陈丙丁于午夜用人站在人肩头的方法,从二层楼窗口开枪刺杀熟睡中的陈秀夔,误毙其妻邵蕙君,而陈秀夔无恙。此案轰动全省,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刘建绪电令漳浦县长郑有泰限期破案,而暂代警察局长翁化清为免予介入这场斗争,不予破案。其时革命游击队日趋活跃,加上国民党内部斗争剧烈,地方动荡,郑县长畏难辞职,省改派卢德明接任漳浦县长,并调我回漳浦任警察局长。
我于1948年11月16日接任警察局长。翁化清在办移交时,特地将在“暗杀陈秀夔案”现场检到的3颗、403型驳壳枪弹壳交给我。我请示卢县长要不要破案,卢县长问我怎样破案,我说:要破案必先逮捕行凶嫌疑犯,缴出那一杆行凶的驳壳枪,我学过验枪科学方法,可以鉴定从现场检到的3颗子弹确是从那杆枪开出来的,再追究那一杆枪是谁提供的,便知道谁是主指者,谁是凶手,便可依法逮捕主使犯魏乃构和陈思明及其弟陈思聪等,但陈思明拥有武力,身边经常跟随警卫,必须出其不意,用闪电式逮捕法,才不致发生火拼。现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地方动荡,为免增加麻烦,此案还是不破为好。卢县长同意我的意见。
我在诏安时,曾奉令配合省保安团及第五区(漳州)保安副司令汤涛召集各县自卫队对乌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其实那时汤涛(后转任云霄县长)及诏安县长钟日兴和我都越来越感到国民党来日不长,对“围剿”抱消极态度,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我回漳浦后不久,任职不上3个月的卢县长因为应付不了革命游击队而被撤职,改派黄清淮来任。省保安团一个团(团长胡季宽)来“清剿”活跃在赤岭、湖西、官浔、佛昙一带的蓝兆熊游击队。这是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在临解放前的一次挣扎。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人员见大势已去,个人何去何从,不能不考虑了。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同时是省参议员、驻会委员,他在省参议会参加议长丁超五的“反征兵征粮运动”后,回到漳浦,我们商量以后,与中共靖和浦边区组织联系,经过准备,于1949年9月时机成熟时起义,漳浦和平解放(详见《漳浦文史资料》第一辑、十辑我的回忆文章及第十三辑《政协委员风采》)。
漳浦的禁烟禁毒
·陈国坚·
鸦片,又叫鸦片烟,漳浦方言叫乌烟。漳浦受鸦片荼毒由来已久,上溯明末清初,时西方列强凭藉船坚炮利,用海盗式的走私行为,把鸦片输入中国,在进行野蛮掠夺的同时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至道光年间,忠贞之士林则徐等疏请禁止鸦片输入,清廷下令执行。英国竟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割地索款,攫取特权,横行霸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华民族的危机。国仇家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而鸦片或以“西药”之名合法输入,或大量走私输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当时人民奋起抵制鸦片斗争中形成的反抗外来侵略的真实写照,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朝政日益腐败,因而吸食鸦片烟之风屡禁不止,乃愈演愈烈。时与作为“五口通商”之一口岸的厦门岛仅一水之隔的漳浦,鸦片输入较早,境内烟馆广设,人们深受鸦片荼毒。当时,流传着这么一首民谣:“鸦片未煮是土,煮了是糊;未吃忠厚,吃了糊涂;妻儿没顾,亲友断路;倚壁穿裤,点灯走路。”愤怒地控诉了鸦片烟的危害,反映了漳浦人民要求禁烟的强烈愿望。然而在封建统治者默许下,更有甚者,还从国外引进罂粟种苗种植,对吸食鸦片烟无疑起推波助澜作用。仅1903年,漳浦鸦片产量达730担,吸烟毒之风日炽。
辛亥革命后,盘踞在闽南的各派军阀为增加军饷来源,无不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不管有种无种均按田亩数计算征收鸦片捐,美其名曰“田亩捐”,仅此一项,从漳浦每年可搜刮55万银元。鸦片苗捐征收方式搞层层承包制,实际征收数额大大超过55万银元。此外,地方政府加征鸦片商品税,即“膏厘”税,及对鸦片烟馆征“封灯”税,借开“绿灯”之机多分一杯羹,生财有道。通过迫种鸦片而能进一步榨取人民的血汗,使各派军阀格外眼红,不惜大打出手,也使地方豪门权贵,为争夺包捐权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给漳浦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漳浦农民为了反抗军阀迫种鸦片,曾多次举行反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1924年秋,以反抗鸦片烟捐为导火线而组织的“乡约”民军,就被北洋军阀杀千余人,群众因牵连受害达2万余家,300多个村庄遭焚毁。1928年间,共产党人在漳浦开展农民运动时,也曾因反抗国民党新军阀迫种罂粟,强征烟苗捐而遭血腥镇压,罂粟花瓣上同样沾满了漳浦人民的鲜血。迫于群众舆论,国民党漳浦县政府不得不成立“禁烟局”,但却是借禁烟之名仍行收鸦片烟捐之实。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才装模作样下令禁烟禁毒。8月21日,漳浦县成立“禁烟委员会”,下设禁烟科,并设立“戒烟医院”,对烟民进行登记并强制入院戒烟,不久机构便撤销了。查禁鸦片任务由警察局承担,适逢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连抗日都无暇顾及,禁烟禁毒更是鞭长莫及,贩烟毒商人便极尽贿赂之能事,警察也乐于敷衍了事。以1939年为例,警察仅查获烟民255人,缴烟土26.6两,烟膏74.03两,烟具64件。可是在翌年3月一次突击搜查中,则发现经登记未戒烟民就有824人(含妇女7人),烟土月总吸量计344.9两,两年数目对比之悬殊令人惊讶。国民党漳浦县政府不得不于1941年间按律对39名贩、吸毒犯判处有期徒刑,以儆效尤,且规定每年6月3日为禁烟节。但官场腐败、丰厚的利润使权势者染指有加,贩毒者铤而走险,因而民国政府禁烟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彻底禁烟禁毒成为人民梦寐以求的迫切愿望。
1950年2月24日,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把禁烟禁毒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福建省人民政府于7月3日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并于当月27日下发《福建省禁烟禁毒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命令各市县组织实施。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执行,在紧张的剿匪、镇反等斗争开展同时,专门部署禁烟禁毒任务,切实加强公安机关禁烟禁毒力度。派遣精干公安干警深入城关、旧镇、赤湖、佛昙、官浔、杜浔等6个集镇调查摸底,查获鸦片烟大贩81人,小烟贩67人,开设烟馆46人,吸食鸦片烟毒者290人。根据所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破获烟毒案110起,缴获鸦片烟土2300市两,并对185名鸦片烟贩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遣送原籍、罚款和教育释放等,同时,彻底铲除二区长兴村16户农民所种3亩地罂粟,初战告捷,显示了人民政府彻底禁烟禁毒的决心。由于正值匪患猖厥,未能达到彻底根除。
随着剿匪、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社会治安同时明显好转和趋于稳定,彻底禁烟禁毒时机已经成熟,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调集精兵良将,以公安、民政部门人员为骨干,抽调宣传、财政、卫生、妇联等部门28名干部配合,组成一支禁烟禁毒专门力量。为了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1952年7月6日,成立“漳浦县禁烟禁毒指挥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德珍任指挥,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陈启祥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并组成逮捕审讯组、武装集训组,其时,各区均相应成立禁烟禁毒领导机构。
机构建立后,首先集中参战人员反复学习《通令》和《暂行条例》等有关指示,领会其精神,崔德珍同志还作了动员报告,并宣布参加此次行动必须遵守的7条纪律,陈启祥同志则部署具体行动方案。8月12日,龙溪专署公安处马振兴副处长专程到漳浦传达省公安厅有关禁烟禁毒的方针政策和应着重打击的13种类型的对象,即打击重点是制毒者;大量或集体贩运组织者、主谋者;武装押运者等。使参战人员进一步提高对这场斗争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任务、掌握政策,以便在运动中能有法可依,做到依法办案、执法必严,更好地深入开展这一斗争。
漳浦禁烟禁毒斗争在上级正确领导下,紧紧地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有步骤、分阶段进行。首先,大张旗鼓地把党有关禁烟禁毒的方针、政策及这场斗争的意义向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和威慑力量,其次,有针对性地召开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调动各方面人士参与这场斗争的积极性,全县共召开有关会议83次,与会人数达2万多人。再次认真做好教育贩、吸烟毒者家属工作,动员他们规劝贩、吸烟毒的亲人能迷途知返,改革恶习,并能检举揭发同伙,争取从宽处理。此外,把浮在面上的贩、吸烟毒犯集中教育,这样,做到宣传与教育、检举与调查、公开与秘密、集训与登记、逮捕与审讯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多管齐下,基本摸清全县12个区中隐藏较深的贩、吸烟毒状况。
第二阶段,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肃毒方针、政策,稳准狠打击应打击对象,坚持注重证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把群众检举揭发的材料与调查摸底的材料反复核对,对新发现的线索进一步深挖,千方百计获取罪证。该阶段共查出经数次打击后,全县尚有烟毒大贩99人;烟毒小贩133人;开设烟馆116人;吸食烟毒者841人,合计贩、吸烟毒犯1189人。
第三阶段,将贩、吸烟毒犯一网打尽并绳之以法。为了达到彻底铲除贩、吸烟毒社会丑恶现象,采取打击与教育相结合的做法,既坚决打击那些占少数人的罪大恶极的烟毒大贩,又彻底改造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社会的烟毒小贩,同时教育和挽救一大批犯有轻微违法犯罪的贩、吸烟毒犯,及真正形成群众自觉抵制吸烟毒的局面,因而把对每个打击对象的处理,量刑的轻重公诸于众,组织群众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根据每个贩、吸烟毒犯的罪恶程度,参照政务院《通令》和省《暂行条例》及群众意见,作出裁决,并完善法律手续,呈报上级审核批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了扩大教育面,在城关、旧镇先后召开公判大会,宽严处理大会4场,共判处贩、吸烟毒犯极刑×人、有期徒刑××人、罚款××人;经教育释放××人;已登记不予处分×××人。被判处极刑贩烟毒犯中,有旧镇镇西示村×××,该犯在解放前后数年间,贩运烟毒62次,累计达9092市两,实属罪恶满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省府批准,于1952年11月19日在旧镇执行枪决,对贩、吸烟毒犯的判决,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威慑声势。
漳浦禁烟禁毒斗争实际进行2个多月已基本结束,禁烟禁毒成效显著,在漳浦大地上,蔓延百余年屡禁不止的贩、吸烟恶习被强有力遏制,并最终被彻底根除;屡见不鲜的因吸烟毒酿成的家庭悲剧已不再重演。禁烟禁毒,深得人心,群众莫不拍手称快,赞颂共产党、人民政府英明领导,有办法、有能力为民除大害、革陋习、办实事、办好事,同时也不愧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漳浦烟毒绝迹的同时,世界上的毒品已发展为多种多样。至90年代,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又有漳浦人涉案烟毒的制造与运销。1993年,有台湾不法分子,以生产清洁剂为名,在霞潭村秘密制造冰毒(安非他命),公安机关察觉这个非法工厂的秘密,经调查布控,于5月8日破获,以案情重大,移送上级处理。
·李松辉·
漳浦有警察始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5年)镇压白扇会起义之后。(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本来镇压“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开始悔悟到必须“维新”,在西安行在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宣布“维新”。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巡警部。光绪三十二年漳浦发生白扇会起义,烧毁县城英国基督教堂,捣毁甘林法国天主教堂,镇压白扇会起义后,漳浦按照“各省官制通则”改革政制,改原来负责缉捕、监狱事务的典史满人达明亚为警务长,改原来“捕快”十多名为巡警)。知县卢元璋奉令向“有匪各乡”(有人参加白扇会起义的乡村)派款赔偿英法教会(协议赔银四万六千四百元,摊派至六万四千元),派县丞朱映青为总办,警务长达明亚为助办。催收这次赔款是漳浦有史以来第一批警察的首次任务,催征孔急,曾开枪击毙梅林秀才陈实卿之母。
辛亥革命后,福建省设警察厅。北洋阀统治时期,漳浦重要集镇曾设警察所,所长由县知事卖放,警察由所长招收流氓充任,人数很少。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漳浦县设立公安局,局长杨子保。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受破坏,县公安局撤销,成立“剿共保安大队”,翁必达(猪母)任大队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成立公安局,设于麦市街烈女祠,林化龙任局长,警察三十多人,身着黑色制服,手执警棍,在街上巡逻。不久撤销。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开始设警察,在省保安处设警务科,县政府设警佐,在各区区署指定一个区员兼巡官,负责警察工作。省设警官训练所,开始训练第一批警察骨于。全省各县分二期设立警察,漳浦为第一期建警县份,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开始设警察机构。
福建初建警时是将原来各县的民政、区政人员调到省警察训练所施加训练后派为警官任用,然后由这些警官在县里成立警察训练班,招收高小毕业以上学历者加以训练,派充警士。后来才由省警官训练所招收高中毕业以上学历者入所训练,毕业后派充警官。我是原来已经在省公务人员训练所毕业派任区员,调到省警官训练所受训后再派回区署当区员兼巡官的福建省第一批警官。后来区成立警察所,脱离区署,独立行使警察职权。由于当时公务员必须回避原籍,我自任巡官至升级任县警察局长,都在云霄、南靖、长泰、诏安等邻县工作,抗战胜利后不再执行回避原籍的规定,才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从诏安调回漳浦任警察局长。但在漳浦任警官的多数是我在警官训练所时的同学,只有少数是中央警校毕业生,所以我对漳浦县的警察工作知之甚详,这里从漳浦1937年开始设警察至1949年9月解放的漳浦警察情况作一个概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省派闽候人张昭鼐来任漳浦县政府警佐,从属于民政科。10月,警察工作从民政科分离出来,成立警佐办公室,省先派张昭鼐来任警佐一个月,后改派冯德(四川人)来任,下设科员、办事员各一人,初由民政科调任,后由省派警官训练所毕业学员充任。年末,成立城区警察所(址在西街李家祠),由警佐冯德兼所长,省派林纯如为督察员,程瑛、黄瑞文、江子民、张怀三、丘大波为巡官,王振华为侦缉组长,叶民懋等为探员,张瑞祥、陈远光、沈光伟、陈瑞彬等为警长。同时,成立警察训练班,冯德兼班主任,以这几个巡官为区队长、教官。第一期招考录取53人,施加半年训练,于翌年5月结业,派充警士,第二期37人于9月毕业,派充警士。并由省第三警察训练所(设在漳州)派来毕业学员多人来漳浦任警士。在各区区署所在地的旧镇、佛昙、石榴坂、官浔各成立警察分驻所,各由一名巡官负责。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城区警察所升格为县警察所。翌年3月,警佐办公室与县警察所合并为县警察局,原警佐兼所长冯德改为局长。局址在南街城隍庙。旧镇、杜浔、佛昙、石榴坂、官浔等区警察分驻所一律升级为区警察所,派任所长。县警察局侦缉组(先后由王振华、李慕韩、杨清滣唇任组长)开级为侦缉队。全县官警增加到一百多人。抗战时期,省保安司令部在县设防空监视哨,由警察局长监督指导。县警察局并曾组织训练义勇警察45名及义勇警察消防队30名,服装由地方筹款制发,武器及器械用警察局拨用,派警长张瑞祥、沈光伟分任队长,事过3年,因队员不可缓服兵役而解散。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时期),针对靖和浦边区及梁山周围共产党游击队,在象牙庄和盘陀设立直属派出所,后撤销,改成立象牙庄派出所。警察配合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对革命根据地的“清剿”,迫使蔡国等叛变革命,向警察局“自新”。警察局令叛徒们带路,袭击中共漳浦县委临时驻地虎空岩。中共漳浦县委委员吴庭坚力战牺牲,县委书记张太西及交通员蔡火弹尽被捕。国民党警察局长冯德因功晋升漳浦县长。蔡国加入警察局侦缉队为探警(后开除,解放后上山为匪被镇压)冯德升任县长后,省派皮励吾(江西萍乡人)来接任警察局长,继续配合第二十师和漳浦县保安队进攻革命根据地。警察和保安队占据原中共漳浦县委驻地下楼村为反共据点,派民工建碉堡,强迫壮丁守望,对村民严厉管制。实行移民并村,强迫小村并入大村,龙潭、后井等自然村被剿到“无社”,溪内村被移民于磁窑村,墓后村和长埔村被移民于下楼村。警察和保安队多次进行搜山,对拒不移民并村的村民肆意胁迫,乘机抢劫、强奸。人民恨之入骨,革命传单骂他们为“下楼警犬”。
在皮励吾之后继位漳浦县警察局长的有:林学占,长乐人。许淑溪,仙游人。吴凌汉,平和人。黄丽川,晋江人。杨崇德,潮州人(旧镇警察所所长,暂代局长一个多月)。张怀三,云霄人。翁化清,本县人,原军事科长,调来暂代。以后,将我从诏安调来接任。
1946年,省政府设立调查室以加强反共活动。各专员公署及各县县政府都设立特种会报秘书室。规定由县长、县政府主任秘书、特种会报秘书、军事科长、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组成“党政特种会报”,每月召开秘密会议一次,对共产党嫌疑分子不必审判定罪,只要“特种会报”会议通过,便可由军事科命令自卫队以“中途脱逃,乱枪击毙”处理。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戡乱建国”政策指导下的一种毒辣作为,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乱枪”之下,其时我在诏安,不知漳浦这种秘密举动详情。1948年7月26、28两天,县城发生反对警察局长张怀三的大风潮。这是由“吃评价”而引起。因为抗日战争期间物价猛涨,县长召集各机关会议,成立物资管制处,分期召集各机关代表集议,对各种重要物资进行“评价”,以图限制物价,但物资既缺,通货又无限度膨胀,“限价”无效,只有由县物资管制处发给公务员、军警以一定数量的“评价”(低于市价十多倍)食油、猪肉凭条,分别由油商和屠宰户购买,油商由油业同业公会分摊各油车(榨花生油的作坊)负担差价,油车将差价损失计入成本;猪肉由屠宰同业公会集议转嫁负担于养猪户,规定每售一头生猪给屠宰户,应扣4市斤不计价,以弥补屠宰户供应“评价”猪肉的损失。抗战胜利后,“评价”停办,而物价猛涨比抗战时更利害,自卫队和警察以“吃评价”为理由,随意向屠宰户以极低的价钱(无标准)强购猪肉,甚至对农民挑入城出售的蔬菜和柴草也要“吃评价”,扰商害民,经地方人士向县长郑有泰反映,要求制止。郑县长召集县参议会、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分团部等首长会议,决定从本县所特有的“米谷出口捐”中拨款补给自卫队和警察副食费,禁止“吃评价”。自卫队大部份派驻海口,自抗战以来,每条渔船“讨海”回来,必交上一条大鱼,已成惯例,抗战胜利后,渔民仍不敢废止那不成文法,所以保安队对在县城禁止“吃评价”比较没有意见。而县城警察不服“禁吃评价”决定,由警察局行政科长林保成带两名警士出面强买“评价”猪肉,谢屠户说“县政府规定,不能再吃评价了”,林保成就诬指谢屠户卖瘟猪肉,谢屠户与之理论,被打倒在地。一时间市场上群众议论纷纷。屠宰公会常务理事陈浯江向县参议会副议长陈则蔡反映情况,要求为民请命。陈则蔡到县政府向郑县长转报,郑县长即与陈同到“县前”市场,当众讲话,表示要惩办肇事警察,劝市场上商贩照常营业。郑县长是广东高要县人,说普通话,由陈则蔡翻译。警察迁怒于陈则蔡,出动多人,到陈家将其强制到市场上,当众向警察道歉。事后,陈到县参议会告诉情况,即由议长杨拔萃以电话集合省参议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地方人士郭祖柴等,一齐到县政府,要求郑县长召警察局长张怀三到县政府讨论此事。警察误以为张怀三到县政府后被软禁,由林保成率一群警察全副武装,包围县政府,将轻机枪对准县政府大门,要挟释放张怀三。郑县长令自卫队在县政府大门架起轻机枪,防止警察冲入。一时剑拔驽张,形势紧张。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抗议警察的不法行径。杨拔萃、陈则蔡、柯汉扬、陈秀夔等各以电话通知与其有关系的乡镇长,调动乡村武装群众三千多人,对包围县政府的警察进行包围,高呼“打倒张怀三、高志道(警察局督察长)、林保成”口号,满城风雨。郑县长打电话报告正在漳州视察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及漳州专员公署。专员公署派保安副司令汤涛到漳浦调查处理。在漳浦县国民党“党、团、参”三巨头强烈要求下,刘主席即下令将漳浦县警察局长张怀三、督察长高志道、行政科长林保成撤职,限日出境,调军事科长翁化清暂代警察局长。不久,调我回漳浦接任局长。
县警察局原设有督察室和行政、司法二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扩大编制,改股为科,增设总务科,由局长兼总务科长。原缉队改为刑事警察队。我于1948年调回漳浦任职后,县警察局的组织已较具有现代警察机关的规模,局本部有督察室(设督察长,相当于幕僚长)、行政科、司法科各有科长、科员。局以下有城区、旧镇、佛昙、杜浔、官浔、石榴坂6个区警察所,各设所长1人。另有事警察队,1949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令县,从原属县政府军事科管理的三个自卫中队中调出一个中队改编为保安警察中队,隶属警察局建制,改编时中队长潘赐福,官兵62名。至此,县警察局有官警130人及保警官兵62人。共192人。此外,警察局长兼负责监督省保安司令部在县政府设立的无线电台,省保安司令部发给密码本及电报纸供警察局长使用。
有一个时期,由于侦缉队只有队长1人,探员2人,探警8人,省令物色本地人组织义务警察,协助搜集情报,协助侦破案件,后来,由于义务警察成份复杂,勾结流氓地痞,包烟(吸毒)、包赌、欺压、勒索之事时有发生,我接任漳浦警察局长后,宣布撤除义务警察。
按警察服装条例,每年可发两套,但因县财政困难,有的年份只发一套。官警每人可配发短枪(驳壳或左轮)一支,但子弹甚少,只得自己补充,有的配带无弹的短枪,有的见习警士未受过训练,无战斗力,佩无弹手枪聊以吓唬老百姓而已。
警察对刑事案件负有侦破责任,但对漳浦一件枪杀要案,本来是容易侦破的,却因为凶手是身居县自卫总队长的军统分子陈思明所指使,不予破案。案发生在1948年8月的一天午夜,地点在三青团漳浦分团部(向姚寿租用的许官巷边大院)后楼,分团干事长陈秀夔的宿舍。起因在陈秀夔与陈思明(两家都是金塘乡敦柄村地主)争夺金塘乡势力范围,陈思明指使其弟陈思聪(时任警察局探警),伙同林铁、陈丙丁于午夜用人站在人肩头的方法,从二层楼窗口开枪刺杀熟睡中的陈秀夔,误毙其妻邵蕙君,而陈秀夔无恙。此案轰动全省,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刘建绪电令漳浦县长郑有泰限期破案,而暂代警察局长翁化清为免予介入这场斗争,不予破案。其时革命游击队日趋活跃,加上国民党内部斗争剧烈,地方动荡,郑县长畏难辞职,省改派卢德明接任漳浦县长,并调我回漳浦任警察局长。
我于1948年11月16日接任警察局长。翁化清在办移交时,特地将在“暗杀陈秀夔案”现场检到的3颗、403型驳壳枪弹壳交给我。我请示卢县长要不要破案,卢县长问我怎样破案,我说:要破案必先逮捕行凶嫌疑犯,缴出那一杆行凶的驳壳枪,我学过验枪科学方法,可以鉴定从现场检到的3颗子弹确是从那杆枪开出来的,再追究那一杆枪是谁提供的,便知道谁是主指者,谁是凶手,便可依法逮捕主使犯魏乃构和陈思明及其弟陈思聪等,但陈思明拥有武力,身边经常跟随警卫,必须出其不意,用闪电式逮捕法,才不致发生火拼。现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地方动荡,为免增加麻烦,此案还是不破为好。卢县长同意我的意见。
我在诏安时,曾奉令配合省保安团及第五区(漳州)保安副司令汤涛召集各县自卫队对乌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其实那时汤涛(后转任云霄县长)及诏安县长钟日兴和我都越来越感到国民党来日不长,对“围剿”抱消极态度,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我回漳浦后不久,任职不上3个月的卢县长因为应付不了革命游击队而被撤职,改派黄清淮来任。省保安团一个团(团长胡季宽)来“清剿”活跃在赤岭、湖西、官浔、佛昙一带的蓝兆熊游击队。这是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在临解放前的一次挣扎。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人员见大势已去,个人何去何从,不能不考虑了。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同时是省参议员、驻会委员,他在省参议会参加议长丁超五的“反征兵征粮运动”后,回到漳浦,我们商量以后,与中共靖和浦边区组织联系,经过准备,于1949年9月时机成熟时起义,漳浦和平解放(详见《漳浦文史资料》第一辑、十辑我的回忆文章及第十三辑《政协委员风采》)。
漳浦的禁烟禁毒
·陈国坚·
鸦片,又叫鸦片烟,漳浦方言叫乌烟。漳浦受鸦片荼毒由来已久,上溯明末清初,时西方列强凭藉船坚炮利,用海盗式的走私行为,把鸦片输入中国,在进行野蛮掠夺的同时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至道光年间,忠贞之士林则徐等疏请禁止鸦片输入,清廷下令执行。英国竟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割地索款,攫取特权,横行霸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华民族的危机。国仇家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而鸦片或以“西药”之名合法输入,或大量走私输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当时人民奋起抵制鸦片斗争中形成的反抗外来侵略的真实写照,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朝政日益腐败,因而吸食鸦片烟之风屡禁不止,乃愈演愈烈。时与作为“五口通商”之一口岸的厦门岛仅一水之隔的漳浦,鸦片输入较早,境内烟馆广设,人们深受鸦片荼毒。当时,流传着这么一首民谣:“鸦片未煮是土,煮了是糊;未吃忠厚,吃了糊涂;妻儿没顾,亲友断路;倚壁穿裤,点灯走路。”愤怒地控诉了鸦片烟的危害,反映了漳浦人民要求禁烟的强烈愿望。然而在封建统治者默许下,更有甚者,还从国外引进罂粟种苗种植,对吸食鸦片烟无疑起推波助澜作用。仅1903年,漳浦鸦片产量达730担,吸烟毒之风日炽。
辛亥革命后,盘踞在闽南的各派军阀为增加军饷来源,无不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不管有种无种均按田亩数计算征收鸦片捐,美其名曰“田亩捐”,仅此一项,从漳浦每年可搜刮55万银元。鸦片苗捐征收方式搞层层承包制,实际征收数额大大超过55万银元。此外,地方政府加征鸦片商品税,即“膏厘”税,及对鸦片烟馆征“封灯”税,借开“绿灯”之机多分一杯羹,生财有道。通过迫种鸦片而能进一步榨取人民的血汗,使各派军阀格外眼红,不惜大打出手,也使地方豪门权贵,为争夺包捐权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给漳浦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漳浦农民为了反抗军阀迫种鸦片,曾多次举行反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1924年秋,以反抗鸦片烟捐为导火线而组织的“乡约”民军,就被北洋军阀杀千余人,群众因牵连受害达2万余家,300多个村庄遭焚毁。1928年间,共产党人在漳浦开展农民运动时,也曾因反抗国民党新军阀迫种罂粟,强征烟苗捐而遭血腥镇压,罂粟花瓣上同样沾满了漳浦人民的鲜血。迫于群众舆论,国民党漳浦县政府不得不成立“禁烟局”,但却是借禁烟之名仍行收鸦片烟捐之实。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才装模作样下令禁烟禁毒。8月21日,漳浦县成立“禁烟委员会”,下设禁烟科,并设立“戒烟医院”,对烟民进行登记并强制入院戒烟,不久机构便撤销了。查禁鸦片任务由警察局承担,适逢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连抗日都无暇顾及,禁烟禁毒更是鞭长莫及,贩烟毒商人便极尽贿赂之能事,警察也乐于敷衍了事。以1939年为例,警察仅查获烟民255人,缴烟土26.6两,烟膏74.03两,烟具64件。可是在翌年3月一次突击搜查中,则发现经登记未戒烟民就有824人(含妇女7人),烟土月总吸量计344.9两,两年数目对比之悬殊令人惊讶。国民党漳浦县政府不得不于1941年间按律对39名贩、吸毒犯判处有期徒刑,以儆效尤,且规定每年6月3日为禁烟节。但官场腐败、丰厚的利润使权势者染指有加,贩毒者铤而走险,因而民国政府禁烟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彻底禁烟禁毒成为人民梦寐以求的迫切愿望。
1950年2月24日,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把禁烟禁毒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福建省人民政府于7月3日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并于当月27日下发《福建省禁烟禁毒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命令各市县组织实施。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执行,在紧张的剿匪、镇反等斗争开展同时,专门部署禁烟禁毒任务,切实加强公安机关禁烟禁毒力度。派遣精干公安干警深入城关、旧镇、赤湖、佛昙、官浔、杜浔等6个集镇调查摸底,查获鸦片烟大贩81人,小烟贩67人,开设烟馆46人,吸食鸦片烟毒者290人。根据所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破获烟毒案110起,缴获鸦片烟土2300市两,并对185名鸦片烟贩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遣送原籍、罚款和教育释放等,同时,彻底铲除二区长兴村16户农民所种3亩地罂粟,初战告捷,显示了人民政府彻底禁烟禁毒的决心。由于正值匪患猖厥,未能达到彻底根除。
随着剿匪、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社会治安同时明显好转和趋于稳定,彻底禁烟禁毒时机已经成熟,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调集精兵良将,以公安、民政部门人员为骨干,抽调宣传、财政、卫生、妇联等部门28名干部配合,组成一支禁烟禁毒专门力量。为了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1952年7月6日,成立“漳浦县禁烟禁毒指挥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德珍任指挥,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陈启祥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并组成逮捕审讯组、武装集训组,其时,各区均相应成立禁烟禁毒领导机构。
机构建立后,首先集中参战人员反复学习《通令》和《暂行条例》等有关指示,领会其精神,崔德珍同志还作了动员报告,并宣布参加此次行动必须遵守的7条纪律,陈启祥同志则部署具体行动方案。8月12日,龙溪专署公安处马振兴副处长专程到漳浦传达省公安厅有关禁烟禁毒的方针政策和应着重打击的13种类型的对象,即打击重点是制毒者;大量或集体贩运组织者、主谋者;武装押运者等。使参战人员进一步提高对这场斗争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任务、掌握政策,以便在运动中能有法可依,做到依法办案、执法必严,更好地深入开展这一斗争。
漳浦禁烟禁毒斗争在上级正确领导下,紧紧地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有步骤、分阶段进行。首先,大张旗鼓地把党有关禁烟禁毒的方针、政策及这场斗争的意义向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和威慑力量,其次,有针对性地召开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调动各方面人士参与这场斗争的积极性,全县共召开有关会议83次,与会人数达2万多人。再次认真做好教育贩、吸烟毒者家属工作,动员他们规劝贩、吸烟毒的亲人能迷途知返,改革恶习,并能检举揭发同伙,争取从宽处理。此外,把浮在面上的贩、吸烟毒犯集中教育,这样,做到宣传与教育、检举与调查、公开与秘密、集训与登记、逮捕与审讯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多管齐下,基本摸清全县12个区中隐藏较深的贩、吸烟毒状况。
第二阶段,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肃毒方针、政策,稳准狠打击应打击对象,坚持注重证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把群众检举揭发的材料与调查摸底的材料反复核对,对新发现的线索进一步深挖,千方百计获取罪证。该阶段共查出经数次打击后,全县尚有烟毒大贩99人;烟毒小贩133人;开设烟馆116人;吸食烟毒者841人,合计贩、吸烟毒犯1189人。
第三阶段,将贩、吸烟毒犯一网打尽并绳之以法。为了达到彻底铲除贩、吸烟毒社会丑恶现象,采取打击与教育相结合的做法,既坚决打击那些占少数人的罪大恶极的烟毒大贩,又彻底改造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社会的烟毒小贩,同时教育和挽救一大批犯有轻微违法犯罪的贩、吸烟毒犯,及真正形成群众自觉抵制吸烟毒的局面,因而把对每个打击对象的处理,量刑的轻重公诸于众,组织群众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根据每个贩、吸烟毒犯的罪恶程度,参照政务院《通令》和省《暂行条例》及群众意见,作出裁决,并完善法律手续,呈报上级审核批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了扩大教育面,在城关、旧镇先后召开公判大会,宽严处理大会4场,共判处贩、吸烟毒犯极刑×人、有期徒刑××人、罚款××人;经教育释放××人;已登记不予处分×××人。被判处极刑贩烟毒犯中,有旧镇镇西示村×××,该犯在解放前后数年间,贩运烟毒62次,累计达9092市两,实属罪恶满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省府批准,于1952年11月19日在旧镇执行枪决,对贩、吸烟毒犯的判决,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威慑声势。
漳浦禁烟禁毒斗争实际进行2个多月已基本结束,禁烟禁毒成效显著,在漳浦大地上,蔓延百余年屡禁不止的贩、吸烟恶习被强有力遏制,并最终被彻底根除;屡见不鲜的因吸烟毒酿成的家庭悲剧已不再重演。禁烟禁毒,深得人心,群众莫不拍手称快,赞颂共产党、人民政府英明领导,有办法、有能力为民除大害、革陋习、办实事、办好事,同时也不愧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漳浦烟毒绝迹的同时,世界上的毒品已发展为多种多样。至90年代,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又有漳浦人涉案烟毒的制造与运销。1993年,有台湾不法分子,以生产清洁剂为名,在霞潭村秘密制造冰毒(安非他命),公安机关察觉这个非法工厂的秘密,经调查布控,于5月8日破获,以案情重大,移送上级处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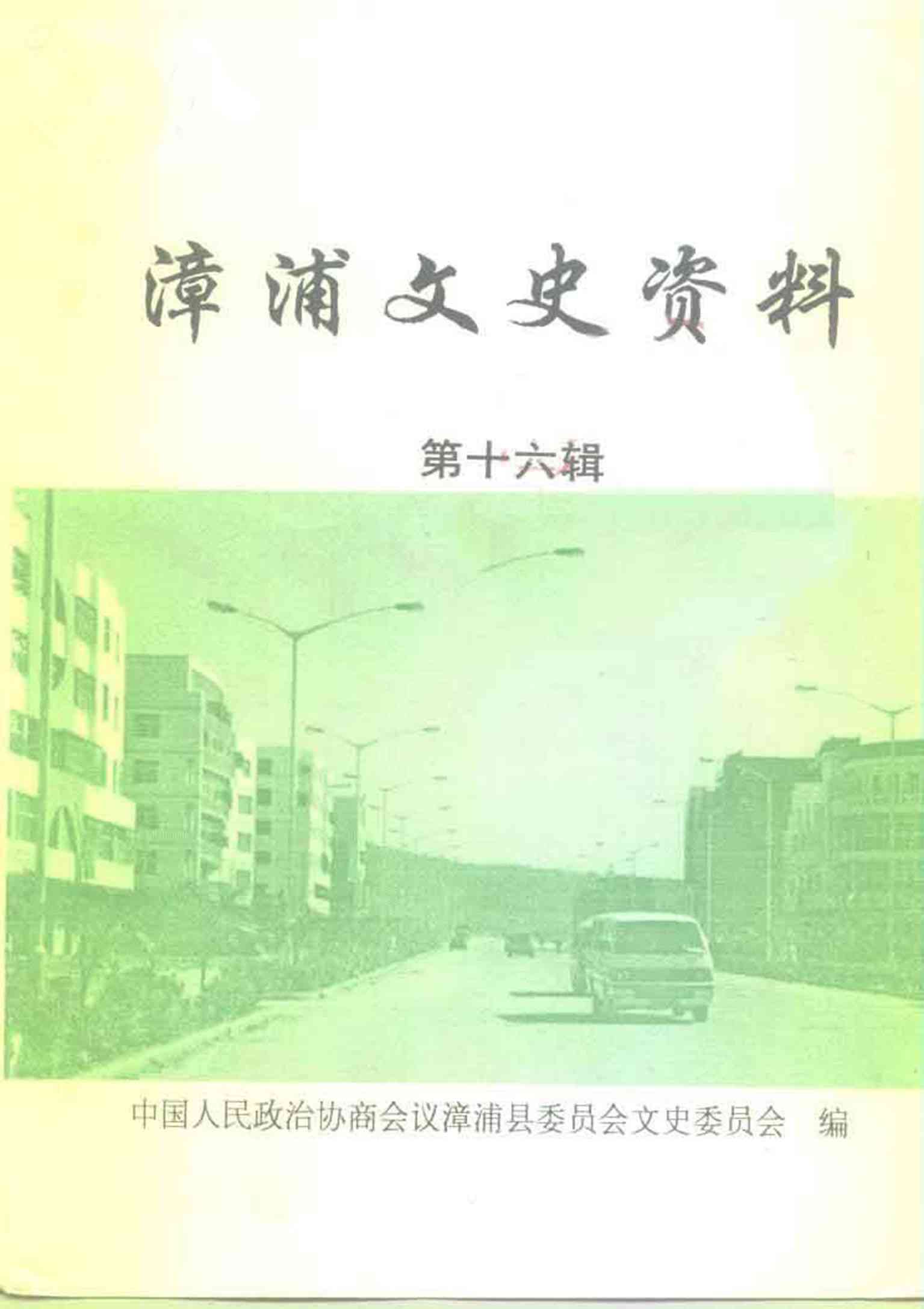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