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华安仙都的蓄奴
| 内容出处: | 《华安文史资料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029 |
| 颗粒名称: | 昔日华安仙都的蓄奴 |
| 分类号: | K825 |
| 页数: | 31 |
| 页码: | 1-31 |
| 摘要: |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收集,研究了华安县仙都公社在解放前奴隶制的残余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蓄奴的起源及客户的社会地位、仙都客户的劳役负担、仙都客户与主家的经济关系、仙都客户的人口与婚姻情况以及仙都客户是奴仆而不是佃仆等问题都被探讨。 |
| 关键词: | 华安县 蓄奴 |
内容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奴隶制残余问题,早已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由于有关资料的不足,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只限于徽州等少数地区,而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为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奴隶制残余诸问题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于一九八二年底两次到华安县仙都公社,实地调查解放前仙都明清时期奴隶制的残余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蓄奴的起源及客户的社会地位
华安县现属福建省龙溪地区行政公署。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以前华安县境分隶漳州府的龙溪县,泉州府的安溪县以及龙岩州的漳平县。民国十七年,由龙溪、安溪、漳平三县分划若干保,正式署县。县境之内山峦环绕,地形起伏,田土贫瘠,人口稀少,建县之时,全县人口仅五万一百余人。
华安县虽然县小人稀,但封建宗族势力却相当稳固,氏族制的残余在解放前之华安处处可见,大部份村落是“聚族而居,同姓相亲”,并且严厉排斥外姓来村居住。据《民国华安县志草稿》氏族志记载,解放前华安县境共有姓氏五十种左右,其中有百分八十以上是聚族而居,自成村落,血缘关系相当牢固。
仙都公社于解放前夕称仙都区、仙都保、宜昭保、义昭乡,位于华安县之东北角,与安溪县相邻,人口约一万人左右。仙都区有一圩场,为邻近数十里各村落及安溪县一部份村落的集市贸易场所。临近仙都圩有云山、下林、招山、中圳、市后、先锋、大地及良村等主要村落,仙都区内各主要大姓皆聚居于以上这些村落(现皆为生产大队)。招山、先锋、中圳、市后为苏林两姓聚居地,解放前约有人口三千余人,大地为刘、蒋二大姓聚居地,刘、蒋两姓各有人口一千人左右,云山为汤姓聚居地,人口约一千人,良村为黄姓聚居地,人口有二千人。这些大姓大多是于明代前中期,由龙岩、漳州等地迁移而来,至今延衍数十代,人口多达数千众。
仙都各大姓都有相当严格的家族组织,每一大姓均设有始祖祠堂,始祖祠堂之下又分设支派祠堂,支派祠堂之下又有大小各房祠堂,每当春、秋二季祭祖之时,各大姓数千名族众依次进行祭祀拜祖,各房子孙,子房祠堂之内拜房祖,各支派子孙又得聚集于支派祠堂拜支祖,闔姓大小还得团聚于始祖总祠堂内,拜祀始祖,缅怀祖先开基之德。同时各大姓还往往闔族公立庙宇,供奉同姓神祗,族内不分老幼,均要虔诚礼拜以求同姓神祗的保祐。
宗族组织的严密与祭祀系统的完备,必然伴随着大量族田的出现。仙都诸大姓的情形正是如此,这些大姓不仅置有供祭祀费用的祭田,同时还有义田,学田等等。这种族田,许多大姓都多达数百亩以上,如良村的黄氏族田,除分布于良村之外,几乎遍及仙都乡,远达四十余里的大地村,亦有许多黄姓的墓田、祠田。
大量族田的购置,以及每年繁多的祭祖形式,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以供役使。于是,仙都一带的各个大姓族内,大都保留着蓄奴的习惯,即所谓“聚族成村到处同,奴婢使役序整然”,解放前当过良村黄姓奴仆的廖三祠回忆,清代末年,良村黄姓所蓄之奴婢,单廖姓一支,竟多达三百余人,其他各姓于清朝末年亦都蓄有奴仆数十人以至数百人不等。
仙都蓄奴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代前中期,根据我们的调查,仙都的林、黄、刘、蒋、汤五大姓的奴仆,有叶、杨、林、刘、罗、乐、丘、李等姓,这些沦为奴仆的姓氏祖宗迁入仙都,都有十至二十代之久,现将仙都诸大姓及其所属之奴仆姓氏迁入仙都之代数。
由此可见,当明代中期林、黄诸大姓迁至仙都不久,蓄奴现象己经出现。
叶、杨诸姓之所以沦为奴仆,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二种:
一、大姓强迫小姓为奴仆,华安仙都一带,地处漳泉二府以及龙岩州交界之处,山陵起伏,交通闭塞,因此于明代以前人口非常稀少。仙都现有之各姓,不论是主姓还是奴姓均于明代之后,陆续迁入定居。林、黄诸姓族大势众,而叶、杨等姓户小丁薄。小姓迁入之后,根本无力与大姓抗衡相争,于是,原来没有任何相属关系的各姓族,这时的阶级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大姓夺占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山林,俨然以主人自居,而诸小姓被迫为大姓的奴役,沦为大姓的奴仆。显然,这种主奴隶属关系,带有严重的村社氏族制度,强大氏族奴役弱小氏族的性质,如仙都林氏属下的叶、杨等姓就是在这种情况沦为奴仆的。
二、投靠。因荒年暴岁,外地小姓流落至仙都,此地大姓势大族众,田地、山场均归大姓所有,新迁来的外地小姓,无立身之地,为了生计,只得投靠某一大姓,为其奴仆,求其庇护。如良村廖姓,原为龙岩、宁洋两县居民,明时迁入仙都后,即依附于良村大姓黄族为奴,据廖三词等说,其祖先迁入仙都认良村黄姓为主人时,双方曾有口头之誓约,即廖姓起愿誓世世代代拜黄为主,永受役使不敢有怠,如有变更初衷愿受主家任意惩处,并得天谴亡子绝孙。而黄姓则让廖姓永佃黄姓族田作为交换条件,并提供廖姓居住的房屋和死后的葬地,同时还可以为廖姓提供某些庇护,以免遭受其他大姓的欺凌等等。
由于仙都各大姓的奴仆均为从外地迁来的小姓,因此,这种奴仆在仙都又被称为“客户”或“客户仔”。这些外地迁来的客户,分别隶属于仙都的黄、林、刘、蒋、汤五大姓,现将解放前仙都林、黄诸大姓的奴仆隶属关系。
以上客户的姓名是根据现在尚健在者回忆的名单,解放前仙都客户的实际数量大大超过此表,如良村黄姓的奴仆,据“仓间”客户廖三祠(现年六十一岁)回忆,其童年时(约五十年前)廖姓客户尚有数十户,五十余人,至四十年前廖姓只剩两户,至解放前夕,仅存廖三祠一家。至于清代以前的奴仆数量就更多了,单廖姓客户,清末时就有三百余人,皆为良村黄姓奴仆。
大姓与小姓主奴的关系一经确认,这二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就有了明显的差别。
其一,奴仆即客户对于大姓主家必须屈尽礼仪。由于客户是闔族公共的奴仆,因此,客户对于所依附的大姓主家,不论年老长幼,均不得直呼其名,务必以某某“官人”相称。阡陌相遇,须先让在一旁,双脚并立,两臂靠背躬腰低头,并遽先以“某官人”称呼,致候问安。主家有事呼唤,客户进主家之门,亦仍以躬腰站立一旁,不得擅自就坐。大姓主家则不论年龄长幼,均可直呼客户为“某奴才”、“某贱人”、“某奴婢”等,客户不敢有任何异议。
其二:奴仆客户不得与大姓主家混杂而居,主家拨出少量低陋小屋,让众客户相聚居住,以便随时呼唤差使。中圳、先锋等地的大姓林氏所属的客户,解放前聚居于林姓的楼仔底约长二十米,宽六米,林姓所属之数十户奴仆聚居其中,房屋破旧,拥挤不堪,又如良村黄姓的奴仆聚居仙都圩的“仓间”。所谓“仓间”,乃是黄姓族田遍布仙都各处,远者距良村不下数十里,黄姓族主为便于收租,于仙都圩旁的山坡上建立临时仓库一座,平日借其奴仆客户居住,这种“仓间”,亦相当低下简陋,据当时各大姓的族规,身份卑下的奴仆只能住如此低陋的房子,凡为客户所居,其房间的规模高度,门户的大小及大梁的尺寸,均不得超过大姓主家的任何一家。据刘姓所属的奴仆林文佃回忆,其父妹广因外出抬轿赚有少许银钱,而原住的房屋过于拥挤,想将土墙加高数尺,建一小小阁楼,但不久被林姓主家发现,随即把它折平。
其三、大姓主家对于客户的服装亦有严格的限制。客户的日常衣饰,大多来源于为主家殓葬时拾来的死人遗物,客户叶火旺说:他从小就是穿死人的衣服长大的。客户即使平日偶有添置,亦只能以短衫、汉装为准。主家规定,客户男性不得穿长衫、戴礼帽,女子不得穿裙子,不论老幼,皆不得穿棉衣。据林姓属下客户林文佃回忆,有一次其岳母穿火红裙子,当众被林家族众责令剥下。大姓的理由是:你等为奴婢者,服饰如此鲜艳,那么我辈主人又将穿何衣服?在大姓眼里,奴仆穿新戴红,即有蔑视主人之意,故应严加禁绝。
其四、大姓主家与客户在葬礼上亦有严格的区别。大姓主家遇有丧事,即可八杠大抬,哀乐齐奏,招摇过市,并勒令众客户为之殓葬吹打。而客户如遇丧事,虽然他们俱具吹打之能,也不得擅自奏乐出殡,只能以薄棺次材,草草收殓,悄然默哀,不得喧闹。客户死后埋葬的坟地,据我们实地调查,绝对不能任意挑选风水宝地,只能由大姓指定的一小块杂草丛生的乱坟岗,不仅客户死后埋葬于此,各种上吊,淹死等,不得以大礼入葬的尸体及剃头、糊纸等下九流的死尸,亦都杂埋于此,以示客户身份低贱。
其五、客户不但不能与大姓主家通婚,而且亦不得与其他大姓通婚,甚至其他的编户齐民,亦皆以客户低贱而不愿与之通婚。但大姓主家却可以任意凌辱客户妻女,大姓男子逼客户妻女与之过夜,客户不得与之计较。据调查,解放前仙都众客户,其妻女面目稍为清秀者,她们的人身自由大部份得不到保障,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主家大姓恶少的侮辱。如有一客户,其妻名曰“菜瓜,长年为大姓七房某一恶棍霸占,其夫只能远离仙都出外谋生而不敢返家。又另一客户周戊之养女年方十五,尚未出嫁,被中圳恶棍林某某于众目睽睽之下,强行拉去行奸,众客户亦只能忍声吞气。
其六、客户无权入学读书,更不得应试科举。但主家为了更方便地役使客户,有控制地让客户子女识少许的字,如新春拜神送福份(即供品)时,闔族数百家的福份均由客户挑送摆设,为了避免各户福份的混乱,挑送的客户必须在每一福份上写上各主家的姓各,这样就需要客户认识少许的字。因此,仙都的大姓主家允许少量客户的儿子进私塾念一、二年书,以便在送福份时能认识各主家的姓名,同时,也使客户更胜任于散发主家请贴的役使。由此可见,主家让客户子弟识几个字,并不表示主家承认这些子弟有受教育的权利,而纯粹是为了让他们能更好地为主人服役。现任华安县农业银行行长叶火旺,解放前也是客户,他在孩儿时为能略记主家姓名,被允许进私塾念二年书。代价是自费束修每月一石两斗米。
其七、各大姓供奉的同姓神祗,庙宇不准客户入内祈求保祐。
总之,仙都大姓与客户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是非常悬殊的,他们之间的主奴隶属关系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各大姓族内贫富的差距很大,阶级对立相当严重,但他们在传统观念上则不论贫富,始终为其社会地位要比众客户高出许多等。客户借以谋生的各种行当,各大姓都是不屑一顾的。在大姓族内,若有贫困者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作客户的行当,即被认为是对宗族的奇耻大辱,而要受族长的惩罚。如解放前中圳林姓有一赤贫者林红雨,家无寸土,长年为人挑担过活,某年终,挑担无着,遇有客商寻求轿夫,轿夫原为客户行当,林红雨在贫困之中不得已受雇抬轿一次,回乡后即被林姓族长驱遂出祖,林红雨走投无路,又不愿从此沦为客户,于是只得逃往南洋谋生。这一例子说明解放前仙都各大姓与客户之间的主仆身份真有天壤之别。
二、仙都客户的劳役负担
仙都客户作为林、黄诸大姓的奴仆,不仅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更重要的是这些客户数百年来一直遭受十分残酷的人身奴役。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农忙农闲,都必须服从大姓主家的役使,长年为大姓主家承担各种劳役。
仙都客户所承担的各种劳役,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固定劳役;二临时差派。根据我们对仙客户以及大姓等多方面的调查综合,解放前仙都客户于每一年之中所承担的固定劳役。
从上表可以看出,仙都每一客户于一年之间所服的固定劳役达六十天以上。所谓固定劳役,就是每年必做,变化不大的劳役。除此之外,众客户还得应付各大姓主家许多临时的派使,这种临时的派使,名目繁多。现将解放前仙都客户所承担的许多主要临时派使劳役。
类似以上的临时劳役,不仅名目繁多,难以细举,同时由于仙都的客户是各大姓闔族公共的奴仆,供大姓整族役使,而每一大姓皆多达数百户,甚至上千户,每一户都有役使客户的权力,而且这数百户大姓人家住地距离客户亦远近不等,远者达数十里,客户来回应付,疲于奔命,再加上各种不时的呼唤,如抬轿殓葬,散发请帖,接送宾客等等,是纷至沓来,穷于应付。因此,客户每年必须花费很多时间来承担劳役。据中圳大姓林氏的客户扬春时、林文佃等人估计,解放前每一客户为其大姓主家所服的临时劳役约有两个月以上。加上每一客户每年为主家大姓服两个多月的固定劳役,即是解放前仙都客户每年必须受到主家四个多月的人身奴役。
客户为了胜任大姓主家的各种役使,还得具备各种役使所必须的用具,如大姓主家外出乘轿,客户必须自备轿子并经常维修;春节来临,大姓主家要迎新去旧,客户必须准备好扫帚等打扫工具,为各主家拂尘;大姓主家遇有丧事,客户必须准备烧水及杠抬棺木的用具,同时还得备有一整套的麻衣丧服,随时供主家使用等等。
不仅如此,客户还得学会为主家服役所应有的各种技能。大姓主家红白大事,需要吹打奏乐,客户必须学会各种乐曲的吹奏,并经常练习不得疏废:大姓主家迎娶送嫁,客户眷属充当送嫁姆,要经常练习吉利话的顺口溜,唱到出口成章,不能有错,如新娘一到男家,送嫁姆就唱:“新娘到厝,买田建屋”,新娘拿起碗,送嫁姆就唱:“摸碗叮叮响,年年买好田”等等。客户的子女,自幼年时,也都必须跟随父母学习抬轿,殓葬,以及吹打陪嫁迎唱等等各种技能,使得客户的所谓“低贱行当”,世代相传,以保证大姓主家对于客户的奴役不致中断。
服劳役是仙都客户的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如上所述,每一客户于一年之中供大姓主家役使的时间长达四、五个月之久,客户对于大姓主家的任何呼唤差使,只能唯命是从,不能有半句怨言,稍有不遂主家之意,大姓主家可以任意惩罚痛打客户。据客户叶火旺回忆,他还在襁褓时,有一次大姓主家呼唤其父前往抬轿,其父身体偶有不适,未能及时前往,大姓主家追至楼仔底客户住处,将叶火旺家的棉被等家杂统统搬至仙都圩场,当众放火烧毁,并将叶火旺强行抢走,准备断其叶家香火。后经叶火旺父母苦苦哀求,多方陪罪,方将叶火旺领回。客户遭受大姓主家的各种惩罚,均不得争辩、反抗,同时冤屈亦无处伸诉。因为在解放以前的仙都一带,大姓主家对奴仆客户施用肉刑,似乎是一种自然之理,无人异议,这种现象说明了大姓主家对奴仆客户有着任意打骂的人身占有关系。
仙都大姓主家对奴仆客户的这种人身占有关系,除了强迫客户们世代为奴仆外,还规定客户的任何婚嫁关系,必须以不影响主家对其奴役得到延续为前提。客户们只要不是完全绝户,那么即使这一客户家庭有何变动,大姓主家对于他们的奴役权利也永远不变。如仓间客户廖三祠,其廖姓原为良村黄姓奴仆,对于良村黄姓有服役的义务,但廖三祠的母亲为先锋林姓的客户叶笑仔之女,叶笑仔独此一女而无男儿,此女许配廖三祠的父亲为妻后,先锋大队林姓主家强令将叶家对于林姓的服役义务,要一同嫁往廖姓,否则不准完婚,因此,从今以后,廖三祠一家不仅要承担原来良村黄姓主人的服役义务,而且还要为先锋林姓服役。这一例子说明仙都大姓主家对于客户的人身束缚是何等的严厉,又是何等的牢固。
三、仙都客户与主家的经济关系
仙都客户做为林、黄诸大姓的奴仆,每年必须为大姓主家承担大量的劳役;而作为交换条件,众客户一般可以种主家的田地,藉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仙都客户是各大姓通族的公共奴仆,他们并不专属于某人家庭,因此客户所耕种的土地,全部都是各大姓主家的族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仙都各大姓对于祠堂族田等设备及经营是十分注意的,每一大姓每一房派,都有相当数量的祠产、族田,每年祠产、族田的收入,由族中轮流的主祭人,即族主经理,作为本族、本房的一年四季祭祖扫墓,以及兴办族学等费用。而这些祠产、族田的收入,则是通过奴仆的耕种并勒取其劳动产品的相当部份而获得的。
仙都客户租种大姓主家族田而交纳的地租形式是相当特殊的,名义上是实行实物定额租制,计算方法习惯上算租谷不算亩,即客户租种大姓主家一亩地每年必须交纳十石租谷,那么这一亩地便称为十石租田,客户租种这块土地,便按这个定额交纳田租。解放前以至明清时期仙都通行的每石约折现在的六十市斤,这就是说,客户每租佃大姓主家一亩族田,每年规定须交纳六百市斤的租谷。我们曾对于四户客户的租佃情况做了典型调查,地租上的剥削情况。
仙都客户租种大姓主家的族田,实物定额租高达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二,轻者亦达百分之五十四,平均可达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一定额租是比较高的,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伪县政府整理的《中国行政区域资料调查表》记载,解放前华安县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地租情况是“其田租普通二分之一,如一亩每年可产二石,佃农应纳田租一石,半年盈余归佃农所得”。由此可知仙都客户租佃大姓主家的族田所交纳的地租额高于百分之五十。不过如果遇上荒年,有的主家大姓如良村黄姓等,亦可酌情减免若干租谷,这当然是大姓主家用以笼络客户的一种手段,同时亦带有主家豢养奴仆之意,这样就能使客户更加听从主家的役使。
众客户除了交纳租谷之外,每年还有收成的百分之四十归自己所有。从上表客户来看,这四个客户共有廿四人,租种族田共十九亩半,一年得剩余稻谷共六千七百八十斤,平均每人每年只有稻谷二百八十斤。但客户租种大姓族田,种子、耕牛、肥料、农具,以及其他农业成本均由客户自己负责,如果扣除这些成本费用,客户租种大姓主家的族田,每人每口只能获得二百斤左右的稻谷。
仙都客户租种大姓主家族田,虽然从名义上讲是实行实物定额租,也许客户初迁入仙都时实行过这种地租制,但从明中叶开始,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货币的大量流通,使仙都客户向大姓主家交纳的地租,开始从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种货币地租的征收办法是:原订的实物租的租额不变,即原订一亩交纳租谷十石仍为十石,将这十石租谷按市价折成货币交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市价不是一年的平均价格,而是按仙都圩上的最高价格为准。大姓主家每一圩日都派人前往打听市价,一旦某一圩日谷价高涨,大姓主家即通知各客户到圩场按此市价折纳货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仙都大姓主家与奴仆客户的租佃关系,既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出现了货市地租的形态,但同时又保留十分浓厚的超经济强制的残余因素。
这种以最高谷价折纳货币的做法,无形加重了对客户的地租剥削,使得客户一年辛勤劳动所得的剩余的部份更少了,因此,客户租种大姓主家的族田,一般只够维持三、四个月的生活,有的租额特别重的,如林文佃租种中圳林姓族田,租率达百分之七十二,他们每年所得的稻谷只够维持全家一个半月至二个月的生活。
仙都客户除了耕种大姓主家族田得到一点经济收入之外,在服劳役之中也可取得少许的酬劳。客户为大姓主家服各种劳役,其中大部份是无偿劳动,如拂尘、修脸、祭祖差役等,但也有一些劳役,得到主家的赏赐,以示豢养奴才之意。这种酬劳可分三种形式:一种是服役时主家供给饭食,如迎神赛会时,主家另备一小桌饭菜,供客户食用。若是大姓主家有婚嫁等大喜事,客户为之抬轿或充当送嫁姆,主家的饭食报酬又稍优厚,客户将新娘送到郎家后,轿夫到伙房洗脸擦脚,脱掉草鞋,穿上主家的布鞋,到专为他们设立的席筵上就餐,送嫁姆在新娘房陪同新郎,新娘吃十二碗,并喂新娘吃菜,每吃一碗菜,送嫁姆都要唱一句吉语。翌日早晨送嫁姆还要洗新郎、新娘的白底衫裤。因此解放前众客户有谚云:“送嫁抬轿贱,到厝酒肉便”。大姓主家对于客户服役的另一种酬劳形式是对抬轿、小殓、埋葬等劳务赏给一点小费,赏钱的多少,全由大姓主家决定,客户不得与之计较,唯有恭敬接受而已;还有一种酬劳是给少量土地耕种不收地租,如大地村客户刘锦山为大姓主家,长年看守坟墓,主人对他的酬劳是将坟地旁边的田地拨一亩给刘锦山耕种,收成全归刘所有,不必交租。以上这些大姓主家对于客户服役的酬劳虽然是相当微薄的,但也是客户借以维持生活的来源之一。
客户为了维持其低下的生活,还利用一些空余时间,出外为人佣工。前面我们讲过,仙都客户于一年之中必须为大姓主家服役四、五个月之久,客户租种主家的族田,一年种两季,亦得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样,客户于一年之中所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二个月,这一、二个月时间,大姓主家允许客户自由支配,各自外出寻找生路。因此,有的客户利用剩余时间到外乡抬轿。抬轿遂成了他们这一、二个月时间中谋生的重要手段。解放前华安一带每抬轿十里,工钱为六角,若是有人招雇,客户外出抬轿一日,一般可得一至二元工钱;有的客户利用剩余时间出外打短工。根据我们了解,仙都现存的客户,凡是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者,几乎都曾经打过短工。据客户林文细回忆,解放前客户打短工,工钱是六天一元,合米三斗三升,折为十九斤半,平均每一天的工钱是大米三斤一两。
为客商挑担,是客户利用剩余时间谋生的另一途径。华安县虽然地处山区,但福建南部最大的河流九龙江从龙岩、漳平等地横穿华安全境,向南流经漳州、石码入海,因此,明清时期华安县的商业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漳州、厦门沿海的盐、鱼等货物由九龙江逆水而上,运往龙岩州各县,而龙岩州各地的木材、纸、茶叶等货物亦顺九龙江而下,运至漳州、厦门等地,并转运出洋。这样,华安县的华崶、新圩等镇便成了这条商业运输线上的重要转运站,客商往来络泽不绝,货物搬运非常繁忙,据老人回忆“每天从早到晚,肩挑工人来回挑运货物,少者几百,多则上千”。于是仙都客户亦利用一些空闲时间,经常到华崶、新圩一带挑盐担纸,挣得一些脚钱。
虽然客户有支配自己剩余时间的权利,但由于身为奴仆,地位低下,客户每向他人抬轿、挑担、打短工时,雇主往往不能以平等合理的工钱相酬,客户亦多不敢与之计较。因此,客户利用这一、二个月剩余时间,外出谋生的收入,也还是相当微薄的,大致亦只能维持全家二、三个月的生活而已。这样就不能不迫使客户们经常陷于极度的贫困之中。
四、仙都客户的人口与婚姻情况
仙都的林、黄、刘、蒋、汤五大姓自明前期迁入定居之后,至今已繁衍二万人以上,而林、黄诸大姓隶属下的客户奴仆,虽然亦定居于仙都数百年之久,但到解放前夕,仙都各姓客户只剩有一百人左右。仙都客户的世系得不到正常的传衍,人丁逐渐减少,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客户在大姓主家的残酷剥削奴役之下,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生活极度贫困,使得数百年来客户始终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我们上面讲过,客户在大姓主家沉重地租和繁重劳役的多层剥削之下,虽然一年到头胼手胝足地辛勤劳动,但亦只能维持七、八个月的生活。有的甚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如下林田头客户周埋吓,解放前穷得晚上睡觉全家只能盖棕衣,治穷无术,周埋吓终成为饿殍。客户偶受风寒,无钱医治,只能任其逐日加重,坐以待毙。据仙都年老的客户回忆,仙都叶姓客户于清末本来也有一百余人,但在民国期间因发生鼠疫,死亡殆尽,至解放时只剩下三户。在正常年景里,客户的人口亦能稍微增加,但一迁凶年,饥荒疾疫,交相侵害,客户人口又急剧下降。数百年来,客户的后裔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幸存下来的。一般客户因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容易感染疾病以致身体衰弱,寿命短促。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凡遇到老年客户,大多是矮小消瘦,这是他们饱受辛酸的痕迹。
数百年来仙都客户传衍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婚姻权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客户们的婚姻选择范围极其狭窄。他们的主要通婚范围只有如下几种:
(一)在不同姓氏的客户之间进行通婚,这一现象在旧社会极为普遍。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存的仙都各姓客户中,他们相互之间大多有因通婚而形成的亲戚关系,如中圳客户叶火旺的姐姐嫁与先锋客户杨春水为妻,而叶火旺的母亲又是下林田头客户周民的女儿。仓间客户廖三祠的母亲娶自先锋叶姓客户,而中圳的客户杨家两兄弟之妻又娶自仓间的廖家。不过由于客户中成家的人不多,可供出嫁的女子自然很有限,因此有女儿的客户,一般喜欢采取招赘的办法,故在客户的相互通婚中,招赘比娶取更为普遍。
(二)与其他的贱民阶层相互通婚。在明清时期的华安一带,除小姓客户沦为大姓的奴仆之外,另外有一些民间所谓之“下九流贱民”,如无籍剃头匠、糊纸匠(为民间进行超度阴鬼,做法场等迷信活动,糊装各种纸厝、纸轿、纸人等)、乞丐等,这些贱民虽非专属于某家某姓的奴才,但他们因社会地位低下,屡为各大姓豪家所欺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与客户就能够经常来往,同苦乐,同呼吸,以至他们的儿女互相通婚。如大地村客户乐随,其弟娶仙都圩剃头匠之女为妻便是一例。
(三)收养童养媳。明清时期至民国,福建一带素有溺女、弃女之风,一般民户产男则养大,产女则多遗弃,于是有一些人贩,从远处各县贩来为其父母摈弃的幼女,到华安仙都一带出卖,价格比较便宜,同时,稍稍养大,又可成为家里的重要辅助劳动力,因此,仙都许多客户都愿意从人贩子那里买来幼女当童养媳或养女,待到长大成姑娘,便配与儿子为妻或招赘其他客户入门成亲。现在还健在的中圳楼仔底客户叶文的母亲,便是清朝末年人贩子从安溪一带贩来,为叶文的祖父所收养长大的童养媳。
仙都客户的婚姻虽然有以上三种来源,但由于本地的大姓及一般的编户齐民均不愿与之通婚,因此,客户的通婚范围仍然是十分狭窄的。同时,客户的经济状况十分恶劣,也使得他们不能进行正常的嫁娶。大凡婚嫁,总须费一笔钱银,但许多客户连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又那有钱银进行婚嫁呢,从我们的调查材料看来,客户中成年男丁因贫难娶,孤独一生的十分普遍。结果人口的繁殖率比一般人低得很多。继嗣香火往往是单线独传,甚至成为绝户的各所在都有。中圳楼仔底客户林文佃一家五代的婚姻情况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现将林文佃一家四代的婚姻并继嗣状况。
林文佃②祖先原是漳浦县林姓,自明代迁居华安仙都,传至林文佃为第十九代,故林文佃的祖父辈应为第十七代,兄弟三人。
第十九代(已解放)
至今全家共有男丁五人,亦即从漳浦林姓迁入仙都为人当奴仆后,传至十九代,历时数百年,经过解放后三十余年的发展,才由一男丁恢复至五男丁。
从上列的客户林文佃四代婚姻传衍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大姓主家对于客户婚姻权利的严格限制下,客户的通婚范围极其狭窄,这就使得客户的许多男丁得不到正常的婚配,终身孤苦伶仃,谈不上所谓“瓜瓞之绵绵”。
综上所述,大姓主家对于客户奴仆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以及对于客户婚姻权利的限制,这是造成客户人口经数百年而无所发展的两大重要原因。我们从其他省外地区的蓄奴情况看来,明清以来以至民国,这些地区奴仆的数量之所以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奴仆的反抗斗争而摆脱奴籍;有清朝雍正年间解放奴婢身份法令的作用等等。但仙都客户数量减少的原因却是例外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仙都客户之所以沦为奴仆,是由大姓宗族封建暴力统治造成的产物。因此,在宗法势力稳固的华安仙都一带,清朝政府有关解放奴仆身份的法令,是很难冲越宗族势力的藩篱,而恩及大姓严格控制下的客户的,其次,在仙都,客户是隶属于整个大姓家族的公共奴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奴仆们不能进行丝毫的反抗,因为客户若有稍微反抗,必将遭到大姓阖族的镇压,因此,自明代客户沦为奴仆以来,仙都始终未能发生过任何的反抗斗争。
五、仙都客户是奴仆而不是佃仆③
上面我们对于仙都客户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婚姻情况、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前仙都各大姓主家属隶下的客户是一种奴仆,是中国奴隶制的严重残余。
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的封建法律和传统观念上,凡是具有“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这三个特点的人,都被划入奴仆类。近年来,有不少同志对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徽州及其他许多地区各种奴隶制残余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具有“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奴仆”,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家族农奴性质的佃仆而不是奴仆。从仙都的情况看,仙都客户同样具有“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的特点,但我们认为这些客户是比佃仆处境更为恶劣和低下的“贱民”,他们与各大姓主家有相当明确的主仆名份,他们受到各大姓主家的任意奴役、敲榨,他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妻子女儿随时有被大姓主家欺凌霸占的可能。这些情况说明了大姓主家,对于隶属于他们的奴仆客户,具有相当程度的人身占有特权,而人身占有特权正是奴隶制最重要的原则。
坚持奴仆是典型的农奴,而不是奴隶的同意,还认为奴仆与家内奴仆,有明显的区别,而不能把这二者混同起来。但我们从仙都客户所被奴役的各种劳役情况来看,仙都客户恰恰是“奴仆与家内奴仆混同起来”的一种贱民,带有严重的家内奴仆的特点。
从我们下面罗列的仙都客户所服劳役的情况表中看,客户所服劳役的一部份,如抬轿、守坟、治葬、祭祖、守粮仓、吹打等,这些劳役与徽州的“佃仆”所服的劳役基本相同,这种劳役,当然很难说带有家内奴仆的性质。但仙都客户对于大姓主家所服的劳役还远不止于此,其他如过年时为大姓主家挨户拂尘,客户眷属为主家大姓,每个成年妇女修脸拔毛,充当送嫁姆等,这些劳役毫无疑义是家内奴仆应干的差使。对于这些劳役,我们在实地调查过中,曾经仔细地访问了大姓主家的有关人员及曾经服过此役的客户,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仙都大族阖族多达数百户,一、二千人,而在解放前夕,幸存的客户极为有限,举林姓为例,林姓通族为二、三千人,七、八百户,而为之服役的客户只有六、七户,人口不过三、四十人,而每逢过年之时,六、七户客户的十来名男丁,必须为大姓全族七、八百家拂尘,假如要认真拂尘打扫的话,一个客户男丁一天大致只能清理一家,那么七、八百户大姓主家,十来名客户男丁势必打扫七、八十天才能完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客户为大姓主家拂尘,大半带有象征性质,即刻每家每户的大厅,用扫帚拂扫清浩即当完事。客户之所以如此应付,并不是客户带有抗拒怠工之意,也不是主家特有的恩典,据双方当事人说,大姓主家之所以要客户为主拂尘,主要目的还不在于真正清理卫生,而是在于从传统观念上讲,客户是大姓的奴仆,必须为各主家拂尘,以示奴才服待主人之意。又如五月端午节时,客户眷属务必为大姓主家各妇人修脸拔毛,修脸是相当细致的活,假如认真从事,大姓阖族上千名妇人,几个客户眷属,亦恐非二、三个月不能完事,但实际上只用五天时间,即五月初一日至五月初五日,可见,这种修脸仍然是一种象征性质的服役,客户眷属为大姓妇人修脸,表示大姓主家有奴婢使唤。其他如当送嫁姆等劳役,都带有服侍主人的意思。毫无疑问,大姓主家强迫各客户承担以上劳役,完全是从家内奴仆,家内奴婢这一观念出发,带有家内奴仆的性质,因此,我们说,仙都客户是一种比佃仆更为低贱的奴仆。
当然,仙都客户具有某种独立性,可以支配自己的剩余时间,有个体的家庭经济,(虽然这种家庭经济是非常贫困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做为奴仆的身份,因为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以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我们怎能要求奴仆与奴隶社会的奴隶完全一样呢!(其实在奴隶社会里,中国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亦各有其特点),因此,封建社会晚期的奴仆,比起奴隶社会的奴隶,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必然的,更何况封建社会晚期的奴仆仅仅是奴隶制度的残余,而並不是完整的奴隶社会,这一点也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
总之,通过这次实地调查,我们弄清楚了仙都客户的人身,在相当程度上被大姓主家所占有,而大姓主家在一定意义上,又把他们当家内奴仆看待,因此,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前,仙都的客户只能是奴仆,而不是佃仆。
一、蓄奴的起源及客户的社会地位
华安县现属福建省龙溪地区行政公署。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以前华安县境分隶漳州府的龙溪县,泉州府的安溪县以及龙岩州的漳平县。民国十七年,由龙溪、安溪、漳平三县分划若干保,正式署县。县境之内山峦环绕,地形起伏,田土贫瘠,人口稀少,建县之时,全县人口仅五万一百余人。
华安县虽然县小人稀,但封建宗族势力却相当稳固,氏族制的残余在解放前之华安处处可见,大部份村落是“聚族而居,同姓相亲”,并且严厉排斥外姓来村居住。据《民国华安县志草稿》氏族志记载,解放前华安县境共有姓氏五十种左右,其中有百分八十以上是聚族而居,自成村落,血缘关系相当牢固。
仙都公社于解放前夕称仙都区、仙都保、宜昭保、义昭乡,位于华安县之东北角,与安溪县相邻,人口约一万人左右。仙都区有一圩场,为邻近数十里各村落及安溪县一部份村落的集市贸易场所。临近仙都圩有云山、下林、招山、中圳、市后、先锋、大地及良村等主要村落,仙都区内各主要大姓皆聚居于以上这些村落(现皆为生产大队)。招山、先锋、中圳、市后为苏林两姓聚居地,解放前约有人口三千余人,大地为刘、蒋二大姓聚居地,刘、蒋两姓各有人口一千人左右,云山为汤姓聚居地,人口约一千人,良村为黄姓聚居地,人口有二千人。这些大姓大多是于明代前中期,由龙岩、漳州等地迁移而来,至今延衍数十代,人口多达数千众。
仙都各大姓都有相当严格的家族组织,每一大姓均设有始祖祠堂,始祖祠堂之下又分设支派祠堂,支派祠堂之下又有大小各房祠堂,每当春、秋二季祭祖之时,各大姓数千名族众依次进行祭祀拜祖,各房子孙,子房祠堂之内拜房祖,各支派子孙又得聚集于支派祠堂拜支祖,闔姓大小还得团聚于始祖总祠堂内,拜祀始祖,缅怀祖先开基之德。同时各大姓还往往闔族公立庙宇,供奉同姓神祗,族内不分老幼,均要虔诚礼拜以求同姓神祗的保祐。
宗族组织的严密与祭祀系统的完备,必然伴随着大量族田的出现。仙都诸大姓的情形正是如此,这些大姓不仅置有供祭祀费用的祭田,同时还有义田,学田等等。这种族田,许多大姓都多达数百亩以上,如良村的黄氏族田,除分布于良村之外,几乎遍及仙都乡,远达四十余里的大地村,亦有许多黄姓的墓田、祠田。
大量族田的购置,以及每年繁多的祭祖形式,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以供役使。于是,仙都一带的各个大姓族内,大都保留着蓄奴的习惯,即所谓“聚族成村到处同,奴婢使役序整然”,解放前当过良村黄姓奴仆的廖三祠回忆,清代末年,良村黄姓所蓄之奴婢,单廖姓一支,竟多达三百余人,其他各姓于清朝末年亦都蓄有奴仆数十人以至数百人不等。
仙都蓄奴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代前中期,根据我们的调查,仙都的林、黄、刘、蒋、汤五大姓的奴仆,有叶、杨、林、刘、罗、乐、丘、李等姓,这些沦为奴仆的姓氏祖宗迁入仙都,都有十至二十代之久,现将仙都诸大姓及其所属之奴仆姓氏迁入仙都之代数。
由此可见,当明代中期林、黄诸大姓迁至仙都不久,蓄奴现象己经出现。
叶、杨诸姓之所以沦为奴仆,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二种:
一、大姓强迫小姓为奴仆,华安仙都一带,地处漳泉二府以及龙岩州交界之处,山陵起伏,交通闭塞,因此于明代以前人口非常稀少。仙都现有之各姓,不论是主姓还是奴姓均于明代之后,陆续迁入定居。林、黄诸姓族大势众,而叶、杨等姓户小丁薄。小姓迁入之后,根本无力与大姓抗衡相争,于是,原来没有任何相属关系的各姓族,这时的阶级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大姓夺占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山林,俨然以主人自居,而诸小姓被迫为大姓的奴役,沦为大姓的奴仆。显然,这种主奴隶属关系,带有严重的村社氏族制度,强大氏族奴役弱小氏族的性质,如仙都林氏属下的叶、杨等姓就是在这种情况沦为奴仆的。
二、投靠。因荒年暴岁,外地小姓流落至仙都,此地大姓势大族众,田地、山场均归大姓所有,新迁来的外地小姓,无立身之地,为了生计,只得投靠某一大姓,为其奴仆,求其庇护。如良村廖姓,原为龙岩、宁洋两县居民,明时迁入仙都后,即依附于良村大姓黄族为奴,据廖三词等说,其祖先迁入仙都认良村黄姓为主人时,双方曾有口头之誓约,即廖姓起愿誓世世代代拜黄为主,永受役使不敢有怠,如有变更初衷愿受主家任意惩处,并得天谴亡子绝孙。而黄姓则让廖姓永佃黄姓族田作为交换条件,并提供廖姓居住的房屋和死后的葬地,同时还可以为廖姓提供某些庇护,以免遭受其他大姓的欺凌等等。
由于仙都各大姓的奴仆均为从外地迁来的小姓,因此,这种奴仆在仙都又被称为“客户”或“客户仔”。这些外地迁来的客户,分别隶属于仙都的黄、林、刘、蒋、汤五大姓,现将解放前仙都林、黄诸大姓的奴仆隶属关系。
以上客户的姓名是根据现在尚健在者回忆的名单,解放前仙都客户的实际数量大大超过此表,如良村黄姓的奴仆,据“仓间”客户廖三祠(现年六十一岁)回忆,其童年时(约五十年前)廖姓客户尚有数十户,五十余人,至四十年前廖姓只剩两户,至解放前夕,仅存廖三祠一家。至于清代以前的奴仆数量就更多了,单廖姓客户,清末时就有三百余人,皆为良村黄姓奴仆。
大姓与小姓主奴的关系一经确认,这二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就有了明显的差别。
其一,奴仆即客户对于大姓主家必须屈尽礼仪。由于客户是闔族公共的奴仆,因此,客户对于所依附的大姓主家,不论年老长幼,均不得直呼其名,务必以某某“官人”相称。阡陌相遇,须先让在一旁,双脚并立,两臂靠背躬腰低头,并遽先以“某官人”称呼,致候问安。主家有事呼唤,客户进主家之门,亦仍以躬腰站立一旁,不得擅自就坐。大姓主家则不论年龄长幼,均可直呼客户为“某奴才”、“某贱人”、“某奴婢”等,客户不敢有任何异议。
其二:奴仆客户不得与大姓主家混杂而居,主家拨出少量低陋小屋,让众客户相聚居住,以便随时呼唤差使。中圳、先锋等地的大姓林氏所属的客户,解放前聚居于林姓的楼仔底约长二十米,宽六米,林姓所属之数十户奴仆聚居其中,房屋破旧,拥挤不堪,又如良村黄姓的奴仆聚居仙都圩的“仓间”。所谓“仓间”,乃是黄姓族田遍布仙都各处,远者距良村不下数十里,黄姓族主为便于收租,于仙都圩旁的山坡上建立临时仓库一座,平日借其奴仆客户居住,这种“仓间”,亦相当低下简陋,据当时各大姓的族规,身份卑下的奴仆只能住如此低陋的房子,凡为客户所居,其房间的规模高度,门户的大小及大梁的尺寸,均不得超过大姓主家的任何一家。据刘姓所属的奴仆林文佃回忆,其父妹广因外出抬轿赚有少许银钱,而原住的房屋过于拥挤,想将土墙加高数尺,建一小小阁楼,但不久被林姓主家发现,随即把它折平。
其三、大姓主家对于客户的服装亦有严格的限制。客户的日常衣饰,大多来源于为主家殓葬时拾来的死人遗物,客户叶火旺说:他从小就是穿死人的衣服长大的。客户即使平日偶有添置,亦只能以短衫、汉装为准。主家规定,客户男性不得穿长衫、戴礼帽,女子不得穿裙子,不论老幼,皆不得穿棉衣。据林姓属下客户林文佃回忆,有一次其岳母穿火红裙子,当众被林家族众责令剥下。大姓的理由是:你等为奴婢者,服饰如此鲜艳,那么我辈主人又将穿何衣服?在大姓眼里,奴仆穿新戴红,即有蔑视主人之意,故应严加禁绝。
其四、大姓主家与客户在葬礼上亦有严格的区别。大姓主家遇有丧事,即可八杠大抬,哀乐齐奏,招摇过市,并勒令众客户为之殓葬吹打。而客户如遇丧事,虽然他们俱具吹打之能,也不得擅自奏乐出殡,只能以薄棺次材,草草收殓,悄然默哀,不得喧闹。客户死后埋葬的坟地,据我们实地调查,绝对不能任意挑选风水宝地,只能由大姓指定的一小块杂草丛生的乱坟岗,不仅客户死后埋葬于此,各种上吊,淹死等,不得以大礼入葬的尸体及剃头、糊纸等下九流的死尸,亦都杂埋于此,以示客户身份低贱。
其五、客户不但不能与大姓主家通婚,而且亦不得与其他大姓通婚,甚至其他的编户齐民,亦皆以客户低贱而不愿与之通婚。但大姓主家却可以任意凌辱客户妻女,大姓男子逼客户妻女与之过夜,客户不得与之计较。据调查,解放前仙都众客户,其妻女面目稍为清秀者,她们的人身自由大部份得不到保障,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主家大姓恶少的侮辱。如有一客户,其妻名曰“菜瓜,长年为大姓七房某一恶棍霸占,其夫只能远离仙都出外谋生而不敢返家。又另一客户周戊之养女年方十五,尚未出嫁,被中圳恶棍林某某于众目睽睽之下,强行拉去行奸,众客户亦只能忍声吞气。
其六、客户无权入学读书,更不得应试科举。但主家为了更方便地役使客户,有控制地让客户子女识少许的字,如新春拜神送福份(即供品)时,闔族数百家的福份均由客户挑送摆设,为了避免各户福份的混乱,挑送的客户必须在每一福份上写上各主家的姓各,这样就需要客户认识少许的字。因此,仙都的大姓主家允许少量客户的儿子进私塾念一、二年书,以便在送福份时能认识各主家的姓名,同时,也使客户更胜任于散发主家请贴的役使。由此可见,主家让客户子弟识几个字,并不表示主家承认这些子弟有受教育的权利,而纯粹是为了让他们能更好地为主人服役。现任华安县农业银行行长叶火旺,解放前也是客户,他在孩儿时为能略记主家姓名,被允许进私塾念二年书。代价是自费束修每月一石两斗米。
其七、各大姓供奉的同姓神祗,庙宇不准客户入内祈求保祐。
总之,仙都大姓与客户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是非常悬殊的,他们之间的主奴隶属关系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各大姓族内贫富的差距很大,阶级对立相当严重,但他们在传统观念上则不论贫富,始终为其社会地位要比众客户高出许多等。客户借以谋生的各种行当,各大姓都是不屑一顾的。在大姓族内,若有贫困者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作客户的行当,即被认为是对宗族的奇耻大辱,而要受族长的惩罚。如解放前中圳林姓有一赤贫者林红雨,家无寸土,长年为人挑担过活,某年终,挑担无着,遇有客商寻求轿夫,轿夫原为客户行当,林红雨在贫困之中不得已受雇抬轿一次,回乡后即被林姓族长驱遂出祖,林红雨走投无路,又不愿从此沦为客户,于是只得逃往南洋谋生。这一例子说明解放前仙都各大姓与客户之间的主仆身份真有天壤之别。
二、仙都客户的劳役负担
仙都客户作为林、黄诸大姓的奴仆,不仅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更重要的是这些客户数百年来一直遭受十分残酷的人身奴役。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农忙农闲,都必须服从大姓主家的役使,长年为大姓主家承担各种劳役。
仙都客户所承担的各种劳役,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固定劳役;二临时差派。根据我们对仙客户以及大姓等多方面的调查综合,解放前仙都客户于每一年之中所承担的固定劳役。
从上表可以看出,仙都每一客户于一年之间所服的固定劳役达六十天以上。所谓固定劳役,就是每年必做,变化不大的劳役。除此之外,众客户还得应付各大姓主家许多临时的派使,这种临时的派使,名目繁多。现将解放前仙都客户所承担的许多主要临时派使劳役。
类似以上的临时劳役,不仅名目繁多,难以细举,同时由于仙都的客户是各大姓闔族公共的奴仆,供大姓整族役使,而每一大姓皆多达数百户,甚至上千户,每一户都有役使客户的权力,而且这数百户大姓人家住地距离客户亦远近不等,远者达数十里,客户来回应付,疲于奔命,再加上各种不时的呼唤,如抬轿殓葬,散发请帖,接送宾客等等,是纷至沓来,穷于应付。因此,客户每年必须花费很多时间来承担劳役。据中圳大姓林氏的客户扬春时、林文佃等人估计,解放前每一客户为其大姓主家所服的临时劳役约有两个月以上。加上每一客户每年为主家大姓服两个多月的固定劳役,即是解放前仙都客户每年必须受到主家四个多月的人身奴役。
客户为了胜任大姓主家的各种役使,还得具备各种役使所必须的用具,如大姓主家外出乘轿,客户必须自备轿子并经常维修;春节来临,大姓主家要迎新去旧,客户必须准备好扫帚等打扫工具,为各主家拂尘;大姓主家遇有丧事,客户必须准备烧水及杠抬棺木的用具,同时还得备有一整套的麻衣丧服,随时供主家使用等等。
不仅如此,客户还得学会为主家服役所应有的各种技能。大姓主家红白大事,需要吹打奏乐,客户必须学会各种乐曲的吹奏,并经常练习不得疏废:大姓主家迎娶送嫁,客户眷属充当送嫁姆,要经常练习吉利话的顺口溜,唱到出口成章,不能有错,如新娘一到男家,送嫁姆就唱:“新娘到厝,买田建屋”,新娘拿起碗,送嫁姆就唱:“摸碗叮叮响,年年买好田”等等。客户的子女,自幼年时,也都必须跟随父母学习抬轿,殓葬,以及吹打陪嫁迎唱等等各种技能,使得客户的所谓“低贱行当”,世代相传,以保证大姓主家对于客户的奴役不致中断。
服劳役是仙都客户的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如上所述,每一客户于一年之中供大姓主家役使的时间长达四、五个月之久,客户对于大姓主家的任何呼唤差使,只能唯命是从,不能有半句怨言,稍有不遂主家之意,大姓主家可以任意惩罚痛打客户。据客户叶火旺回忆,他还在襁褓时,有一次大姓主家呼唤其父前往抬轿,其父身体偶有不适,未能及时前往,大姓主家追至楼仔底客户住处,将叶火旺家的棉被等家杂统统搬至仙都圩场,当众放火烧毁,并将叶火旺强行抢走,准备断其叶家香火。后经叶火旺父母苦苦哀求,多方陪罪,方将叶火旺领回。客户遭受大姓主家的各种惩罚,均不得争辩、反抗,同时冤屈亦无处伸诉。因为在解放以前的仙都一带,大姓主家对奴仆客户施用肉刑,似乎是一种自然之理,无人异议,这种现象说明了大姓主家对奴仆客户有着任意打骂的人身占有关系。
仙都大姓主家对奴仆客户的这种人身占有关系,除了强迫客户们世代为奴仆外,还规定客户的任何婚嫁关系,必须以不影响主家对其奴役得到延续为前提。客户们只要不是完全绝户,那么即使这一客户家庭有何变动,大姓主家对于他们的奴役权利也永远不变。如仓间客户廖三祠,其廖姓原为良村黄姓奴仆,对于良村黄姓有服役的义务,但廖三祠的母亲为先锋林姓的客户叶笑仔之女,叶笑仔独此一女而无男儿,此女许配廖三祠的父亲为妻后,先锋大队林姓主家强令将叶家对于林姓的服役义务,要一同嫁往廖姓,否则不准完婚,因此,从今以后,廖三祠一家不仅要承担原来良村黄姓主人的服役义务,而且还要为先锋林姓服役。这一例子说明仙都大姓主家对于客户的人身束缚是何等的严厉,又是何等的牢固。
三、仙都客户与主家的经济关系
仙都客户做为林、黄诸大姓的奴仆,每年必须为大姓主家承担大量的劳役;而作为交换条件,众客户一般可以种主家的田地,藉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仙都客户是各大姓通族的公共奴仆,他们并不专属于某人家庭,因此客户所耕种的土地,全部都是各大姓主家的族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仙都各大姓对于祠堂族田等设备及经营是十分注意的,每一大姓每一房派,都有相当数量的祠产、族田,每年祠产、族田的收入,由族中轮流的主祭人,即族主经理,作为本族、本房的一年四季祭祖扫墓,以及兴办族学等费用。而这些祠产、族田的收入,则是通过奴仆的耕种并勒取其劳动产品的相当部份而获得的。
仙都客户租种大姓主家族田而交纳的地租形式是相当特殊的,名义上是实行实物定额租制,计算方法习惯上算租谷不算亩,即客户租种大姓主家一亩地每年必须交纳十石租谷,那么这一亩地便称为十石租田,客户租种这块土地,便按这个定额交纳田租。解放前以至明清时期仙都通行的每石约折现在的六十市斤,这就是说,客户每租佃大姓主家一亩族田,每年规定须交纳六百市斤的租谷。我们曾对于四户客户的租佃情况做了典型调查,地租上的剥削情况。
仙都客户租种大姓主家的族田,实物定额租高达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二,轻者亦达百分之五十四,平均可达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一定额租是比较高的,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伪县政府整理的《中国行政区域资料调查表》记载,解放前华安县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地租情况是“其田租普通二分之一,如一亩每年可产二石,佃农应纳田租一石,半年盈余归佃农所得”。由此可知仙都客户租佃大姓主家的族田所交纳的地租额高于百分之五十。不过如果遇上荒年,有的主家大姓如良村黄姓等,亦可酌情减免若干租谷,这当然是大姓主家用以笼络客户的一种手段,同时亦带有主家豢养奴仆之意,这样就能使客户更加听从主家的役使。
众客户除了交纳租谷之外,每年还有收成的百分之四十归自己所有。从上表客户来看,这四个客户共有廿四人,租种族田共十九亩半,一年得剩余稻谷共六千七百八十斤,平均每人每年只有稻谷二百八十斤。但客户租种大姓族田,种子、耕牛、肥料、农具,以及其他农业成本均由客户自己负责,如果扣除这些成本费用,客户租种大姓主家的族田,每人每口只能获得二百斤左右的稻谷。
仙都客户租种大姓主家族田,虽然从名义上讲是实行实物定额租,也许客户初迁入仙都时实行过这种地租制,但从明中叶开始,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货币的大量流通,使仙都客户向大姓主家交纳的地租,开始从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种货币地租的征收办法是:原订的实物租的租额不变,即原订一亩交纳租谷十石仍为十石,将这十石租谷按市价折成货币交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市价不是一年的平均价格,而是按仙都圩上的最高价格为准。大姓主家每一圩日都派人前往打听市价,一旦某一圩日谷价高涨,大姓主家即通知各客户到圩场按此市价折纳货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仙都大姓主家与奴仆客户的租佃关系,既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出现了货市地租的形态,但同时又保留十分浓厚的超经济强制的残余因素。
这种以最高谷价折纳货币的做法,无形加重了对客户的地租剥削,使得客户一年辛勤劳动所得的剩余的部份更少了,因此,客户租种大姓主家的族田,一般只够维持三、四个月的生活,有的租额特别重的,如林文佃租种中圳林姓族田,租率达百分之七十二,他们每年所得的稻谷只够维持全家一个半月至二个月的生活。
仙都客户除了耕种大姓主家族田得到一点经济收入之外,在服劳役之中也可取得少许的酬劳。客户为大姓主家服各种劳役,其中大部份是无偿劳动,如拂尘、修脸、祭祖差役等,但也有一些劳役,得到主家的赏赐,以示豢养奴才之意。这种酬劳可分三种形式:一种是服役时主家供给饭食,如迎神赛会时,主家另备一小桌饭菜,供客户食用。若是大姓主家有婚嫁等大喜事,客户为之抬轿或充当送嫁姆,主家的饭食报酬又稍优厚,客户将新娘送到郎家后,轿夫到伙房洗脸擦脚,脱掉草鞋,穿上主家的布鞋,到专为他们设立的席筵上就餐,送嫁姆在新娘房陪同新郎,新娘吃十二碗,并喂新娘吃菜,每吃一碗菜,送嫁姆都要唱一句吉语。翌日早晨送嫁姆还要洗新郎、新娘的白底衫裤。因此解放前众客户有谚云:“送嫁抬轿贱,到厝酒肉便”。大姓主家对于客户服役的另一种酬劳形式是对抬轿、小殓、埋葬等劳务赏给一点小费,赏钱的多少,全由大姓主家决定,客户不得与之计较,唯有恭敬接受而已;还有一种酬劳是给少量土地耕种不收地租,如大地村客户刘锦山为大姓主家,长年看守坟墓,主人对他的酬劳是将坟地旁边的田地拨一亩给刘锦山耕种,收成全归刘所有,不必交租。以上这些大姓主家对于客户服役的酬劳虽然是相当微薄的,但也是客户借以维持生活的来源之一。
客户为了维持其低下的生活,还利用一些空余时间,出外为人佣工。前面我们讲过,仙都客户于一年之中必须为大姓主家服役四、五个月之久,客户租种主家的族田,一年种两季,亦得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样,客户于一年之中所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二个月,这一、二个月时间,大姓主家允许客户自由支配,各自外出寻找生路。因此,有的客户利用剩余时间到外乡抬轿。抬轿遂成了他们这一、二个月时间中谋生的重要手段。解放前华安一带每抬轿十里,工钱为六角,若是有人招雇,客户外出抬轿一日,一般可得一至二元工钱;有的客户利用剩余时间出外打短工。根据我们了解,仙都现存的客户,凡是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者,几乎都曾经打过短工。据客户林文细回忆,解放前客户打短工,工钱是六天一元,合米三斗三升,折为十九斤半,平均每一天的工钱是大米三斤一两。
为客商挑担,是客户利用剩余时间谋生的另一途径。华安县虽然地处山区,但福建南部最大的河流九龙江从龙岩、漳平等地横穿华安全境,向南流经漳州、石码入海,因此,明清时期华安县的商业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漳州、厦门沿海的盐、鱼等货物由九龙江逆水而上,运往龙岩州各县,而龙岩州各地的木材、纸、茶叶等货物亦顺九龙江而下,运至漳州、厦门等地,并转运出洋。这样,华安县的华崶、新圩等镇便成了这条商业运输线上的重要转运站,客商往来络泽不绝,货物搬运非常繁忙,据老人回忆“每天从早到晚,肩挑工人来回挑运货物,少者几百,多则上千”。于是仙都客户亦利用一些空闲时间,经常到华崶、新圩一带挑盐担纸,挣得一些脚钱。
虽然客户有支配自己剩余时间的权利,但由于身为奴仆,地位低下,客户每向他人抬轿、挑担、打短工时,雇主往往不能以平等合理的工钱相酬,客户亦多不敢与之计较。因此,客户利用这一、二个月剩余时间,外出谋生的收入,也还是相当微薄的,大致亦只能维持全家二、三个月的生活而已。这样就不能不迫使客户们经常陷于极度的贫困之中。
四、仙都客户的人口与婚姻情况
仙都的林、黄、刘、蒋、汤五大姓自明前期迁入定居之后,至今已繁衍二万人以上,而林、黄诸大姓隶属下的客户奴仆,虽然亦定居于仙都数百年之久,但到解放前夕,仙都各姓客户只剩有一百人左右。仙都客户的世系得不到正常的传衍,人丁逐渐减少,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客户在大姓主家的残酷剥削奴役之下,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生活极度贫困,使得数百年来客户始终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我们上面讲过,客户在大姓主家沉重地租和繁重劳役的多层剥削之下,虽然一年到头胼手胝足地辛勤劳动,但亦只能维持七、八个月的生活。有的甚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如下林田头客户周埋吓,解放前穷得晚上睡觉全家只能盖棕衣,治穷无术,周埋吓终成为饿殍。客户偶受风寒,无钱医治,只能任其逐日加重,坐以待毙。据仙都年老的客户回忆,仙都叶姓客户于清末本来也有一百余人,但在民国期间因发生鼠疫,死亡殆尽,至解放时只剩下三户。在正常年景里,客户的人口亦能稍微增加,但一迁凶年,饥荒疾疫,交相侵害,客户人口又急剧下降。数百年来,客户的后裔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幸存下来的。一般客户因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容易感染疾病以致身体衰弱,寿命短促。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凡遇到老年客户,大多是矮小消瘦,这是他们饱受辛酸的痕迹。
数百年来仙都客户传衍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婚姻权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客户们的婚姻选择范围极其狭窄。他们的主要通婚范围只有如下几种:
(一)在不同姓氏的客户之间进行通婚,这一现象在旧社会极为普遍。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存的仙都各姓客户中,他们相互之间大多有因通婚而形成的亲戚关系,如中圳客户叶火旺的姐姐嫁与先锋客户杨春水为妻,而叶火旺的母亲又是下林田头客户周民的女儿。仓间客户廖三祠的母亲娶自先锋叶姓客户,而中圳的客户杨家两兄弟之妻又娶自仓间的廖家。不过由于客户中成家的人不多,可供出嫁的女子自然很有限,因此有女儿的客户,一般喜欢采取招赘的办法,故在客户的相互通婚中,招赘比娶取更为普遍。
(二)与其他的贱民阶层相互通婚。在明清时期的华安一带,除小姓客户沦为大姓的奴仆之外,另外有一些民间所谓之“下九流贱民”,如无籍剃头匠、糊纸匠(为民间进行超度阴鬼,做法场等迷信活动,糊装各种纸厝、纸轿、纸人等)、乞丐等,这些贱民虽非专属于某家某姓的奴才,但他们因社会地位低下,屡为各大姓豪家所欺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与客户就能够经常来往,同苦乐,同呼吸,以至他们的儿女互相通婚。如大地村客户乐随,其弟娶仙都圩剃头匠之女为妻便是一例。
(三)收养童养媳。明清时期至民国,福建一带素有溺女、弃女之风,一般民户产男则养大,产女则多遗弃,于是有一些人贩,从远处各县贩来为其父母摈弃的幼女,到华安仙都一带出卖,价格比较便宜,同时,稍稍养大,又可成为家里的重要辅助劳动力,因此,仙都许多客户都愿意从人贩子那里买来幼女当童养媳或养女,待到长大成姑娘,便配与儿子为妻或招赘其他客户入门成亲。现在还健在的中圳楼仔底客户叶文的母亲,便是清朝末年人贩子从安溪一带贩来,为叶文的祖父所收养长大的童养媳。
仙都客户的婚姻虽然有以上三种来源,但由于本地的大姓及一般的编户齐民均不愿与之通婚,因此,客户的通婚范围仍然是十分狭窄的。同时,客户的经济状况十分恶劣,也使得他们不能进行正常的嫁娶。大凡婚嫁,总须费一笔钱银,但许多客户连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又那有钱银进行婚嫁呢,从我们的调查材料看来,客户中成年男丁因贫难娶,孤独一生的十分普遍。结果人口的繁殖率比一般人低得很多。继嗣香火往往是单线独传,甚至成为绝户的各所在都有。中圳楼仔底客户林文佃一家五代的婚姻情况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现将林文佃一家四代的婚姻并继嗣状况。
林文佃②祖先原是漳浦县林姓,自明代迁居华安仙都,传至林文佃为第十九代,故林文佃的祖父辈应为第十七代,兄弟三人。
第十九代(已解放)
至今全家共有男丁五人,亦即从漳浦林姓迁入仙都为人当奴仆后,传至十九代,历时数百年,经过解放后三十余年的发展,才由一男丁恢复至五男丁。
从上列的客户林文佃四代婚姻传衍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大姓主家对于客户婚姻权利的严格限制下,客户的通婚范围极其狭窄,这就使得客户的许多男丁得不到正常的婚配,终身孤苦伶仃,谈不上所谓“瓜瓞之绵绵”。
综上所述,大姓主家对于客户奴仆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以及对于客户婚姻权利的限制,这是造成客户人口经数百年而无所发展的两大重要原因。我们从其他省外地区的蓄奴情况看来,明清以来以至民国,这些地区奴仆的数量之所以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奴仆的反抗斗争而摆脱奴籍;有清朝雍正年间解放奴婢身份法令的作用等等。但仙都客户数量减少的原因却是例外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仙都客户之所以沦为奴仆,是由大姓宗族封建暴力统治造成的产物。因此,在宗法势力稳固的华安仙都一带,清朝政府有关解放奴仆身份的法令,是很难冲越宗族势力的藩篱,而恩及大姓严格控制下的客户的,其次,在仙都,客户是隶属于整个大姓家族的公共奴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奴仆们不能进行丝毫的反抗,因为客户若有稍微反抗,必将遭到大姓阖族的镇压,因此,自明代客户沦为奴仆以来,仙都始终未能发生过任何的反抗斗争。
五、仙都客户是奴仆而不是佃仆③
上面我们对于仙都客户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婚姻情况、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前仙都各大姓主家属隶下的客户是一种奴仆,是中国奴隶制的严重残余。
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的封建法律和传统观念上,凡是具有“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这三个特点的人,都被划入奴仆类。近年来,有不少同志对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徽州及其他许多地区各种奴隶制残余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具有“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奴仆”,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家族农奴性质的佃仆而不是奴仆。从仙都的情况看,仙都客户同样具有“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的特点,但我们认为这些客户是比佃仆处境更为恶劣和低下的“贱民”,他们与各大姓主家有相当明确的主仆名份,他们受到各大姓主家的任意奴役、敲榨,他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妻子女儿随时有被大姓主家欺凌霸占的可能。这些情况说明了大姓主家,对于隶属于他们的奴仆客户,具有相当程度的人身占有特权,而人身占有特权正是奴隶制最重要的原则。
坚持奴仆是典型的农奴,而不是奴隶的同意,还认为奴仆与家内奴仆,有明显的区别,而不能把这二者混同起来。但我们从仙都客户所被奴役的各种劳役情况来看,仙都客户恰恰是“奴仆与家内奴仆混同起来”的一种贱民,带有严重的家内奴仆的特点。
从我们下面罗列的仙都客户所服劳役的情况表中看,客户所服劳役的一部份,如抬轿、守坟、治葬、祭祖、守粮仓、吹打等,这些劳役与徽州的“佃仆”所服的劳役基本相同,这种劳役,当然很难说带有家内奴仆的性质。但仙都客户对于大姓主家所服的劳役还远不止于此,其他如过年时为大姓主家挨户拂尘,客户眷属为主家大姓,每个成年妇女修脸拔毛,充当送嫁姆等,这些劳役毫无疑义是家内奴仆应干的差使。对于这些劳役,我们在实地调查过中,曾经仔细地访问了大姓主家的有关人员及曾经服过此役的客户,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仙都大族阖族多达数百户,一、二千人,而在解放前夕,幸存的客户极为有限,举林姓为例,林姓通族为二、三千人,七、八百户,而为之服役的客户只有六、七户,人口不过三、四十人,而每逢过年之时,六、七户客户的十来名男丁,必须为大姓全族七、八百家拂尘,假如要认真拂尘打扫的话,一个客户男丁一天大致只能清理一家,那么七、八百户大姓主家,十来名客户男丁势必打扫七、八十天才能完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客户为大姓主家拂尘,大半带有象征性质,即刻每家每户的大厅,用扫帚拂扫清浩即当完事。客户之所以如此应付,并不是客户带有抗拒怠工之意,也不是主家特有的恩典,据双方当事人说,大姓主家之所以要客户为主拂尘,主要目的还不在于真正清理卫生,而是在于从传统观念上讲,客户是大姓的奴仆,必须为各主家拂尘,以示奴才服待主人之意。又如五月端午节时,客户眷属务必为大姓主家各妇人修脸拔毛,修脸是相当细致的活,假如认真从事,大姓阖族上千名妇人,几个客户眷属,亦恐非二、三个月不能完事,但实际上只用五天时间,即五月初一日至五月初五日,可见,这种修脸仍然是一种象征性质的服役,客户眷属为大姓妇人修脸,表示大姓主家有奴婢使唤。其他如当送嫁姆等劳役,都带有服侍主人的意思。毫无疑问,大姓主家强迫各客户承担以上劳役,完全是从家内奴仆,家内奴婢这一观念出发,带有家内奴仆的性质,因此,我们说,仙都客户是一种比佃仆更为低贱的奴仆。
当然,仙都客户具有某种独立性,可以支配自己的剩余时间,有个体的家庭经济,(虽然这种家庭经济是非常贫困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做为奴仆的身份,因为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以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我们怎能要求奴仆与奴隶社会的奴隶完全一样呢!(其实在奴隶社会里,中国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亦各有其特点),因此,封建社会晚期的奴仆,比起奴隶社会的奴隶,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必然的,更何况封建社会晚期的奴仆仅仅是奴隶制度的残余,而並不是完整的奴隶社会,这一点也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
总之,通过这次实地调查,我们弄清楚了仙都客户的人身,在相当程度上被大姓主家所占有,而大姓主家在一定意义上,又把他们当家内奴仆看待,因此,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前,仙都的客户只能是奴仆,而不是佃仆。
附注
注解:①我们对于仙都蓄奴的调查,得启发于黄仲琴教授于民国十七年“民俗周刊”第一期所发表的“仙都之蓄奴”一文,故本文仍沿用“蓄奴”一词,意为“收养奴仆”。
②中圳林姓所属客户林文佃等,虽与其主家同姓,然并非同族,乃明前期自漳浦迁进中圳而被迫论为客户者。
③佃仆,即佃田之仆,是一种社会地位比佃农更为低下,封建依附关系较强的农奴。佃仆与地主有主仆名份,没有脱业和迁移的自由,既受到封建地主的地租剥削,又受到封建地主的劳役剥削。但佃仆又不同于家内奴婢一般不承担主家的服役义务。关于明清时期佃仆制问题,可参看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等著作。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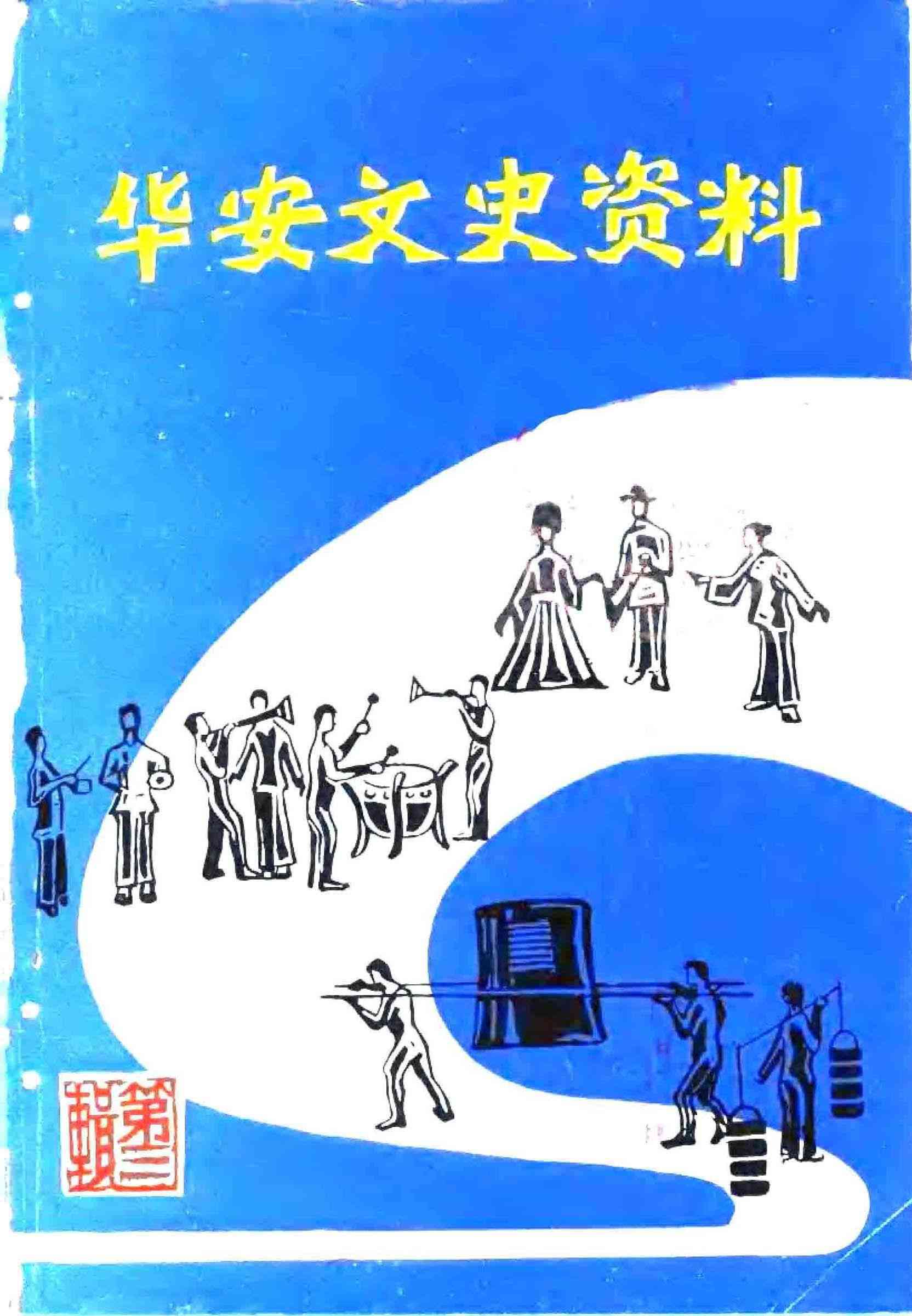
《华安文史资料第三辑》
本书共分五节:一、蓄奴的起源及客户的社会地位;二、仙都客户的劳役负担;三、仙都客户与主家的经济关系;四、仙都客户的人口与婚姻情况;五、仙都客户是奴仆而不是佃仆。另附仙都之蓄奴。
阅读
相关地名
华安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