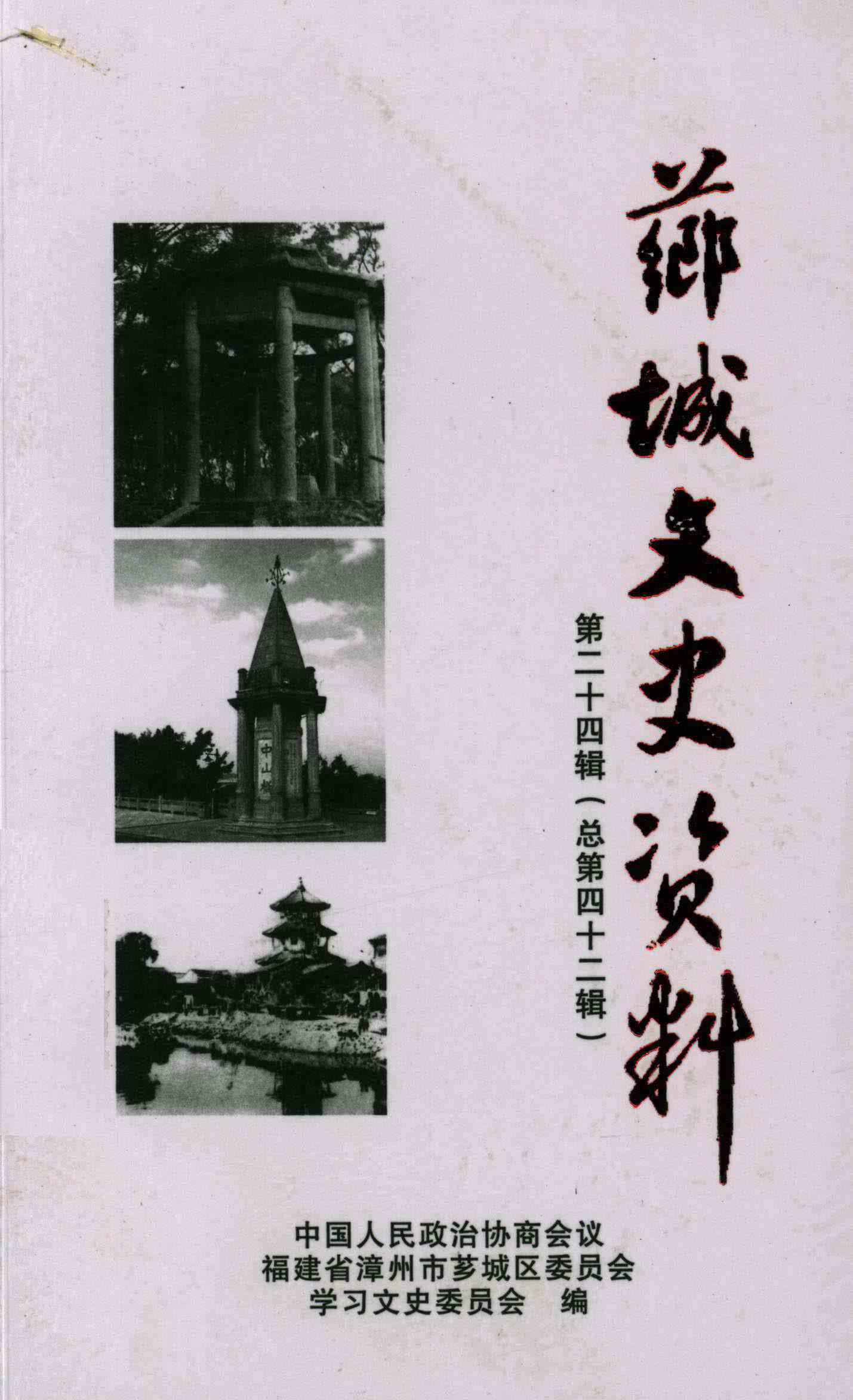文革残忆
| 内容出处: | 《芗城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5878 |
| 颗粒名称: | 文革残忆 |
| 分类号: | D652 |
| 页数: | 11 |
| 页码: | 80-90 |
| 摘要: | 1967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丁未年的正月初一,不满20岁的我,走在去井冈山、韶山的路上。那个时候,我身着绿色的解放军旧军装,头戴旧军帽,脚踏旧军鞋,腰挎旧军包,背上,还背了个旧军被包。那个时候,天阴沉沉的,下着雨,不是单纯的雨,是雨加冰,寒风夹着冰碴,打在脸上,钻心痛。这条通往井冈山的公路,没有其他行人,只有我们这一支红卫兵队伍。我们打着红旗,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司机向我们敬个军礼,把车子开走了。从于都到赣州,大约下午5点多,冬季日短,夜色业已降临。扑灭山火下山,已经是黎明时分。回想45年前的“长征”,是精神上的一种寻找,一种追求。 |
| 关键词: | 漳州 芗城区 文革残忆 |
内容
大串联记忆:我走在上井冈山的路上
秦河
1967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丁未年的正月初一,不满20岁的我,走在去井冈山、韶山的路上。那个时候,我身着绿色的解放军旧军装,头戴旧军帽,脚踏旧军鞋,腰挎旧军包,背上,还背了个旧军被包。那个时候,天阴沉沉的,下着雨,不是单纯的雨,是雨加冰,寒风夹着冰碴,打在脸上,钻心痛。
这条通往井冈山的公路,没有其他行人,只有我们这一支红卫兵队伍。我们打着红旗,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偶尔有军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把我们的红旗刮得哗啦啦地响,仿佛在为我们壮行。
在一个风口,一辆嘎斯(苏联产)军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司机从驾驶室探头说,红卫兵小将请上车吧,天太冷。我们说,不,我们要学习红军,用自己的双脚走上井冈山。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司机向我们敬个军礼,把车子开走了。
我们是在赣州过的除夕夜。从于都到赣州,大约下午5点多,冬季日短,夜色业已降临。我们是在一个机关的食堂里吃的年夜饭,吃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灯光朦胧,食堂正要关门,见我们来,师傅又特地为我们把饭菜热了一下。那时的红卫兵是很吃香的,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当今的大腕。吃过饭,我们还冒着寒风,走了赣州城,不是逛,是走,因为那时的赣州城没什么好逛的,宽广的街道上,除了昏黄的街灯,漆黑一片,只有澡堂门口亮着灯,从厚厚的棉布门帘往外冒着热气,把原本暗淡的灯光笼罩得扑朔迷离。
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在外地过年。我没想到我会在赣州过年三十,更没想到我20岁的春节会走在上井冈山的路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串联,先是乘火车,以后提倡步行。坐车走的是大城市,“串联点火,造反闹革命”;步行走的革命圣地,深入民间,学习革命传统。我们一行15人,有学生也有老师,打背包走路,一支名副其实的长征队。最初的计划是用半年的时间,从漳州走到延安。后来走两个月,到韶山,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便从湘潭转长沙返回。我们又是一支文艺宣传队,一路走一路表演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从漳州到湘潭,横跨三省,行程1000来公里,全靠“11号自行车”(时人对步行的戏称)。这是我这辈子走的最长的路。我们在芝山红楼红军进漳纪念馆前“誓师”,“行军”路线如下:漳州——适中——龙岩——古田——上杭——才溪——长汀——古城——瑞金——于都——赣州——遂川——井冈山——醴陵——湘潭——韶山。
沿途风光无限。在龙岩,印象最深的是闽西革命烈士碑,那么空旷的场所,那么高大的石碑,给我以震撼。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风过树林,涛声阵阵,仿佛烈士的英灵在呼唤,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在那里照了张相。面对相机,那个稚气未消的红卫兵心中鼓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情,以至45年之后,我依然能从画面上感受到当时的蓬勃朝气。途经上杭,我们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在县城大礼堂连演了三个晚上,第三天半夜,还参加了军方组织的扑灭山火。当时正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被叫醒,上了军车,就上山,就扑火,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危险。打火是临时学的,手执青树枝,顺风站,跟火走,边走边打。扑灭山火下山,已经是黎明时分。后来,我们在广播里听到,有一位来自延安的红卫兵小将在灭火中英勇牺牲了。
在上杭才溪乡光荣亭,我们照了张集体照。这是我们长征队唯一的一张合影。才溪乡在当时很有名气,1930年到1933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多次到才溪调查,写下著名的《才溪乡调查》,据说,当时才溪乡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总数的80%以上,被授予“才溪模范乡”。后来有“九军十八师”之称,即这里出了9个军长18个师长。1933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拨款在才溪乡圩坪盖了“光荣亭”,一年后被国民党烧毁。1956年重建,“光荣亭”三字由毛泽东亲笔题写。我们就是在有毛泽东手书的光荣亭前照的相。这张照片上的题字与我的记忆相对应,不仅让时间的座标从模糊走向清晰,而且让我回味当年的激情,对比当下的世态民情,恍如隔世。照片上的我们,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管是站着的还是蹲着的,无不手捧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脸虔诚。岁月的磨洗使照片上的我们斑驳难辨,题字却清晰可见:“毛泽东时代新红军漳州一中长征队才溪留影,六七.一.廿一。”这文字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我们当时心态的写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思维模式,平常人难以超越。由于十几年的禁锢,国人几乎与世界隔绝,我们很真诚地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生活如倒吃甘蔗,节节甜。而中国大陆之外,暗无天日。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人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于我们去解救。因此,我们必需学习红军的革命精神,把“长征”进行到底,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从长汀到瑞金,革命遗址众多,目不遐接。在长汀,记忆最深的是瞿秋白就义的街口。由于和鲁迅的友谊,瞿秋白给我留下美好的革命形象,他在长汀就义也是十分悲壮的。但当时流传着他被捕之后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便有人指责他是一个变节者。瞿秋白是我心中最早的复杂形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那个街口的,那时正值下雨。于是,那个凄风苦雨的街口一直在我的心中滞留了几十年。红都瑞金看的地方太多,反而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离开瑞金,我们来到于都,于都的渡口十分破旧,当年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突破国民党封锁线而开始万里长征的。我们在渡口放声歌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记不清走了几天才到遂川,我们打算从遂川上井冈山。到遂川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昏暗的“餐馆”里吃了一餐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晚餐。我们吃的是炒猪肝,5块钱的炒猪肝十几个人吃不完。红卫兵“长征”沿途都有接待站,管吃管住,住的大都是学校的教室或村里的祠堂,在地上或课桌上舖着稻草,草席和被褥是我们自带的。吃的大都是白米饭和水煮“菜头”(白萝卜)。米是新米,很香,水煮“菜头”只放盐,不见一星油花。一路走来,餐餐如此,天天如此,以至闻到萝卜味就呕水(吐酸水)。我们一边自我批判“娇生惯养”,不配当革命接班人,一边渴望油腥。一到城镇就迫不及待地“地主资产阶级”一回。遂川炒猪肝是记忆中最“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次。我们在遂川滞留了三天,因为有传言,说井冈山上由于人太多而流行乙型脑膜炎。犹豫再三之后我们还是上了山,山上一片清新,风光秀丽。传言使上山的人大大减少,我们很从容地在茨坪参观了两天。两天后,我们下山,去了韶山。
1967年正月的天空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阴沉而寒冷的。我在毛泽东故居前留影。尽管天空阴霾不展,但我的心中充满阳光,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那轮普照天下光芒万丈的红太阳就是从我的身后的那座不起眼的农舍升起来的。我没能记住此刻的具体日期,因为照片下“参观毛主席旧居韶山留影”后面的日期1967年之后字迹,已被时光蚀去。
从韶山往回走,我北望延安,心中充满遗憾。一年多前上映的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一句朗诵词一直在我的耳边回旋:“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向往着你啊,延安!”
回想45年前的“长征”,是精神上的一种寻找,一种追求。我们的心中迷漫着那个时代赋于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不再尘封的往事——漳州一中呐喊漫画组
吴明晖
在“文革”红旗猎猎造反有理的动乱岁月里,一拨学生凝聚在一位教师身边,以芝山山麓的漳州一中为起点,躲开派性远避武斗,他们挥动着手中的画笔,足迹遍布漳州城乡,投身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还相互间结下了深深情缘。数十年后,这段往事仍让这拨学生念念不忘,而那位风趣诙谐让人敬爱的李修煜老师,却早已作古了。
1966年,“文革”拉开序幕,这年年底的一天,正是漳州一中校园大操场早训时候,面对如火如荼的形势,一中美术教师李修煜与美术兴趣小组的学生黄启根筹划成立“漳州一中呐喊漫画组”。漫画组的任务是用美术宣传毛泽东思想,漫画组成员先后有十几名学生,他们是:黄启根、蔡绍瑜、张森、林琦锵、侯凯雄、蔡剑虹、蔡文忠、李哲文、李颖白、侯哲美、李文颖、王东黎、蔡丽芬、黄素华、余苏闽、吴玉丽等,黄启根任组长、张森任副组长。
当时“文革”正甚嚣尘上,却让漳州多了一处“桃花源”——漫画组成员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涉世未深,单纯天真,在李修煜老师的指导下,他们躲在漳州一中图书馆,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埋头于美术创作,画领袖肖像油画、写革命标语、抄毛主席语录、做展览会上的剪纸,将手头工夫锤炼得得心应手,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香饽悖”,部队、地方、企业、农村常常请他们去搞宣传、画壁画、写标语。
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却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漫画组的师生经常得忍饥挨饿、触风雨犯寒暑,却都能出色完成各种宣传任务。他们凭着对画画的自发性兴趣,热情高涨地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将青春汗水抛掷在这场看似遥遥无期的蹉跎时光里。李修煜老师是这个漫画组的凝聚核,“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在漫画组里俨然一介长者。在漳州一中师生们的记忆里,李修煜为人和蔼,与学生们亲密无间,师生间情谊融融。大概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风云变幻,李修煜对这场“革命”中的派性斗争打砸抢很反感,他只是不动声色地瞩咐学生安心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去参与人斗人的事情,不要去搞武斗。学生日后回忆,李老师似乎能洞察这场运动的表象,他曾经私下对学生讲:别看他们搞得气势汹汹,再过几十年会倒霉的。当年的语文老师洪锡金对李修煜印象深刻,他觉得李老师专业好、指导能力强,学生们很乐意受他调教。正是因为有了李老师的告诫引导,一种重业务探讨的健康氛围始终在漫画组氤氲流动着,学生们远离了运动的喧嚣,专心地在小团体里搞创作,他们誊刻蜡版印制歌曲本、宣传册、毛主席诗词。漫画组在“文革”中还曾经庇护了马海髯先生,让这位在运动中被错批的革命前辈到漫画组里帮忙抄写书法文字,暂时免去了批斗的折磨。
这是一次次没有物质回报的投入,未来的风险无从投保,满腔的激情却急需释放。宣传创作其实蛮辛苦,经常弄得满身油漆,有一餐没一顿的,有时因为缺颜料还得土法自制。宣传创作还时有危险和不测发生。组长黄启根在角美解放军某部画壁画,有一次得搞定一片三层楼高的墙壁,启根站在脚手架上画得入神时后脚踏空,幸有腰间保险链索拉住才免失足摔伤。创作中还曾遭遇“暗箭”来袭,学生李颖白为一中的墙壁画毛主席像,有人举报她画的葵花十二瓣象国民党“青天白日”党徽,这事事涉政治,可吓人不轻,还好颖白及时更改了葵花的花瓣数才躲过这一劫。
一中漫画组前后延续了八九年时间,象个无形的纽带聚拢着师生们,即便在上山下乡时,漫画组成员被分置到长泰各村搞宣传,他们仍能不时聚集到长泰县城接受宣传任务搞创作,见面时总是其乐融融。一中漫画组成员的李哲文、李文颖、李颖白是兄妹,亲情因为这个小团体的生活而扩展了外延,日后,李文颖与另一个漫画组成员蔡绍瑜结成连理,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中漫画组也是播种机,将人生的轨迹引向命运的四面八方,后来漫画组成员都各有所成,供职于市、区的机关、文化教育、企业等部门单位,漫画组组长黄启根则一根筋走到底,成了全国知名画家。
1980年,李修煜老师病逝。漳州知名画家林育培为李修煜绘制了素描遗像,悼念活动在漳州一中大礼堂进行,现场师生云集,盛况感人。今年盛夏里,一中漫画组成员小聚于中山公园里的漳州画院,他们动情地回忆:没有李修煜老师,就没有漳州一中漫画组。
【漳州方言】
酒〓
早年有一首很有名的闽南语歌曲叫《酒干倘卖无》。歌词中的“酒干”指“酒瓶子”。说实在的,是天大的错误,用一字与“瓶子”毫无相关的“干”字来指代,是违背了汉字的“六书”原理的。
那闽南方言应用哪个字来作“瓶子”?窃以为“〓”字为是。“〓”,现代语音gān,《集韵》姑男切。与闽南方言音gān,求干切,完全相同。且据《集韵·覃韵》注:“〓,器敛口者”之释,即是指腹大口小的器皿,字义亦相同。实际应用上,也可用“瓶”字。“瓶”,现代语音píng,《广韵》薄经切。其闽南方言音gān,正是方言文读音pān的音转。
长期以来,闽台两地多以“矸”做为“瓶子”的方言用字,这是一种误用。“矸”有多种字音和字义,唯独不具备“瓶”的含义。方言用“矸”是典型的表音字。
⊙李竹深
秦河
1967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丁未年的正月初一,不满20岁的我,走在去井冈山、韶山的路上。那个时候,我身着绿色的解放军旧军装,头戴旧军帽,脚踏旧军鞋,腰挎旧军包,背上,还背了个旧军被包。那个时候,天阴沉沉的,下着雨,不是单纯的雨,是雨加冰,寒风夹着冰碴,打在脸上,钻心痛。
这条通往井冈山的公路,没有其他行人,只有我们这一支红卫兵队伍。我们打着红旗,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偶尔有军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把我们的红旗刮得哗啦啦地响,仿佛在为我们壮行。
在一个风口,一辆嘎斯(苏联产)军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司机从驾驶室探头说,红卫兵小将请上车吧,天太冷。我们说,不,我们要学习红军,用自己的双脚走上井冈山。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司机向我们敬个军礼,把车子开走了。
我们是在赣州过的除夕夜。从于都到赣州,大约下午5点多,冬季日短,夜色业已降临。我们是在一个机关的食堂里吃的年夜饭,吃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灯光朦胧,食堂正要关门,见我们来,师傅又特地为我们把饭菜热了一下。那时的红卫兵是很吃香的,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当今的大腕。吃过饭,我们还冒着寒风,走了赣州城,不是逛,是走,因为那时的赣州城没什么好逛的,宽广的街道上,除了昏黄的街灯,漆黑一片,只有澡堂门口亮着灯,从厚厚的棉布门帘往外冒着热气,把原本暗淡的灯光笼罩得扑朔迷离。
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在外地过年。我没想到我会在赣州过年三十,更没想到我20岁的春节会走在上井冈山的路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串联,先是乘火车,以后提倡步行。坐车走的是大城市,“串联点火,造反闹革命”;步行走的革命圣地,深入民间,学习革命传统。我们一行15人,有学生也有老师,打背包走路,一支名副其实的长征队。最初的计划是用半年的时间,从漳州走到延安。后来走两个月,到韶山,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便从湘潭转长沙返回。我们又是一支文艺宣传队,一路走一路表演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从漳州到湘潭,横跨三省,行程1000来公里,全靠“11号自行车”(时人对步行的戏称)。这是我这辈子走的最长的路。我们在芝山红楼红军进漳纪念馆前“誓师”,“行军”路线如下:漳州——适中——龙岩——古田——上杭——才溪——长汀——古城——瑞金——于都——赣州——遂川——井冈山——醴陵——湘潭——韶山。
沿途风光无限。在龙岩,印象最深的是闽西革命烈士碑,那么空旷的场所,那么高大的石碑,给我以震撼。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风过树林,涛声阵阵,仿佛烈士的英灵在呼唤,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在那里照了张相。面对相机,那个稚气未消的红卫兵心中鼓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情,以至45年之后,我依然能从画面上感受到当时的蓬勃朝气。途经上杭,我们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在县城大礼堂连演了三个晚上,第三天半夜,还参加了军方组织的扑灭山火。当时正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被叫醒,上了军车,就上山,就扑火,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危险。打火是临时学的,手执青树枝,顺风站,跟火走,边走边打。扑灭山火下山,已经是黎明时分。后来,我们在广播里听到,有一位来自延安的红卫兵小将在灭火中英勇牺牲了。
在上杭才溪乡光荣亭,我们照了张集体照。这是我们长征队唯一的一张合影。才溪乡在当时很有名气,1930年到1933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多次到才溪调查,写下著名的《才溪乡调查》,据说,当时才溪乡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总数的80%以上,被授予“才溪模范乡”。后来有“九军十八师”之称,即这里出了9个军长18个师长。1933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拨款在才溪乡圩坪盖了“光荣亭”,一年后被国民党烧毁。1956年重建,“光荣亭”三字由毛泽东亲笔题写。我们就是在有毛泽东手书的光荣亭前照的相。这张照片上的题字与我的记忆相对应,不仅让时间的座标从模糊走向清晰,而且让我回味当年的激情,对比当下的世态民情,恍如隔世。照片上的我们,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管是站着的还是蹲着的,无不手捧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脸虔诚。岁月的磨洗使照片上的我们斑驳难辨,题字却清晰可见:“毛泽东时代新红军漳州一中长征队才溪留影,六七.一.廿一。”这文字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我们当时心态的写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思维模式,平常人难以超越。由于十几年的禁锢,国人几乎与世界隔绝,我们很真诚地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生活如倒吃甘蔗,节节甜。而中国大陆之外,暗无天日。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人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于我们去解救。因此,我们必需学习红军的革命精神,把“长征”进行到底,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从长汀到瑞金,革命遗址众多,目不遐接。在长汀,记忆最深的是瞿秋白就义的街口。由于和鲁迅的友谊,瞿秋白给我留下美好的革命形象,他在长汀就义也是十分悲壮的。但当时流传着他被捕之后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便有人指责他是一个变节者。瞿秋白是我心中最早的复杂形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那个街口的,那时正值下雨。于是,那个凄风苦雨的街口一直在我的心中滞留了几十年。红都瑞金看的地方太多,反而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离开瑞金,我们来到于都,于都的渡口十分破旧,当年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突破国民党封锁线而开始万里长征的。我们在渡口放声歌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记不清走了几天才到遂川,我们打算从遂川上井冈山。到遂川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昏暗的“餐馆”里吃了一餐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晚餐。我们吃的是炒猪肝,5块钱的炒猪肝十几个人吃不完。红卫兵“长征”沿途都有接待站,管吃管住,住的大都是学校的教室或村里的祠堂,在地上或课桌上舖着稻草,草席和被褥是我们自带的。吃的大都是白米饭和水煮“菜头”(白萝卜)。米是新米,很香,水煮“菜头”只放盐,不见一星油花。一路走来,餐餐如此,天天如此,以至闻到萝卜味就呕水(吐酸水)。我们一边自我批判“娇生惯养”,不配当革命接班人,一边渴望油腥。一到城镇就迫不及待地“地主资产阶级”一回。遂川炒猪肝是记忆中最“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次。我们在遂川滞留了三天,因为有传言,说井冈山上由于人太多而流行乙型脑膜炎。犹豫再三之后我们还是上了山,山上一片清新,风光秀丽。传言使上山的人大大减少,我们很从容地在茨坪参观了两天。两天后,我们下山,去了韶山。
1967年正月的天空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阴沉而寒冷的。我在毛泽东故居前留影。尽管天空阴霾不展,但我的心中充满阳光,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那轮普照天下光芒万丈的红太阳就是从我的身后的那座不起眼的农舍升起来的。我没能记住此刻的具体日期,因为照片下“参观毛主席旧居韶山留影”后面的日期1967年之后字迹,已被时光蚀去。
从韶山往回走,我北望延安,心中充满遗憾。一年多前上映的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一句朗诵词一直在我的耳边回旋:“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向往着你啊,延安!”
回想45年前的“长征”,是精神上的一种寻找,一种追求。我们的心中迷漫着那个时代赋于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不再尘封的往事——漳州一中呐喊漫画组
吴明晖
在“文革”红旗猎猎造反有理的动乱岁月里,一拨学生凝聚在一位教师身边,以芝山山麓的漳州一中为起点,躲开派性远避武斗,他们挥动着手中的画笔,足迹遍布漳州城乡,投身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还相互间结下了深深情缘。数十年后,这段往事仍让这拨学生念念不忘,而那位风趣诙谐让人敬爱的李修煜老师,却早已作古了。
1966年,“文革”拉开序幕,这年年底的一天,正是漳州一中校园大操场早训时候,面对如火如荼的形势,一中美术教师李修煜与美术兴趣小组的学生黄启根筹划成立“漳州一中呐喊漫画组”。漫画组的任务是用美术宣传毛泽东思想,漫画组成员先后有十几名学生,他们是:黄启根、蔡绍瑜、张森、林琦锵、侯凯雄、蔡剑虹、蔡文忠、李哲文、李颖白、侯哲美、李文颖、王东黎、蔡丽芬、黄素华、余苏闽、吴玉丽等,黄启根任组长、张森任副组长。
当时“文革”正甚嚣尘上,却让漳州多了一处“桃花源”——漫画组成员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涉世未深,单纯天真,在李修煜老师的指导下,他们躲在漳州一中图书馆,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埋头于美术创作,画领袖肖像油画、写革命标语、抄毛主席语录、做展览会上的剪纸,将手头工夫锤炼得得心应手,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香饽悖”,部队、地方、企业、农村常常请他们去搞宣传、画壁画、写标语。
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却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漫画组的师生经常得忍饥挨饿、触风雨犯寒暑,却都能出色完成各种宣传任务。他们凭着对画画的自发性兴趣,热情高涨地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将青春汗水抛掷在这场看似遥遥无期的蹉跎时光里。李修煜老师是这个漫画组的凝聚核,“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在漫画组里俨然一介长者。在漳州一中师生们的记忆里,李修煜为人和蔼,与学生们亲密无间,师生间情谊融融。大概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风云变幻,李修煜对这场“革命”中的派性斗争打砸抢很反感,他只是不动声色地瞩咐学生安心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去参与人斗人的事情,不要去搞武斗。学生日后回忆,李老师似乎能洞察这场运动的表象,他曾经私下对学生讲:别看他们搞得气势汹汹,再过几十年会倒霉的。当年的语文老师洪锡金对李修煜印象深刻,他觉得李老师专业好、指导能力强,学生们很乐意受他调教。正是因为有了李老师的告诫引导,一种重业务探讨的健康氛围始终在漫画组氤氲流动着,学生们远离了运动的喧嚣,专心地在小团体里搞创作,他们誊刻蜡版印制歌曲本、宣传册、毛主席诗词。漫画组在“文革”中还曾经庇护了马海髯先生,让这位在运动中被错批的革命前辈到漫画组里帮忙抄写书法文字,暂时免去了批斗的折磨。
这是一次次没有物质回报的投入,未来的风险无从投保,满腔的激情却急需释放。宣传创作其实蛮辛苦,经常弄得满身油漆,有一餐没一顿的,有时因为缺颜料还得土法自制。宣传创作还时有危险和不测发生。组长黄启根在角美解放军某部画壁画,有一次得搞定一片三层楼高的墙壁,启根站在脚手架上画得入神时后脚踏空,幸有腰间保险链索拉住才免失足摔伤。创作中还曾遭遇“暗箭”来袭,学生李颖白为一中的墙壁画毛主席像,有人举报她画的葵花十二瓣象国民党“青天白日”党徽,这事事涉政治,可吓人不轻,还好颖白及时更改了葵花的花瓣数才躲过这一劫。
一中漫画组前后延续了八九年时间,象个无形的纽带聚拢着师生们,即便在上山下乡时,漫画组成员被分置到长泰各村搞宣传,他们仍能不时聚集到长泰县城接受宣传任务搞创作,见面时总是其乐融融。一中漫画组成员的李哲文、李文颖、李颖白是兄妹,亲情因为这个小团体的生活而扩展了外延,日后,李文颖与另一个漫画组成员蔡绍瑜结成连理,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中漫画组也是播种机,将人生的轨迹引向命运的四面八方,后来漫画组成员都各有所成,供职于市、区的机关、文化教育、企业等部门单位,漫画组组长黄启根则一根筋走到底,成了全国知名画家。
1980年,李修煜老师病逝。漳州知名画家林育培为李修煜绘制了素描遗像,悼念活动在漳州一中大礼堂进行,现场师生云集,盛况感人。今年盛夏里,一中漫画组成员小聚于中山公园里的漳州画院,他们动情地回忆:没有李修煜老师,就没有漳州一中漫画组。
【漳州方言】
酒〓
早年有一首很有名的闽南语歌曲叫《酒干倘卖无》。歌词中的“酒干”指“酒瓶子”。说实在的,是天大的错误,用一字与“瓶子”毫无相关的“干”字来指代,是违背了汉字的“六书”原理的。
那闽南方言应用哪个字来作“瓶子”?窃以为“〓”字为是。“〓”,现代语音gān,《集韵》姑男切。与闽南方言音gān,求干切,完全相同。且据《集韵·覃韵》注:“〓,器敛口者”之释,即是指腹大口小的器皿,字义亦相同。实际应用上,也可用“瓶”字。“瓶”,现代语音píng,《广韵》薄经切。其闽南方言音gān,正是方言文读音pān的音转。
长期以来,闽台两地多以“矸”做为“瓶子”的方言用字,这是一种误用。“矸”有多种字音和字义,唯独不具备“瓶”的含义。方言用“矸”是典型的表音字。
⊙李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