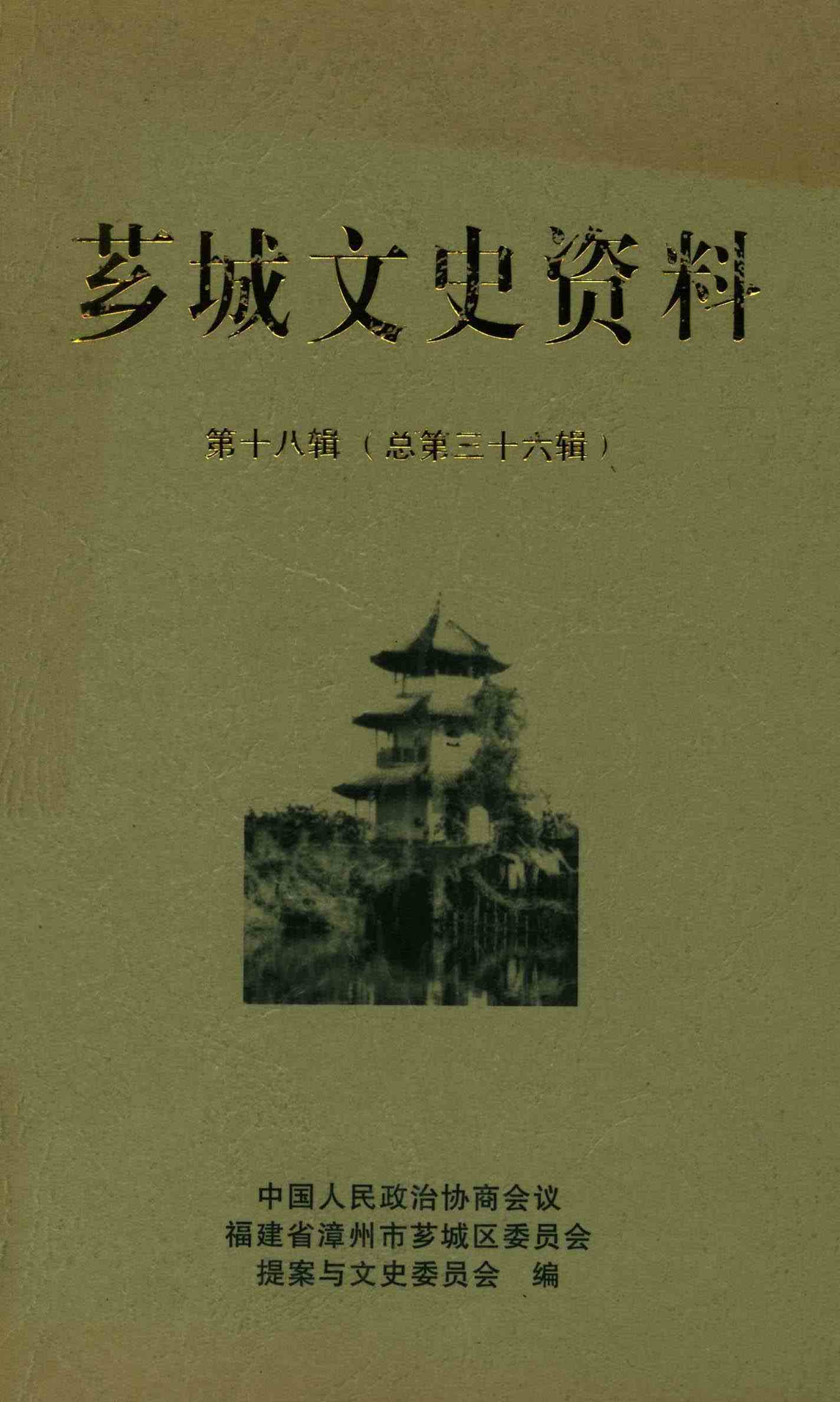邑人书架
内容
小巷深深 乡韵浓浓
——读张胡山《漳州事迹古今谈》
徐苍生
新近,有幸拜读漳州文史学者张胡山先生的《漳州事迹古今谈》一书,感受极深,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是一本集漳州历史、文化、宗教、民俗风情于一体的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史资料。
(一)漳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而古城已无迹可寻,要开启古城漫长的历史沧桑,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追寻和考究。胡山先生在浩瀚的古籍新志中寻觅,在古迹古诗词中校核,终于在书中为读者绘就了漳州古城的蓝图。其中历史事件,人物春秋,地方掌故,风物习俗,均可窥见一斑。
胡山先生在众多资料中,认真阅读,辨别真伪,去虚就实,综合整理,在书中为读者介绍漳州古城垣的千年嬗变:漳自唐建州后,一直是有署无城。至宋太宗“筑土为子城,周四里,辟门六”;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城外河沟竣,形成护城河;真宗大祥符六年(1013年),郡守王冕扩城周为十五里,围木栅为外城。一百廿一年后,郡守张成大折内土墙及外木栅,改建为土城垣,原护城河成了城内濠;至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太守赵汝譡将东城土墙改为石墙。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漳州太守江模、郡悴林有宗,一股作气把西南北三面土墙,全改建为石墙,城周三千丈,辟门七,城上建候亭、城楼、哨所,古城始现规模。至南宋年间(1249年),郡守章大任重修城门,增筑城背,铺设环城石路。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总制郡事官张理问将城垣缩小三分之一,重砌东西北三面石城,设四门。翌年,明师入闽,又增固城垣,建女墙雉堞1514垛,各门月城建城楼25座,城铺(兵房)23间,敌台、哨所数十间。清康熙八年(1669年),城上增设火药局18间,城防功能大为增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洪患,全城淹没。事后,在东门南侧(今水德宫附近)辟一水门,专供排泄城内洪水。而后,清末民初,城垣无重大改变。漳州古城的变化,张胡山以明快的笔调,层次分明的叙述,随历史延伸而展开。
书中云及,漳州古城垣毁于1918年粤军陈炯明驻漳,拆除城垣建马路,千年古城毁于一旦。残留100多米长的东城门城墙,亦于1996年10月,在旧城改造中拆除。历经千年的漳州古城垣至此片石不留。在旧城改造同时,东城门原址建新城楼,保留“文昌”楼古名,古味已随岁月逝去。胡山先生的这些记载饱含着他研究的心血。
(二)
胡山先生善于从文物古迹中,去发掘深层内涵,让一个个历史人物显露在读者面前。书中“台湾路觅唐风宋韵”、“修文路上史海钩沉”,以及“香港路千年话沧桑”、“两巷桥头论古说今”等等文章,不仅把漳州著名的历史名街、桥头古巷的人文景观,尽收书中,让读者一饱眼福。而且把那些早被历史尘垢深埋的废毁的古代名坊碑表,也发掘出来,展现给读者。如书中列举的位于旧府路口、现仅存石柱痕迹的明朝“五星聚奎坊”,这是为表彰尚书朱天球、林士章、戴耀、待郎卢维桢、石应岳等五位漳籍高官而建。这“五星”为官清正,勤政爱民,故立坊敬之。在卫前街,还有四座早毁坊表:一曰“柱史坊”;二曰“世勋坊”;三曰“大司成少宗伯坊”;四曰“进士坊”。胡山先生读志寻根,把这些已毁坊表的建置历史、纪念何人,有何功德,等等,一一人书上册,让读者知其然。
在漳州修文路的史海中,胡山先生从历史沉淀中,为读者钩起了许多早已尘封的角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面世。如漳州第一位名列进士的是唐周匡物,此君未第时已名声早誉,诗赋极佳,后仕至高州刺史,封建王朝为其立的“名第坊”,虽已毁,但其诗文仍有传颂者。再如建于东桥的“邦伯坊”,是明景泰年间为曾任池州知府的郭舒立。此公任内兴学劝农,省刑息讼,以忤直指,后致仕归,淡泊以终。在今区防疫站西侧,还有一座已毁碑坊和一座“王升祠”。坊叫“岳伯尉坊”,是为王升立。王升字日初,明永乐甲申年(1404年)进士,官至抚州知府,兴学重礼,曾捐俸赈救数千灾民,后因疾辞归,明王朝为其建祠立坊。王升的儿子王彝,天性至孝,其父病痢,为其尝粪,疾愈;其母目疾,为其舐目,目明;母患瘤,以口吮之,亦愈。父母逝后,墓侧守孝三年。现王升祠内还保有“孝子厅”,即为宣扬此君德行。
诸如此类人物,在胡山先生书中,不下几十位,活灵活现,让读者在浏览历史中,吸取有益的启示,古为今用。
(三)
文史资料是史学中的新学科,是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述贵在“三亲”(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胡山先生的书,许多文章体现了“三亲”特色,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漳州某一时期、某一行当、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比较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胡山先生曾经是一名颇有名气的记者、编辑,当过《大刀报》和《闽南新报》的总编,对漳州报业的内情,熟如手指。收入本书的《漳州辛亥光复后至建国前报刊通讯社概况》一文,就较全面、真实地记载了解放前三十多年间漳州报业状况。文章从清未朝廷通报政讯的《京报》说起,着重向读者介绍了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漳州报业的史实。据作者说,这期间,漳州(其中少量是郊县办的)共有地方报刊77家,期刊15家,通讯社7家.这些媒传行业,有官办、军办、党团办、民办、商办、校办等等。办报宗旨各异,良莠混杂,让人眼花瞭乱。作者在书中逐一列举了各报刊的兴衰史,让读者了解漳州媒传行业,在辛亥革命、民国期间、抗战时期,直至解放前夕的演变。比如,书中提到漳州最早的报纸诞生于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前四天(1911年11月7日),由同盟会员林者仁等四人创办,名曰《录各报要闻》。该报旨在鼓动反清起义,为漳州光复造舆论。此报就如当今的“报刊文摘”,其全部字数仅二千,新闻长者不超百字,短者只有九个字,颇具特色。它存在16天,出版16期,漳州光复后,完成使命停刊。可以说是开创漳州报业的首朵迎春花。
在众多媒体中,据胡山先生书中披露,时间最长的是《闽南新报》,该报前身为军队所办的《复兴报》,1934年9月创刊,1938年11月由漳州地方官接办,改为《闽南新报》。直至1949年9月漳州解放停刊。
漳州期刊始自1913年《漳州旬报》开篇,随后有1920年出版的,以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为内容的《自治》半月刊;有1927年创刊的以抨击恶行、宣扬建设“新社会”的《虚风月刊》;有1920年由龙溪通俗教育会主办的早期畅销刊物《通俗周刊》。此外,先后还有一些校办刊物,如漳州二师的《二师周刊》等等。
1928年成立、1930年停办的《闽南通讯社》,是漳州首家通讯媒传。小小漳州城,前前后后竟有《晨光通讯社》、《闽星通讯社》、《汀漳通讯社》等等七家。而历史较长的为官办《华声通讯社》,1941年10月10日开始发稿,供全国约220多家报社采用,至1948年10月停办。
胡山先生是漳州旧报业史话的见证人,他书中详述,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但他深考细究的严谨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让人钦佩起敬。
(四)
民俗学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意识的综合,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山先生用不少的篇章,再现了漳州传统的民俗风情,让人读了回味无穷。在《漳州岁节习俗与婚葬寿庆》、《漳州端午节及其习俗》等等文中,给读者了解漳州人过节的原汁原味,从正月初一的“新正”,到正月十五的“闹元霄”。几乎天天有喜庆。随后,他从二月的“花朝节”、“中和节”;三月的扫墓祭祖的“清明节”;四月的“浴佛节”;五月的“端午节”;六月的“半年节”;七月的“乞巧节”,亦称“少女节”、“中元节”(即俗称‘普渡’);八月的“中秋节”;九月的“重阳节”(今老人节);十月的“‘下元节”;十一月的“冬节”;亡直讲到十二月的“尾牙”、“送尪”(送神)、“除夕”等等过节的习俗新风,让人回味无穷。婚庆是人生一大事。在胡山先生笔下,旧社会明媒正娶,要经过许多繁杂礼俗,如今年轻人会觉得不可理喻,认为是在讲“古”。而历史的原汁就是那味,让人觉得相去已远,追回的也只是当“烂谷”丢弃,新的婚俗才是正码。
胡山先生对漳州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大加赞颂,而对某些封建的愚昧的劣俗,则不惜一笔加以批判。有一篇《求雨》的文章,说的是漳州1939年和1946年的两次大旱,田地龟裂,官民无策,惟有问天祁求降雨。当年,从伪县长到乡绅、组织农工商学名界,上千人群,按一定程序、路线,抬着神,去头冠,唱号念,在烈日下三步一拜,祁天降甘露。胡山先生当年亲历其景,他入木三分地指出求雨的是旧社会“不科学的愚昧习俗”,如今科学进步,水利丰泽人间,“求神降雨的封建迷信活动便绝迹了。”
(五)
收入《漳州事迹古今谈》的还有许多值得细读的好文章,如他以亲身经历,详述了抗战时期漳州人民的爱国行动,溶入了作者爱国之情。如在“抗战回忆”专栏里,他搜集整理出了市区及漳属各县遭日机狂疯滥炸的资料,列出了一笔笔统计数字,读了让人们对当年日寇的罪行无不愤慨。再如《抗战中漳州人民的几项爱国行动》、《万人狂欢胜利夜》、《抗战胜利后漳城三次灯谜征射盛况》、《抗战胜利后漳州人民抗双灾斗贪官二、三事》等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漳州人民的苦难、奋起和欢乐。
胡山先生从少年起就酷爱武术,是漳州“开元派”拳术嫡系传人之一。书中“武林逸事”专栏,详尽介绍了解放前漳州武林门派的源流和武林人物,还考证了海峡两岸武术源出一家,为研究漳州和台湾武林史迹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胡山先生的这本书,有极浓的地方色调。“人物春秋”、“地方掌故”、“寺庙史话”、“芗城风物”等等专栏,使读者了解了古城《三庵两院七桥亭》、《七阴八阳与九街十三巷》,以及古刹南山寺、比干庙、玄妙观等等宗教场所的史话,和芗城众多的古迹名胜的风物。对漳州旧地名的演变,作者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写出了《漳州城区旧地名采摭录》一、二、三,这对漳州旧城改造后,许多老街老巷已消失,老地方已不存在,无疑的是提供了很好的对照资料。
此外,漳州的名优特产、风味小吃也都上了书。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家乡的秀美和温馨,流露出的那种自豪和一片深情。
胡山先生在他居住的深巷中,行医从善几十年,他是个亦文、亦武、亦医的传奇老人。他有过辉煌的年代,也有过坎坷的岁月。正如漳州图书馆馆长张大伟先生在出版此书时,为其所写《杉巷尾内话沧桑(代序)》中所说,他“笔下流淌着人生沧桑,记载的可都是小城的掌故”。
张胡山先生是1920年出生的,其父是漳州知名中医,兼之文墨尚好,待人热情,家中常是“谈笑有鸿儒”之景象。其父经常借客为师,请来家作客的一些国学名师教习其子,故张胡山国学基础较胜于常人,其后教书、办报、写史均得益于幼时所学。胡山先生年轻时习医、习文兼习武,均有所造诣,花甲之年欣逢盛世,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又为其搭造平台,胡山先生满心喜悦,似有“老夫聊作少年狂”之态,发愤读书,深究古迹,细探文物,广泛调查,不辍笔耕,写出二十多万字文章。
小巷深深,乡韵浓浓,2006年春天,老先生无疾而终,安详谢世。我仅以此文向这位87岁老文史学者致以怀念和敬意。
漳州杉巷尾里的传奇
——记漳州市芗城区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张胡山先生
陈志宏
我是从市图书馆馆长张大伟赠送的漳州地方文献丛刊《漳州事迹古今谈》一书,才开始了解张胡山先生。老人笔下流淌的人生沧桑,记载的漳州古城掌故,深深地吸引了我。终于在一个细雨濛濠的清晨,我叫大伟先生带路在市区厦门路和青年路相交处一条鲜为人知的百米小巷“杉巷尾”见到张胡山老人。
老人的家是一栋二层旧楼。一楼临巷的厅堂,是老人每天坐堂门诊的地方。打过招呼,说明来意,在老人让座请茶之际,我环视厅堂的四周,只见一张简陋的桌子放着一大叠《闽南日报》,墙上挂着一张卫生管理部门出具的开业说明,和一幅马其宽教授书写的石鼓门书法条幅,没有一样陈设能够说明这是一个看病的场所,我的感觉就像是和邻居老大爷泡茶聊天的地方。
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满脸红光。他的体态,谈吐,一举手、一投足都非常敏捷,有“功夫人”的做派,见我一脸的惊奇,大伟偷偷告诉我,老人是漳州名拳师高复明的高徒,是漳州武术“开元派”的嫡系传人之一。
老人1920年出生,世居杉巷尾。在这条小巷里进进出出忙碌了大半个世纪,其亦文、亦医、亦武的传奇色彩,如同一本传奇故事,让我只能静静聆听他滔滔不绝的叙述。
他说自己少年时代,书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行医的父亲嗜爱好烟名茶,在家中品茗常客中,有杨遂庵、徐飞仙、陈鉴修、庄世光等四人,都是当年漳州文教界名流。有一次,父亲以“好茶要换‘浓痰涎’”为由“要挟”他们兼任儿子的家庭教师。从此,张胡山每天就有一位先生为自己讲授《古文观止》。当年在名师的培育下,打下的坚实国文功底,让他受用了一辈子。
上世纪四十年代经人介绍,张胡山先生在龙溪县立初级中学、漳州崇正中学任教员。恰少年风华正茂和当时热血青年一样,追求邹韬奋文风,常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直抒胸臆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因此,被聘为《大刀报》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厦门沦陷而转到漳州办报的文化人纷纷回厦,漳州报界人物一时出现真空状态,张胡山竟然同时出任《大刀报》和《闽南新报》两报的总编辑。
得“天时”、“地利”的他秉笔直书,写下“小人国漫游记”、“仁义猫”、“无底洞”等文章,对当时各阶层腐败现象给予揭发和抨击,引起不小的震撼。
抗战胜利不久,漳州水旱为灾,粮食歉收,米珠薪桂,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当时通过省党部主委陈肇英的背景来漳任龙溪县长的陈石不是体恤民情,为民排扰解难,而是趁此百业待兴的时机混水摸鱼,大发其不义之财,甚至胆大妄为,出卖乡镇长职位,每名要数十两至百两黄金,在重要水陆交通之处,设卡检查,从中牟取暴利。张胡山任总编的《闽南新报》对陈石欲私吞省府救灾用的3000担平价米一事,时有论评。陈石感到独吞平价米已无能为力,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分赃散罪的“金蝉脱壳”的办法,准备将平价米摊分到各机关社团去,答应以1000担平价米无偿地给党团和报社作补助费。党团、报社的头子,承诺即日停止发表揭发陈石劣迹的新闻。但《闽南新报》编辑部所有人员仍然穷追猛打,编排一组揭发稿准备重炮轰击。党团和报社的头子知道此事立即赶到排书房,勒令工人将揭发稿取出,换上其他新闻。因事出唐突,这伙人走后,字房工人漏夜通知了张胡山到字房定夺。张胡山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明知对自身安危有关,还是义无反顾,将揭发陈石所有罪迹的稿件全部发出。由于此事,张胡山不得不离开他所钟爱的新闻事业,他被解聘了。恼羞成怒的陈石还扬言要给他好看,以至以后一段时间,他出门,行医的父亲(同盟会会员)还跟在背后当“保镖”,恐有不测。直至1947年4月,由于漳州各界联合发出声明,公开列举陈石罪迹,陈石被迫调走,才告一段落。
由于时代变革,以张胡山的经历,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毫无疑问要在文化舞台上销声匿迹的,只能靠祖传医术行医济世,养家糊口。他写下的包括剧本、小说在内的数十万文字全部化为乌有。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过花甲的他先后受聘为市、区两级政协文史员、才又拿起笔,重操旧业,应邀为市、区两级政协文史部门和报刊撰写回忆文章。老人笔下,关于抗日回忆中的《万人狂欢胜利夜》、《日机疯狂滥炸漳属各县统计表》和《漳州武林逸事》等文章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史资料。1994年他被有关部门评为保护文物工作积极分子,1998年被评为漳州市芗城区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劳动得到社会的肯定,使老人焕发出极大的热情,至今还笔耕不缀,一直有新的作品面世。
采访结束了,当我离开这尾巴似的“杉巷尾”,回望倚在门口向我们招手话别的老文化人时,心想,旧城改造的铲车,也许不久就会将“杉巷尾”这个地名从漳州地图上抹去,但在小巷内生活了八十多年的老人的传奇故事,一定不会随时间流逝而被忘却的。
忆书法家魏宝贵先生
段冬寿
魏宝贵先生于八十多岁高龄离我们而去,我想写一篇回忆文章。每次坐在电脑前,眼前濛濛一片,手也显得笨拙,不知道怎么写下去。然而,一个老人,慈祥和蔼,不辞辛苦,默默无闻地耕耘于书墨里,那情景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于弱冠之年已闻魏宝贵的书法造诣,一直不敢登门拜访。也许是受他人误导,形成了一个印象:他是个老古板式,不易接近的人;更不要说,我字写得那么差,愧于同他交往。我到而立之年,萌发学篆刻的想法,郑玉水①很支持我,他说,你要打好篆书基础,魏宝贵石鼓文写的很好,你还是向他请教。我看过郑玉水临云开山竞秀
写的散氏盘,柔劲有力,飘逸萧洒,可是,他谦逊地退避三舍,劝我向魏老学习。
俗话说:“南门银”,可想而知,香港路是一条商业繁荣的地方,我走进魏家时,老人热情地走上前来和我握手。一种亲切感把我的疑虑、陈见全打消了。我也很惊讶,在一个充满市井气氛中,老人离世俗于书道之中,可想而知他处世何等超脱。
我们俩整整一辈之差,他把当作朋友,同好。他问我学过什么贴时。我想起他曾把一本《麻姑仙坛记》②(俗称“大字麻姑”)借给我一位朋友,就告诉他临过“大字麻姑”。
“你临哪个藏本?”他问我。
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在此之前,我接触过那些写毛笔字的人可谓有份量,他们说,“学上得中。”由此得知,临书要有好的字帖。最好是珂罗版。当时,一般人根本要不到。一位同好很幸运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郑玉水也有一本,他非常的珍惜,不轻易出示,我也偶然看到的。他生前忘记借给谁,曾问过我。一个那么珍爱自己藏品的人,除非好友,一般人是不借的。东西找不到时,自然想到我。到他千古也没想到,字贴借给一位权势者的儿子。这件事,我也是听一位朋友说的才知道。
魏老见我一点也没有版本学知识,不是嫌弃,而是耐心引导,他说“大字麻姑”较好的有南皮张之洞③,戴熙④二个藏本,尤以后者为佳。接着,他把二个版本的差别之处一一介绍。从这以后,我才懂得不同版本的暇疵。
在老人的指导下,我从石鼓文的基本知识学起,包括内容的考正,解释,版本等等。这些资料都是他借给我。他的为人跟别人家说的截然不同,并非“东西宝贝的要命,连看都舍不得。”
魏老生前完整临过石鼓“中权”本二通,一通在我手上。我把他的临本拿给郑玉水看,他也惊奇了。叫我把封面做好,还亲自题书签。
在我手上,有老人写的《岳阳楼记》小楷全文,一气呵成,字字稳重,力透纸背,明显带“张黑女”笔意,章法有序,可谓佳品。在我看过当今名藻书坛者,那种小楷怎能和他比?老人尤擅行楷,还特地另写一幅给我。
他说学篆刻,不但要写篆书作基础,临刻要从汉印入手。他在写的条幅上铃印,有三枚交替使用:一方“南州魏氏”,一方“宝贵之书”,一方“魏长年”。我误以为是马海髯⑤刻,我一次问他,他才微笑说是自己刻的。他从来不显耀自己,我也没听人家讲过他会篆刻。他用“汉印”入石,已到炉火纯青,闲熟自如之步。每一方印,平正而鲜丽,毫无板滞之弊。这样,同他的交往,我是书印兼得。
在同魏宝贵交往中,让我学的东西很多。没有学篆刻之前,我文字学知识有限,从汉字演成篆字,曾经摸不到头绪,只好去找他。老人把古文字跟现代的差异,如何索本寻源,一一讲得清楚透彻。
二十多年的来往,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成为挚友。每次到他家,一坐就是大半天,还舍不得走。每当我穿过那热热闹闹做生意的人群,一般人怎么会想到一个读书人,会在这种环境中坚持自己一块平静之地,看书写字。他是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选送到日本参展,并被收藏,在国内也广为收藏。现在所谓书家者,知道老人的书法成就有几人?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曾问过他所在单位的人,对方摇摇头,一点也不清楚。魏宝贵就是这样,他把艺术当作陶冶情操,以益身心健康的学习,练字之余也画国画,可惜所见太少。我回忆时,说起此事,他大女儿丽冬拿出一幅遗画。可见,老人对艺术的追求是多方面的。
他在病笃之时,还交代家人给我一件东西留念。我到他病塌前,他已处濒危之时,无法再说下去。具体什么东西,表达不出来,手只指着一个方向。我劝他好好养病。老人无力地摇头。他在为自己遗憾,没办法表达清楚。后来,我到他家,家里人说到这里,禁不住流泪。写到这里,我眼前一片模糊,泪水已盈眶,电脑屏幕上的字成了一个个小黑点,逐渐连成一片。老人生前待我那么好,我却不能给他做些有益的事!
老人走了!同我交往的书法界同好是这样的少,他们把学书法练字当作一种爱好,与世无争,默默临贴,写字。他们是我的老师,益友,前辈。当他们一一离我而去的时候,我内心无限悲伤,惋惜,将有何人与我同玩?以后,我在书法、篆刻上碰到问题向谁请教!
星岛漳人施香沱的艺术人生
施正渊
施香沱,字宏泽(1906—1990),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原称龙溪县)。他的著作有古装本《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施香沱书法》、《香沱印存》《香沱丛稿》,还有新加坡政府出资出版的《先驱画家施香沱的艺术世界》。2007年6月,新加坡先驱画家施香沱先生的儿子——年届七旬的施一般先生从新加坡回家乡漳州探亲,带其父遗著数部回来,送给几位亲友和漳州市图书馆。阅者翻开书页,粗略一览,即被书中水墨画佳作、行草篆隶的书法艺术及金石精品所吸引,爱不释手。施香沱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魅力?从施一般先生曾先后寄来《星洲日报》、《星洲画报》、《星加坡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南洋商报》……均屡屡报导施香沱书画金石杰出成就和各方评论及有关事迹,可看到大家对施香沱及其作品如何评价。
(一)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长郭建超先生著文评述,他说“在今日新加坡,水墨画的艺术传统得以持续,施香沱先生是新加坡水墨画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施香沱于1938年前往新加坡,1941年受聘新加坡美专讲师,1958年起又任南洋大学书画导师,长达三十一年,他在教学中从来不忘书画创作。1976年他被推选为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他的作品“新几内亚藤”一幅被选入新加坡国家画廊,列为国宝,显示他在新加坡的艺术地位
施香沱的绘画以南洋风格水墨画著称。南洋风格的中国画当时在新加坡画坛是一项创新,施香沱创作时常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审视东南亚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激起创作灵感,将具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事物入画,如多彩多姿的神仙鱼、舞翅蹁跹的天堂鸟,土著人的皮影戏……等等。使时代精神与南洋风格用传统画法在水墨画上表现出来。因此,郭建超先生及同仁都说:“施香沱堪称是南洋风格在水墨画这个领域中的先驱画家。”
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施香沱逃难到苏门答腊过着荷锄耕耘的山芭生活。在这三年里,他没有蹉跎岁月,耕作之外,他留心观察生活中的南洋独特风物。爬满昆虫的泥地像是元代水墨大家黄公望的泼墨;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和独特事物,如黄昏下的大蝙蝠、巨扇般的槟椰叶、章鱼足般的马九树……提供了来自生活的南洋特有色彩。以中国传统绘画手法突出“南洋”特色。不是更加令人感到亲切、鲜明、有地方印记吗?从此,他摸索创造被人赞赏的南洋画风,在中国画独树一帜。
日寇投降后,施香沱继续在新加坡美专任教,他十分重视“时代精神”和南洋风格在水墨画中的表现,在教学中,他常常带学生到植物园、飞禽公园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写生,积累画稿,过后他将画稿加工转为水墨画作品,这种独特的作画风格,他用来传授画艺,渐渐地形成了“香沱风”,也就是说形成了门下的一种作画流派。几十年来他栽培了数不清的水墨画、书法、篆刻人才,其中不乏艺坛的佼佼者。如高足黄崇禧、林万菁、黄明宗都是荣获博士学位的画家,有几批学生组织了墨澜社和啸涛书画研究会,相承老师的画风,常年举办美展。南洋美专学生和其他接受香沱先生熏陶的学生,自然地形成了举世瞩目、影响大的“施香沱派”,“施香沱派”正方兴未艾地发展。施香沱的门生及再传学子正在将他的艺术风格传播到可能传播的每个地方。施香沱先生确实无愧为华夏精英。
(二)
施香沱的书法,自小得益家学渊源。他出身漳州一户书香门第,二叔祖施调赓清末癸未进士,钦点翰林;三叔祖施槃同治甲戍朝考第一。两人都是书法名家。香沱之父施拱南也是名闻海内外的书法家、所以他从小就得到严格家学教导和熏陶。他自己具有天份,对习字有兴趣,能勤学苦练,因此年方弱冠,书写行草篆隶皆超过同窗学友。当时社会上向书法家施拱南求墨宝者甚多,遇到求字过急无法及时应给时,其父常命香沱代书,香沱的字使他人难辨真伪,以为出自拱南手笔,从此香沱初露锋芒。
后来,香沱书法钻研更深,历代重要碑帖无所不攻,一一临遍,尤其石鼓文及汉祀三公山碑,研习更有所得。新加坡评论家陈建坡先生说:“施先生精于石鼓八分,其石鼓深受吴昌硕的启发,然不为所囿,笔圆力饱,自出新意。八分则与齐白石一样出自汉祀三公山碑,沉稳浑拙,但没有齐白石那分野气。形成了他现在雄迈浑厚,古朴苍劲的风格。”新加坡美术馆馆长郭建超先生说:“香沱先生书写的行草如游龙,真隶如卧虎,篆籀如岳峙云亭,渊雅幽邃,都体现苍劲古朴的风格。香沱先生一贯强调作书一气呵成,笔笔有情,对‘行气’极重视,他每幅书法都贯彻他的书法思想。”《施香沱书法》篆隶行草造诣皆深。新加坡老一辈篆刻书法名家黄载灵老先生说:在新加坡施香沱的书法一流,尤其是篆书上的造诣,要是他认为第二,这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了。”
(三)
再谈篆刻。香沱先生的父亲施拱南是书法篆刻名家,还出版《荔香楼印存》。香沱从小目濡耳染和得到父亲亲自教导,怎么不成为出色的篆刻者。他深得浙、皖两派之长,创作既能循法度,又能突破陈规。对印的章法,讲究布局、讲究呼应、也讲究匀称,疏密得体,顾盼有情。从整体的美学效果来看,几乎是无懈可击、天衣无缝。他提出用刀如用笔,刻者必须先打好篆书的基础,才能窥其门径,还要经过长期探讨磨练,才能得其神韵。如果不懂写篆,就谈不上好的篆刻。同时,用刀技艺,求合乎规矩。《香沱印存》收入先生治的295方印章的印章作品,他的方寸世界追摹汉印,朱文圆劲秀丽,白文古拙大方,作品题材丰富而儒雅,风格古朴,给人一种味榄回甘的感觉。名篆刻家黄载灵老先生评曰:“香沱先生治印数十年,博取众长、不为皖、浙派所囿,更而上追秦汉,故所治印章能拙朴而无板滞、雄奇而不矫揉造作,秀逸雄浑古朴,有独自风格,盖其自得者深也。”
先驱画家施香沱先生萃绘画、书画、篆刻无一不精于一身,是不多见。他能够在画、题欺、印存三方面配合得天衣无无缝、浑然统一、格调又高,殊属难得。评论家赞其“书画金石共一炉,火候纯青见功夫。”
(四)
先驱画家施香沱先生在1976年至1981年担任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副会长期间,屡次举办和主持新、马高层美术家的各种类型的美术展,成绩斐然。1981年,他参加第二届国际书展并任主席团成员,是他艺术事业顶峰时期。他常常应邀到电台、院校、学术团体、训练班作专题演讲。他讲的“中国书法的学习”一文,被新加坡教育部收入《高中写作参考资料》。“怎样鉴赏彩墨画”的演讲,被新加坡电台录音在全国广播。他一生忘我浸泳墨池,勤于创作,精益求精、作品数量与质量不断取得新高峰的成就,他的作品多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展出,都受到各国艺术家的好评。1979年他应邀在日本名古屋、横滨举办篆刻书画展和当场作画,得到媒体很好评介与轰动。同年7月,国家派他为副团长率领新加坡文化考察团到我国访问,成为增进中新人民友谊和平使者之一。他载誉归来,新加坡总统薛尔斯以隆重仪式授予公共服务星章,表彰他对国家、对社会、对艺术的贡献。
1990年4月25日施香沱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5岁。南洋美专校友会,在8月于吉隆坡隆重举办“施香沱老师追思纪念遗作展”和“施香沱对新、马画坛的贡献”讲座。1991年6月,他的遗作参加新加坡中国书画名家展。1996年和1997年,遗作又参加国家美术馆主办的新加坡美术百年展和“先驱画家施香沱的艺术世界”的个人篆刻书画展,参观人士非常踊跃,《星洲日报》予醒目的版地报导,表达人们对他的艺术成就永恒敬仰和对他的深情怀念。
六十二年前《艺苑丛刊》漳州发行
艺苑丛刊社于民国卅年(1946年)元旦在厦门成立,四月一日由厦门迁漳州平等路七十五号。该社先后出版了《艺苑》丛刊五辑第一辑《诗歌与木刻》、第二辑《木刻与图案》、第三辑《小说与插图》、第四辑《音乐与附图》、第五辑《木刻挂联》。发行人兼主编人:艺苑丛刊社。总发行处大众文化出版社。第二辑木刻作者吴忠翰。该刊受到广大的读者群众的爱护和推祟。
——读张胡山《漳州事迹古今谈》
徐苍生
新近,有幸拜读漳州文史学者张胡山先生的《漳州事迹古今谈》一书,感受极深,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是一本集漳州历史、文化、宗教、民俗风情于一体的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史资料。
(一)漳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而古城已无迹可寻,要开启古城漫长的历史沧桑,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追寻和考究。胡山先生在浩瀚的古籍新志中寻觅,在古迹古诗词中校核,终于在书中为读者绘就了漳州古城的蓝图。其中历史事件,人物春秋,地方掌故,风物习俗,均可窥见一斑。
胡山先生在众多资料中,认真阅读,辨别真伪,去虚就实,综合整理,在书中为读者介绍漳州古城垣的千年嬗变:漳自唐建州后,一直是有署无城。至宋太宗“筑土为子城,周四里,辟门六”;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城外河沟竣,形成护城河;真宗大祥符六年(1013年),郡守王冕扩城周为十五里,围木栅为外城。一百廿一年后,郡守张成大折内土墙及外木栅,改建为土城垣,原护城河成了城内濠;至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太守赵汝譡将东城土墙改为石墙。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漳州太守江模、郡悴林有宗,一股作气把西南北三面土墙,全改建为石墙,城周三千丈,辟门七,城上建候亭、城楼、哨所,古城始现规模。至南宋年间(1249年),郡守章大任重修城门,增筑城背,铺设环城石路。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总制郡事官张理问将城垣缩小三分之一,重砌东西北三面石城,设四门。翌年,明师入闽,又增固城垣,建女墙雉堞1514垛,各门月城建城楼25座,城铺(兵房)23间,敌台、哨所数十间。清康熙八年(1669年),城上增设火药局18间,城防功能大为增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洪患,全城淹没。事后,在东门南侧(今水德宫附近)辟一水门,专供排泄城内洪水。而后,清末民初,城垣无重大改变。漳州古城的变化,张胡山以明快的笔调,层次分明的叙述,随历史延伸而展开。
书中云及,漳州古城垣毁于1918年粤军陈炯明驻漳,拆除城垣建马路,千年古城毁于一旦。残留100多米长的东城门城墙,亦于1996年10月,在旧城改造中拆除。历经千年的漳州古城垣至此片石不留。在旧城改造同时,东城门原址建新城楼,保留“文昌”楼古名,古味已随岁月逝去。胡山先生的这些记载饱含着他研究的心血。
(二)
胡山先生善于从文物古迹中,去发掘深层内涵,让一个个历史人物显露在读者面前。书中“台湾路觅唐风宋韵”、“修文路上史海钩沉”,以及“香港路千年话沧桑”、“两巷桥头论古说今”等等文章,不仅把漳州著名的历史名街、桥头古巷的人文景观,尽收书中,让读者一饱眼福。而且把那些早被历史尘垢深埋的废毁的古代名坊碑表,也发掘出来,展现给读者。如书中列举的位于旧府路口、现仅存石柱痕迹的明朝“五星聚奎坊”,这是为表彰尚书朱天球、林士章、戴耀、待郎卢维桢、石应岳等五位漳籍高官而建。这“五星”为官清正,勤政爱民,故立坊敬之。在卫前街,还有四座早毁坊表:一曰“柱史坊”;二曰“世勋坊”;三曰“大司成少宗伯坊”;四曰“进士坊”。胡山先生读志寻根,把这些已毁坊表的建置历史、纪念何人,有何功德,等等,一一人书上册,让读者知其然。
在漳州修文路的史海中,胡山先生从历史沉淀中,为读者钩起了许多早已尘封的角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面世。如漳州第一位名列进士的是唐周匡物,此君未第时已名声早誉,诗赋极佳,后仕至高州刺史,封建王朝为其立的“名第坊”,虽已毁,但其诗文仍有传颂者。再如建于东桥的“邦伯坊”,是明景泰年间为曾任池州知府的郭舒立。此公任内兴学劝农,省刑息讼,以忤直指,后致仕归,淡泊以终。在今区防疫站西侧,还有一座已毁碑坊和一座“王升祠”。坊叫“岳伯尉坊”,是为王升立。王升字日初,明永乐甲申年(1404年)进士,官至抚州知府,兴学重礼,曾捐俸赈救数千灾民,后因疾辞归,明王朝为其建祠立坊。王升的儿子王彝,天性至孝,其父病痢,为其尝粪,疾愈;其母目疾,为其舐目,目明;母患瘤,以口吮之,亦愈。父母逝后,墓侧守孝三年。现王升祠内还保有“孝子厅”,即为宣扬此君德行。
诸如此类人物,在胡山先生书中,不下几十位,活灵活现,让读者在浏览历史中,吸取有益的启示,古为今用。
(三)
文史资料是史学中的新学科,是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述贵在“三亲”(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胡山先生的书,许多文章体现了“三亲”特色,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漳州某一时期、某一行当、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比较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胡山先生曾经是一名颇有名气的记者、编辑,当过《大刀报》和《闽南新报》的总编,对漳州报业的内情,熟如手指。收入本书的《漳州辛亥光复后至建国前报刊通讯社概况》一文,就较全面、真实地记载了解放前三十多年间漳州报业状况。文章从清未朝廷通报政讯的《京报》说起,着重向读者介绍了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漳州报业的史实。据作者说,这期间,漳州(其中少量是郊县办的)共有地方报刊77家,期刊15家,通讯社7家.这些媒传行业,有官办、军办、党团办、民办、商办、校办等等。办报宗旨各异,良莠混杂,让人眼花瞭乱。作者在书中逐一列举了各报刊的兴衰史,让读者了解漳州媒传行业,在辛亥革命、民国期间、抗战时期,直至解放前夕的演变。比如,书中提到漳州最早的报纸诞生于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前四天(1911年11月7日),由同盟会员林者仁等四人创办,名曰《录各报要闻》。该报旨在鼓动反清起义,为漳州光复造舆论。此报就如当今的“报刊文摘”,其全部字数仅二千,新闻长者不超百字,短者只有九个字,颇具特色。它存在16天,出版16期,漳州光复后,完成使命停刊。可以说是开创漳州报业的首朵迎春花。
在众多媒体中,据胡山先生书中披露,时间最长的是《闽南新报》,该报前身为军队所办的《复兴报》,1934年9月创刊,1938年11月由漳州地方官接办,改为《闽南新报》。直至1949年9月漳州解放停刊。
漳州期刊始自1913年《漳州旬报》开篇,随后有1920年出版的,以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为内容的《自治》半月刊;有1927年创刊的以抨击恶行、宣扬建设“新社会”的《虚风月刊》;有1920年由龙溪通俗教育会主办的早期畅销刊物《通俗周刊》。此外,先后还有一些校办刊物,如漳州二师的《二师周刊》等等。
1928年成立、1930年停办的《闽南通讯社》,是漳州首家通讯媒传。小小漳州城,前前后后竟有《晨光通讯社》、《闽星通讯社》、《汀漳通讯社》等等七家。而历史较长的为官办《华声通讯社》,1941年10月10日开始发稿,供全国约220多家报社采用,至1948年10月停办。
胡山先生是漳州旧报业史话的见证人,他书中详述,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但他深考细究的严谨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让人钦佩起敬。
(四)
民俗学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意识的综合,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山先生用不少的篇章,再现了漳州传统的民俗风情,让人读了回味无穷。在《漳州岁节习俗与婚葬寿庆》、《漳州端午节及其习俗》等等文中,给读者了解漳州人过节的原汁原味,从正月初一的“新正”,到正月十五的“闹元霄”。几乎天天有喜庆。随后,他从二月的“花朝节”、“中和节”;三月的扫墓祭祖的“清明节”;四月的“浴佛节”;五月的“端午节”;六月的“半年节”;七月的“乞巧节”,亦称“少女节”、“中元节”(即俗称‘普渡’);八月的“中秋节”;九月的“重阳节”(今老人节);十月的“‘下元节”;十一月的“冬节”;亡直讲到十二月的“尾牙”、“送尪”(送神)、“除夕”等等过节的习俗新风,让人回味无穷。婚庆是人生一大事。在胡山先生笔下,旧社会明媒正娶,要经过许多繁杂礼俗,如今年轻人会觉得不可理喻,认为是在讲“古”。而历史的原汁就是那味,让人觉得相去已远,追回的也只是当“烂谷”丢弃,新的婚俗才是正码。
胡山先生对漳州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大加赞颂,而对某些封建的愚昧的劣俗,则不惜一笔加以批判。有一篇《求雨》的文章,说的是漳州1939年和1946年的两次大旱,田地龟裂,官民无策,惟有问天祁求降雨。当年,从伪县长到乡绅、组织农工商学名界,上千人群,按一定程序、路线,抬着神,去头冠,唱号念,在烈日下三步一拜,祁天降甘露。胡山先生当年亲历其景,他入木三分地指出求雨的是旧社会“不科学的愚昧习俗”,如今科学进步,水利丰泽人间,“求神降雨的封建迷信活动便绝迹了。”
(五)
收入《漳州事迹古今谈》的还有许多值得细读的好文章,如他以亲身经历,详述了抗战时期漳州人民的爱国行动,溶入了作者爱国之情。如在“抗战回忆”专栏里,他搜集整理出了市区及漳属各县遭日机狂疯滥炸的资料,列出了一笔笔统计数字,读了让人们对当年日寇的罪行无不愤慨。再如《抗战中漳州人民的几项爱国行动》、《万人狂欢胜利夜》、《抗战胜利后漳城三次灯谜征射盛况》、《抗战胜利后漳州人民抗双灾斗贪官二、三事》等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漳州人民的苦难、奋起和欢乐。
胡山先生从少年起就酷爱武术,是漳州“开元派”拳术嫡系传人之一。书中“武林逸事”专栏,详尽介绍了解放前漳州武林门派的源流和武林人物,还考证了海峡两岸武术源出一家,为研究漳州和台湾武林史迹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胡山先生的这本书,有极浓的地方色调。“人物春秋”、“地方掌故”、“寺庙史话”、“芗城风物”等等专栏,使读者了解了古城《三庵两院七桥亭》、《七阴八阳与九街十三巷》,以及古刹南山寺、比干庙、玄妙观等等宗教场所的史话,和芗城众多的古迹名胜的风物。对漳州旧地名的演变,作者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写出了《漳州城区旧地名采摭录》一、二、三,这对漳州旧城改造后,许多老街老巷已消失,老地方已不存在,无疑的是提供了很好的对照资料。
此外,漳州的名优特产、风味小吃也都上了书。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家乡的秀美和温馨,流露出的那种自豪和一片深情。
胡山先生在他居住的深巷中,行医从善几十年,他是个亦文、亦武、亦医的传奇老人。他有过辉煌的年代,也有过坎坷的岁月。正如漳州图书馆馆长张大伟先生在出版此书时,为其所写《杉巷尾内话沧桑(代序)》中所说,他“笔下流淌着人生沧桑,记载的可都是小城的掌故”。
张胡山先生是1920年出生的,其父是漳州知名中医,兼之文墨尚好,待人热情,家中常是“谈笑有鸿儒”之景象。其父经常借客为师,请来家作客的一些国学名师教习其子,故张胡山国学基础较胜于常人,其后教书、办报、写史均得益于幼时所学。胡山先生年轻时习医、习文兼习武,均有所造诣,花甲之年欣逢盛世,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又为其搭造平台,胡山先生满心喜悦,似有“老夫聊作少年狂”之态,发愤读书,深究古迹,细探文物,广泛调查,不辍笔耕,写出二十多万字文章。
小巷深深,乡韵浓浓,2006年春天,老先生无疾而终,安详谢世。我仅以此文向这位87岁老文史学者致以怀念和敬意。
漳州杉巷尾里的传奇
——记漳州市芗城区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张胡山先生
陈志宏
我是从市图书馆馆长张大伟赠送的漳州地方文献丛刊《漳州事迹古今谈》一书,才开始了解张胡山先生。老人笔下流淌的人生沧桑,记载的漳州古城掌故,深深地吸引了我。终于在一个细雨濛濠的清晨,我叫大伟先生带路在市区厦门路和青年路相交处一条鲜为人知的百米小巷“杉巷尾”见到张胡山老人。
老人的家是一栋二层旧楼。一楼临巷的厅堂,是老人每天坐堂门诊的地方。打过招呼,说明来意,在老人让座请茶之际,我环视厅堂的四周,只见一张简陋的桌子放着一大叠《闽南日报》,墙上挂着一张卫生管理部门出具的开业说明,和一幅马其宽教授书写的石鼓门书法条幅,没有一样陈设能够说明这是一个看病的场所,我的感觉就像是和邻居老大爷泡茶聊天的地方。
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满脸红光。他的体态,谈吐,一举手、一投足都非常敏捷,有“功夫人”的做派,见我一脸的惊奇,大伟偷偷告诉我,老人是漳州名拳师高复明的高徒,是漳州武术“开元派”的嫡系传人之一。
老人1920年出生,世居杉巷尾。在这条小巷里进进出出忙碌了大半个世纪,其亦文、亦医、亦武的传奇色彩,如同一本传奇故事,让我只能静静聆听他滔滔不绝的叙述。
他说自己少年时代,书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行医的父亲嗜爱好烟名茶,在家中品茗常客中,有杨遂庵、徐飞仙、陈鉴修、庄世光等四人,都是当年漳州文教界名流。有一次,父亲以“好茶要换‘浓痰涎’”为由“要挟”他们兼任儿子的家庭教师。从此,张胡山每天就有一位先生为自己讲授《古文观止》。当年在名师的培育下,打下的坚实国文功底,让他受用了一辈子。
上世纪四十年代经人介绍,张胡山先生在龙溪县立初级中学、漳州崇正中学任教员。恰少年风华正茂和当时热血青年一样,追求邹韬奋文风,常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直抒胸臆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因此,被聘为《大刀报》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厦门沦陷而转到漳州办报的文化人纷纷回厦,漳州报界人物一时出现真空状态,张胡山竟然同时出任《大刀报》和《闽南新报》两报的总编辑。
得“天时”、“地利”的他秉笔直书,写下“小人国漫游记”、“仁义猫”、“无底洞”等文章,对当时各阶层腐败现象给予揭发和抨击,引起不小的震撼。
抗战胜利不久,漳州水旱为灾,粮食歉收,米珠薪桂,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当时通过省党部主委陈肇英的背景来漳任龙溪县长的陈石不是体恤民情,为民排扰解难,而是趁此百业待兴的时机混水摸鱼,大发其不义之财,甚至胆大妄为,出卖乡镇长职位,每名要数十两至百两黄金,在重要水陆交通之处,设卡检查,从中牟取暴利。张胡山任总编的《闽南新报》对陈石欲私吞省府救灾用的3000担平价米一事,时有论评。陈石感到独吞平价米已无能为力,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分赃散罪的“金蝉脱壳”的办法,准备将平价米摊分到各机关社团去,答应以1000担平价米无偿地给党团和报社作补助费。党团、报社的头子,承诺即日停止发表揭发陈石劣迹的新闻。但《闽南新报》编辑部所有人员仍然穷追猛打,编排一组揭发稿准备重炮轰击。党团和报社的头子知道此事立即赶到排书房,勒令工人将揭发稿取出,换上其他新闻。因事出唐突,这伙人走后,字房工人漏夜通知了张胡山到字房定夺。张胡山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明知对自身安危有关,还是义无反顾,将揭发陈石所有罪迹的稿件全部发出。由于此事,张胡山不得不离开他所钟爱的新闻事业,他被解聘了。恼羞成怒的陈石还扬言要给他好看,以至以后一段时间,他出门,行医的父亲(同盟会会员)还跟在背后当“保镖”,恐有不测。直至1947年4月,由于漳州各界联合发出声明,公开列举陈石罪迹,陈石被迫调走,才告一段落。
由于时代变革,以张胡山的经历,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毫无疑问要在文化舞台上销声匿迹的,只能靠祖传医术行医济世,养家糊口。他写下的包括剧本、小说在内的数十万文字全部化为乌有。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过花甲的他先后受聘为市、区两级政协文史员、才又拿起笔,重操旧业,应邀为市、区两级政协文史部门和报刊撰写回忆文章。老人笔下,关于抗日回忆中的《万人狂欢胜利夜》、《日机疯狂滥炸漳属各县统计表》和《漳州武林逸事》等文章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史资料。1994年他被有关部门评为保护文物工作积极分子,1998年被评为漳州市芗城区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劳动得到社会的肯定,使老人焕发出极大的热情,至今还笔耕不缀,一直有新的作品面世。
采访结束了,当我离开这尾巴似的“杉巷尾”,回望倚在门口向我们招手话别的老文化人时,心想,旧城改造的铲车,也许不久就会将“杉巷尾”这个地名从漳州地图上抹去,但在小巷内生活了八十多年的老人的传奇故事,一定不会随时间流逝而被忘却的。
忆书法家魏宝贵先生
段冬寿
魏宝贵先生于八十多岁高龄离我们而去,我想写一篇回忆文章。每次坐在电脑前,眼前濛濛一片,手也显得笨拙,不知道怎么写下去。然而,一个老人,慈祥和蔼,不辞辛苦,默默无闻地耕耘于书墨里,那情景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于弱冠之年已闻魏宝贵的书法造诣,一直不敢登门拜访。也许是受他人误导,形成了一个印象:他是个老古板式,不易接近的人;更不要说,我字写得那么差,愧于同他交往。我到而立之年,萌发学篆刻的想法,郑玉水①很支持我,他说,你要打好篆书基础,魏宝贵石鼓文写的很好,你还是向他请教。我看过郑玉水临云开山竞秀
写的散氏盘,柔劲有力,飘逸萧洒,可是,他谦逊地退避三舍,劝我向魏老学习。
俗话说:“南门银”,可想而知,香港路是一条商业繁荣的地方,我走进魏家时,老人热情地走上前来和我握手。一种亲切感把我的疑虑、陈见全打消了。我也很惊讶,在一个充满市井气氛中,老人离世俗于书道之中,可想而知他处世何等超脱。
我们俩整整一辈之差,他把当作朋友,同好。他问我学过什么贴时。我想起他曾把一本《麻姑仙坛记》②(俗称“大字麻姑”)借给我一位朋友,就告诉他临过“大字麻姑”。
“你临哪个藏本?”他问我。
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在此之前,我接触过那些写毛笔字的人可谓有份量,他们说,“学上得中。”由此得知,临书要有好的字帖。最好是珂罗版。当时,一般人根本要不到。一位同好很幸运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郑玉水也有一本,他非常的珍惜,不轻易出示,我也偶然看到的。他生前忘记借给谁,曾问过我。一个那么珍爱自己藏品的人,除非好友,一般人是不借的。东西找不到时,自然想到我。到他千古也没想到,字贴借给一位权势者的儿子。这件事,我也是听一位朋友说的才知道。
魏老见我一点也没有版本学知识,不是嫌弃,而是耐心引导,他说“大字麻姑”较好的有南皮张之洞③,戴熙④二个藏本,尤以后者为佳。接着,他把二个版本的差别之处一一介绍。从这以后,我才懂得不同版本的暇疵。
在老人的指导下,我从石鼓文的基本知识学起,包括内容的考正,解释,版本等等。这些资料都是他借给我。他的为人跟别人家说的截然不同,并非“东西宝贝的要命,连看都舍不得。”
魏老生前完整临过石鼓“中权”本二通,一通在我手上。我把他的临本拿给郑玉水看,他也惊奇了。叫我把封面做好,还亲自题书签。
在我手上,有老人写的《岳阳楼记》小楷全文,一气呵成,字字稳重,力透纸背,明显带“张黑女”笔意,章法有序,可谓佳品。在我看过当今名藻书坛者,那种小楷怎能和他比?老人尤擅行楷,还特地另写一幅给我。
他说学篆刻,不但要写篆书作基础,临刻要从汉印入手。他在写的条幅上铃印,有三枚交替使用:一方“南州魏氏”,一方“宝贵之书”,一方“魏长年”。我误以为是马海髯⑤刻,我一次问他,他才微笑说是自己刻的。他从来不显耀自己,我也没听人家讲过他会篆刻。他用“汉印”入石,已到炉火纯青,闲熟自如之步。每一方印,平正而鲜丽,毫无板滞之弊。这样,同他的交往,我是书印兼得。
在同魏宝贵交往中,让我学的东西很多。没有学篆刻之前,我文字学知识有限,从汉字演成篆字,曾经摸不到头绪,只好去找他。老人把古文字跟现代的差异,如何索本寻源,一一讲得清楚透彻。
二十多年的来往,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成为挚友。每次到他家,一坐就是大半天,还舍不得走。每当我穿过那热热闹闹做生意的人群,一般人怎么会想到一个读书人,会在这种环境中坚持自己一块平静之地,看书写字。他是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选送到日本参展,并被收藏,在国内也广为收藏。现在所谓书家者,知道老人的书法成就有几人?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曾问过他所在单位的人,对方摇摇头,一点也不清楚。魏宝贵就是这样,他把艺术当作陶冶情操,以益身心健康的学习,练字之余也画国画,可惜所见太少。我回忆时,说起此事,他大女儿丽冬拿出一幅遗画。可见,老人对艺术的追求是多方面的。
他在病笃之时,还交代家人给我一件东西留念。我到他病塌前,他已处濒危之时,无法再说下去。具体什么东西,表达不出来,手只指着一个方向。我劝他好好养病。老人无力地摇头。他在为自己遗憾,没办法表达清楚。后来,我到他家,家里人说到这里,禁不住流泪。写到这里,我眼前一片模糊,泪水已盈眶,电脑屏幕上的字成了一个个小黑点,逐渐连成一片。老人生前待我那么好,我却不能给他做些有益的事!
老人走了!同我交往的书法界同好是这样的少,他们把学书法练字当作一种爱好,与世无争,默默临贴,写字。他们是我的老师,益友,前辈。当他们一一离我而去的时候,我内心无限悲伤,惋惜,将有何人与我同玩?以后,我在书法、篆刻上碰到问题向谁请教!
星岛漳人施香沱的艺术人生
施正渊
施香沱,字宏泽(1906—1990),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原称龙溪县)。他的著作有古装本《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施香沱书法》、《香沱印存》《香沱丛稿》,还有新加坡政府出资出版的《先驱画家施香沱的艺术世界》。2007年6月,新加坡先驱画家施香沱先生的儿子——年届七旬的施一般先生从新加坡回家乡漳州探亲,带其父遗著数部回来,送给几位亲友和漳州市图书馆。阅者翻开书页,粗略一览,即被书中水墨画佳作、行草篆隶的书法艺术及金石精品所吸引,爱不释手。施香沱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魅力?从施一般先生曾先后寄来《星洲日报》、《星洲画报》、《星加坡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南洋商报》……均屡屡报导施香沱书画金石杰出成就和各方评论及有关事迹,可看到大家对施香沱及其作品如何评价。
(一)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长郭建超先生著文评述,他说“在今日新加坡,水墨画的艺术传统得以持续,施香沱先生是新加坡水墨画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施香沱于1938年前往新加坡,1941年受聘新加坡美专讲师,1958年起又任南洋大学书画导师,长达三十一年,他在教学中从来不忘书画创作。1976年他被推选为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他的作品“新几内亚藤”一幅被选入新加坡国家画廊,列为国宝,显示他在新加坡的艺术地位
施香沱的绘画以南洋风格水墨画著称。南洋风格的中国画当时在新加坡画坛是一项创新,施香沱创作时常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审视东南亚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激起创作灵感,将具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事物入画,如多彩多姿的神仙鱼、舞翅蹁跹的天堂鸟,土著人的皮影戏……等等。使时代精神与南洋风格用传统画法在水墨画上表现出来。因此,郭建超先生及同仁都说:“施香沱堪称是南洋风格在水墨画这个领域中的先驱画家。”
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施香沱逃难到苏门答腊过着荷锄耕耘的山芭生活。在这三年里,他没有蹉跎岁月,耕作之外,他留心观察生活中的南洋独特风物。爬满昆虫的泥地像是元代水墨大家黄公望的泼墨;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和独特事物,如黄昏下的大蝙蝠、巨扇般的槟椰叶、章鱼足般的马九树……提供了来自生活的南洋特有色彩。以中国传统绘画手法突出“南洋”特色。不是更加令人感到亲切、鲜明、有地方印记吗?从此,他摸索创造被人赞赏的南洋画风,在中国画独树一帜。
日寇投降后,施香沱继续在新加坡美专任教,他十分重视“时代精神”和南洋风格在水墨画中的表现,在教学中,他常常带学生到植物园、飞禽公园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写生,积累画稿,过后他将画稿加工转为水墨画作品,这种独特的作画风格,他用来传授画艺,渐渐地形成了“香沱风”,也就是说形成了门下的一种作画流派。几十年来他栽培了数不清的水墨画、书法、篆刻人才,其中不乏艺坛的佼佼者。如高足黄崇禧、林万菁、黄明宗都是荣获博士学位的画家,有几批学生组织了墨澜社和啸涛书画研究会,相承老师的画风,常年举办美展。南洋美专学生和其他接受香沱先生熏陶的学生,自然地形成了举世瞩目、影响大的“施香沱派”,“施香沱派”正方兴未艾地发展。施香沱的门生及再传学子正在将他的艺术风格传播到可能传播的每个地方。施香沱先生确实无愧为华夏精英。
(二)
施香沱的书法,自小得益家学渊源。他出身漳州一户书香门第,二叔祖施调赓清末癸未进士,钦点翰林;三叔祖施槃同治甲戍朝考第一。两人都是书法名家。香沱之父施拱南也是名闻海内外的书法家、所以他从小就得到严格家学教导和熏陶。他自己具有天份,对习字有兴趣,能勤学苦练,因此年方弱冠,书写行草篆隶皆超过同窗学友。当时社会上向书法家施拱南求墨宝者甚多,遇到求字过急无法及时应给时,其父常命香沱代书,香沱的字使他人难辨真伪,以为出自拱南手笔,从此香沱初露锋芒。
后来,香沱书法钻研更深,历代重要碑帖无所不攻,一一临遍,尤其石鼓文及汉祀三公山碑,研习更有所得。新加坡评论家陈建坡先生说:“施先生精于石鼓八分,其石鼓深受吴昌硕的启发,然不为所囿,笔圆力饱,自出新意。八分则与齐白石一样出自汉祀三公山碑,沉稳浑拙,但没有齐白石那分野气。形成了他现在雄迈浑厚,古朴苍劲的风格。”新加坡美术馆馆长郭建超先生说:“香沱先生书写的行草如游龙,真隶如卧虎,篆籀如岳峙云亭,渊雅幽邃,都体现苍劲古朴的风格。香沱先生一贯强调作书一气呵成,笔笔有情,对‘行气’极重视,他每幅书法都贯彻他的书法思想。”《施香沱书法》篆隶行草造诣皆深。新加坡老一辈篆刻书法名家黄载灵老先生说:在新加坡施香沱的书法一流,尤其是篆书上的造诣,要是他认为第二,这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了。”
(三)
再谈篆刻。香沱先生的父亲施拱南是书法篆刻名家,还出版《荔香楼印存》。香沱从小目濡耳染和得到父亲亲自教导,怎么不成为出色的篆刻者。他深得浙、皖两派之长,创作既能循法度,又能突破陈规。对印的章法,讲究布局、讲究呼应、也讲究匀称,疏密得体,顾盼有情。从整体的美学效果来看,几乎是无懈可击、天衣无缝。他提出用刀如用笔,刻者必须先打好篆书的基础,才能窥其门径,还要经过长期探讨磨练,才能得其神韵。如果不懂写篆,就谈不上好的篆刻。同时,用刀技艺,求合乎规矩。《香沱印存》收入先生治的295方印章的印章作品,他的方寸世界追摹汉印,朱文圆劲秀丽,白文古拙大方,作品题材丰富而儒雅,风格古朴,给人一种味榄回甘的感觉。名篆刻家黄载灵老先生评曰:“香沱先生治印数十年,博取众长、不为皖、浙派所囿,更而上追秦汉,故所治印章能拙朴而无板滞、雄奇而不矫揉造作,秀逸雄浑古朴,有独自风格,盖其自得者深也。”
先驱画家施香沱先生萃绘画、书画、篆刻无一不精于一身,是不多见。他能够在画、题欺、印存三方面配合得天衣无无缝、浑然统一、格调又高,殊属难得。评论家赞其“书画金石共一炉,火候纯青见功夫。”
(四)
先驱画家施香沱先生在1976年至1981年担任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副会长期间,屡次举办和主持新、马高层美术家的各种类型的美术展,成绩斐然。1981年,他参加第二届国际书展并任主席团成员,是他艺术事业顶峰时期。他常常应邀到电台、院校、学术团体、训练班作专题演讲。他讲的“中国书法的学习”一文,被新加坡教育部收入《高中写作参考资料》。“怎样鉴赏彩墨画”的演讲,被新加坡电台录音在全国广播。他一生忘我浸泳墨池,勤于创作,精益求精、作品数量与质量不断取得新高峰的成就,他的作品多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展出,都受到各国艺术家的好评。1979年他应邀在日本名古屋、横滨举办篆刻书画展和当场作画,得到媒体很好评介与轰动。同年7月,国家派他为副团长率领新加坡文化考察团到我国访问,成为增进中新人民友谊和平使者之一。他载誉归来,新加坡总统薛尔斯以隆重仪式授予公共服务星章,表彰他对国家、对社会、对艺术的贡献。
1990年4月25日施香沱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5岁。南洋美专校友会,在8月于吉隆坡隆重举办“施香沱老师追思纪念遗作展”和“施香沱对新、马画坛的贡献”讲座。1991年6月,他的遗作参加新加坡中国书画名家展。1996年和1997年,遗作又参加国家美术馆主办的新加坡美术百年展和“先驱画家施香沱的艺术世界”的个人篆刻书画展,参观人士非常踊跃,《星洲日报》予醒目的版地报导,表达人们对他的艺术成就永恒敬仰和对他的深情怀念。
六十二年前《艺苑丛刊》漳州发行
艺苑丛刊社于民国卅年(1946年)元旦在厦门成立,四月一日由厦门迁漳州平等路七十五号。该社先后出版了《艺苑》丛刊五辑第一辑《诗歌与木刻》、第二辑《木刻与图案》、第三辑《小说与插图》、第四辑《音乐与附图》、第五辑《木刻挂联》。发行人兼主编人:艺苑丛刊社。总发行处大众文化出版社。第二辑木刻作者吴忠翰。该刊受到广大的读者群众的爱护和推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