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入西藏
| 内容出处: | 《漳州文史资料1921-1991》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4122 |
| 颗粒名称: | 西行入西藏 |
| 分类号: | K250.6 |
| 页数: | 5 |
| 页码: | 136-140 |
| 摘要: | 第二天便和西调同学一起到外交部报到,我们先抵重庆外事处作进藏前的准备工作,经成都、康定、甘孜抵达当时川藏公路终点站海×山。回头看坡下是万丈深沟,听说从二郎山山脚到山顶有百里长,车到山巅便见晴朗天空,阳坡脚下是泸定县,我们特地下车去紧接县城的泸定铁索桥走了走,走在桥面上摇摇晃晃,想当年红军战士抢渡大渡河,从泸定沿瓦斯沟溪流上行到康定,但想到进藏干革命,终于来到甘孜终点车站,开始徒走向西藏方向行进。我们和西南军区派赴西藏工作的干部汇合,雇上藏胞赶着牦牛向昌都进发。 |
| 关键词: | 漳州 西藏 叶雪音 |
内容
1948年,我在龙溪中学念书时加入了中共漳州工委组织。1949年“九·一九”漳州解放,便在老家漳州工作。1951年1月,作为一名调于生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我们一批初进北京的外地同学,都想在暑假期间到颐和园一游,游泳游泳度度署,便提前予购了入园游泳的门票。当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解放了,需要许多干部去那里工作。学院放暑假前两天,辅导员正儿八经地找我谈话,说外交部要在拉萨设外事处,决定调我到该处工作,同去的还有五名闽籍和北京籍同学。对组织决定,我们这些人毫不含糊,一点也不讲“价钱”,说走就走,我是党员,到“世界屋脊”额下的西藏去干革命,还有什么二话。第二天便和西调同学一起到外交部报到,把颐和园游泳门票撂掉。
随后,我们先抵重庆外事处作进藏前的准备工作,由杨公素处长组织学习,学外事纪律、民族政策,要我们明确进藏任务,
号召我们要吃大苦耐大劳,增强革命意志力,克服“高山反应”困难,保证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拉萨。
7月下旬,我们一行18人从重庆乘车出发,经成都、康定、甘孜抵达当时川藏公路终点站海×山。旅途中,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大山,便是闻名于世的二郎山,这座大山海拔3000多公尺,山分阳坡、阴坡,那阴坡多雨潮湿,森林茂密,云雾弥漫,山路艰险,公路沿坡盘旋而上,回头看坡下是万丈深沟,见不到过往车辆的车影,却能够听到车轮滚动的马达声。我们坐在车上颠颠簸簸,有些同志晕车呕吐,但谁也不叫苦。据说修筑这条盘山公路,还有筑路工人献出了年青的性命,我们受点苦算得了什么!大家互勉互励,高唱革命歌曲向前进。后来,听说从二郎山山脚到山顶有百里长,因为是高原的衔接处,车到山巅便见晴朗天空,沿山巅滑下坡,两旁几乎没有树木,这就叫阳坡。阳坡脚下是泸定县,著名的大渡河流经这里。我们特地下车去紧接县城的泸定铁索桥走了走,桥下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桥面用木板条铺成,没有用铁钉固定,走在桥面上摇摇晃晃,铁索也因而左右晃动,想当年红军战士抢渡大渡河,横跨铁索桥,该是何等英勇,个个雄姿跃在眼前,令人敬佩!
从泸定沿瓦斯沟溪流上行到康定,沿途村落稀少,一片荒凉。康定是国民党西康省省会,可是市面小,只沿河一条街,还不如内地的一个镇,但这里已闻高原风味,藏胞、汉胞杂居一起,生活都很穷苦。我们的车出康定不远,便到折多山,这里比二郎山还高得多,开始“高山反应”了,胸闷头晕,特别是长在东南海滨的我尤其敏感,但想到进藏干革命,克服“高原反应”的意志力也加大起来,终于来到甘孜终点车站,开始徒走向西藏方向行进。在甘孜,我们和西南军区派赴西藏工作的干部汇合,组成以杨公素处长为领队的一个小队,雇上藏胞赶着牦牛向昌都进发,坐牛皮筏渡过金沙江。金沙江正逢洪水期,江面很宽,江水黄浊,旋涡套旋涡,渡口又在德格县的岗托,而牛皮筏只两米来长米把宽,用木条支撑着如船的筏体,这种牛皮筏离水时,一人可扛到肩膀上行走,下水只容载四至五人,我们坐在这样的牛皮筏上横渡江面宽阔、流水湍急的金沙江,简直像一片树叶在大江中飘动一样,随时有翻覆丧命的危险,可是我们一行人一船又一船地平安渡过。不过,我在渡江时紧闭双眼,不敢睁目看看江上险境。
从德格到昌都一带,都是解放不满一年久的新区,沿途兵站布点少,保证不了我们一行人的住宿,经常露宿在杳无人烟的草地上。看上去,草地是干干的,可睡上一宵,第二天早起,贴身的褥子已经湿透了,要是碰上雨天就更糟啦!高原气候真是瞬时骤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天昏地暗,狂风大作,不是一阵暴雨便是一阵冰雹。我们随身携带的方块防雨布,根本抵挡不住这种风雨雹雪的袭击,为了胜利西行到拉萨,同志们都用双手护住面部,任雨雹撕打。幸好这种变化莫测的恶劣天气,来得快也消逝得快,风暴一过,又是万里晴空,令人神舒。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高原跋涉,我们于九月下旬胜抵昌都。
在昌都稍事休整,便要继续向拉萨进军。高原地区有句行路俗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必须争取利用“正好走”的有利季节向前走,10月上旬,雇上藏胞骡帮,由10几头骡子驮着行李离开昌都,经类乌齐、丁青、雅岸多、索县,下秋卡、那曲,我们选走这条大北路是个牧区,虽然海拔的绝对高度大,但是这山走向那山的相对高度却小一些,走起路来不会那么吁喘吃力。这里,雪山茫茫,银光灿灿,一路满是冰雪,一脚踩下便陷入一尺多深,寒气袭人躯体,大伙为着增强御冷能力,便在翻山前夕多喝酥油茶,有的同志受不了酥油那股腥腥味,也只好捏住鼻子清落滑落地咽下去。翻山越岭上陡坡,身强力壮的同志当先,后续同志一手拉住前面同志的衣衫角,一手柱着木棍一步步往上蹬,谁先锋到达山顶就当起啦啦队员,给后续同志鼓劲:“加油!加油!”下坡了,因为崎岖跋涉,加上“高原反应”,有些同志走路不能保持自身平衡,直挺躯干前进仍有困难,照样要靠前面同志的辅力和自柱木棍的协助,才能够一步又一步地蹒跚下行。
我们小队伍虽然有骡帮驮行,但每个人的身上负担也不轻:头戴毛皮帽,身着毛皮衣裤,脚穿大头毛皮鞋,肩背一条装米的长条布袋和一块五、六斤重的帐蓬防雨布,外加少量杂物,也是鼓鼓囊囊的,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路,有时还要赶八、九十里,往往是天未亮动身,月升空还在途中走。高原行军,其日行程的远近,要取决于沿途的水草状况,因为牲口吃不上草、喝不上水,次日便休想赶路,所以高原行军很难取决于人的意志力。牲口要吃草喝水了,我们只好搭作帐蓬,挖排水沟,就地宿营,入晚顾不得跋涉疲累,大伙儿又轮流站岗放哨保安全。
西行路上的生活,真有点类似原始人那样过。因为高原的气压低,水不到沸点便滚开,每顿饭都做得夹生不熟,我们也只好采折灌木小枝条当筷子,夹起半生半熟的饭团嚼起来,再动手抓熟羊肉作菜下饭。那时候,做饭用的燃料,主要是靠我们在行军路上拾来的干牛粪烧,女同志开始觉得恶心,后来在燃烧的牛粪上烤馒头,吃入口也不觉得脏臭。雪地行军,根本无法洗漱,口渴了,就地抓把雪往嘴里塞,脸面脏得难受,就捧起雪往脸上搓搓擦擦,正规点的洗脸、洗脚,只能够等到兵站享受啦!进军西藏的生活是艰苦的,党中央对西行入藏的同志十分关心,为着保证进藏人员的身体健康,特地从内地给各兵站运送了许多代食粉、蛋黄腊等军用食品。这类食品的原设计是按人体正常所需要的营养成分选用精料配制的,可是承制这两种食品的不法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暗地里私自改变配方,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致使我们一行人吃了霉变品,发生肚胀腹痛事件,有的同志剧痛得倒在地上打滚。进藏后听说,伤天害理的不法资本家受到人民政府的应有惩处。
经过近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人终于1951年11月27日胜利到达西藏首府拉萨。目的地到达了,大家喜颜悦色,可是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已经褴褛难辩,面相也和年龄不相称,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个个像三、四十岁的大中年。一到拉萨,大伙都围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为了不给藏族中的反动分子授予讥讽的把柄,我们选择了僻静小道,绕进事先安排好了的住处,然后逐渐开辟工作,完成进藏任务。事过40年,如今回想西行入藏,饶有情趣:虽然历尽千艰百苦,但从艰苦生活中,我们的思想、意志、毅力都经受住磨炼和考验。
随后,我们先抵重庆外事处作进藏前的准备工作,由杨公素处长组织学习,学外事纪律、民族政策,要我们明确进藏任务,
号召我们要吃大苦耐大劳,增强革命意志力,克服“高山反应”困难,保证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拉萨。
7月下旬,我们一行18人从重庆乘车出发,经成都、康定、甘孜抵达当时川藏公路终点站海×山。旅途中,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大山,便是闻名于世的二郎山,这座大山海拔3000多公尺,山分阳坡、阴坡,那阴坡多雨潮湿,森林茂密,云雾弥漫,山路艰险,公路沿坡盘旋而上,回头看坡下是万丈深沟,见不到过往车辆的车影,却能够听到车轮滚动的马达声。我们坐在车上颠颠簸簸,有些同志晕车呕吐,但谁也不叫苦。据说修筑这条盘山公路,还有筑路工人献出了年青的性命,我们受点苦算得了什么!大家互勉互励,高唱革命歌曲向前进。后来,听说从二郎山山脚到山顶有百里长,因为是高原的衔接处,车到山巅便见晴朗天空,沿山巅滑下坡,两旁几乎没有树木,这就叫阳坡。阳坡脚下是泸定县,著名的大渡河流经这里。我们特地下车去紧接县城的泸定铁索桥走了走,桥下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桥面用木板条铺成,没有用铁钉固定,走在桥面上摇摇晃晃,铁索也因而左右晃动,想当年红军战士抢渡大渡河,横跨铁索桥,该是何等英勇,个个雄姿跃在眼前,令人敬佩!
从泸定沿瓦斯沟溪流上行到康定,沿途村落稀少,一片荒凉。康定是国民党西康省省会,可是市面小,只沿河一条街,还不如内地的一个镇,但这里已闻高原风味,藏胞、汉胞杂居一起,生活都很穷苦。我们的车出康定不远,便到折多山,这里比二郎山还高得多,开始“高山反应”了,胸闷头晕,特别是长在东南海滨的我尤其敏感,但想到进藏干革命,克服“高原反应”的意志力也加大起来,终于来到甘孜终点车站,开始徒走向西藏方向行进。在甘孜,我们和西南军区派赴西藏工作的干部汇合,组成以杨公素处长为领队的一个小队,雇上藏胞赶着牦牛向昌都进发,坐牛皮筏渡过金沙江。金沙江正逢洪水期,江面很宽,江水黄浊,旋涡套旋涡,渡口又在德格县的岗托,而牛皮筏只两米来长米把宽,用木条支撑着如船的筏体,这种牛皮筏离水时,一人可扛到肩膀上行走,下水只容载四至五人,我们坐在这样的牛皮筏上横渡江面宽阔、流水湍急的金沙江,简直像一片树叶在大江中飘动一样,随时有翻覆丧命的危险,可是我们一行人一船又一船地平安渡过。不过,我在渡江时紧闭双眼,不敢睁目看看江上险境。
从德格到昌都一带,都是解放不满一年久的新区,沿途兵站布点少,保证不了我们一行人的住宿,经常露宿在杳无人烟的草地上。看上去,草地是干干的,可睡上一宵,第二天早起,贴身的褥子已经湿透了,要是碰上雨天就更糟啦!高原气候真是瞬时骤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天昏地暗,狂风大作,不是一阵暴雨便是一阵冰雹。我们随身携带的方块防雨布,根本抵挡不住这种风雨雹雪的袭击,为了胜利西行到拉萨,同志们都用双手护住面部,任雨雹撕打。幸好这种变化莫测的恶劣天气,来得快也消逝得快,风暴一过,又是万里晴空,令人神舒。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高原跋涉,我们于九月下旬胜抵昌都。
在昌都稍事休整,便要继续向拉萨进军。高原地区有句行路俗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必须争取利用“正好走”的有利季节向前走,10月上旬,雇上藏胞骡帮,由10几头骡子驮着行李离开昌都,经类乌齐、丁青、雅岸多、索县,下秋卡、那曲,我们选走这条大北路是个牧区,虽然海拔的绝对高度大,但是这山走向那山的相对高度却小一些,走起路来不会那么吁喘吃力。这里,雪山茫茫,银光灿灿,一路满是冰雪,一脚踩下便陷入一尺多深,寒气袭人躯体,大伙为着增强御冷能力,便在翻山前夕多喝酥油茶,有的同志受不了酥油那股腥腥味,也只好捏住鼻子清落滑落地咽下去。翻山越岭上陡坡,身强力壮的同志当先,后续同志一手拉住前面同志的衣衫角,一手柱着木棍一步步往上蹬,谁先锋到达山顶就当起啦啦队员,给后续同志鼓劲:“加油!加油!”下坡了,因为崎岖跋涉,加上“高原反应”,有些同志走路不能保持自身平衡,直挺躯干前进仍有困难,照样要靠前面同志的辅力和自柱木棍的协助,才能够一步又一步地蹒跚下行。
我们小队伍虽然有骡帮驮行,但每个人的身上负担也不轻:头戴毛皮帽,身着毛皮衣裤,脚穿大头毛皮鞋,肩背一条装米的长条布袋和一块五、六斤重的帐蓬防雨布,外加少量杂物,也是鼓鼓囊囊的,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路,有时还要赶八、九十里,往往是天未亮动身,月升空还在途中走。高原行军,其日行程的远近,要取决于沿途的水草状况,因为牲口吃不上草、喝不上水,次日便休想赶路,所以高原行军很难取决于人的意志力。牲口要吃草喝水了,我们只好搭作帐蓬,挖排水沟,就地宿营,入晚顾不得跋涉疲累,大伙儿又轮流站岗放哨保安全。
西行路上的生活,真有点类似原始人那样过。因为高原的气压低,水不到沸点便滚开,每顿饭都做得夹生不熟,我们也只好采折灌木小枝条当筷子,夹起半生半熟的饭团嚼起来,再动手抓熟羊肉作菜下饭。那时候,做饭用的燃料,主要是靠我们在行军路上拾来的干牛粪烧,女同志开始觉得恶心,后来在燃烧的牛粪上烤馒头,吃入口也不觉得脏臭。雪地行军,根本无法洗漱,口渴了,就地抓把雪往嘴里塞,脸面脏得难受,就捧起雪往脸上搓搓擦擦,正规点的洗脸、洗脚,只能够等到兵站享受啦!进军西藏的生活是艰苦的,党中央对西行入藏的同志十分关心,为着保证进藏人员的身体健康,特地从内地给各兵站运送了许多代食粉、蛋黄腊等军用食品。这类食品的原设计是按人体正常所需要的营养成分选用精料配制的,可是承制这两种食品的不法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暗地里私自改变配方,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致使我们一行人吃了霉变品,发生肚胀腹痛事件,有的同志剧痛得倒在地上打滚。进藏后听说,伤天害理的不法资本家受到人民政府的应有惩处。
经过近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人终于1951年11月27日胜利到达西藏首府拉萨。目的地到达了,大家喜颜悦色,可是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已经褴褛难辩,面相也和年龄不相称,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个个像三、四十岁的大中年。一到拉萨,大伙都围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为了不给藏族中的反动分子授予讥讽的把柄,我们选择了僻静小道,绕进事先安排好了的住处,然后逐渐开辟工作,完成进藏任务。事过40年,如今回想西行入藏,饶有情趣:虽然历尽千艰百苦,但从艰苦生活中,我们的思想、意志、毅力都经受住磨炼和考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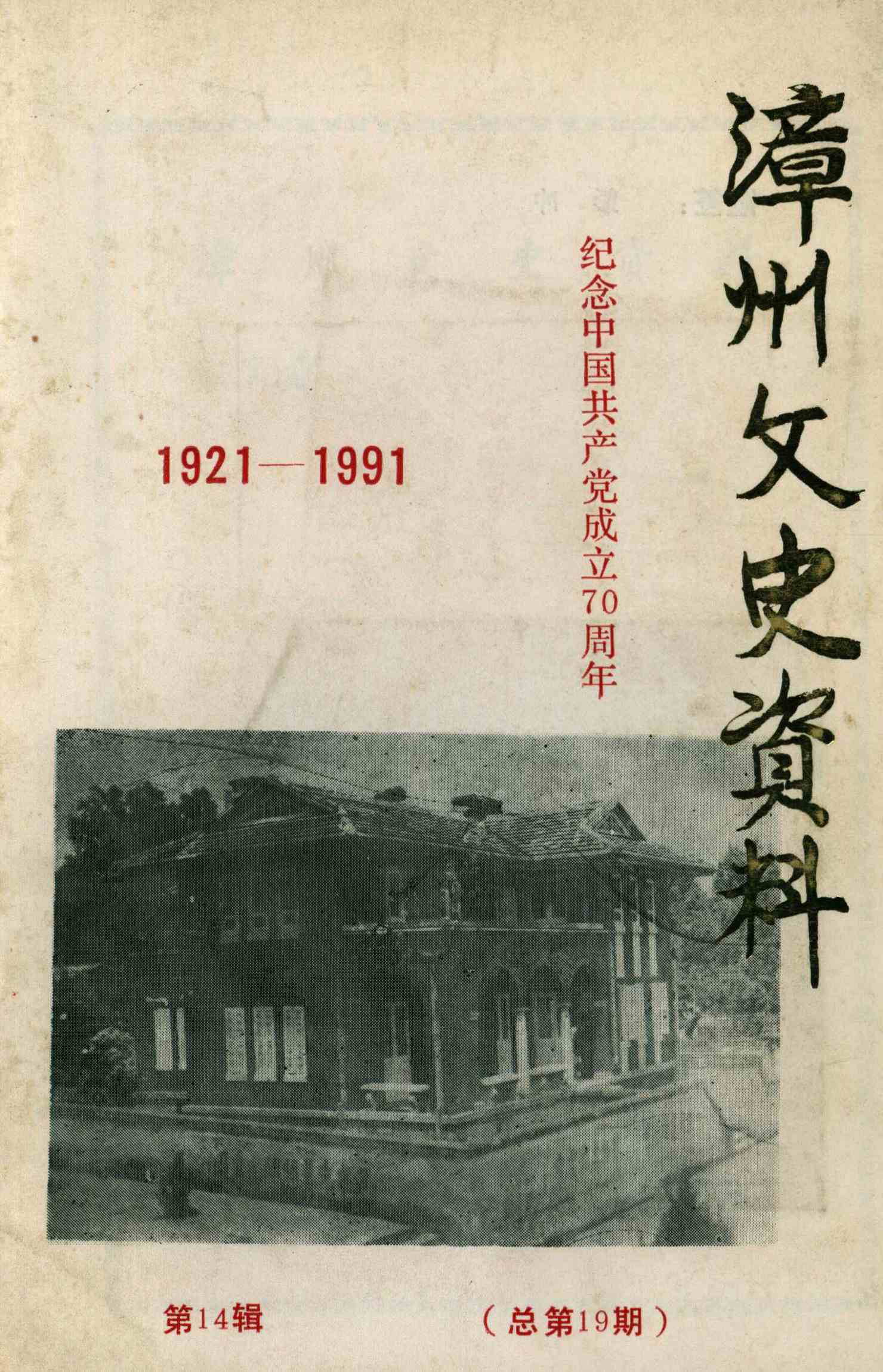
《漳州文史资料1921-1991》
本书记述了漳州文史资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深深地在闽南城乡植播了爱党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争取胜利的光荣传统。他们所创建的战斗业绩和精神财富,功垂史册,光照后人!它必将激励各界人上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旗帜,结成广泛的统.战线,团结侨胞、港胞、台胞,推进漳州的开放改革,为建设漳州、振兴漳州,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作出新的奉献。
阅读
相关人物
叶雪音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漳州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