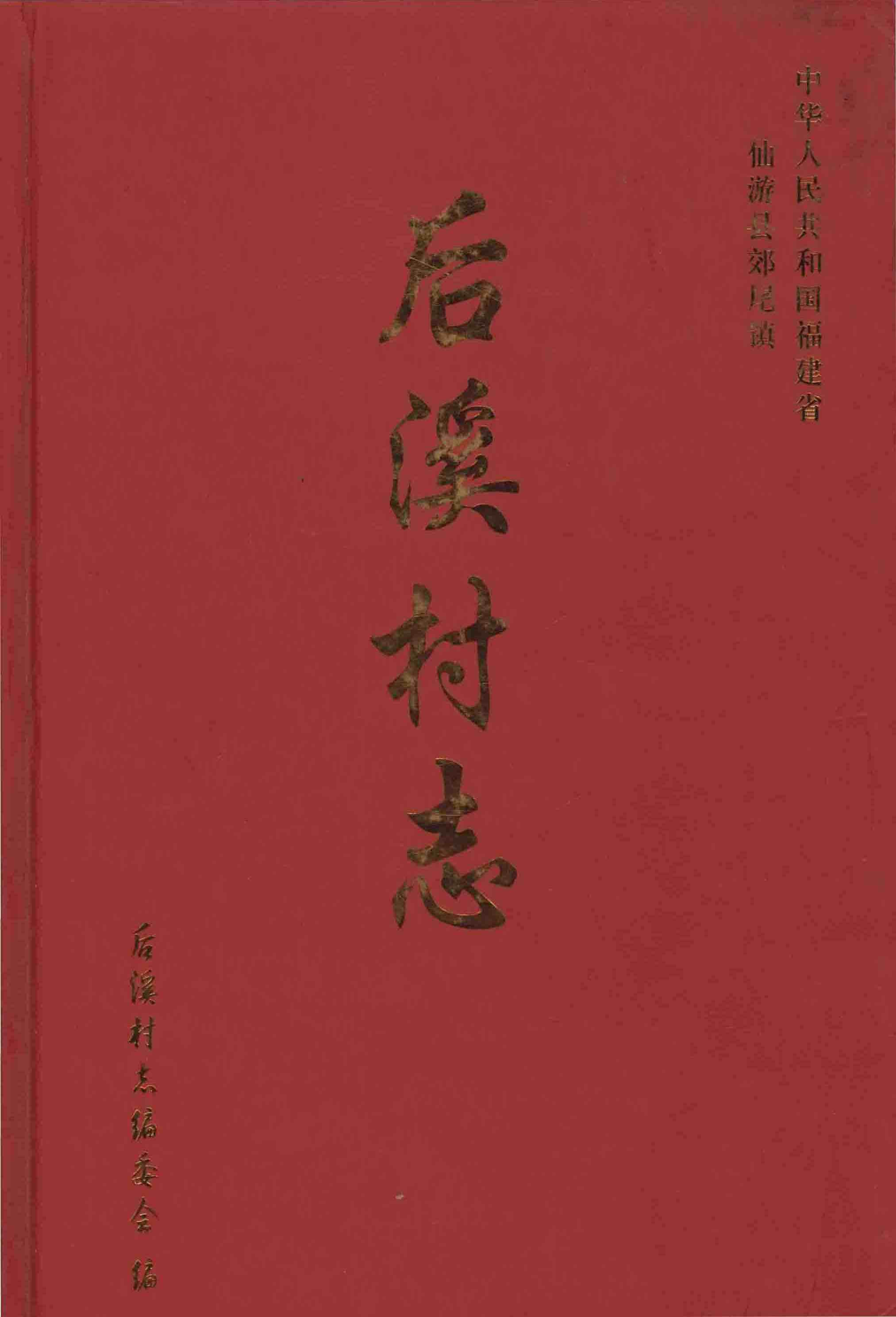内容
第一节 人口概略
一、人口来源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阮庄阮氏肇基祖宏孙公六世孙阮哲,由阮庄迁居后溪,为后溪阮氏之宗。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阮庄宏孙八世孙阮鉴,由阮庄迁居顶沟尾,为下底寨、竹戈阮氏之宗。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惠安县官林颍水陈氏之一支,迁居仙游县香田里后溪,居于磨头山下,为长厝尾陈氏之宗。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蔡而书由仙游嘉禾乡仁德里(今龙华)磨头,迁居唐安乡香田里后溪,为下磨头荔谱蔡氏之宗。清乾隆中期(1760年前后),一对施姓年轻夫妇从惠安南埔移居香田里后溪靠近下磨头处,为长厝尾施氏之宗。清道光中期(1840年前后),一户林姓从枫亭兰友迁居顶沟尾,为下底寨九牧林氏之宗。清同治(1862—1874年)年间,一户林姓、一户刘姓,相继从惠安蜂尾迁至仙游香田里后溪西北隅定居,为顶磨头林氏、刘氏之宗。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蔡祥从莆田金沙铺东沙北上,迁居仙游香田里后溪,为长厝尾荔谱蔡氏之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阮丹堂举家由阮庄迁居长厝尾,为长厝尾阮氏之宗。另有一阮姓,系民国1,4年(1925年)长厝尾施元苍入赘后溪下厝,后回归长厝尾定居,其后代以阮氏为姓。
二、姓氏溯源
阮氏 源出于偃姓,乃黄帝之后。阮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八十九位的姓氏,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五。阮氏发祥地是河南陈留(今开封)。汉南阳太守阮况、侍中阮胥卿闻名于世;魏晋期间,阮籍、阮咸叔侄,与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故阮籍、阮咸后裔以竹林为堂号。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阮咸后裔弥之入闽,任晋安(今属福州)郡守,其后,弥之弟仁之、永之相继任晋安郡守,世称“晋郡三太守”,是为竹林阮氏入闽始祖。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阮弥之二十二世孙阮鹏,官协律郎,避黄巢乱,由福州迁移仙游嘉禾乡仁德里(今龙华),居于金沙上库,是为阮氏入仙始祖。阮鹏生宜耕、宜耘二子。宜耕四世孙阮沂和沂子阮程,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迁居莆田阮巷,是为莆阳阮氏肇基祖。宋代,阮氏在莆阳已衍成巨族。
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九月,阮鹏十六世孙、阮沂十一世孙阮宏孙,由莆田迁返仙游,居于香田里阮庄,是为阮庄竹林阮氏肇基祖。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宏孙六世孙阮哲,字原明,由阮庄迁居后溪。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阮哲四十五岁被荐充贡,景泰三年(1452年)出任湖南卢溪知县,天顺五年,(1461年)辞官归隐返后溪。其后裔改堂号“竹林”为“苏溪”,尊阮哲为苏溪阮氏始祖。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宏孙八世孙阮鉴,字景昭,官江西广信府教谕,与其兄阮马由阮庄析居顶沟尾,是为下底寨、竹戈阮氏之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阮丹堂由阮庄举家移居长厝尾,是为长厝尾阮氏之宗。
竹林阮氏昭穆辈序是:举进存仁、端庄树则、克家象贤、立朝司直、忠孝有源、图书惟式、名策清时、勋昭王国、奕叶绍兴、绪光千亿。1951年土地改革时,后溪境内有阮氏188户781人;至2010年,增至815户3176人。
蔡 源出于姬姓,乃黄帝之后。
西周始祖稷系黄帝曾孙帝喾的长子,袭姬姓。公元前1046年,稷的后裔周武王姬发克纣灭商,建立周朝。是年九月,武王分封天下,其中分封了五十五姬姓侯国。武王的十四弟姬度,封于蔡国,后人称之为蔡叔度。周贞定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47年),蔡国被楚所灭,蔡齐侯的后裔即以国号为姓,改姬姓为蔡氏。汉代,蔡氏发祥于河南陈留和济阳,因而堂号为“陈留”或“济阳”。
隋唐时,蔡用元、蔡用明两兄弟的祖先由河南迁居浙江。唐懿宗咸通元年(880年),用元、用明两兄弟随王潮、王审知入闽,由浙江钱塘迁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后由南安再迁往仙游,定居在仙游慈孝里赤湖蕉溪(今枫亭东宅)。北宋末丞相蔡京、蔡卞系用明之后;端明学士蔡襄系用元之第六世孙。蔡襄曾作《荔枝谱》,其后裔取“荔谱”为堂号,祠堂、祖居称为“荔谱流芳”。
北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蔡襄置家于莆田蔡宅。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至1224年),蔡襄五世孙蔡度由蔡宅迁居莆田东沙。明成祖年间,蔡度第十四代孙由蔡宅迁居仙游仁德里。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蔡而书和母亲、胞弟一家三口,由龙华金沙磨头迁居香田后溪,居于下磨头。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蔡祥从莆田东沙迁居后溪长厝尾。
1951年土地改革时期,后溪有蔡姓47户199人。至2010年底,增至190户714人。
林 源出于姬姓,乃黄帝之后。黄帝曾孙帝喾有四妃,次妃简狄生契。契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授为司徒,封于商地,赐子姓。契的十四世孙商汤,灭夏建商朝。商朝末年,纣王残暴无道,公元前1047年秋,纣王将胞叔比干剜心处死。比干正妃陈氏怀有3个月身孕,恐遭株连,带四名婢女逃出京城,躲进牧野郊外一片长林的石室中。武王克纣灭商后,陈氏已产下一男,取名坚,母子归顺周朝。武王以陈氏居长林而生坚,遂赐坚以林为姓氏,林坚即为林氏得姓始祖。
林坚长成,字长思,娶莘氏为妻,生子名载,字元超,世居西河郡(亦称博陵郡),自此子孙绵延不绝。西河郡(博陵郡)是林氏发祥地,故林氏堂号为西河、博陵。
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动荡,林、陈等姓入闽。林氏入闽始祖林禄,奉敕镇温陵(今泉州)晋,安,举家定居温陵。林禄69岁病故后,晋廷追授晋安郡王。唐初,林禄七世孙林茂,茂子孝宝,由温陵迁居莆田县北螺村。孝宝五世孙林披,由北螺迁居澄渚。林披先后任潭州、康州、睦州刺吏,生苇、藻、著等九子,均任州刺吏,世称“九牧”,林披是“九牧林”始祖。自唐至宋,九牧林分居全国各地。
清代后期,先后有2支林氏迁入后溪,其中来自惠安蜂尾林氏,定居在顶磨头,来自枫亭兰友林氏,定居在下底寨。
“九牧林”昭穆辈序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立身行道、显亲扬名、博施济众、崇德利生、宽裕温柔、发聪刚毅、乾堃化育、感应万霖。
1951年土地改革时,后溪有林氏20户84人。至2010年底,增至118户451人。
陈 源出于妫姓,乃帝舜之后。
帝舜生于姚墟,居于妫汭,因而有姚舜、妫舜之称。商朝末年,妫舜三十三世裔孙妫阏父,在西周任陶正(掌管全国陶瓷业的行政长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纣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分封天下。是年九月十八日,武王敕封阏父之子妫满为陈侯,划河南颍水河流域为陈国属地,定陈国都城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并把长女太姬嫁与妫满为妻。妫满谥号陈胡公,以国号为姓氏的陈氏自此始。
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八大姓入闽,陈润是陈氏入闽始祖,官居散骑常侍,居福州乌石山,自撰《闽中草寓记》,追忆入闽经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闽南啸乱,朝议大夫陈政奉旨戍闽,与子陈元光率士兵3600名,偏将120员,,自河南光州固始县出发,赴闽南靖边。陈政、陈元光父子屯兵于云霄绥安,把家眷安置在枫亭陈庐园。陈元光后累升开漳圣王,子孙四代相继开漳,其家属留居枫亭长达四十三年。
陈元光十一世孙陈洪进,生于枫亭陈庐园,后移居秀峰村侯览。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洪进纳漳泉二州十四县归宋,累功升至同知平章事、岐国公,病故后追授南康郡王。四弟七子俱受宋廷荣封,其五子均任州刺吏,世称“五侯”。宋代之后,五侯陈氏分散在兴化、闽南、广东、海南、台湾等地。
明正德(1506至1521年)年间,惠安县官林有两支陈洪进的后裔先后迁居仙游县香田里,前一支肇基于郊尾麟角,后一支肇基于后溪长厝尾。长厝尾的五侯陈氏,历史虽悠久,人口繁衍较慢。1951年1月,长厝尾陈氏仅有6户33人,2010年底,增至20户98人。
自第十三至二十二代,长厝尾颍水五侯陈氏的昭穆辈序是:良臣忠仕主,百行孝传家。
刘 刘氏的来源有五方面。
其一,源出于祁姓,乃帝尧之后。夏初,帝尧伊祁氏后裔之一支,被封于刘邑(今河北唐县),其后代以封地取姓为刘。
其二,源出于姬姓,乃帝舜之后。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武王同父异母弟姬高,其后代改姬姓为王氏。武王之孙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其后代也取刘为姓,是姬姓刘氏。
其三,源出于汉代匈奴族之后。
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淑女嫁予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为妻。按照匈奴习俗,贵族子女随母姓,因而冒顿单于后代为刘氏。南北朝时建立前赵,自称汉王的刘渊,即是匈奴刘氏后代。
其四,公元前206年刘邦建西汉,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前后历时420多年。“刘”是两汉的国姓,两汉天子经常给外族首领、有功之臣,赐以国姓,以示褒奖,如赐项伯、娄敬为刘姓。
其五、取“留”的谐音“刘”为姓氏。
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晋国君晋襄公病故,大臣们商议,派杜士会为使,赴秦国迎回襄公之弟公子雍续任晋君。士会君臣踏进故土,晋国已立襄公幼子夷皋为君。秦国护送部队与晋军发生激战,秦军败。杜士会等便留在秦国,其后代改杜姓为刘姓。
有以上五方面的来源,故中国刘姓人口众多,居全国姓氏排行第四位。但后溪刘姓人口较少,1951年初仅有5户24人,至2010年底,增至9户54人。
施 施氏来源有二。
其一,源出于姬姓,乃周公旦后裔。
公元前1046年秋,周武王封堂弟伯禽(周公姬旦长子)于鲁国,疆域在今山东省境内,春秋初期,鲁惠公之子姬尾(公子尾),字施父。姬尾生一子姬伯,姬伯取乃父之字“施”为姓氏,改称施伯,后裔即是姬姓施氏。此支施氏望族在浙江吴兴,堂号为“吴兴”。
其二,夏、商时期,有个施国,在今湖北省恩施县一带。商朝末期,施国灭,遗民遂取国号“施”为姓氏。
唐僖宗乾符年间(874至879年),黄巢起义军南下,途经福建。有王潮、王审知等河南光州固始县籍数万官兵随义军入闽后,留居福建,据州占县,独霸一方,唐廷委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驻守福州。秘书中丞施典随王潮兄弟入闽后,置家于泉州晋江南门外。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大理寺评事施炳由光州固始县举家南迁入闽,肇基于浔阳衙口乡。元中叶,施炳六世孙施守忠移居惠安南埔施厝村。不久,施典十三世孙施菊齐、施九思兄弟也移居南埔施厝。清乾隆中期,南埔施厝一对年轻夫妇迁居后溪长厝尾。
1950年初,长厝尾施氏只有2户7人。2010年底,增至5户35人。
施氏的昭穆辈序是:伯跃兆起、公乾于师、怀尚侯子、元建序宗、文章华国、诗礼传家。
三、人口分布
(一)村落人口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清朝末年,随着阮、陈、蔡、施、林、刘诸姓先民迁入定居,繁衍生息,绵延相继,始有后溪、下底寨、竹戈、长厝尾、下磨头、顶磨头、坝洋等自然村落。1950年后,上述七个自然村落构成后溪的主体。
从1950年底到2010年底的六十年间,后溪人口净增3400人。2010年底的人口是土地改革前夕人口的4倍。其中下底寨净增219人;竹戈净增308人;坝洋净增304人;长厝尾净增163人;下磨头净增372人;顶磨头净增470人;后溪自然村净增1564人。
(二)姓氏分布
2010年11月1日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后溪农业户口共有1157户4528人,其中阮氏815户3176人,占全村总人口的70.15%;蔡氏190户714人,占15.76%;林氏118户451人,占9.96%;陈氏20户98人,占2.16%;刘氏9户54人,占1.14%;施氏5户35人,占0.78%。
嫁入后溪的女村民中,还有张、杨、吴、王、周、欧、史、朱、郑、邱、连、余、彭、潘、赖、李、卢、徐、苏、沈、俞、谢、田、严、许、陆、方、凌、戴、肖、薛、翁、黄、郭、辜、颜、檀等37个姓氏,连同阮、蔡、林、陈、刘、施,境内共有姓氏43个。
(三)人口密度
郊尾镇是仙游县人口高密度区,后溪也是郊尾镇内人口密度较高的村庄,1951年土地改革时期,已达每平方公里386人。从1956年至1982年的农业集体化阶段,境内人口密度与全镇人口密度同步上升,上升幅度略高于全镇平均水平。
1982年的人口密度是1956年的2.14倍。
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大。由于后溪认真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建立流动人口登记卡,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密度上升势头减缓。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后溪村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40人/平方公里的11倍,是福建省平均人口密度445人/平方公里的3.5倍。
四、人口构成
(一)性别
从1950年至80年代,后溪人口总数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80年代后,男女比例趋向总体平衡。但不同年龄段又不平衡,1—15岁年龄段,男性比例大于女性;65岁以上老龄段,女性则高于男性。
(二)年龄
清朝末年至民国26年(1937年),社会秩序纷乱,天灾人祸频繁,境内单身汉多,人均寿命短,人口年龄呈成年型。
民国2年(1913年),染厝佛公底司马桥竣工,该桥是仙游县城通往枫亭的必经之路。举行通桥仪式时,后溪六祖三十二世庄光公(俗名九哥)时年仅36岁,其孙则勤(名金明)年已3岁,公孙两人一起参加落成剪彩活动,留下“三十六岁牵孙过桥”的轶闻。
民国26年至1949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瘟疫横行,医疗条件差,死亡率较高,自然增长率低,人口年龄仍呈成年型。
1950年后,人口年龄发生明显变化。政府重视民生,推广新式接生法,婴儿成活率大为提高,加上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青少年比例上升,人口结构呈年轻型。1969年底,全村人口2064人中,17周岁以下人口1045人,占50.63%。
1970至1989年,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深化,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少年儿童比例明显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境内人口年龄构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
90年代,人民生活向小康迈进,老年人口增多,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继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人口结构由成年型开始向老年型过渡。
进入21世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安定和谐,经济繁荣昌盛,医疗保险普及,人民健康长寿,初步构成人口老年型。
2010年60岁以上比率,与全国13.26%相比,高2.24个百分点,与福建省11.42%相比,高4.08个百分点;65岁以上比率,分别比全国8.87%、全省7.8%高3.16个、4.14个百分点。至2010年底,后溪村有80—89岁寿星84位,90岁以上寿星13位。其中阮
金明101岁。
阮金明,1911年11月25日生,子孙昌盛,五代同堂。
(三)文化
1949年前,由于经济状况等客观条件制约,绝大多数农家子弟未进校门接受教育,文化水平低,文盲覆盖面广。
1950年后普及小学教育,农家子弟和大多数女孩,进入郊尾中心小学接受教育,农村开展业余教育,村民文化程度有所提高。1960年仙游八中的创办和1970年复办,为后溪村民接受初等教育提供方便。1964年7月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后溪有小学生431人,初中生97人,高中生14人。1982年,有小学生1072人,初中毕业的378人,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56人。
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为农村子女接受教育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毕业生免试进入初中学习,农村文化水平更上一个台阶。1988年,后溪户籍人口中,有本科生、大专生13人,中专生48人,高中生162人,初中生513人。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达100%。
进入21世纪,每年有部分初中毕业生放弃上高中机会,或进厂打工,或随父母兄嫂从事二、三产业。离退休人员回原籍,提升了高学历人员比例。至2010年底,境内有博士11人,硕士15人,学士101人,教授、副教授12人。户籍挂靠后溪的郊尾中学、郊尾中心小学、郊尾中心幼儿园三所学校教师377人。但仍有308人中老年村民(其中女性212人)属文盲或半文盲,占总人口的6.8%。
五、职业
明、清时期,境内劳动人口,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只有个别家庭开店经商。民国时期,劳动人口仍以农业种植为主,少数人口从事私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服务业。
1950年至1982年,除国家选调的工作人员外,境内劳动人口中,97%人员从事农业耕作,3%人员从事建筑、运输、砖瓦厂等副业生产。
1983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传统农业局面,大批劳力有序转向二、三产业。1988年,全村1323个农业劳动力中,只有905个劳力从事1209亩农地耕作,418个劳力改行,其中从事建筑业的182人,从事运输业的34人,饮食服务业的17人,进厂务工的45人,文化体育卫生服务业9人,下海经商或外出办加油站131人。从事第一产业的905个劳动力中,还兼营家庭养殖业。1989年,饲养乳牛19头,年产牛乳25吨,出售生猪874只、羊113只。
2007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全村1672个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种植和家庭养殖的有75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5.1%;从事第二产业的436人,占26%;从事第三产业的389人,占23.3%;另有93人从事废纸、废铁、废塑回收,占5.6%。
六、经济 生活
(一)经济
明、清至民国时期,境内经济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粮食生产不足于自给,家庭收入以出售蔗糖、龙眼、桂圆为主。1950年至1956年,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属单一农业经济。零星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加工业,其收入比例不大。
1956年后,实行农业集体化,土地和龙眼归集体所有,农民靠挣工分维持家庭生活,盈余者年终有所分红,兑现部分现金购买年货;透支者需交部分透支款,不交者以口粮折款抵扣。粮食亩产和总产虽逐年上升,但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均口粮逐年下降,制约了社会财富人均占有量的增长。1981年后溪大队粮食总产515.9吨,比1965年总产431.1吨净增84.8吨,但1981年人均口粮仅是1965年的69.4%。
1983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溪社会生产总值直线上升。
1997年,全村年产值达3124万元,上交国家税金22.1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435元,是1981年人均55.3元的44倍。2010年,全村社会生产总值达6200万元,上交税金280万元,人均纯收入5600元,是1981年的101.3倍。1983年至2010年,全村耕地逐年递减。2010年底人均耕地只有0.26亩,是1951年人均1.08亩的24%,耕地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紧缺困境。
(二)生活
明、清至民国时期,境内贫雇农租地耕种,交纳田租后收成所剩无几,卯吃寅粮,三餐难继。自耕农也因苛捐杂税繁多,青黄不接时缺衣少食,生活艰难。
1950年后,后溪农民分到田地,生活基本得到保障。从单干户到互助组,所产粮食除上交公粮外,均由农户自行支配,物质生活初步得到改善。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从农业合作化到农业集体化,村民生活在低水平徘徊,进入70年代,市场商品较为充裕,凭证购物制渐被废除,但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仍较单调。
1984年后,富余劳力转向二、三产业,单一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化,村民收入成倍增长,生活得以显著改善,高中档家电涌进寻常百姓家。90年代,村民物质生活继续提高,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日益丰富,80%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12%的家庭迈进小康行列。
进入21世纪,村民生活继续向宽裕型小康迈进。至2010年底,全村人均年收入5600元,人均住房面积32平方米。平均每百户村民拥有小车2部、摩托车22辆、电冰箱56架,洗衣机47台,手机242部。2010年,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为46.18%,比2000年下降5.2个百分点。
第二节 婚姻 家庭
一、婚姻
明、清至民国时期,后溪婚姻习俗一般为一夫一妻制,个别乡绅纳妾。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乡俗,一般以男满18岁、女满16岁即达到结婚年龄,家长就会托媒说亲。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定双方婚姻关系,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有的家庭实行养媳婚、交换婚、表亲婚等,双方缺乏感情基础,由此造成的婚姻悲剧,时有发生。同时,受婚俗、环境、经济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困家庭男子,终身无法娶妻。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封建社会的婚姻弊端仍在延续,抱童养媳、买卖婚姻现象严重。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因不堪家庭暴力和虐待而投水、服毒、上吊自杀者,屡有发生。因生活所迫,忍痛卖儿鬻女者有之。孀居寡妇身受封建礼教观念的桎梏,改嫁或招夫被视为不贞,寡居苦熬遭受世俗岐视。家庭中“夫权”观念占支配地位,达官贵人、商贾富豪娶妻纳妾不受法律约束。
1949年后,废除早婚制,严禁买卖婚姻,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自1950年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境内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双方通过自由恋爱后,到区(乡)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确定婚姻关系。未到法定婚龄,或是家庭强迫包办者,政府不予登记。妇女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政治地位的提高,婚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择偶重人品而不重财礼。女子以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吃苦耐劳、举止文明作为选择伴侣的首要条件。结婚时不计较嫁妆、不讲究排场,侧重于孝顺长辈、勤俭持家、妯娌团结、家庭和睦、夫妻恩爱等道德、政治因素的考量。
1962年,随着经济好转,女性择偶偏向于现役军人或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国家工作人员。1966年后,受“左”的思潮影响,男女择偶讲究阶级成份。70年代,县城和集镇经济发展较快,受其影响,条件较好的女性,偏重于有地位、有固定收入的城镇男青年,并开始讲究彩礼的品牌和档次,“三车一转”是彩礼中必不可缺的“硬件”。少数受经济条件限制,难以找到合适对象的农家男青年,往往寻觅同等类型的家庭,进行“姑嫂换亲”或“三家转亲”,以期节省婚嫁开支。
1978年政府号召晚婚晚育,规定男满25岁、女满23岁,方可登记结婚。1988年,《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重申这一规定。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青年偏向选择条件优于自身的男友,不仅要讲究对方的经济状况,而且要考察对方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技术水平等。在彩礼上,男方大多都能满足女方对洗衣机、彩电、电冰箱、摩托车等的要求。男女外出打工、经商、求学的,也有选择外地人为配偶。
1990年起,按照宪法规定,男满22周岁、女满20周岁,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生活水平提高,境内婚姻形式趋于多元化。男方到女方落户入赘、丧偶老人重组家庭、孀居女性自由改嫁渐成社会习俗。自由恋爱、集体婚礼、旅游结婚,渐成婚姻新风尚。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夫妇共同赡养双方父母成为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封建社会中,出于政治、宗法、伦理、健康等方面原因,朝廷规定“同姓不得通婚”,1949年后,这一禁忌已被废除。改革开放后,只要男女双方彼此信赖、两厢情愿、无近亲血缘关系,同姓联姻亦被认可。境内同姓联姻者十来对,家庭和谐、子女健康聪颖。
二、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按其规模、结构划分,一般家庭有“核心家庭”型和“直系家庭”型。核心家庭包括父母和未成年子女,规模小,结构简单。直系家庭包括户主的父母、配偶、子、媳、孙等,规模较大。
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阮哲公迁居后溪后,境内的平民家庭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家庭大事、对外事务,全由男主人处理,丈夫是“当家的”,是家庭的主宰,妻子对丈夫而言,只是“做饭的”、“家里人”,只在家中料理家务,生儿育女,足不出户。在家庭中儿媳的地位更低下,若只生女孩必遭丈夫的埋怨和翁婆的指责;若婚后几年没有生育,更遭世人白眼。
核心家庭中,形成以长者为一家之主的“主从合作”状态。这种“主从合作”、“男尊女卑”的社会陋习,在农村不同阶层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农村中约有十分之一家庭,条件较好,经济较富裕,户主一般受过教育,以耕读传家,用孔孟之道教育子女、治理家庭,恪守伦理道德,这类家庭,处理家内矛盾和邻里关系,奉行“和为贵”信条,讲究“家和万事兴”、“夫妻和而家道兴”等,子女或晚辈不愿主动分家,怕落下不孝与不肖恶名。因此,形成多代人共聚的直系大家庭,以“四代同堂”为荣耀、“五代同堂”为楷模,以拆灶分居为耻辱。这样的直系大家庭通常是家长治理有方、兄弟友爱、妯娌团结、婆媳和睦、子孙孝顺。
1950年前,农村中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的现象普遍,因此“多子多福”、“人多势众”的封建传统观念,对平民家庭的影响深刻,企望“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在两性联姻方面,也要考虑对方是否大房大姓。在家庭问题上,多数家庭在老人去世后,兄弟便分家。也有因天灾人祸,家道中落或妯娌不睦,兄弟不和;或子女不孝,父母怀忿;或对待不公,心存岐偏等,导致一个直系家庭分拆成若干个较小家庭。兄弟分家,须请母舅主持,族亲作证。分家时,父母赡养、财产分配、权益继承等,经兄弟协商、族亲调解、母舅裁决,以求合理解决,一般是老人不离祖宅,生活由兄弟供养,病、葬费用兄弟均摊。住房按兄上弟下,大兄大房厝,兄弟多的小弟无房分。土地按好坏搭配均分,其他财产按等值搭配抓阄。拆居时,女儿没有家庭财产继承权,全由男儿均分。各方无异议后,写成“阄书”(又称契约),每男各存一份。每份“阄书”上,均有主持人、见证人、当事人签名盖章,在社会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分家之际,选一吉日,家庭全体成员聚餐一顿,饭后正式分开,各自分灶煮饭,成家立业。
1950年实施新《婚姻法》后,农村家庭随社会进步而变化,抛弃族权、神权、夫权观念,提倡夫妻互尊互敬、男女平等,青年夫妻互称“爱人”,老年夫妻互称“老伴”,家庭成员中,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年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土地改革后,妇女走出厨房,参与政治活动和田间劳动,接受文化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其中部分优秀分子,锻炼成为乡村基层干部或农会骨干。家庭内部和睦相处,患难与共,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使家庭关系向民主型发展。
1954至1982年,农村集体化道路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阶段,男女社员在集体组织中,共同劳动,一起生活。家中男女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辅助劳力操持家务,少年儿童进学校读书。劳动收入(包括粮食、现金),由生产队按工分逐户核算,张榜公布。各个家庭经济状况明朗,生活消费比较简单、节俭。家庭内部财产分配,由家长主持,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经济管理趋向民主,男女均享有支配权。
1983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各户呈现“瓮中有余粮,柜中有新衣,口中无怨言,合家喜洋洋”升平气象,经济更富裕,生活大提高,住房条件、家庭设备大改善。农村家庭的变化,促进了邻里关系更加融洽,社会安定团结。
进入21世纪,境内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上升,直系家庭所占比例下降。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男到女家上门落户以及夫妇共同赡养双方父母蔚然成风。农村家庭文化程度向中等文化素质发展,家庭经济由传统农业型向亦农亦工亦商的综合型转变,生活水平由温饱型向宽裕型小康迈进。
2010年,家庭规模比全国户均3.10人多0.81人,比全省户均2.98人多0.93人。
三、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对家庭成员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教育的内容包括尊敬长辈、尊师求进、兄弟友爱、邻里和睦、交友至诚、处世正直、勤俭节约、爱护物产、勤劳创业、心地坦荡、维护家风、祭祀虔诚等。
后溪阮氏肇基祖哲公,是家庭教育的首倡者和楷模。年轻时,他白天辛勤劳作,亲为塾师多年,夜间挑灯苦读,博览群书。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年届45岁的阮哲被郡守提名为例贡,推荐赴京入国子监侍读,后参加科举考试,获中高等,任翰林庶吉士文林郎。景泰三年(1452年),阮哲授湖南卢溪知县,任职九年,为政廉明,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天顺五年(1461年),告老归乡,其行李除衣裳、书籍外,仅有碎银四金,众人惊讶不已,阮哲答曰:“众遗子孙以富贵,吾遗子孙以清贫。富贵生怠,清贫致警,何必剥民自润?”只留美德、不留金钱的家训流传至今。哲公后裔,把乃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不图私利、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作为代代相承的典范。阮哲妻蔡氏,悉心相夫教子,勤俭图强,督促子媳耕读传家。重视家庭教育,弘扬良好家风在境内蔚成风尚。
1950年后,家庭教育与时俱进,增加爱国爱乡、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知荣明耻、尊老爱幼、注重卫生、保护环境等内容。各个家庭更重视对子女的党纪国法、方针政策教育,对在学的子女,则主动配合学校、社会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家庭教育,企望子女学有长进,荣宗耀祖。
至2010年,境内受镇、县、市表彰的“五好家庭”有8户,王信英被县、市授予“敬老好儿女”称号。
第三节 计划生育
一、生育
自明正统六年(1421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境内人口出生呈盲目状态,受“多子多福”封建观念的影响,多胎生育很普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从清初到道光末年,是境内人口快速增长阶段。道光以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灾荒肆虐,卫生医疗条件差,婴儿成活率低,人口增长率下降。光绪十六至十八年(1890—1892),瘟疫流行,疾病丛生,使境内人口大幅度下降。
民国初年至28年(1912—1939年),境内人口逐年上升。民国29至38年(1940——1949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抓丁拉佚,使无辜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口呈负增长。
1950年后,随着社会秩序趋向稳定,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婴儿成活率明显提高,人口呈快速上升趋势。50年代,后溪形成有史以来最大生育高峰期。1957年人口1453人,比1951年1128人增加325人,增长28.8%。
1960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后溪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居高不下。1961年全大队1525人,1979年增至2876人,十八年间净增1351人。
1980年起,境内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1980年至2010年,后溪村人口增长率,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
二、组织机构
1956年,国家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63年9月,后溪大队响应政府号召,开始实行计划生育,采取上环、药具控制等节育措施。1985年2月,村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村委阮金实兼任村计生助理员。自1991年3月至2010年底,村计生历届助理员是:陈明楷、阮世钗、阮国忠。
1988年底,村计划生育协会成立,阮元和任首届协会会长。至2010年,村计生协会历经三届。
三、指标管理
(一)人口计划
20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实行年度控制指标管理。1965年后溪大队进行人口指标控制审核,并依据指标分解到各个生产队。70年代,提倡晚婚晚育,严禁早婚早育;提倡“晚、稀、少”,严禁“早、密、多”。1980年9月,开始实行一对育龄夫妇只生育一胎。1990年开始,实行人口目标任期责任制,把计划生育和人口计划的执行情况作为村委会年度业绩和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后溪村委会设立计划生育台账,专人登账,主任把关,实施计划生育科学管理机制。
(二)晚婚晚育
1950年至1977年底,境内男女青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满法定婚龄,始行婚嫁。1978年5月,仙游县革命委员会发出[78—134]号文件,规定农村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始可登记结婚;市民户口的男青年满28周岁、女满25周岁,持有晚婚证者,方可结婚。1988年4月,《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后,统一规定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为晚婚年龄;女24周岁以后生育为晚育。
(三)节育
20世纪50和60年代,采用以避孕方式为节制生育的主要手段,避孕的药具由政府免费提供。60年代初期,自觉实行绝育的育龄男女,主动到仙游县医院施行结扎手术。1967年,郊尾卫生院开办绝育手术业务,为实行计划生育提供方便。至1978年4月,后溪实施男扎15例,女扎49例。
其时,实施女扎的育妇是:(1队)颜福英、张淑娥。(2队)潘爱云、阮阿姐。(3队)朱玉芹。(5队)蔡玉容、阮秀兰、阮梅玉、蔡美金、陈阿英、卢林哥、阮钦云、王钦花、林英吓、陈冬姐。(6队)郑秀梅、林清英、陈其英、王芹英、阮亚玉、薛春治、许美姐。(7队)陈世芹、刘东姐、刘瑞烟、陈兰英、张成英、阮明秀、蔡丽清、张美金、蔡金钗。(9队)陈美云、林美钦、潘美连、连美英、阮美钦、蔡美烟、黄玉英、陈秀玉。(10队)蔡水烟。(12队)陈钦英、徐秀烟、阮清秀、阮美烟、蔡游罗、杨色珍、严燕钦。(13队)陈秀烟。(14队)陈加姐。
1980年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家喻户晓,98%以上育龄夫妇落实节育措施。
1983年全大队400对育龄夫妇中,393对采取了节育措施,占节育对象总数的98.3%,未采取节育措施的7对,占1.7%,其中175对采取绝育措施,占43.75%,11对领取独生子女证,占2.75%。
进入21世纪,规定生育一胎后45至90天内须上环(剖腹产半年后上环)。农村第一胎为女孩,在间隔3年又2个月,育妇达到24周岁又2个月,经审批可生胎第二胎,第二胎生育后45天内必须结扎。
计划生育部分优先优惠政策:1、法定奖励制度。2002年9月1日新《条例》实施以后,农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生育两个女孩并已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妻,一次性发给不低于500元奖励费;农村生育一个女孩,符合再生育条件,不再生育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一次性发给不低于1000元奖励费。2、奖励扶助制度。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发给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3、贡献奖励制度。对只生育一个女孩,符合再生育条件自愿放弃生育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村夫妻,每人每月发给不低于50元的奖励费,直至夫妻年满60周岁,自动转入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4、养老保险制度。对已落实绝育手术的二女户夫妻,每人每年给予100元的保险,直至对象年满60周岁为止,然后自动转入奖励扶助制度。60周岁后,可一次性领取全部养老保险金,也可以按年领取。5、安居工程,通过提供经济补助、协助解决建房用地和减免税费等办法,帮助无房居住或居住危房的农村计生二女户解决住房困难。县、镇各为安居对象提供5000元的补助。全县每年实施60户。6、成才工程。农村“二女结扎户”女儿上高中录取时,分别给予一级达标校加5分、二级达标校加10分;农村“二女结扎户”女儿高中学费给予减免30%,属于低保家庭的农村“二女结扎户”高中学费全免;考上大学本科的,一次性给予奖励2000元。
2010年,全村施行男扎9人,女扎9人,上环64人,人流19人,引产4人,二女扎5人。至是年底,历年来累计男扎218人,女扎390人,上环364人,药具节育5人,全村采取各种节育措施总人数977人。
(四)少生优育
1979年,境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9月,全面贯彻“晚婚晚育,少生优育”方针。大力提倡“一胎化”。
1983年元旦后,后溪大队管委会根据有关文件精神,作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限制第二胎,杜绝第三胎”的决定,并对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及其子女,给予一系列的优待,让独生子女优先入托、优先入学,直至14周岁。在农村,独生子女的自留地、自留果、责任田等,按双份安排,直至14周岁。对施行节育、绝育手术者,分别给予优待,奖励金如期兑现,标准不断提高。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部、群众,给予批评教育,并按政策征收社会扶养费。
1989年7月,后溪村委会认真落实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实施办法》,核实准生对象,发放准生证,进一步落实独生子女优待政策,促进计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1991年,遵照上级部署,开展“计划生育五清理”,推动计生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
2005年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落实为民办实事项目,执行“五项奖励制度”,实施“六项工程”。五项奖励制度包括:法定奖励制度、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贡献奖励制度、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家庭困难求助制度和农村二女结扎户养老保险制度。六项工程是:(1)保障工程:二女结扎户、独生户家庭免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母亲每年一次到县妇幼保健院免费进行生殖检查。(2)致富工程:对计生户实施小额贴息贷款,扶持他们自主创业,勤劳致富。(3)安居工程:本年度建房有困难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00元。(4)成才工程:农村独生户或二女结扎户,子女初中升高中时给予照顾5至20分,高中学费给予减免30%(属于低保户的全免),子女考上大学本科,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5)亲情工程:县、镇副科级以上干部挂钩扶持贫困二女结扎户。(6)幸福工程:帮助独女户或二女结扎户困难母亲发展生产。
在对计划生育实行奖励扶助的同时,对违反计生的处罚措施也更为严厉,从2008年起,政策外提前生育的,应交纳社会扶养费9470元;多生育一个孩子的应交纳社会扶养费28410元;多生育两个孩子或婚外生育一个孩子的,应交纳社会扶养费56820元,不按时参加“双查”和落实节育措施的,可以给予500元罚款。
2010年,后溪村对4户政策外生育者,征收社会扶养费123500元。依据“安居工程”给予林志东、阮子武、林新添、阮良辉等四户建房补助,每户5000元。全村有6户二女结扎户享受农村低保,有40户二女结扎户免费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四、计生成效
1980年至2010年底,后溪村矢志不移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30年间减少出生人口2113人。2010年度,全村出生婴儿66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2%,是年底,全村共领取《独生子女证》145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145户,《双女结扎证》46户。逐步实行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和创建“诚信计生”活动,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诚信化的良性轨道。
一、人口来源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阮庄阮氏肇基祖宏孙公六世孙阮哲,由阮庄迁居后溪,为后溪阮氏之宗。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阮庄宏孙八世孙阮鉴,由阮庄迁居顶沟尾,为下底寨、竹戈阮氏之宗。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惠安县官林颍水陈氏之一支,迁居仙游县香田里后溪,居于磨头山下,为长厝尾陈氏之宗。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蔡而书由仙游嘉禾乡仁德里(今龙华)磨头,迁居唐安乡香田里后溪,为下磨头荔谱蔡氏之宗。清乾隆中期(1760年前后),一对施姓年轻夫妇从惠安南埔移居香田里后溪靠近下磨头处,为长厝尾施氏之宗。清道光中期(1840年前后),一户林姓从枫亭兰友迁居顶沟尾,为下底寨九牧林氏之宗。清同治(1862—1874年)年间,一户林姓、一户刘姓,相继从惠安蜂尾迁至仙游香田里后溪西北隅定居,为顶磨头林氏、刘氏之宗。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蔡祥从莆田金沙铺东沙北上,迁居仙游香田里后溪,为长厝尾荔谱蔡氏之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阮丹堂举家由阮庄迁居长厝尾,为长厝尾阮氏之宗。另有一阮姓,系民国1,4年(1925年)长厝尾施元苍入赘后溪下厝,后回归长厝尾定居,其后代以阮氏为姓。
二、姓氏溯源
阮氏 源出于偃姓,乃黄帝之后。阮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八十九位的姓氏,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五。阮氏发祥地是河南陈留(今开封)。汉南阳太守阮况、侍中阮胥卿闻名于世;魏晋期间,阮籍、阮咸叔侄,与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故阮籍、阮咸后裔以竹林为堂号。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阮咸后裔弥之入闽,任晋安(今属福州)郡守,其后,弥之弟仁之、永之相继任晋安郡守,世称“晋郡三太守”,是为竹林阮氏入闽始祖。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阮弥之二十二世孙阮鹏,官协律郎,避黄巢乱,由福州迁移仙游嘉禾乡仁德里(今龙华),居于金沙上库,是为阮氏入仙始祖。阮鹏生宜耕、宜耘二子。宜耕四世孙阮沂和沂子阮程,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迁居莆田阮巷,是为莆阳阮氏肇基祖。宋代,阮氏在莆阳已衍成巨族。
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九月,阮鹏十六世孙、阮沂十一世孙阮宏孙,由莆田迁返仙游,居于香田里阮庄,是为阮庄竹林阮氏肇基祖。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宏孙六世孙阮哲,字原明,由阮庄迁居后溪。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阮哲四十五岁被荐充贡,景泰三年(1452年)出任湖南卢溪知县,天顺五年,(1461年)辞官归隐返后溪。其后裔改堂号“竹林”为“苏溪”,尊阮哲为苏溪阮氏始祖。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宏孙八世孙阮鉴,字景昭,官江西广信府教谕,与其兄阮马由阮庄析居顶沟尾,是为下底寨、竹戈阮氏之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阮丹堂由阮庄举家移居长厝尾,是为长厝尾阮氏之宗。
竹林阮氏昭穆辈序是:举进存仁、端庄树则、克家象贤、立朝司直、忠孝有源、图书惟式、名策清时、勋昭王国、奕叶绍兴、绪光千亿。1951年土地改革时,后溪境内有阮氏188户781人;至2010年,增至815户3176人。
蔡 源出于姬姓,乃黄帝之后。
西周始祖稷系黄帝曾孙帝喾的长子,袭姬姓。公元前1046年,稷的后裔周武王姬发克纣灭商,建立周朝。是年九月,武王分封天下,其中分封了五十五姬姓侯国。武王的十四弟姬度,封于蔡国,后人称之为蔡叔度。周贞定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47年),蔡国被楚所灭,蔡齐侯的后裔即以国号为姓,改姬姓为蔡氏。汉代,蔡氏发祥于河南陈留和济阳,因而堂号为“陈留”或“济阳”。
隋唐时,蔡用元、蔡用明两兄弟的祖先由河南迁居浙江。唐懿宗咸通元年(880年),用元、用明两兄弟随王潮、王审知入闽,由浙江钱塘迁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后由南安再迁往仙游,定居在仙游慈孝里赤湖蕉溪(今枫亭东宅)。北宋末丞相蔡京、蔡卞系用明之后;端明学士蔡襄系用元之第六世孙。蔡襄曾作《荔枝谱》,其后裔取“荔谱”为堂号,祠堂、祖居称为“荔谱流芳”。
北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蔡襄置家于莆田蔡宅。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至1224年),蔡襄五世孙蔡度由蔡宅迁居莆田东沙。明成祖年间,蔡度第十四代孙由蔡宅迁居仙游仁德里。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蔡而书和母亲、胞弟一家三口,由龙华金沙磨头迁居香田后溪,居于下磨头。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蔡祥从莆田东沙迁居后溪长厝尾。
1951年土地改革时期,后溪有蔡姓47户199人。至2010年底,增至190户714人。
林 源出于姬姓,乃黄帝之后。黄帝曾孙帝喾有四妃,次妃简狄生契。契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授为司徒,封于商地,赐子姓。契的十四世孙商汤,灭夏建商朝。商朝末年,纣王残暴无道,公元前1047年秋,纣王将胞叔比干剜心处死。比干正妃陈氏怀有3个月身孕,恐遭株连,带四名婢女逃出京城,躲进牧野郊外一片长林的石室中。武王克纣灭商后,陈氏已产下一男,取名坚,母子归顺周朝。武王以陈氏居长林而生坚,遂赐坚以林为姓氏,林坚即为林氏得姓始祖。
林坚长成,字长思,娶莘氏为妻,生子名载,字元超,世居西河郡(亦称博陵郡),自此子孙绵延不绝。西河郡(博陵郡)是林氏发祥地,故林氏堂号为西河、博陵。
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动荡,林、陈等姓入闽。林氏入闽始祖林禄,奉敕镇温陵(今泉州)晋,安,举家定居温陵。林禄69岁病故后,晋廷追授晋安郡王。唐初,林禄七世孙林茂,茂子孝宝,由温陵迁居莆田县北螺村。孝宝五世孙林披,由北螺迁居澄渚。林披先后任潭州、康州、睦州刺吏,生苇、藻、著等九子,均任州刺吏,世称“九牧”,林披是“九牧林”始祖。自唐至宋,九牧林分居全国各地。
清代后期,先后有2支林氏迁入后溪,其中来自惠安蜂尾林氏,定居在顶磨头,来自枫亭兰友林氏,定居在下底寨。
“九牧林”昭穆辈序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立身行道、显亲扬名、博施济众、崇德利生、宽裕温柔、发聪刚毅、乾堃化育、感应万霖。
1951年土地改革时,后溪有林氏20户84人。至2010年底,增至118户451人。
陈 源出于妫姓,乃帝舜之后。
帝舜生于姚墟,居于妫汭,因而有姚舜、妫舜之称。商朝末年,妫舜三十三世裔孙妫阏父,在西周任陶正(掌管全国陶瓷业的行政长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纣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分封天下。是年九月十八日,武王敕封阏父之子妫满为陈侯,划河南颍水河流域为陈国属地,定陈国都城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并把长女太姬嫁与妫满为妻。妫满谥号陈胡公,以国号为姓氏的陈氏自此始。
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八大姓入闽,陈润是陈氏入闽始祖,官居散骑常侍,居福州乌石山,自撰《闽中草寓记》,追忆入闽经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闽南啸乱,朝议大夫陈政奉旨戍闽,与子陈元光率士兵3600名,偏将120员,,自河南光州固始县出发,赴闽南靖边。陈政、陈元光父子屯兵于云霄绥安,把家眷安置在枫亭陈庐园。陈元光后累升开漳圣王,子孙四代相继开漳,其家属留居枫亭长达四十三年。
陈元光十一世孙陈洪进,生于枫亭陈庐园,后移居秀峰村侯览。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洪进纳漳泉二州十四县归宋,累功升至同知平章事、岐国公,病故后追授南康郡王。四弟七子俱受宋廷荣封,其五子均任州刺吏,世称“五侯”。宋代之后,五侯陈氏分散在兴化、闽南、广东、海南、台湾等地。
明正德(1506至1521年)年间,惠安县官林有两支陈洪进的后裔先后迁居仙游县香田里,前一支肇基于郊尾麟角,后一支肇基于后溪长厝尾。长厝尾的五侯陈氏,历史虽悠久,人口繁衍较慢。1951年1月,长厝尾陈氏仅有6户33人,2010年底,增至20户98人。
自第十三至二十二代,长厝尾颍水五侯陈氏的昭穆辈序是:良臣忠仕主,百行孝传家。
刘 刘氏的来源有五方面。
其一,源出于祁姓,乃帝尧之后。夏初,帝尧伊祁氏后裔之一支,被封于刘邑(今河北唐县),其后代以封地取姓为刘。
其二,源出于姬姓,乃帝舜之后。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武王同父异母弟姬高,其后代改姬姓为王氏。武王之孙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其后代也取刘为姓,是姬姓刘氏。
其三,源出于汉代匈奴族之后。
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淑女嫁予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为妻。按照匈奴习俗,贵族子女随母姓,因而冒顿单于后代为刘氏。南北朝时建立前赵,自称汉王的刘渊,即是匈奴刘氏后代。
其四,公元前206年刘邦建西汉,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前后历时420多年。“刘”是两汉的国姓,两汉天子经常给外族首领、有功之臣,赐以国姓,以示褒奖,如赐项伯、娄敬为刘姓。
其五、取“留”的谐音“刘”为姓氏。
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晋国君晋襄公病故,大臣们商议,派杜士会为使,赴秦国迎回襄公之弟公子雍续任晋君。士会君臣踏进故土,晋国已立襄公幼子夷皋为君。秦国护送部队与晋军发生激战,秦军败。杜士会等便留在秦国,其后代改杜姓为刘姓。
有以上五方面的来源,故中国刘姓人口众多,居全国姓氏排行第四位。但后溪刘姓人口较少,1951年初仅有5户24人,至2010年底,增至9户54人。
施 施氏来源有二。
其一,源出于姬姓,乃周公旦后裔。
公元前1046年秋,周武王封堂弟伯禽(周公姬旦长子)于鲁国,疆域在今山东省境内,春秋初期,鲁惠公之子姬尾(公子尾),字施父。姬尾生一子姬伯,姬伯取乃父之字“施”为姓氏,改称施伯,后裔即是姬姓施氏。此支施氏望族在浙江吴兴,堂号为“吴兴”。
其二,夏、商时期,有个施国,在今湖北省恩施县一带。商朝末期,施国灭,遗民遂取国号“施”为姓氏。
唐僖宗乾符年间(874至879年),黄巢起义军南下,途经福建。有王潮、王审知等河南光州固始县籍数万官兵随义军入闽后,留居福建,据州占县,独霸一方,唐廷委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驻守福州。秘书中丞施典随王潮兄弟入闽后,置家于泉州晋江南门外。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大理寺评事施炳由光州固始县举家南迁入闽,肇基于浔阳衙口乡。元中叶,施炳六世孙施守忠移居惠安南埔施厝村。不久,施典十三世孙施菊齐、施九思兄弟也移居南埔施厝。清乾隆中期,南埔施厝一对年轻夫妇迁居后溪长厝尾。
1950年初,长厝尾施氏只有2户7人。2010年底,增至5户35人。
施氏的昭穆辈序是:伯跃兆起、公乾于师、怀尚侯子、元建序宗、文章华国、诗礼传家。
三、人口分布
(一)村落人口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清朝末年,随着阮、陈、蔡、施、林、刘诸姓先民迁入定居,繁衍生息,绵延相继,始有后溪、下底寨、竹戈、长厝尾、下磨头、顶磨头、坝洋等自然村落。1950年后,上述七个自然村落构成后溪的主体。
从1950年底到2010年底的六十年间,后溪人口净增3400人。2010年底的人口是土地改革前夕人口的4倍。其中下底寨净增219人;竹戈净增308人;坝洋净增304人;长厝尾净增163人;下磨头净增372人;顶磨头净增470人;后溪自然村净增1564人。
(二)姓氏分布
2010年11月1日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后溪农业户口共有1157户4528人,其中阮氏815户3176人,占全村总人口的70.15%;蔡氏190户714人,占15.76%;林氏118户451人,占9.96%;陈氏20户98人,占2.16%;刘氏9户54人,占1.14%;施氏5户35人,占0.78%。
嫁入后溪的女村民中,还有张、杨、吴、王、周、欧、史、朱、郑、邱、连、余、彭、潘、赖、李、卢、徐、苏、沈、俞、谢、田、严、许、陆、方、凌、戴、肖、薛、翁、黄、郭、辜、颜、檀等37个姓氏,连同阮、蔡、林、陈、刘、施,境内共有姓氏43个。
(三)人口密度
郊尾镇是仙游县人口高密度区,后溪也是郊尾镇内人口密度较高的村庄,1951年土地改革时期,已达每平方公里386人。从1956年至1982年的农业集体化阶段,境内人口密度与全镇人口密度同步上升,上升幅度略高于全镇平均水平。
1982年的人口密度是1956年的2.14倍。
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大。由于后溪认真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建立流动人口登记卡,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密度上升势头减缓。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后溪村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40人/平方公里的11倍,是福建省平均人口密度445人/平方公里的3.5倍。
四、人口构成
(一)性别
从1950年至80年代,后溪人口总数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80年代后,男女比例趋向总体平衡。但不同年龄段又不平衡,1—15岁年龄段,男性比例大于女性;65岁以上老龄段,女性则高于男性。
(二)年龄
清朝末年至民国26年(1937年),社会秩序纷乱,天灾人祸频繁,境内单身汉多,人均寿命短,人口年龄呈成年型。
民国2年(1913年),染厝佛公底司马桥竣工,该桥是仙游县城通往枫亭的必经之路。举行通桥仪式时,后溪六祖三十二世庄光公(俗名九哥)时年仅36岁,其孙则勤(名金明)年已3岁,公孙两人一起参加落成剪彩活动,留下“三十六岁牵孙过桥”的轶闻。
民国26年至1949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瘟疫横行,医疗条件差,死亡率较高,自然增长率低,人口年龄仍呈成年型。
1950年后,人口年龄发生明显变化。政府重视民生,推广新式接生法,婴儿成活率大为提高,加上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青少年比例上升,人口结构呈年轻型。1969年底,全村人口2064人中,17周岁以下人口1045人,占50.63%。
1970至1989年,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深化,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少年儿童比例明显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境内人口年龄构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
90年代,人民生活向小康迈进,老年人口增多,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继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人口结构由成年型开始向老年型过渡。
进入21世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安定和谐,经济繁荣昌盛,医疗保险普及,人民健康长寿,初步构成人口老年型。
2010年60岁以上比率,与全国13.26%相比,高2.24个百分点,与福建省11.42%相比,高4.08个百分点;65岁以上比率,分别比全国8.87%、全省7.8%高3.16个、4.14个百分点。至2010年底,后溪村有80—89岁寿星84位,90岁以上寿星13位。其中阮
金明101岁。
阮金明,1911年11月25日生,子孙昌盛,五代同堂。
(三)文化
1949年前,由于经济状况等客观条件制约,绝大多数农家子弟未进校门接受教育,文化水平低,文盲覆盖面广。
1950年后普及小学教育,农家子弟和大多数女孩,进入郊尾中心小学接受教育,农村开展业余教育,村民文化程度有所提高。1960年仙游八中的创办和1970年复办,为后溪村民接受初等教育提供方便。1964年7月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后溪有小学生431人,初中生97人,高中生14人。1982年,有小学生1072人,初中毕业的378人,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56人。
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为农村子女接受教育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毕业生免试进入初中学习,农村文化水平更上一个台阶。1988年,后溪户籍人口中,有本科生、大专生13人,中专生48人,高中生162人,初中生513人。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达100%。
进入21世纪,每年有部分初中毕业生放弃上高中机会,或进厂打工,或随父母兄嫂从事二、三产业。离退休人员回原籍,提升了高学历人员比例。至2010年底,境内有博士11人,硕士15人,学士101人,教授、副教授12人。户籍挂靠后溪的郊尾中学、郊尾中心小学、郊尾中心幼儿园三所学校教师377人。但仍有308人中老年村民(其中女性212人)属文盲或半文盲,占总人口的6.8%。
五、职业
明、清时期,境内劳动人口,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只有个别家庭开店经商。民国时期,劳动人口仍以农业种植为主,少数人口从事私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服务业。
1950年至1982年,除国家选调的工作人员外,境内劳动人口中,97%人员从事农业耕作,3%人员从事建筑、运输、砖瓦厂等副业生产。
1983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传统农业局面,大批劳力有序转向二、三产业。1988年,全村1323个农业劳动力中,只有905个劳力从事1209亩农地耕作,418个劳力改行,其中从事建筑业的182人,从事运输业的34人,饮食服务业的17人,进厂务工的45人,文化体育卫生服务业9人,下海经商或外出办加油站131人。从事第一产业的905个劳动力中,还兼营家庭养殖业。1989年,饲养乳牛19头,年产牛乳25吨,出售生猪874只、羊113只。
2007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全村1672个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种植和家庭养殖的有75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5.1%;从事第二产业的436人,占26%;从事第三产业的389人,占23.3%;另有93人从事废纸、废铁、废塑回收,占5.6%。
六、经济 生活
(一)经济
明、清至民国时期,境内经济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粮食生产不足于自给,家庭收入以出售蔗糖、龙眼、桂圆为主。1950年至1956年,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属单一农业经济。零星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加工业,其收入比例不大。
1956年后,实行农业集体化,土地和龙眼归集体所有,农民靠挣工分维持家庭生活,盈余者年终有所分红,兑现部分现金购买年货;透支者需交部分透支款,不交者以口粮折款抵扣。粮食亩产和总产虽逐年上升,但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均口粮逐年下降,制约了社会财富人均占有量的增长。1981年后溪大队粮食总产515.9吨,比1965年总产431.1吨净增84.8吨,但1981年人均口粮仅是1965年的69.4%。
1983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溪社会生产总值直线上升。
1997年,全村年产值达3124万元,上交国家税金22.1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435元,是1981年人均55.3元的44倍。2010年,全村社会生产总值达6200万元,上交税金280万元,人均纯收入5600元,是1981年的101.3倍。1983年至2010年,全村耕地逐年递减。2010年底人均耕地只有0.26亩,是1951年人均1.08亩的24%,耕地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紧缺困境。
(二)生活
明、清至民国时期,境内贫雇农租地耕种,交纳田租后收成所剩无几,卯吃寅粮,三餐难继。自耕农也因苛捐杂税繁多,青黄不接时缺衣少食,生活艰难。
1950年后,后溪农民分到田地,生活基本得到保障。从单干户到互助组,所产粮食除上交公粮外,均由农户自行支配,物质生活初步得到改善。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从农业合作化到农业集体化,村民生活在低水平徘徊,进入70年代,市场商品较为充裕,凭证购物制渐被废除,但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仍较单调。
1984年后,富余劳力转向二、三产业,单一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化,村民收入成倍增长,生活得以显著改善,高中档家电涌进寻常百姓家。90年代,村民物质生活继续提高,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日益丰富,80%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12%的家庭迈进小康行列。
进入21世纪,村民生活继续向宽裕型小康迈进。至2010年底,全村人均年收入5600元,人均住房面积32平方米。平均每百户村民拥有小车2部、摩托车22辆、电冰箱56架,洗衣机47台,手机242部。2010年,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为46.18%,比2000年下降5.2个百分点。
第二节 婚姻 家庭
一、婚姻
明、清至民国时期,后溪婚姻习俗一般为一夫一妻制,个别乡绅纳妾。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乡俗,一般以男满18岁、女满16岁即达到结婚年龄,家长就会托媒说亲。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定双方婚姻关系,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有的家庭实行养媳婚、交换婚、表亲婚等,双方缺乏感情基础,由此造成的婚姻悲剧,时有发生。同时,受婚俗、环境、经济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困家庭男子,终身无法娶妻。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封建社会的婚姻弊端仍在延续,抱童养媳、买卖婚姻现象严重。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因不堪家庭暴力和虐待而投水、服毒、上吊自杀者,屡有发生。因生活所迫,忍痛卖儿鬻女者有之。孀居寡妇身受封建礼教观念的桎梏,改嫁或招夫被视为不贞,寡居苦熬遭受世俗岐视。家庭中“夫权”观念占支配地位,达官贵人、商贾富豪娶妻纳妾不受法律约束。
1949年后,废除早婚制,严禁买卖婚姻,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自1950年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境内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双方通过自由恋爱后,到区(乡)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确定婚姻关系。未到法定婚龄,或是家庭强迫包办者,政府不予登记。妇女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政治地位的提高,婚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择偶重人品而不重财礼。女子以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吃苦耐劳、举止文明作为选择伴侣的首要条件。结婚时不计较嫁妆、不讲究排场,侧重于孝顺长辈、勤俭持家、妯娌团结、家庭和睦、夫妻恩爱等道德、政治因素的考量。
1962年,随着经济好转,女性择偶偏向于现役军人或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国家工作人员。1966年后,受“左”的思潮影响,男女择偶讲究阶级成份。70年代,县城和集镇经济发展较快,受其影响,条件较好的女性,偏重于有地位、有固定收入的城镇男青年,并开始讲究彩礼的品牌和档次,“三车一转”是彩礼中必不可缺的“硬件”。少数受经济条件限制,难以找到合适对象的农家男青年,往往寻觅同等类型的家庭,进行“姑嫂换亲”或“三家转亲”,以期节省婚嫁开支。
1978年政府号召晚婚晚育,规定男满25岁、女满23岁,方可登记结婚。1988年,《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重申这一规定。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青年偏向选择条件优于自身的男友,不仅要讲究对方的经济状况,而且要考察对方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技术水平等。在彩礼上,男方大多都能满足女方对洗衣机、彩电、电冰箱、摩托车等的要求。男女外出打工、经商、求学的,也有选择外地人为配偶。
1990年起,按照宪法规定,男满22周岁、女满20周岁,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生活水平提高,境内婚姻形式趋于多元化。男方到女方落户入赘、丧偶老人重组家庭、孀居女性自由改嫁渐成社会习俗。自由恋爱、集体婚礼、旅游结婚,渐成婚姻新风尚。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夫妇共同赡养双方父母成为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封建社会中,出于政治、宗法、伦理、健康等方面原因,朝廷规定“同姓不得通婚”,1949年后,这一禁忌已被废除。改革开放后,只要男女双方彼此信赖、两厢情愿、无近亲血缘关系,同姓联姻亦被认可。境内同姓联姻者十来对,家庭和谐、子女健康聪颖。
二、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按其规模、结构划分,一般家庭有“核心家庭”型和“直系家庭”型。核心家庭包括父母和未成年子女,规模小,结构简单。直系家庭包括户主的父母、配偶、子、媳、孙等,规模较大。
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阮哲公迁居后溪后,境内的平民家庭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家庭大事、对外事务,全由男主人处理,丈夫是“当家的”,是家庭的主宰,妻子对丈夫而言,只是“做饭的”、“家里人”,只在家中料理家务,生儿育女,足不出户。在家庭中儿媳的地位更低下,若只生女孩必遭丈夫的埋怨和翁婆的指责;若婚后几年没有生育,更遭世人白眼。
核心家庭中,形成以长者为一家之主的“主从合作”状态。这种“主从合作”、“男尊女卑”的社会陋习,在农村不同阶层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农村中约有十分之一家庭,条件较好,经济较富裕,户主一般受过教育,以耕读传家,用孔孟之道教育子女、治理家庭,恪守伦理道德,这类家庭,处理家内矛盾和邻里关系,奉行“和为贵”信条,讲究“家和万事兴”、“夫妻和而家道兴”等,子女或晚辈不愿主动分家,怕落下不孝与不肖恶名。因此,形成多代人共聚的直系大家庭,以“四代同堂”为荣耀、“五代同堂”为楷模,以拆灶分居为耻辱。这样的直系大家庭通常是家长治理有方、兄弟友爱、妯娌团结、婆媳和睦、子孙孝顺。
1950年前,农村中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的现象普遍,因此“多子多福”、“人多势众”的封建传统观念,对平民家庭的影响深刻,企望“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在两性联姻方面,也要考虑对方是否大房大姓。在家庭问题上,多数家庭在老人去世后,兄弟便分家。也有因天灾人祸,家道中落或妯娌不睦,兄弟不和;或子女不孝,父母怀忿;或对待不公,心存岐偏等,导致一个直系家庭分拆成若干个较小家庭。兄弟分家,须请母舅主持,族亲作证。分家时,父母赡养、财产分配、权益继承等,经兄弟协商、族亲调解、母舅裁决,以求合理解决,一般是老人不离祖宅,生活由兄弟供养,病、葬费用兄弟均摊。住房按兄上弟下,大兄大房厝,兄弟多的小弟无房分。土地按好坏搭配均分,其他财产按等值搭配抓阄。拆居时,女儿没有家庭财产继承权,全由男儿均分。各方无异议后,写成“阄书”(又称契约),每男各存一份。每份“阄书”上,均有主持人、见证人、当事人签名盖章,在社会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分家之际,选一吉日,家庭全体成员聚餐一顿,饭后正式分开,各自分灶煮饭,成家立业。
1950年实施新《婚姻法》后,农村家庭随社会进步而变化,抛弃族权、神权、夫权观念,提倡夫妻互尊互敬、男女平等,青年夫妻互称“爱人”,老年夫妻互称“老伴”,家庭成员中,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年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土地改革后,妇女走出厨房,参与政治活动和田间劳动,接受文化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其中部分优秀分子,锻炼成为乡村基层干部或农会骨干。家庭内部和睦相处,患难与共,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使家庭关系向民主型发展。
1954至1982年,农村集体化道路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阶段,男女社员在集体组织中,共同劳动,一起生活。家中男女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辅助劳力操持家务,少年儿童进学校读书。劳动收入(包括粮食、现金),由生产队按工分逐户核算,张榜公布。各个家庭经济状况明朗,生活消费比较简单、节俭。家庭内部财产分配,由家长主持,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经济管理趋向民主,男女均享有支配权。
1983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各户呈现“瓮中有余粮,柜中有新衣,口中无怨言,合家喜洋洋”升平气象,经济更富裕,生活大提高,住房条件、家庭设备大改善。农村家庭的变化,促进了邻里关系更加融洽,社会安定团结。
进入21世纪,境内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上升,直系家庭所占比例下降。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男到女家上门落户以及夫妇共同赡养双方父母蔚然成风。农村家庭文化程度向中等文化素质发展,家庭经济由传统农业型向亦农亦工亦商的综合型转变,生活水平由温饱型向宽裕型小康迈进。
2010年,家庭规模比全国户均3.10人多0.81人,比全省户均2.98人多0.93人。
三、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对家庭成员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教育的内容包括尊敬长辈、尊师求进、兄弟友爱、邻里和睦、交友至诚、处世正直、勤俭节约、爱护物产、勤劳创业、心地坦荡、维护家风、祭祀虔诚等。
后溪阮氏肇基祖哲公,是家庭教育的首倡者和楷模。年轻时,他白天辛勤劳作,亲为塾师多年,夜间挑灯苦读,博览群书。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年届45岁的阮哲被郡守提名为例贡,推荐赴京入国子监侍读,后参加科举考试,获中高等,任翰林庶吉士文林郎。景泰三年(1452年),阮哲授湖南卢溪知县,任职九年,为政廉明,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天顺五年(1461年),告老归乡,其行李除衣裳、书籍外,仅有碎银四金,众人惊讶不已,阮哲答曰:“众遗子孙以富贵,吾遗子孙以清贫。富贵生怠,清贫致警,何必剥民自润?”只留美德、不留金钱的家训流传至今。哲公后裔,把乃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不图私利、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作为代代相承的典范。阮哲妻蔡氏,悉心相夫教子,勤俭图强,督促子媳耕读传家。重视家庭教育,弘扬良好家风在境内蔚成风尚。
1950年后,家庭教育与时俱进,增加爱国爱乡、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知荣明耻、尊老爱幼、注重卫生、保护环境等内容。各个家庭更重视对子女的党纪国法、方针政策教育,对在学的子女,则主动配合学校、社会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家庭教育,企望子女学有长进,荣宗耀祖。
至2010年,境内受镇、县、市表彰的“五好家庭”有8户,王信英被县、市授予“敬老好儿女”称号。
第三节 计划生育
一、生育
自明正统六年(1421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境内人口出生呈盲目状态,受“多子多福”封建观念的影响,多胎生育很普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从清初到道光末年,是境内人口快速增长阶段。道光以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灾荒肆虐,卫生医疗条件差,婴儿成活率低,人口增长率下降。光绪十六至十八年(1890—1892),瘟疫流行,疾病丛生,使境内人口大幅度下降。
民国初年至28年(1912—1939年),境内人口逐年上升。民国29至38年(1940——1949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抓丁拉佚,使无辜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口呈负增长。
1950年后,随着社会秩序趋向稳定,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婴儿成活率明显提高,人口呈快速上升趋势。50年代,后溪形成有史以来最大生育高峰期。1957年人口1453人,比1951年1128人增加325人,增长28.8%。
1960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后溪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居高不下。1961年全大队1525人,1979年增至2876人,十八年间净增1351人。
1980年起,境内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1980年至2010年,后溪村人口增长率,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
二、组织机构
1956年,国家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63年9月,后溪大队响应政府号召,开始实行计划生育,采取上环、药具控制等节育措施。1985年2月,村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村委阮金实兼任村计生助理员。自1991年3月至2010年底,村计生历届助理员是:陈明楷、阮世钗、阮国忠。
1988年底,村计划生育协会成立,阮元和任首届协会会长。至2010年,村计生协会历经三届。
三、指标管理
(一)人口计划
20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实行年度控制指标管理。1965年后溪大队进行人口指标控制审核,并依据指标分解到各个生产队。70年代,提倡晚婚晚育,严禁早婚早育;提倡“晚、稀、少”,严禁“早、密、多”。1980年9月,开始实行一对育龄夫妇只生育一胎。1990年开始,实行人口目标任期责任制,把计划生育和人口计划的执行情况作为村委会年度业绩和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后溪村委会设立计划生育台账,专人登账,主任把关,实施计划生育科学管理机制。
(二)晚婚晚育
1950年至1977年底,境内男女青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满法定婚龄,始行婚嫁。1978年5月,仙游县革命委员会发出[78—134]号文件,规定农村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始可登记结婚;市民户口的男青年满28周岁、女满25周岁,持有晚婚证者,方可结婚。1988年4月,《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后,统一规定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为晚婚年龄;女24周岁以后生育为晚育。
(三)节育
20世纪50和60年代,采用以避孕方式为节制生育的主要手段,避孕的药具由政府免费提供。60年代初期,自觉实行绝育的育龄男女,主动到仙游县医院施行结扎手术。1967年,郊尾卫生院开办绝育手术业务,为实行计划生育提供方便。至1978年4月,后溪实施男扎15例,女扎49例。
其时,实施女扎的育妇是:(1队)颜福英、张淑娥。(2队)潘爱云、阮阿姐。(3队)朱玉芹。(5队)蔡玉容、阮秀兰、阮梅玉、蔡美金、陈阿英、卢林哥、阮钦云、王钦花、林英吓、陈冬姐。(6队)郑秀梅、林清英、陈其英、王芹英、阮亚玉、薛春治、许美姐。(7队)陈世芹、刘东姐、刘瑞烟、陈兰英、张成英、阮明秀、蔡丽清、张美金、蔡金钗。(9队)陈美云、林美钦、潘美连、连美英、阮美钦、蔡美烟、黄玉英、陈秀玉。(10队)蔡水烟。(12队)陈钦英、徐秀烟、阮清秀、阮美烟、蔡游罗、杨色珍、严燕钦。(13队)陈秀烟。(14队)陈加姐。
1980年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家喻户晓,98%以上育龄夫妇落实节育措施。
1983年全大队400对育龄夫妇中,393对采取了节育措施,占节育对象总数的98.3%,未采取节育措施的7对,占1.7%,其中175对采取绝育措施,占43.75%,11对领取独生子女证,占2.75%。
进入21世纪,规定生育一胎后45至90天内须上环(剖腹产半年后上环)。农村第一胎为女孩,在间隔3年又2个月,育妇达到24周岁又2个月,经审批可生胎第二胎,第二胎生育后45天内必须结扎。
计划生育部分优先优惠政策:1、法定奖励制度。2002年9月1日新《条例》实施以后,农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生育两个女孩并已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妻,一次性发给不低于500元奖励费;农村生育一个女孩,符合再生育条件,不再生育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一次性发给不低于1000元奖励费。2、奖励扶助制度。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发给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3、贡献奖励制度。对只生育一个女孩,符合再生育条件自愿放弃生育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村夫妻,每人每月发给不低于50元的奖励费,直至夫妻年满60周岁,自动转入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4、养老保险制度。对已落实绝育手术的二女户夫妻,每人每年给予100元的保险,直至对象年满60周岁为止,然后自动转入奖励扶助制度。60周岁后,可一次性领取全部养老保险金,也可以按年领取。5、安居工程,通过提供经济补助、协助解决建房用地和减免税费等办法,帮助无房居住或居住危房的农村计生二女户解决住房困难。县、镇各为安居对象提供5000元的补助。全县每年实施60户。6、成才工程。农村“二女结扎户”女儿上高中录取时,分别给予一级达标校加5分、二级达标校加10分;农村“二女结扎户”女儿高中学费给予减免30%,属于低保家庭的农村“二女结扎户”高中学费全免;考上大学本科的,一次性给予奖励2000元。
2010年,全村施行男扎9人,女扎9人,上环64人,人流19人,引产4人,二女扎5人。至是年底,历年来累计男扎218人,女扎390人,上环364人,药具节育5人,全村采取各种节育措施总人数977人。
(四)少生优育
1979年,境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9月,全面贯彻“晚婚晚育,少生优育”方针。大力提倡“一胎化”。
1983年元旦后,后溪大队管委会根据有关文件精神,作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限制第二胎,杜绝第三胎”的决定,并对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及其子女,给予一系列的优待,让独生子女优先入托、优先入学,直至14周岁。在农村,独生子女的自留地、自留果、责任田等,按双份安排,直至14周岁。对施行节育、绝育手术者,分别给予优待,奖励金如期兑现,标准不断提高。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部、群众,给予批评教育,并按政策征收社会扶养费。
1989年7月,后溪村委会认真落实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实施办法》,核实准生对象,发放准生证,进一步落实独生子女优待政策,促进计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1991年,遵照上级部署,开展“计划生育五清理”,推动计生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
2005年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落实为民办实事项目,执行“五项奖励制度”,实施“六项工程”。五项奖励制度包括:法定奖励制度、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贡献奖励制度、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家庭困难求助制度和农村二女结扎户养老保险制度。六项工程是:(1)保障工程:二女结扎户、独生户家庭免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母亲每年一次到县妇幼保健院免费进行生殖检查。(2)致富工程:对计生户实施小额贴息贷款,扶持他们自主创业,勤劳致富。(3)安居工程:本年度建房有困难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00元。(4)成才工程:农村独生户或二女结扎户,子女初中升高中时给予照顾5至20分,高中学费给予减免30%(属于低保户的全免),子女考上大学本科,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5)亲情工程:县、镇副科级以上干部挂钩扶持贫困二女结扎户。(6)幸福工程:帮助独女户或二女结扎户困难母亲发展生产。
在对计划生育实行奖励扶助的同时,对违反计生的处罚措施也更为严厉,从2008年起,政策外提前生育的,应交纳社会扶养费9470元;多生育一个孩子的应交纳社会扶养费28410元;多生育两个孩子或婚外生育一个孩子的,应交纳社会扶养费56820元,不按时参加“双查”和落实节育措施的,可以给予500元罚款。
2010年,后溪村对4户政策外生育者,征收社会扶养费123500元。依据“安居工程”给予林志东、阮子武、林新添、阮良辉等四户建房补助,每户5000元。全村有6户二女结扎户享受农村低保,有40户二女结扎户免费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四、计生成效
1980年至2010年底,后溪村矢志不移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30年间减少出生人口2113人。2010年度,全村出生婴儿66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2%,是年底,全村共领取《独生子女证》145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145户,《双女结扎证》46户。逐步实行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和创建“诚信计生”活动,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诚信化的良性轨道。
相关地名
后溪村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