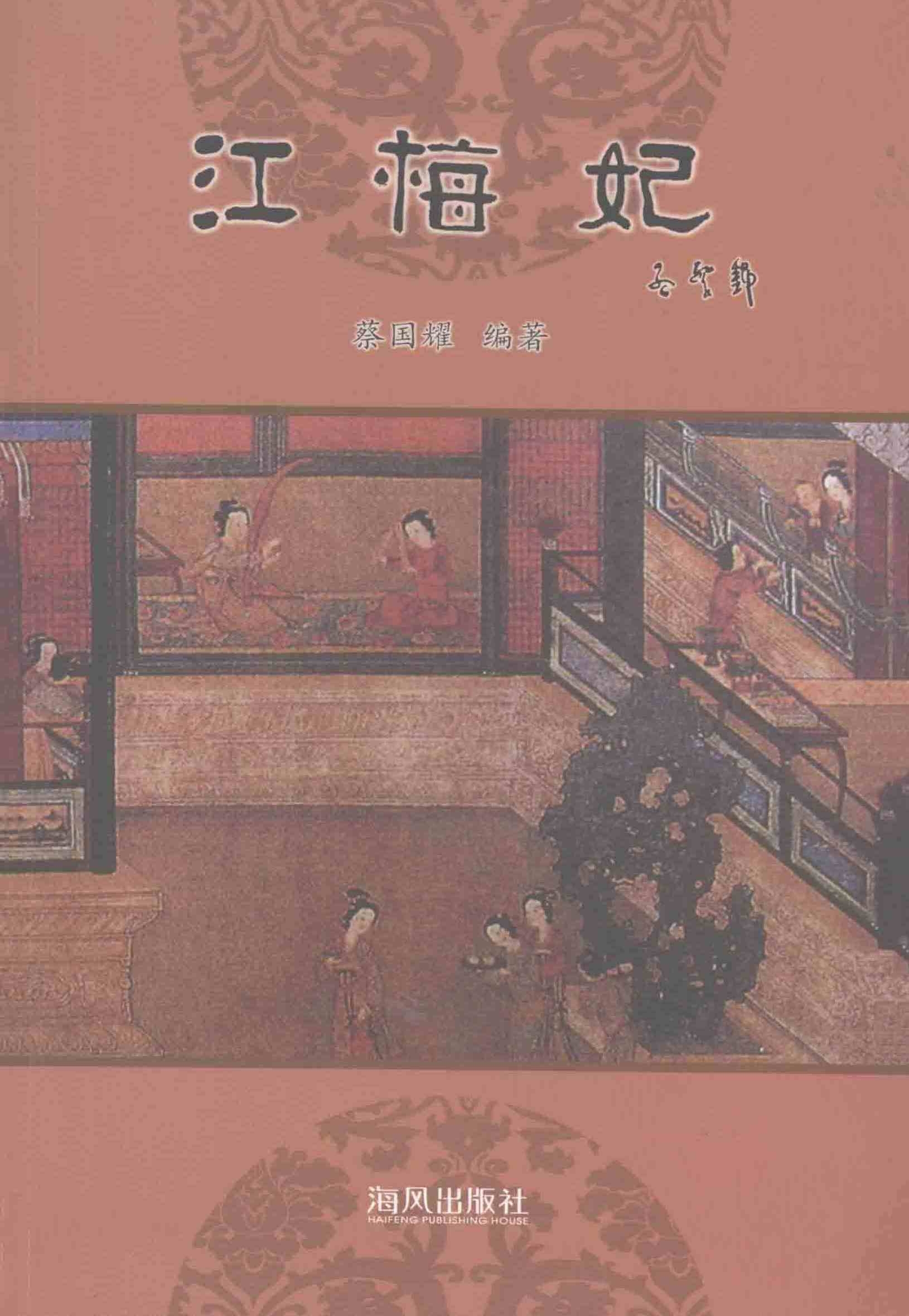内容
第十章千年吟赞江梅妃
第一节宋代的作品
一、李纲首喻梅妃
北宋后期,李纲的《梅花赋》首次以梅花比喻梅妃。李纲(1083—1140),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徙居无锡。北宋政和二年(1112)进士,官至丞相。据《李纲年谱》,宣和三年(1121),李纲转宣教郎,泛大江归在海陵(今江苏泰州)的父亲膝下,因唐时宋广平的《梅花赋》已阙,而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且标格清高为余花未及,遂作《梅花赋》:梅花,“丰肌莹白,娇额涂黄,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在小说笔记篇,笔者已分析,由其“丰肌”、“娇额涂黄”、“临镜严妆”,可知与《梅妃传》的梅妃对不上。《梅妃传》里的梅妃:偏瘦,讥杨贵妃为肥婵;“铅华不御得天真”。《梅花赋》中的梅妃,是宋本《梅妃传》以前的梅妃形象,而为宋本《梅妃传》的创作提供了一些素材。
《全宋诗》27册载李纲咏梅诗32首及咏开元天宝史事诗10多首,仅宣和元年(1119)李纲1监沙县(属今福建)时作的《用韵赋梅花三首·再赋一首》与此后《梅妃传》中的梅妃事相近。即“粉质不浴骊汤温”,天生丽质,不需像杨贵妃的浴骊汤;“吹残楼角真可惜”,但却不是《楼东赋》中的楼东!
二、晁说之诗咏梅妃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进道、伯以。号景迂生、老法华、国安堂主。河南开封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元祐(1086—1093)时相继任兖州司法参军、蔡州教授。绍圣(1094—1097)时为宿州教授,元符(1098—1100)中知磁州武安县。他上书指斥王安石政事之非与绍述诸臣之谬,入党籍邪等,崇宁二年(1103)知定州无极县,后相继任嵩山中岳祠、陕州集津仓、华山西岳祠。大观(1107—1110)间监明州船场。政和四至六年(1114—1116)通判鄜州,宣和元年(1119)提点南京鸿庆宫。三年初春知成州。五年因岁旱尽蠲其税,而转运使大怒,乞致仕。靖康元年(1126)二月应诏封事,任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坚决反对太子读《孟子》,遂免职流放,九月出京逃亡后避兵高邮。高宗继位,授以徽猷阁待制兼侍读,后提举杭州洞宵宫。建炎二年(1128)寓居海陵,三年正月七日卒于建康,71岁。赠通奉大夫、后累赠至光禄大夫。
说之的《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之五咏道①:
莫道梅花取次开,馨香须待百层台。
不同碧玉小家女,宝策皇妃元姓梅。
该诗未点明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的梅妃。而此后《梅妃传》中的梅妃姓江,不姓梅。
《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简称《枕》诗)是组诗。《全宋诗》卷1211晁说之集中载有说之与圆机酬和的诗57首。
从这些诗中可知:
圆机,即郭执中。《万姓统谱》卷一百十九与《记纂渊海》卷二十五引《舆地纪胜》记载:郭执中,华亭人,累官枢密承旨,建中靖国初应诏言事切直,忤蔡京,籍为元祐党,入邪等,斥居同谷(今甘肃成县)20多年,因家焉。绍兴初,执中集乡豪御金,立斩来招降的金使,后以功累迁新安郡王。郭执中多才多艺:“却问人间梅几种,郭仙尔有古人辞①”;“君乎学问二刘比,南北该通酸自甘②”;他“淡墨书名二十年③”;“当年郭有道,今日更谈禅④”。
(一)时间。《枕》诗作于北宋后期。《枕》诗之二载“梨园弟子强因依,羯鼓声中学御诗。十月胡雏来唤仗,新梅谁复增新辞。”即宋金协议夹攻辽国之事。《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载:宣和二年(1120)八月,宋金签订联合夹攻辽国的《海上盟约》。
冬十月,金主草国书,遣哈噜与政等来报。聘书中大略云:“前日赵良嗣等回,许燕京东路州镇,已载国书,若不夹攻,应难如约。今若更欲西京,请便计度收取,若难果意,冀为报示。”
《枕》诗之五有句:“莫道梅花取次开,罄香须待百层台(四库本注:今洛中名园犹竞于梅台,贵自上接其香)。”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一书指出:宋代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记载富郑公梅台、湖园梅台、大隐庄早梅都是梅花专题景观。张氏(景昱、景昌兄弟)南园“凭高种岭梅”,“纷披百株密⑤”。品种也有多样;中有高台俯临,是赏梅的最佳处,极负盛名①。仁宗嘉祐(1056—1063)以来,尤是神宗熙宁(1068—1077)间,洛中名流园林雅集,诗酒游观,梅作剧增。这是说之回忆并联想洛阳的梅景。
《枕》诗之七喻梅是霜女、月娥下降人间。据查,元丰五年(1082)苏轼咏《红梅》三首。此后,诗人们普遍以月宫嫦娥、瑶池仙姝、姑射神女、深宫贵妃、林中美人、幽谷佳人等美人形象来喻梅。
《枕》诗之十四自注:“今日天庆节,两处朝拜。又孝惠忌行香疲,且手寒,草草增愧也。然不犯从前梅事如前村之类,亦可一笑也”。据查,宋真宗掩饰澶渊城下之盟的耻辱,景德五年(1008)伪造天书下降承天门,下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并于十一月决定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命各州兴建天庆观。百官赴宫观或僧寺进香,朝廷赐百官御宴。京城宫观斋醮七天,后相继减为三天、一天。宋仁宗初年,因天庆等5节“费用尤广”,遂将各宫观同时设醮改为轮流设醮②,后渐废罢。到南宋时,京城不再庆祝;仅外州官员赴天庆观朝拜和休假两天③。由上可知:说之一天内朝拜二处,是北宋后期。
《枕》诗后还有:《亡友陈无已有立春诗,云:朱门谁送青丝莱,下里难酬白雪歌,颇为都下诗人所称,今日立春诵之而作》。
陈无已即陈师道,逝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还有《七月一日作(昨日闻陈莹中卒)》。陈瓘(1057—1122),字莹中,号了翁、了斋,沙县人。元丰二年(1079)进士,徽宗时历右司谏,权给事中。《宋史》本传称其最被蔡京、蔡卞忌恨,故得祸最酷。崇宁中,以党籍除名,卒于楚州。靖康中,赠谏议大夫。绍兴中,赠溢忠肃,有《了斋集》。
(二)地点。《枕》诗的前面,有《依韵谢圆机送梅绝句二首》、《再和圆机梅绝句》、《申前意和圆机绝句梅花》,均是说之在西安与执中的酬和。《枕》诗之一有句“据渭浮泾雪浪开”。之三有句“泾南渭北花如锦,太白山头只有梅”。泾水、渭河、太白山(终南山)均在今陕西。之四有句“孤芳寒艳绝难依,鄴下关中不赋诗”。关中的范围相当于今之陕西。之六有句“梅寒恨不出豳诗”。《诗》国风有“豳风”,共7篇27章。唐开元十三年(725),改豳州为邠州,故治在今陕西彬县。
程杰教授查知,《枕》诗作于宣和四年(1122)春,晁说之知成州(今甘肃成县)时①。该地在甘肃东南部,与陕西相邻,距西安不远。
《全宋诗》中收有晁说之24首咏梅诗,其他23首再未提及梅妃。笔者查阅说之的《景迂生集》二十卷、《儒言》一卷、《晁氏客语》一卷,也未谈及梅妃。可知这是北宋中期以来喻梅为美人的文风中,继李纲喻梅花为梅妃后,再喻梅花为梅妃。皆为特例,均跟《梅妃传》中的梅妃形象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晁说之笔下的梅妃比李纲笔下的梅妃更具体,她不是碧玉小家女,而是皇妃;该诗似乎还对张泌笔下的梅妃予以塑造,即与梅花相关联而咏。
三、江妃转化为江梅妃
南宋时,高观国的《满江红》词有句:“十万江妃留醉梦,二三沙鸟惊吟魄”。项安世(1129—1208)的《腊尽仅得微雪》
诗有句:“可是江妃悭笑粲,都能无意管呻吟”。
卒于乾道、淳熙间(约1173—1174)的侯置是最早咏及梅妃的词人,其《水龙吟·老人寿》词有句:“正梅妃月姊,雪肌粉面,争妆点、潇湘好”。可知,梅妃的故事传衍在潇湘(今湖南)一带。
赵以夫(1189—1256),字用父,号虚斋,福建长乐人。嘉定十定(1217)进士,资政殿学士,吏部尚书兼侍读,与刘克庄同纂修国史,可能因此与闻福建诞生的宋本《梅妃传》、《莆阳比事》梅妃入侍条。其《解语花》词序曰:东湖赋莲后五曰,双苞呈瑞。昌化史君持以见遗,因用时父韵。词为:
红星湿月,翠影停云,罗袜尘生步。并肩私语。知何事、暗遣玉容泣露。闲情最苦。任笑道、争妍似妒。倒银河、秋夜双星,不到佳期误。
拟把江妃共赋。当时携手,烟水深处。明珠溅雨。凝脂滑、洗出一番铅素。凭谁说与。莫便化、彩鸾飞去。待玉童,双节来迎,为作芙蓉主①。
词中咏及“争妍似妒”、“拟把江妃共赋”,隐约点到江梅妃的故事。联系到关于解语花的典故,才能明瞭。《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条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而宋代比赵以夫更早的文人已谈到解语梅花的典故。
李之仪,字端叔,沧州无棣人,进士。政和七年(1117)终朝请大夫。年80余,有姑溪居士文集。其《清平乐·橘》有句:“画屏斜倚窗纱。睡痕犹带朝霞。为问清香绝韵,何如解语梅花②”。
笔者认为,唐时明皇喻杨贵妃为解语花(千叶百莲)后,北宋时文人又喻梅花为解语花。到南宋初,赵以夫的《解语花》词就联系了杨、梅两妃的故事。
但是,还有认为江妃是水神的。如黄公绍,字直翁,邵武人,咸淳元年(1265)进士,隐居樵溪。有在轩集。其《汉宫春·郡圃赏白莲》词,就有句:“青冥世界,向龙宫、涌出江妃①”。
淳祐十年(1250)至咸淳五年(1269)间,莆田人刘克庄写了6首关于梅妃的诗。
景定三年(1262)进士的庐陵人刘辰翁,其《酹江月·北客用坡韵改赋访梅》词有句:“戴花人去,江妃空弄明月”。到《八声甘州(春雪奇丽,未能赋也,因古岩韵志喜)》词,又有句“招得梅妃魂也,好似去年春”。
综上所述,诗词中,江妃转化为江梅妃的时间为乾道、淳熙间(1173—1174)至咸淳五年(1269)。
四、刘克庄三咏江梅妃
南宋后期的莆田人刘克庄(1178—1260),所咏梅妃的诗词最多。
开禧元年(1205),刘克庄19岁,在临安,补国子监生。嘉定二年(1209),以门荫补将仕郎。次年,初仕靖安主簿。嘉定六年(1213)七月至七年父卒乡居,十二年初夏至十四年冬监南岳祠,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八月辞广西经略安抚使幕乡居。十七年春,刘赴临安改秩宣教郎,看到并赋诗《明皇按乐图》。绍定元年(1228)秋至六年,刘因梅花案而贬主仙都观,端平三年(1236)春至嘉熙元年(1237)春贬主玉局观,嘉熙元年中秋至三年九月贬主云台观,淳祐元年(1241)冬至四年秋贬主崇禧观。六年,刘以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十二月至十一年三月贬主明道宫①。而“祠官之任,家居而食厚禄②”。刘克庄乡居时,或是看到莆田同乡李俊甫写的《莆阳比事》(内录有“梅妃入侍”条)或是看到宋本《梅妃传》,淳祐十年(1250)始咏梅妃。即《梅花十绝答石塘二林》三叠之五:
半卸红绡出洞房,依稀侍辇幸温汤。
三郎方爱霓裳舞,珍重梅姬且素妆。
温泉宫在骊山,距西京长安60里。唐玄宗虽方爱善跳霓裳羽衣舞的杨贵妃,但仍珍重素妆的梅姬。
淳祐十一年(1251)四月,刘克庄在里居5年后复出,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等官,闰十月又罢官。乡居时,刘克庄于宝祐元年(1253)看到两妃的像,遂咏诗《唐二妃像(梅妃、杨妃)》:
不但烹三庶,东宫亦屡危。
元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
素艳羞妆额,红膏妒雪肤。
宁临白刃死,不受赤眉污。
唐开元二年(714)十二月,玄宗因宠赵丽妃而封其子李瑛为太子。赵丽妃亡故后,玄宗因宠武惠妃而钟爱其子寿王。二十四年十一月,武惠妃诬陷:太子结党、欲害惠妃母子并指斥玄宗。玄宗欲废太子与鄂王、光王,中书令张九龄据理力谏而丢了宰相之职。二十五年四月,惠妃又指使女婿杨洄诬陷太子与鄂王、光王及太子妃之兄薛锈异谋兵变。四月乙丑日,玄宗废太子、鄂王、光王为庶人,流薛锈于瀼州,同日又赐死4人,坐流贬者数十人,株连甚众。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评曰:“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①”。
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安禄山包藏祸心而认杨贵妃为母;杨亦用锦绣做大襁褓洗儿裹之、生日赐钱,演出干母子的丑剧。唐元和十二年(817)元稹《连昌宫祠》已有句:“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姚崇、宋璟是名宰相。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天宝十载(751)下记:“自是安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醒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这些记载与《开元天宝遗事》卷下《金牌断酒》条相符。唐玄宗等人与杨贵妃三姐虢国夫人有私情。安禄山随后率军叛乱,屡危朝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素妆但天姿国色的江梅妃,屡被杨贵妃嫉妒而贬至冷宫,在安史之乱时宁死而不受污辱。“素艳羞妆额”的出处在《白氏六帖》卷四《人日》的“梅花妆”。五代末明经及第的莆田人徐昌图《木兰花令》,最早咏及:“汉宫花面学梅妆②”。
此后,刘克庄看到《明皇幸蜀图》,并赋诗。
宝祐四年(1256),克庄《冬夜读几案间杂书,得六言二十四首》,其十七咏道:
李妹玉曜肤色,梅娘淡妆素衣。
大主嗔老奴爱,三郎怕肥婢知。
唐代,陈鸿的《长恨歌传》喻杨贵妃为汉武帝所宠的李夫人。李夫人出身于中山国的音乐歌舞之家,容貌姣好,早卒。武帝怜而画其像,作《悼李夫人赋》,以皇后规格礼葬,封其两个兄长。唐末,莆田人徐寅曾咏《李夫人二首》,有句:“人间乐极即须悲”,“汉王不及吴王乐”。梅妃玉肤明亮,似李夫人的妹妹。她淡妆素衣,仍美貌无比,连太监高力士也望之动心。玄宗既嗔斥高力士,又怕自己亲近梅妃时被杨贵妃知道。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738)五月条载:高力士是“我(玄宗)家老奴”。淳祐四年(1244)秋,刘克庄除江东提刑时,作《杂咏一百首·高力士》,已咏:“五十年间事,浑如晓梦余。三郎南内里,何况老家奴”。南内即唐代长安的兴庆宫,原为玄宗当藩王时的故宅。玄宗即位后,高知内侍省事,宠任极专。杨贵妃体态丰满。景定元年(1260),克庄《海棠七首》之四描述:“一种穠纤态,三郎未必知。浪将妃子比,妃子太浓肥”。
景定元年(1260)十一月,刘克庄权兵部侍郎等官。三年三月,权工部尚书,兼侍读,九月告老归里。四年封莆田县开国子,加食邑三百户。五年,克庄的《诸公载酒贺余休致水村农卿有诗次韵》之八也有句:“论定会盼银信召,眷浓漫妒玉环肥(梅妃目太真为肥婢)”。
五、刘克庄《读〈开元天宝遗事》一首》
咸淳三年(1267),克庄81岁,致仕里居,失明,进封莆田县开国男,食邑达九百户。四年五月,特除龙图阁学士,仍致仕。克庄失明后,赋诗《读〈开元天宝遗事〉一首》,曰:
环子受兵火涴,梅姬如玉雪清。
二妃未免遗恨,三郎可煞无情。
该诗把受兵火沾污的杨妃与如白雪清的梅妃作了对比,放弃了从前已咏的杨妃祸国的看法,矛头直指宠用奸相权宦、沉溺声色的唐玄宗。早在唐时,莆田人、乾宁元年(894)进士徐寅
《开元即事》诗已归罪于杨国忠,有句评价杨贵妃:“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莆田人、乾宁二年进士黄滔也有类似看法,《马嵬》诗咏道:“锦江晴碧剑锋奇,合有千年降圣时。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
《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五代后周王仁裕著。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天水人,以文辞知名于秦陇间,唐末任秦州节度判官,五代时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工诗文、晓音律,与和凝等以文章知名于五代。有《西江集》、《唐末见闻录》等著作。
新旧《五代史》有传。
南宋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载《开元天宝遗事》为4卷159条。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一书,言明传世刻本有:明张氏建业铜活字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均二卷。200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开元天宝遗事》,言明张氏铜活字本有黄丕烈跋3条;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刻本二卷,有王仁裕自序,目录列146条、但正文缺“暖玉鞍”条;两种版本均重印自宋绍定戊子(1228)桐江学宫刊本(山阴陆子遹书)。可知,绍定刊本时已只有146条。
如今我们看到的只有146条,其中没有江梅妃的内容。北宋大诗人苏轼,赋有《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南宋时王灼的笔记《碧鸡漫志》,汇有《开元天宝遗事》的《凌波曲》佚文。刘克庄所见的《开元天宝遗事》,应是兴化军学刊本。笔者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开元天宝遗事》足本中有记载江梅妃,详见下述。二是刘克庄失明后浮想联翩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莆田两位诗人的作品均未提江梅妃。
黄滔(840—911),字文江,乾宁二年(895)进士,国子四门博士,寻弃职返乡。闽王王审知奏请朝廷授为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今福州)节度推官。黄滔规劝王审知放弃称帝,是闽中诗坛的领袖,有《马嵬》诗、《马嵬二首》诗、《明皇回驾经马嵬赋》等①,并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评论《长恨歌》,皆未提到江梅妃。清代李调元的《赋话·新话》卷四指出:“唐人咏马嵬诗甚多,文江更演为赋耳。芊眼凄戾,不减《长恨歌》、《连昌宫词》。”马积高《赋史》372页指出:唐朝的盛衰,玄宗时期是个关键。且中唐以后,皇帝常常播迁,晚唐尤甚,故诗人多喜咏玄宗及贵妃事,晚唐律赋中除莆田人黄滔的《明皇回驾经马嵬赋》外,尚有徐寅(莆田人)、王棨及张读各一篇,而黄滔这一篇写得最为凄凉,充满着感叹帝王末路的感情,尤显有讽谕时世之义,不独以对语为工。
徐寅,字昭梦(865?—928?)②,乾宁元年(894)进士,秘书省正字。唐亡后,闽王王审知聘为书记官,后唐同光元年(923)李存勖要闽王诛杀徐寅,寅遂辞官隐居家乡。其诗作之多,为唐五代闽人之冠。徐寅有《华清宫》、《再幸华清宫》、《开元即事》、《马嵬》等诗和《过骊山赋》等,也未谈及江梅妃。
南宋洪迈(1123—1201)著《容斋随笔》一书,卷一《浅妄书》驳《开元天宝遗事》一书4事而认为:《开元天宝遗事》是浅妄之书;近岁,兴化军学所刊此书,可毁。据《四库全书总目》,洪迈,字景庐,鄱阳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容斋随笔》先成十六卷(一笔),刻于婺州。淳熙(1174—1189)间传入禁中。此后,续笔有隆兴二年(1164)自序,称作一笔18年,作续笔13年。则一笔作于靖康元年至绍兴十四年(1126—1144)。由此可知,“近岁”的兴化军学所刊《开元天宝遗事》,早于绍定刊本80年左右。应是4卷159条的。
2006年3月,曾贻芬的《开元天宝遗事·点校说明》指出:该书的舛谬不仅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所指出的4条。但这也不足以证明此书托名王仁裕,是伪书当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159条,分为4卷”。该书中记的内容,源于民言委巷相传而语多失实,王仁裕又未能详核史实,疏失舛误自然不免。何况《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唐末见闻录》,说明王仁裕对唐代史事的关注,可以作为《开元天宝遗事》出于王仁裕之手的一个佐证。其次,从《开元天宝遗事》所记玄宗、姚崇、宋璟、卢奂事与旧唐书的记载联系比较,可以认为《开元天宝遗事》所述史事有相当的可靠性,而这确实得到后世的认同。第三,《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下的记述,与《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依冰山》条的部分内容相近。《资治通鉴》采用《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充分肯定了《开元天宝遗事》的史料价值。
六、刘克庄的《梅妃》叹惜梅妃
咸淳五年(1269)正月,刘克庄赋诗《梅妃》,同月去世,享年83岁,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梅妃》是克庄咏江梅妃的最后之作①。
箫能妻弄玉,琴可挑文君。
吹彻宁哥笛,梅妃未必闻。
该诗短短四句,用了三个朝代的四个典故。魏晋间《列仙传》记载:箫史善吹箫,秦穆公因而将好吹箫的女儿弄玉嫁给箫史。数年后,箫史乘龙、弄玉御凤,双双升天而仙。《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描述了相如对文君的巧恋:“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卓文君因此动心,夜奔相如,同归成都。景云元年(710),临淄郡王李隆基平韦氏乱有功,太子宁王(680—741)因此让位于平王隆基。先天元年(712),隆基即位为玄宗,称兄宁王为宁哥。宁王以识曲辨声而闻名,唐代温庭筠《弹筝人》诗有句:“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嘉定十七年(1224),克庄《明皇按乐图》诗,也有句:“戏呼宁哥吹玉笛,催唤花奴打羯鼓。”花奴即汝南王李琎。玄宗要宁王、汝南王吹笛打鼓,但“梅妃未必闻”。
唐世宫禁与外廷不相隔绝、唐诗对此也不避讳。南宋《容斋随笔》“翰苑亲近”、“唐诗无避讳”两条已载,并引白乐天、元稹、杜子美等人的诗为证。宋代《杨太真外传》载:玄宗与贺怀智、马仙期、张野狐、李龟年、宁王、杨贵妃等演奏乐器,秦国夫人在旁观赏。宋代《莆阳比事·梅妃入侍》也载:玄宗顾诸王戏曰:梅妃“吹玉笛、作惊鸿舞,一一光辉”。可知,唐室诸王与玄宗妃子常在一起;其中的笛、舞爱好者如宁王、梅妃、杨贵妃等的互演互评,习以为常。83岁的刘克庄临去世时,为何叹惜开元二十九年(741)宁哥去世前“梅妃未必闻”到宁哥笛呢?由于史料流失甚多,又事隔700多年;如今无从考查。
莆田人卢兆荫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初有考证,在《江采苹有无其人》一文中指出①:《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均未记载梅妃。唐玄宗即位前,宠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先天元年(712)即位后,专宠武惠妃。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武惠妃死后,专宠杨贵妃;《莆阳比事·梅妃入侍》说梅妃遭妒遂迁东都上阳宫。史载: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玄宗从东都洛阳迁回西京长安后,再未去过东都;二十五年十二月杨玉环入侍后,也未去过东都;此后,不存在唐玄宗再去东都会梅妃的史实①。总之,正史记载中,均未见与唐玄宗生活在一起的江梅妃。如今,我们必须发掘正史以外的文字记载。
第二节 元明与清代前中期的作品
一、元时梅妃与杨贵妃多混为一人
《元诗选》一套9大册,全无正面咏及江梅妃的诗。只有以下数首,隐约点到江梅妃的史事,或是将江梅妃与杨贵妃混为一谈。
明本(1262—1323),钱塘人,朝廷赐为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其《梅花百咏和冯学士海栗作·录十二》之三有句:“三郎正爱《霓裳》舞,珍重椒房自惜春”。椒房,代称后妃;指自己惜春的梅妃。之十有句:“云开巫女多娇面,浴出杨妃一丽人②”。早在北宋时,大诗人王安石的《次韵徐仲元咏梅二首》有句:“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肌冰绰约如姑射,肤雪参差是太真”。《西江月·红梅》词有句:“真妃初出华清池。酒入琼姬半醉。”三次喻梅为杨贵妃。苏轼《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花落复次前韵》也有句:“玉妃谪坠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嫡坠”二字出《杨太真外传》。玉妃,即贵妃也。韩子苍云③。可知北宋时,王安石、苏轼等大诗人皆喻梅为杨贵妃。南宋时,莆田人刘克庄的《汉宫春·秘书弟家赏红梅》也有句:“还似得、华清汤暖,薄绡半卸冰肌”。以杨贵妃浴罢喻梅花的娇艳光鲜。
王冕(约1310—1359),元时诸暨(今属浙江)布衣,工于画梅,其《红梅四首》之三有句:“昭阳殿里醉春风”,“玉箫吹过小楼东①”。汉成帝时,赵飞燕居后宫昭阳殿。此后,多以昭阳指皇后之宫。这里借喻杨贵妃享皇后之礼而“醉春风”;隐指梅妃的被贬东宫而写《东楼赋》。
《元诗选》以外,倒是发见数首咏及梅妃的诗。
段克己(1196—1254),字复之,号遁庵,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幼时与弟成己并以才名,礼部尚书赵秉文誉为“二妙”。金末,克己以进士贡,金亡,与其弟隐居于龙门山中,兄弟俩有《二妙集》,是“河汾诸老”的领军人物,今存的作品多写于元初。《雪梅》诗未载于《元诗选》二集上册,而载于《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该诗批评唐玄宗不珍惜梅妃:“风流谁似李三郎,不记仙姿委路旁。天上人间无觅处,风流罗幂只闻香。”胡祗遹(1227—1295),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官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赠礼部尚书,谥文靖。《元史》有传,著《紫山大全集》。《永乐大典(残卷)》2813卷《紫山集》中录诗《题杜君复家藏王黄华〈雪梅图〉》,有句:“罗浮窗户愧庸俗,江妃篱落羞寒乞。赵昌徐熙尘土人,办与凡花逞颜色。仙人飞升今几秋,高气清香尚蒸湿。人间宝墨有如此,锦囊玉轴如珍惜”。这是今见最早的咏及江梅妃的雪梅图。
胡天游,名乘龙,别号松竹主人,自号傲轩,平江人,元隐居不出,其《傲轩吟稿》中录有《黄梅谷》诗,有句:“高人卒岁守穷谷,自笑谷中无一物。何年招得玉妃魂,夜半挥锄种明月”。“北风吹面君始归,正恐梅妃有嗔语”。该诗中玉妃即梅妃,高人在黄梅谷中浮想联翩,赋成长诗。
高棅(1350—1423),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福建长乐人,永乐间自布衣征为翰林侍诏,升典籍,见《明史·文苑传·林鸿传附》,是闽中十子之一。高棅于明洪武十七(1384)至二十六年编成《唐诗品汇》,三十一年又增补,共100卷。《唐诗品汇》标举盛唐,推崇李、杜,在反对宋末“猥杂细碎”和元人“妖治俶诡”的诗风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拉开了文论中唐、宋之争的帷幕,开了明人摹拟复古倾向的先河,引导了整个文学潮流,对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的研究具有特殊贡献。卷五十五载《杨妃·谢赐珍珠(玄宗有题梅妃图,真妃故有此谢)》:“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与寂寥”。该书所录的《谢赐珍珠》诗,是元时流传的,也把梅妃与杨贵妃混为一人。直到清时,还有人这样认为。如高凤翰(1683—1748),字西园,号南村,胶州(今山东胶县)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赋诗《题梅花册》①,有句:“月底衣裳舞太真”。杨贵妃,号太真。
二、明代的诗词和画作
岳正(1420—1474),字季方,号蒙泉,顺天(今北京)人,明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成化元(1465)至三年任兴化知府,五年致仕。《无题四首追和元马伯庸韵》之三有句:“宫婢貌难当万乘,玉环心不在三郎②”。叹曰:宫婢江采苹的美貌留不住唐玄宗,万岁爷倾心杨贵妃但贵妃心不在玄宗。
俞泰,字国昌,号正斋,无锡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户科给事中,擅诗文工书画。赋诗《梅妃吹笛图》:“音律从来寿邸长,宫中新调称新妆。谁知吹出无双曲,究为嵬坡诉断肠①”。该诗认为杨玉环赐死后,梅妃仍在。
仇英(1498—1520),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后居苏州。初为漆工,曾向周臣学画,后在鉴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观摩大量古代名作,技艺大进,自成一家,擅长山水、人物。“世称之为有明人物第一大家②”。仇英的人物画以工笔重彩为主,尤善仕女画,体态俊美、笔法细微、敷色妍柔、雅俗共赏,有“仇派”仕女之誉;亦能作精简的水墨人物画。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梅妃写真图》(藏徐悲鸿纪念馆),布局、画法几乎完全一样。前者笔墨灵秀,是真迹。后者较为工板,应是摹本③。
《梅妃写真图》有二十二个人物,梅妃端坐厅堂的中央、屏风之前。梅妃的左侧有6个宫女在交头接耳,且带惊诧之情。图的左侧,两个宫女从里屋探头而出,和屏风右侧探头的宫娥一样,是听到梅妃画像场面的声音,带着好奇欲出的表情。图右侧也有4个宫女,其中3个正聚精会神地看画家在为梅妃画像,另一个宫女头转向后看,暗示右边也有宫女欲出。厅堂四周是雕梁画栋、浓彩的围栏柱廊,显出豪华气派。围栏之外、玉阶之下有2个太监作议论之态。为梅妃作像的画师面向梅妃,端坐姿态的背影前、图幅上,有艳丽的梅妃像,画中像与图中人物酷真毕俏,工笔重彩,人物栩栩如生。1950年初,北京举办画展,徐悲鸿前往参观时看到这幅佳作。一位外国驻华大使正在与主人讨价还价,要买此图。徐悲鸿不愿这幅国宝流落国外,就毅然上前说:“我买了,不还价。”本来这位驻华大使与徐悲鸿有私交,而且已商议过邀请他到大使的国家去办画展。大使怪悲鸿夺其所爱,一气之下,就取消邀请徐悲鸿去办画展的事。但徐悲鸿一点也不后悔,他把国家的历代名画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但徐悲鸿儿子、中央美院美术史学研究生导师徐庆平副教授却说:《梅妃写真图》是元代王振鹏的作品。元刻本《图绘宝鉴》卷五载:“王振鹏,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运千户,界画极工致。仁宗眷爱之,赐号孤云处士”。
成书于明代的《新镌绣像列仙传》有张果图,四川新都人(时居成都府)、还初道人洪自诚辑,木刻本卷首有吉石金尔珍的题记,谈及:虽然这些插图的画工及镌刻匠的姓名不详,但可与明代名画家仇英所绘的《列女传》相媲美。今所见的木刻本,是光绪十三年(1887)扫叶山房校刊;1921年上海大成书局以木刻本为底本石印。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插图采用石刻本。《隋唐演义》载:安史之乱时,张果救助梅妃。
明代,裘昌今《太真全史》卷首有幅木刻插图,题为《惊鸿舞》,描绘梅妃身穿长袖舞衣,长裙曳地,肩披长巾,正在做纵身飞舞的动作,犹如惊飞的鸿雁。
唐寅(1470—1523),字子畏,号伯虎,别号桃花庵主,又号六如居士,吴县(今苏州)人。16岁时,秀才考试得第一名;他随父到仙游县九鲤湖祈梦求取功名。25岁时,父、母、妻、妹在一年内相继去世。他悲痛读书,弘治十一年(1498)应天府试得第一名,名震江南,诗、书、画三绝,自称“江南第一才子”。有《六如居士集》。《唐伯虎全集》卷三,载诗《梅妃嗅香》:
梅花香满石榴裙,底用频频艾纳熏。
仙馆已于尘世隔,此心犹不负东昏。
画家文征明的二子文嘉,在《写生逸致图》上题诗《梅花》,有句:“瑶篇曾呈梅妃传,素箑新窥点额图①”。
唐、文的这两首吟咏,此后却被收入江砢玉的《珊瑚网》,分别题为《梅妃》(载卷十五)、《梅花》(载卷四十六)。江砢玉,字玉水,徽州(属今安徽)人,寄籍嘉兴,崇祯时官山东盐运使判官,所撰的《珊瑚网》48卷,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
明万历以前,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女诗人王凤娴与女引元两人吟唱了《梅妃怨》三首②。因同是女性而感叹:“多才纵有东楼赋,不入离宫弦管声。”“宁将哀怨赋东楼”,“始知笑语在西宫”。梅妃咏有《东楼赋》,西宫指杨贵妃所居处。
费元禄,字无学,又字学卿,江西铅山人,其《甲秀园集》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75)。录《梅妃村(兴化府)》、《梅妃谢珠》两诗,详见五章三节二目。
徐渭(1521—1593),字文长,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秀才,16世纪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其《书唐伯虎所画美人·眼儿媚》词也对比了梅妃与贵妃,有句:“可是华清春昼永,睡起海棠么。只将穠质,欺梅压柳,雨罢云拖③”。北宋时,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已载:唐玄宗说杨妃醉时,似“海棠睡未足耳”。《梅妃传》则载:江梅妃是柳叶眉。徐渭的《双调清江引·题花卉卷》,由题花而起兴:“瘦梅妃、肥太真,恁自忖④”。
明代坊贾托名钟惺(1574—1625)的《名媛诗归》,卷十载有《一斛珠》,评“桂叶双眉久不描”句:“桂叶”二字便新,若入“柳叶”等语,却陋极矣。又评“残妆和泪湿红绡”句:他本作“污”,不如“湿”字宛闲。崇祯三年(1630),海盐人胡震亨(1569—1642?)编成《唐音统签》1033卷,卷一三录有江梅妃的《一斛珠》。清时,陆昶的《历朝名媛诗词》卷四也评《一斛曲》:诗少婉曲,一气而出,可以想其怨愤不觉触发之意。
朝鲜半岛的柳潚(1564—1636),字渊叔,号醉吃,1597年进士,有诗《喜春雪》;南龙翼,字云卿,号壶谷,明末为副使出使中国,有诗《问梅花》、《和赤谷〈惜花〉十绝之八〈玉梅花〉》;均咏及梅妃。
董以宁(1630—1669),字文友,常州人。明末诸生,有才子之称。早年的《蓉渡词》录有《虞美人·限韵咏池上杨妃海棠》,下阕为:“梅妃应笑胭脂重,欲唤从前梦,临池照处映鱼茵,疑向三郎传语倩双鳞”。
三、清代前中期的诗词和画作
清顺治、康熙时,兴化府诗人林尧英、林宾王、陈延彬、游谦征、林琅玉均咏及莆田的江妃村,载《莆风清籁集》卷四十、三十八、四十一与《兴安风雅》卷三,都是指东华村,详见史志篇。
周亮工(1612—1672),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有诗《竹枝词为胡彦远纳姬赋》①。胡彦远,名介,钱塘(杭州)人,有《旅堂诗集》,布衣,妻女皆能诗;晚逃于禅,年未五十而卒②。顺治中,彦远游京师③,旧姬是唐山人。
亮工为其新姬而咏诗:“蛮妆新样木兰陂,学得金陵百事宜(姬初至榕城,学为秣陵妆)。莫羡江苹黄石好(江苹,莆之黄石人),我侬乡里有西施。”诗由新姬(涵江人)的蛮妆(木兰陂妆)改为秣陵妆(金陵妆)而联想,把(福建莆田涵江)美女江[采]苹(江梅妃)与春秋时越国苧罗山(今浙江诸暨县南)美女西施相比。
陈维崧(1626—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以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清初阳羡词派领袖。他以梅妃喻梅花,《画堂春·小春》有句:“记得年时岭外,梅妃犹未胜妆。如今花满纸糊房,红紫成行①”。《花发沁园春(月夜布席绿萼梅花下、同友人小饮)》有句:“念月姊、彻夜孤寒,梅妃自小幽独”。“夜深沉,我醉休扶,和月和花同宿”。《贺新郎·月夜看梅花》评说杨贵妃与梅妃:“忽忆开元当日事,中有梅妃蛾绿。何必羡玉奴新浴,可惜楼东三十树,雨霖铃,都做连昌竹。花应叹,睡难足②”。
吕履恒,字元素,河南新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有《梦月岩集》。其《江妃怨》诗有句:“羯鼓听残宫漏沉,楼东赋就更微吟③。”
山东德平诗人、康熙间举人李鹏九的《江水儿》,也有句:“月落光犹在,情留梦不舒,伤心雁唳楼东赋”。载《骨董三记》卷一。
朝鲜半岛的金万重(1637—1692),字重叔,号西浦,1665年文科状元,1674年《读班婕妤、梅妃故事,感而赋之》。
王士禛(1634—1711),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少时作《咏梅妃·减字木兰花》①,点及一斛珠与东楼赋。此后,《骊山怀古八首》之三增加对比:“舞罢惊鸿岁月徂”,“君王自爱霓裳序②”。《季园赏白牡丹》,则加调侃:“太真霞脸带醉色,睹次亦学江妃酸。”
张宗橚(约1700年前后在世),字永川,号思崖,浙江海盐人,监生。其《琐窗寒·珍珠梅篱间盛开》把南海鲛人泪、江汉江妃的典故都融入江梅妃的故事:“似鲛人易泣,泪珠都陨。解佩携来,梦绕湘皋无准。想惊鸿、舞罢妆残,楼东一斛愁瘦损③”。《述异记》载:南海中有鲛人室,水居如鱼,不废机织,其眼泣则出珠。
尤侗(1618—1704),字同人,号悔庵,又号艮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官至侍讲。其词《疏影·黄梅花》将江妃喻为江梅妃④,有句:“前身本是江妃种,催妆早、先来一霎”。还有词《摸鱼儿·春怨》,有句:“梅妃休怨楼东赋,吊取马嵬黄土”。
江南武进(今属江苏人)董大伦(1666—1705),字敷五、畴叙,号叔鱼,著《梅坪诗钞》三卷,《竹夫人词》八首之五有句:“清绝梅妃较若何,冷然姑射不争多⑤”。
冯光裕,字叔益,号损庵,代州人,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官至湖南巡抚,有《柴门老树村稿》。其《古意》二首之二有句:“谁知月下江妃树,别殿无人慰寂寥”,载《晚晴簃诗汇》卷五十八。
黄唐棠,名之隽,官中允,曾视学闽中,以事去官①。黄集唐诗百余联,咏梅妃之句有“却嫌脂粉污颜色,何必珍珠慰寂寞”。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闽县人孟超然有《沈学子文自淮南寄示同黄唐棠先生山游诗因题其后》,载《国朝全闽诗录》初集卷十七。
朱仕玠,字壁丰,号筠园,贡生,福建建宁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台湾凤山县教谕。《过江妃故里》四首对比杨妃②:“翻笑上皇诚错计,马嵬亡国竟何人?”认为:梅妃“古来嫔御谁相匹”,“青塚魂归同寄恨”。
乾隆三十七年(1772),莆田人郑王臣编有《莆风清籁集》(附《兰陔诗话》),卷五十一录有郑王臣《过江妃村》五首,郑远芳《莆阳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上册还录有郑王臣《江妃村》一首。这时的江妃村,是江东村,详见史志篇。
舒位,字立人,又字铁云,大兴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其《瓶水斋集·冷枚(华清新浴图〉》有句:“江妃辞去念奴陪,迟日熏风汤殿开”。叙及杨玉环、江梅妃、念奴、安禄山等人与唐玄宗之间的故事③。
梅妃的故事还引起乾隆皇帝的诗兴。《御制诗集三集》卷五十七载有《山茶》诗,有句:“设拟唐宫斗绝色,梅妃侧畔有杨妃”。《御制诗集四集》卷三十九载有《红梅》诗:
气味本来自相亲,妆成不语亦传神。
试看泪污红绡处,合唤唐宫江采蘋。
兴化府教授林朝阳赋诗《江梅妃思莆》,有句“春光独占锦江隈”,“美人终有荒村在”。乾隆《莆田县志》未载林朝阳,应是乾隆后任职的。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官至江宁知县。十七年,袁赋诗《再题马嵬驿》①,有句:“听说西宫恩幸少,梅花犹得落昭阳”。
事指明皇密召被贬的梅妃到翠华西阁叙旧爱,次晨被杨妃发觉而仍归东宫。安史之乱时死,葬于温泉池侧梅树下。袁枚39岁就辞官终养,诗倡性灵说,是乾隆三大家之首。莆田人、兰州知府郑王臣以弟丧去官,载万卷书回莆,在袁枚处舣舟三天索序,袁枚遂写《兰陔堂诗序》。四十四年,袁枚又赋《元日牡丹诗》贬杨妃褒梅妃②,有句:“如何绝代玉环姿,蜂未闻香蝶未知。想与梅妃争早起,严妆同对雪飞时。”
赵翼(1727—1814),字雪菘,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探花,官至贵州分巡道贵西兵备道,是乾隆三大诗家之一、著名史学家。五十三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备办军需,赵翼与浙江孝廉李莪州同在李侍尧幕府,赵翼赋诗《莪州以陕中游草见示,和其五首》,之五《马嵬坡》抨击唐明皇“宠极强藩已不臣”,“召乱何关一美人”。由杨贵妃想到:“谁知几点胭脂泪,别有生离江采苹③”。
嘉庆六年(1801)举人、江西籍著名诗人乐钧的词《探春·宋云墅仪曹座上咏白丁香花》,下阕有句:“是小玉娇魂,烟外吹坠。屈与添香,烦教贴翠,除是梅妃才可④”。
王筠(1749—1819),字松坪,号绿窗女史,长安县(今属陕西省西安市)人,清代戏曲女作家,诗歌200多首附于其父王元常的《西园瓣香集》中,其诗《江梅妃》有句:“有金难买楼东赋,寂寞梅花老上阳”。
刘嗣绾(1762—1820),字醇甫,号英初,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其《鬲溪梅令·烟陇探梅》词有句;“好在东风庭院、见梅妃。绿苔生卧衣①”。
嘉庆(1796—1820)时,莆田县诗人郭尚先、陈池养与福清诗人、尚先的叔叔郭龙光也诗咏江梅妃,分载于《郭大理遗稿》卷二、《慎余书屋诗集》卷一、《韶溪诗集》卷一,详见史志篇。
王翙,字钵池,寿春(今安徽寿县)人,活动于清乾、嘉(1736—1820)时期。王氏善山水、花鸟、虫兽,“而于人物为尤著”,“曾供奉内廷”。绘有《百美新咏图传》,刊于嘉庆时。河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影印为《百美图谱》,可惜删去了颜鉴塘的题诗。书首有“雪月华岁最信君”“犹疑照颜印”《题王钵池画图并序》;嘉庆九年(1804)十一月,小西涯居士法式善《序》。梅妃图传载于《百美图谱》图传二十一。
萧重,字远村,静海(今属天津)人,嘉庆十七(1812)起任职莆田,道光六年(1826)由莆田县尹调摄金门篆,道光十年后再游莆田。赋诗中10多次咏及江梅妃②,使人们了解到梅花书屋、江妃墓、江妃墩、梅岭、梅花村等的情况。作者所吟丰富了梅妃的故事,详见史志篇。
日本诗人田能村竹田(1777—1831)的《梅花》诗联吟杨贵妃与梅妃的故事:“梅月影香云母屏,桂眉不画立闲庭。君王徒有真珠赐,唯道海棠眠未醒①”。
第三节 清后期以来的作品
一、清后期诗作
道光(1821—1850)时,山阴(今绍兴)人高颂禾任职闽地,有诗四首和刘左黄的《题梅妃小像绝句》,载于《暴麦亭集·闽游集》卷下,由画而咏梅妃,详见史志篇。
鸦片战争以后,九江府德化县万梦丹的《梅妃》诗有句:“纵使珍珠倾万斛,算来不敌泪珠多②”。她从女性诗人的角度,感叹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迫下女同胞的悲哀。同治时,湖南长沙女诗人杨蕙卿的《梅花四首》其一也是同样的情怀,有句:“一枝初绽名园里,凄绝梅妃带泪看③”。
莆田人郭篯龄(1825—1886),字子寿,号山民,道光二十一年(1841)县学秀才,后例贡入太学,选为州同知,候补浙江。太平天国起义后隐居莆田。有诗《江妃村》④,赞曰:“灵秀千秋毓此村”;以荔喻杨贵妃、以梅喻江梅妃:“荔子竟遮天暗昧,梅花能耐月黄昏”。
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莆田人宋际春,同治时任台湾教谕,对江梅妃推崇备至,诗咏《江妃村》6首⑤。在《绿天偶笔》中评曰:江梅妃的一首《一斛珠》岂抵一本诗集;在《竹素园诗·序》中,认为《一斛珠》是千年莆诗之倡⑥;在《闽中论诗绝句》中两赞梅妃①;在《莆中名迹》中再咏江妃村②。
咸丰时,莆田儒妇陈淑英著《竹素园集句》、《竹素园诗钞》,咏及梅妃的有7首。林有珠、唐韵、刘璋寿、杨端、江大球、江宪章、翁大奎各有题词,誉陈淑英为江梅妃之后莆田又一女诗人,详见史志篇。
清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广西象州县壮族诗人、曾任户部主事的韦陟云《羁栖四十韵》,有句:“地与生番界,溪曾大甲沿。鸡笼云漠漠,沪尾月娟娟。人忆梅妃丽,男宜草席妍。轮舟通曲折,铁路绕回旋”。载《历代壮族文人诗选》288页。
清末,新安(属今河南)人程羽文(荩臣)撰写有《鸳鸯牒》:“江采苹,俊朗高洁,抱恨楼东,宜遥配孟浩然、林君复,肆癖湖山,共对梅花索句③”。赞誉江梅妃也是高士。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湘北襄樊)人,盛唐诗人,怀有用世之心,因不涉事务,拙于奉迎,功名无着,遂以漫游为事;后为荆州从事,开元末卒于疽。孟浩然与张九龄、王维为忘形交。王维私邀孟浩然入内署,适明皇至,浩然匿床下。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诏浩然出,孟诵诗至“不才明主弃”。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孟有《早梅》诗:“园中有早梅,年例犯寒开。少妇争攀折,将归插镜台。犹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④”。吴乔《围炉诗话》卷二说:“孟浩然诗宛如高士”。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人。无意仕途、虚名,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娶,所居植梅蓄鹤,人因称“梅妻鹤子”,溢号和靖先生。其诗大多表现了隐者的高雅情怀,其对雅格品位的追求,影响了整个宋代文化的品位。林逋开了宋人顶礼膜拜梅花的先河。梅花已经化入其心魄,梅花即我、我即梅花矣①。
《香艳丛书》三集卷三还载有吴江(属今江苏)人杨淮(蓣远)的《古艳乐府·楼东怨》,其咏有句:“海棠开、江梅落”。“空留月影伴楼东”。海棠指杨贵妃,江梅即江梅妃。
文廷式(1857—1904),字道希,号云阁,晚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江西萍乡人,生长岭南。光绪十六(1890)进士,官至侍读学士,二十一年参与发起强学会提倡变法,次年被革职。戊戌政变后避居上海。精子史之学,尤工诗词。有《纯常子枝语》、《补晋书艺文志》、《云起轩词钞》、《文道希先生遗诗》、《闻尘偶记》、《罗霄山人醉语》等。其诗《落花》十二首之九有句:“有情湖畔三生石。无用楼东一斛珠”。
二、丘逢甲的诗作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晚号仓海君,台湾淡水(今苗栗县铜锣镇)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赋诗《题杨太真外传》②,十首之一有句:“双陆家风传李老,斛珠恩宠妒梅精。谁知得宝宫中乐,惊破开元曲太平”。
甲午战后(1895),丘逢甲倡建“台湾民主国”,声明永奉中国。次年内渡广东办学,任临时参议院参议员。三十四年赋诗《李湘文(启隆)邀同雪澄实甫陶阳二子上涌村啖荔枝作》③,有句:“少年最爱十八娘,至今追忆神犹驰。自来岭南日啖三百颗,临风辄念天人姿。门书荔子甲天下,已生荔子生梅妃(兴化府署大书:‘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为楹联)。梅妃生闽杨妃粤,杨妃宠盛梅妃衰。人间选色论品目,两皆尤物天所遗。亦如荔枝各具色香味,相看不厌不见常相思。奈何玉环不自爱乡味,坐令蜀产称珍奇。蜀荔之佳万万逊闽粤,维髯蜀客亦谓言非欺。惜髯但啖粤荔未到闽海湄”。以下予以赏析。
北宋时仙游枫亭人蔡襄的《荔枝谱》载:“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时人以少女比之。俚传闽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其塚在(福州)城东报国院,塚旁有此树云”。北宋李纲《初食荔枝四绝句(所居报国,有十八娘荔枝)》之四咏道:“平昔传闻十八娘,丰肌秀骨有余香。今朝亲到芳丛下,应许幽人餍饫尝”。
南宋淳熙九年(1182)成书的《三山志》土俗三记载:“十八娘红,色深红而细长,以少女比之。俚传闽王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蔡公所谱)”。“状元红,于荔枝为第一,出东报国院(曾公巩所记)”。同书寺观一载:易俗里的东报国院。
笔者奇怪的是:《三山志》未记十八娘红荔枝在东报国院,只记状元红荔枝在东报国院;可知北宋末李纲到东报国院尝食十八娘红荔枝后,到南宋《三山志》成书时该树已无。福州人遂将院中另有的状元红讹为十八娘红。而状元红确出于宋代的枫亭。熙宁九年(1076),莆田人徐铎中文状元,将延寿红荔种赠亲家枫亭人、同年武状元薛奕。宋神宗赋诗:“一方文武魁天下”,延寿红遂称状元红。南宋宝祐五年(1257)成书的《仙溪志》,物产荔枝目中未记载十八娘红。
蔡襄《荔枝谱》流传后,宋代诗人苏轼《减字木兰花》、苏辙《干荔枝》、洪炎《初食生荔枝二首》之二、王十朋等人,都吟诗咏到了著名的十八娘红荔枝。
明时,王世贞赠诗嘉靖举人、全椒知县弃归的莆田人佘翔,
有句:“十八娘红莆荔枝①”。明末,福州人曹学佺《荔枝叹》诗有句:“十八娘家粉黛残,玉肌罗帐泪阑干。枫亭三日无消息,马上空歌行路难”。该诗明确指出:十八娘红荔枝在枫亭。
清康熙时,郑德来《连江里志》记载:忠顺王女陈机,号二十小娘,捐首饰买地开圳,深8尺阔1.2丈,抵驿坂,远15里余,灌之。父洪进所舍法石禅寺之田,号金钗庄,立石记之。可知陈洪进之女名二十小娘,不叫十八娘。
但乾隆《仙游县志》列女传则改为:“陈玑,别字十八娘,洪进女,尝捐钗钏买地开沟,深八尺阔丈二尺,自枫亭抵惠安县之驿坂十五里以灌田,号为金钗沟,其庄为金钗庄。又尝手植荔支,至今称为十八娘,香味尤绝。”
乾隆《福州府志》寺观载:东报国院,在易俗里,久废。由于枫亭位于驿道,自宋至明,十八娘红荔枝在枫亭的传说逐渐占了上风,而福州的东报国院已废。此后,乾隆《仙游县志》遂附会为北宋时陈洪进的第十八女所植。
到道光时,林朗如的《枫亭志》仍表示怀疑,他引述蔡襄《荔枝谱》始载的闽王女十八娘红与康熙《连江里志》以后枫亭所传陈洪进女十八娘红“并同,然则十八娘荔枝,犹有二种也与?”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的江苏人石韫玉,官至山东按察使,被劾归乡,掌教20多年,有《梅妃作赋》杂剧,已说梅妃是广南人。民国时许啸天的《唐宫二十朝演义》,也衍说是广南人。
三、民国时期内地诗作
杭州诗人陆微照(1899—1980),民国时吟诗《杨玉环》,咏道:“一样烟尘埋玉骨,九原应不妒梅妃①”。
民国建立时的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学校校长、贵阳人姚华(1876—1930),赋词《一斛珠·梅妃》,有句:“长门尽日,残妆坐,懒梳慵栉,双眉冷淡春风笔②”。
1915年,莆田人李光荣(1850—1920年后)辑成《兴安风雅》诗集,卷三收录咏梅妃村的诗作甚多。有刘尚文3首、李光荣4首、林津4首,黄尚忠、林习伦、黄家鼎、程登瀛、唐焕章、周天章、周维新、陈维新各1首。咏及江梅妃的故宅、祖塚等;李光荣还有《村妇》竹枝词,写出江家妆的具体装扮,均详见史志篇。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属今福州)人,近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有《陈石遗集》(上、中、下),《陈衍诗论合集》(上、下),共320多万字。其《岂有》诗咏道:
岂有宁哥玉笛声,更无肥婢与梅精。
方床大被还长枕,不忍楼将花尊名。
该诗作于戊午(1918),载《陈石遗集》上册252页。陈衍史学亦著,他认为没有杨玉环与梅妃争宠事。可知梅妃故事,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论。
1920年五月四日,莆田人林翰、关佛心发起成立壶社,创会期历二年有余,社友10多人,一个月诗咏一题,遂成《壶社诗草》。贞部28卷的《梅妃村》录有14人诗作:林翰、关佛心、萧敦甫、陈耀枢(2首)、陈敬汤、温筱珊、方西湖、林及锋、郑渠、陈元璋、张景棠、游介园(4首)、黄祖汉、宋仁陶。他们到村访俗,抚今怀古,浮想联翩,佳咏争辉,详见史志篇。林翰1913年始任福建省议长,其《梅妃村》诗道:
一乡轶事唐天宝,千载齐名越苎萝。
故老相传鹅脰冢(东华村有小阜,在水中,
形如鹅脰,相传为妃归骨处),当年竟殉马嵬坡。
野梅树树精魂在,江水澌澌怨恨多。
隔岸犹听村女唱,斛珠一阙当山歌。
轶事即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事迹。林将江梅妃与出生于苎萝山的越国美女西施相提并论,又将“相传”骨葬鹅脰冢的江梅妃与赐死马嵬坡的杨贵妃分别褒贬。林翰还有《秋日杂兴并留别里中诸友》之四,载《山与楼诗集》卷二;宋仁陶还有《题宋宫人斜》、载《宋仁陶遗集》,《福州西湖强小姐墓(分来字)》六首之二、载《宋幼石诗草》,均咏及江梅妃,详见史志篇。
四、日据时期台湾诗作
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统治不断深化,诗人们的梅妃诗作,抒发了爱国反抗的心声。
洪弃生(1867—1929),原名攀桂,又名一枝,字月樵,后改名儒,字弃生。日人居台后,他拒不出任伪职,不与日吏交往,是日据初期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尤以歌行体闻名台湾诗坛。他到过莆仙,《寄鹤斋诗选》中有《过枫亭偶眺》、《过濑溪偶咏》、《兴化渡口三首》等。其咏梅妃诗4首中均寓入中国惨遭日寇侵略的悲痛心情。《闽中杂咏》有句:“半楼明月梅妃里”,“不堪萧瑟送残阳①”。《闻病偶咏》有句“愧落歌中一斛珠”,“不知瘴入梅花树②”。《虞美人·咏花二十韵》有句:“梅妃貌比菊妃扬”,“河山回首恨苍茫①”。《记梦》有句“敢将杜牧耽轻薄,欲与梅妃慰寂寞②”。
台湾诗人王效良,其《美人十咏·美人舞》有句:“唱彻江妃一斛珠,族扶倩影十毡毹③”。
陈髯僧,字佑余,福建晋江人,清末民初寓台10多年,曾鬻字集资而刻先人遗墨。《题忆梅诗录》有句:“驿使何人传庾岭,江妃尽日怨长门④”。
林仲衡(1877—1940),号壶隐,台中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栎社,为雾峰三诗人之一,其《仲衡诗集》1992年3月收入《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1辑,龙文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吊梅吟有序》有句:“红颜自古天相妒,不见梅妃憔悴身”。
谢汝铨(1871—1953),字雪渔,号奎府楼主,日据后从台南迁居台北。前清秀才,在《台湾新新日报》工作,兼《风月报》主笔。宣统元年(1909)参与倡设台北瀛社,有《奎府楼诗草》、《蓬莱角楼诗存》。其《疏梅》有句:“几枝无赖怯风霜,对镜江妃未竟妆⑤”。
陈静园,台南诗人。其《迎春》有句:“想到唐宫催羯鼓,江妃依旧怨东风⑥”。
东明,笔名,新竹人,其《美人蕉》有句:“潇潇雨滴芳心碎,遮莫梅妃一段愁⑦”。
义山,笔名,嘉义丽泽吟社社员,其《白扇》有句:“几度深闺评玉貌,满车皎洁比梅妃①”。
郑雨轩,新竹人,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书画家。其《春妆》有句:“轻涂浓抹坐清晨,对镜梅妃点额真②”。
王则修,台南县新化镇人,清光绪廪生,1928年8月在新化创办虎溪吟社,任社长,日据时是台南县的诗文名家,其《香冢》有句:“敢是梅妃死后魂,香留窀穸月黄昏。葬身艳说花无语,埋骨深怜玉比温③”。他认为鹅脰是梅妃的骨葬坟。
林又春,屏东人,1940年在东港区林边乡创办兴亚吟社,任社长。其《画梅》有句:“可怜静草楼中夜,添写江妃泪暗垂④”。
蔡旨禅(1900—1958),女,名罔甘,道号明慧,澎湖才女。1926年参与创建高雄莲社,弘扬佛法。晚居新竹,1957年返澎主持马公澄源堂。弟子辑其作为《旨禅诗画集》。其中1949年前所作的:《红梅》有句:“梅妃宠罢雪交加,偶着红绡韵孔嘉”;《红梅鹊》有句:“疑是梅妃初睡起,如何晕颊印霞新”。
五、郭沫若、张大千等分咏梅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两位大文人也咏及梅妃。
1962年11月,郭沫若及夫人于立群到莆,其《途次莆田》诗有句:“梅妃生里传犹在⑤”。1983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纪游诗选注》一书,由林东海、史为乐联合选注,其中录有《途次莆田》诗,郭沫若的原注是:“唐玄宗初宠梅妃,莆田江东村人,村中有浦口宫纪念之,今尚存①”。由此可见,郭沫若确认这个史实。郭沫若早年对梅花已偏爱,1920年3月30日咏《梅花树下的醉歌(游日本太宰府)》。太宰府,在日本九州福冈市,该诗收入《女神》。
80年代,浦口宫修复,江梅妃由陪祀变为主祀。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学名正权,乳名小八。
1917—1919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学名援、爱、季爰、爰,法号大千。1927年,他开始“行万里路”的艺术历程。1949年9月,张大千离川去海外。1953年后移居巴西。1956年7月28日,大千夫妇与毕加索相见,互相赠画。这是中西画坛两巨子的高峰会晤。1958年,大千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并授予金质奖章。
1972年,张大千夫妇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环筚庵,其名取自《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典故,含有创业维艰之意。他同侯北人经常切磋画艺,“环筚庵种梅百本,颇有非议者,百本栽梅亦知嗟,看花坠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颇无耻,不认梅花是国花”。于是,大千于“上元后二日,写艺新衡吾兄环筚厂添种垂枝梅”,诗曰:
万里从君乞一株,柔枝瘦影正须扶。
濛濛月色开生面,得似江妃对镜无。
大千还有首《题红梅图》:
十年流荡海西涯,结个茅堂不似家。
不是不归归自好,只愁移不得梅花。
大千思乡情切,1976年移居台北。他的画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展,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是中国的“文化大使①”。
张大千对莆田亦有印象。193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涵江发生大火灾,延烧200多户、损失数十万金。原莆田县长黄缃组织“涵江火灾善后委员会”,请省里长官林森、萨镇冰、杨树庄发动全国名流捐赠书画作品,一年来征集到1000多人5000件,其中有张大千的作品。作品的一部分展览义卖后,据以重建涵江。
至于其他诗人所咏,那就更多了。例如莆田裔马来西亚的华侨陈少白《访莆田江东梅妃故里》、莆田学院副教授刘福铸《和乡侨陈少白〈梅妃故里〉》、《莆田县志》副主编李光岱《浦口宫集句》三首之三、《湄洲日报》专刊部主任林金松《忆江南·梅妃》等。
美籍江西九江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蒋彝(1905—1977)撰《香港竹枝词》,五十首之四十六有句:“而今人造珠充斥,梅妃不必苦吟哦”。科技的发展,使当代人对梅妃故事有了新的感触②。
第一节宋代的作品
一、李纲首喻梅妃
北宋后期,李纲的《梅花赋》首次以梅花比喻梅妃。李纲(1083—1140),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徙居无锡。北宋政和二年(1112)进士,官至丞相。据《李纲年谱》,宣和三年(1121),李纲转宣教郎,泛大江归在海陵(今江苏泰州)的父亲膝下,因唐时宋广平的《梅花赋》已阙,而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且标格清高为余花未及,遂作《梅花赋》:梅花,“丰肌莹白,娇额涂黄,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在小说笔记篇,笔者已分析,由其“丰肌”、“娇额涂黄”、“临镜严妆”,可知与《梅妃传》的梅妃对不上。《梅妃传》里的梅妃:偏瘦,讥杨贵妃为肥婵;“铅华不御得天真”。《梅花赋》中的梅妃,是宋本《梅妃传》以前的梅妃形象,而为宋本《梅妃传》的创作提供了一些素材。
《全宋诗》27册载李纲咏梅诗32首及咏开元天宝史事诗10多首,仅宣和元年(1119)李纲1监沙县(属今福建)时作的《用韵赋梅花三首·再赋一首》与此后《梅妃传》中的梅妃事相近。即“粉质不浴骊汤温”,天生丽质,不需像杨贵妃的浴骊汤;“吹残楼角真可惜”,但却不是《楼东赋》中的楼东!
二、晁说之诗咏梅妃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进道、伯以。号景迂生、老法华、国安堂主。河南开封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元祐(1086—1093)时相继任兖州司法参军、蔡州教授。绍圣(1094—1097)时为宿州教授,元符(1098—1100)中知磁州武安县。他上书指斥王安石政事之非与绍述诸臣之谬,入党籍邪等,崇宁二年(1103)知定州无极县,后相继任嵩山中岳祠、陕州集津仓、华山西岳祠。大观(1107—1110)间监明州船场。政和四至六年(1114—1116)通判鄜州,宣和元年(1119)提点南京鸿庆宫。三年初春知成州。五年因岁旱尽蠲其税,而转运使大怒,乞致仕。靖康元年(1126)二月应诏封事,任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坚决反对太子读《孟子》,遂免职流放,九月出京逃亡后避兵高邮。高宗继位,授以徽猷阁待制兼侍读,后提举杭州洞宵宫。建炎二年(1128)寓居海陵,三年正月七日卒于建康,71岁。赠通奉大夫、后累赠至光禄大夫。
说之的《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之五咏道①:
莫道梅花取次开,馨香须待百层台。
不同碧玉小家女,宝策皇妃元姓梅。
该诗未点明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的梅妃。而此后《梅妃传》中的梅妃姓江,不姓梅。
《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简称《枕》诗)是组诗。《全宋诗》卷1211晁说之集中载有说之与圆机酬和的诗57首。
从这些诗中可知:
圆机,即郭执中。《万姓统谱》卷一百十九与《记纂渊海》卷二十五引《舆地纪胜》记载:郭执中,华亭人,累官枢密承旨,建中靖国初应诏言事切直,忤蔡京,籍为元祐党,入邪等,斥居同谷(今甘肃成县)20多年,因家焉。绍兴初,执中集乡豪御金,立斩来招降的金使,后以功累迁新安郡王。郭执中多才多艺:“却问人间梅几种,郭仙尔有古人辞①”;“君乎学问二刘比,南北该通酸自甘②”;他“淡墨书名二十年③”;“当年郭有道,今日更谈禅④”。
(一)时间。《枕》诗作于北宋后期。《枕》诗之二载“梨园弟子强因依,羯鼓声中学御诗。十月胡雏来唤仗,新梅谁复增新辞。”即宋金协议夹攻辽国之事。《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载:宣和二年(1120)八月,宋金签订联合夹攻辽国的《海上盟约》。
冬十月,金主草国书,遣哈噜与政等来报。聘书中大略云:“前日赵良嗣等回,许燕京东路州镇,已载国书,若不夹攻,应难如约。今若更欲西京,请便计度收取,若难果意,冀为报示。”
《枕》诗之五有句:“莫道梅花取次开,罄香须待百层台(四库本注:今洛中名园犹竞于梅台,贵自上接其香)。”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一书指出:宋代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记载富郑公梅台、湖园梅台、大隐庄早梅都是梅花专题景观。张氏(景昱、景昌兄弟)南园“凭高种岭梅”,“纷披百株密⑤”。品种也有多样;中有高台俯临,是赏梅的最佳处,极负盛名①。仁宗嘉祐(1056—1063)以来,尤是神宗熙宁(1068—1077)间,洛中名流园林雅集,诗酒游观,梅作剧增。这是说之回忆并联想洛阳的梅景。
《枕》诗之七喻梅是霜女、月娥下降人间。据查,元丰五年(1082)苏轼咏《红梅》三首。此后,诗人们普遍以月宫嫦娥、瑶池仙姝、姑射神女、深宫贵妃、林中美人、幽谷佳人等美人形象来喻梅。
《枕》诗之十四自注:“今日天庆节,两处朝拜。又孝惠忌行香疲,且手寒,草草增愧也。然不犯从前梅事如前村之类,亦可一笑也”。据查,宋真宗掩饰澶渊城下之盟的耻辱,景德五年(1008)伪造天书下降承天门,下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并于十一月决定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命各州兴建天庆观。百官赴宫观或僧寺进香,朝廷赐百官御宴。京城宫观斋醮七天,后相继减为三天、一天。宋仁宗初年,因天庆等5节“费用尤广”,遂将各宫观同时设醮改为轮流设醮②,后渐废罢。到南宋时,京城不再庆祝;仅外州官员赴天庆观朝拜和休假两天③。由上可知:说之一天内朝拜二处,是北宋后期。
《枕》诗后还有:《亡友陈无已有立春诗,云:朱门谁送青丝莱,下里难酬白雪歌,颇为都下诗人所称,今日立春诵之而作》。
陈无已即陈师道,逝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还有《七月一日作(昨日闻陈莹中卒)》。陈瓘(1057—1122),字莹中,号了翁、了斋,沙县人。元丰二年(1079)进士,徽宗时历右司谏,权给事中。《宋史》本传称其最被蔡京、蔡卞忌恨,故得祸最酷。崇宁中,以党籍除名,卒于楚州。靖康中,赠谏议大夫。绍兴中,赠溢忠肃,有《了斋集》。
(二)地点。《枕》诗的前面,有《依韵谢圆机送梅绝句二首》、《再和圆机梅绝句》、《申前意和圆机绝句梅花》,均是说之在西安与执中的酬和。《枕》诗之一有句“据渭浮泾雪浪开”。之三有句“泾南渭北花如锦,太白山头只有梅”。泾水、渭河、太白山(终南山)均在今陕西。之四有句“孤芳寒艳绝难依,鄴下关中不赋诗”。关中的范围相当于今之陕西。之六有句“梅寒恨不出豳诗”。《诗》国风有“豳风”,共7篇27章。唐开元十三年(725),改豳州为邠州,故治在今陕西彬县。
程杰教授查知,《枕》诗作于宣和四年(1122)春,晁说之知成州(今甘肃成县)时①。该地在甘肃东南部,与陕西相邻,距西安不远。
《全宋诗》中收有晁说之24首咏梅诗,其他23首再未提及梅妃。笔者查阅说之的《景迂生集》二十卷、《儒言》一卷、《晁氏客语》一卷,也未谈及梅妃。可知这是北宋中期以来喻梅为美人的文风中,继李纲喻梅花为梅妃后,再喻梅花为梅妃。皆为特例,均跟《梅妃传》中的梅妃形象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晁说之笔下的梅妃比李纲笔下的梅妃更具体,她不是碧玉小家女,而是皇妃;该诗似乎还对张泌笔下的梅妃予以塑造,即与梅花相关联而咏。
三、江妃转化为江梅妃
南宋时,高观国的《满江红》词有句:“十万江妃留醉梦,二三沙鸟惊吟魄”。项安世(1129—1208)的《腊尽仅得微雪》
诗有句:“可是江妃悭笑粲,都能无意管呻吟”。
卒于乾道、淳熙间(约1173—1174)的侯置是最早咏及梅妃的词人,其《水龙吟·老人寿》词有句:“正梅妃月姊,雪肌粉面,争妆点、潇湘好”。可知,梅妃的故事传衍在潇湘(今湖南)一带。
赵以夫(1189—1256),字用父,号虚斋,福建长乐人。嘉定十定(1217)进士,资政殿学士,吏部尚书兼侍读,与刘克庄同纂修国史,可能因此与闻福建诞生的宋本《梅妃传》、《莆阳比事》梅妃入侍条。其《解语花》词序曰:东湖赋莲后五曰,双苞呈瑞。昌化史君持以见遗,因用时父韵。词为:
红星湿月,翠影停云,罗袜尘生步。并肩私语。知何事、暗遣玉容泣露。闲情最苦。任笑道、争妍似妒。倒银河、秋夜双星,不到佳期误。
拟把江妃共赋。当时携手,烟水深处。明珠溅雨。凝脂滑、洗出一番铅素。凭谁说与。莫便化、彩鸾飞去。待玉童,双节来迎,为作芙蓉主①。
词中咏及“争妍似妒”、“拟把江妃共赋”,隐约点到江梅妃的故事。联系到关于解语花的典故,才能明瞭。《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条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而宋代比赵以夫更早的文人已谈到解语梅花的典故。
李之仪,字端叔,沧州无棣人,进士。政和七年(1117)终朝请大夫。年80余,有姑溪居士文集。其《清平乐·橘》有句:“画屏斜倚窗纱。睡痕犹带朝霞。为问清香绝韵,何如解语梅花②”。
笔者认为,唐时明皇喻杨贵妃为解语花(千叶百莲)后,北宋时文人又喻梅花为解语花。到南宋初,赵以夫的《解语花》词就联系了杨、梅两妃的故事。
但是,还有认为江妃是水神的。如黄公绍,字直翁,邵武人,咸淳元年(1265)进士,隐居樵溪。有在轩集。其《汉宫春·郡圃赏白莲》词,就有句:“青冥世界,向龙宫、涌出江妃①”。
淳祐十年(1250)至咸淳五年(1269)间,莆田人刘克庄写了6首关于梅妃的诗。
景定三年(1262)进士的庐陵人刘辰翁,其《酹江月·北客用坡韵改赋访梅》词有句:“戴花人去,江妃空弄明月”。到《八声甘州(春雪奇丽,未能赋也,因古岩韵志喜)》词,又有句“招得梅妃魂也,好似去年春”。
综上所述,诗词中,江妃转化为江梅妃的时间为乾道、淳熙间(1173—1174)至咸淳五年(1269)。
四、刘克庄三咏江梅妃
南宋后期的莆田人刘克庄(1178—1260),所咏梅妃的诗词最多。
开禧元年(1205),刘克庄19岁,在临安,补国子监生。嘉定二年(1209),以门荫补将仕郎。次年,初仕靖安主簿。嘉定六年(1213)七月至七年父卒乡居,十二年初夏至十四年冬监南岳祠,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八月辞广西经略安抚使幕乡居。十七年春,刘赴临安改秩宣教郎,看到并赋诗《明皇按乐图》。绍定元年(1228)秋至六年,刘因梅花案而贬主仙都观,端平三年(1236)春至嘉熙元年(1237)春贬主玉局观,嘉熙元年中秋至三年九月贬主云台观,淳祐元年(1241)冬至四年秋贬主崇禧观。六年,刘以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十二月至十一年三月贬主明道宫①。而“祠官之任,家居而食厚禄②”。刘克庄乡居时,或是看到莆田同乡李俊甫写的《莆阳比事》(内录有“梅妃入侍”条)或是看到宋本《梅妃传》,淳祐十年(1250)始咏梅妃。即《梅花十绝答石塘二林》三叠之五:
半卸红绡出洞房,依稀侍辇幸温汤。
三郎方爱霓裳舞,珍重梅姬且素妆。
温泉宫在骊山,距西京长安60里。唐玄宗虽方爱善跳霓裳羽衣舞的杨贵妃,但仍珍重素妆的梅姬。
淳祐十一年(1251)四月,刘克庄在里居5年后复出,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等官,闰十月又罢官。乡居时,刘克庄于宝祐元年(1253)看到两妃的像,遂咏诗《唐二妃像(梅妃、杨妃)》:
不但烹三庶,东宫亦屡危。
元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
素艳羞妆额,红膏妒雪肤。
宁临白刃死,不受赤眉污。
唐开元二年(714)十二月,玄宗因宠赵丽妃而封其子李瑛为太子。赵丽妃亡故后,玄宗因宠武惠妃而钟爱其子寿王。二十四年十一月,武惠妃诬陷:太子结党、欲害惠妃母子并指斥玄宗。玄宗欲废太子与鄂王、光王,中书令张九龄据理力谏而丢了宰相之职。二十五年四月,惠妃又指使女婿杨洄诬陷太子与鄂王、光王及太子妃之兄薛锈异谋兵变。四月乙丑日,玄宗废太子、鄂王、光王为庶人,流薛锈于瀼州,同日又赐死4人,坐流贬者数十人,株连甚众。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评曰:“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①”。
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安禄山包藏祸心而认杨贵妃为母;杨亦用锦绣做大襁褓洗儿裹之、生日赐钱,演出干母子的丑剧。唐元和十二年(817)元稹《连昌宫祠》已有句:“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姚崇、宋璟是名宰相。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天宝十载(751)下记:“自是安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醒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这些记载与《开元天宝遗事》卷下《金牌断酒》条相符。唐玄宗等人与杨贵妃三姐虢国夫人有私情。安禄山随后率军叛乱,屡危朝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素妆但天姿国色的江梅妃,屡被杨贵妃嫉妒而贬至冷宫,在安史之乱时宁死而不受污辱。“素艳羞妆额”的出处在《白氏六帖》卷四《人日》的“梅花妆”。五代末明经及第的莆田人徐昌图《木兰花令》,最早咏及:“汉宫花面学梅妆②”。
此后,刘克庄看到《明皇幸蜀图》,并赋诗。
宝祐四年(1256),克庄《冬夜读几案间杂书,得六言二十四首》,其十七咏道:
李妹玉曜肤色,梅娘淡妆素衣。
大主嗔老奴爱,三郎怕肥婢知。
唐代,陈鸿的《长恨歌传》喻杨贵妃为汉武帝所宠的李夫人。李夫人出身于中山国的音乐歌舞之家,容貌姣好,早卒。武帝怜而画其像,作《悼李夫人赋》,以皇后规格礼葬,封其两个兄长。唐末,莆田人徐寅曾咏《李夫人二首》,有句:“人间乐极即须悲”,“汉王不及吴王乐”。梅妃玉肤明亮,似李夫人的妹妹。她淡妆素衣,仍美貌无比,连太监高力士也望之动心。玄宗既嗔斥高力士,又怕自己亲近梅妃时被杨贵妃知道。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738)五月条载:高力士是“我(玄宗)家老奴”。淳祐四年(1244)秋,刘克庄除江东提刑时,作《杂咏一百首·高力士》,已咏:“五十年间事,浑如晓梦余。三郎南内里,何况老家奴”。南内即唐代长安的兴庆宫,原为玄宗当藩王时的故宅。玄宗即位后,高知内侍省事,宠任极专。杨贵妃体态丰满。景定元年(1260),克庄《海棠七首》之四描述:“一种穠纤态,三郎未必知。浪将妃子比,妃子太浓肥”。
景定元年(1260)十一月,刘克庄权兵部侍郎等官。三年三月,权工部尚书,兼侍读,九月告老归里。四年封莆田县开国子,加食邑三百户。五年,克庄的《诸公载酒贺余休致水村农卿有诗次韵》之八也有句:“论定会盼银信召,眷浓漫妒玉环肥(梅妃目太真为肥婢)”。
五、刘克庄《读〈开元天宝遗事》一首》
咸淳三年(1267),克庄81岁,致仕里居,失明,进封莆田县开国男,食邑达九百户。四年五月,特除龙图阁学士,仍致仕。克庄失明后,赋诗《读〈开元天宝遗事〉一首》,曰:
环子受兵火涴,梅姬如玉雪清。
二妃未免遗恨,三郎可煞无情。
该诗把受兵火沾污的杨妃与如白雪清的梅妃作了对比,放弃了从前已咏的杨妃祸国的看法,矛头直指宠用奸相权宦、沉溺声色的唐玄宗。早在唐时,莆田人、乾宁元年(894)进士徐寅
《开元即事》诗已归罪于杨国忠,有句评价杨贵妃:“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莆田人、乾宁二年进士黄滔也有类似看法,《马嵬》诗咏道:“锦江晴碧剑锋奇,合有千年降圣时。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
《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五代后周王仁裕著。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天水人,以文辞知名于秦陇间,唐末任秦州节度判官,五代时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工诗文、晓音律,与和凝等以文章知名于五代。有《西江集》、《唐末见闻录》等著作。
新旧《五代史》有传。
南宋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载《开元天宝遗事》为4卷159条。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一书,言明传世刻本有:明张氏建业铜活字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均二卷。200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开元天宝遗事》,言明张氏铜活字本有黄丕烈跋3条;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刻本二卷,有王仁裕自序,目录列146条、但正文缺“暖玉鞍”条;两种版本均重印自宋绍定戊子(1228)桐江学宫刊本(山阴陆子遹书)。可知,绍定刊本时已只有146条。
如今我们看到的只有146条,其中没有江梅妃的内容。北宋大诗人苏轼,赋有《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南宋时王灼的笔记《碧鸡漫志》,汇有《开元天宝遗事》的《凌波曲》佚文。刘克庄所见的《开元天宝遗事》,应是兴化军学刊本。笔者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开元天宝遗事》足本中有记载江梅妃,详见下述。二是刘克庄失明后浮想联翩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莆田两位诗人的作品均未提江梅妃。
黄滔(840—911),字文江,乾宁二年(895)进士,国子四门博士,寻弃职返乡。闽王王审知奏请朝廷授为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今福州)节度推官。黄滔规劝王审知放弃称帝,是闽中诗坛的领袖,有《马嵬》诗、《马嵬二首》诗、《明皇回驾经马嵬赋》等①,并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评论《长恨歌》,皆未提到江梅妃。清代李调元的《赋话·新话》卷四指出:“唐人咏马嵬诗甚多,文江更演为赋耳。芊眼凄戾,不减《长恨歌》、《连昌宫词》。”马积高《赋史》372页指出:唐朝的盛衰,玄宗时期是个关键。且中唐以后,皇帝常常播迁,晚唐尤甚,故诗人多喜咏玄宗及贵妃事,晚唐律赋中除莆田人黄滔的《明皇回驾经马嵬赋》外,尚有徐寅(莆田人)、王棨及张读各一篇,而黄滔这一篇写得最为凄凉,充满着感叹帝王末路的感情,尤显有讽谕时世之义,不独以对语为工。
徐寅,字昭梦(865?—928?)②,乾宁元年(894)进士,秘书省正字。唐亡后,闽王王审知聘为书记官,后唐同光元年(923)李存勖要闽王诛杀徐寅,寅遂辞官隐居家乡。其诗作之多,为唐五代闽人之冠。徐寅有《华清宫》、《再幸华清宫》、《开元即事》、《马嵬》等诗和《过骊山赋》等,也未谈及江梅妃。
南宋洪迈(1123—1201)著《容斋随笔》一书,卷一《浅妄书》驳《开元天宝遗事》一书4事而认为:《开元天宝遗事》是浅妄之书;近岁,兴化军学所刊此书,可毁。据《四库全书总目》,洪迈,字景庐,鄱阳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容斋随笔》先成十六卷(一笔),刻于婺州。淳熙(1174—1189)间传入禁中。此后,续笔有隆兴二年(1164)自序,称作一笔18年,作续笔13年。则一笔作于靖康元年至绍兴十四年(1126—1144)。由此可知,“近岁”的兴化军学所刊《开元天宝遗事》,早于绍定刊本80年左右。应是4卷159条的。
2006年3月,曾贻芬的《开元天宝遗事·点校说明》指出:该书的舛谬不仅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所指出的4条。但这也不足以证明此书托名王仁裕,是伪书当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159条,分为4卷”。该书中记的内容,源于民言委巷相传而语多失实,王仁裕又未能详核史实,疏失舛误自然不免。何况《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唐末见闻录》,说明王仁裕对唐代史事的关注,可以作为《开元天宝遗事》出于王仁裕之手的一个佐证。其次,从《开元天宝遗事》所记玄宗、姚崇、宋璟、卢奂事与旧唐书的记载联系比较,可以认为《开元天宝遗事》所述史事有相当的可靠性,而这确实得到后世的认同。第三,《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下的记述,与《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依冰山》条的部分内容相近。《资治通鉴》采用《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充分肯定了《开元天宝遗事》的史料价值。
六、刘克庄的《梅妃》叹惜梅妃
咸淳五年(1269)正月,刘克庄赋诗《梅妃》,同月去世,享年83岁,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梅妃》是克庄咏江梅妃的最后之作①。
箫能妻弄玉,琴可挑文君。
吹彻宁哥笛,梅妃未必闻。
该诗短短四句,用了三个朝代的四个典故。魏晋间《列仙传》记载:箫史善吹箫,秦穆公因而将好吹箫的女儿弄玉嫁给箫史。数年后,箫史乘龙、弄玉御凤,双双升天而仙。《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描述了相如对文君的巧恋:“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卓文君因此动心,夜奔相如,同归成都。景云元年(710),临淄郡王李隆基平韦氏乱有功,太子宁王(680—741)因此让位于平王隆基。先天元年(712),隆基即位为玄宗,称兄宁王为宁哥。宁王以识曲辨声而闻名,唐代温庭筠《弹筝人》诗有句:“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嘉定十七年(1224),克庄《明皇按乐图》诗,也有句:“戏呼宁哥吹玉笛,催唤花奴打羯鼓。”花奴即汝南王李琎。玄宗要宁王、汝南王吹笛打鼓,但“梅妃未必闻”。
唐世宫禁与外廷不相隔绝、唐诗对此也不避讳。南宋《容斋随笔》“翰苑亲近”、“唐诗无避讳”两条已载,并引白乐天、元稹、杜子美等人的诗为证。宋代《杨太真外传》载:玄宗与贺怀智、马仙期、张野狐、李龟年、宁王、杨贵妃等演奏乐器,秦国夫人在旁观赏。宋代《莆阳比事·梅妃入侍》也载:玄宗顾诸王戏曰:梅妃“吹玉笛、作惊鸿舞,一一光辉”。可知,唐室诸王与玄宗妃子常在一起;其中的笛、舞爱好者如宁王、梅妃、杨贵妃等的互演互评,习以为常。83岁的刘克庄临去世时,为何叹惜开元二十九年(741)宁哥去世前“梅妃未必闻”到宁哥笛呢?由于史料流失甚多,又事隔700多年;如今无从考查。
莆田人卢兆荫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初有考证,在《江采苹有无其人》一文中指出①:《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均未记载梅妃。唐玄宗即位前,宠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先天元年(712)即位后,专宠武惠妃。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武惠妃死后,专宠杨贵妃;《莆阳比事·梅妃入侍》说梅妃遭妒遂迁东都上阳宫。史载: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玄宗从东都洛阳迁回西京长安后,再未去过东都;二十五年十二月杨玉环入侍后,也未去过东都;此后,不存在唐玄宗再去东都会梅妃的史实①。总之,正史记载中,均未见与唐玄宗生活在一起的江梅妃。如今,我们必须发掘正史以外的文字记载。
第二节 元明与清代前中期的作品
一、元时梅妃与杨贵妃多混为一人
《元诗选》一套9大册,全无正面咏及江梅妃的诗。只有以下数首,隐约点到江梅妃的史事,或是将江梅妃与杨贵妃混为一谈。
明本(1262—1323),钱塘人,朝廷赐为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其《梅花百咏和冯学士海栗作·录十二》之三有句:“三郎正爱《霓裳》舞,珍重椒房自惜春”。椒房,代称后妃;指自己惜春的梅妃。之十有句:“云开巫女多娇面,浴出杨妃一丽人②”。早在北宋时,大诗人王安石的《次韵徐仲元咏梅二首》有句:“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肌冰绰约如姑射,肤雪参差是太真”。《西江月·红梅》词有句:“真妃初出华清池。酒入琼姬半醉。”三次喻梅为杨贵妃。苏轼《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花落复次前韵》也有句:“玉妃谪坠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嫡坠”二字出《杨太真外传》。玉妃,即贵妃也。韩子苍云③。可知北宋时,王安石、苏轼等大诗人皆喻梅为杨贵妃。南宋时,莆田人刘克庄的《汉宫春·秘书弟家赏红梅》也有句:“还似得、华清汤暖,薄绡半卸冰肌”。以杨贵妃浴罢喻梅花的娇艳光鲜。
王冕(约1310—1359),元时诸暨(今属浙江)布衣,工于画梅,其《红梅四首》之三有句:“昭阳殿里醉春风”,“玉箫吹过小楼东①”。汉成帝时,赵飞燕居后宫昭阳殿。此后,多以昭阳指皇后之宫。这里借喻杨贵妃享皇后之礼而“醉春风”;隐指梅妃的被贬东宫而写《东楼赋》。
《元诗选》以外,倒是发见数首咏及梅妃的诗。
段克己(1196—1254),字复之,号遁庵,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幼时与弟成己并以才名,礼部尚书赵秉文誉为“二妙”。金末,克己以进士贡,金亡,与其弟隐居于龙门山中,兄弟俩有《二妙集》,是“河汾诸老”的领军人物,今存的作品多写于元初。《雪梅》诗未载于《元诗选》二集上册,而载于《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该诗批评唐玄宗不珍惜梅妃:“风流谁似李三郎,不记仙姿委路旁。天上人间无觅处,风流罗幂只闻香。”胡祗遹(1227—1295),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官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赠礼部尚书,谥文靖。《元史》有传,著《紫山大全集》。《永乐大典(残卷)》2813卷《紫山集》中录诗《题杜君复家藏王黄华〈雪梅图〉》,有句:“罗浮窗户愧庸俗,江妃篱落羞寒乞。赵昌徐熙尘土人,办与凡花逞颜色。仙人飞升今几秋,高气清香尚蒸湿。人间宝墨有如此,锦囊玉轴如珍惜”。这是今见最早的咏及江梅妃的雪梅图。
胡天游,名乘龙,别号松竹主人,自号傲轩,平江人,元隐居不出,其《傲轩吟稿》中录有《黄梅谷》诗,有句:“高人卒岁守穷谷,自笑谷中无一物。何年招得玉妃魂,夜半挥锄种明月”。“北风吹面君始归,正恐梅妃有嗔语”。该诗中玉妃即梅妃,高人在黄梅谷中浮想联翩,赋成长诗。
高棅(1350—1423),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福建长乐人,永乐间自布衣征为翰林侍诏,升典籍,见《明史·文苑传·林鸿传附》,是闽中十子之一。高棅于明洪武十七(1384)至二十六年编成《唐诗品汇》,三十一年又增补,共100卷。《唐诗品汇》标举盛唐,推崇李、杜,在反对宋末“猥杂细碎”和元人“妖治俶诡”的诗风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拉开了文论中唐、宋之争的帷幕,开了明人摹拟复古倾向的先河,引导了整个文学潮流,对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的研究具有特殊贡献。卷五十五载《杨妃·谢赐珍珠(玄宗有题梅妃图,真妃故有此谢)》:“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与寂寥”。该书所录的《谢赐珍珠》诗,是元时流传的,也把梅妃与杨贵妃混为一人。直到清时,还有人这样认为。如高凤翰(1683—1748),字西园,号南村,胶州(今山东胶县)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赋诗《题梅花册》①,有句:“月底衣裳舞太真”。杨贵妃,号太真。
二、明代的诗词和画作
岳正(1420—1474),字季方,号蒙泉,顺天(今北京)人,明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成化元(1465)至三年任兴化知府,五年致仕。《无题四首追和元马伯庸韵》之三有句:“宫婢貌难当万乘,玉环心不在三郎②”。叹曰:宫婢江采苹的美貌留不住唐玄宗,万岁爷倾心杨贵妃但贵妃心不在玄宗。
俞泰,字国昌,号正斋,无锡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户科给事中,擅诗文工书画。赋诗《梅妃吹笛图》:“音律从来寿邸长,宫中新调称新妆。谁知吹出无双曲,究为嵬坡诉断肠①”。该诗认为杨玉环赐死后,梅妃仍在。
仇英(1498—1520),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后居苏州。初为漆工,曾向周臣学画,后在鉴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观摩大量古代名作,技艺大进,自成一家,擅长山水、人物。“世称之为有明人物第一大家②”。仇英的人物画以工笔重彩为主,尤善仕女画,体态俊美、笔法细微、敷色妍柔、雅俗共赏,有“仇派”仕女之誉;亦能作精简的水墨人物画。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梅妃写真图》(藏徐悲鸿纪念馆),布局、画法几乎完全一样。前者笔墨灵秀,是真迹。后者较为工板,应是摹本③。
《梅妃写真图》有二十二个人物,梅妃端坐厅堂的中央、屏风之前。梅妃的左侧有6个宫女在交头接耳,且带惊诧之情。图的左侧,两个宫女从里屋探头而出,和屏风右侧探头的宫娥一样,是听到梅妃画像场面的声音,带着好奇欲出的表情。图右侧也有4个宫女,其中3个正聚精会神地看画家在为梅妃画像,另一个宫女头转向后看,暗示右边也有宫女欲出。厅堂四周是雕梁画栋、浓彩的围栏柱廊,显出豪华气派。围栏之外、玉阶之下有2个太监作议论之态。为梅妃作像的画师面向梅妃,端坐姿态的背影前、图幅上,有艳丽的梅妃像,画中像与图中人物酷真毕俏,工笔重彩,人物栩栩如生。1950年初,北京举办画展,徐悲鸿前往参观时看到这幅佳作。一位外国驻华大使正在与主人讨价还价,要买此图。徐悲鸿不愿这幅国宝流落国外,就毅然上前说:“我买了,不还价。”本来这位驻华大使与徐悲鸿有私交,而且已商议过邀请他到大使的国家去办画展。大使怪悲鸿夺其所爱,一气之下,就取消邀请徐悲鸿去办画展的事。但徐悲鸿一点也不后悔,他把国家的历代名画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但徐悲鸿儿子、中央美院美术史学研究生导师徐庆平副教授却说:《梅妃写真图》是元代王振鹏的作品。元刻本《图绘宝鉴》卷五载:“王振鹏,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运千户,界画极工致。仁宗眷爱之,赐号孤云处士”。
成书于明代的《新镌绣像列仙传》有张果图,四川新都人(时居成都府)、还初道人洪自诚辑,木刻本卷首有吉石金尔珍的题记,谈及:虽然这些插图的画工及镌刻匠的姓名不详,但可与明代名画家仇英所绘的《列女传》相媲美。今所见的木刻本,是光绪十三年(1887)扫叶山房校刊;1921年上海大成书局以木刻本为底本石印。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插图采用石刻本。《隋唐演义》载:安史之乱时,张果救助梅妃。
明代,裘昌今《太真全史》卷首有幅木刻插图,题为《惊鸿舞》,描绘梅妃身穿长袖舞衣,长裙曳地,肩披长巾,正在做纵身飞舞的动作,犹如惊飞的鸿雁。
唐寅(1470—1523),字子畏,号伯虎,别号桃花庵主,又号六如居士,吴县(今苏州)人。16岁时,秀才考试得第一名;他随父到仙游县九鲤湖祈梦求取功名。25岁时,父、母、妻、妹在一年内相继去世。他悲痛读书,弘治十一年(1498)应天府试得第一名,名震江南,诗、书、画三绝,自称“江南第一才子”。有《六如居士集》。《唐伯虎全集》卷三,载诗《梅妃嗅香》:
梅花香满石榴裙,底用频频艾纳熏。
仙馆已于尘世隔,此心犹不负东昏。
画家文征明的二子文嘉,在《写生逸致图》上题诗《梅花》,有句:“瑶篇曾呈梅妃传,素箑新窥点额图①”。
唐、文的这两首吟咏,此后却被收入江砢玉的《珊瑚网》,分别题为《梅妃》(载卷十五)、《梅花》(载卷四十六)。江砢玉,字玉水,徽州(属今安徽)人,寄籍嘉兴,崇祯时官山东盐运使判官,所撰的《珊瑚网》48卷,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
明万历以前,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女诗人王凤娴与女引元两人吟唱了《梅妃怨》三首②。因同是女性而感叹:“多才纵有东楼赋,不入离宫弦管声。”“宁将哀怨赋东楼”,“始知笑语在西宫”。梅妃咏有《东楼赋》,西宫指杨贵妃所居处。
费元禄,字无学,又字学卿,江西铅山人,其《甲秀园集》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75)。录《梅妃村(兴化府)》、《梅妃谢珠》两诗,详见五章三节二目。
徐渭(1521—1593),字文长,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秀才,16世纪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其《书唐伯虎所画美人·眼儿媚》词也对比了梅妃与贵妃,有句:“可是华清春昼永,睡起海棠么。只将穠质,欺梅压柳,雨罢云拖③”。北宋时,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已载:唐玄宗说杨妃醉时,似“海棠睡未足耳”。《梅妃传》则载:江梅妃是柳叶眉。徐渭的《双调清江引·题花卉卷》,由题花而起兴:“瘦梅妃、肥太真,恁自忖④”。
明代坊贾托名钟惺(1574—1625)的《名媛诗归》,卷十载有《一斛珠》,评“桂叶双眉久不描”句:“桂叶”二字便新,若入“柳叶”等语,却陋极矣。又评“残妆和泪湿红绡”句:他本作“污”,不如“湿”字宛闲。崇祯三年(1630),海盐人胡震亨(1569—1642?)编成《唐音统签》1033卷,卷一三录有江梅妃的《一斛珠》。清时,陆昶的《历朝名媛诗词》卷四也评《一斛曲》:诗少婉曲,一气而出,可以想其怨愤不觉触发之意。
朝鲜半岛的柳潚(1564—1636),字渊叔,号醉吃,1597年进士,有诗《喜春雪》;南龙翼,字云卿,号壶谷,明末为副使出使中国,有诗《问梅花》、《和赤谷〈惜花〉十绝之八〈玉梅花〉》;均咏及梅妃。
董以宁(1630—1669),字文友,常州人。明末诸生,有才子之称。早年的《蓉渡词》录有《虞美人·限韵咏池上杨妃海棠》,下阕为:“梅妃应笑胭脂重,欲唤从前梦,临池照处映鱼茵,疑向三郎传语倩双鳞”。
三、清代前中期的诗词和画作
清顺治、康熙时,兴化府诗人林尧英、林宾王、陈延彬、游谦征、林琅玉均咏及莆田的江妃村,载《莆风清籁集》卷四十、三十八、四十一与《兴安风雅》卷三,都是指东华村,详见史志篇。
周亮工(1612—1672),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有诗《竹枝词为胡彦远纳姬赋》①。胡彦远,名介,钱塘(杭州)人,有《旅堂诗集》,布衣,妻女皆能诗;晚逃于禅,年未五十而卒②。顺治中,彦远游京师③,旧姬是唐山人。
亮工为其新姬而咏诗:“蛮妆新样木兰陂,学得金陵百事宜(姬初至榕城,学为秣陵妆)。莫羡江苹黄石好(江苹,莆之黄石人),我侬乡里有西施。”诗由新姬(涵江人)的蛮妆(木兰陂妆)改为秣陵妆(金陵妆)而联想,把(福建莆田涵江)美女江[采]苹(江梅妃)与春秋时越国苧罗山(今浙江诸暨县南)美女西施相比。
陈维崧(1626—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以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清初阳羡词派领袖。他以梅妃喻梅花,《画堂春·小春》有句:“记得年时岭外,梅妃犹未胜妆。如今花满纸糊房,红紫成行①”。《花发沁园春(月夜布席绿萼梅花下、同友人小饮)》有句:“念月姊、彻夜孤寒,梅妃自小幽独”。“夜深沉,我醉休扶,和月和花同宿”。《贺新郎·月夜看梅花》评说杨贵妃与梅妃:“忽忆开元当日事,中有梅妃蛾绿。何必羡玉奴新浴,可惜楼东三十树,雨霖铃,都做连昌竹。花应叹,睡难足②”。
吕履恒,字元素,河南新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有《梦月岩集》。其《江妃怨》诗有句:“羯鼓听残宫漏沉,楼东赋就更微吟③。”
山东德平诗人、康熙间举人李鹏九的《江水儿》,也有句:“月落光犹在,情留梦不舒,伤心雁唳楼东赋”。载《骨董三记》卷一。
朝鲜半岛的金万重(1637—1692),字重叔,号西浦,1665年文科状元,1674年《读班婕妤、梅妃故事,感而赋之》。
王士禛(1634—1711),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少时作《咏梅妃·减字木兰花》①,点及一斛珠与东楼赋。此后,《骊山怀古八首》之三增加对比:“舞罢惊鸿岁月徂”,“君王自爱霓裳序②”。《季园赏白牡丹》,则加调侃:“太真霞脸带醉色,睹次亦学江妃酸。”
张宗橚(约1700年前后在世),字永川,号思崖,浙江海盐人,监生。其《琐窗寒·珍珠梅篱间盛开》把南海鲛人泪、江汉江妃的典故都融入江梅妃的故事:“似鲛人易泣,泪珠都陨。解佩携来,梦绕湘皋无准。想惊鸿、舞罢妆残,楼东一斛愁瘦损③”。《述异记》载:南海中有鲛人室,水居如鱼,不废机织,其眼泣则出珠。
尤侗(1618—1704),字同人,号悔庵,又号艮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官至侍讲。其词《疏影·黄梅花》将江妃喻为江梅妃④,有句:“前身本是江妃种,催妆早、先来一霎”。还有词《摸鱼儿·春怨》,有句:“梅妃休怨楼东赋,吊取马嵬黄土”。
江南武进(今属江苏人)董大伦(1666—1705),字敷五、畴叙,号叔鱼,著《梅坪诗钞》三卷,《竹夫人词》八首之五有句:“清绝梅妃较若何,冷然姑射不争多⑤”。
冯光裕,字叔益,号损庵,代州人,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官至湖南巡抚,有《柴门老树村稿》。其《古意》二首之二有句:“谁知月下江妃树,别殿无人慰寂寥”,载《晚晴簃诗汇》卷五十八。
黄唐棠,名之隽,官中允,曾视学闽中,以事去官①。黄集唐诗百余联,咏梅妃之句有“却嫌脂粉污颜色,何必珍珠慰寂寞”。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闽县人孟超然有《沈学子文自淮南寄示同黄唐棠先生山游诗因题其后》,载《国朝全闽诗录》初集卷十七。
朱仕玠,字壁丰,号筠园,贡生,福建建宁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台湾凤山县教谕。《过江妃故里》四首对比杨妃②:“翻笑上皇诚错计,马嵬亡国竟何人?”认为:梅妃“古来嫔御谁相匹”,“青塚魂归同寄恨”。
乾隆三十七年(1772),莆田人郑王臣编有《莆风清籁集》(附《兰陔诗话》),卷五十一录有郑王臣《过江妃村》五首,郑远芳《莆阳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上册还录有郑王臣《江妃村》一首。这时的江妃村,是江东村,详见史志篇。
舒位,字立人,又字铁云,大兴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其《瓶水斋集·冷枚(华清新浴图〉》有句:“江妃辞去念奴陪,迟日熏风汤殿开”。叙及杨玉环、江梅妃、念奴、安禄山等人与唐玄宗之间的故事③。
梅妃的故事还引起乾隆皇帝的诗兴。《御制诗集三集》卷五十七载有《山茶》诗,有句:“设拟唐宫斗绝色,梅妃侧畔有杨妃”。《御制诗集四集》卷三十九载有《红梅》诗:
气味本来自相亲,妆成不语亦传神。
试看泪污红绡处,合唤唐宫江采蘋。
兴化府教授林朝阳赋诗《江梅妃思莆》,有句“春光独占锦江隈”,“美人终有荒村在”。乾隆《莆田县志》未载林朝阳,应是乾隆后任职的。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官至江宁知县。十七年,袁赋诗《再题马嵬驿》①,有句:“听说西宫恩幸少,梅花犹得落昭阳”。
事指明皇密召被贬的梅妃到翠华西阁叙旧爱,次晨被杨妃发觉而仍归东宫。安史之乱时死,葬于温泉池侧梅树下。袁枚39岁就辞官终养,诗倡性灵说,是乾隆三大家之首。莆田人、兰州知府郑王臣以弟丧去官,载万卷书回莆,在袁枚处舣舟三天索序,袁枚遂写《兰陔堂诗序》。四十四年,袁枚又赋《元日牡丹诗》贬杨妃褒梅妃②,有句:“如何绝代玉环姿,蜂未闻香蝶未知。想与梅妃争早起,严妆同对雪飞时。”
赵翼(1727—1814),字雪菘,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探花,官至贵州分巡道贵西兵备道,是乾隆三大诗家之一、著名史学家。五十三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备办军需,赵翼与浙江孝廉李莪州同在李侍尧幕府,赵翼赋诗《莪州以陕中游草见示,和其五首》,之五《马嵬坡》抨击唐明皇“宠极强藩已不臣”,“召乱何关一美人”。由杨贵妃想到:“谁知几点胭脂泪,别有生离江采苹③”。
嘉庆六年(1801)举人、江西籍著名诗人乐钧的词《探春·宋云墅仪曹座上咏白丁香花》,下阕有句:“是小玉娇魂,烟外吹坠。屈与添香,烦教贴翠,除是梅妃才可④”。
王筠(1749—1819),字松坪,号绿窗女史,长安县(今属陕西省西安市)人,清代戏曲女作家,诗歌200多首附于其父王元常的《西园瓣香集》中,其诗《江梅妃》有句:“有金难买楼东赋,寂寞梅花老上阳”。
刘嗣绾(1762—1820),字醇甫,号英初,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其《鬲溪梅令·烟陇探梅》词有句;“好在东风庭院、见梅妃。绿苔生卧衣①”。
嘉庆(1796—1820)时,莆田县诗人郭尚先、陈池养与福清诗人、尚先的叔叔郭龙光也诗咏江梅妃,分载于《郭大理遗稿》卷二、《慎余书屋诗集》卷一、《韶溪诗集》卷一,详见史志篇。
王翙,字钵池,寿春(今安徽寿县)人,活动于清乾、嘉(1736—1820)时期。王氏善山水、花鸟、虫兽,“而于人物为尤著”,“曾供奉内廷”。绘有《百美新咏图传》,刊于嘉庆时。河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影印为《百美图谱》,可惜删去了颜鉴塘的题诗。书首有“雪月华岁最信君”“犹疑照颜印”《题王钵池画图并序》;嘉庆九年(1804)十一月,小西涯居士法式善《序》。梅妃图传载于《百美图谱》图传二十一。
萧重,字远村,静海(今属天津)人,嘉庆十七(1812)起任职莆田,道光六年(1826)由莆田县尹调摄金门篆,道光十年后再游莆田。赋诗中10多次咏及江梅妃②,使人们了解到梅花书屋、江妃墓、江妃墩、梅岭、梅花村等的情况。作者所吟丰富了梅妃的故事,详见史志篇。
日本诗人田能村竹田(1777—1831)的《梅花》诗联吟杨贵妃与梅妃的故事:“梅月影香云母屏,桂眉不画立闲庭。君王徒有真珠赐,唯道海棠眠未醒①”。
第三节 清后期以来的作品
一、清后期诗作
道光(1821—1850)时,山阴(今绍兴)人高颂禾任职闽地,有诗四首和刘左黄的《题梅妃小像绝句》,载于《暴麦亭集·闽游集》卷下,由画而咏梅妃,详见史志篇。
鸦片战争以后,九江府德化县万梦丹的《梅妃》诗有句:“纵使珍珠倾万斛,算来不敌泪珠多②”。她从女性诗人的角度,感叹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迫下女同胞的悲哀。同治时,湖南长沙女诗人杨蕙卿的《梅花四首》其一也是同样的情怀,有句:“一枝初绽名园里,凄绝梅妃带泪看③”。
莆田人郭篯龄(1825—1886),字子寿,号山民,道光二十一年(1841)县学秀才,后例贡入太学,选为州同知,候补浙江。太平天国起义后隐居莆田。有诗《江妃村》④,赞曰:“灵秀千秋毓此村”;以荔喻杨贵妃、以梅喻江梅妃:“荔子竟遮天暗昧,梅花能耐月黄昏”。
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莆田人宋际春,同治时任台湾教谕,对江梅妃推崇备至,诗咏《江妃村》6首⑤。在《绿天偶笔》中评曰:江梅妃的一首《一斛珠》岂抵一本诗集;在《竹素园诗·序》中,认为《一斛珠》是千年莆诗之倡⑥;在《闽中论诗绝句》中两赞梅妃①;在《莆中名迹》中再咏江妃村②。
咸丰时,莆田儒妇陈淑英著《竹素园集句》、《竹素园诗钞》,咏及梅妃的有7首。林有珠、唐韵、刘璋寿、杨端、江大球、江宪章、翁大奎各有题词,誉陈淑英为江梅妃之后莆田又一女诗人,详见史志篇。
清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广西象州县壮族诗人、曾任户部主事的韦陟云《羁栖四十韵》,有句:“地与生番界,溪曾大甲沿。鸡笼云漠漠,沪尾月娟娟。人忆梅妃丽,男宜草席妍。轮舟通曲折,铁路绕回旋”。载《历代壮族文人诗选》288页。
清末,新安(属今河南)人程羽文(荩臣)撰写有《鸳鸯牒》:“江采苹,俊朗高洁,抱恨楼东,宜遥配孟浩然、林君复,肆癖湖山,共对梅花索句③”。赞誉江梅妃也是高士。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湘北襄樊)人,盛唐诗人,怀有用世之心,因不涉事务,拙于奉迎,功名无着,遂以漫游为事;后为荆州从事,开元末卒于疽。孟浩然与张九龄、王维为忘形交。王维私邀孟浩然入内署,适明皇至,浩然匿床下。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诏浩然出,孟诵诗至“不才明主弃”。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孟有《早梅》诗:“园中有早梅,年例犯寒开。少妇争攀折,将归插镜台。犹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④”。吴乔《围炉诗话》卷二说:“孟浩然诗宛如高士”。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人。无意仕途、虚名,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娶,所居植梅蓄鹤,人因称“梅妻鹤子”,溢号和靖先生。其诗大多表现了隐者的高雅情怀,其对雅格品位的追求,影响了整个宋代文化的品位。林逋开了宋人顶礼膜拜梅花的先河。梅花已经化入其心魄,梅花即我、我即梅花矣①。
《香艳丛书》三集卷三还载有吴江(属今江苏)人杨淮(蓣远)的《古艳乐府·楼东怨》,其咏有句:“海棠开、江梅落”。“空留月影伴楼东”。海棠指杨贵妃,江梅即江梅妃。
文廷式(1857—1904),字道希,号云阁,晚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江西萍乡人,生长岭南。光绪十六(1890)进士,官至侍读学士,二十一年参与发起强学会提倡变法,次年被革职。戊戌政变后避居上海。精子史之学,尤工诗词。有《纯常子枝语》、《补晋书艺文志》、《云起轩词钞》、《文道希先生遗诗》、《闻尘偶记》、《罗霄山人醉语》等。其诗《落花》十二首之九有句:“有情湖畔三生石。无用楼东一斛珠”。
二、丘逢甲的诗作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晚号仓海君,台湾淡水(今苗栗县铜锣镇)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赋诗《题杨太真外传》②,十首之一有句:“双陆家风传李老,斛珠恩宠妒梅精。谁知得宝宫中乐,惊破开元曲太平”。
甲午战后(1895),丘逢甲倡建“台湾民主国”,声明永奉中国。次年内渡广东办学,任临时参议院参议员。三十四年赋诗《李湘文(启隆)邀同雪澄实甫陶阳二子上涌村啖荔枝作》③,有句:“少年最爱十八娘,至今追忆神犹驰。自来岭南日啖三百颗,临风辄念天人姿。门书荔子甲天下,已生荔子生梅妃(兴化府署大书:‘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为楹联)。梅妃生闽杨妃粤,杨妃宠盛梅妃衰。人间选色论品目,两皆尤物天所遗。亦如荔枝各具色香味,相看不厌不见常相思。奈何玉环不自爱乡味,坐令蜀产称珍奇。蜀荔之佳万万逊闽粤,维髯蜀客亦谓言非欺。惜髯但啖粤荔未到闽海湄”。以下予以赏析。
北宋时仙游枫亭人蔡襄的《荔枝谱》载:“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时人以少女比之。俚传闽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其塚在(福州)城东报国院,塚旁有此树云”。北宋李纲《初食荔枝四绝句(所居报国,有十八娘荔枝)》之四咏道:“平昔传闻十八娘,丰肌秀骨有余香。今朝亲到芳丛下,应许幽人餍饫尝”。
南宋淳熙九年(1182)成书的《三山志》土俗三记载:“十八娘红,色深红而细长,以少女比之。俚传闽王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蔡公所谱)”。“状元红,于荔枝为第一,出东报国院(曾公巩所记)”。同书寺观一载:易俗里的东报国院。
笔者奇怪的是:《三山志》未记十八娘红荔枝在东报国院,只记状元红荔枝在东报国院;可知北宋末李纲到东报国院尝食十八娘红荔枝后,到南宋《三山志》成书时该树已无。福州人遂将院中另有的状元红讹为十八娘红。而状元红确出于宋代的枫亭。熙宁九年(1076),莆田人徐铎中文状元,将延寿红荔种赠亲家枫亭人、同年武状元薛奕。宋神宗赋诗:“一方文武魁天下”,延寿红遂称状元红。南宋宝祐五年(1257)成书的《仙溪志》,物产荔枝目中未记载十八娘红。
蔡襄《荔枝谱》流传后,宋代诗人苏轼《减字木兰花》、苏辙《干荔枝》、洪炎《初食生荔枝二首》之二、王十朋等人,都吟诗咏到了著名的十八娘红荔枝。
明时,王世贞赠诗嘉靖举人、全椒知县弃归的莆田人佘翔,
有句:“十八娘红莆荔枝①”。明末,福州人曹学佺《荔枝叹》诗有句:“十八娘家粉黛残,玉肌罗帐泪阑干。枫亭三日无消息,马上空歌行路难”。该诗明确指出:十八娘红荔枝在枫亭。
清康熙时,郑德来《连江里志》记载:忠顺王女陈机,号二十小娘,捐首饰买地开圳,深8尺阔1.2丈,抵驿坂,远15里余,灌之。父洪进所舍法石禅寺之田,号金钗庄,立石记之。可知陈洪进之女名二十小娘,不叫十八娘。
但乾隆《仙游县志》列女传则改为:“陈玑,别字十八娘,洪进女,尝捐钗钏买地开沟,深八尺阔丈二尺,自枫亭抵惠安县之驿坂十五里以灌田,号为金钗沟,其庄为金钗庄。又尝手植荔支,至今称为十八娘,香味尤绝。”
乾隆《福州府志》寺观载:东报国院,在易俗里,久废。由于枫亭位于驿道,自宋至明,十八娘红荔枝在枫亭的传说逐渐占了上风,而福州的东报国院已废。此后,乾隆《仙游县志》遂附会为北宋时陈洪进的第十八女所植。
到道光时,林朗如的《枫亭志》仍表示怀疑,他引述蔡襄《荔枝谱》始载的闽王女十八娘红与康熙《连江里志》以后枫亭所传陈洪进女十八娘红“并同,然则十八娘荔枝,犹有二种也与?”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的江苏人石韫玉,官至山东按察使,被劾归乡,掌教20多年,有《梅妃作赋》杂剧,已说梅妃是广南人。民国时许啸天的《唐宫二十朝演义》,也衍说是广南人。
三、民国时期内地诗作
杭州诗人陆微照(1899—1980),民国时吟诗《杨玉环》,咏道:“一样烟尘埋玉骨,九原应不妒梅妃①”。
民国建立时的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学校校长、贵阳人姚华(1876—1930),赋词《一斛珠·梅妃》,有句:“长门尽日,残妆坐,懒梳慵栉,双眉冷淡春风笔②”。
1915年,莆田人李光荣(1850—1920年后)辑成《兴安风雅》诗集,卷三收录咏梅妃村的诗作甚多。有刘尚文3首、李光荣4首、林津4首,黄尚忠、林习伦、黄家鼎、程登瀛、唐焕章、周天章、周维新、陈维新各1首。咏及江梅妃的故宅、祖塚等;李光荣还有《村妇》竹枝词,写出江家妆的具体装扮,均详见史志篇。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属今福州)人,近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有《陈石遗集》(上、中、下),《陈衍诗论合集》(上、下),共320多万字。其《岂有》诗咏道:
岂有宁哥玉笛声,更无肥婢与梅精。
方床大被还长枕,不忍楼将花尊名。
该诗作于戊午(1918),载《陈石遗集》上册252页。陈衍史学亦著,他认为没有杨玉环与梅妃争宠事。可知梅妃故事,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论。
1920年五月四日,莆田人林翰、关佛心发起成立壶社,创会期历二年有余,社友10多人,一个月诗咏一题,遂成《壶社诗草》。贞部28卷的《梅妃村》录有14人诗作:林翰、关佛心、萧敦甫、陈耀枢(2首)、陈敬汤、温筱珊、方西湖、林及锋、郑渠、陈元璋、张景棠、游介园(4首)、黄祖汉、宋仁陶。他们到村访俗,抚今怀古,浮想联翩,佳咏争辉,详见史志篇。林翰1913年始任福建省议长,其《梅妃村》诗道:
一乡轶事唐天宝,千载齐名越苎萝。
故老相传鹅脰冢(东华村有小阜,在水中,
形如鹅脰,相传为妃归骨处),当年竟殉马嵬坡。
野梅树树精魂在,江水澌澌怨恨多。
隔岸犹听村女唱,斛珠一阙当山歌。
轶事即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事迹。林将江梅妃与出生于苎萝山的越国美女西施相提并论,又将“相传”骨葬鹅脰冢的江梅妃与赐死马嵬坡的杨贵妃分别褒贬。林翰还有《秋日杂兴并留别里中诸友》之四,载《山与楼诗集》卷二;宋仁陶还有《题宋宫人斜》、载《宋仁陶遗集》,《福州西湖强小姐墓(分来字)》六首之二、载《宋幼石诗草》,均咏及江梅妃,详见史志篇。
四、日据时期台湾诗作
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统治不断深化,诗人们的梅妃诗作,抒发了爱国反抗的心声。
洪弃生(1867—1929),原名攀桂,又名一枝,字月樵,后改名儒,字弃生。日人居台后,他拒不出任伪职,不与日吏交往,是日据初期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尤以歌行体闻名台湾诗坛。他到过莆仙,《寄鹤斋诗选》中有《过枫亭偶眺》、《过濑溪偶咏》、《兴化渡口三首》等。其咏梅妃诗4首中均寓入中国惨遭日寇侵略的悲痛心情。《闽中杂咏》有句:“半楼明月梅妃里”,“不堪萧瑟送残阳①”。《闻病偶咏》有句“愧落歌中一斛珠”,“不知瘴入梅花树②”。《虞美人·咏花二十韵》有句:“梅妃貌比菊妃扬”,“河山回首恨苍茫①”。《记梦》有句“敢将杜牧耽轻薄,欲与梅妃慰寂寞②”。
台湾诗人王效良,其《美人十咏·美人舞》有句:“唱彻江妃一斛珠,族扶倩影十毡毹③”。
陈髯僧,字佑余,福建晋江人,清末民初寓台10多年,曾鬻字集资而刻先人遗墨。《题忆梅诗录》有句:“驿使何人传庾岭,江妃尽日怨长门④”。
林仲衡(1877—1940),号壶隐,台中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栎社,为雾峰三诗人之一,其《仲衡诗集》1992年3月收入《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1辑,龙文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吊梅吟有序》有句:“红颜自古天相妒,不见梅妃憔悴身”。
谢汝铨(1871—1953),字雪渔,号奎府楼主,日据后从台南迁居台北。前清秀才,在《台湾新新日报》工作,兼《风月报》主笔。宣统元年(1909)参与倡设台北瀛社,有《奎府楼诗草》、《蓬莱角楼诗存》。其《疏梅》有句:“几枝无赖怯风霜,对镜江妃未竟妆⑤”。
陈静园,台南诗人。其《迎春》有句:“想到唐宫催羯鼓,江妃依旧怨东风⑥”。
东明,笔名,新竹人,其《美人蕉》有句:“潇潇雨滴芳心碎,遮莫梅妃一段愁⑦”。
义山,笔名,嘉义丽泽吟社社员,其《白扇》有句:“几度深闺评玉貌,满车皎洁比梅妃①”。
郑雨轩,新竹人,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书画家。其《春妆》有句:“轻涂浓抹坐清晨,对镜梅妃点额真②”。
王则修,台南县新化镇人,清光绪廪生,1928年8月在新化创办虎溪吟社,任社长,日据时是台南县的诗文名家,其《香冢》有句:“敢是梅妃死后魂,香留窀穸月黄昏。葬身艳说花无语,埋骨深怜玉比温③”。他认为鹅脰是梅妃的骨葬坟。
林又春,屏东人,1940年在东港区林边乡创办兴亚吟社,任社长。其《画梅》有句:“可怜静草楼中夜,添写江妃泪暗垂④”。
蔡旨禅(1900—1958),女,名罔甘,道号明慧,澎湖才女。1926年参与创建高雄莲社,弘扬佛法。晚居新竹,1957年返澎主持马公澄源堂。弟子辑其作为《旨禅诗画集》。其中1949年前所作的:《红梅》有句:“梅妃宠罢雪交加,偶着红绡韵孔嘉”;《红梅鹊》有句:“疑是梅妃初睡起,如何晕颊印霞新”。
五、郭沫若、张大千等分咏梅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两位大文人也咏及梅妃。
1962年11月,郭沫若及夫人于立群到莆,其《途次莆田》诗有句:“梅妃生里传犹在⑤”。1983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纪游诗选注》一书,由林东海、史为乐联合选注,其中录有《途次莆田》诗,郭沫若的原注是:“唐玄宗初宠梅妃,莆田江东村人,村中有浦口宫纪念之,今尚存①”。由此可见,郭沫若确认这个史实。郭沫若早年对梅花已偏爱,1920年3月30日咏《梅花树下的醉歌(游日本太宰府)》。太宰府,在日本九州福冈市,该诗收入《女神》。
80年代,浦口宫修复,江梅妃由陪祀变为主祀。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学名正权,乳名小八。
1917—1919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学名援、爱、季爰、爰,法号大千。1927年,他开始“行万里路”的艺术历程。1949年9月,张大千离川去海外。1953年后移居巴西。1956年7月28日,大千夫妇与毕加索相见,互相赠画。这是中西画坛两巨子的高峰会晤。1958年,大千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并授予金质奖章。
1972年,张大千夫妇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环筚庵,其名取自《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典故,含有创业维艰之意。他同侯北人经常切磋画艺,“环筚庵种梅百本,颇有非议者,百本栽梅亦知嗟,看花坠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颇无耻,不认梅花是国花”。于是,大千于“上元后二日,写艺新衡吾兄环筚厂添种垂枝梅”,诗曰:
万里从君乞一株,柔枝瘦影正须扶。
濛濛月色开生面,得似江妃对镜无。
大千还有首《题红梅图》:
十年流荡海西涯,结个茅堂不似家。
不是不归归自好,只愁移不得梅花。
大千思乡情切,1976年移居台北。他的画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展,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是中国的“文化大使①”。
张大千对莆田亦有印象。193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涵江发生大火灾,延烧200多户、损失数十万金。原莆田县长黄缃组织“涵江火灾善后委员会”,请省里长官林森、萨镇冰、杨树庄发动全国名流捐赠书画作品,一年来征集到1000多人5000件,其中有张大千的作品。作品的一部分展览义卖后,据以重建涵江。
至于其他诗人所咏,那就更多了。例如莆田裔马来西亚的华侨陈少白《访莆田江东梅妃故里》、莆田学院副教授刘福铸《和乡侨陈少白〈梅妃故里〉》、《莆田县志》副主编李光岱《浦口宫集句》三首之三、《湄洲日报》专刊部主任林金松《忆江南·梅妃》等。
美籍江西九江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蒋彝(1905—1977)撰《香港竹枝词》,五十首之四十六有句:“而今人造珠充斥,梅妃不必苦吟哦”。科技的发展,使当代人对梅妃故事有了新的感触②。
附注
①载《全宋诗》卷1211。
①《枕》诗之十。
②《谢圆机梅子》。
③《圆机用墨淡甚辄以上色三丸为好》。
④《方上人处见圆机五字辄用其韵作》。
⑤司马光《和君贶宴张氏梅台》。
①邵雍《同诸友城南张园赏梅十首》:“台边况有数十株,仍在名园最深处”。“梅花四种或红黄,颜色不同香颇同”。
②《宋会要》礼·五七之28—31。
③《容斋五笔》卷一《天庆诸节》。
①程杰《江梅妃研究·序》。
①载《全宋词》1797页。
②载《全宋词》240页。
①载《全宋词》2256页。
①载《刘克庄年谱》。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四·任宫观》。
①《新唐书·南蛮传中·赞》。
②载《兴化文痕》。
①载《黄御史集》。
②据许更生《徐寅生卒考辨》,载《湄州日报》2003年3月24日。
①均载《全宋诗》58册。
①载《莆田文史资料》第6辑。
①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113页则考证为:开元二十六年十月,杨玉环才入侍。
②载《元诗选》二集下册。
③载宋代曾季狸《艇斋诗话》。
①载《元诗选》二集下册。
①载《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
②载《类博稿》卷二。
①载《历代题画诗类》卷四十三。
②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289页。
③单国强在《美术报》书画鉴定研修班的讲课。
①载《明清花鸟画题画诗选注》79页。
②载《笔精》卷五。
③载《徐文长三集》卷十二·词。
④载《明曲三百首》236页。
① 载《赖古堂集》卷十一。
② 《静志居诗话》。
③ 见王士禛《渔洋诗话》。
①载《清名家词》。
②均载《迦陵词全集》。
③引自清代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
①载《香祖笔记》卷十二。
②载《渔洋精华录集注》577页。
③载《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
④载《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
⑤载清代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
①载嘉庆时,海宁吴骞《拜经楼诗话》卷四。
②载道光林扬祖《莆田县志稿》古迹卷。
③载《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
①载《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八。
②同上,诗集卷二十六。
③载《瓯北集》卷三十一。
④载《历代名家咏花词全集》。
①载《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
②载《剖瓠存稿》卷九、卷十、卷十三、卷十七、卷十八与《莆阳乐府》。
①载《日本汉诗撷英》。
②载《国朝闺阁诗钞》。
③载《湘雅摭残》841页。
④载《吉雨山房遗集》卷五。
⑤载《柘耕诗文集》卷三。
⑥载《竹素园诗钞》卷一。
①载《柘耕诗文集》卷五。
②载《柘耕诗文集》卷六。
③载《香艳丛书》一集一卷。
④《全唐诗》卷一百六十。
①木斋《宋诗流变》61—63页。
②载《丘逢甲集》柏庄诗草。
③载《丘逢甲集》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十一。
①朱维干《莆田县简志》二十章·镇前。
①载《兼于阁诗话》,陈声聪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载《弗堂词》卷一。
①载《八州诗草》卷五。
②载《披晞集》卷七。
①载《枯烂集》。
②载《壮悔余集》。
③载《台湾时报》1922年5月号。
④载《林小眉三草·天池草》。
⑤载台湾《风月报》1939年2月1日。
⑥载《诗报》1940年3月1日。
⑦载《诗报》1940年6月27日。
①载《诗报》1941年5月19日。
②载台湾《风月报》1939年7月号上卷。
③载《诗报》1942年7月24日。
④载《诗报》1940年5月8日。
⑤载《莆田县志》彩照。
①林青松《郭沫若确认唐朝莆田有江梅妃》,载《莆田侨乡时报》2005年7月1日。
①《郑板桥与张大千画传》、《历代梅花写意画风》。
②载《蒋彝诗集》。
相关人物
江梅妃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