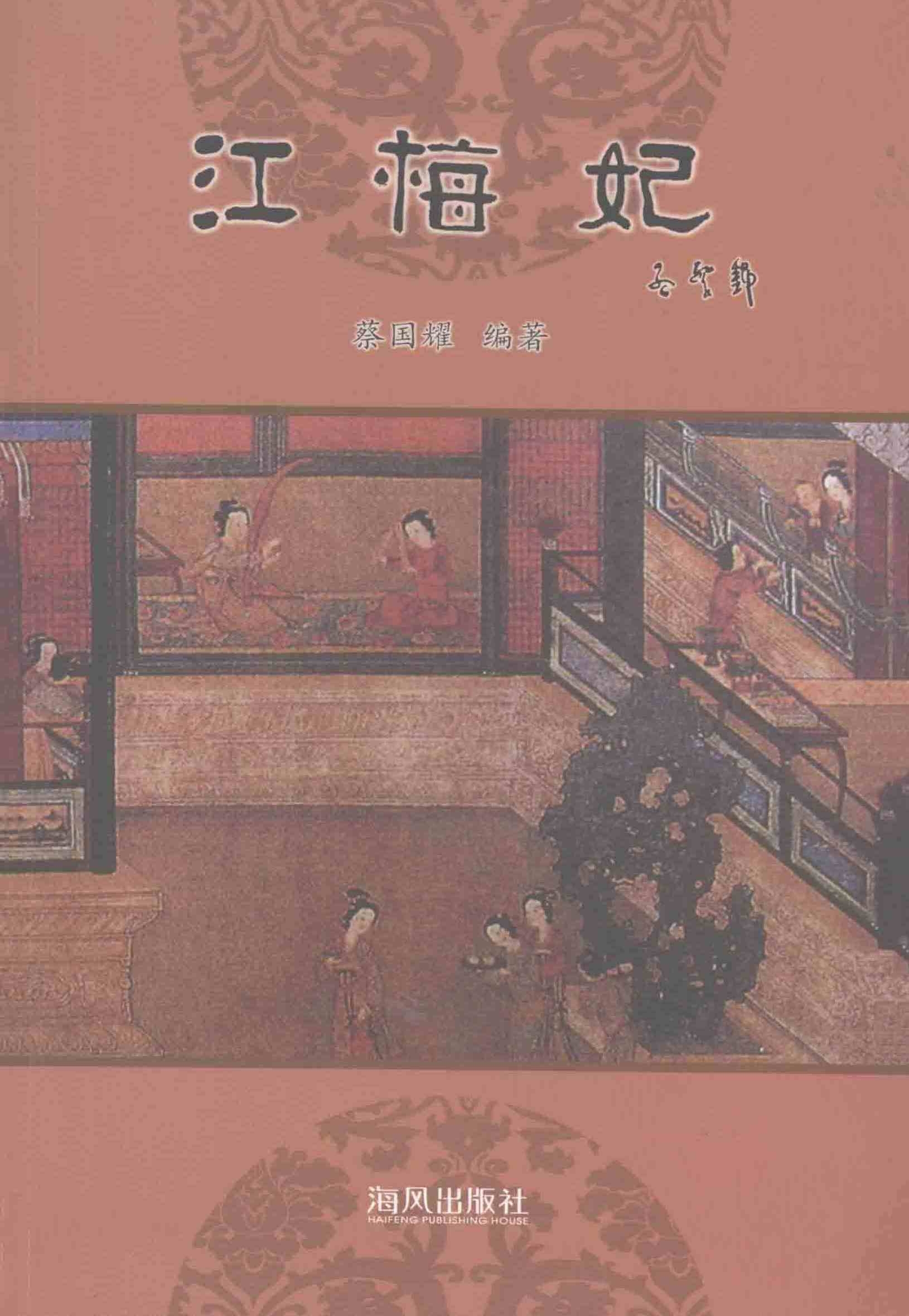内容
福建莆田蔡国耀先生寄来《江梅妃研究》书稿三大册,嘱为写一序言。古人所谓为人作序,或门生故吏,心所怀感,称道德业;或朋友姻旧,揄扬其美。或求重言,取信于人;或求能文,为之延誉。我于蔡先生非亲非故,至今尚未谋面,而自度学识浅陋,言无以增重,才藻更悭,文不足益美,实不当其选。谅蔡先生之付我,大概是因我写过几篇梅花方面的论文,其中也偶涉梅妃问题。记得两年前,蔡先生来信征取我的《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一书,顺便询问对梅妃问题的看法。我即回信表示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怀疑和对这一传奇故事的关注,并提醒他注意历史与小说要区别对待。此中有两个基本问题迄今无法解决:一是历史上是否真有梅妃其人;二是《梅妃传》的作者及其时代。我对此谈不上研究,现在想来,当时的回答还是比较草率的。捧读蔡先生新作,颇受激发,于是集中精力检阅有关资料,不意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不妨趁此机会聊为一谈。
首先是梅妃其人:
梅妃不见于各种正史著述,唐人小说若《明皇杂录》、《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等载明皇朝事者,也未提及。相关事迹都出于旧题唐曹邺所撰《梅妃传》,而《梅妃传》内容情节与历史事实多相抵牾,显系对唐史不甚了了者之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大多对梅妃其人持怀疑态度,甚至有学者断言是“‘无’中生有”。但自古后宫三千,见于史乘者又有几个? 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梅妃其人虽属宫闱秘事,正史不载,但在其故里或其他关系密切地却不乏知情者,所知所闻也倍受珍视,凤爪片羽得以耳拾绵传于世。进而野史稗官,逐步在文人层面浮现出来。至少我们看到,北宋后期有两篇诗文作品言及梅妃。
一是李纲《梅花赋》:“若夫含芳雪径,擢秀烟村,亚竹篱而绚彩,映柴扉而断魂。暗香浮动,虽远犹闻,正如梅仙隐居吴门。丰肌莹白,娇额涂黄,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吸风饮露,绰约婵娟,肌肤冰雪,秀色可怜,姑射神人御气登仙;绛襦素裳,步摇之冠,璀璨的皪,光彩烨然,瑶台玉姬谪堕人间。”此赋作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 冬。作者排比四个人物形象来比拟梅花之高雅幽洁:梅福、梅妃、姑射神人、瑶台玉妃。从文理上说,两个一组,后两人分别出自《庄子》与苏轼《松风亭》梅花诗,都是虚构之形象。前两人即梅福与梅妃为一组,应同属历史人物。
二是晁说之《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其五:“莫道梅花取次开,馨香须待百层台。不同碧玉小家女,宝策皇妃元姓梅。”此诗作于宣和四年(1022) 春知成州(今甘肃成县)时。诗中以梅妃比拟梅花之高贵,但并未点明这一皇妃究属何朝何帝。晁说之作诗好自作注,纪本事,注典故,或阐发立意。这组绝句前后同题同韵叠和共二十二首,其中有十处出注。这一首“百层台”下即注云:“今洛中名园犹竞于梅台,贵自上接其香。”但末句所说梅妃未注,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至少不太冷僻的故事。整组诗二十二首,多用汉唐长安宫廷典故,这里所说梅妃也应属唐室之事。
这两条材料透露的梅妃形象与现存《梅妃传》中所写有明显出入:一、《梅妃传》中梅妃是其别号,本人姓江,而晁说之所说梅妃姓梅。二、《梅妃传》中梅妃“自比谢女,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又訾杨玉环为“肥婢”,可见其自身体态气质是属于清秀瘦条型的。而李纲笔下的梅妃“丰肌莹白,娇额涂黄”,“娇困无力,嫣然欲狂”云云,与杜甫《丽人行》所说“肌理细腻骨肉匀”,白居易《长恨歌》所说“侍儿扶起娇无力”之杨贵妃等人丰腴形象几无二致。可见有关说法并不同源,至少应该有两个“版本”。今本《梅妃传》跋文也透露了另外的信息:“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也就是说在今传《梅妃传》写定之前,已有梅妃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先,有关梅妃的传说应该由来已久。当然这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纲、晁说之所本也只是“图画美人把梅者”一类泛指,引为诗赋比喻形象,并无确切的文字来源与史实根据。但即便这一假设成立,也不影响梅妃传说由来已久这一事实。
所幸另有材料可资参证。陶珽重辑百二十卷本《说郛》卷七十七下张泌《妆楼记》:“除夕,梅妃与宫人戏镕黄金散,泻入水中,视巧拙,以卜来年否泰。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首、尾、足、翅,无不悉备。”此事不见于今本《梅妃传》,所写与宫娥、侍宦之流熔金问卜之戏乐、喜获全凤吉兆之情状也与《梅妃传》中诸王调嬉、列妃争宠大异其趣,显然与《梅妃传》之本事了不相关。此前曾有学者提到这条材料,但并未引起重视,大概是碍于《说郛》辑书署名多有可疑,而元明以来小说丛编所收志怪、传奇作品托名张泌者也不少见。笔者就电子版两宋时期文献反复搜检,觉得《妆楼记》这一材料对梅妃真伪问题不乏参考价值。
首先,从《说郛》辑抄《妆楼记》七十余条可见,该书掇集闺阁脂粉类轶闻琐事,较少鬼怪灵异色彩,材料多取自正史、杂纂、碑刻、诗语等,内容以汉、唐为主,所收事类时间可稽者止于中唐。虽然梅妃此事来源未明,同时也未交代属于何朝何帝,但时间也应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内。
其次是《妆楼记》的成书时间。宛委山房百二十卷本《说郛》所载《妆楼记》内容,北宋孔传《续六帖》、南宋孝宗朝《锦绣万花谷》等类书已见引用,更早的《云仙散录》也掇录其四条。《云仙散录》,旧题后唐冯贽编,编者自序署后唐天成元年(926),则《妆楼记》当成于此前。惟《云仙散录》一书可靠性向多疑问,如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即指为南北宋之交王铚所伪。有关问题较为复杂,详情请见中华书局1998年版《云仙散录》整理者张力伟所撰《前言》。张氏认为前人的种种怀疑“未必能站得住脚”,“不能作为推翻本书为五代时人冯贽所作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云仙散录》所载姓名、年代可考者均为宋以前故实、传说,因此笔者同意这一判断。即或如宋人所疑,《云仙散录》为南北宋之交王铚所伪,《妆楼记》也当成于北宋中期之前。若《妆楼记》所题编者张泌属实,当为晚唐人。历史上张泌同名同姓者当不在少数,所知晚唐五代至北宋至少有三位。一是南唐张泌(一作佖),字子澄,常州(一作淮南)人,事后主任内史舍人,归宋官虞部郎中。二是宋初真、仁朝张泌,浦城人,字顺之,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此二人立朝清正,生活俭朴,尤其是浦城张泌于仁宗朝知谏院,奏乞减后宫浮费,而《妆楼记》以编掇宫闺奢华之事为意,与二人品节、行实殊不相类。另一是《花间集》所载张泌,生卒、籍贯无考,编列于牛峤(848? —?)、毛文锡(872? —917)之间,年辈应介于其中,仕历也应与牛、毛二氏相若,由唐入蜀,在唐都长安、蜀都成都两地居住过。《花间集》称其“舍人”,当为前蜀开国时授职。冯贽所采《妆楼记》或即其所作,时间正在冯氏《云仙散录》之前。
综上两点,可见梅妃之事至迟在晚唐已见于著述。这与今本《梅妃传》跋文所记“大中二年”写本,正为同时。由于这一唐人摘编材料的佐证,鄙意以为唐室必有一梅妃,只是今本《梅妃传》之外,无法证明其事必属明皇朝。有关记载出于稗官野史,具体情节容可怀疑,但决不能遽断其人子虚乌有,认其为宋人杜撰。
第二个问题是《梅妃传》的作者与时代:
《梅妃传》旧题唐曹邺撰,颇多可疑。今本《梅妃传》全文最早见于《说郛》,北京图书馆藏涵芬楼明钞本《说郛》不题撰人①,明中叶正德、嘉靖间所刻《顾氏文房小说》本也不署撰者,而北图藏钮氏世学楼明抄本、明末清初陶氏重辑百二十卷本《说郛》题作唐曹邺撰,孰是孰非,殊难分解。无奈之下,只能退归传本寻求内证。其实细加玩味,今本《梅妃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今本《梅妃传》后有无名氏跋文: “汉兴尊春秋,诸儒持《公》、《谷》角胜负,《左传》独隐而不宣,最后乃出,盖古书历久始传者极众。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盖明皇失邦,咎归杨氏,故词人喜传之,梅妃特嫔御擅美,显晦不同,理应尔也。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②七月所书,字亦端好。其言时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说,略加修润,而曲循旧语,惧没其实也。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又记其所从来如此。”首先必须辩明的是,《梅妃传》正本自有传赞,这一段文字书于传赞之后,不属正本范围,而是独立、完整的跋尾。有学者认为这一跋文是《梅妃传》作者之饰辞,跋文的作者正是《传》文的作者。这一理解欠妥,首先,如果作者传赞之后再缀语虚饰,无异于画蛇添足,与唐宋时此类传体小说写作惯例不合。其次,跋文中直接指涉叶梦得。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文人,从后面的论证可知,今本《梅妃传》至迟也应写定于绍兴十八、九年间,叶梦得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去世,晚年的叶梦得历镇大藩、声名显赫。即或作者跋中托言虚张,理应不会拉此当世名人说事。因此,我认为跋文的内容应是真实可信的。该跋语也是迄今所见有关《梅妃传》写作情况的唯一材料,理应作为我们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和首要依据。
跋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一、《梅妃传》有一唐大中年间①写本。二、《梅妃传》长期湮没。三、唐写本为南唐藏书家朱遵度家所传。四、唐写本由跋文作者与叶梦得(字少蕴)得之;五、今本《梅妃传》非唐本原貌,而是经过跋文作者润饰过的新本。除了这些一目了然的认识外,关于《梅妃传》作者,该跋也有所启发:一、跋文于唐写本藏家、续得者乃至于书写时间及字迹等都交代荦荦,而于作者这样关键的问题却只字未提,显然不合常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其所见唐写本未署撰者。南宋末年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二编述梅妃故事,尾注:“此传叶石林得之朱遵度家,乃唐大中二年七月所著云。”此与今本《梅妃传》所言一致,也未提撰者,或即出于今本跋文。该书所述除出于方志和通行史著外,单篇文章多注明撰者与篇名,谅其所见《梅妃传》也不署撰者。二、跋文称唐写本“时有涉俗”,而要“略加修润”。曹邺是大中四年进士,《唐才子传》称其“雅道甚古”,诗才姣然,有传世作品为证,想必所作不致受此菲薄。若唐写本署明曹邺所撰,宋人也不会轻下雌黄。即便是经过润色的今本《梅妃传》,人们仍发现存在象梅妃从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大内夜中竟能步归上阳宫(在今河南洛阳)这样大的常识性漏洞,诗人曹邺更不会如此疏谬。尝见有学者举曹邺《五情》、《恃宠》等诗咏陈阿娇、赵飞燕之语,认为“其撰《梅妃传》,题材既同,命意亦似,哀梅复悯己也”。但详检今存曹邺诗作,了无梅妃之事的蛛丝马迹,仅凭题材相类远不足为证。因此我认为,事实应该如《梅妃传》跋文所说,《梅妃传》有一唐写本,撰者不明,语辞凡俗,经跋文作者略加润色,而成今本面貌。
明确此点,再来说今本作者及写定时间。关于今本《梅妃传》的写定者或跋文作者,有一点是公认的,此人与叶梦得同时,甚或相识乃至交往密切。另有学者指出:“《梅妃传》篇首记梅妃籍贯,径书‘莆田人’,而不云‘闽之莆田人’,莆田小邑,以中国之大,外方人未必一望而即知其地,其在闽人,固无须注明。”“《梅妃传》的作者是南宋初年一位闽籍或虽非闽籍而关心闽事的文士”。笔者对此推理深表赞同,只是所说“《梅妃传》的作者”应理解为今本修订者或跋文作者。今本《梅妃传》中,所写斗茶之事特具闽瓯地方色彩,也资佐证。
关于定稿时间。有学者根据宣和三年李纲《梅花赋》中已提到梅妃,认为《梅妃传》当成于宣和二年之前,此说不妥。前述已言,李纲笔下梅妃与《梅妃传》所写形象迥异,所本不同,更不待言孰先孰后。问题还得从跋文所提两位人物着手。一是朱遵度。郑文宝《江表志》卷二:“朱遵度,本青州书生,好藏书,高尚不仕,闲居金陵,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经》数卷,皆行于世。”朱遵度以藏书之富、博学强记闻名于时,人称“万卷”、“书厨”。马永易《实宾录》卷五称其当五代乱世,“挈其妻孥,携书杂商贾”南下投奔楚王马殷,待之甚薄,遂举家迁南唐金陵(今江苏南京),隐居不仕。其后裔不显,当世守江宁,无力播迁。另一是叶梦得。叶氏绍圣四年(1097)及第,北宋时任丹徒(今属江苏镇江)尉、婺州(今浙江金华)教授,入京试院检点试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因涉党争,外放辗转知汝州(今河南临汝)、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杭州(今属浙江)等,间也奉祠居楚州(今江苏淮安)、苏州(今属江苏)、湖州(今属浙江)。南渡后召至行在,复翰林学士,迁尚书左丞,奔走于扬州前线与杭州间,积极支应、扶持时局。绍兴元年(1131)九月任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治所驻今江苏南京),次年三月罢归湖州园墅。绍兴八年(1138)五月再起前任,绍兴十二年(1142)底移知福州(今属福建),绍兴十四年底落职奉祠归休湖州,直至去世。纵观叶梦得一生仕履行止荦荦清晰,其中绍兴间两任建康,前后累计五年。其唐写本《梅妃传》“得自朱遵度家”事,最有可能发生此间。宋高宗建炎间(1127—1140)建康迭遭兵火,始有南宋驻军军校周德之乱,继而金人攻陷入据,兵马蹂躏,生民涂炭,破坏惨重。叶梦得《紬书阁记》自叙绍兴元年初帅建康时,“营理学校,延集诸生,得军赋余缗六百万以授学官,使刊六经”。绍兴八年再至,“公厨适有羡钱二百万,不敢他费,乃用遍售经史诸书,凡得若干卷”,“为之藏而著其籍于有司”。周煇《清波杂志》卷三也载:“建康六朝故都,叶石林少蕴居留日,尝命诸邑官能文者搜访古迹,制图经。”可见建康任上,叶梦得重视当地文教复兴之事,于大兵乱后营建府衙学舍,收购文物遗籍。而金陵朱氏后裔,居此乱世危城,当是家业难守,庋藏离析流失。唐写本《梅妃传》或在其中,幸为叶梦得与跋文作者所得。叶梦得初任建康,为时不足半年,来去匆匆,未及经营。再任四年,治迹显明,文教方面经度尤为从容。揣度情形,其获朱遵度家旧藏,应在后一任期内。继而移知福州,或随携入闽,闽士得睹此本,为之润饰行世。因此笔者认为,今本《梅妃传》写定时间当在叶梦得移守福州的绍兴十三年(1143) 之后。
至于其时间下限,可以由叶梦得同时叶廷珪所编《海录碎事》一书推证。该书采录今本《梅妃传》五条,四条摘有文字,另一复出。《四库全书》本《海录碎事》卷十下:“梅妃:梅妃姓江氏,名采蘋,高力士使闽粤,选归侍明皇。性喜梅,所居植梅,上榜曰梅亭。梅开,赋赏花下,夜分不去,以其好,戏名曰梅妃。”卷十六:“《一斛珠》:会夷使至,封珍珠一斛赐妃。妃不受,以诗报上,上怅然,命乐府度新声,号《一斛珠》。”卷十九:“八赋:梅妃有《萧》、《兰》、《梨园》、《梅花》、《凤笛》、《玻璃杯》、《剪刀》、《绮窗》八赋。”“《东楼赋》:梅妃为太真忌,迁于上阳宫,以千金祷高力士,求人拟长门赋。力士畏太真势,不果,乃作《东楼赋》。有‘嫉色慵慵,妬色忡忡,夺我之爱去,斥我乎幽宫’之语。”不难看出,这四段文字都是今本《梅妃传》相应内容的简单节抄或檃括,唯“《东楼赋》”条,今本《梅妃传》作《楼东赋》,《海录碎事》卷十下先出此条作“《东楼赋》”,可见以“《东楼赋》”为是。《海录碎事》编者叶廷珪①,福建瓯宁(今福建建瓯)人,生卒不详,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绍兴十八年(1148)秋知泉州,移知漳州。其《海录碎事》自序署时“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序称知泉州日,公余得闲,取游宦四十年间读书杂抄可用碎事分门别类编成是书。书末又有漳州通判傅自得绍兴十九年十一月所撰后序。可见是书编定于绍兴十八、九年间,而今本《梅妃传》则应成于此前,至迟也不能晚于绍兴十九年五月。
综上可知,今本《梅妃传》写定时间当在叶梦得移任福州的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八年的五、六年间(1143—1148),或第二次任职建康以来的十年间(1138—1148),从宽考虑,也只在叶梦得绍兴元年初帅建康以来的十八年间,而定稿者当是叶廷珪之类与叶梦得年龄相若之闽籍人士。
这是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最新认识,与蔡先生书中观点大同小异。由于相关材料极其有限,所谓小异处更多的也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撑,因此很难自信必是,只是提出来作为阅读蔡先生这部著作的一种参考。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课题,进一步开展讨论。
梅妃之事史逸其说,茫昧难辨,但由《梅妃传》演绎派生之故事传说、戏文小说却构成了一道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风景线。蔡先生是著着力于对此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历述和分析,披览全稿,不难看出蔡先生的工作有这样几个特色:
一是展开充分。全稿就小说笔记、戏曲、史志、诗文几方面梅妃之事自古至今的演进情况分别进行纵向梳理,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各方面的发展线索和具体成就。
二是资料翔实。作者广泛搜罗有关资料,囊括了古今中外各个方面,凡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和时贤论述靡不毕采。整个论述几乎构成了一个资料长编,集中了这一课题最为丰富的资料信息。
三是论述细致。蔡先生对所见材料都认真排比,细加分析,同时参合诸说,融发己见,因而无论细节还是全局,都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评议与总结,极富启发意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蔡先生长期从事莆田地方志工作,莆田正是梅妃的故乡,想其对这一古史轶事研究之如此投入其来有自,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其对故里旧事的浓厚兴趣和对乡邦文化的深切责任,细细读来也不难发现,书中也以对相关地方文献记载和传说遗迹的考述、阐发最为具切,最富价值。
最后想特别强调的是,就我所见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梅妃问题专题研究的学术专著,是这一课题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2006年4月14日
注:该序先摘发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此后收录于《梅文化论丛》一书,程杰著,中华书局2007年5月出版。
首先是梅妃其人:
梅妃不见于各种正史著述,唐人小说若《明皇杂录》、《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等载明皇朝事者,也未提及。相关事迹都出于旧题唐曹邺所撰《梅妃传》,而《梅妃传》内容情节与历史事实多相抵牾,显系对唐史不甚了了者之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大多对梅妃其人持怀疑态度,甚至有学者断言是“‘无’中生有”。但自古后宫三千,见于史乘者又有几个? 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梅妃其人虽属宫闱秘事,正史不载,但在其故里或其他关系密切地却不乏知情者,所知所闻也倍受珍视,凤爪片羽得以耳拾绵传于世。进而野史稗官,逐步在文人层面浮现出来。至少我们看到,北宋后期有两篇诗文作品言及梅妃。
一是李纲《梅花赋》:“若夫含芳雪径,擢秀烟村,亚竹篱而绚彩,映柴扉而断魂。暗香浮动,虽远犹闻,正如梅仙隐居吴门。丰肌莹白,娇额涂黄,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吸风饮露,绰约婵娟,肌肤冰雪,秀色可怜,姑射神人御气登仙;绛襦素裳,步摇之冠,璀璨的皪,光彩烨然,瑶台玉姬谪堕人间。”此赋作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 冬。作者排比四个人物形象来比拟梅花之高雅幽洁:梅福、梅妃、姑射神人、瑶台玉妃。从文理上说,两个一组,后两人分别出自《庄子》与苏轼《松风亭》梅花诗,都是虚构之形象。前两人即梅福与梅妃为一组,应同属历史人物。
二是晁说之《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其五:“莫道梅花取次开,馨香须待百层台。不同碧玉小家女,宝策皇妃元姓梅。”此诗作于宣和四年(1022) 春知成州(今甘肃成县)时。诗中以梅妃比拟梅花之高贵,但并未点明这一皇妃究属何朝何帝。晁说之作诗好自作注,纪本事,注典故,或阐发立意。这组绝句前后同题同韵叠和共二十二首,其中有十处出注。这一首“百层台”下即注云:“今洛中名园犹竞于梅台,贵自上接其香。”但末句所说梅妃未注,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至少不太冷僻的故事。整组诗二十二首,多用汉唐长安宫廷典故,这里所说梅妃也应属唐室之事。
这两条材料透露的梅妃形象与现存《梅妃传》中所写有明显出入:一、《梅妃传》中梅妃是其别号,本人姓江,而晁说之所说梅妃姓梅。二、《梅妃传》中梅妃“自比谢女,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又訾杨玉环为“肥婢”,可见其自身体态气质是属于清秀瘦条型的。而李纲笔下的梅妃“丰肌莹白,娇额涂黄”,“娇困无力,嫣然欲狂”云云,与杜甫《丽人行》所说“肌理细腻骨肉匀”,白居易《长恨歌》所说“侍儿扶起娇无力”之杨贵妃等人丰腴形象几无二致。可见有关说法并不同源,至少应该有两个“版本”。今本《梅妃传》跋文也透露了另外的信息:“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也就是说在今传《梅妃传》写定之前,已有梅妃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先,有关梅妃的传说应该由来已久。当然这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纲、晁说之所本也只是“图画美人把梅者”一类泛指,引为诗赋比喻形象,并无确切的文字来源与史实根据。但即便这一假设成立,也不影响梅妃传说由来已久这一事实。
所幸另有材料可资参证。陶珽重辑百二十卷本《说郛》卷七十七下张泌《妆楼记》:“除夕,梅妃与宫人戏镕黄金散,泻入水中,视巧拙,以卜来年否泰。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首、尾、足、翅,无不悉备。”此事不见于今本《梅妃传》,所写与宫娥、侍宦之流熔金问卜之戏乐、喜获全凤吉兆之情状也与《梅妃传》中诸王调嬉、列妃争宠大异其趣,显然与《梅妃传》之本事了不相关。此前曾有学者提到这条材料,但并未引起重视,大概是碍于《说郛》辑书署名多有可疑,而元明以来小说丛编所收志怪、传奇作品托名张泌者也不少见。笔者就电子版两宋时期文献反复搜检,觉得《妆楼记》这一材料对梅妃真伪问题不乏参考价值。
首先,从《说郛》辑抄《妆楼记》七十余条可见,该书掇集闺阁脂粉类轶闻琐事,较少鬼怪灵异色彩,材料多取自正史、杂纂、碑刻、诗语等,内容以汉、唐为主,所收事类时间可稽者止于中唐。虽然梅妃此事来源未明,同时也未交代属于何朝何帝,但时间也应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内。
其次是《妆楼记》的成书时间。宛委山房百二十卷本《说郛》所载《妆楼记》内容,北宋孔传《续六帖》、南宋孝宗朝《锦绣万花谷》等类书已见引用,更早的《云仙散录》也掇录其四条。《云仙散录》,旧题后唐冯贽编,编者自序署后唐天成元年(926),则《妆楼记》当成于此前。惟《云仙散录》一书可靠性向多疑问,如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即指为南北宋之交王铚所伪。有关问题较为复杂,详情请见中华书局1998年版《云仙散录》整理者张力伟所撰《前言》。张氏认为前人的种种怀疑“未必能站得住脚”,“不能作为推翻本书为五代时人冯贽所作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云仙散录》所载姓名、年代可考者均为宋以前故实、传说,因此笔者同意这一判断。即或如宋人所疑,《云仙散录》为南北宋之交王铚所伪,《妆楼记》也当成于北宋中期之前。若《妆楼记》所题编者张泌属实,当为晚唐人。历史上张泌同名同姓者当不在少数,所知晚唐五代至北宋至少有三位。一是南唐张泌(一作佖),字子澄,常州(一作淮南)人,事后主任内史舍人,归宋官虞部郎中。二是宋初真、仁朝张泌,浦城人,字顺之,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此二人立朝清正,生活俭朴,尤其是浦城张泌于仁宗朝知谏院,奏乞减后宫浮费,而《妆楼记》以编掇宫闺奢华之事为意,与二人品节、行实殊不相类。另一是《花间集》所载张泌,生卒、籍贯无考,编列于牛峤(848? —?)、毛文锡(872? —917)之间,年辈应介于其中,仕历也应与牛、毛二氏相若,由唐入蜀,在唐都长安、蜀都成都两地居住过。《花间集》称其“舍人”,当为前蜀开国时授职。冯贽所采《妆楼记》或即其所作,时间正在冯氏《云仙散录》之前。
综上两点,可见梅妃之事至迟在晚唐已见于著述。这与今本《梅妃传》跋文所记“大中二年”写本,正为同时。由于这一唐人摘编材料的佐证,鄙意以为唐室必有一梅妃,只是今本《梅妃传》之外,无法证明其事必属明皇朝。有关记载出于稗官野史,具体情节容可怀疑,但决不能遽断其人子虚乌有,认其为宋人杜撰。
第二个问题是《梅妃传》的作者与时代:
《梅妃传》旧题唐曹邺撰,颇多可疑。今本《梅妃传》全文最早见于《说郛》,北京图书馆藏涵芬楼明钞本《说郛》不题撰人①,明中叶正德、嘉靖间所刻《顾氏文房小说》本也不署撰者,而北图藏钮氏世学楼明抄本、明末清初陶氏重辑百二十卷本《说郛》题作唐曹邺撰,孰是孰非,殊难分解。无奈之下,只能退归传本寻求内证。其实细加玩味,今本《梅妃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今本《梅妃传》后有无名氏跋文: “汉兴尊春秋,诸儒持《公》、《谷》角胜负,《左传》独隐而不宣,最后乃出,盖古书历久始传者极众。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盖明皇失邦,咎归杨氏,故词人喜传之,梅妃特嫔御擅美,显晦不同,理应尔也。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②七月所书,字亦端好。其言时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说,略加修润,而曲循旧语,惧没其实也。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又记其所从来如此。”首先必须辩明的是,《梅妃传》正本自有传赞,这一段文字书于传赞之后,不属正本范围,而是独立、完整的跋尾。有学者认为这一跋文是《梅妃传》作者之饰辞,跋文的作者正是《传》文的作者。这一理解欠妥,首先,如果作者传赞之后再缀语虚饰,无异于画蛇添足,与唐宋时此类传体小说写作惯例不合。其次,跋文中直接指涉叶梦得。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文人,从后面的论证可知,今本《梅妃传》至迟也应写定于绍兴十八、九年间,叶梦得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去世,晚年的叶梦得历镇大藩、声名显赫。即或作者跋中托言虚张,理应不会拉此当世名人说事。因此,我认为跋文的内容应是真实可信的。该跋语也是迄今所见有关《梅妃传》写作情况的唯一材料,理应作为我们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和首要依据。
跋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一、《梅妃传》有一唐大中年间①写本。二、《梅妃传》长期湮没。三、唐写本为南唐藏书家朱遵度家所传。四、唐写本由跋文作者与叶梦得(字少蕴)得之;五、今本《梅妃传》非唐本原貌,而是经过跋文作者润饰过的新本。除了这些一目了然的认识外,关于《梅妃传》作者,该跋也有所启发:一、跋文于唐写本藏家、续得者乃至于书写时间及字迹等都交代荦荦,而于作者这样关键的问题却只字未提,显然不合常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其所见唐写本未署撰者。南宋末年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二编述梅妃故事,尾注:“此传叶石林得之朱遵度家,乃唐大中二年七月所著云。”此与今本《梅妃传》所言一致,也未提撰者,或即出于今本跋文。该书所述除出于方志和通行史著外,单篇文章多注明撰者与篇名,谅其所见《梅妃传》也不署撰者。二、跋文称唐写本“时有涉俗”,而要“略加修润”。曹邺是大中四年进士,《唐才子传》称其“雅道甚古”,诗才姣然,有传世作品为证,想必所作不致受此菲薄。若唐写本署明曹邺所撰,宋人也不会轻下雌黄。即便是经过润色的今本《梅妃传》,人们仍发现存在象梅妃从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大内夜中竟能步归上阳宫(在今河南洛阳)这样大的常识性漏洞,诗人曹邺更不会如此疏谬。尝见有学者举曹邺《五情》、《恃宠》等诗咏陈阿娇、赵飞燕之语,认为“其撰《梅妃传》,题材既同,命意亦似,哀梅复悯己也”。但详检今存曹邺诗作,了无梅妃之事的蛛丝马迹,仅凭题材相类远不足为证。因此我认为,事实应该如《梅妃传》跋文所说,《梅妃传》有一唐写本,撰者不明,语辞凡俗,经跋文作者略加润色,而成今本面貌。
明确此点,再来说今本作者及写定时间。关于今本《梅妃传》的写定者或跋文作者,有一点是公认的,此人与叶梦得同时,甚或相识乃至交往密切。另有学者指出:“《梅妃传》篇首记梅妃籍贯,径书‘莆田人’,而不云‘闽之莆田人’,莆田小邑,以中国之大,外方人未必一望而即知其地,其在闽人,固无须注明。”“《梅妃传》的作者是南宋初年一位闽籍或虽非闽籍而关心闽事的文士”。笔者对此推理深表赞同,只是所说“《梅妃传》的作者”应理解为今本修订者或跋文作者。今本《梅妃传》中,所写斗茶之事特具闽瓯地方色彩,也资佐证。
关于定稿时间。有学者根据宣和三年李纲《梅花赋》中已提到梅妃,认为《梅妃传》当成于宣和二年之前,此说不妥。前述已言,李纲笔下梅妃与《梅妃传》所写形象迥异,所本不同,更不待言孰先孰后。问题还得从跋文所提两位人物着手。一是朱遵度。郑文宝《江表志》卷二:“朱遵度,本青州书生,好藏书,高尚不仕,闲居金陵,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经》数卷,皆行于世。”朱遵度以藏书之富、博学强记闻名于时,人称“万卷”、“书厨”。马永易《实宾录》卷五称其当五代乱世,“挈其妻孥,携书杂商贾”南下投奔楚王马殷,待之甚薄,遂举家迁南唐金陵(今江苏南京),隐居不仕。其后裔不显,当世守江宁,无力播迁。另一是叶梦得。叶氏绍圣四年(1097)及第,北宋时任丹徒(今属江苏镇江)尉、婺州(今浙江金华)教授,入京试院检点试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因涉党争,外放辗转知汝州(今河南临汝)、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杭州(今属浙江)等,间也奉祠居楚州(今江苏淮安)、苏州(今属江苏)、湖州(今属浙江)。南渡后召至行在,复翰林学士,迁尚书左丞,奔走于扬州前线与杭州间,积极支应、扶持时局。绍兴元年(1131)九月任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治所驻今江苏南京),次年三月罢归湖州园墅。绍兴八年(1138)五月再起前任,绍兴十二年(1142)底移知福州(今属福建),绍兴十四年底落职奉祠归休湖州,直至去世。纵观叶梦得一生仕履行止荦荦清晰,其中绍兴间两任建康,前后累计五年。其唐写本《梅妃传》“得自朱遵度家”事,最有可能发生此间。宋高宗建炎间(1127—1140)建康迭遭兵火,始有南宋驻军军校周德之乱,继而金人攻陷入据,兵马蹂躏,生民涂炭,破坏惨重。叶梦得《紬书阁记》自叙绍兴元年初帅建康时,“营理学校,延集诸生,得军赋余缗六百万以授学官,使刊六经”。绍兴八年再至,“公厨适有羡钱二百万,不敢他费,乃用遍售经史诸书,凡得若干卷”,“为之藏而著其籍于有司”。周煇《清波杂志》卷三也载:“建康六朝故都,叶石林少蕴居留日,尝命诸邑官能文者搜访古迹,制图经。”可见建康任上,叶梦得重视当地文教复兴之事,于大兵乱后营建府衙学舍,收购文物遗籍。而金陵朱氏后裔,居此乱世危城,当是家业难守,庋藏离析流失。唐写本《梅妃传》或在其中,幸为叶梦得与跋文作者所得。叶梦得初任建康,为时不足半年,来去匆匆,未及经营。再任四年,治迹显明,文教方面经度尤为从容。揣度情形,其获朱遵度家旧藏,应在后一任期内。继而移知福州,或随携入闽,闽士得睹此本,为之润饰行世。因此笔者认为,今本《梅妃传》写定时间当在叶梦得移守福州的绍兴十三年(1143) 之后。
至于其时间下限,可以由叶梦得同时叶廷珪所编《海录碎事》一书推证。该书采录今本《梅妃传》五条,四条摘有文字,另一复出。《四库全书》本《海录碎事》卷十下:“梅妃:梅妃姓江氏,名采蘋,高力士使闽粤,选归侍明皇。性喜梅,所居植梅,上榜曰梅亭。梅开,赋赏花下,夜分不去,以其好,戏名曰梅妃。”卷十六:“《一斛珠》:会夷使至,封珍珠一斛赐妃。妃不受,以诗报上,上怅然,命乐府度新声,号《一斛珠》。”卷十九:“八赋:梅妃有《萧》、《兰》、《梨园》、《梅花》、《凤笛》、《玻璃杯》、《剪刀》、《绮窗》八赋。”“《东楼赋》:梅妃为太真忌,迁于上阳宫,以千金祷高力士,求人拟长门赋。力士畏太真势,不果,乃作《东楼赋》。有‘嫉色慵慵,妬色忡忡,夺我之爱去,斥我乎幽宫’之语。”不难看出,这四段文字都是今本《梅妃传》相应内容的简单节抄或檃括,唯“《东楼赋》”条,今本《梅妃传》作《楼东赋》,《海录碎事》卷十下先出此条作“《东楼赋》”,可见以“《东楼赋》”为是。《海录碎事》编者叶廷珪①,福建瓯宁(今福建建瓯)人,生卒不详,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绍兴十八年(1148)秋知泉州,移知漳州。其《海录碎事》自序署时“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序称知泉州日,公余得闲,取游宦四十年间读书杂抄可用碎事分门别类编成是书。书末又有漳州通判傅自得绍兴十九年十一月所撰后序。可见是书编定于绍兴十八、九年间,而今本《梅妃传》则应成于此前,至迟也不能晚于绍兴十九年五月。
综上可知,今本《梅妃传》写定时间当在叶梦得移任福州的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八年的五、六年间(1143—1148),或第二次任职建康以来的十年间(1138—1148),从宽考虑,也只在叶梦得绍兴元年初帅建康以来的十八年间,而定稿者当是叶廷珪之类与叶梦得年龄相若之闽籍人士。
这是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最新认识,与蔡先生书中观点大同小异。由于相关材料极其有限,所谓小异处更多的也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撑,因此很难自信必是,只是提出来作为阅读蔡先生这部著作的一种参考。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课题,进一步开展讨论。
梅妃之事史逸其说,茫昧难辨,但由《梅妃传》演绎派生之故事传说、戏文小说却构成了一道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风景线。蔡先生是著着力于对此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历述和分析,披览全稿,不难看出蔡先生的工作有这样几个特色:
一是展开充分。全稿就小说笔记、戏曲、史志、诗文几方面梅妃之事自古至今的演进情况分别进行纵向梳理,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各方面的发展线索和具体成就。
二是资料翔实。作者广泛搜罗有关资料,囊括了古今中外各个方面,凡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和时贤论述靡不毕采。整个论述几乎构成了一个资料长编,集中了这一课题最为丰富的资料信息。
三是论述细致。蔡先生对所见材料都认真排比,细加分析,同时参合诸说,融发己见,因而无论细节还是全局,都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评议与总结,极富启发意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蔡先生长期从事莆田地方志工作,莆田正是梅妃的故乡,想其对这一古史轶事研究之如此投入其来有自,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其对故里旧事的浓厚兴趣和对乡邦文化的深切责任,细细读来也不难发现,书中也以对相关地方文献记载和传说遗迹的考述、阐发最为具切,最富价值。
最后想特别强调的是,就我所见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梅妃问题专题研究的学术专著,是这一课题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2006年4月14日
注:该序先摘发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此后收录于《梅文化论丛》一书,程杰著,中华书局2007年5月出版。
附注
① 此或即鲁迅先生所见。
② 引者案:百二十卷本作戍年。
①二年(戊辰848)、八年(甲戌854)或十二年(戊寅858)。
① 自序书作叶庭珪。
相关人物
程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