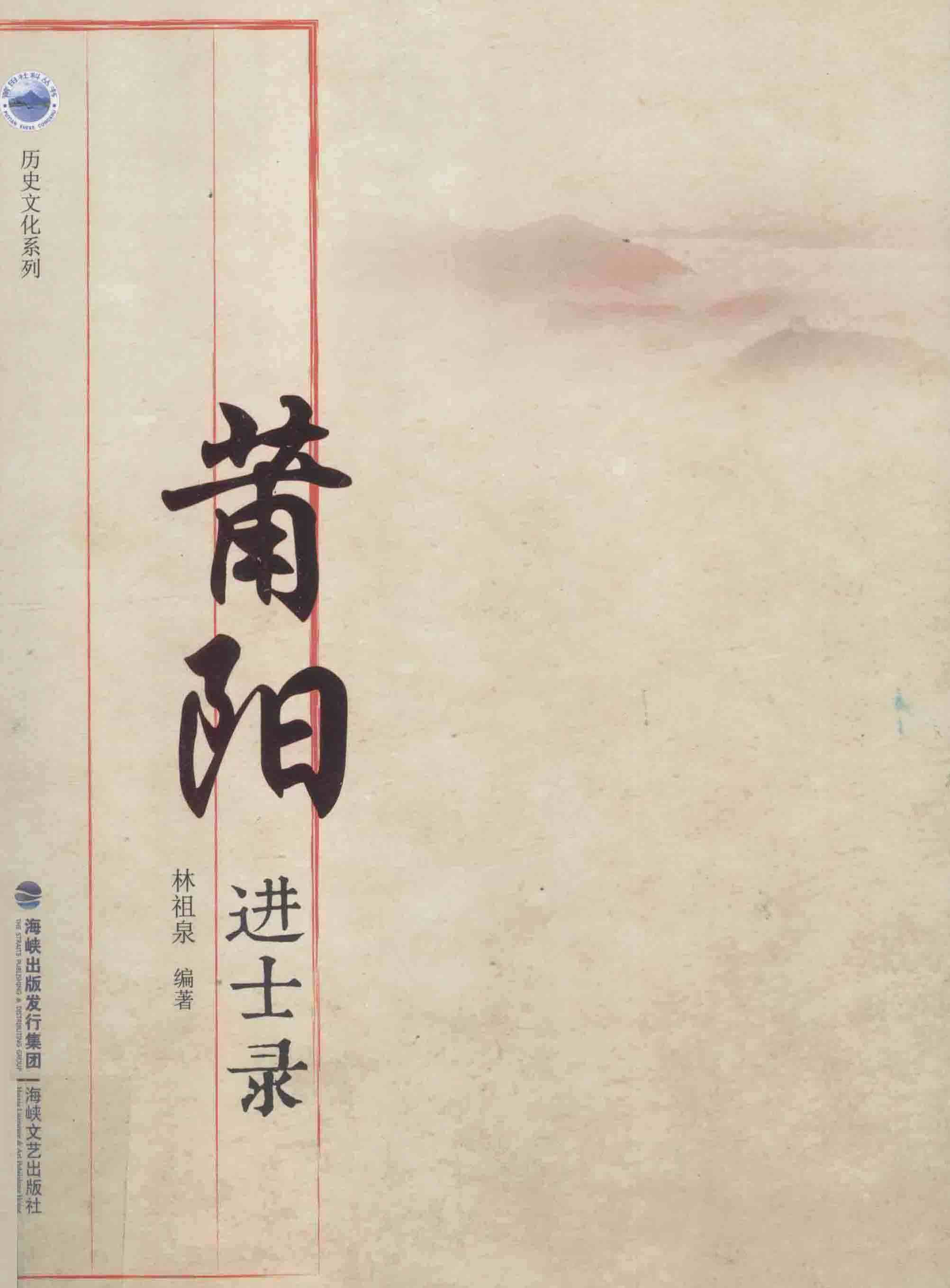内容
(三)林环殿试卷
殿试策问 明成祖朱棣
皇帝制曰:朕承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洪业,舆图之广,生齿之繁,从古莫比。故穷发之地咸为编户,雕题椎结悉化冠裳。来虽如归而治虑未浃,朕夙夜惟念,期在雍熙。然十室之邑,人人教之且有弗及,矧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夫存诚过化,不见其迹。欲臻其极,谅必有要,不明诸心,曷由达效?
唐虞三代之治,其来尚矣,而汉、唐、宋之治,犹可指而言之。自夔典乐教胄子而学校兴,而汉、唐、宋之学校有因革,其教化可得而闻?自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科目举,而汉、唐、宋之科目有异同,其名实可得而议?自小司徒经土地而田制定,而汉、唐、宋之田制有屯营,其计画可得而言?自校人掌王马之政,而马政立,而汉、唐、宋之畜牧有耗息,其详悉可得而数?之数者,有宜于古而合于今,若何施而可以几治?夫政不稽古,则无以验今,事不究迹,则无以见实。子大夫博古以知今,明体以适用。陈其当否,以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状元殿试卷 林环
臣对:臣闻出治有本,在乎先明诸心;为治有法,在乎远稽诸古。盖明诸心者,其本也;而稽诸古者,其迹也。圣人之治天下,未尝不以稽古为道,而亦曷尝不本诸心,以为出治之本乎?
钦惟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肇造洪基,抚校有可考者矣。若宋之时,有国子监、太学,有武学,有书、算学。天下已平,儒者往往依山林以讲授,当时于嵩阳、岳麓、雎阳、白鹿四书院为尤著。厥后,如胡安定教授苏湖,立经义、治事斋以教学者,此尤表表足称。则宋之学校,其颠末亦有可稽者焉。
夫学校教化之本,唐虞三代之时,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故学校之立而教化为特盛。若汉之治杂霸,唐之治杂夷,宋之治亦有未醇,躬行之实,已无其本,则学校虽立,而教化终有愧于古者,抑有由矣。
人君用人亮天之道,莫大于科目。成周之时,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岁大比,而宾兴夫贤者能者,故命乡论秀而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升之学,曰“俊士”。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大司马论辨官材以告于王,论定而后官之,任官而后爵之,以至太宰招废置而持其柄,内史赞予夺而贰于中。司士掌郡士之版,岁登记其损益之数。此科目所由举也。若汉之时,则有孝廉、孝弟、力田、贤良、明经诸科。唐之时,则由学馆进者,曰“生徒”,由州县进者,曰“乡贡”,而又有进士、开元礼、缘举、杂录、制举、孝廉、三礼、五传、一史、三史、童子、明经、明法、明算诸科。宋之时,则有诸贤良,有宏词,有童子学,漕试、推恩诸科。此汉、唐、宋科目之名,其异同固可稽矣。然成周之时,教养有法,且选任之际,循名责实。故所进之人,无非适用之士。
若汉唐而后,则养非所用,用非所养,故进用之际,不无贤否相半。是故汉之仲舒以贤良进,倪宽以明经举,似矣。而徐淑之不逃冒年,陈汤之不奔父丧,乃与科选,果何欤?唐之制科,则有裴度、韩休,而皇甫镈亦以是进。博学宏词,则有陆贽、杜黄裳,而王涯、刘禹锡亦以是进,又何欤?宋之富弼、苏轼,以制科进,杜邝公、范文正、欧阳公由进士举,是皆可取。然以丁谓之謀佞,且居要路,则又不能无可议者焉。此其名实不称,视成周得人之盛,盖不能无歉矣。
至若足民足国之良图,莫要于定田制;备兵讲武之先事,莫要于立马政。周制,小司徒均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人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故成周无不受田之家。阡陌既开,井田法废。自汉文帝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制。赵充国击先零,分兵久驻,于是有屯田之说。至唐之时,则有营田之制。至宋之兴,或屯或营,盖兼用也。大抵汉之屯田以兵,唐之营田以民,而宋之或兵或民,盖不一焉。夫其屯田以兵,斯可以免军旅坐食之费,营田以民,斯可以足国家储备之资,此其计划之善,亦有可取者矣。
至若校人掌王马之政,此马政所由立也。汉置仆牧帅诸苑,而众庶街巷有马,则不特养于官矣。暨大将军骠骑屡出,而马大耗。唐自张万岁领群牧,马至七十万六千,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至四十三万。自群牧失职,国马益耗。宋则牧马有监,掌牧有职。又或畜之于官,或养之于民,或市之于边。大抵市之于边者不可常,莫若畜之于官为有常也。专畜于官者为限,莫若兼养于民者为益广也。若是息耗之由,亦可概见矣。
皇上既举数者之目,详列于前,而又以数者之政,宜于今者总询于后。臣学不足以稽古,用不足以适今,曷足以上揆圣哀。愚昧之见,谓是数者,皆皇上酌古准今,已行之效,而拳拳以为问,特皇上谦让不自满足之心耳。夫方今学校,内自京畿,外达郡国,莫不有学,此盖太祖高皇帝参酌古制而用之者。今皇上遵而行之,迩者车驾临幸太学,俎豆生辉,衣冠增气,天下士子,知所向方,则教人之法,固可比隆唐虞三代,而陋汉、唐、宋于下风矣。方今进于学校者有科贡,选于乡里者有人材,是亦太祖高皇帝错综古典而行之者。今皇上嗣而守之。兹者临轩策问,茅茹汇征,衣冠云集,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则用人之道,亦可媲美唐虞三代,而薄汉、唐、宋于下流矣。至若田制之立,虽非尽成周之旧,马政之立,亦参用校人之政。然其屯营之必备,畜牧之必专,是亦酌古而宜于今者耳。是二者,亦太祖高皇帝已试之法,今皇上率而由之者。况于屯田则劝督之必严,于畜牧则孳息之益众,殆恐古昔盛际,亦不过是,而汉、唐、宋又乌可以同日而语哉!然臣于终篇,愿有献焉。
夫是数者,特冶之法也。其本则系之皇上之心。盖以是心而兴学校,则朱熹所谓本之躬行心得之余是也。以是心而兴贤才,则大禹所谓光天之下是也。以是心而定田制,则《大学》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是也。以是心而立马政,则《诗》所谓“秉心塞渊”与“思无邪”者是也。合而论之,则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愿皇上终始此心,斯可以终始此治矣。
臣于博古通今,明体适用,乌足以当。特以上之问,适有以发臣愚忠,故敢冒昧陈献。伏冀万幾之暇,少垂圣览。生民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惓惓。臣谨对。
(四)柯潜殿试卷
殿试策问 明代宗朱祁钰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如伏羲、神农、黄帝,德莫如尧、舜,功莫如禹、汤、文、武。此数圣人者,万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事著于《易》,禹、汤、文、武之迹存乎《书》。其所以为道、为德、为功者,朕欲究其心术之精微。其推以治,教、养天下,所尚虽殊,然不出乎耕桑、贡赋、学校、礼乐、征伐、刑辟之外,朕欲参其制作之会通。
夫无所酌于古,将何以准于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拳拳于心,亦惟以古圣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养自励。兹欲尽驱天下游谈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尽约天下浮冗之征,以归贡赋,使各膏肥其体,而无或失所养;尽导天下狠戾之顽,以从学校,使各复还其善;尽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礼乐,使各易移其俗,而无或违于教;尽作天下庸怯之兵,以奋征伐,使各销沮其凶;尽化天下争斗之讼,以远刑辟,使各崇尚其耻,而无或外于治。皆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养矣。于古圣人之道、德、功,有可以庶几乎?
伏羲、神农、黄帝曰皇,尧、舜曰帝,禹、汤、文、武曰王,其称号之所以异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养有隆替而然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兹欲措天下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称惟一,而无隆杀之别,亦必有其道乎?
子大夫习之于师,而得之于己,宜无不悉其说者,兹承有司宾兴而来,其具为陈之。朕将亲览焉。
状元殿试卷 柯潜
臣对:臣闻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本,亦莫不有其要。盖先明诸心,则事得其本;远稽诸古,则事得其要。圣人之理天下,固莫不稽诸古以为之要,而亦曷当不明诸心以为之本乎?本诸心以治民,而政化隆;本诸心以教民,而民性复;本诸心以养民,而民生遂。故曰心也者,万化之原,万事之本。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道、德、功者,固不外乎此心。后世之所以法古为治者,亦不外乎此心。孟子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此之谓也。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备圣神文武之德。居五位之尊,以缵承列圣;妙一心之用,以中兴家邦。混车书文轨八紘,采玉帛衣裳于万国,治化可谓极其盛,功业可谓极其隆矣。然犹不自满假,复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以远求皇、帝、王、道、德、功之懿,以大施今天下治、教、养之仁。臣有以知陛下之心,其即大舜好问好察,文王望道未见之心。真欲听而行之,非以布衣微陋,不足以与天下之计,姑以此试之也。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陛下之明命乎?谨因圣策所及而条陈之。
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所谓道莫如伏羲、神农、黄帝,德莫如尧、舜,功莫如禹、汤、文、武者,非谓皇有是道而帝、王莫能与,帝有是德而皇、王莫之及,王有是功而皇、帝莫与比。盖皇、帝、王随遇而施其所宜,非谓长于此而不足于彼也。
夫三皇之世,其民皞皞,其俗熙熙,虽无二帝之孝弟以导之,而民自无不亲不逊之患,虽无三王之征伐以救之,而民自无涂泥炭火之虞。其所急者,在于道焉。昔也,民未知所以养,伏羲始结网罟以教畋渔,神农始为耒耜以教耕耨,教民日中为市,交易而退。黄帝则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于是,民始得其所养。所谓道莫如三王者,此也。其事之著于《易》者如此。
迨夫尧舜之世,开物成务之道已大备,吊民伐罪之功无所施,其所急者,在于德焉。盖民既得所养,而其巧伪日生,不可逸居无教。观其克明峻德,慎徽五典,而师天下以仁;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敷五教以契。于是,民始得由于教。所谓德莫如尧舜者,此也。
三代之时,承伏羲、神农、黄帝之绕,绍尧、舜允执厥中之传,其所急者,独不在于功乎?盖洪水为害于先,桀、纣为虐于后,圣人不得不任其责。观其修治府事,而致万世永赖之休;取彼凶残,而收四海永清之效,于是,民始得安于治,又非所谓功莫如禹、汤、文、武乎?此其迹之存乎《书》者,又如此。
观于《易》、《书》,则数圣人所以为道,为德,为功,无非随遇而施所宜。然究其心术之精微,欲以治、教、养于天下,则一而己。势有不同,故道、德、功之施,先后异宜;理无或异,故治、教、养之方,古今一致。是故,耕桑、贡赋,养之所由出;学校、礼乐,教之所由兴;征伐、刑辟,治之所由举。此古圣王已行之迹,万世所不能外者也。
陛下嗣登大宝,夙夜惓惓于心,以古圣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养自励,此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臣虽愚昧,岂敢不罄一得之愚,以为海岳涓埃之助?
陛下诚欲尽驱天下游谈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尽约天下浮冗之征以归贡赋,使各膏肥其体。臣愿陛下心古圣人之心,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俾之有常生之产,而禁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徒,则国无游民,而生之者众矣。制节谨度,轻徭薄赋,俾土方成,惟正之供,而凡所用者有养,所养者有用,则朝无倖位,而食之者寡矣。如是,人皆得以衣食其力,膏肥其体,而失所养者无有也。诚欲尽导天下狠戾之顽,使各复还其善;尽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礼乐,使各移易其俗。臣愿陛下心古圣人之心,大兴学校,慎选范模,躬行道德以先之,使为师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学,而时无不可化之人。崇重衣冠,惇尚廉耻,修礼乐以导之,使人皆知礼义之为贵,鄙陋之可贱,而世无不可变之风。如是,人皆得以复还其善,移易其俗,而违所教者无有也。诚欲尽作天下慵怯之兵以奋征伐,使各销沮其凶;尽化天下争嗣之讼以远刑辟,使各崇尚其耻。臣愿陛下亦惟以古圣人之心为心,结之以深思厚德,使人于见危也,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事。临之以信赏必罚,使人于赴嗣也,至死不变,而临难毋荀免。上有敢死之士,斯下无反侧之心矣。道民以政,不若道之以德,使知入则孝出则弟,下不敢犯上,卑不敢踰尊。齐民以刑,不若齐之以礼,使知少事长,贱事贵,耕者必让畔,行者必让路,下无争闘之讼,斯上有可措之刑矣。如是,人皆得以销沮其凶,崇尚其耻,而岂有外于治者哉!
夫治、教、养之方,臣所陈于前者。陛下不用则已,用则必臻其效。既臻其效,则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德、功,奚不可几及之有哉?在力行何如耳。伏羲、神农、黄帝,开物成务,以道导天下者莫大,故称曰皇。尧、舜渐仁摩义,以德主宰乎天下者莫先,故称曰帝。禹、汤、文、武吊民伐罪,以功济天下者莫急,故称曰王。曰皇,曰帝,曰王,其称号虽殊,而其心则一;曰道,曰德,曰功,其事业虽一,而其势实殊。故世之有皇、帝、王、霸,犹岁之有春、夏、秋、冬,非势之使然乎?陛下诚欲措天下于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称惟一,而无隆杀之别,臣则以为,惟当先明诸心而已。心同,则无所往而不同矣。
盖以是心而治民,则征伐有道,刑辟惟中,即《诗》所谓“王猷允塞”,《易》所谓“明慎用刑”是也。以是心而教民,则学校振举,礼乐兴行,即朱子所谓“建学立师以培其根”,周子所谓“阴阳理而后和”是也。以是心而养民,则农桑之务举,厚敛之患无,即《诗》所谓“星焉夙驾,税于桑田”,《书》所谓“财赋底慎,庶土交正”是也。臣愿陛下始终此心,则始终此治、此教,而始终此养矣。矧圣朝太祖高皇帝,勤是心以图治于先,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勤是心以继续于后。太上皇帝承之,神此心于於穆之上。陛下嗣而守之,运此心于九五之尊,远而祖述于前古,近而宪章于祖宗,登用贤才,密勿廊庙,制作礼乐,统和天人,复隆古之盛治,恢中兴之大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安得专其美于前哉!此固陛下宜以自励于心者。
臣应有司宾兴而来,幸得立玉阶方寸地,安敢不罄平日习之于师,而得之于已者,恳恳焉为陛下重言之乎?若夫阿意以求恩,逢迎以徼宠,则非臣之所学,亦非陛下求言之本意也。伏惟陛下俯垂睿览。
臣干冒天威,不胜怖惧之至。臣谨对。
殿试策问 明成祖朱棣
皇帝制曰:朕承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洪业,舆图之广,生齿之繁,从古莫比。故穷发之地咸为编户,雕题椎结悉化冠裳。来虽如归而治虑未浃,朕夙夜惟念,期在雍熙。然十室之邑,人人教之且有弗及,矧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夫存诚过化,不见其迹。欲臻其极,谅必有要,不明诸心,曷由达效?
唐虞三代之治,其来尚矣,而汉、唐、宋之治,犹可指而言之。自夔典乐教胄子而学校兴,而汉、唐、宋之学校有因革,其教化可得而闻?自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科目举,而汉、唐、宋之科目有异同,其名实可得而议?自小司徒经土地而田制定,而汉、唐、宋之田制有屯营,其计画可得而言?自校人掌王马之政,而马政立,而汉、唐、宋之畜牧有耗息,其详悉可得而数?之数者,有宜于古而合于今,若何施而可以几治?夫政不稽古,则无以验今,事不究迹,则无以见实。子大夫博古以知今,明体以适用。陈其当否,以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状元殿试卷 林环
臣对:臣闻出治有本,在乎先明诸心;为治有法,在乎远稽诸古。盖明诸心者,其本也;而稽诸古者,其迹也。圣人之治天下,未尝不以稽古为道,而亦曷尝不本诸心,以为出治之本乎?
钦惟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肇造洪基,抚校有可考者矣。若宋之时,有国子监、太学,有武学,有书、算学。天下已平,儒者往往依山林以讲授,当时于嵩阳、岳麓、雎阳、白鹿四书院为尤著。厥后,如胡安定教授苏湖,立经义、治事斋以教学者,此尤表表足称。则宋之学校,其颠末亦有可稽者焉。
夫学校教化之本,唐虞三代之时,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故学校之立而教化为特盛。若汉之治杂霸,唐之治杂夷,宋之治亦有未醇,躬行之实,已无其本,则学校虽立,而教化终有愧于古者,抑有由矣。
人君用人亮天之道,莫大于科目。成周之时,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岁大比,而宾兴夫贤者能者,故命乡论秀而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升之学,曰“俊士”。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大司马论辨官材以告于王,论定而后官之,任官而后爵之,以至太宰招废置而持其柄,内史赞予夺而贰于中。司士掌郡士之版,岁登记其损益之数。此科目所由举也。若汉之时,则有孝廉、孝弟、力田、贤良、明经诸科。唐之时,则由学馆进者,曰“生徒”,由州县进者,曰“乡贡”,而又有进士、开元礼、缘举、杂录、制举、孝廉、三礼、五传、一史、三史、童子、明经、明法、明算诸科。宋之时,则有诸贤良,有宏词,有童子学,漕试、推恩诸科。此汉、唐、宋科目之名,其异同固可稽矣。然成周之时,教养有法,且选任之际,循名责实。故所进之人,无非适用之士。
若汉唐而后,则养非所用,用非所养,故进用之际,不无贤否相半。是故汉之仲舒以贤良进,倪宽以明经举,似矣。而徐淑之不逃冒年,陈汤之不奔父丧,乃与科选,果何欤?唐之制科,则有裴度、韩休,而皇甫镈亦以是进。博学宏词,则有陆贽、杜黄裳,而王涯、刘禹锡亦以是进,又何欤?宋之富弼、苏轼,以制科进,杜邝公、范文正、欧阳公由进士举,是皆可取。然以丁谓之謀佞,且居要路,则又不能无可议者焉。此其名实不称,视成周得人之盛,盖不能无歉矣。
至若足民足国之良图,莫要于定田制;备兵讲武之先事,莫要于立马政。周制,小司徒均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人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故成周无不受田之家。阡陌既开,井田法废。自汉文帝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制。赵充国击先零,分兵久驻,于是有屯田之说。至唐之时,则有营田之制。至宋之兴,或屯或营,盖兼用也。大抵汉之屯田以兵,唐之营田以民,而宋之或兵或民,盖不一焉。夫其屯田以兵,斯可以免军旅坐食之费,营田以民,斯可以足国家储备之资,此其计划之善,亦有可取者矣。
至若校人掌王马之政,此马政所由立也。汉置仆牧帅诸苑,而众庶街巷有马,则不特养于官矣。暨大将军骠骑屡出,而马大耗。唐自张万岁领群牧,马至七十万六千,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至四十三万。自群牧失职,国马益耗。宋则牧马有监,掌牧有职。又或畜之于官,或养之于民,或市之于边。大抵市之于边者不可常,莫若畜之于官为有常也。专畜于官者为限,莫若兼养于民者为益广也。若是息耗之由,亦可概见矣。
皇上既举数者之目,详列于前,而又以数者之政,宜于今者总询于后。臣学不足以稽古,用不足以适今,曷足以上揆圣哀。愚昧之见,谓是数者,皆皇上酌古准今,已行之效,而拳拳以为问,特皇上谦让不自满足之心耳。夫方今学校,内自京畿,外达郡国,莫不有学,此盖太祖高皇帝参酌古制而用之者。今皇上遵而行之,迩者车驾临幸太学,俎豆生辉,衣冠增气,天下士子,知所向方,则教人之法,固可比隆唐虞三代,而陋汉、唐、宋于下风矣。方今进于学校者有科贡,选于乡里者有人材,是亦太祖高皇帝错综古典而行之者。今皇上嗣而守之。兹者临轩策问,茅茹汇征,衣冠云集,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则用人之道,亦可媲美唐虞三代,而薄汉、唐、宋于下流矣。至若田制之立,虽非尽成周之旧,马政之立,亦参用校人之政。然其屯营之必备,畜牧之必专,是亦酌古而宜于今者耳。是二者,亦太祖高皇帝已试之法,今皇上率而由之者。况于屯田则劝督之必严,于畜牧则孳息之益众,殆恐古昔盛际,亦不过是,而汉、唐、宋又乌可以同日而语哉!然臣于终篇,愿有献焉。
夫是数者,特冶之法也。其本则系之皇上之心。盖以是心而兴学校,则朱熹所谓本之躬行心得之余是也。以是心而兴贤才,则大禹所谓光天之下是也。以是心而定田制,则《大学》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是也。以是心而立马政,则《诗》所谓“秉心塞渊”与“思无邪”者是也。合而论之,则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愿皇上终始此心,斯可以终始此治矣。
臣于博古通今,明体适用,乌足以当。特以上之问,适有以发臣愚忠,故敢冒昧陈献。伏冀万幾之暇,少垂圣览。生民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惓惓。臣谨对。
(四)柯潜殿试卷
殿试策问 明代宗朱祁钰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如伏羲、神农、黄帝,德莫如尧、舜,功莫如禹、汤、文、武。此数圣人者,万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事著于《易》,禹、汤、文、武之迹存乎《书》。其所以为道、为德、为功者,朕欲究其心术之精微。其推以治,教、养天下,所尚虽殊,然不出乎耕桑、贡赋、学校、礼乐、征伐、刑辟之外,朕欲参其制作之会通。
夫无所酌于古,将何以准于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拳拳于心,亦惟以古圣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养自励。兹欲尽驱天下游谈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尽约天下浮冗之征,以归贡赋,使各膏肥其体,而无或失所养;尽导天下狠戾之顽,以从学校,使各复还其善;尽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礼乐,使各易移其俗,而无或违于教;尽作天下庸怯之兵,以奋征伐,使各销沮其凶;尽化天下争斗之讼,以远刑辟,使各崇尚其耻,而无或外于治。皆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养矣。于古圣人之道、德、功,有可以庶几乎?
伏羲、神农、黄帝曰皇,尧、舜曰帝,禹、汤、文、武曰王,其称号之所以异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养有隆替而然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兹欲措天下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称惟一,而无隆杀之别,亦必有其道乎?
子大夫习之于师,而得之于己,宜无不悉其说者,兹承有司宾兴而来,其具为陈之。朕将亲览焉。
状元殿试卷 柯潜
臣对:臣闻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本,亦莫不有其要。盖先明诸心,则事得其本;远稽诸古,则事得其要。圣人之理天下,固莫不稽诸古以为之要,而亦曷当不明诸心以为之本乎?本诸心以治民,而政化隆;本诸心以教民,而民性复;本诸心以养民,而民生遂。故曰心也者,万化之原,万事之本。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道、德、功者,固不外乎此心。后世之所以法古为治者,亦不外乎此心。孟子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此之谓也。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备圣神文武之德。居五位之尊,以缵承列圣;妙一心之用,以中兴家邦。混车书文轨八紘,采玉帛衣裳于万国,治化可谓极其盛,功业可谓极其隆矣。然犹不自满假,复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以远求皇、帝、王、道、德、功之懿,以大施今天下治、教、养之仁。臣有以知陛下之心,其即大舜好问好察,文王望道未见之心。真欲听而行之,非以布衣微陋,不足以与天下之计,姑以此试之也。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陛下之明命乎?谨因圣策所及而条陈之。
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所谓道莫如伏羲、神农、黄帝,德莫如尧、舜,功莫如禹、汤、文、武者,非谓皇有是道而帝、王莫能与,帝有是德而皇、王莫之及,王有是功而皇、帝莫与比。盖皇、帝、王随遇而施其所宜,非谓长于此而不足于彼也。
夫三皇之世,其民皞皞,其俗熙熙,虽无二帝之孝弟以导之,而民自无不亲不逊之患,虽无三王之征伐以救之,而民自无涂泥炭火之虞。其所急者,在于道焉。昔也,民未知所以养,伏羲始结网罟以教畋渔,神农始为耒耜以教耕耨,教民日中为市,交易而退。黄帝则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于是,民始得其所养。所谓道莫如三王者,此也。其事之著于《易》者如此。
迨夫尧舜之世,开物成务之道已大备,吊民伐罪之功无所施,其所急者,在于德焉。盖民既得所养,而其巧伪日生,不可逸居无教。观其克明峻德,慎徽五典,而师天下以仁;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敷五教以契。于是,民始得由于教。所谓德莫如尧舜者,此也。
三代之时,承伏羲、神农、黄帝之绕,绍尧、舜允执厥中之传,其所急者,独不在于功乎?盖洪水为害于先,桀、纣为虐于后,圣人不得不任其责。观其修治府事,而致万世永赖之休;取彼凶残,而收四海永清之效,于是,民始得安于治,又非所谓功莫如禹、汤、文、武乎?此其迹之存乎《书》者,又如此。
观于《易》、《书》,则数圣人所以为道,为德,为功,无非随遇而施所宜。然究其心术之精微,欲以治、教、养于天下,则一而己。势有不同,故道、德、功之施,先后异宜;理无或异,故治、教、养之方,古今一致。是故,耕桑、贡赋,养之所由出;学校、礼乐,教之所由兴;征伐、刑辟,治之所由举。此古圣王已行之迹,万世所不能外者也。
陛下嗣登大宝,夙夜惓惓于心,以古圣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养自励,此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臣虽愚昧,岂敢不罄一得之愚,以为海岳涓埃之助?
陛下诚欲尽驱天下游谈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尽约天下浮冗之征以归贡赋,使各膏肥其体。臣愿陛下心古圣人之心,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俾之有常生之产,而禁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徒,则国无游民,而生之者众矣。制节谨度,轻徭薄赋,俾土方成,惟正之供,而凡所用者有养,所养者有用,则朝无倖位,而食之者寡矣。如是,人皆得以衣食其力,膏肥其体,而失所养者无有也。诚欲尽导天下狠戾之顽,使各复还其善;尽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礼乐,使各移易其俗。臣愿陛下心古圣人之心,大兴学校,慎选范模,躬行道德以先之,使为师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学,而时无不可化之人。崇重衣冠,惇尚廉耻,修礼乐以导之,使人皆知礼义之为贵,鄙陋之可贱,而世无不可变之风。如是,人皆得以复还其善,移易其俗,而违所教者无有也。诚欲尽作天下慵怯之兵以奋征伐,使各销沮其凶;尽化天下争嗣之讼以远刑辟,使各崇尚其耻。臣愿陛下亦惟以古圣人之心为心,结之以深思厚德,使人于见危也,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事。临之以信赏必罚,使人于赴嗣也,至死不变,而临难毋荀免。上有敢死之士,斯下无反侧之心矣。道民以政,不若道之以德,使知入则孝出则弟,下不敢犯上,卑不敢踰尊。齐民以刑,不若齐之以礼,使知少事长,贱事贵,耕者必让畔,行者必让路,下无争闘之讼,斯上有可措之刑矣。如是,人皆得以销沮其凶,崇尚其耻,而岂有外于治者哉!
夫治、教、养之方,臣所陈于前者。陛下不用则已,用则必臻其效。既臻其效,则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德、功,奚不可几及之有哉?在力行何如耳。伏羲、神农、黄帝,开物成务,以道导天下者莫大,故称曰皇。尧、舜渐仁摩义,以德主宰乎天下者莫先,故称曰帝。禹、汤、文、武吊民伐罪,以功济天下者莫急,故称曰王。曰皇,曰帝,曰王,其称号虽殊,而其心则一;曰道,曰德,曰功,其事业虽一,而其势实殊。故世之有皇、帝、王、霸,犹岁之有春、夏、秋、冬,非势之使然乎?陛下诚欲措天下于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称惟一,而无隆杀之别,臣则以为,惟当先明诸心而已。心同,则无所往而不同矣。
盖以是心而治民,则征伐有道,刑辟惟中,即《诗》所谓“王猷允塞”,《易》所谓“明慎用刑”是也。以是心而教民,则学校振举,礼乐兴行,即朱子所谓“建学立师以培其根”,周子所谓“阴阳理而后和”是也。以是心而养民,则农桑之务举,厚敛之患无,即《诗》所谓“星焉夙驾,税于桑田”,《书》所谓“财赋底慎,庶土交正”是也。臣愿陛下始终此心,则始终此治、此教,而始终此养矣。矧圣朝太祖高皇帝,勤是心以图治于先,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勤是心以继续于后。太上皇帝承之,神此心于於穆之上。陛下嗣而守之,运此心于九五之尊,远而祖述于前古,近而宪章于祖宗,登用贤才,密勿廊庙,制作礼乐,统和天人,复隆古之盛治,恢中兴之大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安得专其美于前哉!此固陛下宜以自励于心者。
臣应有司宾兴而来,幸得立玉阶方寸地,安敢不罄平日习之于师,而得之于已者,恳恳焉为陛下重言之乎?若夫阿意以求恩,逢迎以徼宠,则非臣之所学,亦非陛下求言之本意也。伏惟陛下俯垂睿览。
臣干冒天威,不胜怖惧之至。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