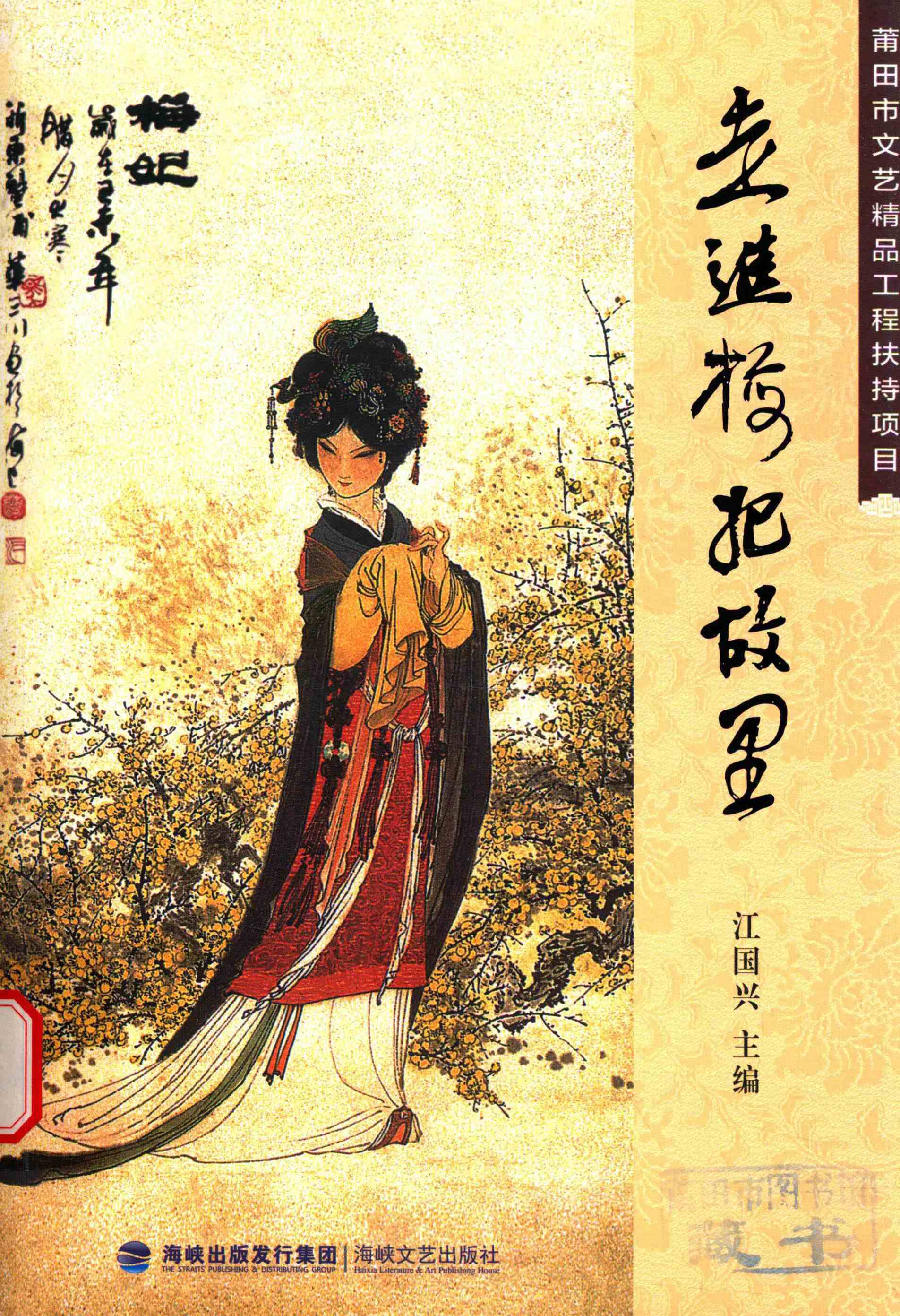内容
在福建文化史上,中唐以前的历史人物缺乏史传记载。这种情况使那个时期的福建历史人物带上了模糊的色彩。梅妃其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臧励龢等人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有一条“江采蘋”,扼要介绍了梅妃的生平:
江采蘋:莆田人。开元中,高力士使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帝以其性喜梅,名曰“梅妃”。后杨太真擅宠,迁之上阳宫。帝念之,适夷使贡珍珠,帝以一斛赐之。妃不受,赋诗以谢。帝命乐府度以新声,名《一斛珠》。
从这个词条的行文语气看,是把梅妃看作实有其人的。它的依据,就是唐宋时期无名氏的《梅妃传》。
《梅妃传》是关于梅妃的唯一原始资料。元末,陶宗仪把它编入《说郛》,不题撰人。明人编《唐人说荟》,收入《梅妃传》,标明作者为唐代的曹邺。另一方面,莆田地区关于梅妃的民间传说很多,莆田县黄石镇有个江东村,据说就是梅妃的故里。这里至今还有江姓族人,世代聚居,还有一座纪念梅妃的浦口宫。当地传说,梅妃自幼貌丑,是个放鸭女子,选官到乡时,她来不及躲藏,惊倒在地。当她从地上爬起来,其容貌竟胜过西施,故被选中。当地人称之为“江东妃”。
宋代以后,人们大多把《梅妃传》看作真实记载。南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二就载入《梅妃传》。李俊甫是莆田人,《莆阳比事》成书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取唐以来上下千百年间,凡莆阳事之可传者”,均可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属辞有法,纪事核真”,是一部可信赖的地方史书。与李俊甫约略同时的莆籍著名诗人刘克庄(1187—1269)也有咏梅妃的诗。明清时期,关于梅妃的传说更广。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四·方域志·东华溪》载:“唐有梅妃者,是里人也,唐人为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六·拾遗》也有梅妃传略,看来都来自《梅妃传》。清康熙年间编的《全唐诗》收入梅妃诗一首,即《梅妃传》所载梅妃谢明皇赐珍珠诗: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不仅如此,还把梅妃列入后妃类,并在诗前加题目:《谢赐珍珠》,题下又加注:“上在花萼楼封珍珠一斛,密赐妃,妃不受。”所录的诗与《梅妃传》略有出入,《梅妃传》“桂叶”作“柳叶”,“污红绡”作“湿红绡”,“尽日”作“自是”,这只是版本不同,所有细节都来自《梅妃传》。
另一方面,明吴世美据《梅妃传》作杂剧《惊鸿记》,清洪昇的名剧《长生殿》也有“夜怨”“絮阁”两折,都是演梅妃事。史书把梅妃看作历史人物,戏曲又把她演为传奇人物,因此梅妃的事迹广为流传。
但到近现代,学术界经过考证,对《梅妃传》是不是唐人所作,梅妃是否实有其人,开始产生怀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梅妃传》放在“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一类,并编入《唐宋传奇集》。他根据《梅妃传》末的跋文所说“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字亦媚好”,“惟叶少蕴与余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判断作跋者就是作者,既与叶少蕴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唐曹邺撰,亦明人妄增之。”本来,唐宋时期,传奇小说盛行,记载唐玄宗和杨贵妃事迹的野史笔记和传奇小说就有十多种,或为时人所记,或是后人得自前朝传闻,里巷之谈,间亦采撷,真伪杂糅,还不时夹杂了一些神仙志怪、荒诞不经的内容。有些可作为历史资料,以补正史之阙,但有些则是文学创作,不能据为史实。梅妃事迹既不见于正史,又是单文孤证,从体裁看,《梅妃传》情节描写生动感人,的确属于传奇小说一类。鲁迅先生著述态度严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考证周详,后人奉为圭臬,所以他的判断影响很大。此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说“明人题为唐曹邺作,不可信。”张友鹤在《唐宋传奇选》里就说《梅妃传》:“应是宋人所作。”综言之,认为《梅妃传》是宋人所作,梅妃是虚构人物的主要论据有:
一、跋文提到叶少蕴,叶是北宋末期人,可见作者是宋代人。
二、梅妃事迹,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都没有记载,《梅妃传》一文,唐人笔记也没有提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等宋代公私目录学著作都没有著录,不会是唐人所作。
三、《梅妃传》说,高力士使闽,但考之于新旧《唐书》,都没有高力士使闽的记载。
四、从历史地理演变看,莆田平原三面濒海,古代原为兴化湾的一部分,是海潮涨落之地。《八闽通志·卷六十》“祠庙·红泉宫”载,“唐元和八年(813),观察使裴次元于(莆)邑之红泉筑海堰潴水,垦辟荒地为田三百二十有二顷,岁收数万斛,以赡军储。”这个红泉宫在县城东南黄石市中,正是江采蘋的家乡。元和八年是在开元(713—740)之后七八十年,这就是说,开元年间,黄石乡江东村一带还没有围垦,海潮出没无常,江东村这个地方可能还不存在,高力士手下的选官不可能到这样的地方来选妃子,能诗善赋的梅妃也不大可能在这样一个海滨僻地生长。
五、据当地民间传说,江采蘋是个放鸭女子,与《梅妃传》所描述的能诗善赋的梅妃相去甚远。
但另一方面,认为《梅妃传》不是凭空虚构的观点也仍然存在,主要论据是。
一、南宋的李俊甫在《莆阳比事》中已载梅妃事迹,刘克庄也有咏梅妃诗,他们都是莆田人,都肯定有梅妃其人。
二、莆田县黄石镇江东村确是江姓族居地,当地还有纪念梅妃的浦口宫,民间传说虽有神话色彩,但总可说明这里是江采蘋的家乡,与《梅妃传》的记载相符,不能不予考虑。如果当时并不存在江东村,《梅妃传》的作者怎么会指明梅妃生活的时间和地点?怎么会编造出与地点和族姓相符的故事?
三、《梅妃传》说,唐明皇读了梅妃的《谢赐珍珠》诗后“帐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始此也”。这说明“一斛珠”这个词调的来源就是唐明皇赐梅妃一斛珠的故事。
总而言之,梅妃是否确有其人,《梅妃传》是唐代的纪实之作,还是出自宋人依托,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定论。因此,现行著作对待这个问题,各有不同的倾向和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根据鲁迅的判断,谓梅妃实无其人,《梅妃传》出宋人伪托。第二种态度是先把梅妃当作历史人物来介绍,末尾引鲁迅的观点,以示客观。如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祖譔主编)有“江妃”条,不仅把江采蘋看作文学家,而且还有生卒年介绍,表明实有其人。在介绍梅妃生平和作品之后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实无其人。”保留鲁迅的观点,以备一说,但其倾向是明显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周勋初主编)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在“江妃”条内,把梅妃看作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唐玄宗之妃,名采蘋,莆田人,”然后介绍其生平作品。最后说:“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推断,梅妃实无其人。”这两部专科辞典吸收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其态度是有代表性的。
1962年郭沫若来闽,作《途次莆田》诗,有句云:“梅妃生里传犹在,夹漈藏书有孑遗。”把梅妃与郑樵并提,似肯定有其人,但较谨慎。
平心而论,《梅妃传》单文孤证,作为直接证据,实嫌不足,而否定梅妃其人的论据则涉及地理文化的大前提,不能不正视。所以,衡量一下双方的比重,肯定的成分只有三四成,否定的成分倒有六七成。梅妃只能作为传说人物,不能作为历史人物。
梅妃的问题在福建文化史上有一定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衡量唐代前期福建沿海地区的汉文化水平。唐开元以前,福建的汉文化只能以漳州的陈元光父子及其部属许天正等人为代表,但他们是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和移植者,而《梅妃传》中的梅妃却是在福建莆田土生土长的女子,如确有其人,那就意味着唐代前期福建沿海地区的汉文化已可以和中原地区相比美。海滨乡下姑娘能这样知书识礼、能诗善文,则当地文化发达程度可想而知。但在唐开元前后,当地缺乏相应的文化氛围,与梅妃同时的福建知名人物,见诸记载的不过一二人。由此可见,梅妃是否真有其人,不是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早唐代前期福建沿海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问题。这方面的史料还需要继续挖掘。
(原载2001年《炎黄纵横》第三期)
臧励龢等人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有一条“江采蘋”,扼要介绍了梅妃的生平:
江采蘋:莆田人。开元中,高力士使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帝以其性喜梅,名曰“梅妃”。后杨太真擅宠,迁之上阳宫。帝念之,适夷使贡珍珠,帝以一斛赐之。妃不受,赋诗以谢。帝命乐府度以新声,名《一斛珠》。
从这个词条的行文语气看,是把梅妃看作实有其人的。它的依据,就是唐宋时期无名氏的《梅妃传》。
《梅妃传》是关于梅妃的唯一原始资料。元末,陶宗仪把它编入《说郛》,不题撰人。明人编《唐人说荟》,收入《梅妃传》,标明作者为唐代的曹邺。另一方面,莆田地区关于梅妃的民间传说很多,莆田县黄石镇有个江东村,据说就是梅妃的故里。这里至今还有江姓族人,世代聚居,还有一座纪念梅妃的浦口宫。当地传说,梅妃自幼貌丑,是个放鸭女子,选官到乡时,她来不及躲藏,惊倒在地。当她从地上爬起来,其容貌竟胜过西施,故被选中。当地人称之为“江东妃”。
宋代以后,人们大多把《梅妃传》看作真实记载。南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二就载入《梅妃传》。李俊甫是莆田人,《莆阳比事》成书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取唐以来上下千百年间,凡莆阳事之可传者”,均可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属辞有法,纪事核真”,是一部可信赖的地方史书。与李俊甫约略同时的莆籍著名诗人刘克庄(1187—1269)也有咏梅妃的诗。明清时期,关于梅妃的传说更广。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四·方域志·东华溪》载:“唐有梅妃者,是里人也,唐人为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六·拾遗》也有梅妃传略,看来都来自《梅妃传》。清康熙年间编的《全唐诗》收入梅妃诗一首,即《梅妃传》所载梅妃谢明皇赐珍珠诗: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不仅如此,还把梅妃列入后妃类,并在诗前加题目:《谢赐珍珠》,题下又加注:“上在花萼楼封珍珠一斛,密赐妃,妃不受。”所录的诗与《梅妃传》略有出入,《梅妃传》“桂叶”作“柳叶”,“污红绡”作“湿红绡”,“尽日”作“自是”,这只是版本不同,所有细节都来自《梅妃传》。
另一方面,明吴世美据《梅妃传》作杂剧《惊鸿记》,清洪昇的名剧《长生殿》也有“夜怨”“絮阁”两折,都是演梅妃事。史书把梅妃看作历史人物,戏曲又把她演为传奇人物,因此梅妃的事迹广为流传。
但到近现代,学术界经过考证,对《梅妃传》是不是唐人所作,梅妃是否实有其人,开始产生怀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梅妃传》放在“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一类,并编入《唐宋传奇集》。他根据《梅妃传》末的跋文所说“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字亦媚好”,“惟叶少蕴与余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判断作跋者就是作者,既与叶少蕴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唐曹邺撰,亦明人妄增之。”本来,唐宋时期,传奇小说盛行,记载唐玄宗和杨贵妃事迹的野史笔记和传奇小说就有十多种,或为时人所记,或是后人得自前朝传闻,里巷之谈,间亦采撷,真伪杂糅,还不时夹杂了一些神仙志怪、荒诞不经的内容。有些可作为历史资料,以补正史之阙,但有些则是文学创作,不能据为史实。梅妃事迹既不见于正史,又是单文孤证,从体裁看,《梅妃传》情节描写生动感人,的确属于传奇小说一类。鲁迅先生著述态度严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考证周详,后人奉为圭臬,所以他的判断影响很大。此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说“明人题为唐曹邺作,不可信。”张友鹤在《唐宋传奇选》里就说《梅妃传》:“应是宋人所作。”综言之,认为《梅妃传》是宋人所作,梅妃是虚构人物的主要论据有:
一、跋文提到叶少蕴,叶是北宋末期人,可见作者是宋代人。
二、梅妃事迹,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都没有记载,《梅妃传》一文,唐人笔记也没有提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等宋代公私目录学著作都没有著录,不会是唐人所作。
三、《梅妃传》说,高力士使闽,但考之于新旧《唐书》,都没有高力士使闽的记载。
四、从历史地理演变看,莆田平原三面濒海,古代原为兴化湾的一部分,是海潮涨落之地。《八闽通志·卷六十》“祠庙·红泉宫”载,“唐元和八年(813),观察使裴次元于(莆)邑之红泉筑海堰潴水,垦辟荒地为田三百二十有二顷,岁收数万斛,以赡军储。”这个红泉宫在县城东南黄石市中,正是江采蘋的家乡。元和八年是在开元(713—740)之后七八十年,这就是说,开元年间,黄石乡江东村一带还没有围垦,海潮出没无常,江东村这个地方可能还不存在,高力士手下的选官不可能到这样的地方来选妃子,能诗善赋的梅妃也不大可能在这样一个海滨僻地生长。
五、据当地民间传说,江采蘋是个放鸭女子,与《梅妃传》所描述的能诗善赋的梅妃相去甚远。
但另一方面,认为《梅妃传》不是凭空虚构的观点也仍然存在,主要论据是。
一、南宋的李俊甫在《莆阳比事》中已载梅妃事迹,刘克庄也有咏梅妃诗,他们都是莆田人,都肯定有梅妃其人。
二、莆田县黄石镇江东村确是江姓族居地,当地还有纪念梅妃的浦口宫,民间传说虽有神话色彩,但总可说明这里是江采蘋的家乡,与《梅妃传》的记载相符,不能不予考虑。如果当时并不存在江东村,《梅妃传》的作者怎么会指明梅妃生活的时间和地点?怎么会编造出与地点和族姓相符的故事?
三、《梅妃传》说,唐明皇读了梅妃的《谢赐珍珠》诗后“帐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始此也”。这说明“一斛珠”这个词调的来源就是唐明皇赐梅妃一斛珠的故事。
总而言之,梅妃是否确有其人,《梅妃传》是唐代的纪实之作,还是出自宋人依托,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定论。因此,现行著作对待这个问题,各有不同的倾向和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根据鲁迅的判断,谓梅妃实无其人,《梅妃传》出宋人伪托。第二种态度是先把梅妃当作历史人物来介绍,末尾引鲁迅的观点,以示客观。如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祖譔主编)有“江妃”条,不仅把江采蘋看作文学家,而且还有生卒年介绍,表明实有其人。在介绍梅妃生平和作品之后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实无其人。”保留鲁迅的观点,以备一说,但其倾向是明显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周勋初主编)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在“江妃”条内,把梅妃看作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唐玄宗之妃,名采蘋,莆田人,”然后介绍其生平作品。最后说:“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推断,梅妃实无其人。”这两部专科辞典吸收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其态度是有代表性的。
1962年郭沫若来闽,作《途次莆田》诗,有句云:“梅妃生里传犹在,夹漈藏书有孑遗。”把梅妃与郑樵并提,似肯定有其人,但较谨慎。
平心而论,《梅妃传》单文孤证,作为直接证据,实嫌不足,而否定梅妃其人的论据则涉及地理文化的大前提,不能不正视。所以,衡量一下双方的比重,肯定的成分只有三四成,否定的成分倒有六七成。梅妃只能作为传说人物,不能作为历史人物。
梅妃的问题在福建文化史上有一定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衡量唐代前期福建沿海地区的汉文化水平。唐开元以前,福建的汉文化只能以漳州的陈元光父子及其部属许天正等人为代表,但他们是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和移植者,而《梅妃传》中的梅妃却是在福建莆田土生土长的女子,如确有其人,那就意味着唐代前期福建沿海地区的汉文化已可以和中原地区相比美。海滨乡下姑娘能这样知书识礼、能诗善文,则当地文化发达程度可想而知。但在唐开元前后,当地缺乏相应的文化氛围,与梅妃同时的福建知名人物,见诸记载的不过一二人。由此可见,梅妃是否真有其人,不是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早唐代前期福建沿海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问题。这方面的史料还需要继续挖掘。
(原载2001年《炎黄纵横》第三期)
相关人物
李瑞良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