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明代倭寇之骚扰,是莆田历史上最大兵祸之一。其对莆田的骚扰,开始于明初永乐八年(1410),而以明中叶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一年最严重。这二十年时间里被兵达十五次,其蹂躏地区,东自江口、涵江,南起南日岛、平海、笏石、黄石至莆郡城,沿这两线的各乡村以抵于滨海各地,概遭其劫掠。最后一次,莆田郡城被陷两个月,自十一月至第二年四月,寇还据莆不退,调浙、赣等地兵来,才平定之。二十年间倭寇十五次祸莆,烧杀劫掠,极其凶残,人民起来抵抗牺牲的,被掳被杀自杀的数以万计,财物被劫去,被破坏烧毁的更难胜记,给莆田人民以很大的灾难。特别最后一次陷城,城内外尸首枕藉,腥秽不堪,群众财物,官家库藏,被劫无遗,民房、官署、祠宇、寺观、典籍,焚毁殆尽。倭寇对福建的骚扰,北则福宁、福安、宁德,南则惠安、南安、同安,以及福州、福清、仙游、永春等地皆被兵,受害的不单是莆田,但莆田却是被祸最烈,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最为惨重。
一、倭寇的来历
考倭寇在唐代就有了。唐林披述刺史黄峰(按:应为黄岸)迁居云:“自桂州航海归,道颉洋,避倭兵,风浪飘荡,登延福山,爱山水之秀,因居焉。”又林藻行述云:“从南越海道归,见蒲田延福山山水之秀,因家焉。”南越就是现在的广东,延福山就是莆田县现在的囊山。可见唐时倭寇就出没沿海一带。但倭寇成为侵扰我国之外患,却还是在明代。盖自元至元到大德(1335-1368),三十余年持续对日本用兵后,日本同我国的关系就很紧张,禁其人民同我国通商,纵其边民侵扰我国沿海。元中叶后,其国分为南北朝,至明初,南并于北,遗臣流落海上,和海盗合伙,海盗之势更盛,屡次骚扰我国沿海各州县。明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即颁谕日本,努力改善中日关系,并派使臣持诏责问日本寇侵沿海的问题,日本不答。于是明太祖就在沿海整饬海防,置兵防倭。洪武二十年(1387),派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当时江夏侯到莆田相度地形,增筑平海、莆禧城寨,加强海防工作。至永乐初日本受明朝封赐,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埚后,于是寇掠才见稀少。莆田县也是从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倭寇在平海舣岸,被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击溃后,一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一百三十年中就都没有倭警。
至明中叶嘉靖二年(1523),中日通商决裂之后,倭祸才又开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记载:“世宗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诸道争贡。……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宋本中国人,投奔日本而归附日本者,此次竟充日本贡使来中国),先后至宁波,争长不相下。故事,番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而素卿狡,贿市舶太监先阅佐货,而宴又坐设上。设不平,遂与佐相雠杀,太监又以素卿故,阴助佐,授之兵器。而设众强,拒杀不已,遂毁嘉宾堂,劫东库,逐瑞佐及余姚江。佐奔绍兴,设追之城下,令缚佐出,不许,乃去,沿途杀掠至西霍山洋,杀捕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进、百户刘恩,又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杀百户胡源,浙中大震。”就是因为这一段纠纷,嘉靖下令罢市舶司,禁止对日通商。但是市舶司罢去,对日通商却禁不绝,沿海豪势之家仍同日本商人交通,日本海贾仍然往来自如,由此又再挑起了倭寇对沿海的骚扰。
《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又载:“自罢市舶后,凡番货至,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贵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没海上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迫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且复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因盘踞岛中不去。”所以嘉靖二年(1523)后,倭寇的骚掠就频繁起来了。山东、江苏、浙江受扰较早,及浙江巡抚胡宗宪招降毛海峰,计杀陈东、麻叶,复杀毛海峰、王直,浙江及江南的倭祸才平定。而其余党就窜来福建,于是倭祸中心移来福建。所以莆田受蹂躏最厉害的,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二年(1545)以后,而在嘉靖三十年至四十二年(1551-1563)特别严重。
所谓倭寇,日本人实际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很大部分是中国人和他们同伍,或入海同真倭一起为寇,或潜在大陆做奸细。祸莆倭寇中也有莆田人和漳泉人。莆田各地都潜有内奸。《明史》日本列传载:“大抵真倭十分之三,从倭者十分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惴怯,所至溃崩。”陈伦炯《海国见闻录》云:“倭寇者,萨峒马岛人也。其始市舶于永嘉,萨岛渔者十八人,被风吹入中国,奸人引以为乱,髡须矱额,什以旁近土语,递相攘掠,群称倭奴。”《皇清文献通考》说:“明代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之人居多。市舶所集,内奸勾引故也。”再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
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入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池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是奸民不唯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原注: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人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爪牙)。可见真倭是不多,内奸参加勾引,并互为耳目、爪牙。
《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记载:“番人……盘踞海岛中不去,并海民生计困迫者纠引之,失职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与通,为之向导,时时寇掠沿海诸郡县。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华人,僭称王号,而其宗族妻子田庐,皆在籍无恙,莫敢谁何。”日本史也载:“明太祖欲通聘日本,道阻不通,当时日本边民侵明之沿海,明称倭寇,甚畏之,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遣使于明成祖,修邻交。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边陲诸侯亦各自通于明,得其勘合符,盛行贸易,明之奸商结连朝臣,给日本之商民,睹物不偿价,于是日本商民愤怒,剽掠其沿岸。当时足利氏威令不行,四方不逞之徒,皆集于明之海岸。明之臣不平者,亦来投,倭寇势益猖獗。嘉靖间最盛,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痛击之,破倭于平海卫,其难始止。”日本史的记载也与明史相同。可见所指倭寇,实际有日本人,也有我国人与之同伍。人数不但占大多数。而且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还称王。再从通倭的人来看,任何阶级都有,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凶徒、逸囚、流氓、无赖等都参与。
《嘉靖东南平倭录》载(见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寇,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浙东大震。至是巡按御史陈九德请置大臣,兼制浙、福,乃以朱纨为御史,巡抚浙江兼领福、兴、泉、漳。……时浮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诸达官家为之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纨因上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衣冠之盗难”。国内有“衣冠之盗”说得很明显。莆田受倭祸,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康大和《重建郡治记》云:“倭寇内侵,土民向导。”《戚少保年谱》及莆旧志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寇由三江口入屯,……是时福清、莆田、惠安三县各大村皆散布寇党”“……船户请郡愿各奋身决死战,一鼓而前,歼贼百余级,侯熙兵阴遮道翼贼,船户反胜为败,多伤退。又虎匠数百人入杭头,以毒矢中贼,贼大溃,移白杜,虎匠潜先往待之,侯兵密报贼。贼伏林莽中,虎匠被伤百余人”“……不意我兵为向导所误,缘向导皆与贼通,特留黄石大道为贼生路,引我兵由西洪小路以入……”。侯熙就是当时莆田的参将,其所带之兵却通贼。倭寇中还有不少是漳、泉人。《戚少保年谱》载:“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率兵来援,刘屯江口不敢进。寇诈饰民求援于刘,刘以兵寡之故直示之,谓需募足始能进兵,寇遂知虚实。及召募令出,寇以漳泉变夷者什新募中,刘周不能察,反遣之入城助守,竟为内应”。从以上这些事实看,倭寇侵莆时,不但莆田有内奸,而所谓倭寇中也有不少是漳泉人,还有莆田人,很明显的,没有莆田人,倭寇如何能“饰良民求援于刘”。
二、明代在莆设置兵备防倭的一般情况
当明太祖整饬海防时,莆田也是确实设置了一些兵备的。洪武二十年(1387)令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整顿海防备倭。江夏侯还亲来莆田勘察地形,决定增筑城塞设置卫所,令兴化卫指挥佥事吕谦监筑平海、莆禧二城。平海城周围八百零六丈七尺,高二丈四尺,女墙一千三百一十,门四,东西各一,南二,曰大南门、小南门,形势北仰南俯,三面阻海不凿濠堑,以海为池,城北不置门,筑高台以资瞭望。莆禧城周围五百九十丈,高一丈九尺,女墙一千四十九,东南北三面阻海,西凿旱濠。又令吕谦督署本司事府吏张得清筑迎仙塞(现在的江口塞),本司巡检韩翱筑冲沁巡检司城,潘琏筑青山巡检司城,黄譛筑嵌头巡检司城,何拜帖木儿筑小屿巡检司城,胡启贤筑吉了巡检司城,这六处虽名叫城(塞),其周围只一百五十丈,但都驻兵巡察。城筑成后,又根据地理情况设墩台,发现敌人夜就举火,昼则举烟报警,计沿东南一路二十九处,正东路二十六处,东北路六处,共设墩台五十九处。并在南日设立水塞,巡哨南北海面。于是莆田就有了二卫、一所、六巡司、五十九墩台、一水塞。(当时全省只设十一卫、十三所、四十四巡司、三水塞)。卫设正三品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佥事四员,卫镇抚二员,皆世袭。二卫各分左右前后中五千户。守御千户所设正千户一员(五品),副千户二员,镇抚一员,皆世袭。千户所设百户十员,每百户总旗二人,每总旗小旗五名,每小旗军十名。于是莆田兴化和平海二卫(兴化卫洪武元年立)的卫军共一万两千三百七十八名,其中平海卫又分操屯旗军五千零三十九名,出海旗军一千一百五十名。每巡检司置巡检一员、兵一百名,各墩台委千百户一员置兵五名,以指挥一名提调之。
既设卫所,又立水寨,初在南日岛设寨,正统间(1436-1449)移入吉了澳牛门。水寨拨兴化、平海两卫旗军充为舟师,由卫拨指挥一员,总管所部三军,谓之卫总,又由卫选指挥一员,谓之把总节制卫总。舟师组织,其船有四百料者,有三百料者,有五十料者,大者谓之快船,小者谓之哨船。
兴化卫轮班把总指挥一员,千户以下官甲九员,军四百零五名,驾官快哨船九只。平海卫轮班把总指挥一员,千户以下官甲十员,军七百七十名,分驾快哨船十只。南北海洋哨捕百户六员,甲军二百六十六名,分驾快哨船六只守备双屿,又三江口设指挥一员,千户四员,百户三员,甲军二百一十八名,分驾官快船七只。是则有舟师一千六百六十二人,配备战船三十二只。陆上城堡墩台星罗棋布,海上驻有舟师巡哨南北海洋,可以说设防相当严密。但实际不是这种情况,卫所等虽设,守备却挂虚名,没有战斗力。明《弘治府志防御志》记:“国初诏民丁壮三令出防倭夫一,至是编成行伍,立平海卫五千户,又立莆禧守御一千户所隶平海卫,共军六千名。继而言事者讼本地军顾恋乡土,有误防守。二十五年乃以平海卫及莆禧守御千户所与镇海卫及铜山守御千户所对调。”就是说卫才设五年,就觉得本地兵有误防守,而换了客兵。客兵怎么样呢?至嘉靖倭祸起时客兵竟成了内奸,而且互相仇杀。
御史林润曾上疏请惩处客兵说:“寇在仙游已遁,竟有客兵至枫亭,戮良民二百余,冒充敌级以请赏。”士兵挂名吃饭不打仗,更是相沿为例。《弘治府志》载:“景泰以来,柄兵者建议凡临敌失一军以上,皆坐以失机罪,自是每遇敌,皆驱民以战,是军食粮而民受死也。此令当思有以通其变矣。”赤裸裸指出了当时的沿海倭备是:军士每月领饷吃饭,有寇警却驱百姓去打仗。成化后兵备更松了,每年都在各巡司内抽去名额,一个巡检司由原设一百名至弘治后剩下十八名,并且军士继续逃跑,所以及戚继光破倭后,就因“卫所军士多老弱瘦罢,选余丁补缺,裁并置营”,墩台也竟至没人管而被人拆毁。《弘治志》载:“今升平日久,烟不昼举,火不夜发,渐有睥睨台石而墙垣之者矣。”嘉靖间(1522-1566)倭寇来犯时,平海卫千户邱珍只能“令数十卒乘夜缒城,从间道鸣金鼓大呼寇至,郡人始知”,是墩台也无人举烽火了,因此,城堡、墩台、旗军、水师至明中叶就完全有名无实了。嘉靖倭寇陷城,要是没有戚继光募浙军来,俞大猷提赣军来,莆田还要陷在倭寇手里多久是很难说的。盖当时不单莆田兵备只徒有虚名,福建全省也是一样的兵备废弛。
三、倭寇扰莆及群众抗倭
倭寇祸莆先后十五次,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无法制止寇掠,加以奸民勾引外匪,官兵通倭,士兵与客兵又互相仇杀,内外交煎,群众遭官役兵祸甚惨。群众看到统治者的无能,有不少自动组织出而抗倭,给倭寇以很大的打击,但却都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和配合,有的更被通倭的官兵暗算、出卖,因而失败。
第一次,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二十六日(农历,以下同):寇驾船二十三艘,有二千余人,由平海舣岸,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率军开平海东门奋击,倭寇溃奔遁去。
第二次,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倭寇突来,兴化卫中所千户白仁在分巡姚凤翔指挥下,带领水军捕追倭寇至连盘四沃,和指挥丁桐并力奋击,生俘倭寇14人。
第三次,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一月中旬,倭寇登陆福清,聚集在海口。参将尹凤命令千户白仁率领所部兵先行,白仁直至柳尾列栅立阵,等待阻击。当时倭寇兵力要强得多,和白仁同时先行的其他所部都据险驻兵自保。白仁刺血立誓,表示抗倭的决心,士气大振,傍晚倭寇到,看到白仁士志激昂,阵容整齐,不敢前进。晚上派四人潜近白仁阵地窥探,被白仁巡获杀掉。倭寇就在当夜天色微明时潜从间道袭击白仁,当时白仁所部正在东岳庙口蓐食,见倭至立即接战,但因众寡悬殊,久战力困,其他所部又不敢前来支持,倭寇再潜兵一支从背后袭击,白仁遂被杀。
第四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平海卫左所正千户叶巨卿带领水军守泥沪沃,在南日塞巡哨,刚巧倭船数十将来偷袭。叶巨卿率水军迎风鏖战,生俘倭寇百余人(县志作十四人)。与此同时,泉州卫右所百户张养正在青山巡守也发觉倭船潜靠岸,被养正连射中三人才退去,但第二天倭寇又再登陆,养正奋前抵御,却因后军奔逃,没有援兵而被杀。
第五次,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半夜顺风偷袭泥沪沃,叶巨卿坚壁静守,于天微明带领所部迫倭力战牺牲。
第六次,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倭寇驾舟百余,乘晚雾企图潜登吉了沃,为我瞭探知道,水塞参军黎鹏举一面令炮台发炮阻击,一方面率哨船并发动商船、渔船共百余条投入战斗。当时正值雾开、潮落、风顺,倭船处境不利,急逃遁,我遂获得大胜。计击沉倭船三只,斩倭百余人,生俘八十七人,战迫溺海死的很多。这是群众第一次参加抗倭获得了大捷。
第七次,十一月倭寇又再来,数十条倭船沿我县海岸,焚掠劫杀滨海乡村,平海卫千户邱珍率领所部至冲要地游动阻击。倭寇无法靠岸,就潜至白湖,焚舟登陆。当时邱珍立即命数十卒乘夜缒城出来,从小路鸣金击鼓,大呼倭寇登陆,群众才知藏匿,郡城才知守御。倭寇知道莆城有备,偷袭不得,就退去,邱珍带轻骑数百人,追杀至海口,倭已破釜沉舟,就拼死战邱珍,邱珍却不幸坠马被倭槊死。这时是在严寒的冬夜,莆人林兆恩倡导劳军,送酒、粥、钱、米犒赏守兵。
这一年倭寇不但焚杀劫掠,还决毁海堤,致使田地受淹不能播种,已种作物也绝收。
第八次,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初十,倭寇千余人,由福清乘胜从三江口登陆,驻兵在新桥头。当时涵江、镇前、洋尾各乡被焚掠一空。十四日进迫莆田城,当时莆田已无兵可用。适时湖湘麻阳兵千人经过莆田,尚在城,林兆恩为保护城池,同各乡绅建议雇广兵御倭,就与广兵立字约,退倭后酬金二千两,广兵缒城奋击,斩真倭两人,倭寇退去。广兵于是向兆恩索酬金,乡绅弃约不肯出钱,兆恩自己拿一百两出,对广兵说无从再筹。广兵大怒,缚兆恩于演武场殴打,并迫其领至爽约的乡绅家中追索。兆恩说:“昔与汝等许盟千金,以图安此城也,今倭夷既退,汝等复肆掠,是仍乱此城也,乌乎可,吾宁死不为也”。乡绅知道后才受感动,就县先借官银二千两,即日交给广兵,广兵才去。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军”、“乡绅”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倭寇的祸民,“官”既知无力抵御倭寇,却不想办法,“军”抗倭却要用钱雇,“乡绅”虽有钱却不肯拔一毛。
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又有倭寇千余人由莆田县往福清天宝陂屯宿溪前马山等处。
第九次,嘉靖三十八年(1559)六月,倭寇又犯平海,官军迎击于峰头沃,倭遁走,一直追至野马外洋,再击溃之。
当时因为倭寇猖獗,各乡村备受蹂躏,郡城虽然也屡有警,但终有城池及卫兵守御没有被陷过,因此城外居民纷纷进城避倭,散处城中以及各处寺观不计其数,人挤至无处居住而据地寝宿的。有倭寇侦探从漳泉潜来,化装为道士,造谣惑众,说马榴精出现,昏晚能眯蛊妇女,须鸣金击鼓,书符让避。城中有妇女受恐吓昏倒的,具金买符的很多,后府官以左道逐之,才逃去。但城中谣言惑众之说仍甚多,如有人说:正月初一夜,城门锁泣,流血如注。有人说梦天上坠一火轮,中出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杀人,毁土纪,灭土城,重熙岁,见太平”。台风暴雨也认为是妖孽出现,人心惶惶,意识祸之将至。这时候的城乡情况是极为混乱的。
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来侵三次,“官兵”已完全不能抵御,当时的参将侯熙,是漳州人,所带的兵都是自己家乡的无赖,不但对倭不抗,而且通倭。都司白震带徭兵来,却又同本地兵互相仇杀,甚至放火烧南关外,烟焰迷天,烧两日才熄,侯白二人却袖手不管。兵内哄,倭寇就更纵横各地寇掠而没有顾忌了。城涵一带各乡皆被掠而至残破不堪,避乱入城者越来越多,晚上露宿,白天行乞的不计其数。群众明白了抗倭不能指望腐败的“官府”和放火的“官兵”了,于是自己组织起来,抗倭自卫。如芦浦乡(现在的濠浦)自倡组织乡团,群众动手筑堡,保卫自己家乡。倭寇多次进攻芦浦,都被击退。最后倭寇集中兵力强攻,众寡悬殊,芦浦危急,派人至城求援,“官府”却不管,参将侯熙登北城谯楼,立视芦浦被攻破。倭寇破芦浦,恨群众屡击败其兵,对芦浦群众进行大屠杀,海水为赤。芦浦距莆城只四、五里,“官兵”却不支持,致使群众抗倭力量终因无援力孤而失败。
第十三次,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倭寇由三江口登陆,聚集蔡坨、杭头等村。这时候莆田以及福清、惠安三县的各大村都潜伏倭寇间谍,莆田城被围不解,倭寇塞城濠上游水道,企图攻下城池,泊舟在城濠的的船户有千余人,以城濠被塞,水断交通也断。将影响其生计,于是自动向“官府”请愿,与倭寇决一死战,一鼓而歼灭倭寇百余人,倭寇已将败溃,可是通倭的侯熙兵却出而掩护倭兵,船民于是反胜为败被伤退走。群众的抗倭力量又被“官兵”出卖。又有华亭猎户(旧称虎匠)数百人,出而袭击驻杭头倭寇,还用毒弩射敌人,倭寇大败溃逃,移营在白杜。虎匠潜往埋伏,等待再歼倭寇,又被侯熙兵告密,倭寇转道潜在林莽中伏击猎户,被伤百余人,猎户回华亭,不再出来。这两支抗倭力量都被官兵出卖了。
至九月戚继光奉命援闽,在福清牛田击破倭寇后,其残余又遁来莆与在莆倭寇合,拟去惠安南辋。福清来的残寇因新败,不同意再远行,认为戚继光客兵不会久留,于是转踞莆城东二十里的林墩。林墩四面环河,通接海港,倭寇在这个险要地形上列栅踞守,又派遣降倭奸民四出侦察,作为耳目,而留四千多黠倭踞守巢穴。戚继光于九月十二日从福清急行军七十里,宿营烽头江口。分遣把总张谏、叶大正、金科、曹南金等带兵一千六百人与中军王辅、百户张元勋配合,留在烽头,限令十三日到涵头,十四日早到宁海桥,闻鼓即刻进攻。戚继光则亲督把总吴唯忠、胡大受、陈子銮、陈大受、王如龙、童子明等兵,在十三日偃旗息鼓潜由囊山间道抵莆城。当时士兵行军辛苦,拟在城外宿营,戚继光认为倭寇侦探分布很广,驻城外容易泄密。分守翁时器也以客兵远道来支援,不敢催促出兵进攻,戚继光说道:“歼穷寇与方张者不同,方张者势众,能分袭,须正以临之,使其狡不得逞,伤弓之鸟,迟则飏矣,所谓拙速,所谓速雷也”。于是傍晚入城,假意从容宴谒,表示不马上进兵,却于半夜传铃吃饭后,立即在东市集合,乘月由阳城、青浦至西洪。月还未落,就命令等待月落后进迫倭巢。天亮倭寇才发觉,尽集黠倭,列大队据小桥抵抗。这时戚继光发觉,原来向导通倭,留黄石大道给倭寇逃生之路,却引戚兵由西洪小路以入。西洪一带沟渠四布,小桥品列,只能鱼贯越河津涉沟堑,兵力不能施展,攻取不易。因之前哨官周能战死,首队三十四人及次队之兵,损失及半,血战一点多钟,三次都冲不上,于是士兵游水夺渡,当时张谏等也在宁海桥击倭兵背后,倭寇才惊退入巢穴。可是戚兵的后援数百人也被倭寇袭击而溃退,戚继光斩临阵脱逃的哨长刘武等十四人,后队才拼死奋战,击败倭兵。倭塞列靠水岸,狭巷委曲,经过短刃巷战,倭寇落水的千余。残余的逃至黄石的窑兜,从倭的漫山四散奔逃,真倭逃入瓦窑。戚兵以火药烧瓦窑,乘势杀入,杀俘很多。这一役,计斩首九百六十人,焚溺两千多人,生俘男女二十六人,救出被俘男女两千一百二十人,戚兵阵亡周能等六十九人。这次出兵很密,至报捷大家才知道。中午,奏凯回莆城,群众扶老携幼郊迎十里,道路为之充塞。十月十五日,戚继光班师回浙江,这是比较大规模歼灭倭寇的一个战役。
第十四次,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倭寇败遁入海,潜伏不动,但却极恨戚兵和不甘心失败。听到戚继光十月班师回浙江,大喜说:“戚老虎去矣,吾又何患”。就一支由上路陷福宁、政和,一支直逼莆田城。城被围困一个月,日夜盼望救兵不至。知府陈瑞龙亲自指挥守陴,命令无论乡绅士民,力能胜兵者,悉入兵籍。组织群众协力守城,日夜亲自巡游指挥,所以城虽久困却不陷。不幸瑞龙母卒,请求人来代理以便治丧,抚按留之。却因哀母和日夜指挥劳瘁卒。当陈瑞龙组织群众守城时,有不少群众来响应其号召,如陈延陛带其所组织的群众,进攻倭寇,一直至南沟牺牲;郡掾常白带群众缒西门出,伏击倭寇至牺牲。陈瑞龙死后,抚按令郡同知奚世亮摄府事。分守翁时器懦弱无谋,兼且城中粮食将尽,有饿死的,又瘟疫大起,有死不得棺葬的,种种原因的影响,守城就不如陈瑞龙时严密了,所以倭寇更嚣张。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率兵来救援,刘显却以兵寡为理由,屯江口桥不敢进。倭寇命降从的化装为群众,到江口假向刘显求援,刘显却实说兵少,俟再招募后进兵,于是虚实被倭探悉了。等到召募令一出,倭寇就派漳泉人能讲莆田话的,混入新募兵中,刘却一点也不知道,反派他们入莆城助守。入城助守的由把总率领,计两百人,背绣“天兵”二字,潜倭就混在中间,于是给倭寇送内应入城。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再派兵八人,穿天兵衣甲,送书给翁时器,被倭寇擒去,倭寇即穿其衣甲,持公牒骗得入城。知府奚世亮,通判李邦光有怀疑,翁时器不但不听,还令八人守北门,潜倭骗守城兵士说大兵约在晚上进攻倭寇,应该刁斗静俟。守城士兵信以为真,对守备表现松懈。当晚四鼓,守城士兵遂被杀,倭寇从城西北角四埔岭靠梯上城垛,一面从城下发铳炮。大家还认为大兵果然在城外交战,但一看沿城垛已经都是倭寇,抵抗已来不及了。倭寇一入城,便乘风放火,各处居民房屋和官廨都起火。翁分守、毕参将、李通判都越城逃跑,摄知府奚世亮、训导傅尧佐被杀死,莆田郡城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天微明时陷入倭寇手中。莆田郡城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被烧杀劫掠一空。
倭寇陷兴化城后,御史李邦珍上疏告急,诏令巡抚游震得待罪行间,又命谭纶抚闽,征召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提兵前来破倭。俞大猷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从江西昼夜兼程至。时郡城已陷二个月,各兵屡次被败,刘显、俞大猷各距倭五十里驻营,按兵不动,等待戚继光兵来。当时倭寇也以城中尸首枕藉,腥秽不堪,财物又焚掠已尽,听说戚继光兵将到,就弃郡城去,南下破崎头城,杀都指挥欧阳深,攻陷平海卫城,招北路各倭兵同据平海城。俞大猷移兵秀山,刘显移兵明山,划地列栅坚守,贼屡挑战,仍按兵不动,移缴催促戚继光兵。戚继光奉诏后,因兵少,就在义乌募兵,历时十六日募得兵万余人。派胡守仁等六支兵先行到闽。三月抵达建阳,游中丞促其进兵,守仁因未奉将令不听,将这问题驰报戚继光,戚继光也以孤兵不宜先入,写信给中丞请罢进兵议。戚继光于四月初八日抵闽,游中丞有责其太慢之意,戚说是因新兵随募随发,并于路上边行军边训练。十一月新中丞谭纶至,并委汪道昆监军。十三日戚兵抵达福清,倭寇得悉,半数以上驾船贿赂海上许朝光所领水师,许朝光纵其逃遁。当时还有真倭三千及附从移兵在渚林迤南许家村据险结巢,分兵赤崎山下联为犄角。戚继光一面向莆田进兵,一面请中丞谭纶亲自来莆,俾便对俞、戚、刘三军统一部署进兵。戚继光兵十七日趋烽头,十八日过黄石,十九日抵东亭,戚继光微服侦察倭营垒。二十日谭纶、汪道昆同到渚林会集三大营布置机宜。以戚继光当中哨,俞、刘所部分左右哨,为掎角之势,冲锋悬示赏二万两,定二十一日进攻。二十日夜四鼓,戚继光分三路衔枚进攻。至五党山侧岭,月光还很亮,就坐待月落,乘昧爽直迫倭巢,倭寇两千,前锋百余,乘马力拼冲突,鏖战一个多钟头,大败倭寇,追至许家大巢,四面合围血战,顺风纵火烧倭寇,倭巢尽扫。日午收兵,获得全胜,计擒斩倭寇两千四百五十一人。夺获器械三千九百六十一件,印信十五颗。在莆田平海等地被虏的男女三千多人全部得救还,戚兵只阵亡十六人。第二天中军总哨胡守仁等又分兵埋伏要道,追剿擒斩残寇一百七十一人,二十三日凯旋回莆城。
第十五次、十六次,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残余倭寇又大举扰骚福建,我莆平海、南日再发生倭警,戚继光遣兵分路清剿,义总金科、叶大正破倭寇于平海后潘及福宁、同峡,把总顾乔破倭于南日。寇掠未遂。
十一月初一,倭寇又驾舟十六艘登犯吾莆青山,复犯晋江、福宁、连江、惠安等海岸,戚继光分兵追击最终在仙游剿灭之。倭寇祸莆历二十余年,至此才平息。
四、倭寇在莆的杀掠破坏
倭寇骚扰之目的,主要是在于抢掠,因此,经受蹂躏地区,都被劫掠一空,其对各方面的破坏烧杀,都极残忍凶暴。莆田自嘉靖二十二年以后至三十四年(1543-1555),各乡村就已被蹂躏得残破不堪,到了四十二年(1563)莆城陷落,更是四野一空,惨不可言。
御史林润请恤三府(兴化、泉州、漳州)奏疏中这样写道:“兴化所属二县,编户共二百二十有余里。……今遭寇患之际,历八年于兹,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徙于他郡者,又不计其数。迩又各府疫病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为虚,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昔之一里十图,今所存者一、二图耳,昔之一图十甲,今所存者一二甲耳。”旧县志赋役志载:“莆在明朝划为四厢三十一里,二百九十四图,每图百一十户。至嘉靖时,图之存者一百七十四,户减八百九十,口减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一。”可见到资财大量被抢劫外,群众死于兵乱的数以万计,房屋被烧殆尽,农商之业也遭严重破坏。因此御史林润曾奏陈六事:“一建公廨门楼以定民心,二刈邻境县属以宽民力,三急筑修陂堰以预民食,四给农事种子以重民事,五请蠲免赋税以苏民困,六请发给官银以济民艰。”祸莆的具体惨况,大部分已湮灭无可考,但到现在还遗存的废墟以及局部的文字记载,已经可以使我们看到五百年前莆田人民所受的浩劫。
惨遭倭乱死的群众,嘉靖二十二年至三十九年(1543-1560),无记载可考。根据《林子(林兆恩)本行实录》:“嘉靖四十年(1561)冬命黄仕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直日佣工于城之内外舁尸,别男女而礼瘗于太平山者两千有奇身。”“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币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圜、平海僧净圆等十余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火而瘗之,文以奠之,约有五千余身。又命僧云章等至城外各乡,凡八月,约收万有余身,郡守陈公瑞龙捐金给米以赞助,而复表揭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鬻田得金,命献策与僧法从等十八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瘗于南北河尾二山,约有四千余身,又瘗余骨百有余担。……三月后,以鬻田之金,命朱禹雍文命等九人往崎头收尸,积薪火化,文以奠之,凡瘗于城外之山者八百余身,而拾遗骨无论。”单林兆恩就瘗尸五次,收埋全尸者三千余身,火化而葬的两万余,还有遗骨百余担之数,虽然其中包括疫疠死的,但其所收埋的应当是无人收的尸首,要是加上死难亲属收埋和其他方面瘗尸,其数将更惊人了。现在的龙琯、东华一带横亘黄石附近有所谓“九十九墩”,据说都是林兆恩埋尸的地方。单最后陷城的一次,旧志有记载的有署知府奚世亮,县丞叶时兰,郡掾常白,县学训导卢尧佐,兴化卫指挥张远,鲁师亮,千户张应望,进士以上的十七人,举人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群众被屠杀更不可胜计。城内外尸首枕藉,新郡守易道谭要来莆,途闻积尸盈野,停车福清,不敢莅任,及闻林兆恩收尸洒道,方入城。考志传和谱牒单就妇女被掳不从,自杀、被杀尚能找到记载的有五十一人,如下表:
倭寇屠杀手段也极残酷,如郑肇妻被洞胸死,黄河妻被割乳死,黄大廉女被削去五指后再刺死,林观文妻被执不从,将其投火中烧死,林承芳妻郑氏遇贼骂不从,被砍掉左手,刈去右耳再刈下鼻子,甚至有断舌、肢解、钉壁等残忍之屠杀手段,刘氏二姐妹不从贼投火自杀后,贼还以枪槊其胸,并立杀被掳者五人以泄怒。林润在奏请恤三府疏中还说:“倭不但屠生民,而且发掘坟冢,悬棺待赎。”
全县被焚毁房屋不可胜计,莆田独田尾安然里存,平海仅存圣庙。现在在莆田的田尾一带,靠北门的前埭一带,靠东门的书仓一带,黄石的水南一带,看到的颓垣废墟遗迹,都是在五百年前被倭焚毁的。我们就有记载下来的查出被烧的衙署祠院:在莆城有府县各署、县学府学、谯楼、瞻阙亭、莆阳驿、大有仓、督粮馆、岳公祠、二忠祠前堂、二烈祠、忠惠祠、林俊祠、彭韶祠、黄仲昭祠、林苇祠、凤山寺、东岩寺、光孝寺、广化寺;在平海的有平海衙署、平海仓;在涵江的有涵江书院、寿泽书院;自城至平海这一线,尚有厝柄朱柄书院、草鞋墩咸淳庵、黄石水南书院;自城至涵江这一线,还有澄渚林藻祠、紫宵山迎福院,以及涵江附近的囊山慈孝寺、上生寺等。从这个记载说明城、涵、黄石、平海之外,囊山、澄渚及紫霄地靠山区较偏僻地带,屋宇也被烧毁,可见不单是滨海平原的各乡被破坏,其蹂躏地区已接近山区。屋宇建筑物既被焚毁,典籍当然也不能免,被焚不知有多少,如郑岳著的《莆阳文献》,兵燹之后,只黄起龙家幸存一部。
水利亦尽为倭寇破坏,林润陈六事疏:“……次则各地陂堰,亦尽为倭寇所决,溪涧悉涸,海水冲流,沃野尽变为斥卤”。特别东角堤被倭寇拆毁后,海堤溃决,海水泛溢至城外。水利既毁,农民又没种子可播种,农业生产的受破坏,可想而知。
所以倭祸在莆田确是一个大灾难,在群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创痛。倭寇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陷城,至第二年(1563)正月二十九日才弃城去,这六十日亲朋戚友各顾逃生,彼此生死不明,几千年相沿一年一度的“团圆做岁”这年却被迫无家可归。因此,倭寇于正月廿九日退至平海后,群众陆续回来,并即于二月初二日至亲戚家中探视死亡情况,初五日补“做岁”。嘉靖四十三年(1564)开始,每年遂以正月初二日为探亡期,俗忌至亲戚人家探视,以正月初五日再过年,俗称“做大岁”,以示纪念沉痛的历史,至今不变。莆田倭祸,在全省全国来说也是倭寇扰华中较大事件之一,当莆城陷落时,八闽震动,调动浙江、江西、广西之兵,开支兵饷三十万两,首尾经六个月才在平海扫平倭寇。
五、善后的一些情况
莆倭祸平后,善后问题,虽有御史林润奏陈六事,但除城楼、衙署、儒学在易道谈任内就修建外,其他建筑至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始复旧观。农田水利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堤决水淹溢至城外”的记载看,是没有“急修筑陂堰以预民食”的(东角堤是第二年四月始修建)。至于“蠲赋税以纾民困,发官银以济民艰”也没有下文。裁并些里图实际却变成了一件害民的坏事。《莆风清籁集》存嘉靖中布衣游日益《未生曲》一首,其序说:
“嘉靖乙卯(1555)倭入寇莆中,大肆荼毒,四郊之外,将无噍类。至壬戌(1562)城陷,惨不可道。御史林公润疏请蠲租发赈,遗黎稍拯残喘。通判陈永者督编户口,伪增民数以媚上官,至立梦生、望生、未生之虚名,登之版籍,遗民饮恨,无所控诉。予卧病山中,闻之孤愤,作此以纪时事。”其诗云:
“烈火焚未熄,黄云愁极目,东市叹零丁,西村惨诛戮。崇墉卒不完,万马城中牧,白骨乱如麻,啾啾新鬼哭。梓泽尽圻墟,台史重颦蹙,三疏渎天朝,春风生槁木。别驾扬军威,里甲供兵粟,储赋以为常,任意乱增续。户丁唯寡妻,日日愁拘逐,有夫阵中亡,有子遗在腹,亡者名未除,胎者复上牍。胥魁诡我名,未生年十六,朝来实版图,暮来派钱谷。终岁饷官银,夫家遭鱼肉,从今誓不供,其奈多鞭搏,此身愿无生,宛转填沟壑。野夫闻叹息,对此泪盈掬,落日掩空扉,聊作未生曲”。
于此可见,莆田在倭祸之后,统治者所做的善后工作的一般。
(摘自莆田县县志编集委员会撰《莆田县志》草稿1963年11月)
一、倭寇的来历
考倭寇在唐代就有了。唐林披述刺史黄峰(按:应为黄岸)迁居云:“自桂州航海归,道颉洋,避倭兵,风浪飘荡,登延福山,爱山水之秀,因居焉。”又林藻行述云:“从南越海道归,见蒲田延福山山水之秀,因家焉。”南越就是现在的广东,延福山就是莆田县现在的囊山。可见唐时倭寇就出没沿海一带。但倭寇成为侵扰我国之外患,却还是在明代。盖自元至元到大德(1335-1368),三十余年持续对日本用兵后,日本同我国的关系就很紧张,禁其人民同我国通商,纵其边民侵扰我国沿海。元中叶后,其国分为南北朝,至明初,南并于北,遗臣流落海上,和海盗合伙,海盗之势更盛,屡次骚扰我国沿海各州县。明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即颁谕日本,努力改善中日关系,并派使臣持诏责问日本寇侵沿海的问题,日本不答。于是明太祖就在沿海整饬海防,置兵防倭。洪武二十年(1387),派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当时江夏侯到莆田相度地形,增筑平海、莆禧城寨,加强海防工作。至永乐初日本受明朝封赐,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埚后,于是寇掠才见稀少。莆田县也是从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倭寇在平海舣岸,被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击溃后,一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一百三十年中就都没有倭警。
至明中叶嘉靖二年(1523),中日通商决裂之后,倭祸才又开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记载:“世宗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诸道争贡。……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宋本中国人,投奔日本而归附日本者,此次竟充日本贡使来中国),先后至宁波,争长不相下。故事,番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而素卿狡,贿市舶太监先阅佐货,而宴又坐设上。设不平,遂与佐相雠杀,太监又以素卿故,阴助佐,授之兵器。而设众强,拒杀不已,遂毁嘉宾堂,劫东库,逐瑞佐及余姚江。佐奔绍兴,设追之城下,令缚佐出,不许,乃去,沿途杀掠至西霍山洋,杀捕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进、百户刘恩,又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杀百户胡源,浙中大震。”就是因为这一段纠纷,嘉靖下令罢市舶司,禁止对日通商。但是市舶司罢去,对日通商却禁不绝,沿海豪势之家仍同日本商人交通,日本海贾仍然往来自如,由此又再挑起了倭寇对沿海的骚扰。
《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又载:“自罢市舶后,凡番货至,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贵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没海上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迫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且复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因盘踞岛中不去。”所以嘉靖二年(1523)后,倭寇的骚掠就频繁起来了。山东、江苏、浙江受扰较早,及浙江巡抚胡宗宪招降毛海峰,计杀陈东、麻叶,复杀毛海峰、王直,浙江及江南的倭祸才平定。而其余党就窜来福建,于是倭祸中心移来福建。所以莆田受蹂躏最厉害的,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二年(1545)以后,而在嘉靖三十年至四十二年(1551-1563)特别严重。
所谓倭寇,日本人实际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很大部分是中国人和他们同伍,或入海同真倭一起为寇,或潜在大陆做奸细。祸莆倭寇中也有莆田人和漳泉人。莆田各地都潜有内奸。《明史》日本列传载:“大抵真倭十分之三,从倭者十分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惴怯,所至溃崩。”陈伦炯《海国见闻录》云:“倭寇者,萨峒马岛人也。其始市舶于永嘉,萨岛渔者十八人,被风吹入中国,奸人引以为乱,髡须矱额,什以旁近土语,递相攘掠,群称倭奴。”《皇清文献通考》说:“明代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之人居多。市舶所集,内奸勾引故也。”再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
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入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池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是奸民不唯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原注: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人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爪牙)。可见真倭是不多,内奸参加勾引,并互为耳目、爪牙。
《明史纪事本末》中《沿海倭乱》记载:“番人……盘踞海岛中不去,并海民生计困迫者纠引之,失职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与通,为之向导,时时寇掠沿海诸郡县。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华人,僭称王号,而其宗族妻子田庐,皆在籍无恙,莫敢谁何。”日本史也载:“明太祖欲通聘日本,道阻不通,当时日本边民侵明之沿海,明称倭寇,甚畏之,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遣使于明成祖,修邻交。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边陲诸侯亦各自通于明,得其勘合符,盛行贸易,明之奸商结连朝臣,给日本之商民,睹物不偿价,于是日本商民愤怒,剽掠其沿岸。当时足利氏威令不行,四方不逞之徒,皆集于明之海岸。明之臣不平者,亦来投,倭寇势益猖獗。嘉靖间最盛,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痛击之,破倭于平海卫,其难始止。”日本史的记载也与明史相同。可见所指倭寇,实际有日本人,也有我国人与之同伍。人数不但占大多数。而且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还称王。再从通倭的人来看,任何阶级都有,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凶徒、逸囚、流氓、无赖等都参与。
《嘉靖东南平倭录》载(见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寇,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浙东大震。至是巡按御史陈九德请置大臣,兼制浙、福,乃以朱纨为御史,巡抚浙江兼领福、兴、泉、漳。……时浮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诸达官家为之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纨因上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衣冠之盗难”。国内有“衣冠之盗”说得很明显。莆田受倭祸,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康大和《重建郡治记》云:“倭寇内侵,土民向导。”《戚少保年谱》及莆旧志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寇由三江口入屯,……是时福清、莆田、惠安三县各大村皆散布寇党”“……船户请郡愿各奋身决死战,一鼓而前,歼贼百余级,侯熙兵阴遮道翼贼,船户反胜为败,多伤退。又虎匠数百人入杭头,以毒矢中贼,贼大溃,移白杜,虎匠潜先往待之,侯兵密报贼。贼伏林莽中,虎匠被伤百余人”“……不意我兵为向导所误,缘向导皆与贼通,特留黄石大道为贼生路,引我兵由西洪小路以入……”。侯熙就是当时莆田的参将,其所带之兵却通贼。倭寇中还有不少是漳、泉人。《戚少保年谱》载:“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率兵来援,刘屯江口不敢进。寇诈饰民求援于刘,刘以兵寡之故直示之,谓需募足始能进兵,寇遂知虚实。及召募令出,寇以漳泉变夷者什新募中,刘周不能察,反遣之入城助守,竟为内应”。从以上这些事实看,倭寇侵莆时,不但莆田有内奸,而所谓倭寇中也有不少是漳泉人,还有莆田人,很明显的,没有莆田人,倭寇如何能“饰良民求援于刘”。
二、明代在莆设置兵备防倭的一般情况
当明太祖整饬海防时,莆田也是确实设置了一些兵备的。洪武二十年(1387)令江夏侯周德兴来福建整顿海防备倭。江夏侯还亲来莆田勘察地形,决定增筑城塞设置卫所,令兴化卫指挥佥事吕谦监筑平海、莆禧二城。平海城周围八百零六丈七尺,高二丈四尺,女墙一千三百一十,门四,东西各一,南二,曰大南门、小南门,形势北仰南俯,三面阻海不凿濠堑,以海为池,城北不置门,筑高台以资瞭望。莆禧城周围五百九十丈,高一丈九尺,女墙一千四十九,东南北三面阻海,西凿旱濠。又令吕谦督署本司事府吏张得清筑迎仙塞(现在的江口塞),本司巡检韩翱筑冲沁巡检司城,潘琏筑青山巡检司城,黄譛筑嵌头巡检司城,何拜帖木儿筑小屿巡检司城,胡启贤筑吉了巡检司城,这六处虽名叫城(塞),其周围只一百五十丈,但都驻兵巡察。城筑成后,又根据地理情况设墩台,发现敌人夜就举火,昼则举烟报警,计沿东南一路二十九处,正东路二十六处,东北路六处,共设墩台五十九处。并在南日设立水塞,巡哨南北海面。于是莆田就有了二卫、一所、六巡司、五十九墩台、一水塞。(当时全省只设十一卫、十三所、四十四巡司、三水塞)。卫设正三品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佥事四员,卫镇抚二员,皆世袭。二卫各分左右前后中五千户。守御千户所设正千户一员(五品),副千户二员,镇抚一员,皆世袭。千户所设百户十员,每百户总旗二人,每总旗小旗五名,每小旗军十名。于是莆田兴化和平海二卫(兴化卫洪武元年立)的卫军共一万两千三百七十八名,其中平海卫又分操屯旗军五千零三十九名,出海旗军一千一百五十名。每巡检司置巡检一员、兵一百名,各墩台委千百户一员置兵五名,以指挥一名提调之。
既设卫所,又立水寨,初在南日岛设寨,正统间(1436-1449)移入吉了澳牛门。水寨拨兴化、平海两卫旗军充为舟师,由卫拨指挥一员,总管所部三军,谓之卫总,又由卫选指挥一员,谓之把总节制卫总。舟师组织,其船有四百料者,有三百料者,有五十料者,大者谓之快船,小者谓之哨船。
兴化卫轮班把总指挥一员,千户以下官甲九员,军四百零五名,驾官快哨船九只。平海卫轮班把总指挥一员,千户以下官甲十员,军七百七十名,分驾快哨船十只。南北海洋哨捕百户六员,甲军二百六十六名,分驾快哨船六只守备双屿,又三江口设指挥一员,千户四员,百户三员,甲军二百一十八名,分驾官快船七只。是则有舟师一千六百六十二人,配备战船三十二只。陆上城堡墩台星罗棋布,海上驻有舟师巡哨南北海洋,可以说设防相当严密。但实际不是这种情况,卫所等虽设,守备却挂虚名,没有战斗力。明《弘治府志防御志》记:“国初诏民丁壮三令出防倭夫一,至是编成行伍,立平海卫五千户,又立莆禧守御一千户所隶平海卫,共军六千名。继而言事者讼本地军顾恋乡土,有误防守。二十五年乃以平海卫及莆禧守御千户所与镇海卫及铜山守御千户所对调。”就是说卫才设五年,就觉得本地兵有误防守,而换了客兵。客兵怎么样呢?至嘉靖倭祸起时客兵竟成了内奸,而且互相仇杀。
御史林润曾上疏请惩处客兵说:“寇在仙游已遁,竟有客兵至枫亭,戮良民二百余,冒充敌级以请赏。”士兵挂名吃饭不打仗,更是相沿为例。《弘治府志》载:“景泰以来,柄兵者建议凡临敌失一军以上,皆坐以失机罪,自是每遇敌,皆驱民以战,是军食粮而民受死也。此令当思有以通其变矣。”赤裸裸指出了当时的沿海倭备是:军士每月领饷吃饭,有寇警却驱百姓去打仗。成化后兵备更松了,每年都在各巡司内抽去名额,一个巡检司由原设一百名至弘治后剩下十八名,并且军士继续逃跑,所以及戚继光破倭后,就因“卫所军士多老弱瘦罢,选余丁补缺,裁并置营”,墩台也竟至没人管而被人拆毁。《弘治志》载:“今升平日久,烟不昼举,火不夜发,渐有睥睨台石而墙垣之者矣。”嘉靖间(1522-1566)倭寇来犯时,平海卫千户邱珍只能“令数十卒乘夜缒城,从间道鸣金鼓大呼寇至,郡人始知”,是墩台也无人举烽火了,因此,城堡、墩台、旗军、水师至明中叶就完全有名无实了。嘉靖倭寇陷城,要是没有戚继光募浙军来,俞大猷提赣军来,莆田还要陷在倭寇手里多久是很难说的。盖当时不单莆田兵备只徒有虚名,福建全省也是一样的兵备废弛。
三、倭寇扰莆及群众抗倭
倭寇祸莆先后十五次,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无法制止寇掠,加以奸民勾引外匪,官兵通倭,士兵与客兵又互相仇杀,内外交煎,群众遭官役兵祸甚惨。群众看到统治者的无能,有不少自动组织出而抗倭,给倭寇以很大的打击,但却都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和配合,有的更被通倭的官兵暗算、出卖,因而失败。
第一次,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二十六日(农历,以下同):寇驾船二十三艘,有二千余人,由平海舣岸,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率军开平海东门奋击,倭寇溃奔遁去。
第二次,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倭寇突来,兴化卫中所千户白仁在分巡姚凤翔指挥下,带领水军捕追倭寇至连盘四沃,和指挥丁桐并力奋击,生俘倭寇14人。
第三次,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一月中旬,倭寇登陆福清,聚集在海口。参将尹凤命令千户白仁率领所部兵先行,白仁直至柳尾列栅立阵,等待阻击。当时倭寇兵力要强得多,和白仁同时先行的其他所部都据险驻兵自保。白仁刺血立誓,表示抗倭的决心,士气大振,傍晚倭寇到,看到白仁士志激昂,阵容整齐,不敢前进。晚上派四人潜近白仁阵地窥探,被白仁巡获杀掉。倭寇就在当夜天色微明时潜从间道袭击白仁,当时白仁所部正在东岳庙口蓐食,见倭至立即接战,但因众寡悬殊,久战力困,其他所部又不敢前来支持,倭寇再潜兵一支从背后袭击,白仁遂被杀。
第四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平海卫左所正千户叶巨卿带领水军守泥沪沃,在南日塞巡哨,刚巧倭船数十将来偷袭。叶巨卿率水军迎风鏖战,生俘倭寇百余人(县志作十四人)。与此同时,泉州卫右所百户张养正在青山巡守也发觉倭船潜靠岸,被养正连射中三人才退去,但第二天倭寇又再登陆,养正奋前抵御,却因后军奔逃,没有援兵而被杀。
第五次,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半夜顺风偷袭泥沪沃,叶巨卿坚壁静守,于天微明带领所部迫倭力战牺牲。
第六次,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倭寇驾舟百余,乘晚雾企图潜登吉了沃,为我瞭探知道,水塞参军黎鹏举一面令炮台发炮阻击,一方面率哨船并发动商船、渔船共百余条投入战斗。当时正值雾开、潮落、风顺,倭船处境不利,急逃遁,我遂获得大胜。计击沉倭船三只,斩倭百余人,生俘八十七人,战迫溺海死的很多。这是群众第一次参加抗倭获得了大捷。
第七次,十一月倭寇又再来,数十条倭船沿我县海岸,焚掠劫杀滨海乡村,平海卫千户邱珍率领所部至冲要地游动阻击。倭寇无法靠岸,就潜至白湖,焚舟登陆。当时邱珍立即命数十卒乘夜缒城出来,从小路鸣金击鼓,大呼倭寇登陆,群众才知藏匿,郡城才知守御。倭寇知道莆城有备,偷袭不得,就退去,邱珍带轻骑数百人,追杀至海口,倭已破釜沉舟,就拼死战邱珍,邱珍却不幸坠马被倭槊死。这时是在严寒的冬夜,莆人林兆恩倡导劳军,送酒、粥、钱、米犒赏守兵。
这一年倭寇不但焚杀劫掠,还决毁海堤,致使田地受淹不能播种,已种作物也绝收。
第八次,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初十,倭寇千余人,由福清乘胜从三江口登陆,驻兵在新桥头。当时涵江、镇前、洋尾各乡被焚掠一空。十四日进迫莆田城,当时莆田已无兵可用。适时湖湘麻阳兵千人经过莆田,尚在城,林兆恩为保护城池,同各乡绅建议雇广兵御倭,就与广兵立字约,退倭后酬金二千两,广兵缒城奋击,斩真倭两人,倭寇退去。广兵于是向兆恩索酬金,乡绅弃约不肯出钱,兆恩自己拿一百两出,对广兵说无从再筹。广兵大怒,缚兆恩于演武场殴打,并迫其领至爽约的乡绅家中追索。兆恩说:“昔与汝等许盟千金,以图安此城也,今倭夷既退,汝等复肆掠,是仍乱此城也,乌乎可,吾宁死不为也”。乡绅知道后才受感动,就县先借官银二千两,即日交给广兵,广兵才去。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军”、“乡绅”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倭寇的祸民,“官”既知无力抵御倭寇,却不想办法,“军”抗倭却要用钱雇,“乡绅”虽有钱却不肯拔一毛。
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又有倭寇千余人由莆田县往福清天宝陂屯宿溪前马山等处。
第九次,嘉靖三十八年(1559)六月,倭寇又犯平海,官军迎击于峰头沃,倭遁走,一直追至野马外洋,再击溃之。
当时因为倭寇猖獗,各乡村备受蹂躏,郡城虽然也屡有警,但终有城池及卫兵守御没有被陷过,因此城外居民纷纷进城避倭,散处城中以及各处寺观不计其数,人挤至无处居住而据地寝宿的。有倭寇侦探从漳泉潜来,化装为道士,造谣惑众,说马榴精出现,昏晚能眯蛊妇女,须鸣金击鼓,书符让避。城中有妇女受恐吓昏倒的,具金买符的很多,后府官以左道逐之,才逃去。但城中谣言惑众之说仍甚多,如有人说:正月初一夜,城门锁泣,流血如注。有人说梦天上坠一火轮,中出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杀人,毁土纪,灭土城,重熙岁,见太平”。台风暴雨也认为是妖孽出现,人心惶惶,意识祸之将至。这时候的城乡情况是极为混乱的。
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来侵三次,“官兵”已完全不能抵御,当时的参将侯熙,是漳州人,所带的兵都是自己家乡的无赖,不但对倭不抗,而且通倭。都司白震带徭兵来,却又同本地兵互相仇杀,甚至放火烧南关外,烟焰迷天,烧两日才熄,侯白二人却袖手不管。兵内哄,倭寇就更纵横各地寇掠而没有顾忌了。城涵一带各乡皆被掠而至残破不堪,避乱入城者越来越多,晚上露宿,白天行乞的不计其数。群众明白了抗倭不能指望腐败的“官府”和放火的“官兵”了,于是自己组织起来,抗倭自卫。如芦浦乡(现在的濠浦)自倡组织乡团,群众动手筑堡,保卫自己家乡。倭寇多次进攻芦浦,都被击退。最后倭寇集中兵力强攻,众寡悬殊,芦浦危急,派人至城求援,“官府”却不管,参将侯熙登北城谯楼,立视芦浦被攻破。倭寇破芦浦,恨群众屡击败其兵,对芦浦群众进行大屠杀,海水为赤。芦浦距莆城只四、五里,“官兵”却不支持,致使群众抗倭力量终因无援力孤而失败。
第十三次,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倭寇由三江口登陆,聚集蔡坨、杭头等村。这时候莆田以及福清、惠安三县的各大村都潜伏倭寇间谍,莆田城被围不解,倭寇塞城濠上游水道,企图攻下城池,泊舟在城濠的的船户有千余人,以城濠被塞,水断交通也断。将影响其生计,于是自动向“官府”请愿,与倭寇决一死战,一鼓而歼灭倭寇百余人,倭寇已将败溃,可是通倭的侯熙兵却出而掩护倭兵,船民于是反胜为败被伤退走。群众的抗倭力量又被“官兵”出卖。又有华亭猎户(旧称虎匠)数百人,出而袭击驻杭头倭寇,还用毒弩射敌人,倭寇大败溃逃,移营在白杜。虎匠潜往埋伏,等待再歼倭寇,又被侯熙兵告密,倭寇转道潜在林莽中伏击猎户,被伤百余人,猎户回华亭,不再出来。这两支抗倭力量都被官兵出卖了。
至九月戚继光奉命援闽,在福清牛田击破倭寇后,其残余又遁来莆与在莆倭寇合,拟去惠安南辋。福清来的残寇因新败,不同意再远行,认为戚继光客兵不会久留,于是转踞莆城东二十里的林墩。林墩四面环河,通接海港,倭寇在这个险要地形上列栅踞守,又派遣降倭奸民四出侦察,作为耳目,而留四千多黠倭踞守巢穴。戚继光于九月十二日从福清急行军七十里,宿营烽头江口。分遣把总张谏、叶大正、金科、曹南金等带兵一千六百人与中军王辅、百户张元勋配合,留在烽头,限令十三日到涵头,十四日早到宁海桥,闻鼓即刻进攻。戚继光则亲督把总吴唯忠、胡大受、陈子銮、陈大受、王如龙、童子明等兵,在十三日偃旗息鼓潜由囊山间道抵莆城。当时士兵行军辛苦,拟在城外宿营,戚继光认为倭寇侦探分布很广,驻城外容易泄密。分守翁时器也以客兵远道来支援,不敢催促出兵进攻,戚继光说道:“歼穷寇与方张者不同,方张者势众,能分袭,须正以临之,使其狡不得逞,伤弓之鸟,迟则飏矣,所谓拙速,所谓速雷也”。于是傍晚入城,假意从容宴谒,表示不马上进兵,却于半夜传铃吃饭后,立即在东市集合,乘月由阳城、青浦至西洪。月还未落,就命令等待月落后进迫倭巢。天亮倭寇才发觉,尽集黠倭,列大队据小桥抵抗。这时戚继光发觉,原来向导通倭,留黄石大道给倭寇逃生之路,却引戚兵由西洪小路以入。西洪一带沟渠四布,小桥品列,只能鱼贯越河津涉沟堑,兵力不能施展,攻取不易。因之前哨官周能战死,首队三十四人及次队之兵,损失及半,血战一点多钟,三次都冲不上,于是士兵游水夺渡,当时张谏等也在宁海桥击倭兵背后,倭寇才惊退入巢穴。可是戚兵的后援数百人也被倭寇袭击而溃退,戚继光斩临阵脱逃的哨长刘武等十四人,后队才拼死奋战,击败倭兵。倭塞列靠水岸,狭巷委曲,经过短刃巷战,倭寇落水的千余。残余的逃至黄石的窑兜,从倭的漫山四散奔逃,真倭逃入瓦窑。戚兵以火药烧瓦窑,乘势杀入,杀俘很多。这一役,计斩首九百六十人,焚溺两千多人,生俘男女二十六人,救出被俘男女两千一百二十人,戚兵阵亡周能等六十九人。这次出兵很密,至报捷大家才知道。中午,奏凯回莆城,群众扶老携幼郊迎十里,道路为之充塞。十月十五日,戚继光班师回浙江,这是比较大规模歼灭倭寇的一个战役。
第十四次,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倭寇败遁入海,潜伏不动,但却极恨戚兵和不甘心失败。听到戚继光十月班师回浙江,大喜说:“戚老虎去矣,吾又何患”。就一支由上路陷福宁、政和,一支直逼莆田城。城被围困一个月,日夜盼望救兵不至。知府陈瑞龙亲自指挥守陴,命令无论乡绅士民,力能胜兵者,悉入兵籍。组织群众协力守城,日夜亲自巡游指挥,所以城虽久困却不陷。不幸瑞龙母卒,请求人来代理以便治丧,抚按留之。却因哀母和日夜指挥劳瘁卒。当陈瑞龙组织群众守城时,有不少群众来响应其号召,如陈延陛带其所组织的群众,进攻倭寇,一直至南沟牺牲;郡掾常白带群众缒西门出,伏击倭寇至牺牲。陈瑞龙死后,抚按令郡同知奚世亮摄府事。分守翁时器懦弱无谋,兼且城中粮食将尽,有饿死的,又瘟疫大起,有死不得棺葬的,种种原因的影响,守城就不如陈瑞龙时严密了,所以倭寇更嚣张。巡抚游震德遣总兵刘显率兵来救援,刘显却以兵寡为理由,屯江口桥不敢进。倭寇命降从的化装为群众,到江口假向刘显求援,刘显却实说兵少,俟再招募后进兵,于是虚实被倭探悉了。等到召募令一出,倭寇就派漳泉人能讲莆田话的,混入新募兵中,刘却一点也不知道,反派他们入莆城助守。入城助守的由把总率领,计两百人,背绣“天兵”二字,潜倭就混在中间,于是给倭寇送内应入城。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再派兵八人,穿天兵衣甲,送书给翁时器,被倭寇擒去,倭寇即穿其衣甲,持公牒骗得入城。知府奚世亮,通判李邦光有怀疑,翁时器不但不听,还令八人守北门,潜倭骗守城兵士说大兵约在晚上进攻倭寇,应该刁斗静俟。守城士兵信以为真,对守备表现松懈。当晚四鼓,守城士兵遂被杀,倭寇从城西北角四埔岭靠梯上城垛,一面从城下发铳炮。大家还认为大兵果然在城外交战,但一看沿城垛已经都是倭寇,抵抗已来不及了。倭寇一入城,便乘风放火,各处居民房屋和官廨都起火。翁分守、毕参将、李通判都越城逃跑,摄知府奚世亮、训导傅尧佐被杀死,莆田郡城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天微明时陷入倭寇手中。莆田郡城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被烧杀劫掠一空。
倭寇陷兴化城后,御史李邦珍上疏告急,诏令巡抚游震得待罪行间,又命谭纶抚闽,征召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提兵前来破倭。俞大猷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从江西昼夜兼程至。时郡城已陷二个月,各兵屡次被败,刘显、俞大猷各距倭五十里驻营,按兵不动,等待戚继光兵来。当时倭寇也以城中尸首枕藉,腥秽不堪,财物又焚掠已尽,听说戚继光兵将到,就弃郡城去,南下破崎头城,杀都指挥欧阳深,攻陷平海卫城,招北路各倭兵同据平海城。俞大猷移兵秀山,刘显移兵明山,划地列栅坚守,贼屡挑战,仍按兵不动,移缴催促戚继光兵。戚继光奉诏后,因兵少,就在义乌募兵,历时十六日募得兵万余人。派胡守仁等六支兵先行到闽。三月抵达建阳,游中丞促其进兵,守仁因未奉将令不听,将这问题驰报戚继光,戚继光也以孤兵不宜先入,写信给中丞请罢进兵议。戚继光于四月初八日抵闽,游中丞有责其太慢之意,戚说是因新兵随募随发,并于路上边行军边训练。十一月新中丞谭纶至,并委汪道昆监军。十三日戚兵抵达福清,倭寇得悉,半数以上驾船贿赂海上许朝光所领水师,许朝光纵其逃遁。当时还有真倭三千及附从移兵在渚林迤南许家村据险结巢,分兵赤崎山下联为犄角。戚继光一面向莆田进兵,一面请中丞谭纶亲自来莆,俾便对俞、戚、刘三军统一部署进兵。戚继光兵十七日趋烽头,十八日过黄石,十九日抵东亭,戚继光微服侦察倭营垒。二十日谭纶、汪道昆同到渚林会集三大营布置机宜。以戚继光当中哨,俞、刘所部分左右哨,为掎角之势,冲锋悬示赏二万两,定二十一日进攻。二十日夜四鼓,戚继光分三路衔枚进攻。至五党山侧岭,月光还很亮,就坐待月落,乘昧爽直迫倭巢,倭寇两千,前锋百余,乘马力拼冲突,鏖战一个多钟头,大败倭寇,追至许家大巢,四面合围血战,顺风纵火烧倭寇,倭巢尽扫。日午收兵,获得全胜,计擒斩倭寇两千四百五十一人。夺获器械三千九百六十一件,印信十五颗。在莆田平海等地被虏的男女三千多人全部得救还,戚兵只阵亡十六人。第二天中军总哨胡守仁等又分兵埋伏要道,追剿擒斩残寇一百七十一人,二十三日凯旋回莆城。
第十五次、十六次,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残余倭寇又大举扰骚福建,我莆平海、南日再发生倭警,戚继光遣兵分路清剿,义总金科、叶大正破倭寇于平海后潘及福宁、同峡,把总顾乔破倭于南日。寇掠未遂。
十一月初一,倭寇又驾舟十六艘登犯吾莆青山,复犯晋江、福宁、连江、惠安等海岸,戚继光分兵追击最终在仙游剿灭之。倭寇祸莆历二十余年,至此才平息。
四、倭寇在莆的杀掠破坏
倭寇骚扰之目的,主要是在于抢掠,因此,经受蹂躏地区,都被劫掠一空,其对各方面的破坏烧杀,都极残忍凶暴。莆田自嘉靖二十二年以后至三十四年(1543-1555),各乡村就已被蹂躏得残破不堪,到了四十二年(1563)莆城陷落,更是四野一空,惨不可言。
御史林润请恤三府(兴化、泉州、漳州)奏疏中这样写道:“兴化所属二县,编户共二百二十有余里。……今遭寇患之际,历八年于兹,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徙于他郡者,又不计其数。迩又各府疫病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为虚,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昔之一里十图,今所存者一、二图耳,昔之一图十甲,今所存者一二甲耳。”旧县志赋役志载:“莆在明朝划为四厢三十一里,二百九十四图,每图百一十户。至嘉靖时,图之存者一百七十四,户减八百九十,口减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一。”可见到资财大量被抢劫外,群众死于兵乱的数以万计,房屋被烧殆尽,农商之业也遭严重破坏。因此御史林润曾奏陈六事:“一建公廨门楼以定民心,二刈邻境县属以宽民力,三急筑修陂堰以预民食,四给农事种子以重民事,五请蠲免赋税以苏民困,六请发给官银以济民艰。”祸莆的具体惨况,大部分已湮灭无可考,但到现在还遗存的废墟以及局部的文字记载,已经可以使我们看到五百年前莆田人民所受的浩劫。
惨遭倭乱死的群众,嘉靖二十二年至三十九年(1543-1560),无记载可考。根据《林子(林兆恩)本行实录》:“嘉靖四十年(1561)冬命黄仕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直日佣工于城之内外舁尸,别男女而礼瘗于太平山者两千有奇身。”“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币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圜、平海僧净圆等十余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火而瘗之,文以奠之,约有五千余身。又命僧云章等至城外各乡,凡八月,约收万有余身,郡守陈公瑞龙捐金给米以赞助,而复表揭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鬻田得金,命献策与僧法从等十八人,在莆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瘗于南北河尾二山,约有四千余身,又瘗余骨百有余担。……三月后,以鬻田之金,命朱禹雍文命等九人往崎头收尸,积薪火化,文以奠之,凡瘗于城外之山者八百余身,而拾遗骨无论。”单林兆恩就瘗尸五次,收埋全尸者三千余身,火化而葬的两万余,还有遗骨百余担之数,虽然其中包括疫疠死的,但其所收埋的应当是无人收的尸首,要是加上死难亲属收埋和其他方面瘗尸,其数将更惊人了。现在的龙琯、东华一带横亘黄石附近有所谓“九十九墩”,据说都是林兆恩埋尸的地方。单最后陷城的一次,旧志有记载的有署知府奚世亮,县丞叶时兰,郡掾常白,县学训导卢尧佐,兴化卫指挥张远,鲁师亮,千户张应望,进士以上的十七人,举人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群众被屠杀更不可胜计。城内外尸首枕藉,新郡守易道谭要来莆,途闻积尸盈野,停车福清,不敢莅任,及闻林兆恩收尸洒道,方入城。考志传和谱牒单就妇女被掳不从,自杀、被杀尚能找到记载的有五十一人,如下表:
倭寇屠杀手段也极残酷,如郑肇妻被洞胸死,黄河妻被割乳死,黄大廉女被削去五指后再刺死,林观文妻被执不从,将其投火中烧死,林承芳妻郑氏遇贼骂不从,被砍掉左手,刈去右耳再刈下鼻子,甚至有断舌、肢解、钉壁等残忍之屠杀手段,刘氏二姐妹不从贼投火自杀后,贼还以枪槊其胸,并立杀被掳者五人以泄怒。林润在奏请恤三府疏中还说:“倭不但屠生民,而且发掘坟冢,悬棺待赎。”
全县被焚毁房屋不可胜计,莆田独田尾安然里存,平海仅存圣庙。现在在莆田的田尾一带,靠北门的前埭一带,靠东门的书仓一带,黄石的水南一带,看到的颓垣废墟遗迹,都是在五百年前被倭焚毁的。我们就有记载下来的查出被烧的衙署祠院:在莆城有府县各署、县学府学、谯楼、瞻阙亭、莆阳驿、大有仓、督粮馆、岳公祠、二忠祠前堂、二烈祠、忠惠祠、林俊祠、彭韶祠、黄仲昭祠、林苇祠、凤山寺、东岩寺、光孝寺、广化寺;在平海的有平海衙署、平海仓;在涵江的有涵江书院、寿泽书院;自城至平海这一线,尚有厝柄朱柄书院、草鞋墩咸淳庵、黄石水南书院;自城至涵江这一线,还有澄渚林藻祠、紫宵山迎福院,以及涵江附近的囊山慈孝寺、上生寺等。从这个记载说明城、涵、黄石、平海之外,囊山、澄渚及紫霄地靠山区较偏僻地带,屋宇也被烧毁,可见不单是滨海平原的各乡被破坏,其蹂躏地区已接近山区。屋宇建筑物既被焚毁,典籍当然也不能免,被焚不知有多少,如郑岳著的《莆阳文献》,兵燹之后,只黄起龙家幸存一部。
水利亦尽为倭寇破坏,林润陈六事疏:“……次则各地陂堰,亦尽为倭寇所决,溪涧悉涸,海水冲流,沃野尽变为斥卤”。特别东角堤被倭寇拆毁后,海堤溃决,海水泛溢至城外。水利既毁,农民又没种子可播种,农业生产的受破坏,可想而知。
所以倭祸在莆田确是一个大灾难,在群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创痛。倭寇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陷城,至第二年(1563)正月二十九日才弃城去,这六十日亲朋戚友各顾逃生,彼此生死不明,几千年相沿一年一度的“团圆做岁”这年却被迫无家可归。因此,倭寇于正月廿九日退至平海后,群众陆续回来,并即于二月初二日至亲戚家中探视死亡情况,初五日补“做岁”。嘉靖四十三年(1564)开始,每年遂以正月初二日为探亡期,俗忌至亲戚人家探视,以正月初五日再过年,俗称“做大岁”,以示纪念沉痛的历史,至今不变。莆田倭祸,在全省全国来说也是倭寇扰华中较大事件之一,当莆城陷落时,八闽震动,调动浙江、江西、广西之兵,开支兵饷三十万两,首尾经六个月才在平海扫平倭寇。
五、善后的一些情况
莆倭祸平后,善后问题,虽有御史林润奏陈六事,但除城楼、衙署、儒学在易道谈任内就修建外,其他建筑至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始复旧观。农田水利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堤决水淹溢至城外”的记载看,是没有“急修筑陂堰以预民食”的(东角堤是第二年四月始修建)。至于“蠲赋税以纾民困,发官银以济民艰”也没有下文。裁并些里图实际却变成了一件害民的坏事。《莆风清籁集》存嘉靖中布衣游日益《未生曲》一首,其序说:
“嘉靖乙卯(1555)倭入寇莆中,大肆荼毒,四郊之外,将无噍类。至壬戌(1562)城陷,惨不可道。御史林公润疏请蠲租发赈,遗黎稍拯残喘。通判陈永者督编户口,伪增民数以媚上官,至立梦生、望生、未生之虚名,登之版籍,遗民饮恨,无所控诉。予卧病山中,闻之孤愤,作此以纪时事。”其诗云:
“烈火焚未熄,黄云愁极目,东市叹零丁,西村惨诛戮。崇墉卒不完,万马城中牧,白骨乱如麻,啾啾新鬼哭。梓泽尽圻墟,台史重颦蹙,三疏渎天朝,春风生槁木。别驾扬军威,里甲供兵粟,储赋以为常,任意乱增续。户丁唯寡妻,日日愁拘逐,有夫阵中亡,有子遗在腹,亡者名未除,胎者复上牍。胥魁诡我名,未生年十六,朝来实版图,暮来派钱谷。终岁饷官银,夫家遭鱼肉,从今誓不供,其奈多鞭搏,此身愿无生,宛转填沟壑。野夫闻叹息,对此泪盈掬,落日掩空扉,聊作未生曲”。
于此可见,莆田在倭祸之后,统治者所做的善后工作的一般。
(摘自莆田县县志编集委员会撰《莆田县志》草稿1963年11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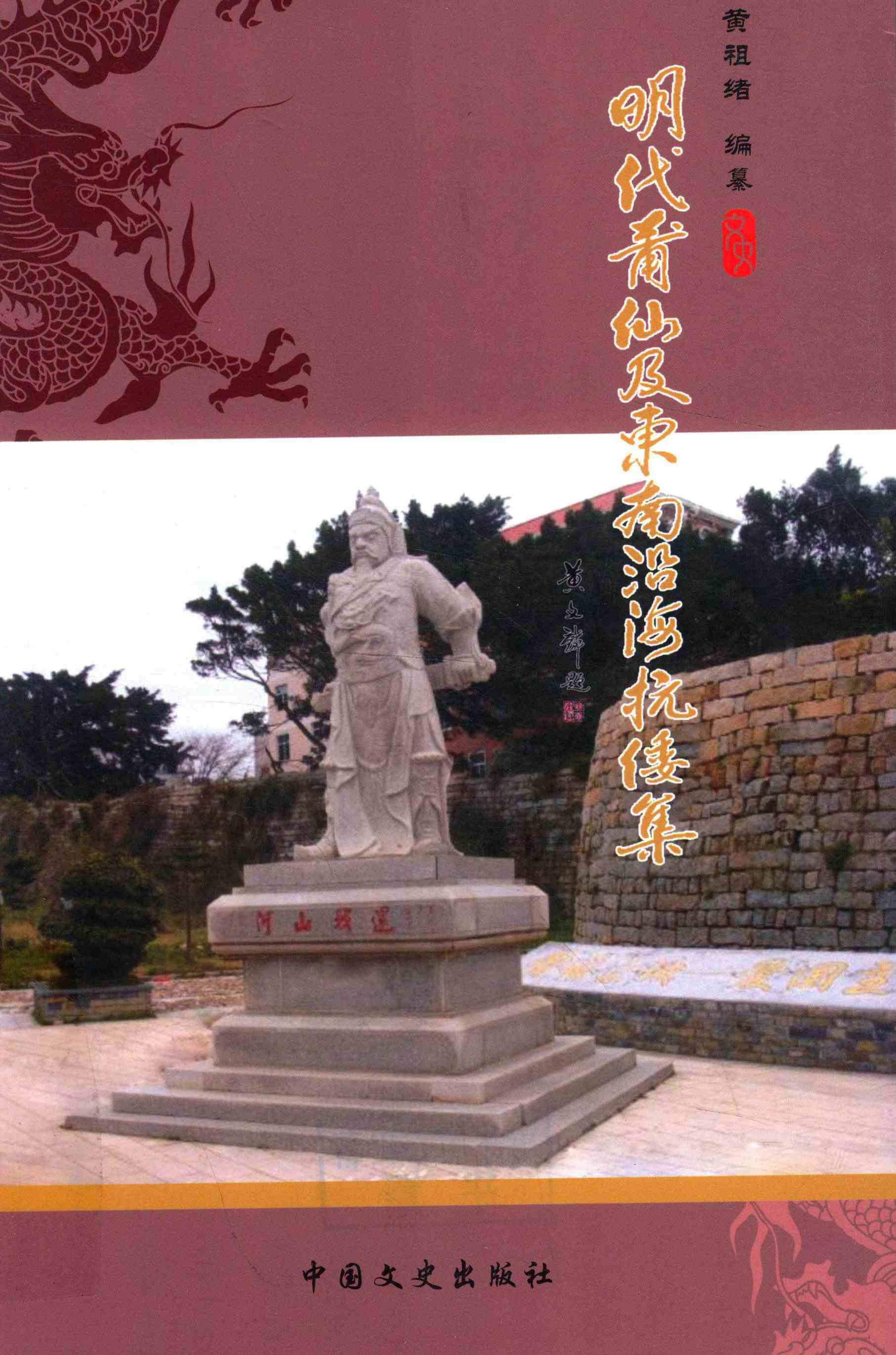
《明代莆仙及东南沿海抗倭集》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明代莆仙人民抗倭事迹;第二部分叙述林兆恩、卓晚春抗倭义举。下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明代东南沿海抗倭实录;第二部分叙述明代嘉靖年间抗倭英烈;第三部分叙述明代嘉靖年间抗倭诗咏及附录、参考文献。
阅读
相关地名
莆田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