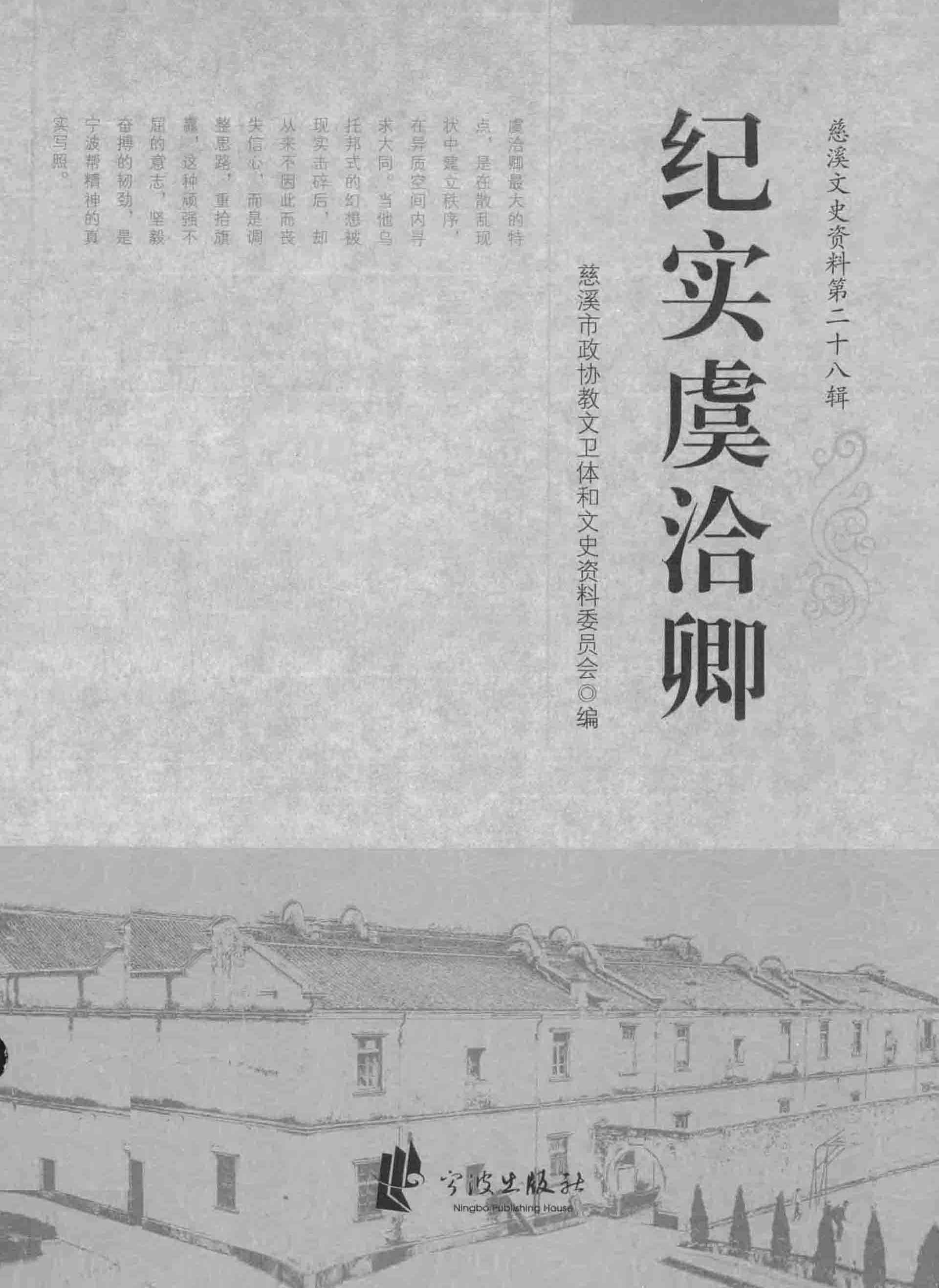内容
虞岫云是虞洽卿的孙女,大约出生在1911~1912年间。1930年1月25日,她的诗集《湖风》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叶灵风为这本诗集设计了封面。鲁迅在看到了这本诗集后,在他的一篇标题为“登龙术拾遗”的文章中,加以无情的嘲弄。鲁迅的话当然有震撼力,影响的人不但是当时,直至今天也照样有人将其捧为圭桌,以致在后来的各类文学史编写中,包括虞岫云在内的一大批女诗人,都被排斥于文学史视野之外。
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有一段话:“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鲁迅全集》在“女诗人”处加了一个注:“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1932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这个注在时间上显然是搞错了。
虞琰的《湖风》诗集初版本,系1929年12月25日付排后,于1930年1月25日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封面设计者叶灵凤是郭沫若旗下创造社的一员,他设计的封面,五光艳丽,引人眼球,令人折服。《湖风》的书封上是一个妙龄女郎,似乎在闭目沉思,她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背影后有绿色的西湖水在荡漾,这位女郎被阵阵湖风吹拂着。翻开书页,跳入眼帘的是作者的一首序诗:
疲倦的灵魂啊
如果尘世的炫熳
掩不住你的残骸
听!来听这少女的琴音
听!来听这芳洁的心籁
瞧那光艳的波幻
这样的小诗,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倪墨炎在评《湖风》这本诗集时曾说:“这样的诗篇能否用‘痛啊’、‘悲愁’等词来概括,这里且不说,但格调并不昂扬却是事实。”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有失偏颇。因“格调的昂扬”这词,已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作品的一个大框,什么都可往里面放,似成了定格的语言惯势,沿袭至今。试想,如果一首诗,一定要找出个所谓的闪光点,才能成为好诗的话,那么无论古代或现代,所谓好诗就所剩无几了。[1]
1930年2月6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有汤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虞琰的《湖风》—
介绍一位我们的女诗人”。虞琰是虞岫云的笔名,这本诗集是1929年下半年虞岫云因身体原因在西子湖畔休养时所作,共38首。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在面对西湖山水时,那种忧郁而又充满奇思幻想的眼神,头脑中闪过的是无奈和惆怅。对于虞岫云及其他一些女诗人的诗,余蔷薇在她的一篇论文中说:“前文论述的《过渡时代的女性》的作者虞岫云,著有诗集《湖风》,曾在各种期刊上发有大量诗作,如今已无人知晓,只是在鲁迅《登龙术拾遗》的注释中一晃而过。因为她是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这个身份,而被鲁迅嘲为‘女诗人’,被指责其内容充满‘痛啊’、‘悲愁’之词。学界权威的贬仰和嘲讽无疑使得女性诗人进入文学史变得更加困难重重。”[2]
虞琰在诗集《后面要说的几句话》中,透露了她的心声:“这本书开始写的时候,是在初春的西子湖边。西湖现在为一般人加以妄意雕琢、私心的侮辱,而至损害了她的天真,但她那不变的温和的湖风,吹动我枯涩的心波,我倾泻我的热泪,进出我的诗句。”
众多诗中,有一首《一只破船》,女诗人用灵敏纤细的感觉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阵狂暴的雷雨倾泻后
驶来一只刚经补就的破船
那里有新的船主与水手
四周只有盘旋上下的海鸥
哀叫着恐怖的将临
船上的旅客都昏沉地入了梦
他们想安乐便在这黑暗中
船主大意地陷入于酒色
为了那刚修好的船的稳固
水手们也都赌博作乐
风是阵阵的吹
云是片片的堆
谁会见着渺小的灯塔在远处!
一个还在爱国女校求学的学生,能期盼“渺小的灯塔在远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爱国女校教出了许多爱国的学生。1929年后,一个上海大亨的孙女,也与当年许多有志的青年一样,做着向往光明的梦。
这首诗曾在2011年被宁波演艺剧团谱上曲,用女中音演唱,委婉动人,感人至深。
作为上海权势显赫一时的虞洽卿的孙女,20世纪30年代的虞琰肯定生活富裕华贵。在优裕的环境下,她却写下了许多忧郁而又向往新生活的诗,并富有哲理,如《无名之花》《酒后》《墓前》《追寻》诸诗,都直抒了这个主题:
当烈士们的尸骸已腐化,四周是那样的死寂(《无名之花》)
我何尝醉了啊!心境更清明、痛苦却更深(《酒后》)
在墓前啊!想起艳丽的花朵总得凋谢/飘渺,飘渺,我只能伸出双手,把那冰冷的墓前轻敲!(《墓前》)追寻啊!奋斗,地执起明炬/奔向那幽暗的森林,回忆不可捉摸的前尘啊!失去了光明的苦闷!(《追寻》)[3]
其实,虞岫云并没有因为鲁迅的嘲讽而停止创作。她是一个有独立见解并有丰富想象力的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虞岫云的诗歌在很多报刊杂志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如1931年由陈穆如主编的《当代文艺》第一卷上,就有她的诗作《过渡时代的牺牲》,在第六卷上也有新作。这本杂志1901年由黄宾虹等创办,邓秋枚任主编,为神州国光社所属,是出版书画、字帖、金石、印谱为主的一家出版社。后因严重亏损,1928年由陈铭枢出资盘下,经理黄居素,总编王礼锡。从此一改原来格局,出刊了《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学术界》等多种社科类刊物,在当时曾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后如由曾今可任主编的《新时代》,属于时代书局,在1931年8月2日的创刊号上,就有虞岫云的诗八首。
曾今可是江西泰和县人,生于1901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他的父亲是商人(也有人说是开钱庄的)。曾今可于1928年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在创刊当天的《申报》上,曾今可做了一则广告:“新时代月刊,为曾今可主编,创刊号于今日出版。钱君陶作书面,有华林、卢剑波、袁牧之、李则刚、曾今可、崔万秋、虞岫云等人作品,计十余万字,三百多页。”也许是曾今可太过张扬,或许是太想标新立异,先后提出了“解放词”和“解放序”两项改革,遭到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文人的痛批,由此引发了一场鲁迅与曾今可的争论。其结局当然是可想而知,以曾今可登报声明脱离文学为终结。
虞岫云一共发表过多少诗作,因资料缺乏而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一些零星的报道看,她当时也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虞岫云毕业于上海爱国女校,这座学校于1902年由蔡元培创办,位于凤阳路。毕业以后,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她在上海滩以诗会友,与徐志摩、洪景深等相交甚厚。
1931年,上海出现了一本很特殊的刊物《絜茜》。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而《絮茜》就是其机关文学刊物。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成立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多次派邓演达与中共负责人联系,但没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响应。诚如周恩来在后来说,这让国共合作失去了一次机会。这本杂志由张资平和丁嘉树任主编,张资平还专门向虞岫云约过稿。所以在第一期上,就有虞岫云的一首《南海沙》。
这种名为“呐喊体”的诗,其中的一节是这样的:
啊,
当我初次遇到你,
我便深深地把你记忆,
昨天大地加上了白雪的披肩,
我冒着寒风又来到你的面前,
你可爱的脸已被推得黢黑,
清幽的香味也被蹂躏无遗。
这一期的出刊时间是1931年12月21日,是虞岫云在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尝试。按照出刊者的初衷,在《絮茜》上发表的作品,应当符合通俗易懂、爽直畅快、言之有物、用笔精练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呐喊体”。虞岫云的这首诗,应该是大致符合了上述四点要求。当时的这本杂志,曾被称作是“第三党”的杂志。所谓“第三党”,也就是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另一党。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钱理群等人曾把这本杂志定性为“反动刊物”。我们不知道钱理群是否真的看过这本杂志,从里面的内容而论,绝大多数是呼吁强国抗日和揭露日本的罪行,这样的内容被定为“反动”当失之偏颇。如果是因为“第三党”主办而是冠以“反动”的帽子,这也难免有点儿古怪滑稽,因为“第三党”的实质是反对国民党右派。这本杂志一共只出刊两期,第二期由丁嘉树主编,内容大多是情诗。[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虞岫云是会员之一。1931年11月1日,《新时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则笔会近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为抗议日本侵华,发表宣言,在邓脱摩饭店举行笔会,邵美等19人参加,虞岫云名列其中。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又刊出消息,为纪念徐志摩,将出版特刊,其中有蔡元培、叶恭绰、杨杏佛、胡适之、章士钊、刘海粟、虞岫云等20人的诗文。虞岫云《悼志摩诗人》一诗。全文如下:
原野布满了狂风狂风吹起了灰尘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关外布满了马蹄马蹄踏断了草茎这时应当有千百万首诗我们在需要这一个诗人今天,如果我们用这首诗来纪念女诗人也不会过分,因为我们的诗坛仍然需要这样的女诗人。[5]
《玲珑》杂志于1931年3月18日创刊于上海,每周三出版,因为是64开的小本,故名“玲珑”。虞岫云在第六期杂志上也发表过诗作,并配有一幅照片于封二。这首诗标题是“不灭的青春底希望”。全诗如下:
月儿微笑的照着春姊,
放出灿烂之光。
灰色的世界,
顿时现出了花开的芬芳。
热情,光明,幸福,
满涨在我们的身傍。
人们啊!
切莫因了你们的青春而悲伤。
这首只有八句的自由体小诗,通篇充满了活力和希望。针对当时社会现状和青年人心中的迷惘,诗人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奔放,把心灵的寄托和对幸福自由的向往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虞岫云的《湖风》到1933年已再版三次,很是畅销。当时这本诗集的价格是每册三角。这一年的《微言》周刊曾发过一则消息,说虞岫云的第二本诗集即将出版,并已将书稿交与马来亚书店。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曾今可为虞岫云出版第二本诗集作准备时,他却与原来的朋友崔万秋闹翻,使这本诗集的出版计划夭折。[6]
崔万秋是山东莘县人,因与江青的老家诸城同属山东聊城市,所以也算是同乡。他曾在日本生活了10年,是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回国后先在报社工作,并应邀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讲学,后来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1971年退休后到美国隐居,1982年在美国去世。198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遗作《江青前传》。
虞岫云在大夏大学毕业后,第一位丈夫是位律师,但结婚后没多久便告离婚。第二位丈夫陈宪谟,后来是中央大学教授。
1921年冬,由应云卫、谷剑尘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戏剧协社。成员有陈宪谟、孟君谋、钱剑秋、王毓清、王毓静等,后来汪优游、欧阳予倩、洪深等也加入该社。戏剧协社的前身是中华职业学校附属学生剧团和少年化装宣讲团,创建剧社的主张是提倡艺术创新。为实现表演艺术的完美,曾大力提倡话剧男女合演。1923年,洪深排了话剧《终身大事》,由钱剑秋、王毓清等男女合演。另一出是《泼妇》,由应云卫、谷剑尘、陈宪谟等男扮女角演出。这两出戏反应迥然不同,前者大受欢迎,后者遭受到嘲笑。后来移植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在中央大戏剧演出时,主演有虞岫云、陈宪谟、黄一美、沈憧、顾秀中等,大获成功。所以,虞岫云与陈宪谟在剧社时,就已相识。
1934年秋,当时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赵景深在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虞岫云作为伴娘出席。在这次婚宴上,她见到了鲁迅。但是据贺玉波在后来的回忆时说,鲁迅一人独自坐在一边,不声不响,一脸庄严和冷酷,既没有人找他说话,他也没有去找人聊天,一直等到开宴时,一声不响地落座。出席的文艺界人士还有沈从文、叶圣陶、徐霞村、周予同等。虞岫云对于这位曾经冷嘲热讽她的文坛前辈,到底有何感想,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
对于家乡龙山的记忆,虞岫云也有一首诗,题目是“别故乡”,收入《湖风》诗集中,全诗如下:
阔大无边的海面,
映着鱼鳞般的波浪闪耀,
遥望故乡啊!渺小!
在那里,有庄严的龙山,
有美丽的小河;
当每一个的黄昏天晓,
我曾独坐在那泰平桥,
河面上的野菱随着那船儿动荡,
两岸的芦荻随着秋风颤摇。
如今啊!是别了!
虽这里的太阳依旧升沉,
月儿依旧的辉照,
奈行一步一步远!
故乡啊!
鱼鳞般的波浪啊!
渺渺!
龙山的美丽秋景,在诗人的笔下是那么的淡恬清朗,大海、小山、秋波、芦荻、河面上漂浮的野菱和那座并不大的石桥,构成了一幅清雅无染的画面,诗人的细腻情感在这里尽情地发挥了出来。这就是印在她心目中的故乡,以及远离故乡后的那种复杂心情,跃然纸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位曾经活跃于诗坛的女诗人,突然离开人们的视线,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的新作问世。
【参考文献】
[1][3][5]张建智.虞琰的《湖风》.博览群书,2009(10).
[2]余蔷薇.193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及其文学史命运.文学评论,2012(4):164.
[4]以《絮茜》杂志的“呐喊诗”为核心的学术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3).
[6]huangyun博文.诗人虞岫云.[2008-12-30].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629724&PostID=16148999.
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有一段话:“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鲁迅全集》在“女诗人”处加了一个注:“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1932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这个注在时间上显然是搞错了。
虞琰的《湖风》诗集初版本,系1929年12月25日付排后,于1930年1月25日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封面设计者叶灵凤是郭沫若旗下创造社的一员,他设计的封面,五光艳丽,引人眼球,令人折服。《湖风》的书封上是一个妙龄女郎,似乎在闭目沉思,她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背影后有绿色的西湖水在荡漾,这位女郎被阵阵湖风吹拂着。翻开书页,跳入眼帘的是作者的一首序诗:
疲倦的灵魂啊
如果尘世的炫熳
掩不住你的残骸
听!来听这少女的琴音
听!来听这芳洁的心籁
瞧那光艳的波幻
这样的小诗,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倪墨炎在评《湖风》这本诗集时曾说:“这样的诗篇能否用‘痛啊’、‘悲愁’等词来概括,这里且不说,但格调并不昂扬却是事实。”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有失偏颇。因“格调的昂扬”这词,已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作品的一个大框,什么都可往里面放,似成了定格的语言惯势,沿袭至今。试想,如果一首诗,一定要找出个所谓的闪光点,才能成为好诗的话,那么无论古代或现代,所谓好诗就所剩无几了。[1]
1930年2月6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有汤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虞琰的《湖风》—
介绍一位我们的女诗人”。虞琰是虞岫云的笔名,这本诗集是1929年下半年虞岫云因身体原因在西子湖畔休养时所作,共38首。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在面对西湖山水时,那种忧郁而又充满奇思幻想的眼神,头脑中闪过的是无奈和惆怅。对于虞岫云及其他一些女诗人的诗,余蔷薇在她的一篇论文中说:“前文论述的《过渡时代的女性》的作者虞岫云,著有诗集《湖风》,曾在各种期刊上发有大量诗作,如今已无人知晓,只是在鲁迅《登龙术拾遗》的注释中一晃而过。因为她是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这个身份,而被鲁迅嘲为‘女诗人’,被指责其内容充满‘痛啊’、‘悲愁’之词。学界权威的贬仰和嘲讽无疑使得女性诗人进入文学史变得更加困难重重。”[2]
虞琰在诗集《后面要说的几句话》中,透露了她的心声:“这本书开始写的时候,是在初春的西子湖边。西湖现在为一般人加以妄意雕琢、私心的侮辱,而至损害了她的天真,但她那不变的温和的湖风,吹动我枯涩的心波,我倾泻我的热泪,进出我的诗句。”
众多诗中,有一首《一只破船》,女诗人用灵敏纤细的感觉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阵狂暴的雷雨倾泻后
驶来一只刚经补就的破船
那里有新的船主与水手
四周只有盘旋上下的海鸥
哀叫着恐怖的将临
船上的旅客都昏沉地入了梦
他们想安乐便在这黑暗中
船主大意地陷入于酒色
为了那刚修好的船的稳固
水手们也都赌博作乐
风是阵阵的吹
云是片片的堆
谁会见着渺小的灯塔在远处!
一个还在爱国女校求学的学生,能期盼“渺小的灯塔在远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爱国女校教出了许多爱国的学生。1929年后,一个上海大亨的孙女,也与当年许多有志的青年一样,做着向往光明的梦。
这首诗曾在2011年被宁波演艺剧团谱上曲,用女中音演唱,委婉动人,感人至深。
作为上海权势显赫一时的虞洽卿的孙女,20世纪30年代的虞琰肯定生活富裕华贵。在优裕的环境下,她却写下了许多忧郁而又向往新生活的诗,并富有哲理,如《无名之花》《酒后》《墓前》《追寻》诸诗,都直抒了这个主题:
当烈士们的尸骸已腐化,四周是那样的死寂(《无名之花》)
我何尝醉了啊!心境更清明、痛苦却更深(《酒后》)
在墓前啊!想起艳丽的花朵总得凋谢/飘渺,飘渺,我只能伸出双手,把那冰冷的墓前轻敲!(《墓前》)追寻啊!奋斗,地执起明炬/奔向那幽暗的森林,回忆不可捉摸的前尘啊!失去了光明的苦闷!(《追寻》)[3]
其实,虞岫云并没有因为鲁迅的嘲讽而停止创作。她是一个有独立见解并有丰富想象力的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虞岫云的诗歌在很多报刊杂志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如1931年由陈穆如主编的《当代文艺》第一卷上,就有她的诗作《过渡时代的牺牲》,在第六卷上也有新作。这本杂志1901年由黄宾虹等创办,邓秋枚任主编,为神州国光社所属,是出版书画、字帖、金石、印谱为主的一家出版社。后因严重亏损,1928年由陈铭枢出资盘下,经理黄居素,总编王礼锡。从此一改原来格局,出刊了《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学术界》等多种社科类刊物,在当时曾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后如由曾今可任主编的《新时代》,属于时代书局,在1931年8月2日的创刊号上,就有虞岫云的诗八首。
曾今可是江西泰和县人,生于1901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他的父亲是商人(也有人说是开钱庄的)。曾今可于1928年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在创刊当天的《申报》上,曾今可做了一则广告:“新时代月刊,为曾今可主编,创刊号于今日出版。钱君陶作书面,有华林、卢剑波、袁牧之、李则刚、曾今可、崔万秋、虞岫云等人作品,计十余万字,三百多页。”也许是曾今可太过张扬,或许是太想标新立异,先后提出了“解放词”和“解放序”两项改革,遭到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文人的痛批,由此引发了一场鲁迅与曾今可的争论。其结局当然是可想而知,以曾今可登报声明脱离文学为终结。
虞岫云一共发表过多少诗作,因资料缺乏而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一些零星的报道看,她当时也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虞岫云毕业于上海爱国女校,这座学校于1902年由蔡元培创办,位于凤阳路。毕业以后,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她在上海滩以诗会友,与徐志摩、洪景深等相交甚厚。
1931年,上海出现了一本很特殊的刊物《絜茜》。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而《絮茜》就是其机关文学刊物。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成立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多次派邓演达与中共负责人联系,但没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响应。诚如周恩来在后来说,这让国共合作失去了一次机会。这本杂志由张资平和丁嘉树任主编,张资平还专门向虞岫云约过稿。所以在第一期上,就有虞岫云的一首《南海沙》。
这种名为“呐喊体”的诗,其中的一节是这样的:
啊,
当我初次遇到你,
我便深深地把你记忆,
昨天大地加上了白雪的披肩,
我冒着寒风又来到你的面前,
你可爱的脸已被推得黢黑,
清幽的香味也被蹂躏无遗。
这一期的出刊时间是1931年12月21日,是虞岫云在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尝试。按照出刊者的初衷,在《絮茜》上发表的作品,应当符合通俗易懂、爽直畅快、言之有物、用笔精练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呐喊体”。虞岫云的这首诗,应该是大致符合了上述四点要求。当时的这本杂志,曾被称作是“第三党”的杂志。所谓“第三党”,也就是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另一党。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钱理群等人曾把这本杂志定性为“反动刊物”。我们不知道钱理群是否真的看过这本杂志,从里面的内容而论,绝大多数是呼吁强国抗日和揭露日本的罪行,这样的内容被定为“反动”当失之偏颇。如果是因为“第三党”主办而是冠以“反动”的帽子,这也难免有点儿古怪滑稽,因为“第三党”的实质是反对国民党右派。这本杂志一共只出刊两期,第二期由丁嘉树主编,内容大多是情诗。[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虞岫云是会员之一。1931年11月1日,《新时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则笔会近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为抗议日本侵华,发表宣言,在邓脱摩饭店举行笔会,邵美等19人参加,虞岫云名列其中。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又刊出消息,为纪念徐志摩,将出版特刊,其中有蔡元培、叶恭绰、杨杏佛、胡适之、章士钊、刘海粟、虞岫云等20人的诗文。虞岫云《悼志摩诗人》一诗。全文如下:
原野布满了狂风狂风吹起了灰尘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关外布满了马蹄马蹄踏断了草茎这时应当有千百万首诗我们在需要这一个诗人今天,如果我们用这首诗来纪念女诗人也不会过分,因为我们的诗坛仍然需要这样的女诗人。[5]
《玲珑》杂志于1931年3月18日创刊于上海,每周三出版,因为是64开的小本,故名“玲珑”。虞岫云在第六期杂志上也发表过诗作,并配有一幅照片于封二。这首诗标题是“不灭的青春底希望”。全诗如下:
月儿微笑的照着春姊,
放出灿烂之光。
灰色的世界,
顿时现出了花开的芬芳。
热情,光明,幸福,
满涨在我们的身傍。
人们啊!
切莫因了你们的青春而悲伤。
这首只有八句的自由体小诗,通篇充满了活力和希望。针对当时社会现状和青年人心中的迷惘,诗人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奔放,把心灵的寄托和对幸福自由的向往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虞岫云的《湖风》到1933年已再版三次,很是畅销。当时这本诗集的价格是每册三角。这一年的《微言》周刊曾发过一则消息,说虞岫云的第二本诗集即将出版,并已将书稿交与马来亚书店。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曾今可为虞岫云出版第二本诗集作准备时,他却与原来的朋友崔万秋闹翻,使这本诗集的出版计划夭折。[6]
崔万秋是山东莘县人,因与江青的老家诸城同属山东聊城市,所以也算是同乡。他曾在日本生活了10年,是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回国后先在报社工作,并应邀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讲学,后来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1971年退休后到美国隐居,1982年在美国去世。198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遗作《江青前传》。
虞岫云在大夏大学毕业后,第一位丈夫是位律师,但结婚后没多久便告离婚。第二位丈夫陈宪谟,后来是中央大学教授。
1921年冬,由应云卫、谷剑尘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戏剧协社。成员有陈宪谟、孟君谋、钱剑秋、王毓清、王毓静等,后来汪优游、欧阳予倩、洪深等也加入该社。戏剧协社的前身是中华职业学校附属学生剧团和少年化装宣讲团,创建剧社的主张是提倡艺术创新。为实现表演艺术的完美,曾大力提倡话剧男女合演。1923年,洪深排了话剧《终身大事》,由钱剑秋、王毓清等男女合演。另一出是《泼妇》,由应云卫、谷剑尘、陈宪谟等男扮女角演出。这两出戏反应迥然不同,前者大受欢迎,后者遭受到嘲笑。后来移植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在中央大戏剧演出时,主演有虞岫云、陈宪谟、黄一美、沈憧、顾秀中等,大获成功。所以,虞岫云与陈宪谟在剧社时,就已相识。
1934年秋,当时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赵景深在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虞岫云作为伴娘出席。在这次婚宴上,她见到了鲁迅。但是据贺玉波在后来的回忆时说,鲁迅一人独自坐在一边,不声不响,一脸庄严和冷酷,既没有人找他说话,他也没有去找人聊天,一直等到开宴时,一声不响地落座。出席的文艺界人士还有沈从文、叶圣陶、徐霞村、周予同等。虞岫云对于这位曾经冷嘲热讽她的文坛前辈,到底有何感想,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
对于家乡龙山的记忆,虞岫云也有一首诗,题目是“别故乡”,收入《湖风》诗集中,全诗如下:
阔大无边的海面,
映着鱼鳞般的波浪闪耀,
遥望故乡啊!渺小!
在那里,有庄严的龙山,
有美丽的小河;
当每一个的黄昏天晓,
我曾独坐在那泰平桥,
河面上的野菱随着那船儿动荡,
两岸的芦荻随着秋风颤摇。
如今啊!是别了!
虽这里的太阳依旧升沉,
月儿依旧的辉照,
奈行一步一步远!
故乡啊!
鱼鳞般的波浪啊!
渺渺!
龙山的美丽秋景,在诗人的笔下是那么的淡恬清朗,大海、小山、秋波、芦荻、河面上漂浮的野菱和那座并不大的石桥,构成了一幅清雅无染的画面,诗人的细腻情感在这里尽情地发挥了出来。这就是印在她心目中的故乡,以及远离故乡后的那种复杂心情,跃然纸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位曾经活跃于诗坛的女诗人,突然离开人们的视线,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的新作问世。
【参考文献】
[1][3][5]张建智.虞琰的《湖风》.博览群书,2009(10).
[2]余蔷薇.193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及其文学史命运.文学评论,2012(4):164.
[4]以《絮茜》杂志的“呐喊诗”为核心的学术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3).
[6]huangyun博文.诗人虞岫云.[2008-12-30].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629724&PostID=16148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