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
| 内容出处: | 《杨贤江全集 第三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6564 |
| 颗粒名称: | 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 |
| 分类号: | G40-092.55 |
| 页数: | 9 |
| 页码: | 155-163 |
| 摘要: | 本文为杨贤江读舒新城君《致青年教育家》的论著作品,原载1929年7月20日《教育杂志》第21卷第7号。 |
| 关键词: | 杨贤江 论著作品 1929年 |
内容
编辑先生:
前读二十一卷二号的《教育杂志》,内有舒新城②君《致青年教育家》通信一则,读后颇有些感想,今特拉杂写下,愿求教于舒君及一般读者。
据我的意见,舒君此信,有几点我表同意;而另有几点,是以为可有商榷之余地的。
我所表同意者,是在舒君较能明白地说出教育的实相——可不是教育的本质——有为一般人所未认识,或认识了而未敢指摘者。这几点是什么呢?
第一是论教育事业并不是神圣清高。且根据事实说:“倘若你们在学校曾经过几次风潮,作教师曾碰过几次钉子,便知道教育界的钻营奔竞、倾轧排挤的种种污浊行为、卑贱勾当,并不亚于其他各界,也非弱于大众所深恶痛绝的政治界,甚至于足资他人仿效。”
第二是论教育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工具;不相信“教育万能”,说破了日本伊藤首相与德国毛奇将军倡导教育万能的作
用。①舒君更说出教育所以不成独立的原因——即所以不能为改造国家社会的唯一工具的原因,是由教育受政治、经济的支配。“把教育和政治及经济比,它便根本是附属品。”“教育的设施都要根据国家政治的变迁而变迁。”
其他各说:“教师的目的既在以教书为职业,自然要迎合雇主的心理,而创造出许多的学说,牢笼主顾。”如说:“教师所过的生活是人生最虚伪的生活。”如说:“教师的生活中不能有感情,所以他们的言行都是些庸人之言、庸人之行。”——这里“都是”二字,虽未免有点武断。——如说:“所以他们除了循规蹈矩地生活下去以外,不能有什么大创造,更不能有什么大破坏。……他们只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凡这些话,也都算是痛快而且恰当的话,足以警醒一般教育者的。
但我所认为尚有商榷之点,最主要的,是在舒君未尝说出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迁,因而他虽然揭破了教育之“黑暗方面”,却不能指出一条教育者所“应走的路”。不特未指出而已,好像还留下了些不大好的印象与夫不大负责的言论。为表明我的意见,请容我先说几句闲话。
我所欲说的,便是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与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换句通俗的话,教育便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①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借用舒君的话,正是所谓“这种事实,原是本着本来需要自然而然发展的,初无所谓教育家,更无所谓教育科学”。教育的发生,简简单单地是在于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之资料与方法,也跟着需要有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基础构造的转轮。故在原始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一种教育方式。
在原始社会,教育是全人类都得享受,也是都当享受的。到了社会分成阶级,于是教育也带上阶级的色彩。在支配阶级方面,有俨然的教育制度,有厘然的教育规则,有专供本阶级适用的教育材料。至于被支配阶级,不是全被摈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便被施以欺瞒的教育。②
因为这个缘故,自社会有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以来,在教育上也就不断地发生对立和斗争。在真正教育史上,教育意义的历次变迁,便是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动期中所表现的形态,便也成为阶级斗争之一个部门、一个阶段。
也便因为这个缘故,凡是真正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负起历史的使命,实践起他们在这个历史变动期中所应尽的责任。
但在舒君的通信中,未说出这个要点,这是我所认为未免有缺憾的。为了他未说出这个要点,所以在我所认为可表同意的几处,似也未见能说得透彻,说得中肯。最显著的,便是舒君虽指出教育事业为并非清高,并非神圣;但他并没有说明:为何而有教育神圣与教育清高这类观念的产生。
跟着这个缺陷而来的缺陷,便有不少。其中,为我所认为留下不大好的印象与不大负责任的,可以说是他的“天才的改途论”。舒君在结尾中很坚决、很郑重似地提醒“青年教育家”说:
……教师只是庸人的佣工之一种,……你们自审是庸人,愿过虚伪的平常生活,从事教育也无妨;若自问是天才,想改造社会、国家,建立不世之勋,我劝你们早早改途,努力从应走的路上走去,不要再在这中庸之道的十字街上徘徊踯躅。
舒君虽自承不敢以“教育叛徒”自居,但这一段的劝告,倒颇有些像“教育叛徒”的口吻。在读过这几句话以后,回想到舒君在信的开端所说的“于预备改途的百忙之中,而作这一篇书信”,不是很容易令读者推想到舒君一定是个“自问是天才”的人吗?我虽不愿说及舒君本身的事情,不过在舒君公然自白“我对于教育本只是藉其名以为生活的工具而已”;由此岂不是可以推论舒君从前的提倡道尔顿制,乃至“最近几年努力于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编者附言”中话——都不是真心在从事教育事业,而只在藉名以为生活吗?这固然是舒君个人言行的自由,我可不必多说;但有二点却不能容我默尔。
一是他视从事教育事业只为吃饭的方便,“最多与烧饭、挑粪相等”,凡是天才,都该早早改途。这个主张之由来,可说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忘记了教育毕竟还是“改造国家、社会”的“工具”——只不是“唯一的工具”;自然更不知道这方面也不失为社会进化之一部门与一阶段之机能而愿意努力;所以在不相信了教育的神圣与清高,不相信了教育万能之后,自己便可昂首远去,而只让“庸人”来从事这“佣工之一种”的教育事业,并不觉得有愧色。
二是舒君既主张有天才的人应该早早离开教育,“努力从应走的路上走去”,但究竟哪些路是“应走的路呢”?又该怎样“努力”呢?这些舒君都未曾有所说明。这似乎不能不再求教于舒君了。
其他尚有数点,我有些补充及修正的意见,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吧:
第一,舒君说“教育在人生、在国家的地位,也不过如其他各种社会事业,与农、工、商等相当,教师也不过等于厨子、粪夫而已”。舒君原意在用以证明教育事业并不具有什么高贵的原素。但不管舒君是否尚有别种含义,我愿就我的意见加以申说:所谓农业、工业、商业,是生产上、实利上的事业,在现代社会中,都由少数有钱的人从事经营;虽有所谓国有或公有的产业,也只为少数人支配,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根本没有所谓“公共所有”的。至于教育事业,有许多人恐必认为这是精神上的事业,即使不算为清高神圣,总也不失为非生产的。这种意见,确有理由。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学”与“行”是分离的;换句话,“知识”与“劳动”是分家的,或“理论”与“实行”是分途的。教育为求“学”的事业,为获得“知识”的事业,为研究“理论”的事业,当然不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事业。所以在这般人看来,他们怕要说舒君的话是失当的。可是在这一点,我倒要说在现社会中,教育事业确与农、工、商业“相当”。为什么呢?是因农、工、商业是支配阶级——一般地说,便是资本家和地主——生产或搬运商品的事业;而教育事业乃是支配阶级制造观念的事业,学校就是最正式的观念制造工场;在这情形底下,学生好比是原料,教师好比是工匠。支配阶级是经济上占优越地位的阶级,同时也就是思想上占优越地位的阶级。任何获胜利、拥权力的支配阶级,总要有它的可供利用的文化政策。秦始皇要焚书,汉武帝要尊儒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便要教臣民忠君爱国,培养拥护祖国意识,都是用教育以生产“观
念商品”的实例。
再说教师的地位。就全体言,他们是所谓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至于厨子、粪夫,则是贫苦的民众,是和劳动者、贫农可以归入一种阵营的。故表面上教师是不“等于厨子、粪夫”的。然实际上,他们实有相同的运命。即因在阶级斗争益形尖锐化的现代,“精神劳动者”(知识分子)有和“筋肉劳动者”合流的趋势。生活的困难,逼得自命非凡的知识分子一日胜似一日地无产者化。虽然知识分子因受了支配阶级的教养——即上述观念商品——雅不愿自见没落,也且不容易认识自身所处的地位,以形成无产者的意识;可是历史的车轮向这个方向转动,知识分子除意识上的差异外,总难自逃于和无产者相同的运命。故教师之“等于厨子、粪夫”,从阶级形势的变化看来,是不错的。——不过,教师中之一部分,很有积财致富的,那种自当别论。
第二,舒君说“……世界最根本的事情是吃饭,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倘若中国先没有这三种人,教育家除了实行神仙的绝食、野人的裸体而外,连生命都不能保持,……”此话虽是用以证明教育事业之非神圣清高,但很容易使人误会为教育的本质便是如此。其实教育之所以这样无用,原因是在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专有品,徒供享乐消遣之用,即为上述把知识与劳动分家以后所生的结果。要知这只是阶级社会中教育的变态,而非人类社会所当有的教育的常态。知识和劳动本不应分,教育本是帮助人生存的手段。教育的结果,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只是某个社会的支配阶级的文化政策所要求,却不能说教育其物是当初就如此,未来也复如此。
第三,舒君说“你们如在人生的许多活动之中,而欢喜干教育事业,只可把教育当作平淡无奇的东西而效厨子、粪夫们的各尽所能,努力干去就行了”。舒君的原意虽为劝青年教育家“不必幻想着什么神圣清高的安琪儿,……更不必不自侪于百工之列,……”但这样的劝告法,究竟也有些不对。何以故?试拿厨子为例。我们知道厨子是专替有钱人“烧饭”的——注意,决不是为“社会服务”。——他须得训练好一副好本领,能满足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食欲,庶几能博得大小东家的欢心,以为自己“生活的工具”。有的厨子,譬如在包饭作做生意的,他便须投合吃包饭者的胃口,不仅如此,还须投合包饭作老板的意旨,好叫他可以赚钱。至于包饭作老板,也许他本身是个厨子,但他已兼有榨取者、剥削者的资格了。要之,厨子们总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如今舒君劝他们效厨子的各尽所能,努力干去,是不是要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味替少数有钱人卖力献功呢?不错,现在的教育原是少数有钱人的专有品,无产者自不必享受教育。——譬如日本政府虽厉行义务教育,但是穷人可以延迟或竟免除这个“义务”!——就是舒君也曾明白地说过:“教师的目的既在以教书为职业,自然要迎合雇主的心理而创造出许多的学理,牢笼主顾,如牧师之藉上帝之名以牢笼教徒的一般。”但我要问,舒君所希望于青年教育家者,莫非真是叫他们“努力干”这样专门迎合雇主心理的教师吗?除此以外,再没有另一型态的教师吗?舒君自己虽痛恶教育界之污浊卑贱,毅然改途,难道忍令教育界就永远如此,无须改革吗?幻想清高神圣的教育,迷信万能的教育,固属不合;但可如舒君这样蔑视教育,轻视教育,听教育终于留在“婢妾下厮”的地位而一若“也无妨”者吗?所以舒君的这种主张,除使教育事业益发糟糕、益发乌烟瘴气而外,似乎不会再有别种好处。
第四,舒君说“把教育和人生可有可无的宗教比,它们可以两不相涉,也可以彼此互相支配”。这话错了。宗教在原人,是日常生活的安慰上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的教育内容,即不外关于宗教的及关于战争的两项。为一般普通教育史家所写在第一页的古希腊教育,尚属如此。在他们,教育和宗教决不是不相涉的,教育而且受制于宗教。到了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中,宗教更被支配阶级用作愚弄人民的手段。这时候,宗教对于被压迫者,固奉为慰藉苦痛、希冀幸福的一种“鸦片”;对于压迫者,又是思想支配的一种利器;在教育上,宗教的影响尤为显著。欧洲中古千余年间,全是宗教教育支配了一切;直到最近,宗教还不能不说仍在支配着教育,安得说宗教与教育两不相涉呢?至于它们之所以发生姻缘,其理由也很简单,即因支配阶级同样地要利用宗教和教育,藉以钳制人民,威吓人民,愚弄人民,并诱惑人民。教育之被视为神圣、为清高,归根还是起于宗教的影响。
以上拉杂地已写了不少字,信笔所至,语不暇择,幸舒君有以谅之,并求舒君和读者给我以指正。
原载1929年7月20日《教育杂志》第21卷第7号
前读二十一卷二号的《教育杂志》,内有舒新城②君《致青年教育家》通信一则,读后颇有些感想,今特拉杂写下,愿求教于舒君及一般读者。
据我的意见,舒君此信,有几点我表同意;而另有几点,是以为可有商榷之余地的。
我所表同意者,是在舒君较能明白地说出教育的实相——可不是教育的本质——有为一般人所未认识,或认识了而未敢指摘者。这几点是什么呢?
第一是论教育事业并不是神圣清高。且根据事实说:“倘若你们在学校曾经过几次风潮,作教师曾碰过几次钉子,便知道教育界的钻营奔竞、倾轧排挤的种种污浊行为、卑贱勾当,并不亚于其他各界,也非弱于大众所深恶痛绝的政治界,甚至于足资他人仿效。”
第二是论教育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工具;不相信“教育万能”,说破了日本伊藤首相与德国毛奇将军倡导教育万能的作
用。①舒君更说出教育所以不成独立的原因——即所以不能为改造国家社会的唯一工具的原因,是由教育受政治、经济的支配。“把教育和政治及经济比,它便根本是附属品。”“教育的设施都要根据国家政治的变迁而变迁。”
其他各说:“教师的目的既在以教书为职业,自然要迎合雇主的心理,而创造出许多的学说,牢笼主顾。”如说:“教师所过的生活是人生最虚伪的生活。”如说:“教师的生活中不能有感情,所以他们的言行都是些庸人之言、庸人之行。”——这里“都是”二字,虽未免有点武断。——如说:“所以他们除了循规蹈矩地生活下去以外,不能有什么大创造,更不能有什么大破坏。……他们只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凡这些话,也都算是痛快而且恰当的话,足以警醒一般教育者的。
但我所认为尚有商榷之点,最主要的,是在舒君未尝说出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迁,因而他虽然揭破了教育之“黑暗方面”,却不能指出一条教育者所“应走的路”。不特未指出而已,好像还留下了些不大好的印象与夫不大负责的言论。为表明我的意见,请容我先说几句闲话。
我所欲说的,便是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与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换句通俗的话,教育便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①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借用舒君的话,正是所谓“这种事实,原是本着本来需要自然而然发展的,初无所谓教育家,更无所谓教育科学”。教育的发生,简简单单地是在于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之资料与方法,也跟着需要有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基础构造的转轮。故在原始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一种教育方式。
在原始社会,教育是全人类都得享受,也是都当享受的。到了社会分成阶级,于是教育也带上阶级的色彩。在支配阶级方面,有俨然的教育制度,有厘然的教育规则,有专供本阶级适用的教育材料。至于被支配阶级,不是全被摈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便被施以欺瞒的教育。②
因为这个缘故,自社会有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以来,在教育上也就不断地发生对立和斗争。在真正教育史上,教育意义的历次变迁,便是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动期中所表现的形态,便也成为阶级斗争之一个部门、一个阶段。
也便因为这个缘故,凡是真正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负起历史的使命,实践起他们在这个历史变动期中所应尽的责任。
但在舒君的通信中,未说出这个要点,这是我所认为未免有缺憾的。为了他未说出这个要点,所以在我所认为可表同意的几处,似也未见能说得透彻,说得中肯。最显著的,便是舒君虽指出教育事业为并非清高,并非神圣;但他并没有说明:为何而有教育神圣与教育清高这类观念的产生。
跟着这个缺陷而来的缺陷,便有不少。其中,为我所认为留下不大好的印象与不大负责任的,可以说是他的“天才的改途论”。舒君在结尾中很坚决、很郑重似地提醒“青年教育家”说:
……教师只是庸人的佣工之一种,……你们自审是庸人,愿过虚伪的平常生活,从事教育也无妨;若自问是天才,想改造社会、国家,建立不世之勋,我劝你们早早改途,努力从应走的路上走去,不要再在这中庸之道的十字街上徘徊踯躅。
舒君虽自承不敢以“教育叛徒”自居,但这一段的劝告,倒颇有些像“教育叛徒”的口吻。在读过这几句话以后,回想到舒君在信的开端所说的“于预备改途的百忙之中,而作这一篇书信”,不是很容易令读者推想到舒君一定是个“自问是天才”的人吗?我虽不愿说及舒君本身的事情,不过在舒君公然自白“我对于教育本只是藉其名以为生活的工具而已”;由此岂不是可以推论舒君从前的提倡道尔顿制,乃至“最近几年努力于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编者附言”中话——都不是真心在从事教育事业,而只在藉名以为生活吗?这固然是舒君个人言行的自由,我可不必多说;但有二点却不能容我默尔。
一是他视从事教育事业只为吃饭的方便,“最多与烧饭、挑粪相等”,凡是天才,都该早早改途。这个主张之由来,可说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忘记了教育毕竟还是“改造国家、社会”的“工具”——只不是“唯一的工具”;自然更不知道这方面也不失为社会进化之一部门与一阶段之机能而愿意努力;所以在不相信了教育的神圣与清高,不相信了教育万能之后,自己便可昂首远去,而只让“庸人”来从事这“佣工之一种”的教育事业,并不觉得有愧色。
二是舒君既主张有天才的人应该早早离开教育,“努力从应走的路上走去”,但究竟哪些路是“应走的路呢”?又该怎样“努力”呢?这些舒君都未曾有所说明。这似乎不能不再求教于舒君了。
其他尚有数点,我有些补充及修正的意见,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吧:
第一,舒君说“教育在人生、在国家的地位,也不过如其他各种社会事业,与农、工、商等相当,教师也不过等于厨子、粪夫而已”。舒君原意在用以证明教育事业并不具有什么高贵的原素。但不管舒君是否尚有别种含义,我愿就我的意见加以申说:所谓农业、工业、商业,是生产上、实利上的事业,在现代社会中,都由少数有钱的人从事经营;虽有所谓国有或公有的产业,也只为少数人支配,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根本没有所谓“公共所有”的。至于教育事业,有许多人恐必认为这是精神上的事业,即使不算为清高神圣,总也不失为非生产的。这种意见,确有理由。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学”与“行”是分离的;换句话,“知识”与“劳动”是分家的,或“理论”与“实行”是分途的。教育为求“学”的事业,为获得“知识”的事业,为研究“理论”的事业,当然不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事业。所以在这般人看来,他们怕要说舒君的话是失当的。可是在这一点,我倒要说在现社会中,教育事业确与农、工、商业“相当”。为什么呢?是因农、工、商业是支配阶级——一般地说,便是资本家和地主——生产或搬运商品的事业;而教育事业乃是支配阶级制造观念的事业,学校就是最正式的观念制造工场;在这情形底下,学生好比是原料,教师好比是工匠。支配阶级是经济上占优越地位的阶级,同时也就是思想上占优越地位的阶级。任何获胜利、拥权力的支配阶级,总要有它的可供利用的文化政策。秦始皇要焚书,汉武帝要尊儒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便要教臣民忠君爱国,培养拥护祖国意识,都是用教育以生产“观
念商品”的实例。
再说教师的地位。就全体言,他们是所谓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至于厨子、粪夫,则是贫苦的民众,是和劳动者、贫农可以归入一种阵营的。故表面上教师是不“等于厨子、粪夫”的。然实际上,他们实有相同的运命。即因在阶级斗争益形尖锐化的现代,“精神劳动者”(知识分子)有和“筋肉劳动者”合流的趋势。生活的困难,逼得自命非凡的知识分子一日胜似一日地无产者化。虽然知识分子因受了支配阶级的教养——即上述观念商品——雅不愿自见没落,也且不容易认识自身所处的地位,以形成无产者的意识;可是历史的车轮向这个方向转动,知识分子除意识上的差异外,总难自逃于和无产者相同的运命。故教师之“等于厨子、粪夫”,从阶级形势的变化看来,是不错的。——不过,教师中之一部分,很有积财致富的,那种自当别论。
第二,舒君说“……世界最根本的事情是吃饭,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倘若中国先没有这三种人,教育家除了实行神仙的绝食、野人的裸体而外,连生命都不能保持,……”此话虽是用以证明教育事业之非神圣清高,但很容易使人误会为教育的本质便是如此。其实教育之所以这样无用,原因是在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专有品,徒供享乐消遣之用,即为上述把知识与劳动分家以后所生的结果。要知这只是阶级社会中教育的变态,而非人类社会所当有的教育的常态。知识和劳动本不应分,教育本是帮助人生存的手段。教育的结果,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只是某个社会的支配阶级的文化政策所要求,却不能说教育其物是当初就如此,未来也复如此。
第三,舒君说“你们如在人生的许多活动之中,而欢喜干教育事业,只可把教育当作平淡无奇的东西而效厨子、粪夫们的各尽所能,努力干去就行了”。舒君的原意虽为劝青年教育家“不必幻想着什么神圣清高的安琪儿,……更不必不自侪于百工之列,……”但这样的劝告法,究竟也有些不对。何以故?试拿厨子为例。我们知道厨子是专替有钱人“烧饭”的——注意,决不是为“社会服务”。——他须得训练好一副好本领,能满足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食欲,庶几能博得大小东家的欢心,以为自己“生活的工具”。有的厨子,譬如在包饭作做生意的,他便须投合吃包饭者的胃口,不仅如此,还须投合包饭作老板的意旨,好叫他可以赚钱。至于包饭作老板,也许他本身是个厨子,但他已兼有榨取者、剥削者的资格了。要之,厨子们总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如今舒君劝他们效厨子的各尽所能,努力干去,是不是要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味替少数有钱人卖力献功呢?不错,现在的教育原是少数有钱人的专有品,无产者自不必享受教育。——譬如日本政府虽厉行义务教育,但是穷人可以延迟或竟免除这个“义务”!——就是舒君也曾明白地说过:“教师的目的既在以教书为职业,自然要迎合雇主的心理而创造出许多的学理,牢笼主顾,如牧师之藉上帝之名以牢笼教徒的一般。”但我要问,舒君所希望于青年教育家者,莫非真是叫他们“努力干”这样专门迎合雇主心理的教师吗?除此以外,再没有另一型态的教师吗?舒君自己虽痛恶教育界之污浊卑贱,毅然改途,难道忍令教育界就永远如此,无须改革吗?幻想清高神圣的教育,迷信万能的教育,固属不合;但可如舒君这样蔑视教育,轻视教育,听教育终于留在“婢妾下厮”的地位而一若“也无妨”者吗?所以舒君的这种主张,除使教育事业益发糟糕、益发乌烟瘴气而外,似乎不会再有别种好处。
第四,舒君说“把教育和人生可有可无的宗教比,它们可以两不相涉,也可以彼此互相支配”。这话错了。宗教在原人,是日常生活的安慰上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的教育内容,即不外关于宗教的及关于战争的两项。为一般普通教育史家所写在第一页的古希腊教育,尚属如此。在他们,教育和宗教决不是不相涉的,教育而且受制于宗教。到了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中,宗教更被支配阶级用作愚弄人民的手段。这时候,宗教对于被压迫者,固奉为慰藉苦痛、希冀幸福的一种“鸦片”;对于压迫者,又是思想支配的一种利器;在教育上,宗教的影响尤为显著。欧洲中古千余年间,全是宗教教育支配了一切;直到最近,宗教还不能不说仍在支配着教育,安得说宗教与教育两不相涉呢?至于它们之所以发生姻缘,其理由也很简单,即因支配阶级同样地要利用宗教和教育,藉以钳制人民,威吓人民,愚弄人民,并诱惑人民。教育之被视为神圣、为清高,归根还是起于宗教的影响。
以上拉杂地已写了不少字,信笔所至,语不暇择,幸舒君有以谅之,并求舒君和读者给我以指正。
原载1929年7月20日《教育杂志》第21卷第7号
附注
①本篇署名:叶公朴。舒新城《致青年教育家》一文,发表于1929年2月《教育杂志》第21卷第2号。
②舒新城(1893—1960)又名维周、心怡。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师,历任成都高师教授、《辞海》主编、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等职。毕生关心教育问题,著有《道尔顿制概观》、《教育通论》、《近代中国留学史》等。
①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首相(1885—1888,1892—1896,1898,1900—1901)。幼名利助,改名俊辅。早年参加“尊王攘夷”和“倒幕”活动。握有权柄后,推行现代化改革,重视教育普及和对外军事扩张。毛奇(MoltkeHel-muth,1800—1891)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总参谋长(1871—
1888)。主持了德国军制的,改革,策划、指挥了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重视“军国民教育”,把国家的强盛,军事的胜利,归之于小学教师之功。
①作者原注:“所谓教育为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手段一语,是把生活看作广义的: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获得,他方面是知识才能的自由发展;又此种生活是集体的社会底的,决不是孤立的个人底的。原人的教育虽说不到完全,但他们的教育却合乎社会集体的需要,而各个人自能从此中得到满足;还有,此语看似‘平淡无奇’,实为一部分学者所怕讲。他们宁愿讲什么教育哲学,谈什么教育原理,却讳言这样粗浅的话。因为这句话太大众化了,太接近实际生活了。”
②作者原注:“如古代的奴隶及农奴等,就没有正式享受教育的权利,但却不能即说他们毫无教育。他们原不受国家法定的教育,可是自有社会生活需要的教育,如欧洲中世纪的工艺品及建筑物,精妙无比;此种技能的获得,决不能不有赖于教育。不过这种教育,只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制度。通常写教育史的,只留意到支配阶级的教育制度,而全不顾虑到被支配阶级的这种教育行动,所以有意无意地使人们获有如下的一种意见,即以国家明定的教育制度算是教育全体,又误以为那种教育就是全人类的教育。其实自有历史——社会分成阶级的所谓文明时代的历史——以来,从未有过普及全人类的教育。我们要知道这是自命为教育史家或教育学家所负历史的罪过。即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进到现下的帝国主义时代,教育的名号算是普及了,而且还叫做义务教育,但实际现在的教育仍是供支配阶级之用,不过不曾也不肯公言罢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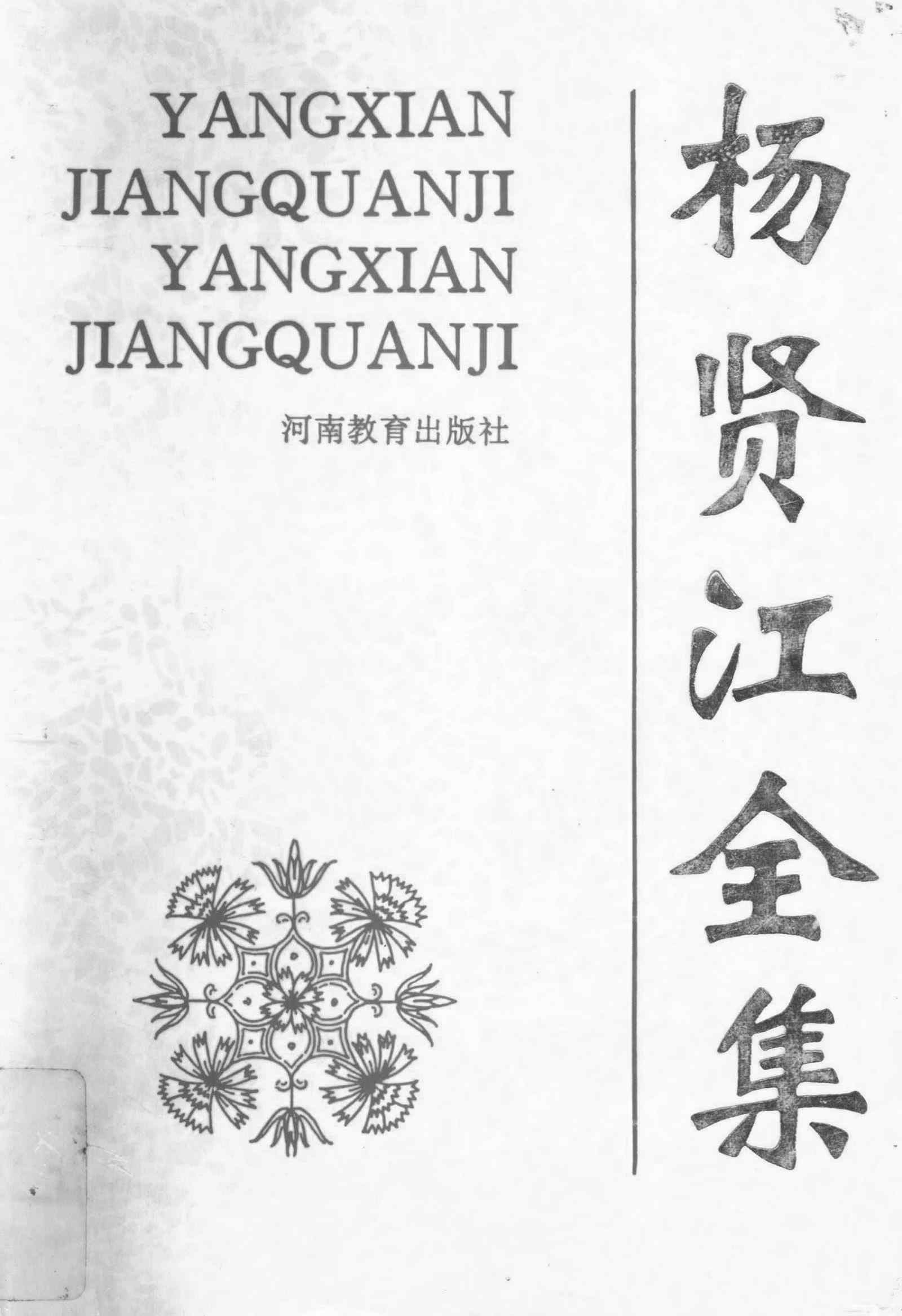
《杨贤江全集 第三卷》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本书为杨贤江全集第三卷,1929~1931年采用文论与专著混合编年方式,具体“编年”原则为:(1)写作(包括演讲等)和发表时间皆备者,以写作时间为据;(2)无写作时间而有发表时间者,以发表时间为据;(3)写作和发表时间皆无者,由编者考定时间,置于相应的时段之后,并在题注中予以说明;(4)报刊上连载的文论,以第一部分的发表时间为编排依据。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