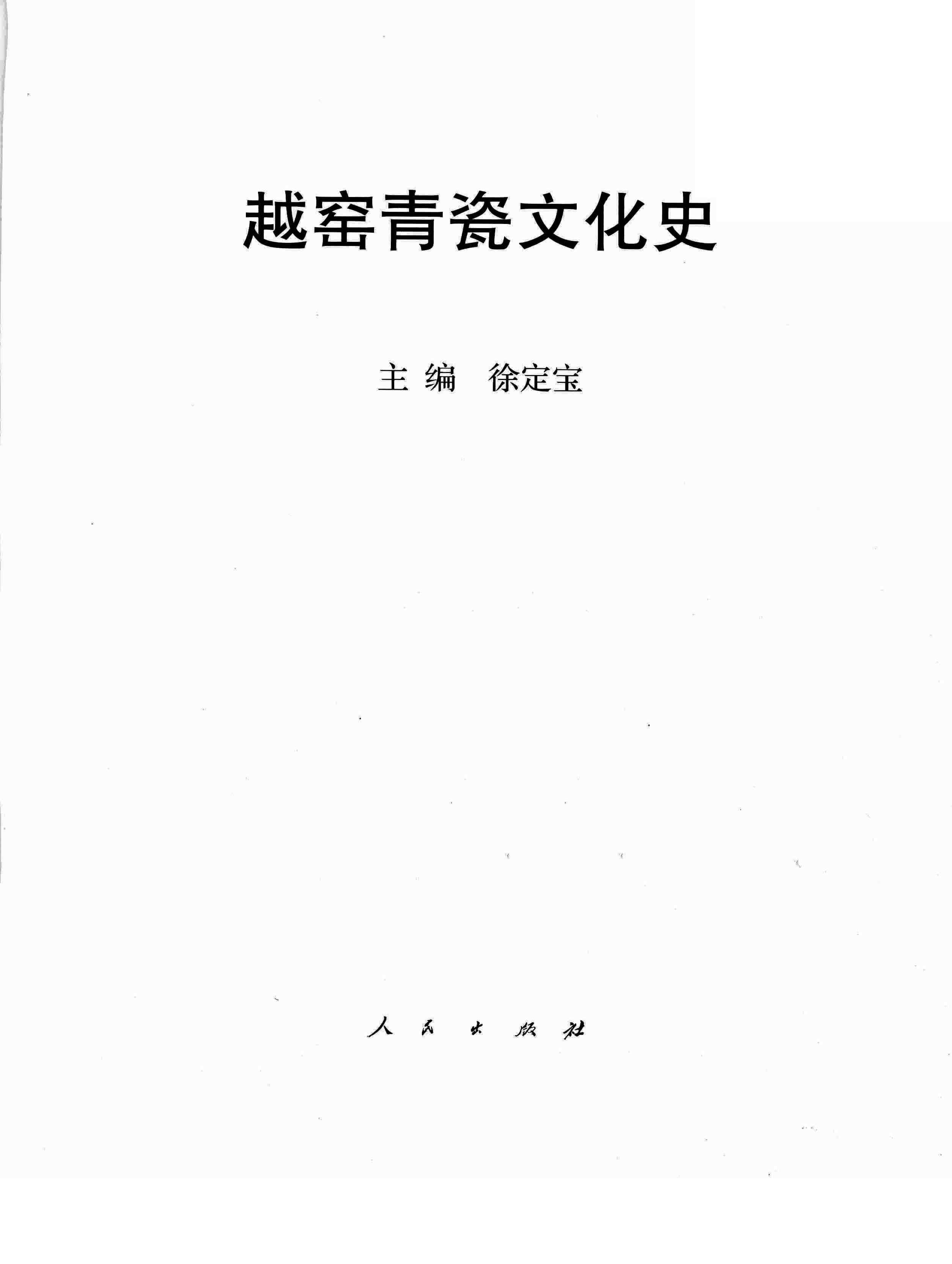第二节 海上陶瓷之路
内容
当西汉王朝迈进鼎盛期时,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出了杰出的使臣张骞访问西域诸国。这位大使在两次出使十余年间内完成了开拓名垂青史的大陆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和西域诸国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展。当封建社会发展至鼎盛期唐代时,丝绸之路已经不能适应国际交流发展之需,于是,另一条国际大道——海上陶瓷之路的开拓事业应运而生。陶瓷产品不但适宜于大批量海上运输而且安全系数大,不易破损,于是,陶瓷制品便大量地从海上涌向世界各地,特别是创制最早的越窑青瓷和后起之秀龙泉青瓷、邢窑白瓷等等,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珍视。
瓷器的外运,最初是零散进行的,如朝廷赐赠周边国家的使节作为礼品,各国商人、僧侣等往来中国者将瓷器作为土特产带回自己的国家,数量很有限,但得到各国人民珍视之后,朝廷便予以重视,于是进行有计划、有意识、有目的的开拓,最终形成海上国际交往大通道。
陶瓷之路的源头在明州(今宁波)。宁波的大量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其一,明州及附近位于杭州湾南岸的慈溪、上虞是世界瓷文化的发祥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研究证明,远在夏商至东汉明期,瓷器的胚胎已在这里孕育出来,经过两千年的不断培育、成长,瓷器至东汉已经成熟,出落成令人顾盼的文明之花。此后,它便在这一地区持续发展,不断完善。越国崛起后,这里更发展成为令人神往的青瓷重镇。经唐、五代、北宋,慈溪上林湖已经成为美名远扬的瓷都。其二,明州港自古便是中国著名的深水良港,战国时期它便是我国的重要海港,至唐代更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商贾云集、货物丰沛的大海港,被朝廷指定为大唐帝国对外开放的大港之一,与扬州、广州并列为中国三大口岸。唐廷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五代、北宋均有朝廷设立的专门商贸机构。这一重要地位一直持续了400多年。
由于这两种天赐良缘,明州港自然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活水。自唐贞元年间,这里的主要贸易品便是越窑青瓷,至唐大中年间形成瓷器贸易的第一高峰。随着瓷器的精品秘色瓷的开创,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外销出现了新的高潮。其后,中国瓷业遍地开花,不但产量大增,而且品种多姿多采,魅力无穷,于是内销、外销量均大增,外销出现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局面。
自于自唐至元,瓷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明州港,这里成为全国诸多瓷窑产品的集散地,其辐射面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并且由近而远,不断拓展。“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将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海底沉船打捞发现的典型瓷器遗存、各种文献资料综合起来,陶瓷之路示意图可以这样来勾勒:自唐代起,闽浙各地瓷器汇集至明州港装船,领取出口证件后,扬帆出海,沿今中南半岛南下,横渡暹罗湾,可至马来半岛中部,穿过克拉地峡进入印度洋,经缅甸、孟加拉、印度东海岸西行;亦可继续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南印度、巴基斯坦、阿曼等地抵达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后来,这条航线进一步疏通,从海上向西亚、北非、东非以及地中海沿岸伸展,越过阿曼,进入红海。
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从明州港始发,经山东登州渡海,抵达朝鲜半岛;从明州港起航,横渡东海,抵达日本列岛九州;从明州港起航至泉州,经台湾南部抵达菲律宾南部的吕宋岛,再南航,则可抵达沙捞越(今马来西亚东北部),亦可抵达爪哇岛东部。唐代,商船由明州港驶向广州,出海扬帆,驶向阿拉伯海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伊朗在这条航线上地位显赫。《新唐书》卷43下,对这条航线已有较为具体、明确的记述。在8世纪70、80年代至8世纪末,外国商船亦由这些航线扬帆至广州,再抵明州。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则可直达。成书于9世纪、10世纪的《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和宝石矿》等著作,对此均有简略的描述。后者称:“在黄巢起义以前,中国商舶皆直扬帆至阿曼”等亚非诸国,“而此等地方之商舶,当时亦直接通航于中国诸港。”据宋代学者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时,已有20多个国家从海上陶瓷之路与我国进行贸易交往;其中,宋廷东渡日本的商船已达20余起。明以后,陶瓷之路则继续向外扩展、伸延,由红海至非洲再转由地中海至欧洲。这时的中国瓷器更加孕英含粹、千姿百态,陶瓷之路亦随之不断拓展、延伸,对外贸易港口除三大港以外,杭州、泉州等均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中国瓷器如同海水一般涌入亚非欧美洲诸国,外国商人无不视之为奇货。明万历四十二年,荷兰一只商船一次就运载我国瓷器7万多件,瑞典于1750年以后5年内从陶瓷之路进口的中国瓷器达1100万件之多。
陶瓷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不仅促进了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而且在精神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诸蕃志》记载:在中国瓷器未进入东南亚之前,那里的人没有饮食器皿,仅以树叶、蕉叶、贝壳为餐具,“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欧洲在未获得中国瓷器前,一般人家以粗陶或木制品为饮食器,上层社会采用金属器皿。法国学者罗伯特·路威的《文明与野蛮》一书对此有所描述。对于人类生活、健康和审美来说,瓷器自然十分优于金属或木头制品。陶瓷之路使他们见到了光彩照人的中国瓷器,所以,无不如获至宝。英国学者马德休斯的《山间邮路》一书记述道:“瓷器精美而昂贵,只有达官显贵才买得起。”海上陶瓷大道的拓展消解了这种状况,17世纪中国瓷器已普及到英国每个较为富裕的市民家庭中。再过一个世纪,中国瓷器已进入一般家庭,“英国的每一个乡村人家都能见到它”。英国著名学者爱特生一唱三叹地写道:“如果没有海外贸易输入各种物品..英国将会成为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社会..”不仅英国如此,其他各国亦复如此。他们称瓷器为china。看来,他们是从中国瓷器开始认识中国的。
在非洲,中世纪末便十分珍视中国瓷器,上层社会无不以家藏中国瓷器精品为荣耀。人们将其作为财富和高雅的象征。
在欧洲,中国瓷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人们把是否藏有中国瓷器作为自己的身份和声望的标识。欧洲瓷器的生产正是在中国瓷的影响和启迪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陶瓷之路对世界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推动了世界瓷艺的发展。11世纪,宋代青瓷传入波斯,波斯人民仿制出晶莹润泽的青釉陶,但仍烧制不出瓷器。阿拔斯大帝酷好中国瓷器,于是特聘300名中国瓷艺家前去传授瓷技。中国瓷器传入欧洲后,价重如金,于是欧洲人开始了中国瓷的仿制,法国人的仿制与研究可谓用尽心计。显然,欧洲的现代陶瓷工业,是在继承我国陶瓷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总之,海上陶瓷之路对世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是绝不亚于物质文化方面的。
自然,在陶瓷之路上,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西域文化渐次传入中国,其中有音乐、舞蹈、服饰和葡萄、鹦鹉等动植物等等。这大量反映在瓷器上。唐代古墓出土的瓷器上的乐俑装饰中,有两个坦胸露背的少女,踏着欢快的鼓乐节奏翩翩起舞,大有奔放刚健的龟兹乐舞风调。这显然是唐代人民引进了这种乐舞并流行起来的结果。浙东出土的五代越窑中以鹦鹉图装饰的瓷器,优美异常,尤其是余姚出土的青瓷碟上的鹦鹉图,更充分表明是以鹦鹉的灵巧、美丽的体态神情为素材构思而成的。随着佛教的传入(按:已有学者经考证后确认,佛教最初并不是由西南陆路传入中国的,而是由东南海路传入中国的。这样,陶瓷之路便增加了佛教的内涵),佛教文化中常见的佛像、莲花等随之成为中国瓷器常用的装饰图案,荷花缸、盆、碟随处可见,有的整个瓷器便是一朵露珠流转的荷花。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拓、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又是一个从善如流,善于借鉴、吸纳、发展外来文化以丰富发展本民族原生文化的伟大民族。
陶瓷之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将永远启示、激励人们不断进行新的开拓。正因如此,当考古家们在古埃及的政治、经济中心福斯塔特(在今开罗南边)发现了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之后,人们进一步明白了中埃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日本学者三上次男1966年到红海岸畔的著名古城库赛尔考察时,又见到了大量唐宋的越窑青瓷,这位学者受到了巨大震撼之后,写成了名著《陶瓷之路》。由于他首先精辟地提出并阐述了这个一崭新概念,科学而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瓷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因之得到了各国学者的认同,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瓷文化的巨大兴趣。
陶瓷之路沿线已发现的考古成果大致如下:
日本:
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2500多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10.1厘米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鳆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州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满胎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英国、1947~1948年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发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4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文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其中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刻划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和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苏莱曼在《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已开始,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瓷之路”上的船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的美誉。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唐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半岛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陆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书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中国在汉朝已有使臣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通过安息道,来自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伊朗人民尤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中国陶瓷在伊朗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司、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与浙江慈溪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面,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1.2万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为中国唐代至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2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他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瓷器的外运,最初是零散进行的,如朝廷赐赠周边国家的使节作为礼品,各国商人、僧侣等往来中国者将瓷器作为土特产带回自己的国家,数量很有限,但得到各国人民珍视之后,朝廷便予以重视,于是进行有计划、有意识、有目的的开拓,最终形成海上国际交往大通道。
陶瓷之路的源头在明州(今宁波)。宁波的大量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其一,明州及附近位于杭州湾南岸的慈溪、上虞是世界瓷文化的发祥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研究证明,远在夏商至东汉明期,瓷器的胚胎已在这里孕育出来,经过两千年的不断培育、成长,瓷器至东汉已经成熟,出落成令人顾盼的文明之花。此后,它便在这一地区持续发展,不断完善。越国崛起后,这里更发展成为令人神往的青瓷重镇。经唐、五代、北宋,慈溪上林湖已经成为美名远扬的瓷都。其二,明州港自古便是中国著名的深水良港,战国时期它便是我国的重要海港,至唐代更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商贾云集、货物丰沛的大海港,被朝廷指定为大唐帝国对外开放的大港之一,与扬州、广州并列为中国三大口岸。唐廷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五代、北宋均有朝廷设立的专门商贸机构。这一重要地位一直持续了400多年。
由于这两种天赐良缘,明州港自然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活水。自唐贞元年间,这里的主要贸易品便是越窑青瓷,至唐大中年间形成瓷器贸易的第一高峰。随着瓷器的精品秘色瓷的开创,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外销出现了新的高潮。其后,中国瓷业遍地开花,不但产量大增,而且品种多姿多采,魅力无穷,于是内销、外销量均大增,外销出现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局面。
自于自唐至元,瓷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明州港,这里成为全国诸多瓷窑产品的集散地,其辐射面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并且由近而远,不断拓展。“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将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海底沉船打捞发现的典型瓷器遗存、各种文献资料综合起来,陶瓷之路示意图可以这样来勾勒:自唐代起,闽浙各地瓷器汇集至明州港装船,领取出口证件后,扬帆出海,沿今中南半岛南下,横渡暹罗湾,可至马来半岛中部,穿过克拉地峡进入印度洋,经缅甸、孟加拉、印度东海岸西行;亦可继续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南印度、巴基斯坦、阿曼等地抵达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后来,这条航线进一步疏通,从海上向西亚、北非、东非以及地中海沿岸伸展,越过阿曼,进入红海。
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从明州港始发,经山东登州渡海,抵达朝鲜半岛;从明州港起航,横渡东海,抵达日本列岛九州;从明州港起航至泉州,经台湾南部抵达菲律宾南部的吕宋岛,再南航,则可抵达沙捞越(今马来西亚东北部),亦可抵达爪哇岛东部。唐代,商船由明州港驶向广州,出海扬帆,驶向阿拉伯海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伊朗在这条航线上地位显赫。《新唐书》卷43下,对这条航线已有较为具体、明确的记述。在8世纪70、80年代至8世纪末,外国商船亦由这些航线扬帆至广州,再抵明州。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则可直达。成书于9世纪、10世纪的《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和宝石矿》等著作,对此均有简略的描述。后者称:“在黄巢起义以前,中国商舶皆直扬帆至阿曼”等亚非诸国,“而此等地方之商舶,当时亦直接通航于中国诸港。”据宋代学者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时,已有20多个国家从海上陶瓷之路与我国进行贸易交往;其中,宋廷东渡日本的商船已达20余起。明以后,陶瓷之路则继续向外扩展、伸延,由红海至非洲再转由地中海至欧洲。这时的中国瓷器更加孕英含粹、千姿百态,陶瓷之路亦随之不断拓展、延伸,对外贸易港口除三大港以外,杭州、泉州等均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中国瓷器如同海水一般涌入亚非欧美洲诸国,外国商人无不视之为奇货。明万历四十二年,荷兰一只商船一次就运载我国瓷器7万多件,瑞典于1750年以后5年内从陶瓷之路进口的中国瓷器达1100万件之多。
陶瓷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不仅促进了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而且在精神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诸蕃志》记载:在中国瓷器未进入东南亚之前,那里的人没有饮食器皿,仅以树叶、蕉叶、贝壳为餐具,“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欧洲在未获得中国瓷器前,一般人家以粗陶或木制品为饮食器,上层社会采用金属器皿。法国学者罗伯特·路威的《文明与野蛮》一书对此有所描述。对于人类生活、健康和审美来说,瓷器自然十分优于金属或木头制品。陶瓷之路使他们见到了光彩照人的中国瓷器,所以,无不如获至宝。英国学者马德休斯的《山间邮路》一书记述道:“瓷器精美而昂贵,只有达官显贵才买得起。”海上陶瓷大道的拓展消解了这种状况,17世纪中国瓷器已普及到英国每个较为富裕的市民家庭中。再过一个世纪,中国瓷器已进入一般家庭,“英国的每一个乡村人家都能见到它”。英国著名学者爱特生一唱三叹地写道:“如果没有海外贸易输入各种物品..英国将会成为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社会..”不仅英国如此,其他各国亦复如此。他们称瓷器为china。看来,他们是从中国瓷器开始认识中国的。
在非洲,中世纪末便十分珍视中国瓷器,上层社会无不以家藏中国瓷器精品为荣耀。人们将其作为财富和高雅的象征。
在欧洲,中国瓷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人们把是否藏有中国瓷器作为自己的身份和声望的标识。欧洲瓷器的生产正是在中国瓷的影响和启迪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陶瓷之路对世界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推动了世界瓷艺的发展。11世纪,宋代青瓷传入波斯,波斯人民仿制出晶莹润泽的青釉陶,但仍烧制不出瓷器。阿拔斯大帝酷好中国瓷器,于是特聘300名中国瓷艺家前去传授瓷技。中国瓷器传入欧洲后,价重如金,于是欧洲人开始了中国瓷的仿制,法国人的仿制与研究可谓用尽心计。显然,欧洲的现代陶瓷工业,是在继承我国陶瓷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总之,海上陶瓷之路对世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是绝不亚于物质文化方面的。
自然,在陶瓷之路上,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西域文化渐次传入中国,其中有音乐、舞蹈、服饰和葡萄、鹦鹉等动植物等等。这大量反映在瓷器上。唐代古墓出土的瓷器上的乐俑装饰中,有两个坦胸露背的少女,踏着欢快的鼓乐节奏翩翩起舞,大有奔放刚健的龟兹乐舞风调。这显然是唐代人民引进了这种乐舞并流行起来的结果。浙东出土的五代越窑中以鹦鹉图装饰的瓷器,优美异常,尤其是余姚出土的青瓷碟上的鹦鹉图,更充分表明是以鹦鹉的灵巧、美丽的体态神情为素材构思而成的。随着佛教的传入(按:已有学者经考证后确认,佛教最初并不是由西南陆路传入中国的,而是由东南海路传入中国的。这样,陶瓷之路便增加了佛教的内涵),佛教文化中常见的佛像、莲花等随之成为中国瓷器常用的装饰图案,荷花缸、盆、碟随处可见,有的整个瓷器便是一朵露珠流转的荷花。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拓、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又是一个从善如流,善于借鉴、吸纳、发展外来文化以丰富发展本民族原生文化的伟大民族。
陶瓷之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将永远启示、激励人们不断进行新的开拓。正因如此,当考古家们在古埃及的政治、经济中心福斯塔特(在今开罗南边)发现了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之后,人们进一步明白了中埃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日本学者三上次男1966年到红海岸畔的著名古城库赛尔考察时,又见到了大量唐宋的越窑青瓷,这位学者受到了巨大震撼之后,写成了名著《陶瓷之路》。由于他首先精辟地提出并阐述了这个一崭新概念,科学而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瓷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因之得到了各国学者的认同,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瓷文化的巨大兴趣。
陶瓷之路沿线已发现的考古成果大致如下:
日本:
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2500多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10.1厘米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鳆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州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满胎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英国、1947~1948年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发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4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文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其中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刻划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和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苏莱曼在《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已开始,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瓷之路”上的船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的美誉。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唐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半岛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陆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书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中国在汉朝已有使臣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通过安息道,来自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伊朗人民尤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中国陶瓷在伊朗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司、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与浙江慈溪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面,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1.2万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为中国唐代至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2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他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