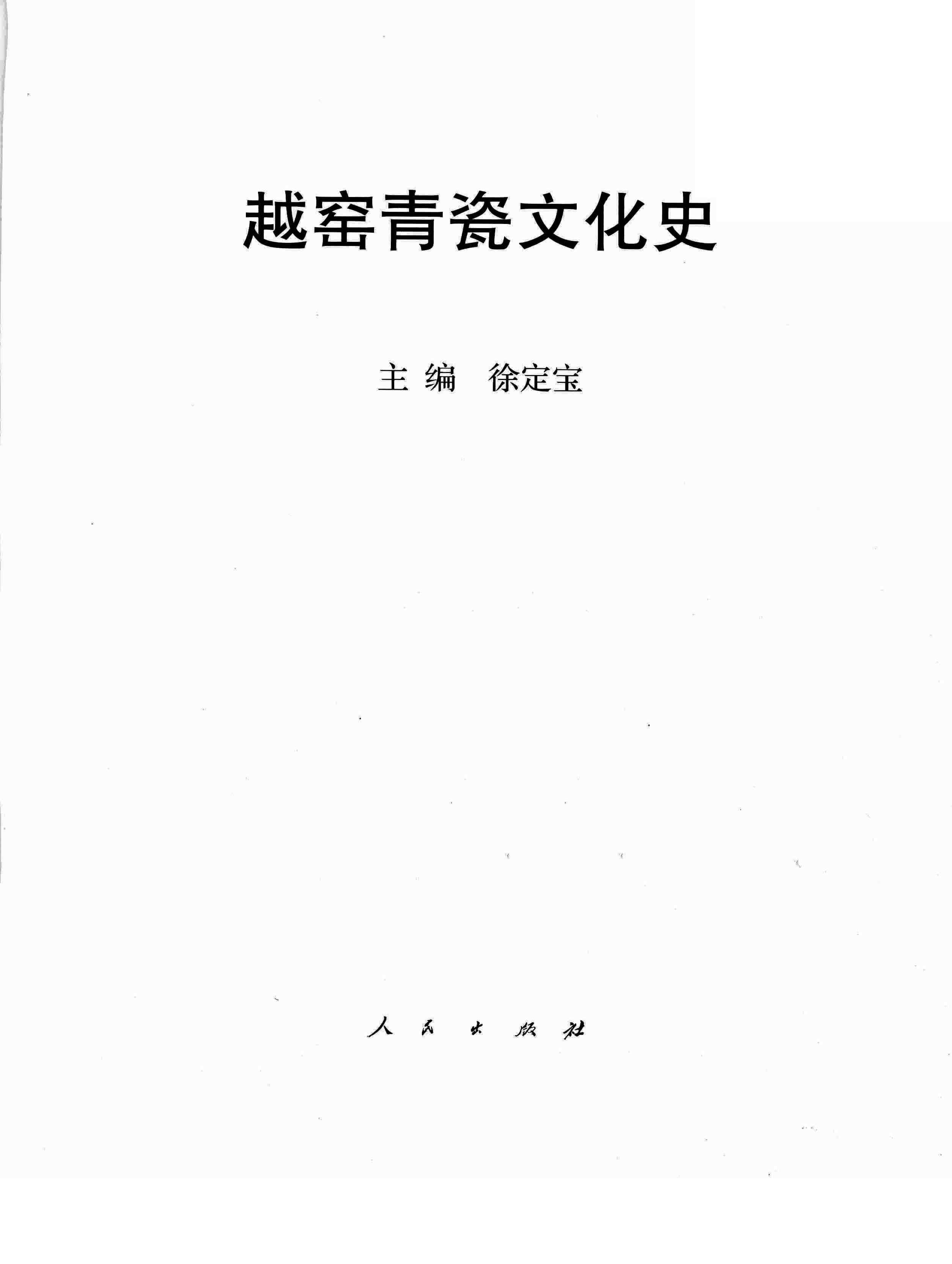内容
越窑青瓷演进至唐五代,不论在工艺上抑或是在艺术特色上都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从审美的角度看,此时作为成熟期的越窑青瓷,已摆脱了早期受陶器、青铜器等相关工艺的造型及装饰的影响,形成具有自身特性的、能充分展示青瓷釉色之美、并在造型和装饰上具有青瓷特色的审美特征。
一、材质之美
瓷器的材质可分为胎质和釉质。
虽然青瓷的材质之美更多地是体现在釉质上,但胎质的色质、细腻程度却对青瓷的外观和釉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东汉到唐初的较长一段时期里,窑工们虽然对瓷土进了选料和淘洗,但淘洗得不够精细,而唐代中晚期坯泥在成型前则往往要经过严格的选料,很好的粉碎和淘洗,并充分揉练。因此,瓷胎细腻致密,无分层现象,这不仅为瓷器的精细加工提高了必要的保证,同时更能使瓷器质地显得细腻、温润而少瑕疵,从而提高青瓷的品相。
绞胎瓷虽不源于越窑,但越窑在掌握了这技术以后,却能成功通过瓷胎材质的不同组合,烧制出绞胎瓷。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出土的灵芝纹伏兽脉枕,其灵芝图案就是利用两种不同色调的瓷土相间糅合在一起,使之自然产生两色相间的纹理,其图案纹理浑然天成,有着十分自然的艺术效果。
“姿如圭璧,色似烟岚”的釉色之美,是越窑青瓷的最大特色。晚唐、五代诗人徐夤曾有过这样的赞美:“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烧成技术的提高是釉色精美的必要保证,而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的提高则是釉色精美的前提,同时使用匣钵密封烧成也使釉面不会有烟熏或粘附砂粒的缺陋,从而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绝妙色泽。莹润如玉、清澈典雅的釉色是越窑青瓷能成为一代名瓷的关键所在。
除清纯釉色外,褐斑加彩也是越窑巧用釉色的一种艺术手法,它能丰富器表的色彩,增加色调的变化,从而通过釉色来表现独特的审美追求。褐斑最初的出现可能只是一种工艺缺陷,或是因着釉的某一部分含铁量较高,或是在与黑瓷同窑烧制中,青釉器物沾上了黑釉浆,然而这无意间产生的奇妙效果,却通过窑工们有意的追求,在不断的探索中将其发展为一种独特的装点瓷器的艺术手段。
二、造型之美
唐代越窑青瓷的造型,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青瓷造型特点,同时由于不同时代和不同人文背景,加之青瓷烧制工艺的提高等因素,又明显地打上这一时期的时代烙印。
总体来看,以动物形为主的拟形器数量已相对较少,而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外型设计却多了起来,例如将茶盏设计成边缘起伏,如一朵盛开的荷花,而托具则呈一卷边荷叶,花与叶珠联璧合,在清纯的釉色映照下,宛如出水之芙蓉,令人赏心悦目。
形式美法则的广泛运用也是这一时期造型的一大特点,每一种器型的出现,由不定型向规整化转变,由自然法则向人工法则进化,而形式美感也就逐步地孕育而成,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变。从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局部的点缀和装饰皆能遵从对称、均衡、主从协调等法则。尤其是设计中没有因过多的装饰和点缀而使器物有一种华而不实、喧宾夺主的感觉,这也有别于前代一些青瓷器的过分装饰,此期人们更注重实用和审美的结合。
由粗犷到精巧,不仅是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的不同,同时也是制瓷工艺自身进步带来的。唐代的青瓷器中出现了许多细巧玲珑的小件瓷器,式样优美,刻划精工,胎体精薄,与前代的青瓷相比,唐代青瓷造型在细节上的精工细作,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唐代青瓷工艺达到高峰的一个标志。
三、文饰之美
由于工艺的进步,特别是施釉技术的成熟,唐以后的青瓷文饰图案以线刻较多,雕刻则以薄意为主,这符合瓷器作为日用器物在不影响实用的前提下进行文饰美化的工艺美术宗旨,同时,也为能充分展示青瓷整体艺术效果,使得文饰与青瓷的釉色及瓷器的造型相得益彰,找到了最佳装饰手段,使青瓷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清新高雅的艺术品貌。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青瓷制造工艺自身的进步,特别是贡窑产品在质量上的严格要求,使胎料的精选及淘洗的细腻更进一步,为线刻和薄意雕作好了材质上的准备。因为凹刻线的精工与流畅,薄意雕的精微与细致只有在胎料细腻的条件下才能得以显现。施釉技术的提高与成熟,则为这一文饰手法提供了工艺上的支持。我们知道,在制瓷工艺中,凹刻线有着容易被釉层遮没或填塞的缺点,因此,线条往往质感不强,轮廓模糊。同时由于凹线底部的积灰不易被清除,易造成工艺上“缩釉”。因此,在施釉技术没有达到较高水准之前,凹线纹饰要成为刻划的主要手法是不可想像的。凸线露筋的手法在有些瓷器的造型中也常常使用,由于凸线不易被釉层覆盖,加之釉的流动性,其颜色往往要淡一些,这使它不仅清晰,而且协调,合理地运用,不仅使瓷器的体积感更加强化,同时也使有些雕刻更具立体感。
由于唐以后,青瓷制品主要以日用器为主,专为陪葬所制的青瓷器,特别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精神需要、具有特定文化观念的精神用器大量减少,因此,装饰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器物的美化方式,而薄意雕刻的线刻正在于它基本不影响或破坏瓷器的实用性,故而在文饰中得以广泛应用,这也是唐代以后青瓷日用器与魏晋南北朝大量墓葬出土的精神用器在装饰手法上的差异所在,因此,成熟期的青瓷制品并没有多少华而不实、过分文饰的现象。
伴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各地瓷窑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艺。越窑青瓷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较为多样的工艺和文饰手法。然而,绞胎瓷在越窑瓷器中为什么只是绝无仅有的尝试,难道越窑排斥外来技术?褐斑加彩虽能丰富器表的色彩,为什么没有广泛使用,后来却发展为以较精细的褐色线,难道是对器表色彩的忽略?其实,以线刻与薄意雕刻作为装饰青瓷器的主要手法,恰恰更能突出青瓷“色似烟岚”的釉色之美,可以说青瓷的特色与魅力正在于其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釉色。绞胎瓷技术和釉下彩手法虽然可以丰富器表釉色,但同时,也破坏了青瓷釉色清纯雅致的艺术风格。因此,不靠丰富的色彩点缀,而以清纯取胜,以线刻和薄意雕刻作为主要装饰手法,可以说正是青瓷作为一代名瓷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也是青瓷工艺发展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古代陶瓷文饰艺术手法的产生和形成,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古人所云“塑画同源”正道出了两者的联系。薄意雕刻明显受到了当时画风的影响。在中国绘画史上,北齐著名画家曹仲达画风十分独特,其画常以细密线条循身体体积结构进行起伏刻划,故其笔下人物的衣服皆好像受了水一般紧贴身上而显现出人体的特点,这种风格被人们称之为“曹衣出水”,在当时画坛,人们竞相仿效,盛极一时。这种风气无疑对陶瓷艺术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薄意雕充分利用线与型两者的关系,在线条之美中展现造型之美,通过线的运用,使形体更加突出,体积感更强,使人们能从中窥视到“出水”之韵。
较之于前,繁盛期的青瓷在装饰纹样的题材上显得更加丰富,除了传统的一些抽象纹样和动物纹样外,植物纹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题材,此外,还出现了以人物纹作为装饰的题材,这可能是受到勒石造像的影响,而莲花纹与摩羯纹的大量出现,显然是佛教文化兴盛的产物。
总的来说,不论是造型还是文饰,作为青瓷艺术美构成的一个方面,与青瓷本身的品质都是统一的,它是特定历史和人文背景下的产物,繁盛期越窑青瓷材质、造型、文饰的珠联璧合,让人们叹服于古代窑工的艺术创造力,这种别具匠心的艺术创造,更给人们带来了美的愉悦,唤起了人们的悠远遐想。
一、材质之美
瓷器的材质可分为胎质和釉质。
虽然青瓷的材质之美更多地是体现在釉质上,但胎质的色质、细腻程度却对青瓷的外观和釉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东汉到唐初的较长一段时期里,窑工们虽然对瓷土进了选料和淘洗,但淘洗得不够精细,而唐代中晚期坯泥在成型前则往往要经过严格的选料,很好的粉碎和淘洗,并充分揉练。因此,瓷胎细腻致密,无分层现象,这不仅为瓷器的精细加工提高了必要的保证,同时更能使瓷器质地显得细腻、温润而少瑕疵,从而提高青瓷的品相。
绞胎瓷虽不源于越窑,但越窑在掌握了这技术以后,却能成功通过瓷胎材质的不同组合,烧制出绞胎瓷。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出土的灵芝纹伏兽脉枕,其灵芝图案就是利用两种不同色调的瓷土相间糅合在一起,使之自然产生两色相间的纹理,其图案纹理浑然天成,有着十分自然的艺术效果。
“姿如圭璧,色似烟岚”的釉色之美,是越窑青瓷的最大特色。晚唐、五代诗人徐夤曾有过这样的赞美:“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烧成技术的提高是釉色精美的必要保证,而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的提高则是釉色精美的前提,同时使用匣钵密封烧成也使釉面不会有烟熏或粘附砂粒的缺陋,从而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绝妙色泽。莹润如玉、清澈典雅的釉色是越窑青瓷能成为一代名瓷的关键所在。
除清纯釉色外,褐斑加彩也是越窑巧用釉色的一种艺术手法,它能丰富器表的色彩,增加色调的变化,从而通过釉色来表现独特的审美追求。褐斑最初的出现可能只是一种工艺缺陷,或是因着釉的某一部分含铁量较高,或是在与黑瓷同窑烧制中,青釉器物沾上了黑釉浆,然而这无意间产生的奇妙效果,却通过窑工们有意的追求,在不断的探索中将其发展为一种独特的装点瓷器的艺术手段。
二、造型之美
唐代越窑青瓷的造型,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青瓷造型特点,同时由于不同时代和不同人文背景,加之青瓷烧制工艺的提高等因素,又明显地打上这一时期的时代烙印。
总体来看,以动物形为主的拟形器数量已相对较少,而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外型设计却多了起来,例如将茶盏设计成边缘起伏,如一朵盛开的荷花,而托具则呈一卷边荷叶,花与叶珠联璧合,在清纯的釉色映照下,宛如出水之芙蓉,令人赏心悦目。
形式美法则的广泛运用也是这一时期造型的一大特点,每一种器型的出现,由不定型向规整化转变,由自然法则向人工法则进化,而形式美感也就逐步地孕育而成,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变。从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局部的点缀和装饰皆能遵从对称、均衡、主从协调等法则。尤其是设计中没有因过多的装饰和点缀而使器物有一种华而不实、喧宾夺主的感觉,这也有别于前代一些青瓷器的过分装饰,此期人们更注重实用和审美的结合。
由粗犷到精巧,不仅是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的不同,同时也是制瓷工艺自身进步带来的。唐代的青瓷器中出现了许多细巧玲珑的小件瓷器,式样优美,刻划精工,胎体精薄,与前代的青瓷相比,唐代青瓷造型在细节上的精工细作,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唐代青瓷工艺达到高峰的一个标志。
三、文饰之美
由于工艺的进步,特别是施釉技术的成熟,唐以后的青瓷文饰图案以线刻较多,雕刻则以薄意为主,这符合瓷器作为日用器物在不影响实用的前提下进行文饰美化的工艺美术宗旨,同时,也为能充分展示青瓷整体艺术效果,使得文饰与青瓷的釉色及瓷器的造型相得益彰,找到了最佳装饰手段,使青瓷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清新高雅的艺术品貌。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青瓷制造工艺自身的进步,特别是贡窑产品在质量上的严格要求,使胎料的精选及淘洗的细腻更进一步,为线刻和薄意雕作好了材质上的准备。因为凹刻线的精工与流畅,薄意雕的精微与细致只有在胎料细腻的条件下才能得以显现。施釉技术的提高与成熟,则为这一文饰手法提供了工艺上的支持。我们知道,在制瓷工艺中,凹刻线有着容易被釉层遮没或填塞的缺点,因此,线条往往质感不强,轮廓模糊。同时由于凹线底部的积灰不易被清除,易造成工艺上“缩釉”。因此,在施釉技术没有达到较高水准之前,凹线纹饰要成为刻划的主要手法是不可想像的。凸线露筋的手法在有些瓷器的造型中也常常使用,由于凸线不易被釉层覆盖,加之釉的流动性,其颜色往往要淡一些,这使它不仅清晰,而且协调,合理地运用,不仅使瓷器的体积感更加强化,同时也使有些雕刻更具立体感。
由于唐以后,青瓷制品主要以日用器为主,专为陪葬所制的青瓷器,特别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精神需要、具有特定文化观念的精神用器大量减少,因此,装饰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器物的美化方式,而薄意雕刻的线刻正在于它基本不影响或破坏瓷器的实用性,故而在文饰中得以广泛应用,这也是唐代以后青瓷日用器与魏晋南北朝大量墓葬出土的精神用器在装饰手法上的差异所在,因此,成熟期的青瓷制品并没有多少华而不实、过分文饰的现象。
伴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各地瓷窑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艺。越窑青瓷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较为多样的工艺和文饰手法。然而,绞胎瓷在越窑瓷器中为什么只是绝无仅有的尝试,难道越窑排斥外来技术?褐斑加彩虽能丰富器表的色彩,为什么没有广泛使用,后来却发展为以较精细的褐色线,难道是对器表色彩的忽略?其实,以线刻与薄意雕刻作为装饰青瓷器的主要手法,恰恰更能突出青瓷“色似烟岚”的釉色之美,可以说青瓷的特色与魅力正在于其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釉色。绞胎瓷技术和釉下彩手法虽然可以丰富器表釉色,但同时,也破坏了青瓷釉色清纯雅致的艺术风格。因此,不靠丰富的色彩点缀,而以清纯取胜,以线刻和薄意雕刻作为主要装饰手法,可以说正是青瓷作为一代名瓷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也是青瓷工艺发展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古代陶瓷文饰艺术手法的产生和形成,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古人所云“塑画同源”正道出了两者的联系。薄意雕刻明显受到了当时画风的影响。在中国绘画史上,北齐著名画家曹仲达画风十分独特,其画常以细密线条循身体体积结构进行起伏刻划,故其笔下人物的衣服皆好像受了水一般紧贴身上而显现出人体的特点,这种风格被人们称之为“曹衣出水”,在当时画坛,人们竞相仿效,盛极一时。这种风气无疑对陶瓷艺术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薄意雕充分利用线与型两者的关系,在线条之美中展现造型之美,通过线的运用,使形体更加突出,体积感更强,使人们能从中窥视到“出水”之韵。
较之于前,繁盛期的青瓷在装饰纹样的题材上显得更加丰富,除了传统的一些抽象纹样和动物纹样外,植物纹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题材,此外,还出现了以人物纹作为装饰的题材,这可能是受到勒石造像的影响,而莲花纹与摩羯纹的大量出现,显然是佛教文化兴盛的产物。
总的来说,不论是造型还是文饰,作为青瓷艺术美构成的一个方面,与青瓷本身的品质都是统一的,它是特定历史和人文背景下的产物,繁盛期越窑青瓷材质、造型、文饰的珠联璧合,让人们叹服于古代窑工的艺术创造力,这种别具匠心的艺术创造,更给人们带来了美的愉悦,唤起了人们的悠远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