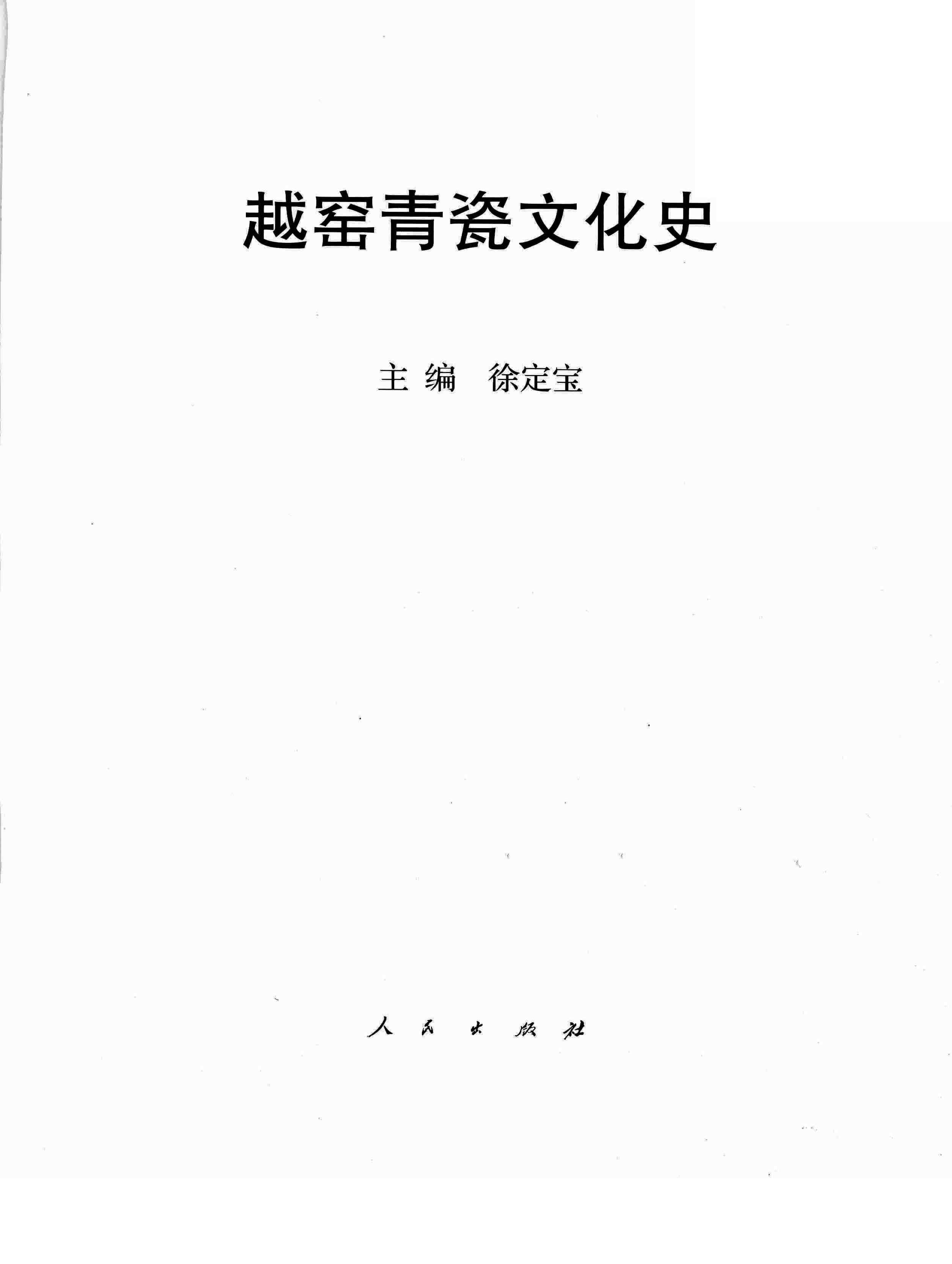内容
第一节 窑址分布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时期,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业生产出现遍地开花、相互争艳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慈溪上林湖越窑是当时南方青瓷中的杰出代表。
考古调查表明,越窑遗址均分布在唐宋时期的越州和明州政区内(今宁绍地区),以慈溪的上林湖地区、上虞的曹娥江中游地区和鄞县东钱湖地区最为密集。根据浙江省文物地图集以及有关发表资料统计,唐宋越窑遗址有293处,现简述如下:
一、慈溪市 窑业主要由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4个窑区组成,共发现171处。
上林湖窑区:位于三北群山主峰栲栳山北麓,在库区内分布着104处唐宋窑址,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20公里的湖岸线上。大部分窑址在湖的南半部,尤以木勺湾、吴石岭、横塘山、黄鳝山、荷花芯、皮刀山、沈家山、狗颈山、后施岙、牛角山、吴家溪、黄婆岙等地最为密集。从各窑址器物特征来看,可认定唐代51处,唐至北宋4处,唐、北宋9处,五代6处,五代北宋14处,北宋20处。1964年被宣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洋湖窑区:在上林湖之东,相距2公里,窑址均分布在湖的南部和西南部,在石马弄、对面山、碗片山、小弄口等地发现窑址12处。根据各窑址器物特征,可确认唐代5处,五代至北宋2处,北宋5处。
里杜湖窑区:杜湖在鸣鹤镇境内,1963年在湖的中部建一堤坝,分为里杜湖和外杜湖,外杜湖与白洋湖相连。窑址分布在里杜湖西岸中部,主要集中在碗窑山、栗子山、大黄山等沿湖平缓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15处。其中唐中期8处,北宋晚期5处。每年丰水期大部分窑址被淹,枯水期时,窑址尽露水面,破坏严重。
古银锭湖窑区:位于上林湖西南,相距2.5公里。早年已废,现为良田。窑址主要分布在石塘山、牧羊山、瓦片滩、野猫洞、汪家坪、大坪里、雉鸡山、开刀山、小姑岭等地,共有窑址29处。从器物特征来看,唐代4处,唐至五代5处,五代北宋6处,北宋8处,北宋南宋6处。
除上述4个窑区之外,其周围的上岙湖、烛溪湖、梅湖等地有窑址11处,其中唐代8处,唐、五代、北宋1处,北宋2处。
二、上虞市 在曹娥江中游两岸发现唐宋时期的窑址34处,分布在上浦镇夏家埠村的帐子山,凌湖村的窑山、台山、甑底山、橡皮地、虎皮岗、蛇头山,石井村的窑山、黄蛇山,甲仗村的庄头山、窑寺前、前岙口、栗树山、道士山、傅家岭、马岙水库、盘家湾、象里山,徐家湾村的里庵基,上宅村的水管头山等;龙浦镇魏家庄村的逍遥岙、窑甏里,前进村的风吹山、窑山、风翼梢山、大鱼山,里氏村的仙人脚掌山,湾头村的叶家山;谢桥镇岙口村的义葬山;汤霸镇蒋村的霸山;梁湖镇倪刘村的牛山等地。从器物的特征来看,唐代11处,唐至五代2处,唐至北宋2处,五代、北宋5处,五代、宋8处,北宋2处,宋4处。
三、鄞县 在东钱湖四周发现窑址39处,其中唐代2处,五代北宋37处。主要分布在五乡镇横省村的屋后山、河头湾,沙堰村的小干岭,周岙村的张家庄,仁久村的双峰山;东钱湖镇上水村的窑岙山,郭家峙村的郭童岙、王家弄、郭家峙,西村的刀子山、蛇山,马山村的窑棚,前堰头村的三甲岙;东吴镇东村的窑头山,南村的古坟潭等地。
四、余姚市 窑址主要集中在姚江两岸的丘陵地区。目前已发现窑址19处,主要分布在马渚镇杨岐岙村的王家山、窑基山,张家山下村的张家山下,藏野湖村的藏野湖;牟山镇竺山村的大园地、料勺嘴、马步龙,湖西村的窑头山;三七市镇剡岙村的橡皮山,相岙村的大池头,石步村的石步;肖东镇郭相桥村的前溪湖,莫家湖村的蛇岗;余姚镇钟家门头村的胡口弄;陆埠镇十五岙村的鲁家坟等地。这些窑址的年代为五代北宋3处,北宋16处。
五、宁海县 现发现4处。分布在茶院乡平窑村的小山,梅林镇何家村和岔路镇虎头山等地。时代均为北宋。
六、奉化市 窑址主要分布于白杜、西坞和尚田三个乡镇,以白杜乡最集中。共发现窑址11处,其中晚唐至宋2处,五代北宋6处,北宋3处。
七、象山县 窑址有2处,其中初唐1处,宋1处。分布在黄避岙乡东塔村的陈岙和丹城镇东门外东塘山。
八、镇海区 窑址主要分布于骆驼镇汶溪小洞岙村的晨钟山、何家园、小洞岙和河头乡十字路水库。目前已发现窑址4处,其中中晚唐3处,北宋1处。
九、绍兴县 发现晚唐至北宋时期的窑址1处,位于平水镇上灶村官山。
十、绍兴市 五代、北宋时期窑址2处。分别位于禹陵乡禹陵村庙湾西水山南坡和东湖乡桐梧村缸窑山东坡。
十一、诸暨市 窑址主要分布于双桥镇、湄池镇、阮市镇、直埠镇、江藻镇、马剑镇、枫桥镇等。唐代窑址有排山坞窑、孤坟仓山窑、土箕山窑、下埠头窑4处;宋代窑址有青山弄窑、月垅湾窑、骆家桥窑、凉西窑、新蒋窑、伏虎山窑、瓶甏山窑、红坞口窑、作坊村窑、龟山窑、船山窑、缸窑山窑等12处。
十二、新昌县 窑址3处,分布在拔茅镇的碗窑山、鞍山和拔茅中学,时代为宋。
十三、嵊州市 主要分布在长乐镇马面村的缸窑背,石阳村的碗盏山头,五村的碗盏山、下阳山;绿溪乡上胡村的瓷窑山;三界镇八郑村的小洋山、下郑山,傅山村的独山等。北宋窑址5处,宋3处。
上述窑址均为龙窑,分布于山麓的缓坡上,那里山峦连绵,湖泊众多,河流纵横交错;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蕴藏着大量瓷石矿,树木茂盛,燃料充足,水运便捷,为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窑址的年代、分布区域、数量及产品质量来看,唐代早期,瓷业生产还未走出低谷,未见规模可观的窑址群落,仍处恢复阶段。进入中唐以后,制瓷技术进一步改进,大量使用匣钵装烧,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窑址数量剧增,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在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上岙湖、烛溪湖以及上虞、镇海、诸暨、鄞县等地相继设立窑场,规模宏大,窑场林立。晚唐时期,瓷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跨入了繁盛时期。这时期的杰出成就是,成功地烧制出优质瓷器——秘色瓷。五代北宋初期,瓷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器类繁多,富有变化,造型轻巧优美,制作十分精致。至北宋中期,瓷业生产已停滞不前,虽有精品,但不及北宋初期的精美。北宋晚期,窑址剧减,上林湖地区仅有10余处,制作工艺衰退,大量产品采用明火装烧,制品粗糙,品种单调,刻划花纹简单、草率,瓷业生产出现大衰败态势。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晚唐时,在上林湖设立贡窑,烧制秘色瓷,贡奉朝廷。五代北宋初,吴越钱氏为了“保境安民”,对中原君主称臣纳贡,秘色瓷成了当时纳贡的重要方物之一,数量极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越窑生产秘色瓷的盛况。随着进贡瓷器的剧增,上林湖及周围的白洋湖、古银锭湖诸窑群生产的秘色瓷不能满足其需要,在上虞的窑寺前、鄞县的东钱湖等地也开辟新窑场,扩大生产规模。由于贡瓷数量与日俱增这一政治因素,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对以上林湖瓷业为中心的越州窑系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窑具铭文的考古发现
1984年文物部门对上林湖地区的瓷窑址进行全面调查,1985年又进行复查,发现瓷窑址190余处,采集了大量的实物标本,在窑具上发现了许多刻划姓(名)氏的铭文。如姚蒲奴、王蒿、魏文、徐信记、马、何、朱、王等。由此引起了古陶瓷研究者的注意,并对之进行多次专题调查、研究,称这些留下姓氏的匠人为“上林窑工。”(1)这批铭文的出土,是研究唐宋时期制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也是探讨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的实物依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窑具铭文72例(表七)。
“窑具”一词,不是广义上的瓷业生产工具,而是专指直接服务于制品烧成的用具,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匣具、垫具、间隔具三类。(2)在72例窑具铭文中,匣具57例,间隔具15例。按窑具质地来分,瓷质窑具44例,夹砂耐火土窑具28例。在46例瓷质窑具中,除1件环形垫圈外,均为匣钵。瓷质匣钵在装烧时,叠接处涂釉密封,烧成后,须破匣钵,才能取出器物,为一次性匣钵。从铭文内容来看,可分为数字和姓名二大类。数字为5例,姓名67例。按采集地点排列,后施岙Y66,黄鳝山Y26出土的标本较多,分别为9例和11例,其他窑址较少。
匣钵是用来装烧瓷坯的。在匣钵外壁刻划姓名,是表示制品的所有者。入窑装烧,烧成后出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某个窑位的制品是谁的,不会与他人的制品混乱。晚唐时期的Y66和Y26窑址出土有“余”、“马”、“马公”、“马公受”、“马使”、“王嵩”、“罗业师记”、“徐庆记烧”、“姚蒲奴”、“李行”、“吴”、“葛”、“郑元”、“方者”等姓名文字,说明他们的制品曾在Y66和Y26号窑焙烧过。这反映了唐代晚期瓷业生产有明确的分工,有专门从事制作瓷坯的和烧窑的手工业者,我们分别称之谓“坯户”和“窑户”。坯户制作好瓷坯后,须到窑户那里焙烧。他们之间既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又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上述晚唐时期各窑址间所出铭文标本中,无一例相同姓名者。可见当时坯户与窑户之间有着相对稳定的组合关系,也就是若干个坯户和一个窑户组成一个大的生产单位。上述姓名者应是某个生产单位的业主,而不是雇请的工匠姓名。
唐代早期的14例铭文标本,均为间隔具,无一例匣钵者。其中姓氏9例,数字5例。唐代早期制品普遍采用明火叠烧,匣钵具很少出现,因此,在间隔具上刻姓氏,入窑装烧时,来区分某个窑位制品是某个业主的。这说明晚唐时期瓷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唐代早期已经形成。
据《余姚彭桥黄氏宗谱》卷首有记载:“江夏宗谱跋:黄氏以汉迁越来,宗法严定,荣族撅声越东,分布越州慈水、明州上林,创建事业,窑业流入东海,功名不忘先世,作为图谱,以贻后人,其贤可知。时天祐四年(907年)九月令吉。”可见黄氏祖先自江厦迁越后,在上林创建事业,到唐末窑业蓬勃发达,名声远扬。宗谱中的余姚彭桥,即现今的慈溪彭桥,在上林湖西约3公里,唐至宋时,属上林乡。在众多的姓氏、姓名中,仅见上Y53出土1例“黄”字款。这件刻划“黄”字的瓷质匣钵的年代与黄氏宗谱记载窑业的时代相当,这个黄姓业主很可能就是余姚彭桥黄氏族人。在上林湖出土的66例姓氏和姓名者,他们都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创造出灿烂的瓷业文化,为越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节 越窑青瓷生产发展诸阶段
唐代的陶瓷比起六朝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窑中心都有了窑名。总的说来,唐代瓷业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白瓷开始向青瓷的优势地位发起挑战,并占有了重要席位,但还不足以动摇青瓷的霸主地位,从唐墓尤其是南方唐墓各期出土瓷器考察,青瓷数量仍然多于白瓷就是明证。虽然唐代的青瓷生产遍布南方,并延伸至北方,但越窑青瓷的烧造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成就。唐代越窑青瓷的生产作坊仍集中在宁绍地区,但其重心明显移向上林湖,而且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社会需要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形成一个庞大的瓷业系统。繁盛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恢复期(初盛唐)。这一时期的越瓷产品种类较少,基本上保持着前代风格,胎质灰白而较粗,釉色青黄或淡黄,容易剥落,产品的造型和种类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时期上虞龙浦、慈溪等地虽均有新建瓷窑,但没有构成大规模的窑群。若从全局看,越窑的作坊分布正在悄悄地出现耐人寻味的变动,其重要标志是上林湖窑业开始走出低谷,春光乍露,活力初现。
上林湖库区现已发现隋唐早期窑址13处,主要分布在木勺湾、黄家庵、横塘山、施家K-1、沈家山、牛角山、黄婆山、狗胫山等地。从采集的大量标本分析,制造工艺沿袭南朝,比较落后。大多数器物为明火叠烧,少部分器物采用对口合烧,泥点间隔,有的还把小件器放置在大件器内进行套烧以增加装烧量。其主要产品,壶、钵等一仍旧制,碗、盘、盏的造型也与南朝大同小异,灯、砚的造型较为新型,但装饰极为单调。釉色普遍呈青黄和青灰色调,器足底多露胎,也有半釉器,釉层薄,大都无光泽感,与覆盖在其上的中唐产品的细腻润泽明显不在一个档次。(1)上林湖越窑复苏期间在烧制青瓷的同时,兼烧酱褐色釉产品。上林湖初唐越窑还发现了不少铭文,可以借此窥见有关生产的一些信息。如黄家庵Y5、木勺湾Y3等垫饼上就书有朱、太、金、孔、王、吴等姓氏,这应是参与制作窑具的家族,查考地方志及族谱资料,有不少姓氏自外地迁来,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参与了上林湖瓷业的振兴。此外,上林湖越瓷的器底还出现了“利记”、“泰作”之类的标记,应是作坊的名称。
初唐越窑在生产格局变动上值得一提的还有象山窑的兴起。1974年在象山港距出海口不远的黄避岙发现初唐龙窑2条。从遗址堆积物看,该窑场产品种类比较单纯,主要有碗、高足盘、钵、瓶、罐,造型古朴,稳重实用,装饰简单,常施以大片的酱色彩斑装饰。这虽然是象山窑最早的发现,但其工艺水平在初唐时实属翘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象山窑远离城镇,背面为延绵不断的大山环绕,面向大海,窑址选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陆上交通不便,而窑场的规模却很大,是完整的瓷窑作坊。这只能说明它主要不是一个就地销售的手工作坊,它的大部分产品就利用便利的海陆交通运往外地销售,既可船运至我国沿海城市,也可以输出海外。象山窑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即越窑青瓷开始通过海路开拓市场,而域外市场的产品认同与大规模需求更加形成了通畅的销售渠道,反过来刺激了近港越窑的生产,从而引起了生产格局的变化。在原料与燃料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窑场的分布会更加集中到港口附近来,便于产品的直接启运。
二、突破期(中唐)。这一时期的越窑正处于由早期向后期转轨的重要阶段,因而在各方面都酝酿着突破。首先,慈溪上林湖取代上虞成为越窑青瓷中心产地的地位已得到初步确立,从而宣告了“上林湖时代”这一新历史阶段的正式诞生。上虞龙浦等地在中唐时盛烧青瓷,产品以碗为主,兼有一些罐、瓯之类的日用品,但因工艺上缺乏改进,故其中心地位遂为工艺先进的上林湖窑所取代。上林湖窑以上林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在其周围的白洋湖、古银锭湖、里杜湖、上岙湖等地置窑烧制。里杜湖现已发现中唐窑址8处,分布在躲主庙、栗子山和大黄山上。杜湖窑区在中唐建窑12处,产品与古银锭湖、上林湖中唐晚期作坊产品完全一致,成为上林湖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在继续烧造初唐时的部分产品并使之更加流行的基础上,试制投产了不少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新创器形。如碗和盘是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餐具,撇口碗初唐虽已出现,但在中唐时更为流行,碗口腹向外斜出,璧形底,制作工整。它与敞口斜壁形底盘和撇口平底碟,器型风格相同,成为一套新型的饮食用具。注子是中唐时出现的一种酒器,它很可能由鸡壶演变而来。隋和初唐越窑仍生产鸡壶,到中唐时期则多生产执壶,而鸡壶少见。瓯是中唐开始流行的茶具,其优美的造型深受文人学士的称赞,顾况《茶赋》就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的句子。其次,匣钵创用是制瓷技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在慈溪里杜湖窑区、上林湖窑区、镇海县小洞岙等几十座中唐窑址中,都发现了匣钵这种新型窑具,其中小洞岙的器物属于中唐元和朝,由此可以判断匣钵的使用不迟于中唐元和朝(806~820年)。其时匣钵还处于初创时期,只有一种形式,仅限于烧造小型器物如碗、盘等,釉色偏于青绿,用以支垫的泥点较大,产品的个性和风格均不够鲜明突出,但其出现的意义不容低估。因为匣钵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窑炉的空间利用率,使产量大幅度增长,而且也大大提升了越窑青瓷的质量档次,避免了烟熏和落砂现象,从而为越窑青瓷走向辉煌奠定了技术基础。越窑在中唐时已经烧制出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瓷器,开始上贡朝廷,这批贡瓷,色泽如秋水般澄清,因而也被研究者目为秘色瓷的初烧产品。而其时上虞龙浦窑的生产虽然达到了一定规模,但装烧工艺仍旧采用传统的泥点间隔、明火叠烧,窑址中没有发现匣钵窑具,产品的质量和成品率都不很理想,已明显落后于宁波诸窑。(1)再次,陶瓷贸易日趋繁荣,明州港陶瓷外销获得突破性进展。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大量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如执壶、碗、盘等,而且质量较好,日本等国也出土了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进一步证实中唐晚期越窑青瓷已开始销往国外了,明州港作为东方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得以正式确立。
三、繁荣期(晚唐):这个时期上林湖的越窑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窑场林立,规模空前。代表性的窑址有马溪滩Y30、荷花芯Y37、黄鳝山Y26。从出土的大批精美标本看,造型趋向轻盈小巧,釉色青绿,釉层深厚如冰玉。产品质量高,品种多,主要有各式碗、壶、盘、盏、托具、杯、罐、灯盏、唾盂、盒、砚台以及瓷塑、墓志、买地券等。晚唐上林湖匠师开发的新产品不少,典型的有海棠式杯、碗,荷叶盘,方形委角盘,大喇叭口唾盂以及造型多姿的各式盒子等。越窑产品釉层匀净,釉面滋润,如冰如玉,在以釉取胜的同时,还采用了刻花、划花、贴花、堆塑和彩绘等装饰技法。大量的精品是由匣钵单件装烧或多件装烧组合生产出来的,确实富有“千峰翠色”的美感,其烧造水平又有所跃升,使越窑牢牢地位居唐代诸名窑之首。这一时期,上林湖窑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两点,一是由原来的上贡瓷器到设立贡窑。顾名思义,贡窑就是地方上烧造贡奉朝廷精美器物(秘色瓷)的窑场。贡窑不同于后来由宫廷直接垄断的官窑,它是主动或被动地由官府派员定额派烧兼监烧,属于民营的又具有官府定点的性质。贡窑接受烧造秘色瓷的重任,它兼烧的下等品可以作为民用瓷在市场上流通。当然,秘色瓷也不全是贡窑的专利,非“贡窑”中也会有部分精品产出,流入消费市场,两者在釉色、配方、工艺、款式、胎质等方面并无多大差异。诸多地点的精粗两类制品的同层混积现象,均表明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的。
由于朝廷日用的迫切需要和上林湖产品的优异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朝廷选择在上林湖设立贡窑是顺理成章的。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光启三年(887年)凌倜青瓷罐,志文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之语。从时间上看,其时越州虽处于武人董昌控制之下,但他对朝廷极尽邀宠之能事,有充分利用上林湖窑作文章的可能;从墓志罐的行文看,凌倜“终于..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则“当保贡窑”应指石贵保所属的贡窑,从窑址的地理位置、生产规模和采集标本判断,贡窑应设在今上林湖的后施岙、施家斗、黄鳝山窑场一带。这里还出土过“贡”、“方贡”等铭文器以及刻有“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场不得滥将恶用”等铭文窑具,进一步佐证贡窑的存在。从施家斗窑址出土大型器盖内书刻“咸通十三年..”的秘色瓷等实物,以及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秘色瓷产地的认定,证明上林湖至迟在晚唐咸通年间就已设立了贡窑。用作外销的瓷器由中唐时的起步发展到规模生产,上林湖成为浙东最大的贸易瓷生产基地和中心。上林湖窑与长沙窑产品联袂在明州港起运,出口势头方兴未艾,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这样,上林湖以宫廷用瓷和贸易瓷两大拳头产品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一时期,上虞窑主要分布在上浦乡徐湾村,联江乡凌湖村,龙浦乡前进村、湾头村等地,产品主要有蟠龙罂、执壶、碗、罐、粉盒、多角瓶、灯盏等。
四、鼎盛时期(吴越时期):乾宁三年(896年),唐帝敕封钱鑃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从此两浙一带进入了钱氏家族统治时期。吴越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国策,在取悦强国、和好邻邦中,“贡献相望于道”。钱氏掌管越窑窑务,为了适应内政外交的需要,必然要超常地发展这一特色产品。其时越窑生产的布局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即慈溪上林湖、上虞、鄞县东钱湖鼎足成为我国三大越窑生产基地,越瓷精品散布极广,上至达官贵族下至一般民众的墓葬中以及各类遗址中,都可见到越窑极盛期烧制的精品的绰约身影。上林湖窑场在晚唐的基础上规模又有大幅扩张,现已查明五代北宋的作坊多达100余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越瓷烧造中心区,这样规模密集的瓷窑体系,在其他地域是罕有其比的,无论质还是量都达到了顶峰。官方经常直接指定上林湖窑按样烧制青瓷器,上林湖窑址中出土过少数刻“官”字款的青瓷碗残片,审其器型、文饰特点,当属晚唐或北宋早期。在唐末五代钱氏墓也发现有这类刻“官”字款的青瓷器。上林湖烧制的秘色瓷,在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还有大量出土,如竹园山等窑址还散布着铭有“太平戊寅”的青瓷器,这些“文明的碎片”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一个侧翼为东钱湖窑场(包括同一类型的边缘窑区——白杜和宝幢窑区)。东钱湖窑场可划分为郭家峙、窑棚、上水、下水、东吴等几个窑区,绝大多数是在吴越晚期发展起来的,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共有35处,占了总数的75%以上,迅速崛起而成为宁波的第二大窑场,不但烧造的品种多,而且质地也很精美。产品以成套的各式碗为大宗,另有盅、盘、钵、洗、壶、罐、盏托、杯、水盂、盒、瓶、香熏等,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与上林湖相似。从成型、胎质、纹样以及烧造工艺看,各窑区基本上都是相当讲究的,坯泥淘洗十分精细,质地细腻坚密,釉层晶莹滋润,色泽分青翠、青黄或青泛黄数种,均有“玉感”,其产品的精美程度虽然稍逊于上林湖,却比同时代的上虞窑寺前窑高出一筹。东钱湖窑的产品,一部分用于上贡朝廷,如上林湖贡窑中发现的碗标本中的莲瓣纹样做法,在东钱湖窑中屡见不鲜,这种仿作应该出于上贡的需要。东钱湖由于靠近明州港,运输方便,故又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于外销,在非洲埃及古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器中,不少器物从造型到纹样都与东钱湖窑场中的产品毫无二致,无疑属于从明州港启运的东钱湖窑场的瓷器产品。
另一侧翼为上虞窑场。上虞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众多,分布于联江乡的帐子山、石井窑山、凌湖蛇头山,上浦乡的甲仗村(窑寺前)、清泽乡的魏家村,汤浦乡的蒋村等地,密集程度仅次于上林湖。据《嘉泰会稽志》卷8《寺院》“广教寺”条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在位时期,上虞设置有官窑36所(《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记载大同小异)
虽然这批窑是否真属于官窑并未得到确证,但吴越王为了政治需要在,上虞大量发展窑场,并派官员监理越州窑务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见广教寺(俗称“窑神庙”)一带应是五代上虞窑场的最重要分布区,其地即今位于百官镇南20公里窑寺前村,那里窑场林立,规模宏大,遗存极为丰富。主要产品有碗、碟、盒、盘、罐、壶、杯、茶盏、托具、灯盏、熏炉、瓷兽等,并多见精工之作,说明其烧造工艺比较先进和讲究。窑寺前窑址(场)的遗物釉色多作青绿,釉层青亮,胎质细腻,成型规整,不唯造型与上林湖窑场一致,而且其繁缛纤柔的纹样,从取材、构图到技法,都与上林湖如出一辙,因而被人目为“上林湖越窑的卫星窑”。以上三大窑群集中了最优秀的匠师,他们烧造的秘色瓷精美绝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流布各地的秘色瓷绝大部分是由这三大窑群生产的。二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县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7座,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这批瓷器,质地细腻,制作精巧,胎壁较薄,表面光滑,釉色滋润光泽,造型新颖优美,而且不少器物带有皇家气象,装饰华贵。如钱元罐墓出土的瓷罂,圆肩球腹,圈足外撇,肩颈两侧各安一对并列的耳形高鋬,腹部浮雕双龙,旁缀云纹,龙腾空飞舞,奋力抢珠,龙身涂金,璀璨辉煌,其造型之庄重,气魄之宏大,绝非唐代一般瓷罂可比。史书所记钱氏多用“金银扣瓷”、“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器”,由此得到证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缸、瓶等大件瓷器的烧成,足以代表五代越窑的工艺成就。如钱元玩墓出土的几件瓷缸,宽厚唇,口下安环耳四个,耳根饰柿蒂形,高37厘米,口径62.5厘米~64.7厘米,底径35厘米~38厘米。临安板桥吴氏墓所出褐彩云纹四系瓶,形似瓷罂,腹部呈椭圆形,高50.7厘米,腹径31.5厘米。这类大件瓷器,无论是成型还是烧成都是相当困难的。越窑工匠能烧造出这样形体高大的秘色瓷珍品,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应该指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只是对工艺超绝、规模庞大的窑群的概括,并非越窑的全部。其实在绍兴、余姚、宁波等地还分布着一些散窑,它们同样受到中心窑的影响,但其规模和产量均难望上述三大窑群之项背。如绍兴的窑址不多,有代表性的是城关上灶官山窑和东湖乡缸窑山窑,北宋时产品相近。绍兴上灶官山窑建在山麓平缓地带,有上灶江连接浙东运河,交通便利,官山南面又有丰富的瓷土矿藏,条件优越。官山窑生产的器物为碗、盘、壶,以及粉盒、砚台等,胎质灰白纯净,施釉均匀,色泽青绿,富有透明性,大多器物施有刻划纹样,其造型逼肖东钱湖窑场的产品,因而可视为受上林湖、东钱湖等窑场影响的作坊,时代自五代以迄北宋,代表了当时绍兴最高的越瓷烧造水平。
越窑的规模生产,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于是朝廷开始置官监窑,其主要任务是征收窑业税,当然也不排除对窑场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督管理。考古工作者在上林湖皮刀山发现一件北宋青瓷卧足残盘,盘外刻有“上林窑[自]..年之内一窑之民[值]于监..[交]代窑民..”等字样,说明该窑属于“置官监窑”的范围,与“民”相对的“监”自然代表了官方,而“监”又与“民[值]”相联系,正表明监窑的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北宋朝廷曾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窑务,差不多同时,陈尧咨为“漕案而行窑所”。置官监窑一方面为朝廷带来了不菲的税收,另一方面还可能以实物商税的形式获取官物瓷器,履行监督“官样”瓷器烧成质量的职责,从而加重了越窑的生产负担。上林湖后施岙发现的内外刻莲瓣纹、器底刻有“官样”二字的残青瓷小碗,“官样”应是官方指定监烧的一种碗的样品,即所谓“禁廷制样需索”的样品,即是明证。
吴越钱氏统治结束之后,越窑宫廷用瓷的数量锐减,政治特贡又一变而为土贡,京都建隆坊专设的瓷器库,掌受贡自明、越两州的青瓷和饶、定两州的青白瓷、白瓷。据《元丰九域志》卷5《两浙路》记载,越州土贡数额仅为“瓷器五十事”,估计明州也不会相差太悬殊,只是秘色瓷的质量每况愈下,己显示出明显的败象。不过,越窑民用商品瓷生产在大约半个世纪中,仍维持了一定的规模,产品从略失旧时风貌演变为粗放拙率。庆历七年(1047年),余姚知县谢景初(10201084年)深入考察了上林湖越窑现场,写下了珍贵的《观上林湖垍器》一诗,中云:“作灶长如丘,取土深如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价,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尤能,今予乃亲觇。”谢诗写到了长长的龙窑、取土留下的深沟,并且提到了用脚踏飞轮制模及采用施釉技术烧造精品。窑匠劳作极为辛苦,力疲身病仍不得休息,而最后烧成的高档瓷成品率仅为百分之一、二。然而物稀价昂,来里中收购的商贾络绎不绝,直到关门时分才渐渐散去。他们把收购来的秘色瓷器出售给北人,没有一个北人不为之爱惜而倾囊的。谢氏这首诗可能是唐宋时期文人惟一亲临上林湖窑场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作品,场面真实可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第四节 越窑青瓷生产繁荣的原因
唐五代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窑场竞起,遍及全国,几乎将后世产瓷中心和名窑均包括在内,而越窑又以其密布的窑群、可观的产量、雄厚的实力、精湛的技艺位居诸窑之首。自中唐以来,越窑青瓷生产越来越繁荣,新的器物被不断根据实际需要设计出来,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瓶、罐和各类陈设瓷,应有尽有,形式新颖多样,造型精美,风格鲜明,生产的规模、产品的质量均超越前代。至五代北宋前期,越窑更盛极一时。越窑青瓷繁荣原因决不是单一的,而是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环境资源的优越:宁绍地区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为窑业的发展提供自然条件方面的保障。烧窑的先决条件是该地是否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浙东瓷窑的聚集地区均具备这一要素,如上虞联江凌湖、龙浦、上浦这一带的山丘谷地瓷土富集,相传凌湖就是因挖取瓷土而成湖的。现场调查证实目前上虞县小仙坛等地与慈溪县上林湖西岸的瓷土资源还相当丰富。充足的燃料供应,也是发展瓷业的必备条件。越窑瓷业依托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自六朝至唐五代,那里树木参天,植被覆盖良好,还未受到严重破坏(浙东丘陵大强度大面积的毁林滥伐是在宋代开始的),所以燃料供给充足,无断薪之虞。便捷的运输条件,是保证瓷业发展的又一前提。瓷器陆运容易破碎损毁,增加运输成本,特别适宜于水运。早期越窑青瓷主要是北向输入太湖流域等地,尤其在江苏一带发现最多,很可能取道运河经破岗渎而达建康,这条河道运输十分繁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较取道长江更为安全而又便捷可靠。唐代以来,越瓷内销急增,外销扩大,既散播于内陆腹地,又散播于海外,因而船运格外繁忙。贯穿上虞的曹娥江,可直达联江窑山、黄蛇山和龙浦的风凰山、风吹山头及上浦的狸猫湖、窑寺前等各大窑场。产品烧成后可直接下船输出,既可以顺水而下,向北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也可向西经过曹娥堰进入萧绍古运河,运销到绍兴、杭州,从杭州进入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口、建业等各大城市;或向东过梁湖堰进入“四十里”古运河,再翻越通明坝进入余姚江,再顺江而下,直达明州港埠。特别是浙东的上林湖,紧靠海边,居高临下的沿山湖水,越过坝口,与浙东著名水道东横河相连,满载于板船、竹排上的瓷品,在这里被卸下转装。直接北上,经古窑、胜山、破山诸浦,可至杭州湾出海,宛转西向,可南上至余姚江;一路西行,沿浙东古运河,越曹娥、钱塘诸江,可抵达杭州,然后进入南北大运河水系而航向全国;一路东行,越河姆、城山诸渡,可抵达宁波,然后进入甬江,由甬江北行至镇海关出海。唐代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不断拓展,明州海商驾风帆,破恶浪,活跃于东海之上,明州港成了当时的四大名港之一,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近港越窑的生产,无疑进一步适应了外销的需要。
二、烧造技术的改进:生产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而科技的发展又进一步激活了生产。陶瓷作为古代物质文明的代表,必须通过原料、成型、高温烧成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才能最后确定其成品价值,因此越窑的兴盛离不开陶瓷科技发展成果的有力支撑。越窑在烧制技术上,中唐时已创造性地使用匣钵装烧,以后又不断地改进,终致于精致完美,为烧造秘色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了适应更高要求的烧造工艺,人们还制作了许多因物制宜的各类间隔窑具,上林湖窑场还更多地使用了瓷质窑具。越窑还成功地利用长石克服釉汁不匀的缺点,从而产生细润光洁的效果。越窑的炉窑结构也得到了很好改进,烧成温度已能有效地控制,很少见到胎质疏松的生烧现象,也很少见到变形流釉的过烧情况。所有这些技术上的改进,都保证了越窑出炉时具有极富美感的理想釉面。在造型装饰上,新颖轻巧,变化多端,端庄秀丽,别饶风韵,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越窑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赢得了各色消费人群的欢迎。
三、江南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经过安史之乱,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却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诚如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所云:“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吕和叔文集》卷6亦云:“天宝之后,中原释末,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在江南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大趋势下,浙东一带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手工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上林湖为代表的制瓷业异军突起。综观唐代明州手工业的分布格局,非常符合地域空间结构构成模式中的增长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唐代明州的其他手工业所占的分量不重,惟有制瓷业独领风骚,而制瓷技术的一系列突破和上贡瓷器等政治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极化效应。所以唐代明州经济的发展流向是以青瓷的极化效应为主,以港口的扩散效应为辅。
四、消费市场的饥渴:任何一类手工业制品的生产总是与消费市场发生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唐代国内外陶瓷市场总的说来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商机无限,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首先,唐代商贸发达,国内发生了“铜币不周于用”的现象。据《唐会要》卷86记载,开元十一年(721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另一方面唐人也发现了日用铜器不适合盛装食物的缺陷,促使消费者纷纷寻求实用而又廉价的耐用品,以取而代之,于是全国的瓷业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迅猛发展,造型优美、款式新颖的越瓷制品大量打入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使瓷器更加普及于民间。其次,生活习俗的改变也与越窑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唐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给瓷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越窑从业人员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紧跟消费心理的高新追求,着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如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精美茶具的需求。唐人饮茶已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的阶段,讲究技艺,意在情趣。饮茶作为日常生活方式而兴起,对茶具的需求大增,茶具不仅是品茶的重要器具,还有助于提高茶的色、香、味。唐代茶具门类齐全,南北方各窑均大量生产瓷碗、瓯、钵等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唐人讲究茶具质地,注意因茶择具。越茶的特点是青绿色,它能借青瓷之色,使茶汤色泽翠青,分外赏心悦目,故而陆羽在《茶经》中有邢瓷不如越瓷之说。唐代南北诸窑以越窑生产的茶具数量最多,最精美绝伦,博得了文人学士的一片赞美之声。可以说,茶艺的需求促进了越瓷的精益求精,而越瓷类玉似冰的极致之美,反过来也促进了茶艺的发展。自晚唐以来,妇女化妆用品使用瓷制香盒、油盒、脂粉盒,于是越窑投其所好,大量生产这类妇女用品。尽管如此,南青北白,诸窑并起,国内市场还是充满着竞争的。而国外市场在唐以前几乎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越窑青瓷在满足内销的同时,已经完全具备了外销的能力,于是借港口之便率先走向世界,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当然,唐代输出海外的还有长沙窑等,但越窑青瓷无疑在海外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瓷器外销畅通无阻,成为刺激越窑制瓷业高度发达的重要因素。吴越时代,越窑生产如火如荼,钱氏将上贡之外的大量青瓷用于海外贸易,成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在澎湖岛发现的大量这一时期的越瓷精品就是外销的有力佐证。
五、政治行为的拉动:唐代越窑的兴盛并非纯属自发的经济行为,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行为的深度介入是促发越窑兴盛的举足轻重的因素。越窑在中唐取得技术上重大突破之后,自然被地方官选为向朝廷进贡的土产,很快博得了统治者的青睐,越窑青瓷因此身价倍增,声誉日隆,这反过来促进了越窑生产的精益求精。晚唐时朝廷又在上林湖特设贡窑,这在当时的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土贡进而演变为特贡,更加刺激了越窑生产规模的大幅扩增。唐末五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所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应是实录。延至五代吴越时期,浙江境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产富庶。吴越钱氏为了巩固和维持他们统治的小天地,不断向中原地区的各王朝进贡。仅瓷器一项据《宋史》、《十国春秋》、《宋会要》、《吴越备史》等文献记载统计,从宝大元年(924年)钱镠向后唐进贡秘色瓷器,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钱惟濬贡宋金银陶器的60年中,吴越国进奉瓷器多达14万件以上,它们绝大多数属于越窑青瓷。尤其是北宋立国至吴越归宋的18年间,各割据政权相继灭亡,钱俶(948~978年在位)自知势单力薄,岌岌可危,为了保全一隅江山,“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定做了大批轻巧精细、装饰华贵的秘色瓷器,贡瓷数量动辄上万。如,此繁重的生产任务,光靠上林湖窑场烧造显然是远远不敷所需的,所以吴越小朝廷又让上虞窑场和鄞县东钱湖窑场在官方监督下承烧部分贡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虞县窑寺前窑场,其极盛期即在吴越后期。《宋会要辑稿》历代朝贡里明确记载了明州贡瓷。如开宝九年(976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濬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当然,秘色瓷在贡奉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产品被吴越国各级显贵留作自己享用,而且往往根据官方的审美情趣到窑场定烧。这种政治行为不仅使上林湖窑厂的烧造达于极限,而且也刺激了上虞窑的蓬勃兴起,东钱湖窑场也得到了迅速开辟,越窑生产因此而臻于极盛。但是政治行为的拉动对于越窑来说毕竟属于外部的强力注入,而非内力的驱动,一旦外力撤去,贡窑易位,那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成为引发越窑衰落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因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王被迫纳土归宋之后,越窑制瓷业便从巅峰一路下滑了。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时期,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业生产出现遍地开花、相互争艳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慈溪上林湖越窑是当时南方青瓷中的杰出代表。
考古调查表明,越窑遗址均分布在唐宋时期的越州和明州政区内(今宁绍地区),以慈溪的上林湖地区、上虞的曹娥江中游地区和鄞县东钱湖地区最为密集。根据浙江省文物地图集以及有关发表资料统计,唐宋越窑遗址有293处,现简述如下:
一、慈溪市 窑业主要由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4个窑区组成,共发现171处。
上林湖窑区:位于三北群山主峰栲栳山北麓,在库区内分布着104处唐宋窑址,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20公里的湖岸线上。大部分窑址在湖的南半部,尤以木勺湾、吴石岭、横塘山、黄鳝山、荷花芯、皮刀山、沈家山、狗颈山、后施岙、牛角山、吴家溪、黄婆岙等地最为密集。从各窑址器物特征来看,可认定唐代51处,唐至北宋4处,唐、北宋9处,五代6处,五代北宋14处,北宋20处。1964年被宣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洋湖窑区:在上林湖之东,相距2公里,窑址均分布在湖的南部和西南部,在石马弄、对面山、碗片山、小弄口等地发现窑址12处。根据各窑址器物特征,可确认唐代5处,五代至北宋2处,北宋5处。
里杜湖窑区:杜湖在鸣鹤镇境内,1963年在湖的中部建一堤坝,分为里杜湖和外杜湖,外杜湖与白洋湖相连。窑址分布在里杜湖西岸中部,主要集中在碗窑山、栗子山、大黄山等沿湖平缓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15处。其中唐中期8处,北宋晚期5处。每年丰水期大部分窑址被淹,枯水期时,窑址尽露水面,破坏严重。
古银锭湖窑区:位于上林湖西南,相距2.5公里。早年已废,现为良田。窑址主要分布在石塘山、牧羊山、瓦片滩、野猫洞、汪家坪、大坪里、雉鸡山、开刀山、小姑岭等地,共有窑址29处。从器物特征来看,唐代4处,唐至五代5处,五代北宋6处,北宋8处,北宋南宋6处。
除上述4个窑区之外,其周围的上岙湖、烛溪湖、梅湖等地有窑址11处,其中唐代8处,唐、五代、北宋1处,北宋2处。
二、上虞市 在曹娥江中游两岸发现唐宋时期的窑址34处,分布在上浦镇夏家埠村的帐子山,凌湖村的窑山、台山、甑底山、橡皮地、虎皮岗、蛇头山,石井村的窑山、黄蛇山,甲仗村的庄头山、窑寺前、前岙口、栗树山、道士山、傅家岭、马岙水库、盘家湾、象里山,徐家湾村的里庵基,上宅村的水管头山等;龙浦镇魏家庄村的逍遥岙、窑甏里,前进村的风吹山、窑山、风翼梢山、大鱼山,里氏村的仙人脚掌山,湾头村的叶家山;谢桥镇岙口村的义葬山;汤霸镇蒋村的霸山;梁湖镇倪刘村的牛山等地。从器物的特征来看,唐代11处,唐至五代2处,唐至北宋2处,五代、北宋5处,五代、宋8处,北宋2处,宋4处。
三、鄞县 在东钱湖四周发现窑址39处,其中唐代2处,五代北宋37处。主要分布在五乡镇横省村的屋后山、河头湾,沙堰村的小干岭,周岙村的张家庄,仁久村的双峰山;东钱湖镇上水村的窑岙山,郭家峙村的郭童岙、王家弄、郭家峙,西村的刀子山、蛇山,马山村的窑棚,前堰头村的三甲岙;东吴镇东村的窑头山,南村的古坟潭等地。
四、余姚市 窑址主要集中在姚江两岸的丘陵地区。目前已发现窑址19处,主要分布在马渚镇杨岐岙村的王家山、窑基山,张家山下村的张家山下,藏野湖村的藏野湖;牟山镇竺山村的大园地、料勺嘴、马步龙,湖西村的窑头山;三七市镇剡岙村的橡皮山,相岙村的大池头,石步村的石步;肖东镇郭相桥村的前溪湖,莫家湖村的蛇岗;余姚镇钟家门头村的胡口弄;陆埠镇十五岙村的鲁家坟等地。这些窑址的年代为五代北宋3处,北宋16处。
五、宁海县 现发现4处。分布在茶院乡平窑村的小山,梅林镇何家村和岔路镇虎头山等地。时代均为北宋。
六、奉化市 窑址主要分布于白杜、西坞和尚田三个乡镇,以白杜乡最集中。共发现窑址11处,其中晚唐至宋2处,五代北宋6处,北宋3处。
七、象山县 窑址有2处,其中初唐1处,宋1处。分布在黄避岙乡东塔村的陈岙和丹城镇东门外东塘山。
八、镇海区 窑址主要分布于骆驼镇汶溪小洞岙村的晨钟山、何家园、小洞岙和河头乡十字路水库。目前已发现窑址4处,其中中晚唐3处,北宋1处。
九、绍兴县 发现晚唐至北宋时期的窑址1处,位于平水镇上灶村官山。
十、绍兴市 五代、北宋时期窑址2处。分别位于禹陵乡禹陵村庙湾西水山南坡和东湖乡桐梧村缸窑山东坡。
十一、诸暨市 窑址主要分布于双桥镇、湄池镇、阮市镇、直埠镇、江藻镇、马剑镇、枫桥镇等。唐代窑址有排山坞窑、孤坟仓山窑、土箕山窑、下埠头窑4处;宋代窑址有青山弄窑、月垅湾窑、骆家桥窑、凉西窑、新蒋窑、伏虎山窑、瓶甏山窑、红坞口窑、作坊村窑、龟山窑、船山窑、缸窑山窑等12处。
十二、新昌县 窑址3处,分布在拔茅镇的碗窑山、鞍山和拔茅中学,时代为宋。
十三、嵊州市 主要分布在长乐镇马面村的缸窑背,石阳村的碗盏山头,五村的碗盏山、下阳山;绿溪乡上胡村的瓷窑山;三界镇八郑村的小洋山、下郑山,傅山村的独山等。北宋窑址5处,宋3处。
上述窑址均为龙窑,分布于山麓的缓坡上,那里山峦连绵,湖泊众多,河流纵横交错;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蕴藏着大量瓷石矿,树木茂盛,燃料充足,水运便捷,为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窑址的年代、分布区域、数量及产品质量来看,唐代早期,瓷业生产还未走出低谷,未见规模可观的窑址群落,仍处恢复阶段。进入中唐以后,制瓷技术进一步改进,大量使用匣钵装烧,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窑址数量剧增,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在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上岙湖、烛溪湖以及上虞、镇海、诸暨、鄞县等地相继设立窑场,规模宏大,窑场林立。晚唐时期,瓷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跨入了繁盛时期。这时期的杰出成就是,成功地烧制出优质瓷器——秘色瓷。五代北宋初期,瓷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器类繁多,富有变化,造型轻巧优美,制作十分精致。至北宋中期,瓷业生产已停滞不前,虽有精品,但不及北宋初期的精美。北宋晚期,窑址剧减,上林湖地区仅有10余处,制作工艺衰退,大量产品采用明火装烧,制品粗糙,品种单调,刻划花纹简单、草率,瓷业生产出现大衰败态势。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晚唐时,在上林湖设立贡窑,烧制秘色瓷,贡奉朝廷。五代北宋初,吴越钱氏为了“保境安民”,对中原君主称臣纳贡,秘色瓷成了当时纳贡的重要方物之一,数量极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越窑生产秘色瓷的盛况。随着进贡瓷器的剧增,上林湖及周围的白洋湖、古银锭湖诸窑群生产的秘色瓷不能满足其需要,在上虞的窑寺前、鄞县的东钱湖等地也开辟新窑场,扩大生产规模。由于贡瓷数量与日俱增这一政治因素,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对以上林湖瓷业为中心的越州窑系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窑具铭文的考古发现
1984年文物部门对上林湖地区的瓷窑址进行全面调查,1985年又进行复查,发现瓷窑址190余处,采集了大量的实物标本,在窑具上发现了许多刻划姓(名)氏的铭文。如姚蒲奴、王蒿、魏文、徐信记、马、何、朱、王等。由此引起了古陶瓷研究者的注意,并对之进行多次专题调查、研究,称这些留下姓氏的匠人为“上林窑工。”(1)这批铭文的出土,是研究唐宋时期制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也是探讨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的实物依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窑具铭文72例(表七)。
“窑具”一词,不是广义上的瓷业生产工具,而是专指直接服务于制品烧成的用具,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匣具、垫具、间隔具三类。(2)在72例窑具铭文中,匣具57例,间隔具15例。按窑具质地来分,瓷质窑具44例,夹砂耐火土窑具28例。在46例瓷质窑具中,除1件环形垫圈外,均为匣钵。瓷质匣钵在装烧时,叠接处涂釉密封,烧成后,须破匣钵,才能取出器物,为一次性匣钵。从铭文内容来看,可分为数字和姓名二大类。数字为5例,姓名67例。按采集地点排列,后施岙Y66,黄鳝山Y26出土的标本较多,分别为9例和11例,其他窑址较少。
匣钵是用来装烧瓷坯的。在匣钵外壁刻划姓名,是表示制品的所有者。入窑装烧,烧成后出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某个窑位的制品是谁的,不会与他人的制品混乱。晚唐时期的Y66和Y26窑址出土有“余”、“马”、“马公”、“马公受”、“马使”、“王嵩”、“罗业师记”、“徐庆记烧”、“姚蒲奴”、“李行”、“吴”、“葛”、“郑元”、“方者”等姓名文字,说明他们的制品曾在Y66和Y26号窑焙烧过。这反映了唐代晚期瓷业生产有明确的分工,有专门从事制作瓷坯的和烧窑的手工业者,我们分别称之谓“坯户”和“窑户”。坯户制作好瓷坯后,须到窑户那里焙烧。他们之间既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又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上述晚唐时期各窑址间所出铭文标本中,无一例相同姓名者。可见当时坯户与窑户之间有着相对稳定的组合关系,也就是若干个坯户和一个窑户组成一个大的生产单位。上述姓名者应是某个生产单位的业主,而不是雇请的工匠姓名。
唐代早期的14例铭文标本,均为间隔具,无一例匣钵者。其中姓氏9例,数字5例。唐代早期制品普遍采用明火叠烧,匣钵具很少出现,因此,在间隔具上刻姓氏,入窑装烧时,来区分某个窑位制品是某个业主的。这说明晚唐时期瓷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唐代早期已经形成。
据《余姚彭桥黄氏宗谱》卷首有记载:“江夏宗谱跋:黄氏以汉迁越来,宗法严定,荣族撅声越东,分布越州慈水、明州上林,创建事业,窑业流入东海,功名不忘先世,作为图谱,以贻后人,其贤可知。时天祐四年(907年)九月令吉。”可见黄氏祖先自江厦迁越后,在上林创建事业,到唐末窑业蓬勃发达,名声远扬。宗谱中的余姚彭桥,即现今的慈溪彭桥,在上林湖西约3公里,唐至宋时,属上林乡。在众多的姓氏、姓名中,仅见上Y53出土1例“黄”字款。这件刻划“黄”字的瓷质匣钵的年代与黄氏宗谱记载窑业的时代相当,这个黄姓业主很可能就是余姚彭桥黄氏族人。在上林湖出土的66例姓氏和姓名者,他们都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创造出灿烂的瓷业文化,为越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节 越窑青瓷生产发展诸阶段
唐代的陶瓷比起六朝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窑中心都有了窑名。总的说来,唐代瓷业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白瓷开始向青瓷的优势地位发起挑战,并占有了重要席位,但还不足以动摇青瓷的霸主地位,从唐墓尤其是南方唐墓各期出土瓷器考察,青瓷数量仍然多于白瓷就是明证。虽然唐代的青瓷生产遍布南方,并延伸至北方,但越窑青瓷的烧造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成就。唐代越窑青瓷的生产作坊仍集中在宁绍地区,但其重心明显移向上林湖,而且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社会需要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形成一个庞大的瓷业系统。繁盛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恢复期(初盛唐)。这一时期的越瓷产品种类较少,基本上保持着前代风格,胎质灰白而较粗,釉色青黄或淡黄,容易剥落,产品的造型和种类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时期上虞龙浦、慈溪等地虽均有新建瓷窑,但没有构成大规模的窑群。若从全局看,越窑的作坊分布正在悄悄地出现耐人寻味的变动,其重要标志是上林湖窑业开始走出低谷,春光乍露,活力初现。
上林湖库区现已发现隋唐早期窑址13处,主要分布在木勺湾、黄家庵、横塘山、施家K-1、沈家山、牛角山、黄婆山、狗胫山等地。从采集的大量标本分析,制造工艺沿袭南朝,比较落后。大多数器物为明火叠烧,少部分器物采用对口合烧,泥点间隔,有的还把小件器放置在大件器内进行套烧以增加装烧量。其主要产品,壶、钵等一仍旧制,碗、盘、盏的造型也与南朝大同小异,灯、砚的造型较为新型,但装饰极为单调。釉色普遍呈青黄和青灰色调,器足底多露胎,也有半釉器,釉层薄,大都无光泽感,与覆盖在其上的中唐产品的细腻润泽明显不在一个档次。(1)上林湖越窑复苏期间在烧制青瓷的同时,兼烧酱褐色釉产品。上林湖初唐越窑还发现了不少铭文,可以借此窥见有关生产的一些信息。如黄家庵Y5、木勺湾Y3等垫饼上就书有朱、太、金、孔、王、吴等姓氏,这应是参与制作窑具的家族,查考地方志及族谱资料,有不少姓氏自外地迁来,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参与了上林湖瓷业的振兴。此外,上林湖越瓷的器底还出现了“利记”、“泰作”之类的标记,应是作坊的名称。
初唐越窑在生产格局变动上值得一提的还有象山窑的兴起。1974年在象山港距出海口不远的黄避岙发现初唐龙窑2条。从遗址堆积物看,该窑场产品种类比较单纯,主要有碗、高足盘、钵、瓶、罐,造型古朴,稳重实用,装饰简单,常施以大片的酱色彩斑装饰。这虽然是象山窑最早的发现,但其工艺水平在初唐时实属翘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象山窑远离城镇,背面为延绵不断的大山环绕,面向大海,窑址选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陆上交通不便,而窑场的规模却很大,是完整的瓷窑作坊。这只能说明它主要不是一个就地销售的手工作坊,它的大部分产品就利用便利的海陆交通运往外地销售,既可船运至我国沿海城市,也可以输出海外。象山窑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即越窑青瓷开始通过海路开拓市场,而域外市场的产品认同与大规模需求更加形成了通畅的销售渠道,反过来刺激了近港越窑的生产,从而引起了生产格局的变化。在原料与燃料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窑场的分布会更加集中到港口附近来,便于产品的直接启运。
二、突破期(中唐)。这一时期的越窑正处于由早期向后期转轨的重要阶段,因而在各方面都酝酿着突破。首先,慈溪上林湖取代上虞成为越窑青瓷中心产地的地位已得到初步确立,从而宣告了“上林湖时代”这一新历史阶段的正式诞生。上虞龙浦等地在中唐时盛烧青瓷,产品以碗为主,兼有一些罐、瓯之类的日用品,但因工艺上缺乏改进,故其中心地位遂为工艺先进的上林湖窑所取代。上林湖窑以上林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在其周围的白洋湖、古银锭湖、里杜湖、上岙湖等地置窑烧制。里杜湖现已发现中唐窑址8处,分布在躲主庙、栗子山和大黄山上。杜湖窑区在中唐建窑12处,产品与古银锭湖、上林湖中唐晚期作坊产品完全一致,成为上林湖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在继续烧造初唐时的部分产品并使之更加流行的基础上,试制投产了不少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新创器形。如碗和盘是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餐具,撇口碗初唐虽已出现,但在中唐时更为流行,碗口腹向外斜出,璧形底,制作工整。它与敞口斜壁形底盘和撇口平底碟,器型风格相同,成为一套新型的饮食用具。注子是中唐时出现的一种酒器,它很可能由鸡壶演变而来。隋和初唐越窑仍生产鸡壶,到中唐时期则多生产执壶,而鸡壶少见。瓯是中唐开始流行的茶具,其优美的造型深受文人学士的称赞,顾况《茶赋》就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的句子。其次,匣钵创用是制瓷技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在慈溪里杜湖窑区、上林湖窑区、镇海县小洞岙等几十座中唐窑址中,都发现了匣钵这种新型窑具,其中小洞岙的器物属于中唐元和朝,由此可以判断匣钵的使用不迟于中唐元和朝(806~820年)。其时匣钵还处于初创时期,只有一种形式,仅限于烧造小型器物如碗、盘等,釉色偏于青绿,用以支垫的泥点较大,产品的个性和风格均不够鲜明突出,但其出现的意义不容低估。因为匣钵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窑炉的空间利用率,使产量大幅度增长,而且也大大提升了越窑青瓷的质量档次,避免了烟熏和落砂现象,从而为越窑青瓷走向辉煌奠定了技术基础。越窑在中唐时已经烧制出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瓷器,开始上贡朝廷,这批贡瓷,色泽如秋水般澄清,因而也被研究者目为秘色瓷的初烧产品。而其时上虞龙浦窑的生产虽然达到了一定规模,但装烧工艺仍旧采用传统的泥点间隔、明火叠烧,窑址中没有发现匣钵窑具,产品的质量和成品率都不很理想,已明显落后于宁波诸窑。(1)再次,陶瓷贸易日趋繁荣,明州港陶瓷外销获得突破性进展。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大量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如执壶、碗、盘等,而且质量较好,日本等国也出土了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进一步证实中唐晚期越窑青瓷已开始销往国外了,明州港作为东方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得以正式确立。
三、繁荣期(晚唐):这个时期上林湖的越窑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窑场林立,规模空前。代表性的窑址有马溪滩Y30、荷花芯Y37、黄鳝山Y26。从出土的大批精美标本看,造型趋向轻盈小巧,釉色青绿,釉层深厚如冰玉。产品质量高,品种多,主要有各式碗、壶、盘、盏、托具、杯、罐、灯盏、唾盂、盒、砚台以及瓷塑、墓志、买地券等。晚唐上林湖匠师开发的新产品不少,典型的有海棠式杯、碗,荷叶盘,方形委角盘,大喇叭口唾盂以及造型多姿的各式盒子等。越窑产品釉层匀净,釉面滋润,如冰如玉,在以釉取胜的同时,还采用了刻花、划花、贴花、堆塑和彩绘等装饰技法。大量的精品是由匣钵单件装烧或多件装烧组合生产出来的,确实富有“千峰翠色”的美感,其烧造水平又有所跃升,使越窑牢牢地位居唐代诸名窑之首。这一时期,上林湖窑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两点,一是由原来的上贡瓷器到设立贡窑。顾名思义,贡窑就是地方上烧造贡奉朝廷精美器物(秘色瓷)的窑场。贡窑不同于后来由宫廷直接垄断的官窑,它是主动或被动地由官府派员定额派烧兼监烧,属于民营的又具有官府定点的性质。贡窑接受烧造秘色瓷的重任,它兼烧的下等品可以作为民用瓷在市场上流通。当然,秘色瓷也不全是贡窑的专利,非“贡窑”中也会有部分精品产出,流入消费市场,两者在釉色、配方、工艺、款式、胎质等方面并无多大差异。诸多地点的精粗两类制品的同层混积现象,均表明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的。
由于朝廷日用的迫切需要和上林湖产品的优异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朝廷选择在上林湖设立贡窑是顺理成章的。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光启三年(887年)凌倜青瓷罐,志文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之语。从时间上看,其时越州虽处于武人董昌控制之下,但他对朝廷极尽邀宠之能事,有充分利用上林湖窑作文章的可能;从墓志罐的行文看,凌倜“终于..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则“当保贡窑”应指石贵保所属的贡窑,从窑址的地理位置、生产规模和采集标本判断,贡窑应设在今上林湖的后施岙、施家斗、黄鳝山窑场一带。这里还出土过“贡”、“方贡”等铭文器以及刻有“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场不得滥将恶用”等铭文窑具,进一步佐证贡窑的存在。从施家斗窑址出土大型器盖内书刻“咸通十三年..”的秘色瓷等实物,以及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秘色瓷产地的认定,证明上林湖至迟在晚唐咸通年间就已设立了贡窑。用作外销的瓷器由中唐时的起步发展到规模生产,上林湖成为浙东最大的贸易瓷生产基地和中心。上林湖窑与长沙窑产品联袂在明州港起运,出口势头方兴未艾,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这样,上林湖以宫廷用瓷和贸易瓷两大拳头产品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一时期,上虞窑主要分布在上浦乡徐湾村,联江乡凌湖村,龙浦乡前进村、湾头村等地,产品主要有蟠龙罂、执壶、碗、罐、粉盒、多角瓶、灯盏等。
四、鼎盛时期(吴越时期):乾宁三年(896年),唐帝敕封钱鑃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从此两浙一带进入了钱氏家族统治时期。吴越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国策,在取悦强国、和好邻邦中,“贡献相望于道”。钱氏掌管越窑窑务,为了适应内政外交的需要,必然要超常地发展这一特色产品。其时越窑生产的布局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即慈溪上林湖、上虞、鄞县东钱湖鼎足成为我国三大越窑生产基地,越瓷精品散布极广,上至达官贵族下至一般民众的墓葬中以及各类遗址中,都可见到越窑极盛期烧制的精品的绰约身影。上林湖窑场在晚唐的基础上规模又有大幅扩张,现已查明五代北宋的作坊多达100余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越瓷烧造中心区,这样规模密集的瓷窑体系,在其他地域是罕有其比的,无论质还是量都达到了顶峰。官方经常直接指定上林湖窑按样烧制青瓷器,上林湖窑址中出土过少数刻“官”字款的青瓷碗残片,审其器型、文饰特点,当属晚唐或北宋早期。在唐末五代钱氏墓也发现有这类刻“官”字款的青瓷器。上林湖烧制的秘色瓷,在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还有大量出土,如竹园山等窑址还散布着铭有“太平戊寅”的青瓷器,这些“文明的碎片”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一个侧翼为东钱湖窑场(包括同一类型的边缘窑区——白杜和宝幢窑区)。东钱湖窑场可划分为郭家峙、窑棚、上水、下水、东吴等几个窑区,绝大多数是在吴越晚期发展起来的,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共有35处,占了总数的75%以上,迅速崛起而成为宁波的第二大窑场,不但烧造的品种多,而且质地也很精美。产品以成套的各式碗为大宗,另有盅、盘、钵、洗、壶、罐、盏托、杯、水盂、盒、瓶、香熏等,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与上林湖相似。从成型、胎质、纹样以及烧造工艺看,各窑区基本上都是相当讲究的,坯泥淘洗十分精细,质地细腻坚密,釉层晶莹滋润,色泽分青翠、青黄或青泛黄数种,均有“玉感”,其产品的精美程度虽然稍逊于上林湖,却比同时代的上虞窑寺前窑高出一筹。东钱湖窑的产品,一部分用于上贡朝廷,如上林湖贡窑中发现的碗标本中的莲瓣纹样做法,在东钱湖窑中屡见不鲜,这种仿作应该出于上贡的需要。东钱湖由于靠近明州港,运输方便,故又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于外销,在非洲埃及古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器中,不少器物从造型到纹样都与东钱湖窑场中的产品毫无二致,无疑属于从明州港启运的东钱湖窑场的瓷器产品。
另一侧翼为上虞窑场。上虞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众多,分布于联江乡的帐子山、石井窑山、凌湖蛇头山,上浦乡的甲仗村(窑寺前)、清泽乡的魏家村,汤浦乡的蒋村等地,密集程度仅次于上林湖。据《嘉泰会稽志》卷8《寺院》“广教寺”条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在位时期,上虞设置有官窑36所(《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记载大同小异)
虽然这批窑是否真属于官窑并未得到确证,但吴越王为了政治需要在,上虞大量发展窑场,并派官员监理越州窑务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见广教寺(俗称“窑神庙”)一带应是五代上虞窑场的最重要分布区,其地即今位于百官镇南20公里窑寺前村,那里窑场林立,规模宏大,遗存极为丰富。主要产品有碗、碟、盒、盘、罐、壶、杯、茶盏、托具、灯盏、熏炉、瓷兽等,并多见精工之作,说明其烧造工艺比较先进和讲究。窑寺前窑址(场)的遗物釉色多作青绿,釉层青亮,胎质细腻,成型规整,不唯造型与上林湖窑场一致,而且其繁缛纤柔的纹样,从取材、构图到技法,都与上林湖如出一辙,因而被人目为“上林湖越窑的卫星窑”。以上三大窑群集中了最优秀的匠师,他们烧造的秘色瓷精美绝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流布各地的秘色瓷绝大部分是由这三大窑群生产的。二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县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7座,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这批瓷器,质地细腻,制作精巧,胎壁较薄,表面光滑,釉色滋润光泽,造型新颖优美,而且不少器物带有皇家气象,装饰华贵。如钱元罐墓出土的瓷罂,圆肩球腹,圈足外撇,肩颈两侧各安一对并列的耳形高鋬,腹部浮雕双龙,旁缀云纹,龙腾空飞舞,奋力抢珠,龙身涂金,璀璨辉煌,其造型之庄重,气魄之宏大,绝非唐代一般瓷罂可比。史书所记钱氏多用“金银扣瓷”、“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器”,由此得到证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缸、瓶等大件瓷器的烧成,足以代表五代越窑的工艺成就。如钱元玩墓出土的几件瓷缸,宽厚唇,口下安环耳四个,耳根饰柿蒂形,高37厘米,口径62.5厘米~64.7厘米,底径35厘米~38厘米。临安板桥吴氏墓所出褐彩云纹四系瓶,形似瓷罂,腹部呈椭圆形,高50.7厘米,腹径31.5厘米。这类大件瓷器,无论是成型还是烧成都是相当困难的。越窑工匠能烧造出这样形体高大的秘色瓷珍品,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应该指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只是对工艺超绝、规模庞大的窑群的概括,并非越窑的全部。其实在绍兴、余姚、宁波等地还分布着一些散窑,它们同样受到中心窑的影响,但其规模和产量均难望上述三大窑群之项背。如绍兴的窑址不多,有代表性的是城关上灶官山窑和东湖乡缸窑山窑,北宋时产品相近。绍兴上灶官山窑建在山麓平缓地带,有上灶江连接浙东运河,交通便利,官山南面又有丰富的瓷土矿藏,条件优越。官山窑生产的器物为碗、盘、壶,以及粉盒、砚台等,胎质灰白纯净,施釉均匀,色泽青绿,富有透明性,大多器物施有刻划纹样,其造型逼肖东钱湖窑场的产品,因而可视为受上林湖、东钱湖等窑场影响的作坊,时代自五代以迄北宋,代表了当时绍兴最高的越瓷烧造水平。
越窑的规模生产,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于是朝廷开始置官监窑,其主要任务是征收窑业税,当然也不排除对窑场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督管理。考古工作者在上林湖皮刀山发现一件北宋青瓷卧足残盘,盘外刻有“上林窑[自]..年之内一窑之民[值]于监..[交]代窑民..”等字样,说明该窑属于“置官监窑”的范围,与“民”相对的“监”自然代表了官方,而“监”又与“民[值]”相联系,正表明监窑的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北宋朝廷曾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窑务,差不多同时,陈尧咨为“漕案而行窑所”。置官监窑一方面为朝廷带来了不菲的税收,另一方面还可能以实物商税的形式获取官物瓷器,履行监督“官样”瓷器烧成质量的职责,从而加重了越窑的生产负担。上林湖后施岙发现的内外刻莲瓣纹、器底刻有“官样”二字的残青瓷小碗,“官样”应是官方指定监烧的一种碗的样品,即所谓“禁廷制样需索”的样品,即是明证。
吴越钱氏统治结束之后,越窑宫廷用瓷的数量锐减,政治特贡又一变而为土贡,京都建隆坊专设的瓷器库,掌受贡自明、越两州的青瓷和饶、定两州的青白瓷、白瓷。据《元丰九域志》卷5《两浙路》记载,越州土贡数额仅为“瓷器五十事”,估计明州也不会相差太悬殊,只是秘色瓷的质量每况愈下,己显示出明显的败象。不过,越窑民用商品瓷生产在大约半个世纪中,仍维持了一定的规模,产品从略失旧时风貌演变为粗放拙率。庆历七年(1047年),余姚知县谢景初(10201084年)深入考察了上林湖越窑现场,写下了珍贵的《观上林湖垍器》一诗,中云:“作灶长如丘,取土深如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价,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尤能,今予乃亲觇。”谢诗写到了长长的龙窑、取土留下的深沟,并且提到了用脚踏飞轮制模及采用施釉技术烧造精品。窑匠劳作极为辛苦,力疲身病仍不得休息,而最后烧成的高档瓷成品率仅为百分之一、二。然而物稀价昂,来里中收购的商贾络绎不绝,直到关门时分才渐渐散去。他们把收购来的秘色瓷器出售给北人,没有一个北人不为之爱惜而倾囊的。谢氏这首诗可能是唐宋时期文人惟一亲临上林湖窑场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作品,场面真实可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第四节 越窑青瓷生产繁荣的原因
唐五代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窑场竞起,遍及全国,几乎将后世产瓷中心和名窑均包括在内,而越窑又以其密布的窑群、可观的产量、雄厚的实力、精湛的技艺位居诸窑之首。自中唐以来,越窑青瓷生产越来越繁荣,新的器物被不断根据实际需要设计出来,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瓶、罐和各类陈设瓷,应有尽有,形式新颖多样,造型精美,风格鲜明,生产的规模、产品的质量均超越前代。至五代北宋前期,越窑更盛极一时。越窑青瓷繁荣原因决不是单一的,而是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环境资源的优越:宁绍地区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为窑业的发展提供自然条件方面的保障。烧窑的先决条件是该地是否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浙东瓷窑的聚集地区均具备这一要素,如上虞联江凌湖、龙浦、上浦这一带的山丘谷地瓷土富集,相传凌湖就是因挖取瓷土而成湖的。现场调查证实目前上虞县小仙坛等地与慈溪县上林湖西岸的瓷土资源还相当丰富。充足的燃料供应,也是发展瓷业的必备条件。越窑瓷业依托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自六朝至唐五代,那里树木参天,植被覆盖良好,还未受到严重破坏(浙东丘陵大强度大面积的毁林滥伐是在宋代开始的),所以燃料供给充足,无断薪之虞。便捷的运输条件,是保证瓷业发展的又一前提。瓷器陆运容易破碎损毁,增加运输成本,特别适宜于水运。早期越窑青瓷主要是北向输入太湖流域等地,尤其在江苏一带发现最多,很可能取道运河经破岗渎而达建康,这条河道运输十分繁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较取道长江更为安全而又便捷可靠。唐代以来,越瓷内销急增,外销扩大,既散播于内陆腹地,又散播于海外,因而船运格外繁忙。贯穿上虞的曹娥江,可直达联江窑山、黄蛇山和龙浦的风凰山、风吹山头及上浦的狸猫湖、窑寺前等各大窑场。产品烧成后可直接下船输出,既可以顺水而下,向北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也可向西经过曹娥堰进入萧绍古运河,运销到绍兴、杭州,从杭州进入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口、建业等各大城市;或向东过梁湖堰进入“四十里”古运河,再翻越通明坝进入余姚江,再顺江而下,直达明州港埠。特别是浙东的上林湖,紧靠海边,居高临下的沿山湖水,越过坝口,与浙东著名水道东横河相连,满载于板船、竹排上的瓷品,在这里被卸下转装。直接北上,经古窑、胜山、破山诸浦,可至杭州湾出海,宛转西向,可南上至余姚江;一路西行,沿浙东古运河,越曹娥、钱塘诸江,可抵达杭州,然后进入南北大运河水系而航向全国;一路东行,越河姆、城山诸渡,可抵达宁波,然后进入甬江,由甬江北行至镇海关出海。唐代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不断拓展,明州海商驾风帆,破恶浪,活跃于东海之上,明州港成了当时的四大名港之一,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近港越窑的生产,无疑进一步适应了外销的需要。
二、烧造技术的改进:生产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而科技的发展又进一步激活了生产。陶瓷作为古代物质文明的代表,必须通过原料、成型、高温烧成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才能最后确定其成品价值,因此越窑的兴盛离不开陶瓷科技发展成果的有力支撑。越窑在烧制技术上,中唐时已创造性地使用匣钵装烧,以后又不断地改进,终致于精致完美,为烧造秘色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了适应更高要求的烧造工艺,人们还制作了许多因物制宜的各类间隔窑具,上林湖窑场还更多地使用了瓷质窑具。越窑还成功地利用长石克服釉汁不匀的缺点,从而产生细润光洁的效果。越窑的炉窑结构也得到了很好改进,烧成温度已能有效地控制,很少见到胎质疏松的生烧现象,也很少见到变形流釉的过烧情况。所有这些技术上的改进,都保证了越窑出炉时具有极富美感的理想釉面。在造型装饰上,新颖轻巧,变化多端,端庄秀丽,别饶风韵,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越窑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赢得了各色消费人群的欢迎。
三、江南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经过安史之乱,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却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诚如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所云:“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吕和叔文集》卷6亦云:“天宝之后,中原释末,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在江南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大趋势下,浙东一带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手工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上林湖为代表的制瓷业异军突起。综观唐代明州手工业的分布格局,非常符合地域空间结构构成模式中的增长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唐代明州的其他手工业所占的分量不重,惟有制瓷业独领风骚,而制瓷技术的一系列突破和上贡瓷器等政治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极化效应。所以唐代明州经济的发展流向是以青瓷的极化效应为主,以港口的扩散效应为辅。
四、消费市场的饥渴:任何一类手工业制品的生产总是与消费市场发生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唐代国内外陶瓷市场总的说来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商机无限,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首先,唐代商贸发达,国内发生了“铜币不周于用”的现象。据《唐会要》卷86记载,开元十一年(721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另一方面唐人也发现了日用铜器不适合盛装食物的缺陷,促使消费者纷纷寻求实用而又廉价的耐用品,以取而代之,于是全国的瓷业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迅猛发展,造型优美、款式新颖的越瓷制品大量打入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使瓷器更加普及于民间。其次,生活习俗的改变也与越窑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唐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给瓷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越窑从业人员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紧跟消费心理的高新追求,着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如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精美茶具的需求。唐人饮茶已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的阶段,讲究技艺,意在情趣。饮茶作为日常生活方式而兴起,对茶具的需求大增,茶具不仅是品茶的重要器具,还有助于提高茶的色、香、味。唐代茶具门类齐全,南北方各窑均大量生产瓷碗、瓯、钵等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唐人讲究茶具质地,注意因茶择具。越茶的特点是青绿色,它能借青瓷之色,使茶汤色泽翠青,分外赏心悦目,故而陆羽在《茶经》中有邢瓷不如越瓷之说。唐代南北诸窑以越窑生产的茶具数量最多,最精美绝伦,博得了文人学士的一片赞美之声。可以说,茶艺的需求促进了越瓷的精益求精,而越瓷类玉似冰的极致之美,反过来也促进了茶艺的发展。自晚唐以来,妇女化妆用品使用瓷制香盒、油盒、脂粉盒,于是越窑投其所好,大量生产这类妇女用品。尽管如此,南青北白,诸窑并起,国内市场还是充满着竞争的。而国外市场在唐以前几乎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越窑青瓷在满足内销的同时,已经完全具备了外销的能力,于是借港口之便率先走向世界,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当然,唐代输出海外的还有长沙窑等,但越窑青瓷无疑在海外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瓷器外销畅通无阻,成为刺激越窑制瓷业高度发达的重要因素。吴越时代,越窑生产如火如荼,钱氏将上贡之外的大量青瓷用于海外贸易,成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在澎湖岛发现的大量这一时期的越瓷精品就是外销的有力佐证。
五、政治行为的拉动:唐代越窑的兴盛并非纯属自发的经济行为,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行为的深度介入是促发越窑兴盛的举足轻重的因素。越窑在中唐取得技术上重大突破之后,自然被地方官选为向朝廷进贡的土产,很快博得了统治者的青睐,越窑青瓷因此身价倍增,声誉日隆,这反过来促进了越窑生产的精益求精。晚唐时朝廷又在上林湖特设贡窑,这在当时的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土贡进而演变为特贡,更加刺激了越窑生产规模的大幅扩增。唐末五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所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应是实录。延至五代吴越时期,浙江境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产富庶。吴越钱氏为了巩固和维持他们统治的小天地,不断向中原地区的各王朝进贡。仅瓷器一项据《宋史》、《十国春秋》、《宋会要》、《吴越备史》等文献记载统计,从宝大元年(924年)钱镠向后唐进贡秘色瓷器,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钱惟濬贡宋金银陶器的60年中,吴越国进奉瓷器多达14万件以上,它们绝大多数属于越窑青瓷。尤其是北宋立国至吴越归宋的18年间,各割据政权相继灭亡,钱俶(948~978年在位)自知势单力薄,岌岌可危,为了保全一隅江山,“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定做了大批轻巧精细、装饰华贵的秘色瓷器,贡瓷数量动辄上万。如,此繁重的生产任务,光靠上林湖窑场烧造显然是远远不敷所需的,所以吴越小朝廷又让上虞窑场和鄞县东钱湖窑场在官方监督下承烧部分贡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虞县窑寺前窑场,其极盛期即在吴越后期。《宋会要辑稿》历代朝贡里明确记载了明州贡瓷。如开宝九年(976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濬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当然,秘色瓷在贡奉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产品被吴越国各级显贵留作自己享用,而且往往根据官方的审美情趣到窑场定烧。这种政治行为不仅使上林湖窑厂的烧造达于极限,而且也刺激了上虞窑的蓬勃兴起,东钱湖窑场也得到了迅速开辟,越窑生产因此而臻于极盛。但是政治行为的拉动对于越窑来说毕竟属于外部的强力注入,而非内力的驱动,一旦外力撤去,贡窑易位,那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成为引发越窑衰落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因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王被迫纳土归宋之后,越窑制瓷业便从巅峰一路下滑了。
附注
(1)童兆良:《上林窑工》,见《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任世龙:《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1)谢纯龙:《隋唐早期上林湖越窑》,《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1)章金焕:《上虞龙浦唐代窑址》,《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