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史伯璿文璣
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通謂朱子四書釋仁義禮智兼體用獨智未有明釋愚嘗欲竊
取朱子之義以補之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
者也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静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輯釋亦
引此説
通補智字之訓如此蓋本朱子大學或問論知字之義而言
也然智是體知是用智是知之理知是智之事知之扵智猶
愛之於仁也今以論知字之言為智字之訓則似乎詳於用
而略於體者恐有未安但以朱子釋仁義禮之義者較之可
見况其語句又非訓釋字義之體沈氏之説亦然若以為論智字之用則可若以為訓智字之義則似未當不識者以
為然否
人生八嵗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通引齊氏謂上三者言節下三者言文文者名物之
謂非其事也通自謂洒掃應對以節言者小學不惟當習其事
事之中有品節存焉是小學當行之事也禮樂射御書數以文
言者小學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而已是小學當知之事也
輯釋亦引齊氏説
以文為名物文義之文主知而言豈非以博文學文之文亦
皆主知而言耶竊恐未然蓋此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
文之節文亦對舉以互見耳非謂言節者不可言文言文者
不可言節也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
之所以又曰古文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
大來都不費力詳此則謂以文言者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
義是小學當知之事者未必然也饒氏亦曰内則十年學書
計即六書九數也成童學射御即五射五御也十年學㓜儀
禮之小者也十三以上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即六樂也詳此
則齊氏非其事也與通未能習其事之説其不然猶為易見
若更以數之一端明之則六年嘗教之數矣非使之習其名
物名義而何至十年又使之學計計非使之以數而計多少
乎此即習九數之事可知讀者其試思之
人君躬行心得通躬行是行心得是知
按陳氏發明云躬行卽行道心得卽有得於心通硬拍上知
行上去先行後知毋乃不可乎愚謂陳氏所以辨通者當矣但旣先行後知之不可而於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
二句何爲又以爲皆先行而後知邪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通謂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
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故曰高而無實輯釋亦引此說
高而無實以程張之言今朱子編入近思錄及小學書者參
之可見通不過牽合字面而巳初無發明無足尙也
饒氏其按其字疑衍輯講論大學綱領其不同於章句者有三今舉
而辯之如左
一謂至善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明徳新民造極之地而言也
按此與章句事理當然之極盡夫天理之極之説不同蓋饒
氏之意以為至善之至是無過不及之意若以為至極之義
則過乎中而不可以為訓矣故如此説殊不思章句曰當然
之極又曰天理之極當然對不當然而言天理對人欲而言
極則盡乎十分之謂當然便是恰好之意即中之所在即無
過不及之謂也天理豈外是哉當然而未至於極便是有不
當然者雜於其中天理而未盡其極便是有人欲雜於其中
當然善也九分當然一分不當然善未得為至也天理善也
九分天理有一分人欲亦善而未至也須是當然則十分當
然天理則純是天理方可為善之至至九分有一分未盡是
於天理當然處有所未至便是不及乎中直至十分全盡方
是恰好處方是無過不及之中以此推之則章句有何可疑
若如饒説則當然不必十分當然天理不必十分天理只五
六分當然天理便是至善所在如此則如堯之仁舜之孝孔
子之學皆不免有過於中反不得為至善耶讀者疑必有見於此
二謂格物只要窮究那日用事物當然之則以知吾所當止之地非
是欲人窮極事物之理以至於無所不知也
此説不為無理但自以為與章句不同則實無不同者此蓋
因誤看了第五章補傳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一句所致
當於彼章辯之
三謂誠意是正心修身之要不是正心脩身之外别有一件事
誠實也此當於第八章辯之
饒氏又謂魯自少讀朱子大學之書於前三者反之於身自覺
未有親切要約受用處近讀先生與勉齋書謂大學一書㸔者
多無入處似此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然後知先生晚
嵗亦不能不自有疑焉
大學一書學者所以學至於聖人之法程也自三代以前能
盡是道而造其域者可數也孔孟既沒因其書而得其傳者
惟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是知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氣
質不齊用力不易所以得造其域者亦鮮至於教人之法則
不容自貶以御學者之不能也蓋其法不如是則不可以
之以造於聖人之極至耳然則朱子與其徒之書非歟曰此
書固宜有之然其本意得非正以教人之法既不容自貶而
又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故𤼵此歎亦猶聖人衰世之意邪
况亦但謂大學一書規模太廣亦未嘗有自病章句之意則
其為無可奈何之辭明矣觀於孟子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
墨等言可見不然誠意一章朱子易簀之際猶不廢改豈有
果知章句有太廣之病乃徒形之嘅歎而不及之改邪且雙峰自謂反身未有親切受用處亦既一切變易章句之㫖而
自為之説固宜自得親切受用處矣愚不知其由此進徳到
得何等地位可以任道學之傳否其亦大言以欺世而已非
實然也
饒氏謂明明徳章句説是明之於既昏之後某亦以經傳文意
詳之似只説因其本明而明之
徳本自明故曰明徳若不因其既昏又何待明之之功而後
明哉雙峰以為只因其本明而明之則是未嘗有所昏也未
嘗有所昏則是生而知安而行唯堯舜性之之徳可以當之
此則不待明之而自無不明者也雖湯武反之之事亦是未
免先有所昏但湯武善反之以復其本然者爾若以本體之
明有未嘗息者為本明則未嘗息者與本自明者固自大有
間哉譬之於火不假吹噓之力自然光燄燭天煙不得鬱物
莫之蔽者本明者也撲滅之餘僅有一燼之微存於死灰之
中不可得而盡熄吹嘘之則仍復熾盛者未嘗息者也讀者
欲分章句饒氏之得失當以是推之
饒氏又曰章句以慎獨為慎之於念慮萌動之始某則謂念慮
自始至終皆在所謹
此當於中庸説慎獨處辯之此不暇及又按語錄有曰這獨
也不是恁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一念或正或不正此
亦是獨處推此可見章句本意非饒氏所識饒氏自謂已説
却不出章句之意此當在第六章饒氏自述其所見與章句
異處而先言之故實於此
經止至善章句止者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叢説至善只是義理極處所中必止於是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此亦祖述雙峰之意以為説者也但雙峰説至字之意明與
章句不同又何必强推章句之説以求合雙峰之意乎竊意
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似矣不遷是不可過則恐未然何則
至善是極好處至是無以復加之意患其不及不患其過如
山之絶頂一般未至絶頂固是不及至絶頂而遷從他處去
亦只是下山了但可言不及不可言過又如月之圎缺一般
唯望夕十分滿輪方是至善之意未望明未滿魄固是不及
之意過望而虧又豈可以言過乎若以至善言之則孝是善
孝如大舜方是至善若以刲股之類為孝此則大舜所必不
為者且不得為至善之至矣况可謂之過乎如此則遷只當
作移動之意説不遷如説不退轉相似語録有曰既至其地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又曰到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其意蓋
可見矣
通謂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之事不遷知終終之之事輯釋亦引
此説
按文言知至至之程傳以為致知也知終終之程傳以為力
行也或問於朱子曰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到
至處方有箇向空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
終之而不去詳此則章句必至於是之至是已至其處之謂
不但如知至至之之為向望要進之意也况必至於是之至
以知言之則智及之之謂以行言之則造其域之謂是固兼
知行而言不如知至至之專指知而言之比其曰不遷以知
言之則知之弗去是也以行言之則仁能守之之謂是亦兼
知行言亦非如知終終之專主行而言之比也今引文言為
證則似乎必至於是是知止於此不遷是行止於此恐於文
言大學之㫖兩不相當而皆失之讀者其參攷焉可也若以
必至於是為知至知終不遷為至之終之則庶乎可耳
饒氏謂至善只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而言也又曰
止者毋過毋不及之謂通謂章句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或問曰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
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然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事理當
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者盡夫天理之則也曷
嘗以造極之地為言哉
此已於前辨之矣又按語録有曰至善只是十分盡善處猶
今人言極好又曰善者固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
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以此觀之則至善之
至朱子何嘗以為不指造極之地而言哉造極之地方是天
理十分盡處天理盡處便是當然之則何過之有其曰本然
一定之則亦以理出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加損又十分盡頭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已若不出於天則非本然之謂若有
一毫未盡則非一定之謂矣然則造極之言正朱子之本意
通者何必為朱子諱哉若必以造極為諱則為善亦以十分
盡頭為諱耶或問章句之意似毋容以異觀雙峰不知己意
與章句之意只一般乃是已非而章句通者又不知或問之
意與章句只一般乃援或問之言以諱章句極字非造極之
謂讀者但以或問語錄玩之則章句之意自明本無可議亦
不必諱也經眀徳至善章句具衆理應萬事事理當然之極通異端言理
不言事大學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徳至善云然
異端以理為障又何嘗言理要之異端只認得箇虚靈不昧
的於具衆理應萬事者皆不知也固是無用體又不成體
定静安慮得饒氏謂定静在事未至之前安慮在事已至之後
此句恐未當竊意安與定静皆在未有事之前慮是處事謂
是事方未按未字似衍來之時可也後字雖亦可通似未甚切當
今輯釋引饒氏此説果云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
至之際與輯講不同想亦覺其未當而改之耳
知止静安慮通引方氏曰異端亦説得能定靜安了只是處置
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慮只是能處置事
大學定靜安是活厎定靜安根源從知止上来如孟子知言
然後自然不動心之意所以事至而能慮異端定靜安是死
厎定靜安但㝠然無覺而已如告子外義而亦能不動心之
意所以事至竟不能慮但猖狂妄行而已如此則異端非獨
不能慮雖硬把捉得定静安亦不可謂之能也疑似之間是
非之辯不可不察
通曰定而能靜則事未来而此心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
則事方来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輯釋亦引此説
易二語以一靜一動對言此是以知行之效騐對言能靜雖
亦是未應事之前然上承志有定向説下来則不可謂之寂
然不動矣若寂然不動又豈可以志言哉志則心有所之矣
謂之寂然不動可乎然則此定靜字只是理明之後外物私
意皆不足以摇奪之而心自不妄耳非對感通言之靜也叢説定靜安以知言慮得以行言
定靜安是未有事之前慮是方應事之時得是事既應之後
慮雖屬處事而未可便以慮為行力行正在慮得之間蓋此
五者是説功效次第則能慮不是行之功效分曉只當與定
靜安皆為知之功效方是
或問篇首之言明明徳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
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徳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
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
以其賔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徳者又三言綱領也至
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天下雖大而
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
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又立言之序
也饒氏輯講問此段最為可疑如言似新民之事在其中此是問
辭却言自明已徳於天下却不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徳也
又如言極其體用之全則似指明明徳為體新民為用此又似
有礙至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
用無不貫其言又似乎明已徳於天下與前章句或問意相反
不知何謂嘗看舊本文或問前段明明徳於天下處云自明其
明徳而推以及於天下今此段似與相著或恐是朱先生改正
之時偶遺忘及此亦未可知
或問之意是合在人在己之明徳以為一而言其體用耳蓋
明明徳於天下固是治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其明徳
然天下舉其全若國若家若身心以上皆已該於其中總言
明明徳於天下則自治國齊家以至於致知格物皆在其中
矣非只平天下於外而小之為國家内之為身心究其極之
為意為知為物皆不用其力也蓋舉大則小無不該然欲致
力於其大則當於其中先致力於其小以為之本耳故言明
明徳於天下則固為新民之極功然明明徳之事亦未嘗不
該於其中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徳四海九州之人固
天下之人一國一家之人與使者之自身亦莫非天下之人
也已欲明其明徳固當格物以致其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
欲使他人各自明其明徳亦不過使之皆如此而已曰極體
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者體即明在已之明徳用即使人各
明其明徳也一言而脩已治人之事無不在非極其體用之
全而何哉曰天下雖大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自有以明其明
徳而新民之體已立天下雖大體亦何所不該乎曰事物雖
多吾心之用無不貫者使人各明其明徳而吾明明徳之用
乃行事物雖多用亦何所不貫乎如此則以明明徳為體新
民為用豈不是經註或問本意而雙峰過疑之耶雙峰蓋以
經註所言專為平天下之事自治國以上皆未之及故如此
見可謂誤矣但以為明己之明徳於天下則本非朱子之意
乃雙峰因誤致誤耳餘見後段辨之
𤼵明輯釋引盧氏觧或問見前段之言曰言明明徳與新民對
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徳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
吾心之體即明徳之虚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徳之靈
而應萬事者也能折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
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祈而遽
欲合之則有虚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此二句其意無窮真西山嘗誦而繼之曰小徳川流大
徳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竊意體即明徳用即新民極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即明
明徳於天下一句而脩已治人之事無不該於其中也觀於
或問前段之言曰所謂明明徳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徳而推
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徳也之言可見天下雖
大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自明其明徳所以立新民之體體固
無不該也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者推以新民使人
各明其明徳所以達明明徳之用用固無不貫也析之極其
精而不亂者篇首明明徳以新民為對分體用而言則明明
徳固專以自明為言合體用而言該自新新民於一句之内
也此二句正是或者所問前後不同之意處熟讀可見或疑
如此説體用似於心之體心之用六字意有未瑩如何曰天
下事物未有不統攝於一心者是故以明明徳為體非心則
徳不能以自明體不能以自立心之體所以該天下之大者
蓋如此以新民為用非心則民不能以自新用不能以自行
心之用所以貫事物之多者蓋如此盧氏所觧則專以明明
徳為自明之事而分其體用故但知虚具衆理者之為體而
不知不明乎徳則無以全此體但知靈應萬事者之為用而
不知不新乎民則無所措其用蓋亦未達經注此句該盡人
已之意而但以明明徳於天下為明已之明徳於天下者不
足以别白此段問答之曲折又恐正墮前段雙峰似乎明已
徳於天下之疑讀者其試思之
𤼵明本當云古之欲平天下者今乃以明明徳於天下代之者以明徳人已所同得明明徳於吾身體也明明徳於天下者新
天下之民使皆明其明徳也用也一言而該大學之體用者如
此
𤼵明此説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徳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徳
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徳於吾身一句是觧篇首在明明徳之
義明明徳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觧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
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
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徳於天下者
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徳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徳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使人命皆該
在此句之中異乎𤼵明之意矣讀者其參考之可也
叢説明明徳於天下此徳字已含明字意在内明徳二字已該
明明徳三字義了上一明字是新民新字之意明明徳猶曰明
明明徳相似與在明明徳不同故章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明其明徳使字便是上明字意按此節所引叢說與原書全不同惟末句稍相似蓋先生所見
與今所傳
本有異
此亦不達或問之意而以明明徳於天下為專指新民而言
不知其該體用故耳其所謂猶曰明明徳相似與使字便是
上明字意之言皆不得經注之㫖而肆為臆説者也讀者知
或問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㫖則叢説之誤不待辨
而明矣已上四條饒氏則專以明明徳於天下為新民之事
而反非或問之可疑盧氏則專以為明己之明徳於天下而
失或問之旨矣𤼵明叢説則皆柤饒説指此句為新民之事
又為章句或問所礙而説得如比朦朧信乎説書之難也又未知愚意能合經註或問之㫖否也姑錄於此以俟明者為
著衷焉
致知在格物通曰章句釋明明徳兼事與理釋至善釋格物亦
曰窮致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徳第
一工夫也故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此一
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徳
而明明徳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潜先生云致知在格物何嘗是明明徳工夫所在後面
一在字與三綱領三个在字各有所指何嘗相應而通不顧
經文摘撮附㑹亂道殊可孝也愚謂經言大學之道在於三
綱領耳何嘗謂三者是綱領所在哉致知在格物亦曰推極
吾之知識在窮致事物之理耳所以不曰欲曰先者盖格物
之外别無致知工夫即在於物之内程子所謂物我一理
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者是已又何嘗謂明徳工夫莫
先於在格物哉
意誠而后心正章句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通意既實則
心之用可得而正
正心該體用動静觀於或問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
之言可見通乃於此添一用字其意蓋謂心之體無不正所
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其實非經㫖也當於第七章辯之
傳之首章饒氏謂此章姑以釋明明徳之義未有下工夫處
此蓋欲歸重於止善章而言也但明明徳工夫全在格物至
脩身五條目上明明徳是五條目之綱領五條目之外别無
明明徳工夫故此章但釋明明徳之義如此而下工夫處却
詳具於五條目之傳非有他也
傳之二章盤銘日新𤼵明愚案日新之藴自仲虺𤼵之湯采之
為此銘輯釋亦引此說
湯銘盤虺作誥其先後似難臆度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章句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饒
氏謂極與至善二義不同此極字是以窮盡無去處為極云云
若至善之至則是以無過不及為至非窮極之義也又謂止於
至善是逐事逐物各各要止於至善無所不用其極是無一事
一物不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是逐一事説是下手處無所不用
其極是該全體説是成就處
按經中章句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與此傳文用其極二
極字皆只是隨事指其十分盡善處為極皆非指衆事窮盡
處為極也自在止於至善處言之則凡事皆有善處善皆以
十分盡處為至十分盡處非極而何又自用其極觀之則此
極字之義亦不過如此而已初未見其指窮盡無去處而言
也必連上文無所不三字説下來方見得窮盡無去處之意
耳雙峰因誤看了此極字之義遂謂經中章句極字之義亦
如此也可謂因誤致誤朱子嘗曰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
之意真雙峰之謂矣
饒氏又曰此章姑以釋新民之義亦未有下工夫處
此與論首章之意同推彼可以明此矣
傳之三章穆穆文王云云饒氏謂但曰止於仁止於孝而不曰
止於至仁至孝以此見至善只是事物上一个無過不及厎道
理非窮髙極厚之謂仁敬孝慈信便是為君臣子父與人交者之至善若更曰至
仁至孝則又似乎言止於至善然者豈不重復矣乎若曰仁
非至仁孝非至孝則仁孝不必十分仁孝已是至善若十分
仁孝則又過於中而反不得為至善也邪如此則雙峰不唯
不識至字之義亦未識中字之義也蓋十分盡善方可謂至
方是無過不及所在若善未至於十分便是不及乎中又何
可以言至乎雙峰每慮其過則仁孝皆不敢做到十分盡處
便自以為至便自以為中天下還有此理否殊不思但言止
於仁孝何嘗不要人十分仁孝觀其引文王為法可見文王
仁孝豈有不十分全盡者耶只因雙峰平日以聖賢自居顧
經註之旨已皆有所未至慮世人以此覘其虛實故將經皆
説降一等求以自便故不得不誣朱子以欺世耳噫
瑟僩章句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𤼵明嚴密在心武毅見於
色
按傳釋瑟僩為恂慄章句又觧恂慄為戰懼下文又以恂慄
為徳為表裏則所謂武毅者似未可指為見於色也語錄云
僩武毅貌能剛强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詳此似亦當以在
心言者未知然否按篡疏引語錄作怠惰闒颯
親賢樂利饒氏謂親賢樂利於此見君子小人分量不同所得
各有淺深所謂新民之止於至善者非是要人人為聖為賢只
如農安畆工安肆商安塗賈安市亦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處
如此則比屋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皆無實之空
言後世如文景太宗之粗可以小康者皆足以為新民極功
而可與唐虞三代比隆矣識者豈宜無見於此饒氏謂明徳新民兩章釋得甚略又但言明新而不言明新之
方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
輯釋諸篇皆引之
篇首三向重在此一句上是固不為無理但言上二章工夫
皆在此一章則非也盖前兩章不言其所以明新之方者明
新之方自具於後六章釋條目工夫處非有他也若至善章
所以詳於前二章而必貫明徳新民二事言者蓋至善不是
懸空物事不過只是明明徳新民所當止之地耳故此章必
貫明明徳新明言之明徳新民工夫既具於後六章之傳則
前二章不容不簡至善雖便是明明徳新民之所當止然其
意則只寓於條目工夫中更無他處可以再詳其義故此章
自不容不詳言至善之義以示人初非以前二章未言明新
之方故如此詳言以補之也蓋綱領雖三事不過二非明徳
新民之外他有止善之事也故釋明徳新民則止至善之意
寓如曰無所不用其極是也釋止至善則明徳新民之義存
如引淇澳烈文之詩是也然亦不過皆言其概而已若謂新
民之方盡具於是則切磋琢磨猶可指為明之之工親賢樂
利何以見得新之之工夫耶
章内五節次序𤼵明輯釋引盧氏曰云云第三節言聖人之止
皆至善以得所止言云云
按此節章句其末曰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
矣則朱子正以此節為知所止之事蓋章句是就學者分上
言盧氏是就文王分上言所以不同要之文王之所已行正
是學者之所當知然則但當以章句為是
傳之四章釋本末或問然則其不論夫終始何也曰古人釋經
取其大畧未必如是之屑屑也目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
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耶
愚聞之章清所先生曰大學諸傳釋工夫而不釋效驗觀於
知止能得與物格至天下平無傳可見蓋效驗只在工夫之
中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終始正是以效驗言所以無傳固
非屑屑不及釋亦非本有而并失之
傳之五章饒氏謂朱子補傳似乎說得太汗漫學者未免望洋
而驚如既謂即凡天下之物則其為物不勝其多又謂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表裏精粗全體大用亦是自
立此八字經傳中元無此意
按即凡天下之物非謂把天下之物一齊格了亦曰就凡衆
物之中隨其所用而逐件格之耳求至乎極亦非謂求至乎
凡物衆多之極亦只是求至此一物義理之盡處耳直至下
文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方
是合衆物之全而言以文勢詳之可見雙峰不詳下文有衆
物二字遽以前節極字為事物當然之極真所謂理有未明
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此其說極字之誤正與前說至善處
極字之誤同知彼則知此矣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八字固是
朱子之所自立然豈不切於格物致知之義耶朱子本不效
傳體行文其所補之文便只如章句一般又何必以經傳所
無而疵之乎至於汗漫望洋之疑則大學之道是教人學至
乎聖人之方法格物致知一章正所謂始條理者之事始偏
則終亦偏始全則終亦全觀於孟子論始終條理處可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奈何患學者之不能
而欲自貶以狥之乎况望洋之疑只因雙峰誤看極字之所
致他人看得極字之義分曉又安有望洋之驚哉
語錄問先生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為之竟
不能成
竊意效傳體行文特文公餘事決無效不能成之理此特姑
為謙辭以答學者之問耳正意恐不止此也蓋若效其文體
則必援引經傳文意簡古學者未必自能通曉須又為之註
解以曉之如此則自為自註豈不為好事者之所譏誚故不
求其文之類但取其義之明所補便如章句一般庶乎人之
易曉耳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饒氏曰愚謂大學之要只在止於至善上格物是隨事隨物每
每要究到至善處致知是要推致其知識使之知此至善不必
必别為之說
朱子之意何嘗以格致不是要知此至善但理是事物之實
理至善又是狀此實理之體段說至善不如說理之實耳只
因饒氏看得至善之至字有礙又疑補傳之太汗漫故如此
見耳要之朱子以致知為知至善朱子與雙峰無異觀於章
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之言可見但雙峰以至善之至為
無過不及之意而非極至之義與朱子不同故於此亦不合
耳汗漫之疑殆亦起此讀者其試思之
饒氏謂或問云聖人說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
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謂聖人設教使之如此求之經傳卻
無證據看或問所引只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為證然德性是說心之理靈是說心之知覺有些不同况道問學是兼知行
言此却是專指致知而言似亦未甚親切
竊意古者八歲入小學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為大學
之基本此豈非聖人設教使之如此似不必他求經傳以為
證據也按語錄問格物問前段有曰聖人於其始教為之小
學處說了此說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裹壓重了不
潔浄詳此則朱子所據之意可見靈字只說知覺之處後第
七章心不在焉處與孟子告子上篇牛山之木章詳之道問
學兼知行之說當於中庸辯之此不贅及
補傳通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良知之知得於天性理有未明
知有未盡此致知之知得於學力
知只一般得於學力者即所以復其得於天性者耳分良知
與致知而言然則得於天性之外又他有得於學力知果由
外鑠我耶
或問取程子格物致知之說十二條朱子取其意以為補傳通
謂補傳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
第一條意程子曰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
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
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是
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又曰
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能有勉而行之
者也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
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
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
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逕皆
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
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第六程子
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則是巳然
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第七程子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
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温凊之節莫不窮究然
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第八條意程子曰物我
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
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之四
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終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
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是取程子第二程子曰
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爾
第三程子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脱然有
箇覺處第四條之意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
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然脱然有悟處自衆物
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
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
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遠而而
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
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
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第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
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六第七條意者皆是矣謂必使學
者至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條八條之意至於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是取程子第二第三第四條之意者皆
得之而未盡謂末節後四句是取程子第九第十之之意則
全失之何則補傳凡三節第一節自起首至窮其理也是說
致知在乎格物此正說以引起第二節說工夫之意下文至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說物未格則知不盡此反說以引起第
三節說效驗之意第二節自是以大學始教至求至乎其極
是就逐物上說格物致知工夫第三節是承上節就衆物上
說物格致知效驗程子十二條前二條與第一第六第七條
皆說工夫如通言可也第八條是說衆物上用工不可不周
通但以為全是補傳第二節所取則有所未盡第九第十條
是說衆物上用工又不可泛然無序正是說工夫處通乃以
為是補傳第三節後四句所取則此四句正是說效驗處以
為有取於彼是不察工夫效驗之有辯也愚則以為此三條
者補傳凡說工夫處如前二節與第三節用力之久一句皆
在所取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此四條是合工夫效驗言者
其實是補傳全章之所通取亦初不分節以配之也通以為
第五條是補傳第二節所取殊不思可推而無不通一句何
嘗不就衆物上說貫通之理耶通又以為第二第三第四條
是補傳第三節起頭二句所取殊不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
一物與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及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
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等語又何嘗不是說就一物上窮格
以至於積累之多正是通謂格致工夫之始終處而通皆指
為二句所取可乎况補傳第三節末後四句正是承豁然貫通之意而言格致之效驗處如此則第二至第五條所謂貫
通處覺處悟處與無不通之言是補傳第三節六句之所通
取通乃獨以起頭二句當前三條之意後四句既曰不取此
意則只得以第九第十條當之而不思二者有工夫效驗之
不同可謂誤矣或問取此十條自有次第第一條說格致用
功之法最為詳備是就逐一物上說故居首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條皆通說工夫效驗之始終是就逐物上說至衆物上
故次之第六第七條皆說就逐一物上當窮到極至處是申
第一條之意故又次之第八條說衆物格之不可不周第九
第十條皆說衆物之中格之又當有先後緩急之序三條皆
是申第二至五條之意故以是終焉大抵說工夫處多說效
驗處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效驗處無只說效驗而不說功
夫處通不察其次序之精密如此乃雜然取以配之於說功
夫處亦取五條意於說效驗處亦取五條意宜乎其致誤也
讀者詳之
矩堂董氏槐以經文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九句合傳
之四章及五章結句共為一章是說釋格物致知之傳朱子不
當更作補亡
按經文自明明德以下三句是一節說工夫自知止而后有
定以下五句是一節說效驗自物有本末以下四句是一節
總結前二節之意此皆是以大學綱領言之者自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一節是逆推工夫之所始自物
格至天下平一節是順序效驗之所極末後二節是結前兩
節之意前節正說結工夫後節反說結效驗此皆是以大學條目言之者其前後次序秩然不可紊亂如此今若掇此九
句以為格知之傳則綱領但說工夫不說效驗又無結意與
後段說條目處不同矣况諸傳之體說工夫處多說效驗處
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效驗者無只說效驗而不說工夫者
盖以無工夫則無效驗效驗不在工夫之外也况格物為大
學始教之事而不詳言其工夫可乎今以經文九句推之則
定静安慮得五字不可謂之工夫明矣知止之知亦已知所
止而非用工求知所止之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亦但言事
物大概如此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亦不過欲知本末終始所
當先後之序庶乎可至於道不遠而已亦不見格之致之所
用之工當何如也更以第四章傳文推之亦不過但言聽訟
之輕重欲人知明德之為本而已初未見欲知明明德新民
之理則當如何下工夫也遽以為物格遽以為知之至可乎
董氏但見經傳二處有此幾箇知字便欲牽合以為格物致
知之傳而不知致之格之之工夫不止如此也觀於中庸以
學問思辨為擇善之事而皆屬乎知說知如彼其詳則格致
之傳必如補亡之言而後盡董氏蓋不足以知此也
傳之六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章句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
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饒氏謂
謹獨只是審其善惡之幾而去取之如此則不自欺而自慊矣
章句謹獨是審其實與不實之幾
詳章句之意此是指獨字而言幾是指好善惡惡之意而言
審是審其幾之實與不實審其幾之實與不實即好善惡惡
之意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與否也雙峰為章句是審其實與不實之幾似未得章句之旨章句特欲審其幾之實與
不實爾至其自謂只是審其善惡之幾而不及好之惡之之
意又似與獨字之意無相關者不知如何
饒氏謂誠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且如顔子問仁而夫子告以
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只在四箇勿字上仁屬心視聽言動屬
身勿與不勿屬意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此心
之仁即存以此見三事只是一串
引四勿為證是矣但經言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雙
峰謂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此心之仁即存
則又似乎意誠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心正者恐不可得而強
合要之牽合附會之言自不能無罅隙亦不足深辯也
問傳之諸章釋八條目處每章皆連兩事言獨此章單舉誠其
意是如何饒氏曰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兩件事當
各用其力所以誠意不連致知說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
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局狹無以見
其功用之廣通引金氏曰大學諸章之傳首辭結語皆以序言
自正心以上獨不以序言蓋心身家國天下各是一節之事而
致知誠意二者同為心上之事心統知意者也若亦以序言則
是一心之中文自截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却自分成三次豈理
也耶然皆以序言於經經傳固互相也通曰大學條目有八
僅作六傳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
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章句謂
誠意者自修之首亦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
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亦可見輯釋亦引饒氏與通之說詳此三說皆不過因誠意自為一章與前後五章皆兼釋二
事者義例不同故此見耳饒氏知行當各用其力之言似矣
竊意知行當各用其力孰與脩已治人之當各用其力耶今
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且以脩己治人之事合而言之然則
以致知合誠意為一章又何為不可哉饒氏此言恐未必然
也若誠意不獨為正心之要者恐亦未必然當於後章辯之
金氏知意皆統於心心上工夫不可截作三次之言亦是自
立此說以經文論條目之工夫效驗處皆相因為序之意推
之何嘗無三節工夫耶且果如饒氏金氏之說則經文次第
皆不若傳文之當耶金氏亦既自知之矣通者援章句自脩
之首四字以合於饒氏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之說亦似矣
殊不思饒氏何嘗以朱子之說為是耶觀其謂首字不若要
字之言可見章末潤身心廣之證亦本饒氏皆未得為的論
也獨通者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之言近之
惜其不能推此以究其義也愚嘗以為傳自五章釋八條目
八條目之中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故經不曰欲致其知者先
格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便見此二者與正心修身修身齊家
齊家治國治國平天下二事相因者不同格物即所以致知
所謂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是已然則第五章釋格
物致知與第六章釋誠意皆是一章釋一事所以然者以二
事用功之不易也章句曰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詳此則此二章皆是一章釋一事之意可見語錄以
第五章為夢覺關第六章為人鬼關又為善惡關詳此則此
二事用功皆不易之意又可見矣自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皆一章兼二事釋者以物既格知既至意既誠之後循序漸進
用功為易耳語錄以為過此兩關夢覺人鬼上面工夫一節
易如一節了詳此則自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用功為易者信
矣然則六章之傳釋條目者前二章皆一章專釋一事以其
難也後四章皆一章兼釋二事以其易也下過如此而已不
知識者以為然否
章句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饒氏謂首字不若要字云云言修
身正心其要只在誠意意既誠則心自正身自修又謂誠意正
心脩身不是三事三事只是一串又謂誠意之外别無正心修
身工夫
首字不若要字之說正如中庸鬼神章包字不若貫字之說
要字貫字自是雙峰意如何亦欲朱子從之其意既誠則心
自正身自修與誠意正心不是三事三事只是一串及誠意
外别無正心脩身工夫之說辯則辯矣新則新矣其如經文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與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這數句何經文明有三節工夫而雙峰
強說誠意外别無正心脩身工夫經文明說而后心正而后
身脩雙峰強說意誠則心自正身自脩然則經何以不曰意
誠而后心正身脩欲脩身正心者先誠其意耶經文分明分
别作三事如此而雙峰強以為不是三事只是一串何耶朱
子嘗言序之不可亂功之不可闕如雙峰說則序皆可亂功
皆可闕矣雙峰勇於背朱子而不思經文之序本不可亂經
文之功本不可闕非朱子創為之說也以經證傳以傳釋經
則雙峰之謬誤不難見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通謂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
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輯釋亦引此說
小人固無二小人但此二章所言一為自脩者之戒一為用
人者之戒以為彼小人即此小人則非傳者之意也
傳之七章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章句蓋是
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
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饒氏謂忿者怒之暴
懥者怒之留恐懼好樂憂患與忿懥為類蓋亦指其情之偏重
者而言也問章句謂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如何饒
氏曰忿懥是不好底因此一件則知下面三件皆指不好底說
按章句云忿懥怒也夫怒所當怒亦未可便謂之不好唯雙
峰以怒之暴怒之留釋之然後二字之義乃不好耳愚嘗徧
考字書並無以暴留之意釋忿懥之義者然則雙峰暴字留
字之意得非本語錄忿又重於怒與忿懥是怒之甚者二句
而言乎然暴留二字與甚重二字之義不同重與甚是因事
有可怒之甚者怒之不得不重未害其為心之用也若暴則
至於虐物留則滯而不化皆過其則而不中其節非所宜有
也雙峰若别無所據但因語錄而推之如此則不若但依章
句平說為怒之得也蓋四者皆心之用今因說忿懥一事作
不好而并與恐懼好樂憂患三者皆以為不好厎而又不能
明言三者所以不好如忿懥二字之故則何以使讀者之無
疑哉豈若朱子只輕說忿懥則四者皆不能無但不可有之
於心之得乎况傳文不但曰有忿懥等而必曰有所以有所
二字觀之則章句之旨似無可疑又按金氏祖饒氏意併以恐懼好樂憂患三者皆連二字言之為不好之證通亦從而
和之然則中庸恐懼不聞孟子生於憂患亦連二字言之則
何以分别其好不好耶
語錄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
一事而在胷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罪而撻之纔撻了
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
按七章四言有所八章五言之其所所之一字皆是指物之
辭蓋人之一心未有事之前事已過之後皆當湛然虚明則
不滯於一隅不偏於一事所以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無有不
得其正者矣今乃於未有事之前或事既過之後其實未有
事之前又是前一件事既過之後非有二也而有所忿懥等
焉則是滯於一隅偏於一事當虚不虚當無而有而心之本
體自有所慮矣宜乎及有當應之事以此先有所主之心應
之鮮有不失其正者也故語錄云有所字正指所憂患之事
所忿懥之物而言以其滯而不化不當有而有故皆以有所
言之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章句心有不存
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
身無不脩也饒氏謂此以心不在明心不正之害心不在未便
是心不正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未便是身不修傳者欲借
粗以明精言心不在則無知覺以為一身之主宰而視不見聽
不聞食不知味矣况心不正則無義理以為一身之主宰亦何
以視所當視聽所當聽食所當食而無不脩乎輯釋諸編皆引
此說按語錄問心不在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纔
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此言可謂至矣讀者更以
孟子告子上篇牛山之木章語錄及中庸章句序之意參之
愚已於孟子備述之則朱子之意顯然可見矣况在之為正
訓雖殊而歸則一朱子於孟子求放心處以昏昩放逸為言
昏昩是就知覺上說放逸是就義理上說昏昩則失其知覺
而無以為燭理之本放逸則徇物於外而不能為應事之主
必兼此四字而後可以盡心不在之義而心不正者亦不外
是矣饒氏以釋氏常惺惺為心在而不正之證則是但以昏
昩為不在而不知放逸之乃所以為不在也泛而觀之昏昩
放逸雖若二事合而言之則未嘗不相關也何則知覺雖不
昏昩然苟為不在理義之中則一有可徇之欲必將徇之以
放逸於外而嚮所謂知覺之不昏昩者亦不過但能不昩於
所徇之欲而於其他當應之事反昏昩而不知矣謂之在可
乎蓋嘗合朱饒之說而觀之則知雙峰但以知覺不昩為在
却以義理無失為正如此則正與在為二而正又在乎在之
外雖不正亦可以為在矣殊不思義理有失便是徇物放逸
於外又可以為在乎朱子則以知覺既不昏昩又能居中役
物嘗在義理之中而不徇物放逸於外者為在如此則在外
無正不正不足以言在矣姑以世人之心言之彼其喻於利
者雖刀錐之末亦皆毫分縷析無有或遺如此者不可謂其
知覺之不在也然心不能以役物反為物所役不免逐物於
外謂之在可乎雙峰惑於知覺不昩之似乎在而許之乃不
察其不免逐物於外之實不可以言在也遂疑在與正之有二毋乃未得在字之意乎又自聖賢之心觀之聖賢之心湛
然虛明則其知覺之不昧可知然其所以爲知覺者則唯見
理而不見物也唯見理故常居中以役物不見物故不外馳
以徇物知覺不昧在也居中不外馳眞在也知覺常在義理
之中不與物欲俱往在外無正正不出於在也朱子不徒指
其知覺不昧者爲在尤必取其不外馳者爲在在又豈有不
正者哉況此章爲釋正心脩身而設章首一節但言心之不
得其正者耳至心不在焉以下方言心不正則身不脩之意
正當直指其義以示人若以爲借粗以明精而卒不明言其
本旨之爲借又遂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結之則人將認粗
以爲精認欲以爲理幾何其不與吿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
之言無以異乎更以前後章傳例攷之未有如此之隱晦者
可見饒氏辨此極詳又摭朱子或問之言節節破之故辨之
不得不詳然大意不過如此讀者攷焉可也
饒氏又以釋氏常惺惺爲心在而未可以爲心正以離婁爲視
見師曠爲聽聞易牙爲食知味而未可以爲身脩如此則心在
未是心正視見聽聞食知味未是身脩不過是借粗以明精了
傳本以心不在焉則一身無所主宰百體皆失其職而身以
不脩亦猶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之意視聽食姑舉其槩以見
例耳雙峯乃以釋氏離婁師曠易牙爲證殊不思傳文四句
只就一人身心上言之有人於此心不外馳而耳目口鼻四
體百骸皆稟命焉而不失其職可不謂之心正身脩乎雙峯
乃以四人之事證其不然宜乎其不合也且釋氏廢心用形
心雖惺惺而置之不用之地則其視聽食特猖狂妄行而巳
固未必見聞而知味也是固不可以證此章之旨矣離婁之
視見則心逐所視之物於外不可謂存與仰面貪看鳥囘頭
錯應人者相去無幾則其聽未必聞食未必知味又可知矣
師曠易牙亦然饒氏不知釋氏之心與離婁之目師曠之耳
易牙之口本不相關而強合之以證一人之身心是猶使甲
口食膾炙而責乙心不能知其味之美也不亦誣乎
在正其心不得其正通謂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
之用耳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直內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
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直內之本體
蓋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
用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潛先生云正心功夫是兼動靜體用觀或問鑑空衡平
之體用可見通謂心之體無不正正其心者正其用耳夫心
體無不正唯聖人爲然若衆人則或有偏倚矣正其心之用
若獨於此用功則未應事時皆無工夫矣又謂心之用或有
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此固未爲的當而謂不得其正此正
字是說本體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章句分明言
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而通謂本體之
失其正豈好奇求異於朱子邪抑未悟朱子之旨邪何先後
自相矛盾若此也愚按此辨當矣但傳謂在正其心此正字
乃是兼體用而通以爲正其心之用旣失之矣不得其正此
正字乃是專指用而通以爲體失其正尤爲失之也何則蓋
傳在正其心是總起下四句之意下四句每句皆兼體用而
言心之本體未應事之時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乃爲得其
正今乃無事而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焉則如鑑未照而
先已不空衡未稱而先已不平豈非體有所累而失其正乎
所以至有當應之事以此先有所主之心以應之或當怒者
倍怒當喜者不喜或當恐者倍恐當好者不好喜怒憂恐不
重卽輕如鑑先不空以照則妍醜不得而明衡先不平以稱
則輕重不得而定豈非用有所偏而失其正乎由此觀之則
有所忿懥四者是心之體失其正處四言則不得其正是心
之用失其正處通不如此看而交差互失惑人甚矣讀者詳
之
叢說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此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
怒而應當喜者或以樂而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
應事上謂身心全不相關通引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
此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主此一節說不
可以無所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存主也心在則羣妄
自然退聽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然則中虛而有所主宰
者正心之藥方也
按二說極當深可以破饒氏之謬故錄之以備參考
饒氏謂七章章下註文似可省
按饒氏自謂正心脩身二章工夫皆在誠意章故如此說然
經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固與章句之意
無異章句自援經文以貫傳義甚爲的當饒氏柰何教玉人
雕琢玉而省此不可省乎
傳之八章饒氏謂此說皆是尋常人有此病痛似不必將敖惰
做合當有底
因敖惰而廢親愛等四者與說忿懥不好之意同知彼則知
此矣但雙峰此段議論極詳大抵皆是諸子之所已破讀者
攷之或問語錄足矣正不在於後學之有辯也
章句之猶於也饒氏謂之者心之所之是向之意本不可訓於
但於於字相近故曰猶於也
雙峰惟如此說之字故以五者皆不可有竊意若改而辟焉
而為則乃可如此說耳
饒氏謂七章言心有所忿忦等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
之道八章言人之其所親愛等則流於辟而不言所以脩之之
方夫有是病必有是藥今詳此二章詳於論證而畧於處方蓋
心與身一物也而心為之主意與心一事也而意為之機故傳
釋誠意一章首之以毋自欺申之以謹獨以明用功之要莫切
於此故終之曰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以著意
誠則心正身脩之要也雖然不特正心脩身為然由是而齊家
治國平天下無往而不自慎獨出也故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
之平天下章曰必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意慎獨之
意也輯釋亦引此意
有心術之病有事為之失心術之病惡也先儒所謂縱有善
亦是黑地上一點白是也事為之失過也先儒所謂縱有未
善亦是白地上一點黑是也然則意不誠則好善不如好好
色惡惡不如惡惡臭甚則至如小人陰惡陽善者之所為此
蓋心術之病非過也惡也惡則治之也難故必毋自欺必谨
其獨而後意可得而誠不然則陷於小人之域矣然意既誠
矣固無為惡之事然於善之中未可保其無所偏無所辟也
此所以雖曰實好善實惡惡至於心之應事猶或至於有所
忿懥等而不得其正者亦有心雖已正至於身之接物猶或
至於之其所親愛等而辟焉者然雖未免有所偏辟亦不過
於善之中有偏辟耳無所謂惡也然不謂之過則不可過則
改之而已所以知其偏則使不至於偏知其辟則不可使之
辟足矣無所偏辟則善之至矣又何方之可處哉蓋大學之
教必須逐節用工隨地致力不可謂意既誠則心自正身自
脩誠意之外他無正心脩身工夫而混然不為之界限也若
果如所說則大學只列六條目足矣又何必虚設正心脩身
二條目於其間而實無所用之功哉心廣體胖之云亦所谓
以明誠意為自修之首之意非謂工夫止於如此也但誠意
正心脩身三者折而言之則自當有序合而驗之却不可以
為截然不相入故日用之間念慮之萌動處便須審其實與
不實此便屬之誠意心之與事應處便須審其正與不正此
便屬之正心身之與物接處便須審其辟與不辟此便屬之
脩身其工夫並行而不可偏廢有似於無二致耳實則界限
不相侵越而不可亂也何可因其似於無二致者遂謂慎獨
一言足以盡三者之工夫而紊其不相侵越之界限哉况如
其言以為自正心至平天下皆無往不出於慎獨則謂正心
以下論證而不處方可也自齊家以下諸傳又何為既論證
而兼處方也哉借曰誠求忠信即慎獨之意則正心脩身兩
章獨不可一言及之如此乎此愚所以不能無疑於雙峰之
說也雙峰之說近代四書通及陳氏發明皆引援而祖述之
故辯之不得不致其詳云傳之九章如保赤子語錄孝弟鮮能守而不失惟保赤子無有
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與孟子孺子入井之意同叢
說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
就愛民處言
案叢說雖於章句之旨有所未盡於語録之論微有不合然
亦似乎有理姑備一說竊意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為君
者則誰為忠乎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若為長者則誰為順
乎故孝弟專為臣與在下位者言之唯慈使衆可以通為君
臣言之故專以此示訓耳未知然否
一家仁讓一人貪戾饒氏謂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
讓屬弟貪戾是本上文慈字而言貪戾者慈之反也
孝弟是專主事親事長而言仁讓則通主待人接物而言若
以為仁屬孝讓屬弟則一家之人父兄亦自在其中為父者
誰為孝為兄者誰為弟乎貪戾二字恐便是仁讓之反貪則
不讓戾則不仁貪戻亦通主待人接物而言非如慈之專主
慈幼言也以為慈之反恐亦未必然近見盧氏亦有貪則不
讓戾則不仁之說乃知固有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非私言
也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通引王氏曰張子所
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此意雖相似而所主則不同大學主治人者言張子主自治
者言不可不辯也
傳之十章上恤孤而民不倍章句倍與背同
案章句不釋不倍之義說者皆以為下民不倍在上者慈幼之心而已雖亦可通竊疑孝便是老老意弟便是長長意不
倍却與恤孤之意不類文須轉摺方通先師冰壺鄭先生嘗
曰坊記有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與以此坊民民
猶偕死而號無告之言鄭氏注云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
呼稱寃無所告而韻書背偝倍皆同音義則不倍正是恤孤
之意豈章句以其易曉故不釋之耶抑但如說者所云也邪
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絜矩通謂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之道志學以下分知
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格物以下亦分知
行到末章方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乍看論語矩字似說
得精絜矩矩字似說得粗要之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矩字
是體絜矩之矩是用輯釋亦引此說
竊意論語矩字是就德上言是義此矩字是就政上言是怒
義與恕要之皆是用恕乃所以為義也今以彼為體此為用
似有可疑况彼章知行之分與此處分知行者不同彼處知
行當於此知行上横貫過夫子十五志學是知之始此便是
於八條目一一攻究了不是只從事於格物致知二者而已
立與不惑以下皆然若以為只是一箇矩則夫子未七十時
若為政於天下猶未有絜矩之體耶觀二矩字一言不踰一
言絜便見聖人學者之分若以彼為此體此為彼用恐皆鬭
凑不著又以不踰矩為生知安行之極致既曰志學則下生
知字不得觀集注於耳順處只說知之之至而不說生而知
之可見
絜矩通䂓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
者止不踰矩即是明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潜先生謂通謂矩方而止以強附於止至善之止尤為無
理矩取方義不取止義也
所惡於下云云章句則身之所處云云而無不方矣饒氏謂方
字恐未安絜矩之喻取其平非取其方也
方字於矩字之義為切方則天下自平恐亦無所謂不安也
好惡通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己
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
人者也云云輯釋亦引之
好惡雖只一般然三章所言各有所指傳者初無相承之意
通者強合以為說不過只是蹈襲雙峰誠意為下五者之要
之言爾此皆所謂詖辭也自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己者以下
皆所謂遁辭也雖若可通實非傳意亦不足深辯也
見賢不能舉云云饒氏謂過之罪小命之罪大如漢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
舉賢退不善二事常相因能用賢必能去不善不能去不善
必不能用賢書曰用賢勿貳去邪勿疑可見二事不可分輕
重若以元帝事證則其不能用望之却由其不能去恭顯况
望之之死又出於恭顯之讒豈可以過之罪為小於命哉
忠信以得之饒氏謂忠信即是慎獨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
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輯釋亦引此
謂意既誠後下五者工夫自然易則可謂五者工夫皆不出
於誠則不可且如忠信固不可不慎獨能慎獨固能忠信但遂以忠信為慎獨則慎獨恐該忠信不盡
君子有大道章句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也饒氏謂大
道乃絜矩之道
章句兼體用說饒氏只就用上言
孟獻子發明輯釋引盧氏曰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
能知絜矩之道
獻子在前子思在後以為獻子嘗師子思不知何據豈傳寫
之誤耶
必自小人矣金氏曰彼為善之上下必有缺文當作彼為不善
之小人與下文雖有善者亦相對通曰誠意章曰小人閒居為
不善故此章曰彼為不善之小人前後正相對
陳公潜先生曰小人雖一般但誠意章為不能慎獨言之以
為學者之戒此章為理財言之以為用人之戒初未嘗有意
於相應且朱子謂疑有缺文誤字正不必添一不字以強合
於為不善之語也愚謂如金氏之言始備一說猶未甚害通
但不當蹈襲而質言之以牽合乎誠意章小人閒居為不善
之意爾此亦本雙峰誠意為下五章之要之說而言也
全章之旨發明南山有臺詩好惡此言絜矩以用人之事節南
山詩言不絜矩而所用非人又於或問申其說曰好惡宜專就
用人說
按好惡所該甚廣用人亦其一事耳章句但言以民心為己
心固不直指所好惡者為何事或問則以好其所好而與之
聚惡其所惡而不以之施而究其義蓋本孟子所欲與聚所
惡勿施之意為說可謂至明白矣發明必以用人實之疑非傳文本意竊詳此章除首二節發出絜矩之名義外其下三
引詩姑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起下文財用用人
二者能絜矩與不能者之意末又以理財不當用小人而總
結之下文既皆以二事分合言之不應南山有臺等三詩獨
偏舉用人一事以發之也蓋用賢固是民之所好上不外本
内末使民皆有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亦豈不是民之所好用
小人固是民之所惡苛征重斂使民無以為仰事俯育之資
亦豈不是民之所惡然則正不當專指南山有臺節南山之
好惡為用人而言也讀者但當熟玩章句或問語錄之意則
發明之說未易以當可知矣
章末
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欲學大學者可須臾毫釐
之不敬哉
陳公潜先生曰按所謂忽恐學者以其書為淺近而忽易讀
過不加深體力行之功耳而通釋為敬引聖學成始成終之
語聖學之敬不但主於讀大學一書而已也
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通謂朱子四書釋仁義禮智兼體用獨智未有明釋愚嘗欲竊
取朱子之義以補之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
者也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静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輯釋亦
引此説
通補智字之訓如此蓋本朱子大學或問論知字之義而言
也然智是體知是用智是知之理知是智之事知之扵智猶
愛之於仁也今以論知字之言為智字之訓則似乎詳於用
而略於體者恐有未安但以朱子釋仁義禮之義者較之可
見况其語句又非訓釋字義之體沈氏之説亦然若以為論智字之用則可若以為訓智字之義則似未當不識者以
為然否
人生八嵗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通引齊氏謂上三者言節下三者言文文者名物之
謂非其事也通自謂洒掃應對以節言者小學不惟當習其事
事之中有品節存焉是小學當行之事也禮樂射御書數以文
言者小學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而已是小學當知之事也
輯釋亦引齊氏説
以文為名物文義之文主知而言豈非以博文學文之文亦
皆主知而言耶竊恐未然蓋此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
文之節文亦對舉以互見耳非謂言節者不可言文言文者
不可言節也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
之所以又曰古文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
大來都不費力詳此則謂以文言者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
義是小學當知之事者未必然也饒氏亦曰内則十年學書
計即六書九數也成童學射御即五射五御也十年學㓜儀
禮之小者也十三以上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即六樂也詳此
則齊氏非其事也與通未能習其事之説其不然猶為易見
若更以數之一端明之則六年嘗教之數矣非使之習其名
物名義而何至十年又使之學計計非使之以數而計多少
乎此即習九數之事可知讀者其試思之
人君躬行心得通躬行是行心得是知
按陳氏發明云躬行卽行道心得卽有得於心通硬拍上知
行上去先行後知毋乃不可乎愚謂陳氏所以辨通者當矣但旣先行後知之不可而於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
二句何爲又以爲皆先行而後知邪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通謂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
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故曰高而無實輯釋亦引此說
高而無實以程張之言今朱子編入近思錄及小學書者參
之可見通不過牽合字面而巳初無發明無足尙也
饒氏其按其字疑衍輯講論大學綱領其不同於章句者有三今舉
而辯之如左
一謂至善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明徳新民造極之地而言也
按此與章句事理當然之極盡夫天理之極之説不同蓋饒
氏之意以為至善之至是無過不及之意若以為至極之義
則過乎中而不可以為訓矣故如此説殊不思章句曰當然
之極又曰天理之極當然對不當然而言天理對人欲而言
極則盡乎十分之謂當然便是恰好之意即中之所在即無
過不及之謂也天理豈外是哉當然而未至於極便是有不
當然者雜於其中天理而未盡其極便是有人欲雜於其中
當然善也九分當然一分不當然善未得為至也天理善也
九分天理有一分人欲亦善而未至也須是當然則十分當
然天理則純是天理方可為善之至至九分有一分未盡是
於天理當然處有所未至便是不及乎中直至十分全盡方
是恰好處方是無過不及之中以此推之則章句有何可疑
若如饒説則當然不必十分當然天理不必十分天理只五
六分當然天理便是至善所在如此則如堯之仁舜之孝孔
子之學皆不免有過於中反不得為至善耶讀者疑必有見於此
二謂格物只要窮究那日用事物當然之則以知吾所當止之地非
是欲人窮極事物之理以至於無所不知也
此説不為無理但自以為與章句不同則實無不同者此蓋
因誤看了第五章補傳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一句所致
當於彼章辯之
三謂誠意是正心修身之要不是正心脩身之外别有一件事
誠實也此當於第八章辯之
饒氏又謂魯自少讀朱子大學之書於前三者反之於身自覺
未有親切要約受用處近讀先生與勉齋書謂大學一書㸔者
多無入處似此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然後知先生晚
嵗亦不能不自有疑焉
大學一書學者所以學至於聖人之法程也自三代以前能
盡是道而造其域者可數也孔孟既沒因其書而得其傳者
惟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是知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氣
質不齊用力不易所以得造其域者亦鮮至於教人之法則
不容自貶以御學者之不能也蓋其法不如是則不可以
之以造於聖人之極至耳然則朱子與其徒之書非歟曰此
書固宜有之然其本意得非正以教人之法既不容自貶而
又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故𤼵此歎亦猶聖人衰世之意邪
况亦但謂大學一書規模太廣亦未嘗有自病章句之意則
其為無可奈何之辭明矣觀於孟子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
墨等言可見不然誠意一章朱子易簀之際猶不廢改豈有
果知章句有太廣之病乃徒形之嘅歎而不及之改邪且雙峰自謂反身未有親切受用處亦既一切變易章句之㫖而
自為之説固宜自得親切受用處矣愚不知其由此進徳到
得何等地位可以任道學之傳否其亦大言以欺世而已非
實然也
饒氏謂明明徳章句説是明之於既昏之後某亦以經傳文意
詳之似只説因其本明而明之
徳本自明故曰明徳若不因其既昏又何待明之之功而後
明哉雙峰以為只因其本明而明之則是未嘗有所昏也未
嘗有所昏則是生而知安而行唯堯舜性之之徳可以當之
此則不待明之而自無不明者也雖湯武反之之事亦是未
免先有所昏但湯武善反之以復其本然者爾若以本體之
明有未嘗息者為本明則未嘗息者與本自明者固自大有
間哉譬之於火不假吹噓之力自然光燄燭天煙不得鬱物
莫之蔽者本明者也撲滅之餘僅有一燼之微存於死灰之
中不可得而盡熄吹嘘之則仍復熾盛者未嘗息者也讀者
欲分章句饒氏之得失當以是推之
饒氏又曰章句以慎獨為慎之於念慮萌動之始某則謂念慮
自始至終皆在所謹
此當於中庸説慎獨處辯之此不暇及又按語錄有曰這獨
也不是恁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一念或正或不正此
亦是獨處推此可見章句本意非饒氏所識饒氏自謂已説
却不出章句之意此當在第六章饒氏自述其所見與章句
異處而先言之故實於此
經止至善章句止者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叢説至善只是義理極處所中必止於是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此亦祖述雙峰之意以為説者也但雙峰説至字之意明與
章句不同又何必强推章句之説以求合雙峰之意乎竊意
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似矣不遷是不可過則恐未然何則
至善是極好處至是無以復加之意患其不及不患其過如
山之絶頂一般未至絶頂固是不及至絶頂而遷從他處去
亦只是下山了但可言不及不可言過又如月之圎缺一般
唯望夕十分滿輪方是至善之意未望明未滿魄固是不及
之意過望而虧又豈可以言過乎若以至善言之則孝是善
孝如大舜方是至善若以刲股之類為孝此則大舜所必不
為者且不得為至善之至矣况可謂之過乎如此則遷只當
作移動之意説不遷如説不退轉相似語録有曰既至其地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又曰到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其意蓋
可見矣
通謂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之事不遷知終終之之事輯釋亦引
此説
按文言知至至之程傳以為致知也知終終之程傳以為力
行也或問於朱子曰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到
至處方有箇向空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
終之而不去詳此則章句必至於是之至是已至其處之謂
不但如知至至之之為向望要進之意也况必至於是之至
以知言之則智及之之謂以行言之則造其域之謂是固兼
知行而言不如知至至之專指知而言之比其曰不遷以知
言之則知之弗去是也以行言之則仁能守之之謂是亦兼
知行言亦非如知終終之專主行而言之比也今引文言為
證則似乎必至於是是知止於此不遷是行止於此恐於文
言大學之㫖兩不相當而皆失之讀者其參攷焉可也若以
必至於是為知至知終不遷為至之終之則庶乎可耳
饒氏謂至善只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而言也又曰
止者毋過毋不及之謂通謂章句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或問曰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
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然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事理當
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者盡夫天理之則也曷
嘗以造極之地為言哉
此已於前辨之矣又按語録有曰至善只是十分盡善處猶
今人言極好又曰善者固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
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以此觀之則至善之
至朱子何嘗以為不指造極之地而言哉造極之地方是天
理十分盡處天理盡處便是當然之則何過之有其曰本然
一定之則亦以理出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加損又十分盡頭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已若不出於天則非本然之謂若有
一毫未盡則非一定之謂矣然則造極之言正朱子之本意
通者何必為朱子諱哉若必以造極為諱則為善亦以十分
盡頭為諱耶或問章句之意似毋容以異觀雙峰不知己意
與章句之意只一般乃是已非而章句通者又不知或問之
意與章句只一般乃援或問之言以諱章句極字非造極之
謂讀者但以或問語錄玩之則章句之意自明本無可議亦
不必諱也經眀徳至善章句具衆理應萬事事理當然之極通異端言理
不言事大學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徳至善云然
異端以理為障又何嘗言理要之異端只認得箇虚靈不昧
的於具衆理應萬事者皆不知也固是無用體又不成體
定静安慮得饒氏謂定静在事未至之前安慮在事已至之後
此句恐未當竊意安與定静皆在未有事之前慮是處事謂
是事方未按未字似衍來之時可也後字雖亦可通似未甚切當
今輯釋引饒氏此説果云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
至之際與輯講不同想亦覺其未當而改之耳
知止静安慮通引方氏曰異端亦説得能定靜安了只是處置
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慮只是能處置事
大學定靜安是活厎定靜安根源從知止上来如孟子知言
然後自然不動心之意所以事至而能慮異端定靜安是死
厎定靜安但㝠然無覺而已如告子外義而亦能不動心之
意所以事至竟不能慮但猖狂妄行而已如此則異端非獨
不能慮雖硬把捉得定静安亦不可謂之能也疑似之間是
非之辯不可不察
通曰定而能靜則事未来而此心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
則事方来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輯釋亦引此説
易二語以一靜一動對言此是以知行之效騐對言能靜雖
亦是未應事之前然上承志有定向説下来則不可謂之寂
然不動矣若寂然不動又豈可以志言哉志則心有所之矣
謂之寂然不動可乎然則此定靜字只是理明之後外物私
意皆不足以摇奪之而心自不妄耳非對感通言之靜也叢説定靜安以知言慮得以行言
定靜安是未有事之前慮是方應事之時得是事既應之後
慮雖屬處事而未可便以慮為行力行正在慮得之間蓋此
五者是説功效次第則能慮不是行之功效分曉只當與定
靜安皆為知之功效方是
或問篇首之言明明徳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
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徳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
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
以其賔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徳者又三言綱領也至
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天下雖大而
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
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又立言之序
也饒氏輯講問此段最為可疑如言似新民之事在其中此是問
辭却言自明已徳於天下却不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徳也
又如言極其體用之全則似指明明徳為體新民為用此又似
有礙至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
用無不貫其言又似乎明已徳於天下與前章句或問意相反
不知何謂嘗看舊本文或問前段明明徳於天下處云自明其
明徳而推以及於天下今此段似與相著或恐是朱先生改正
之時偶遺忘及此亦未可知
或問之意是合在人在己之明徳以為一而言其體用耳蓋
明明徳於天下固是治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其明徳
然天下舉其全若國若家若身心以上皆已該於其中總言
明明徳於天下則自治國齊家以至於致知格物皆在其中
矣非只平天下於外而小之為國家内之為身心究其極之
為意為知為物皆不用其力也蓋舉大則小無不該然欲致
力於其大則當於其中先致力於其小以為之本耳故言明
明徳於天下則固為新民之極功然明明徳之事亦未嘗不
該於其中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徳四海九州之人固
天下之人一國一家之人與使者之自身亦莫非天下之人
也已欲明其明徳固當格物以致其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
欲使他人各自明其明徳亦不過使之皆如此而已曰極體
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者體即明在已之明徳用即使人各
明其明徳也一言而脩已治人之事無不在非極其體用之
全而何哉曰天下雖大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自有以明其明
徳而新民之體已立天下雖大體亦何所不該乎曰事物雖
多吾心之用無不貫者使人各明其明徳而吾明明徳之用
乃行事物雖多用亦何所不貫乎如此則以明明徳為體新
民為用豈不是經註或問本意而雙峰過疑之耶雙峰蓋以
經註所言專為平天下之事自治國以上皆未之及故如此
見可謂誤矣但以為明己之明徳於天下則本非朱子之意
乃雙峰因誤致誤耳餘見後段辨之
𤼵明輯釋引盧氏觧或問見前段之言曰言明明徳與新民對
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徳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
吾心之體即明徳之虚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徳之靈
而應萬事者也能折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
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祈而遽
欲合之則有虚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此二句其意無窮真西山嘗誦而繼之曰小徳川流大
徳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竊意體即明徳用即新民極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即明
明徳於天下一句而脩已治人之事無不該於其中也觀於
或問前段之言曰所謂明明徳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徳而推
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徳也之言可見天下雖
大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自明其明徳所以立新民之體體固
無不該也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者推以新民使人
各明其明徳所以達明明徳之用用固無不貫也析之極其
精而不亂者篇首明明徳以新民為對分體用而言則明明
徳固專以自明為言合體用而言該自新新民於一句之内
也此二句正是或者所問前後不同之意處熟讀可見或疑
如此説體用似於心之體心之用六字意有未瑩如何曰天
下事物未有不統攝於一心者是故以明明徳為體非心則
徳不能以自明體不能以自立心之體所以該天下之大者
蓋如此以新民為用非心則民不能以自新用不能以自行
心之用所以貫事物之多者蓋如此盧氏所觧則專以明明
徳為自明之事而分其體用故但知虚具衆理者之為體而
不知不明乎徳則無以全此體但知靈應萬事者之為用而
不知不新乎民則無所措其用蓋亦未達經注此句該盡人
已之意而但以明明徳於天下為明已之明徳於天下者不
足以别白此段問答之曲折又恐正墮前段雙峰似乎明已
徳於天下之疑讀者其試思之
𤼵明本當云古之欲平天下者今乃以明明徳於天下代之者以明徳人已所同得明明徳於吾身體也明明徳於天下者新
天下之民使皆明其明徳也用也一言而該大學之體用者如
此
𤼵明此説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徳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徳
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徳於吾身一句是觧篇首在明明徳之
義明明徳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觧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
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
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徳於天下者
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徳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徳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使人命皆該
在此句之中異乎𤼵明之意矣讀者其參考之可也
叢説明明徳於天下此徳字已含明字意在内明徳二字已該
明明徳三字義了上一明字是新民新字之意明明徳猶曰明
明明徳相似與在明明徳不同故章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明其明徳使字便是上明字意按此節所引叢說與原書全不同惟末句稍相似蓋先生所見
與今所傳
本有異
此亦不達或問之意而以明明徳於天下為專指新民而言
不知其該體用故耳其所謂猶曰明明徳相似與使字便是
上明字意之言皆不得經注之㫖而肆為臆説者也讀者知
或問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㫖則叢説之誤不待辨
而明矣已上四條饒氏則專以明明徳於天下為新民之事
而反非或問之可疑盧氏則專以為明己之明徳於天下而
失或問之旨矣𤼵明叢説則皆柤饒説指此句為新民之事
又為章句或問所礙而説得如比朦朧信乎説書之難也又未知愚意能合經註或問之㫖否也姑錄於此以俟明者為
著衷焉
致知在格物通曰章句釋明明徳兼事與理釋至善釋格物亦
曰窮致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徳第
一工夫也故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此一
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徳
而明明徳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潜先生云致知在格物何嘗是明明徳工夫所在後面
一在字與三綱領三个在字各有所指何嘗相應而通不顧
經文摘撮附㑹亂道殊可孝也愚謂經言大學之道在於三
綱領耳何嘗謂三者是綱領所在哉致知在格物亦曰推極
吾之知識在窮致事物之理耳所以不曰欲曰先者盖格物
之外别無致知工夫即在於物之内程子所謂物我一理
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者是已又何嘗謂明徳工夫莫
先於在格物哉
意誠而后心正章句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通意既實則
心之用可得而正
正心該體用動静觀於或問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
之言可見通乃於此添一用字其意蓋謂心之體無不正所
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其實非經㫖也當於第七章辯之
傳之首章饒氏謂此章姑以釋明明徳之義未有下工夫處
此蓋欲歸重於止善章而言也但明明徳工夫全在格物至
脩身五條目上明明徳是五條目之綱領五條目之外别無
明明徳工夫故此章但釋明明徳之義如此而下工夫處却
詳具於五條目之傳非有他也
傳之二章盤銘日新𤼵明愚案日新之藴自仲虺𤼵之湯采之
為此銘輯釋亦引此說
湯銘盤虺作誥其先後似難臆度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章句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饒
氏謂極與至善二義不同此極字是以窮盡無去處為極云云
若至善之至則是以無過不及為至非窮極之義也又謂止於
至善是逐事逐物各各要止於至善無所不用其極是無一事
一物不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是逐一事説是下手處無所不用
其極是該全體説是成就處
按經中章句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與此傳文用其極二
極字皆只是隨事指其十分盡善處為極皆非指衆事窮盡
處為極也自在止於至善處言之則凡事皆有善處善皆以
十分盡處為至十分盡處非極而何又自用其極觀之則此
極字之義亦不過如此而已初未見其指窮盡無去處而言
也必連上文無所不三字説下來方見得窮盡無去處之意
耳雙峰因誤看了此極字之義遂謂經中章句極字之義亦
如此也可謂因誤致誤朱子嘗曰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
之意真雙峰之謂矣
饒氏又曰此章姑以釋新民之義亦未有下工夫處
此與論首章之意同推彼可以明此矣
傳之三章穆穆文王云云饒氏謂但曰止於仁止於孝而不曰
止於至仁至孝以此見至善只是事物上一个無過不及厎道
理非窮髙極厚之謂仁敬孝慈信便是為君臣子父與人交者之至善若更曰至
仁至孝則又似乎言止於至善然者豈不重復矣乎若曰仁
非至仁孝非至孝則仁孝不必十分仁孝已是至善若十分
仁孝則又過於中而反不得為至善也邪如此則雙峰不唯
不識至字之義亦未識中字之義也蓋十分盡善方可謂至
方是無過不及所在若善未至於十分便是不及乎中又何
可以言至乎雙峰每慮其過則仁孝皆不敢做到十分盡處
便自以為至便自以為中天下還有此理否殊不思但言止
於仁孝何嘗不要人十分仁孝觀其引文王為法可見文王
仁孝豈有不十分全盡者耶只因雙峰平日以聖賢自居顧
經註之旨已皆有所未至慮世人以此覘其虛實故將經皆
説降一等求以自便故不得不誣朱子以欺世耳噫
瑟僩章句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𤼵明嚴密在心武毅見於
色
按傳釋瑟僩為恂慄章句又觧恂慄為戰懼下文又以恂慄
為徳為表裏則所謂武毅者似未可指為見於色也語錄云
僩武毅貌能剛强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詳此似亦當以在
心言者未知然否按篡疏引語錄作怠惰闒颯
親賢樂利饒氏謂親賢樂利於此見君子小人分量不同所得
各有淺深所謂新民之止於至善者非是要人人為聖為賢只
如農安畆工安肆商安塗賈安市亦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處
如此則比屋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皆無實之空
言後世如文景太宗之粗可以小康者皆足以為新民極功
而可與唐虞三代比隆矣識者豈宜無見於此饒氏謂明徳新民兩章釋得甚略又但言明新而不言明新之
方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
輯釋諸篇皆引之
篇首三向重在此一句上是固不為無理但言上二章工夫
皆在此一章則非也盖前兩章不言其所以明新之方者明
新之方自具於後六章釋條目工夫處非有他也若至善章
所以詳於前二章而必貫明徳新民二事言者蓋至善不是
懸空物事不過只是明明徳新民所當止之地耳故此章必
貫明明徳新明言之明徳新民工夫既具於後六章之傳則
前二章不容不簡至善雖便是明明徳新民之所當止然其
意則只寓於條目工夫中更無他處可以再詳其義故此章
自不容不詳言至善之義以示人初非以前二章未言明新
之方故如此詳言以補之也蓋綱領雖三事不過二非明徳
新民之外他有止善之事也故釋明徳新民則止至善之意
寓如曰無所不用其極是也釋止至善則明徳新民之義存
如引淇澳烈文之詩是也然亦不過皆言其概而已若謂新
民之方盡具於是則切磋琢磨猶可指為明之之工親賢樂
利何以見得新之之工夫耶
章内五節次序𤼵明輯釋引盧氏曰云云第三節言聖人之止
皆至善以得所止言云云
按此節章句其末曰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
矣則朱子正以此節為知所止之事蓋章句是就學者分上
言盧氏是就文王分上言所以不同要之文王之所已行正
是學者之所當知然則但當以章句為是
傳之四章釋本末或問然則其不論夫終始何也曰古人釋經
取其大畧未必如是之屑屑也目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
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耶
愚聞之章清所先生曰大學諸傳釋工夫而不釋效驗觀於
知止能得與物格至天下平無傳可見蓋效驗只在工夫之
中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終始正是以效驗言所以無傳固
非屑屑不及釋亦非本有而并失之
傳之五章饒氏謂朱子補傳似乎說得太汗漫學者未免望洋
而驚如既謂即凡天下之物則其為物不勝其多又謂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表裏精粗全體大用亦是自
立此八字經傳中元無此意
按即凡天下之物非謂把天下之物一齊格了亦曰就凡衆
物之中隨其所用而逐件格之耳求至乎極亦非謂求至乎
凡物衆多之極亦只是求至此一物義理之盡處耳直至下
文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方
是合衆物之全而言以文勢詳之可見雙峰不詳下文有衆
物二字遽以前節極字為事物當然之極真所謂理有未明
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此其說極字之誤正與前說至善處
極字之誤同知彼則知此矣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八字固是
朱子之所自立然豈不切於格物致知之義耶朱子本不效
傳體行文其所補之文便只如章句一般又何必以經傳所
無而疵之乎至於汗漫望洋之疑則大學之道是教人學至
乎聖人之方法格物致知一章正所謂始條理者之事始偏
則終亦偏始全則終亦全觀於孟子論始終條理處可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奈何患學者之不能
而欲自貶以狥之乎况望洋之疑只因雙峰誤看極字之所
致他人看得極字之義分曉又安有望洋之驚哉
語錄問先生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為之竟
不能成
竊意效傳體行文特文公餘事決無效不能成之理此特姑
為謙辭以答學者之問耳正意恐不止此也蓋若效其文體
則必援引經傳文意簡古學者未必自能通曉須又為之註
解以曉之如此則自為自註豈不為好事者之所譏誚故不
求其文之類但取其義之明所補便如章句一般庶乎人之
易曉耳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饒氏曰愚謂大學之要只在止於至善上格物是隨事隨物每
每要究到至善處致知是要推致其知識使之知此至善不必
必别為之說
朱子之意何嘗以格致不是要知此至善但理是事物之實
理至善又是狀此實理之體段說至善不如說理之實耳只
因饒氏看得至善之至字有礙又疑補傳之太汗漫故如此
見耳要之朱子以致知為知至善朱子與雙峰無異觀於章
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之言可見但雙峰以至善之至為
無過不及之意而非極至之義與朱子不同故於此亦不合
耳汗漫之疑殆亦起此讀者其試思之
饒氏謂或問云聖人說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
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謂聖人設教使之如此求之經傳卻
無證據看或問所引只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為證然德性是說心之理靈是說心之知覺有些不同况道問學是兼知行
言此却是專指致知而言似亦未甚親切
竊意古者八歲入小學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為大學
之基本此豈非聖人設教使之如此似不必他求經傳以為
證據也按語錄問格物問前段有曰聖人於其始教為之小
學處說了此說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裹壓重了不
潔浄詳此則朱子所據之意可見靈字只說知覺之處後第
七章心不在焉處與孟子告子上篇牛山之木章詳之道問
學兼知行之說當於中庸辯之此不贅及
補傳通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良知之知得於天性理有未明
知有未盡此致知之知得於學力
知只一般得於學力者即所以復其得於天性者耳分良知
與致知而言然則得於天性之外又他有得於學力知果由
外鑠我耶
或問取程子格物致知之說十二條朱子取其意以為補傳通
謂補傳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
第一條意程子曰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
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
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是
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又曰
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能有勉而行之
者也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
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
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
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逕皆
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
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第六程子
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則是巳然
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第七程子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
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温凊之節莫不窮究然
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第八條意程子曰物我
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
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之四
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終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
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是取程子第二程子曰
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爾
第三程子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脱然有
箇覺處第四條之意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
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然脱然有悟處自衆物
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
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
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遠而而
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
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
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第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
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六第七條意者皆是矣謂必使學
者至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條八條之意至於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是取程子第二第三第四條之意者皆
得之而未盡謂末節後四句是取程子第九第十之之意則
全失之何則補傳凡三節第一節自起首至窮其理也是說
致知在乎格物此正說以引起第二節說工夫之意下文至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說物未格則知不盡此反說以引起第
三節說效驗之意第二節自是以大學始教至求至乎其極
是就逐物上說格物致知工夫第三節是承上節就衆物上
說物格致知效驗程子十二條前二條與第一第六第七條
皆說工夫如通言可也第八條是說衆物上用工不可不周
通但以為全是補傳第二節所取則有所未盡第九第十條
是說衆物上用工又不可泛然無序正是說工夫處通乃以
為是補傳第三節後四句所取則此四句正是說效驗處以
為有取於彼是不察工夫效驗之有辯也愚則以為此三條
者補傳凡說工夫處如前二節與第三節用力之久一句皆
在所取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此四條是合工夫效驗言者
其實是補傳全章之所通取亦初不分節以配之也通以為
第五條是補傳第二節所取殊不思可推而無不通一句何
嘗不就衆物上說貫通之理耶通又以為第二第三第四條
是補傳第三節起頭二句所取殊不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
一物與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及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
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等語又何嘗不是說就一物上窮格
以至於積累之多正是通謂格致工夫之始終處而通皆指
為二句所取可乎况補傳第三節末後四句正是承豁然貫通之意而言格致之效驗處如此則第二至第五條所謂貫
通處覺處悟處與無不通之言是補傳第三節六句之所通
取通乃獨以起頭二句當前三條之意後四句既曰不取此
意則只得以第九第十條當之而不思二者有工夫效驗之
不同可謂誤矣或問取此十條自有次第第一條說格致用
功之法最為詳備是就逐一物上說故居首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條皆通說工夫效驗之始終是就逐物上說至衆物上
故次之第六第七條皆說就逐一物上當窮到極至處是申
第一條之意故又次之第八條說衆物格之不可不周第九
第十條皆說衆物之中格之又當有先後緩急之序三條皆
是申第二至五條之意故以是終焉大抵說工夫處多說效
驗處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效驗處無只說效驗而不說功
夫處通不察其次序之精密如此乃雜然取以配之於說功
夫處亦取五條意於說效驗處亦取五條意宜乎其致誤也
讀者詳之
矩堂董氏槐以經文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九句合傳
之四章及五章結句共為一章是說釋格物致知之傳朱子不
當更作補亡
按經文自明明德以下三句是一節說工夫自知止而后有
定以下五句是一節說效驗自物有本末以下四句是一節
總結前二節之意此皆是以大學綱領言之者自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一節是逆推工夫之所始自物
格至天下平一節是順序效驗之所極末後二節是結前兩
節之意前節正說結工夫後節反說結效驗此皆是以大學條目言之者其前後次序秩然不可紊亂如此今若掇此九
句以為格知之傳則綱領但說工夫不說效驗又無結意與
後段說條目處不同矣况諸傳之體說工夫處多說效驗處
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效驗者無只說效驗而不說工夫者
盖以無工夫則無效驗效驗不在工夫之外也况格物為大
學始教之事而不詳言其工夫可乎今以經文九句推之則
定静安慮得五字不可謂之工夫明矣知止之知亦已知所
止而非用工求知所止之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亦但言事
物大概如此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亦不過欲知本末終始所
當先後之序庶乎可至於道不遠而已亦不見格之致之所
用之工當何如也更以第四章傳文推之亦不過但言聽訟
之輕重欲人知明德之為本而已初未見欲知明明德新民
之理則當如何下工夫也遽以為物格遽以為知之至可乎
董氏但見經傳二處有此幾箇知字便欲牽合以為格物致
知之傳而不知致之格之之工夫不止如此也觀於中庸以
學問思辨為擇善之事而皆屬乎知說知如彼其詳則格致
之傳必如補亡之言而後盡董氏蓋不足以知此也
傳之六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章句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
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饒氏謂
謹獨只是審其善惡之幾而去取之如此則不自欺而自慊矣
章句謹獨是審其實與不實之幾
詳章句之意此是指獨字而言幾是指好善惡惡之意而言
審是審其幾之實與不實審其幾之實與不實即好善惡惡
之意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與否也雙峰為章句是審其實與不實之幾似未得章句之旨章句特欲審其幾之實與
不實爾至其自謂只是審其善惡之幾而不及好之惡之之
意又似與獨字之意無相關者不知如何
饒氏謂誠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且如顔子問仁而夫子告以
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只在四箇勿字上仁屬心視聽言動屬
身勿與不勿屬意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此心
之仁即存以此見三事只是一串
引四勿為證是矣但經言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雙
峰謂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此心之仁即存
則又似乎意誠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心正者恐不可得而強
合要之牽合附會之言自不能無罅隙亦不足深辯也
問傳之諸章釋八條目處每章皆連兩事言獨此章單舉誠其
意是如何饒氏曰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兩件事當
各用其力所以誠意不連致知說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
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局狹無以見
其功用之廣通引金氏曰大學諸章之傳首辭結語皆以序言
自正心以上獨不以序言蓋心身家國天下各是一節之事而
致知誠意二者同為心上之事心統知意者也若亦以序言則
是一心之中文自截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却自分成三次豈理
也耶然皆以序言於經經傳固互相也通曰大學條目有八
僅作六傳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
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章句謂
誠意者自修之首亦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
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亦可見輯釋亦引饒氏與通之說詳此三說皆不過因誠意自為一章與前後五章皆兼釋二
事者義例不同故此見耳饒氏知行當各用其力之言似矣
竊意知行當各用其力孰與脩已治人之當各用其力耶今
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且以脩己治人之事合而言之然則
以致知合誠意為一章又何為不可哉饒氏此言恐未必然
也若誠意不獨為正心之要者恐亦未必然當於後章辯之
金氏知意皆統於心心上工夫不可截作三次之言亦是自
立此說以經文論條目之工夫效驗處皆相因為序之意推
之何嘗無三節工夫耶且果如饒氏金氏之說則經文次第
皆不若傳文之當耶金氏亦既自知之矣通者援章句自脩
之首四字以合於饒氏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之說亦似矣
殊不思饒氏何嘗以朱子之說為是耶觀其謂首字不若要
字之言可見章末潤身心廣之證亦本饒氏皆未得為的論
也獨通者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之言近之
惜其不能推此以究其義也愚嘗以為傳自五章釋八條目
八條目之中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故經不曰欲致其知者先
格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便見此二者與正心修身修身齊家
齊家治國治國平天下二事相因者不同格物即所以致知
所謂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是已然則第五章釋格
物致知與第六章釋誠意皆是一章釋一事所以然者以二
事用功之不易也章句曰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詳此則此二章皆是一章釋一事之意可見語錄以
第五章為夢覺關第六章為人鬼關又為善惡關詳此則此
二事用功皆不易之意又可見矣自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皆一章兼二事釋者以物既格知既至意既誠之後循序漸進
用功為易耳語錄以為過此兩關夢覺人鬼上面工夫一節
易如一節了詳此則自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用功為易者信
矣然則六章之傳釋條目者前二章皆一章專釋一事以其
難也後四章皆一章兼釋二事以其易也下過如此而已不
知識者以為然否
章句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饒氏謂首字不若要字云云言修
身正心其要只在誠意意既誠則心自正身自修又謂誠意正
心脩身不是三事三事只是一串又謂誠意之外别無正心修
身工夫
首字不若要字之說正如中庸鬼神章包字不若貫字之說
要字貫字自是雙峰意如何亦欲朱子從之其意既誠則心
自正身自修與誠意正心不是三事三事只是一串及誠意
外别無正心脩身工夫之說辯則辯矣新則新矣其如經文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與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這數句何經文明有三節工夫而雙峰
強說誠意外别無正心脩身工夫經文明說而后心正而后
身脩雙峰強說意誠則心自正身自脩然則經何以不曰意
誠而后心正身脩欲脩身正心者先誠其意耶經文分明分
别作三事如此而雙峰強以為不是三事只是一串何耶朱
子嘗言序之不可亂功之不可闕如雙峰說則序皆可亂功
皆可闕矣雙峰勇於背朱子而不思經文之序本不可亂經
文之功本不可闕非朱子創為之說也以經證傳以傳釋經
則雙峰之謬誤不難見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通謂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
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輯釋亦引此說
小人固無二小人但此二章所言一為自脩者之戒一為用
人者之戒以為彼小人即此小人則非傳者之意也
傳之七章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章句蓋是
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
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饒氏謂忿者怒之暴
懥者怒之留恐懼好樂憂患與忿懥為類蓋亦指其情之偏重
者而言也問章句謂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如何饒
氏曰忿懥是不好底因此一件則知下面三件皆指不好底說
按章句云忿懥怒也夫怒所當怒亦未可便謂之不好唯雙
峰以怒之暴怒之留釋之然後二字之義乃不好耳愚嘗徧
考字書並無以暴留之意釋忿懥之義者然則雙峰暴字留
字之意得非本語錄忿又重於怒與忿懥是怒之甚者二句
而言乎然暴留二字與甚重二字之義不同重與甚是因事
有可怒之甚者怒之不得不重未害其為心之用也若暴則
至於虐物留則滯而不化皆過其則而不中其節非所宜有
也雙峰若别無所據但因語錄而推之如此則不若但依章
句平說為怒之得也蓋四者皆心之用今因說忿懥一事作
不好而并與恐懼好樂憂患三者皆以為不好厎而又不能
明言三者所以不好如忿懥二字之故則何以使讀者之無
疑哉豈若朱子只輕說忿懥則四者皆不能無但不可有之
於心之得乎况傳文不但曰有忿懥等而必曰有所以有所
二字觀之則章句之旨似無可疑又按金氏祖饒氏意併以恐懼好樂憂患三者皆連二字言之為不好之證通亦從而
和之然則中庸恐懼不聞孟子生於憂患亦連二字言之則
何以分别其好不好耶
語錄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
一事而在胷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罪而撻之纔撻了
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
按七章四言有所八章五言之其所所之一字皆是指物之
辭蓋人之一心未有事之前事已過之後皆當湛然虚明則
不滯於一隅不偏於一事所以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無有不
得其正者矣今乃於未有事之前或事既過之後其實未有
事之前又是前一件事既過之後非有二也而有所忿懥等
焉則是滯於一隅偏於一事當虚不虚當無而有而心之本
體自有所慮矣宜乎及有當應之事以此先有所主之心應
之鮮有不失其正者也故語錄云有所字正指所憂患之事
所忿懥之物而言以其滯而不化不當有而有故皆以有所
言之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章句心有不存
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
身無不脩也饒氏謂此以心不在明心不正之害心不在未便
是心不正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未便是身不修傳者欲借
粗以明精言心不在則無知覺以為一身之主宰而視不見聽
不聞食不知味矣况心不正則無義理以為一身之主宰亦何
以視所當視聽所當聽食所當食而無不脩乎輯釋諸編皆引
此說按語錄問心不在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纔
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此言可謂至矣讀者更以
孟子告子上篇牛山之木章語錄及中庸章句序之意參之
愚已於孟子備述之則朱子之意顯然可見矣况在之為正
訓雖殊而歸則一朱子於孟子求放心處以昏昩放逸為言
昏昩是就知覺上說放逸是就義理上說昏昩則失其知覺
而無以為燭理之本放逸則徇物於外而不能為應事之主
必兼此四字而後可以盡心不在之義而心不正者亦不外
是矣饒氏以釋氏常惺惺為心在而不正之證則是但以昏
昩為不在而不知放逸之乃所以為不在也泛而觀之昏昩
放逸雖若二事合而言之則未嘗不相關也何則知覺雖不
昏昩然苟為不在理義之中則一有可徇之欲必將徇之以
放逸於外而嚮所謂知覺之不昏昩者亦不過但能不昩於
所徇之欲而於其他當應之事反昏昩而不知矣謂之在可
乎蓋嘗合朱饒之說而觀之則知雙峰但以知覺不昩為在
却以義理無失為正如此則正與在為二而正又在乎在之
外雖不正亦可以為在矣殊不思義理有失便是徇物放逸
於外又可以為在乎朱子則以知覺既不昏昩又能居中役
物嘗在義理之中而不徇物放逸於外者為在如此則在外
無正不正不足以言在矣姑以世人之心言之彼其喻於利
者雖刀錐之末亦皆毫分縷析無有或遺如此者不可謂其
知覺之不在也然心不能以役物反為物所役不免逐物於
外謂之在可乎雙峰惑於知覺不昩之似乎在而許之乃不
察其不免逐物於外之實不可以言在也遂疑在與正之有二毋乃未得在字之意乎又自聖賢之心觀之聖賢之心湛
然虛明則其知覺之不昧可知然其所以爲知覺者則唯見
理而不見物也唯見理故常居中以役物不見物故不外馳
以徇物知覺不昧在也居中不外馳眞在也知覺常在義理
之中不與物欲俱往在外無正正不出於在也朱子不徒指
其知覺不昧者爲在尤必取其不外馳者爲在在又豈有不
正者哉況此章爲釋正心脩身而設章首一節但言心之不
得其正者耳至心不在焉以下方言心不正則身不脩之意
正當直指其義以示人若以爲借粗以明精而卒不明言其
本旨之爲借又遂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結之則人將認粗
以爲精認欲以爲理幾何其不與吿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
之言無以異乎更以前後章傳例攷之未有如此之隱晦者
可見饒氏辨此極詳又摭朱子或問之言節節破之故辨之
不得不詳然大意不過如此讀者攷焉可也
饒氏又以釋氏常惺惺爲心在而未可以爲心正以離婁爲視
見師曠爲聽聞易牙爲食知味而未可以爲身脩如此則心在
未是心正視見聽聞食知味未是身脩不過是借粗以明精了
傳本以心不在焉則一身無所主宰百體皆失其職而身以
不脩亦猶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之意視聽食姑舉其槩以見
例耳雙峯乃以釋氏離婁師曠易牙爲證殊不思傳文四句
只就一人身心上言之有人於此心不外馳而耳目口鼻四
體百骸皆稟命焉而不失其職可不謂之心正身脩乎雙峯
乃以四人之事證其不然宜乎其不合也且釋氏廢心用形
心雖惺惺而置之不用之地則其視聽食特猖狂妄行而巳
固未必見聞而知味也是固不可以證此章之旨矣離婁之
視見則心逐所視之物於外不可謂存與仰面貪看鳥囘頭
錯應人者相去無幾則其聽未必聞食未必知味又可知矣
師曠易牙亦然饒氏不知釋氏之心與離婁之目師曠之耳
易牙之口本不相關而強合之以證一人之身心是猶使甲
口食膾炙而責乙心不能知其味之美也不亦誣乎
在正其心不得其正通謂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
之用耳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直內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
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直內之本體
蓋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
用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潛先生云正心功夫是兼動靜體用觀或問鑑空衡平
之體用可見通謂心之體無不正正其心者正其用耳夫心
體無不正唯聖人爲然若衆人則或有偏倚矣正其心之用
若獨於此用功則未應事時皆無工夫矣又謂心之用或有
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此固未爲的當而謂不得其正此正
字是說本體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章句分明言
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而通謂本體之
失其正豈好奇求異於朱子邪抑未悟朱子之旨邪何先後
自相矛盾若此也愚按此辨當矣但傳謂在正其心此正字
乃是兼體用而通以爲正其心之用旣失之矣不得其正此
正字乃是專指用而通以爲體失其正尤爲失之也何則蓋
傳在正其心是總起下四句之意下四句每句皆兼體用而
言心之本體未應事之時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乃爲得其
正今乃無事而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焉則如鑑未照而
先已不空衡未稱而先已不平豈非體有所累而失其正乎
所以至有當應之事以此先有所主之心以應之或當怒者
倍怒當喜者不喜或當恐者倍恐當好者不好喜怒憂恐不
重卽輕如鑑先不空以照則妍醜不得而明衡先不平以稱
則輕重不得而定豈非用有所偏而失其正乎由此觀之則
有所忿懥四者是心之體失其正處四言則不得其正是心
之用失其正處通不如此看而交差互失惑人甚矣讀者詳
之
叢說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此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
怒而應當喜者或以樂而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
應事上謂身心全不相關通引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
此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主此一節說不
可以無所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存主也心在則羣妄
自然退聽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然則中虛而有所主宰
者正心之藥方也
按二說極當深可以破饒氏之謬故錄之以備參考
饒氏謂七章章下註文似可省
按饒氏自謂正心脩身二章工夫皆在誠意章故如此說然
經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固與章句之意
無異章句自援經文以貫傳義甚爲的當饒氏柰何教玉人
雕琢玉而省此不可省乎
傳之八章饒氏謂此說皆是尋常人有此病痛似不必將敖惰
做合當有底
因敖惰而廢親愛等四者與說忿懥不好之意同知彼則知
此矣但雙峰此段議論極詳大抵皆是諸子之所已破讀者
攷之或問語錄足矣正不在於後學之有辯也
章句之猶於也饒氏謂之者心之所之是向之意本不可訓於
但於於字相近故曰猶於也
雙峰惟如此說之字故以五者皆不可有竊意若改而辟焉
而為則乃可如此說耳
饒氏謂七章言心有所忿忦等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
之道八章言人之其所親愛等則流於辟而不言所以脩之之
方夫有是病必有是藥今詳此二章詳於論證而畧於處方蓋
心與身一物也而心為之主意與心一事也而意為之機故傳
釋誠意一章首之以毋自欺申之以謹獨以明用功之要莫切
於此故終之曰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以著意
誠則心正身脩之要也雖然不特正心脩身為然由是而齊家
治國平天下無往而不自慎獨出也故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
之平天下章曰必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意慎獨之
意也輯釋亦引此意
有心術之病有事為之失心術之病惡也先儒所謂縱有善
亦是黑地上一點白是也事為之失過也先儒所謂縱有未
善亦是白地上一點黑是也然則意不誠則好善不如好好
色惡惡不如惡惡臭甚則至如小人陰惡陽善者之所為此
蓋心術之病非過也惡也惡則治之也難故必毋自欺必谨
其獨而後意可得而誠不然則陷於小人之域矣然意既誠
矣固無為惡之事然於善之中未可保其無所偏無所辟也
此所以雖曰實好善實惡惡至於心之應事猶或至於有所
忿懥等而不得其正者亦有心雖已正至於身之接物猶或
至於之其所親愛等而辟焉者然雖未免有所偏辟亦不過
於善之中有偏辟耳無所謂惡也然不謂之過則不可過則
改之而已所以知其偏則使不至於偏知其辟則不可使之
辟足矣無所偏辟則善之至矣又何方之可處哉蓋大學之
教必須逐節用工隨地致力不可謂意既誠則心自正身自
脩誠意之外他無正心脩身工夫而混然不為之界限也若
果如所說則大學只列六條目足矣又何必虚設正心脩身
二條目於其間而實無所用之功哉心廣體胖之云亦所谓
以明誠意為自修之首之意非謂工夫止於如此也但誠意
正心脩身三者折而言之則自當有序合而驗之却不可以
為截然不相入故日用之間念慮之萌動處便須審其實與
不實此便屬之誠意心之與事應處便須審其正與不正此
便屬之正心身之與物接處便須審其辟與不辟此便屬之
脩身其工夫並行而不可偏廢有似於無二致耳實則界限
不相侵越而不可亂也何可因其似於無二致者遂謂慎獨
一言足以盡三者之工夫而紊其不相侵越之界限哉况如
其言以為自正心至平天下皆無往不出於慎獨則謂正心
以下論證而不處方可也自齊家以下諸傳又何為既論證
而兼處方也哉借曰誠求忠信即慎獨之意則正心脩身兩
章獨不可一言及之如此乎此愚所以不能無疑於雙峰之
說也雙峰之說近代四書通及陳氏發明皆引援而祖述之
故辯之不得不致其詳云傳之九章如保赤子語錄孝弟鮮能守而不失惟保赤子無有
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與孟子孺子入井之意同叢
說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
就愛民處言
案叢說雖於章句之旨有所未盡於語録之論微有不合然
亦似乎有理姑備一說竊意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為君
者則誰為忠乎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若為長者則誰為順
乎故孝弟專為臣與在下位者言之唯慈使衆可以通為君
臣言之故專以此示訓耳未知然否
一家仁讓一人貪戾饒氏謂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
讓屬弟貪戾是本上文慈字而言貪戾者慈之反也
孝弟是專主事親事長而言仁讓則通主待人接物而言若
以為仁屬孝讓屬弟則一家之人父兄亦自在其中為父者
誰為孝為兄者誰為弟乎貪戾二字恐便是仁讓之反貪則
不讓戾則不仁貪戻亦通主待人接物而言非如慈之專主
慈幼言也以為慈之反恐亦未必然近見盧氏亦有貪則不
讓戾則不仁之說乃知固有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非私言
也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通引王氏曰張子所
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此意雖相似而所主則不同大學主治人者言張子主自治
者言不可不辯也
傳之十章上恤孤而民不倍章句倍與背同
案章句不釋不倍之義說者皆以為下民不倍在上者慈幼之心而已雖亦可通竊疑孝便是老老意弟便是長長意不
倍却與恤孤之意不類文須轉摺方通先師冰壺鄭先生嘗
曰坊記有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與以此坊民民
猶偕死而號無告之言鄭氏注云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
呼稱寃無所告而韻書背偝倍皆同音義則不倍正是恤孤
之意豈章句以其易曉故不釋之耶抑但如說者所云也邪
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絜矩通謂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之道志學以下分知
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格物以下亦分知
行到末章方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乍看論語矩字似說
得精絜矩矩字似說得粗要之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矩字
是體絜矩之矩是用輯釋亦引此說
竊意論語矩字是就德上言是義此矩字是就政上言是怒
義與恕要之皆是用恕乃所以為義也今以彼為體此為用
似有可疑况彼章知行之分與此處分知行者不同彼處知
行當於此知行上横貫過夫子十五志學是知之始此便是
於八條目一一攻究了不是只從事於格物致知二者而已
立與不惑以下皆然若以為只是一箇矩則夫子未七十時
若為政於天下猶未有絜矩之體耶觀二矩字一言不踰一
言絜便見聖人學者之分若以彼為此體此為彼用恐皆鬭
凑不著又以不踰矩為生知安行之極致既曰志學則下生
知字不得觀集注於耳順處只說知之之至而不說生而知
之可見
絜矩通䂓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
者止不踰矩即是明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潜先生謂通謂矩方而止以強附於止至善之止尤為無
理矩取方義不取止義也
所惡於下云云章句則身之所處云云而無不方矣饒氏謂方
字恐未安絜矩之喻取其平非取其方也
方字於矩字之義為切方則天下自平恐亦無所謂不安也
好惡通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己
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
人者也云云輯釋亦引之
好惡雖只一般然三章所言各有所指傳者初無相承之意
通者強合以為說不過只是蹈襲雙峰誠意為下五者之要
之言爾此皆所謂詖辭也自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己者以下
皆所謂遁辭也雖若可通實非傳意亦不足深辯也
見賢不能舉云云饒氏謂過之罪小命之罪大如漢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
舉賢退不善二事常相因能用賢必能去不善不能去不善
必不能用賢書曰用賢勿貳去邪勿疑可見二事不可分輕
重若以元帝事證則其不能用望之却由其不能去恭顯况
望之之死又出於恭顯之讒豈可以過之罪為小於命哉
忠信以得之饒氏謂忠信即是慎獨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
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輯釋亦引此
謂意既誠後下五者工夫自然易則可謂五者工夫皆不出
於誠則不可且如忠信固不可不慎獨能慎獨固能忠信但遂以忠信為慎獨則慎獨恐該忠信不盡
君子有大道章句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也饒氏謂大
道乃絜矩之道
章句兼體用說饒氏只就用上言
孟獻子發明輯釋引盧氏曰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
能知絜矩之道
獻子在前子思在後以為獻子嘗師子思不知何據豈傳寫
之誤耶
必自小人矣金氏曰彼為善之上下必有缺文當作彼為不善
之小人與下文雖有善者亦相對通曰誠意章曰小人閒居為
不善故此章曰彼為不善之小人前後正相對
陳公潜先生曰小人雖一般但誠意章為不能慎獨言之以
為學者之戒此章為理財言之以為用人之戒初未嘗有意
於相應且朱子謂疑有缺文誤字正不必添一不字以強合
於為不善之語也愚謂如金氏之言始備一說猶未甚害通
但不當蹈襲而質言之以牽合乎誠意章小人閒居為不善
之意爾此亦本雙峰誠意為下五章之要之說而言也
全章之旨發明南山有臺詩好惡此言絜矩以用人之事節南
山詩言不絜矩而所用非人又於或問申其說曰好惡宜專就
用人說
按好惡所該甚廣用人亦其一事耳章句但言以民心為己
心固不直指所好惡者為何事或問則以好其所好而與之
聚惡其所惡而不以之施而究其義蓋本孟子所欲與聚所
惡勿施之意為說可謂至明白矣發明必以用人實之疑非傳文本意竊詳此章除首二節發出絜矩之名義外其下三
引詩姑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起下文財用用人
二者能絜矩與不能者之意末又以理財不當用小人而總
結之下文既皆以二事分合言之不應南山有臺等三詩獨
偏舉用人一事以發之也蓋用賢固是民之所好上不外本
内末使民皆有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亦豈不是民之所好用
小人固是民之所惡苛征重斂使民無以為仰事俯育之資
亦豈不是民之所惡然則正不當專指南山有臺節南山之
好惡為用人而言也讀者但當熟玩章句或問語錄之意則
發明之說未易以當可知矣
章末
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欲學大學者可須臾毫釐
之不敬哉
陳公潜先生曰按所謂忽恐學者以其書為淺近而忽易讀
過不加深體力行之功耳而通釋為敬引聖學成始成終之
語聖學之敬不但主於讀大學一書而已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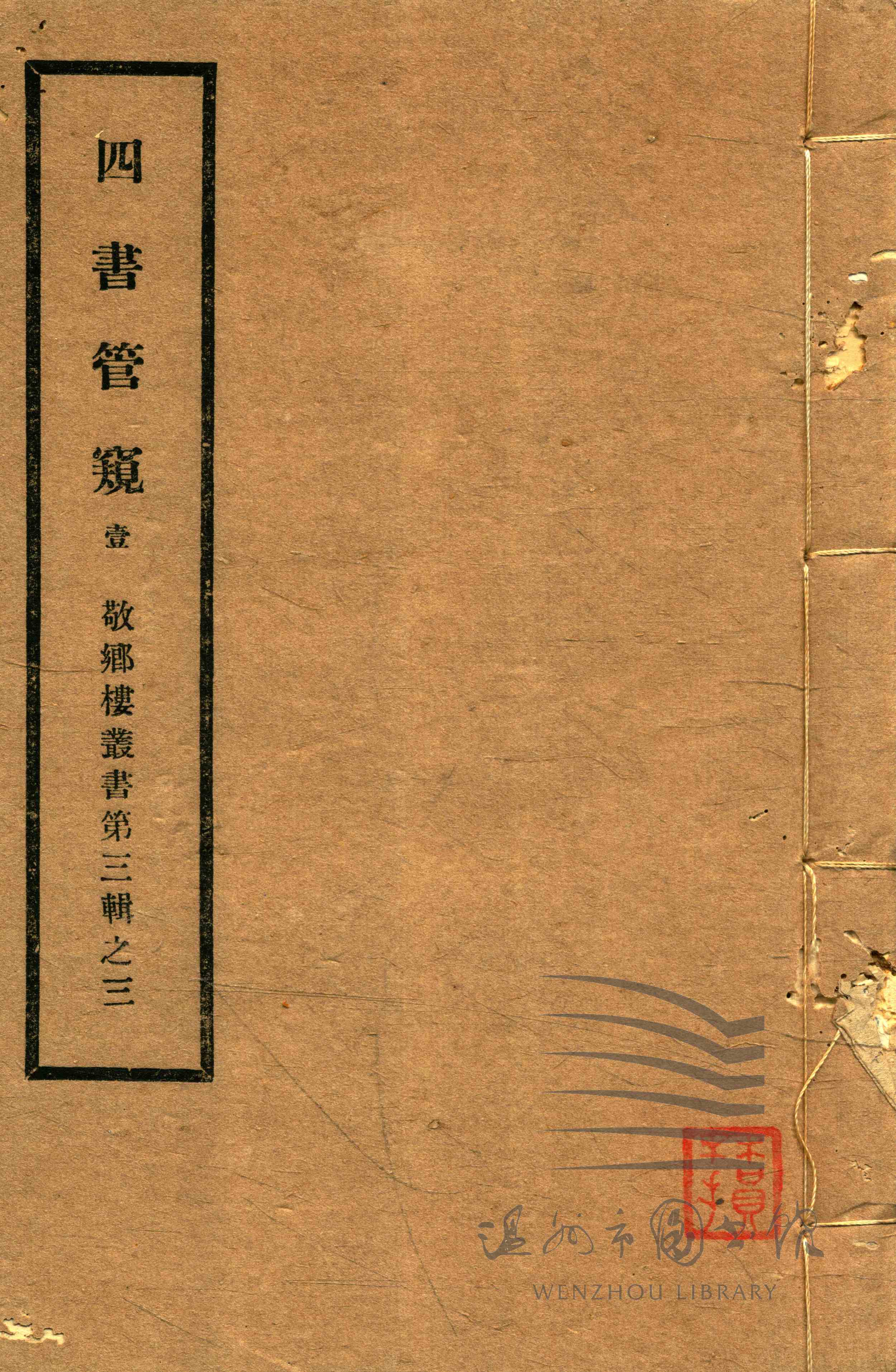
《四书管窥十卷》
出版地:温州
元史伯璿(字文玑)撰。该书见于秘阁书目者五册。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于府学。是明初印行已有二种版本。然刻版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抄。《大学》、《中庸》、《孟子》尚全,唯《论语》缺《先进》篇以下。然量其篇页,厘面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是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倪士毅《四书辑释》及饶鲁氏张栻氏诸说,取其与朱子《四书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诸说之互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如《大学》“君子有大道”。《章句》“道,谓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术也”。饶鲁氏谓“大道,乃絜矩之道”。该书认为:“《章句》兼体用说,饶氏只就用上言,以上文‘先慎乎德’之意推之,则《章句》之说有据。”又如《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谰章”。《发明》引张氏说,以几谰为谰于未著,又引饶氏说,以不违为且顺父母意思,不可与之违逆。《发明》自谓张南轩、饶双峰不妨自为一说。该书认为:“二说皆《语录》之所不取,《发明》又引之何耶?大凡说经贵得其旨,得其旨则一说足矣,兼存异说,只惑人耳。若以为有补于世教而取之,则当自为书,不当附在圣经之后也。”书凡三十年而后成。此书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略同,而更为重视别白。其中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多。虽其间不免有舛异疏误,然于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有《四库全书》本。
阅读
相关人物
史伯璿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