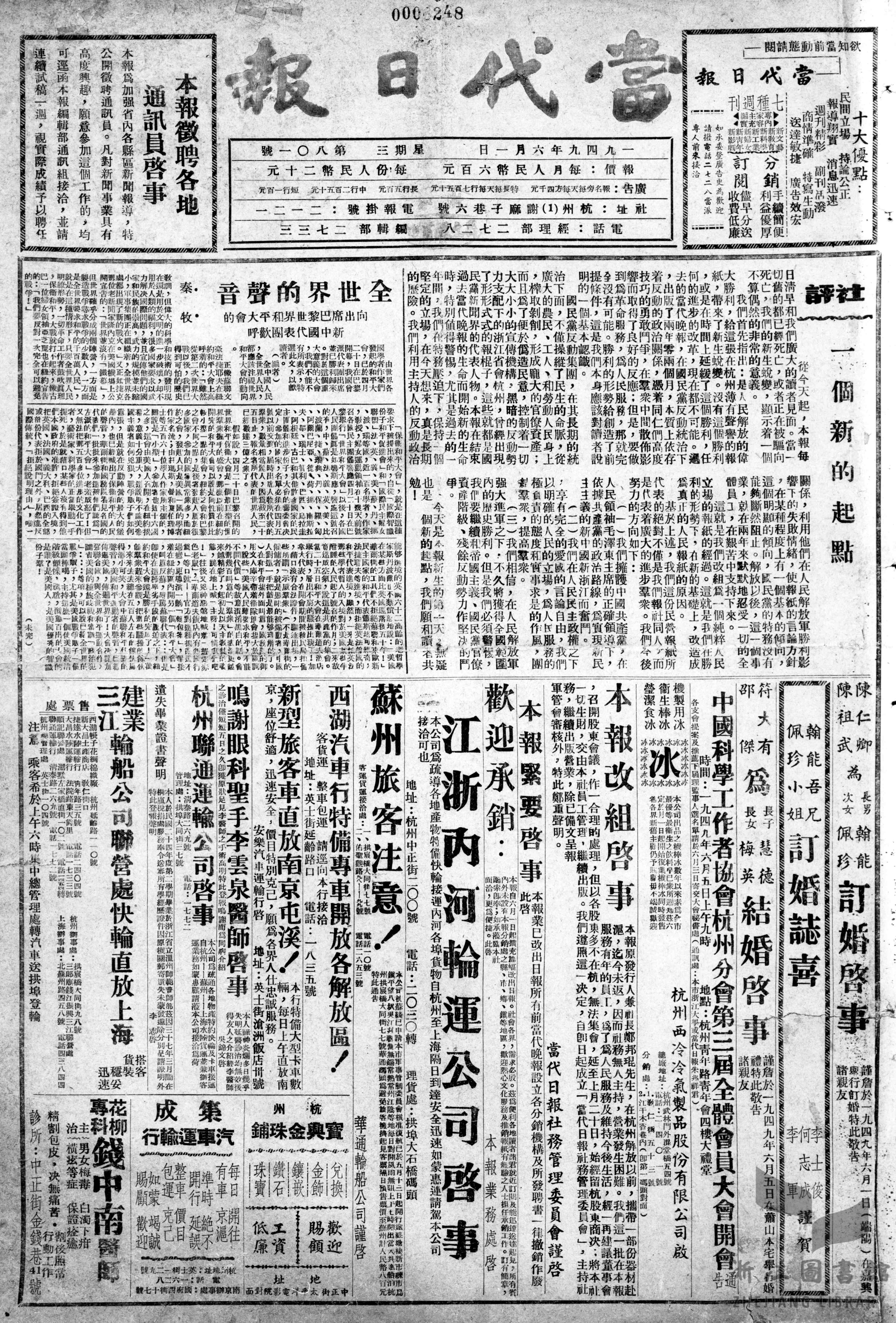内容
新華社記者袁蓬
京漢鐵路中段,在滾滾東流的黃河上,橫跨着我國第一座大鐵橋——京漢路黃河鐵橋。它把我國華北、中南、西北、華東廣大地區連接起來,是北方和南方物資交流的樞紐。
黃河鐵橋是在五十二年前由法國和比利時的包商承建的。修成時,工程師就把行車速度規定爲最高每小時十五公里。以後,在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時期,黃河鐵橋又受到多次嚴重的破壞,行車速度更是每况愈下。解放前坐車通過黃河鐵橋的人恐怕都還記得那時候的艱難情景:短短二十幾個車廂的列車,要分兩次才能過橋。從黃河南站到北站不到五公里的路程,旅客得在車上熬上三個鐘頭。
那時候,人們都認爲黃河鐵橋像是已經活够了歲數該死的人。無法挽救了。國民黨政府曾經兩次請美國人設計另建新橋。第一次在一九二九年請來了一個名叫瓦德爾的橋樑專家。他只是坐火車從橋上過了一趟,連車都未下。自然談不到作任何勘察工作,就派他的助手魏爾工程師來試打新橋樁了。這位魏爾工程師在黃河岸邊住了將近一月,一根普通的木樁打進土裏不過十公尺,比起老橋樁的入土深度還淺得多。現在坐車過橋的人還可以看見橋南頭東邊一百公尺處河水裏的那根樁子,就是美國專家的可憐的紀念物。一九四六年,國民黨政府又請美國馬力生公司設計新橋,花了十萬元美金的設計費,並從國內派了一批工程師去實習。鄭州鉄路局的工程師劉鴻鈞就是其中的一個。據劉鴻鈞說,他們那次滿懷希望而去,却大失所望而歸,因爲美國資本家並沒有眞心幫助中國進行建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蘇聯橋樑專家金戈連克等來到了黃河橋上。金戈連克已經是禿頂、白髮的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他懷着援助我國進行經濟建設的國際主義精神與滿腔熱忱,不顧嚴冬的寒風,從橋這頭到那頭,爬上爬下對各部分進行了詳細檢查。他拿着鐵錘敲聽了許多節鋼樑以辨認鋼的應力,化驗了鋼質。然後,他在鄭州鐵路管理局召開的一次工程會議上,提出了黃河鐵橋應該進行加固改善的意見。金戈連克說:目前中國正處在經濟恢復時期,應使一切生產設備充分發揮効用,並努力節約。他根據實地勘察與科學計算指出:黃河鉄橋進行加固改善之後,完全可以改變運輸狀况。當時,許多解放前就在鄭州局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聽了並不相信。他們想:「美國專家來了都沒辦法,也是說要另建新橋………」金戈連克就告訴他們說:「根據蘇聯的經驗,這個橋加固後繼續使用沒有什麽問題。」
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堅决採納了蘇聯專家的意見,責成鄭州鐵路管理局根據運輸發展的需要分期進行加固工程。金戈連克和另一位蘇聯專家西林親自參加指導製訂了頭三期的加固工程計劃。第一期工程僅僅用了十天時間,初步改善了橋面綫路,就使行車速度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到一九五〇年九月完成了第三期加固工程,更使黃河鐵橋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行了大型機車。
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正是第三期加固工程緊張進行的時候,又有一位蘇聯橋樑專家吉赫諾夫親自來到工地,籌劃第四期和第五期的加固工程。那天,吉赫諾夫的臨時辦公室——車廂裏的溫床在華氏一百度以上,吉赫諾夫就坐在那裏從早晨六點鐘一直工作到下午六點,午飯都沒有顧得吃。有人勸他到外邊休息一會、乘乘涼。他說:「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吉赫諾夫詳細了解了黃河鐵橋過去每次被破壞的情形、修復的經過以及每年的黄河水位,仔細聽取了每個曾在黄河鉄橋工作過的工程技術人員的經驗。曾經親眼見過極端驕橫、不負責任的美國專家瓦德爾並曾到美國馬力生公司「實習」過的鄭州鐵路管理局工程師劉鴻鈞感動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專家』眞是沒法比較!」
不久,吉赫諾夫就提出了解决第四、五兩期加固工程(着重加固橋樑下部)中兩個關鍵問題的辦法:打鋼軌樁和做柴排。黃河鉄橋原來的橋樁都是鋼管樁,打樁時是利用管樁下頭螺旋錐的轉動而擰入河底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幾十根鋼管樁連同橋墩等被破壞了,以後就再沒有辦法補充上去。因為自黃河建橋以來,爲了防洪,曾抛落大批片石,在河底結成了一個厚厚的石層。再拿鋼管樁往石層裏擰就擰不進去了。因此,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原來那幾十根鋼管樁被破壞了的地方都是用木樁代替。而木樁不僅力量不如原來的鋼管樁,並且打下去的深度也不如原來的鋼管樁,所以橋的載重能力就大大降低。這是黃河鐵橋長期以來沒法解决的重要問題。吉赫諾夫介紹的打鋼軌樁的辦法是把四根鋼軌鉚到一起,可以打過石層。鋼軌樁和鋼管樁同樣能够支持最大型的機車通過,這就使得整個橋樑的載重力量達到平衡。關於柴排,它是保護橋樁免被洪水冲擊的好辦法。做法是把許多細柳枝連結爲一個平排,上面等距離插許多木棍,木棍之間的空格裏放上石頭。過去黃河鐵橋防洪完全是靠抛石頭。因爲黄河是淤沙底,石頭拋下去後就往下沉,沉了一批再抛一批。據統計,自建橋以來已抛石頭約三十萬公方,每公方石頭的價錢合三四十斤小米,所以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現在用了柴排,可以節省許多石頭。柴排下部的柳綑性軟,容易和河底的泥沙結合在一起,它上面插的許多木棍又把一塊塊石頭固定下來,這樣就不像過去單個抛落的石塊容易被河水冲動,而把橋樁保護得更加牢固了。
打鋼軌樁和做柴排都是蘇聯早已實驗成功的先進經驗,但是黃河鐵橋過去沒有用過,所以開始時鄭州鐵路管理局的許多工程領導人員思想上不樂意接受。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吉赫諾夫又來到黃河鉄橋時,他們還說:「鋼軌那麼細長的東西,能頂住大型機車跑嗎?」吉赫諾夫爲了有效地說服他們接受先進經驗,便親自主持着在黃河灘裏先試打了幾根鋼軌樁,用千斤頂往下壓。然後科學的紀錄擺出來了:每根鋼軌樁能承受一百九十噸左右的壓力,而每個小橋墩有四根樁,大墩有六根樁,計算起來,它們的力量支持最大型的機車通過還綽綽有餘。這樣一來,原來思想很不通的人都非常自然地接受了這個先進經驗,並且工作起來充滿了信心。不久,原來的幾十根木樁就全部換成了鋼軌樁。
用於做柴排的辦法,有一些老工人思想十首先接受了,因爲他們記得五十二年前修建這座橋時曾經用過類似的辦法,但是當時沒人總結,所以失傳了。他們聽到吉赫諾夫介紹的這個辦法比原來那個辦法還好,非常擁護。但是許多工程技術人員對於柴排仍抱懷疑態度。吉赫諾夫考慮到,現場的工作,是這些技術人員直接領導的,必須把他們的思想弄通,工作才能順利進行。因此,他又採取了用實際試驗的辦法,在一九五一年試做了三個柴排,結果效果很好。今年現場便自動做了十個。鄭州鐵路管理局並已把做柴排列為黃河鐵橋今後經常整修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鄭州鐵路管理局工務處負責指導黃河鐵橋加固工程的工程師林暄現在回憶起打鋼軌樁和做柴排的經過,還常常感激地說:「蘇聯專家爲了幫助我們搞好工作,他的耐心眞是出乎尋常!」
一九五一年五月間,黃河鐵橋工地上發生了一個激烈的爭論。當時,第四期加固工程快要完工,第五期工程即將開始。在第五期工程中,要把一百孔舊樑全部換成新鋼樑,並要調整許多橋墩的高度,這些工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浩大而且艱難。當時許多人提出:進行第五期工程,黃河鐵橋需要中斷行車一個月到兩個月。也有人認為這樣作使交通損失太大,但這種意見不佔優勢。正當這時,吉赫諾夫從衡陽鉄路管理局工作回來,和從北京來的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在黃河橋頭會面。呂正操和吉赫諾夫愼重考慮了以上兩種意見的得失,認爲黃河鐵橋如果中斷行車,就使本來北京、鄭州間直達的列車要繞到東邊津浦和隴海綫上去轉一個大彎子,並且勢必造成這兩條綫上列車擁擠的現象,影響全國運輸。他們指出:寧肯把工程時間拖長一些,也必須在每天不間斷行車的條件下進行加固。任務交下來之後,全體職工開動腦筋想辦法,果然克服了重重困難,結果一天車也沒停,順利地完成了第五期加固工程。
吉赫諾夫曾經九次親自到黃河鉄橋工地指導工作。他除奉鉄道部的命令專門爲解决黃河鉄橋工程問題而來以外,每逢他出外工作,不論是到什麼地方去,只要路過黃河鐵橋,他都要下車來看看。每次來,他都找工地領導幹部問問工作中有沒有什麽困難,每次來,他都要上橋看看。他看得非常細心,有許多一般人不注意的缺點都被他及時發現。有一次,一孔連結樑上少上了一個螺絲釘也被他發現了。當他看到一座縱墊樑上有塊「加勁角鉄」沒有上緊,留有一個縫隙,他就建議工程師專門召集工人開會,讓工程師給工人講解「加勁角鉄」有什麽用處,如果上不緊有多大的害處。工人張祿回憶到這件事的時候說:「從那以後,我們在工作中都提高了警惕,克服了馬虎思想。我們自動建立了質量檢查制度,不但要求數量高,而且保證質量好。感謝蘇聯專家幫助我們提高了政治覺悟水平。」工人黃文明說:「想想蘇聯專家對我們的工作比我們自己還關心,我們要不加勁幹,怎配當國家的主人翁呢?」
在蘇聯專家的熱誠幫助下,全體修橋職工發揮了無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黃河鐵橋已經全部加固完成了。在原來破爛不堪的舊橋址上,已經巍然立起一座非常堅固的名符其實的「鋼鐵的橋」。現在這座橋樑的效用完全等於一座新橋。黃河鐵橋加固工程的勝利不只在於爲國家節省了大量資金——全部加固工程費用只等於現在另建一座新橋費用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在爭取了時間,並避免了目前在修建新橋中必然會發生的器材上、技術上的困難。
一向被稱爲京漢綫上的「死疙瘩」,算是被徹底地解開了。黄河鉄橋勝任愉快地担當起了我國南北物資交流樞紐的任務。現在黃河鐵橋上的行車速度已經完全不加限制了。由大型機車牽引的一列列滿載超軸的火車,從橋上飛馳而過。每天,成千上萬的旅客,懷着對蘇聯專家的無私援助無限感激的心情,坐在火車上迅速地通過鐵橋。
京漢鐵路中段,在滾滾東流的黃河上,橫跨着我國第一座大鐵橋——京漢路黃河鐵橋。它把我國華北、中南、西北、華東廣大地區連接起來,是北方和南方物資交流的樞紐。
黃河鐵橋是在五十二年前由法國和比利時的包商承建的。修成時,工程師就把行車速度規定爲最高每小時十五公里。以後,在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時期,黃河鐵橋又受到多次嚴重的破壞,行車速度更是每况愈下。解放前坐車通過黃河鐵橋的人恐怕都還記得那時候的艱難情景:短短二十幾個車廂的列車,要分兩次才能過橋。從黃河南站到北站不到五公里的路程,旅客得在車上熬上三個鐘頭。
那時候,人們都認爲黃河鐵橋像是已經活够了歲數該死的人。無法挽救了。國民黨政府曾經兩次請美國人設計另建新橋。第一次在一九二九年請來了一個名叫瓦德爾的橋樑專家。他只是坐火車從橋上過了一趟,連車都未下。自然談不到作任何勘察工作,就派他的助手魏爾工程師來試打新橋樁了。這位魏爾工程師在黃河岸邊住了將近一月,一根普通的木樁打進土裏不過十公尺,比起老橋樁的入土深度還淺得多。現在坐車過橋的人還可以看見橋南頭東邊一百公尺處河水裏的那根樁子,就是美國專家的可憐的紀念物。一九四六年,國民黨政府又請美國馬力生公司設計新橋,花了十萬元美金的設計費,並從國內派了一批工程師去實習。鄭州鉄路局的工程師劉鴻鈞就是其中的一個。據劉鴻鈞說,他們那次滿懷希望而去,却大失所望而歸,因爲美國資本家並沒有眞心幫助中國進行建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蘇聯橋樑專家金戈連克等來到了黃河橋上。金戈連克已經是禿頂、白髮的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他懷着援助我國進行經濟建設的國際主義精神與滿腔熱忱,不顧嚴冬的寒風,從橋這頭到那頭,爬上爬下對各部分進行了詳細檢查。他拿着鐵錘敲聽了許多節鋼樑以辨認鋼的應力,化驗了鋼質。然後,他在鄭州鐵路管理局召開的一次工程會議上,提出了黃河鐵橋應該進行加固改善的意見。金戈連克說:目前中國正處在經濟恢復時期,應使一切生產設備充分發揮効用,並努力節約。他根據實地勘察與科學計算指出:黃河鉄橋進行加固改善之後,完全可以改變運輸狀况。當時,許多解放前就在鄭州局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聽了並不相信。他們想:「美國專家來了都沒辦法,也是說要另建新橋………」金戈連克就告訴他們說:「根據蘇聯的經驗,這個橋加固後繼續使用沒有什麽問題。」
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堅决採納了蘇聯專家的意見,責成鄭州鐵路管理局根據運輸發展的需要分期進行加固工程。金戈連克和另一位蘇聯專家西林親自參加指導製訂了頭三期的加固工程計劃。第一期工程僅僅用了十天時間,初步改善了橋面綫路,就使行車速度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到一九五〇年九月完成了第三期加固工程,更使黃河鐵橋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行了大型機車。
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正是第三期加固工程緊張進行的時候,又有一位蘇聯橋樑專家吉赫諾夫親自來到工地,籌劃第四期和第五期的加固工程。那天,吉赫諾夫的臨時辦公室——車廂裏的溫床在華氏一百度以上,吉赫諾夫就坐在那裏從早晨六點鐘一直工作到下午六點,午飯都沒有顧得吃。有人勸他到外邊休息一會、乘乘涼。他說:「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吉赫諾夫詳細了解了黃河鐵橋過去每次被破壞的情形、修復的經過以及每年的黄河水位,仔細聽取了每個曾在黄河鉄橋工作過的工程技術人員的經驗。曾經親眼見過極端驕橫、不負責任的美國專家瓦德爾並曾到美國馬力生公司「實習」過的鄭州鐵路管理局工程師劉鴻鈞感動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專家』眞是沒法比較!」
不久,吉赫諾夫就提出了解决第四、五兩期加固工程(着重加固橋樑下部)中兩個關鍵問題的辦法:打鋼軌樁和做柴排。黃河鉄橋原來的橋樁都是鋼管樁,打樁時是利用管樁下頭螺旋錐的轉動而擰入河底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幾十根鋼管樁連同橋墩等被破壞了,以後就再沒有辦法補充上去。因為自黃河建橋以來,爲了防洪,曾抛落大批片石,在河底結成了一個厚厚的石層。再拿鋼管樁往石層裏擰就擰不進去了。因此,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原來那幾十根鋼管樁被破壞了的地方都是用木樁代替。而木樁不僅力量不如原來的鋼管樁,並且打下去的深度也不如原來的鋼管樁,所以橋的載重能力就大大降低。這是黃河鐵橋長期以來沒法解决的重要問題。吉赫諾夫介紹的打鋼軌樁的辦法是把四根鋼軌鉚到一起,可以打過石層。鋼軌樁和鋼管樁同樣能够支持最大型的機車通過,這就使得整個橋樑的載重力量達到平衡。關於柴排,它是保護橋樁免被洪水冲擊的好辦法。做法是把許多細柳枝連結爲一個平排,上面等距離插許多木棍,木棍之間的空格裏放上石頭。過去黃河鐵橋防洪完全是靠抛石頭。因爲黄河是淤沙底,石頭拋下去後就往下沉,沉了一批再抛一批。據統計,自建橋以來已抛石頭約三十萬公方,每公方石頭的價錢合三四十斤小米,所以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現在用了柴排,可以節省許多石頭。柴排下部的柳綑性軟,容易和河底的泥沙結合在一起,它上面插的許多木棍又把一塊塊石頭固定下來,這樣就不像過去單個抛落的石塊容易被河水冲動,而把橋樁保護得更加牢固了。
打鋼軌樁和做柴排都是蘇聯早已實驗成功的先進經驗,但是黃河鐵橋過去沒有用過,所以開始時鄭州鐵路管理局的許多工程領導人員思想上不樂意接受。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吉赫諾夫又來到黃河鉄橋時,他們還說:「鋼軌那麼細長的東西,能頂住大型機車跑嗎?」吉赫諾夫爲了有效地說服他們接受先進經驗,便親自主持着在黃河灘裏先試打了幾根鋼軌樁,用千斤頂往下壓。然後科學的紀錄擺出來了:每根鋼軌樁能承受一百九十噸左右的壓力,而每個小橋墩有四根樁,大墩有六根樁,計算起來,它們的力量支持最大型的機車通過還綽綽有餘。這樣一來,原來思想很不通的人都非常自然地接受了這個先進經驗,並且工作起來充滿了信心。不久,原來的幾十根木樁就全部換成了鋼軌樁。
用於做柴排的辦法,有一些老工人思想十首先接受了,因爲他們記得五十二年前修建這座橋時曾經用過類似的辦法,但是當時沒人總結,所以失傳了。他們聽到吉赫諾夫介紹的這個辦法比原來那個辦法還好,非常擁護。但是許多工程技術人員對於柴排仍抱懷疑態度。吉赫諾夫考慮到,現場的工作,是這些技術人員直接領導的,必須把他們的思想弄通,工作才能順利進行。因此,他又採取了用實際試驗的辦法,在一九五一年試做了三個柴排,結果效果很好。今年現場便自動做了十個。鄭州鐵路管理局並已把做柴排列為黃河鐵橋今後經常整修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鄭州鐵路管理局工務處負責指導黃河鐵橋加固工程的工程師林暄現在回憶起打鋼軌樁和做柴排的經過,還常常感激地說:「蘇聯專家爲了幫助我們搞好工作,他的耐心眞是出乎尋常!」
一九五一年五月間,黃河鐵橋工地上發生了一個激烈的爭論。當時,第四期加固工程快要完工,第五期工程即將開始。在第五期工程中,要把一百孔舊樑全部換成新鋼樑,並要調整許多橋墩的高度,這些工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浩大而且艱難。當時許多人提出:進行第五期工程,黃河鐵橋需要中斷行車一個月到兩個月。也有人認為這樣作使交通損失太大,但這種意見不佔優勢。正當這時,吉赫諾夫從衡陽鉄路管理局工作回來,和從北京來的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在黃河橋頭會面。呂正操和吉赫諾夫愼重考慮了以上兩種意見的得失,認爲黃河鐵橋如果中斷行車,就使本來北京、鄭州間直達的列車要繞到東邊津浦和隴海綫上去轉一個大彎子,並且勢必造成這兩條綫上列車擁擠的現象,影響全國運輸。他們指出:寧肯把工程時間拖長一些,也必須在每天不間斷行車的條件下進行加固。任務交下來之後,全體職工開動腦筋想辦法,果然克服了重重困難,結果一天車也沒停,順利地完成了第五期加固工程。
吉赫諾夫曾經九次親自到黃河鉄橋工地指導工作。他除奉鉄道部的命令專門爲解决黃河鉄橋工程問題而來以外,每逢他出外工作,不論是到什麼地方去,只要路過黃河鐵橋,他都要下車來看看。每次來,他都找工地領導幹部問問工作中有沒有什麽困難,每次來,他都要上橋看看。他看得非常細心,有許多一般人不注意的缺點都被他及時發現。有一次,一孔連結樑上少上了一個螺絲釘也被他發現了。當他看到一座縱墊樑上有塊「加勁角鉄」沒有上緊,留有一個縫隙,他就建議工程師專門召集工人開會,讓工程師給工人講解「加勁角鉄」有什麽用處,如果上不緊有多大的害處。工人張祿回憶到這件事的時候說:「從那以後,我們在工作中都提高了警惕,克服了馬虎思想。我們自動建立了質量檢查制度,不但要求數量高,而且保證質量好。感謝蘇聯專家幫助我們提高了政治覺悟水平。」工人黃文明說:「想想蘇聯專家對我們的工作比我們自己還關心,我們要不加勁幹,怎配當國家的主人翁呢?」
在蘇聯專家的熱誠幫助下,全體修橋職工發揮了無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黃河鐵橋已經全部加固完成了。在原來破爛不堪的舊橋址上,已經巍然立起一座非常堅固的名符其實的「鋼鐵的橋」。現在這座橋樑的效用完全等於一座新橋。黃河鐵橋加固工程的勝利不只在於爲國家節省了大量資金——全部加固工程費用只等於現在另建一座新橋費用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在爭取了時間,並避免了目前在修建新橋中必然會發生的器材上、技術上的困難。
一向被稱爲京漢綫上的「死疙瘩」,算是被徹底地解開了。黄河鉄橋勝任愉快地担當起了我國南北物資交流樞紐的任務。現在黃河鐵橋上的行車速度已經完全不加限制了。由大型機車牽引的一列列滿載超軸的火車,從橋上飛馳而過。每天,成千上萬的旅客,懷着對蘇聯專家的無私援助無限感激的心情,坐在火車上迅速地通過鐵橋。
相关机构
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蘇聯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