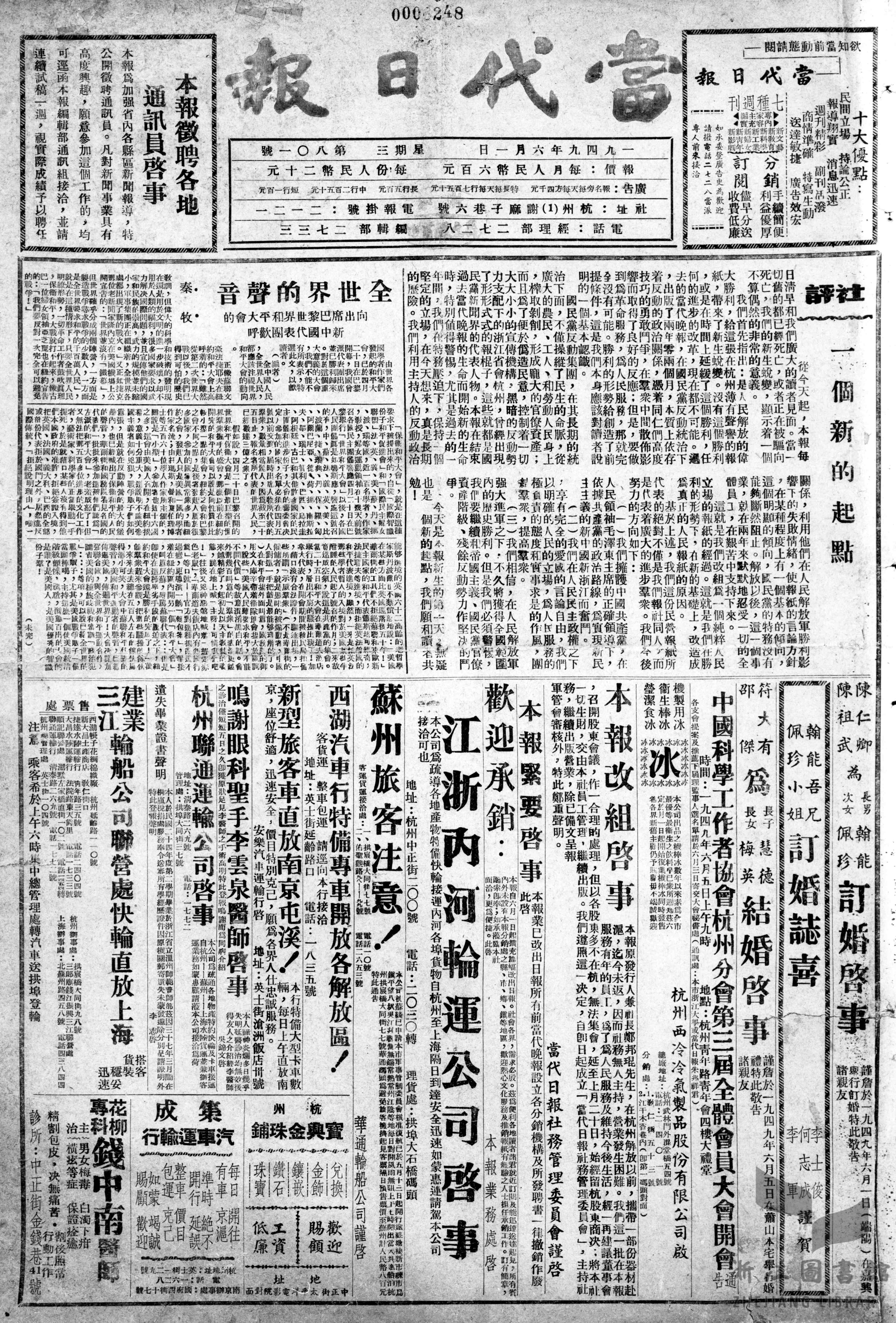内容
答A·H·諾特京同志諾特京同志!
我沒有急於囘信,因為你所提出的問題,我認爲並不是緊急的。加之還有別的帶緊急性的問題,自然,就把對你的來信的注意力轉移了。
我來逐點囘答。
關於第一點。
在我的「意見」中有一個大家知道的原理:社會在科學法則面前並不是無能爲力的,人們認識了經濟法則,就能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你斷定說,這一原理不能適用於其他社會形態,它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有效,比方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過程的自發性質,就不會使社會有可能利用經濟法則來為社會謀福利。
這是不對的。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例如,在法國,資產階級就曾利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大家知道的法則來反對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新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並且使這種生產關係和在封建制度內部生長起來的生產力的性質相適合。資產階級做到了這件事,並不是由於它的特殊本領,而是因爲它對於這件事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封建主反抗這件事,並不是由於他們的愚鈍,而是由於他們有切身的利害關係,要來阻撓這一法則的實現。
關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應該這樣說。工人階級利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並且使這種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性質相適合。工人階級能够做到了這件事,並不是由於它的特殊本領,而是因爲它對於這件事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已從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的先進力量變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資產階級,曾經竭力反抗這一法則的實現,——它之所以反抗,並不是由於它沒有組織性,也不是因爲經濟過程的自發性質推動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於它有切身的利害關係,要來反對這一法則的實現。
由此可見:
一、在某種程度內利用經濟過程、經濟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這樣的事情也不僅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發生,而且在其他社會形態下也發生。
二、在階級社會裡利用經濟法則無論何時何地都有階級背景,而且利用經濟法則爲社會謀福利的旗手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先進階級,而衰朽的階級則反抗這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無產階級與其他曾在歷史上完成過生產關係變革的階級間的差別就在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和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是消滅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剝削,而是消滅任何剝削;至於其他階級的革命,却只是消滅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剝削,而爲它們與社會絕大多數人利益相矛盾的狹隘階級利益所限制。
在「意見」中說到利用經濟法則為社會謀福利這件事的階級背景。那裡說:「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和應用新的法則是或多或少順利地進行的;與此相反,在經濟學領域中,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則,却要遇到這些力量極强烈的反抗。」但是你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關於第二點。
你斷定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達到使生產關係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而在其他社會形態下,只能實現不完全的適合。
這是不對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當資產階級破壞了封建的生產關係、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的時代,無疑地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否則,資本主義就不會像它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那樣迅速地發展了。
其次,「完全適合」這種說法是不能在絕對的意義上來理解的。不能把這種說法理解爲彷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决沒有生產關係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的現象。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無可爭辯地是走在生產關係前面的。生產關係只是經過一些時候,才會被改造得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
那末,「完全適合」這種說法該怎樣來理解呢?應該理解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後了的生產關係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做到這點,是因爲在這社會的成份中沒有那些能够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當然,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有落後的惰性的力量,它們不了解生產關係有改變的必要,但是這種力量,當然不難克服,而不致把事情弄到衝突的地步。
關於第三點。
從你的議論中可以看出,你把我們國有化企業所生產的生產資料,首先是生產工具,看做是商品。
可不可以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資料看做是商品呢?據我看來,無論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這樣的一種產品,它可以出售給任何買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後,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對商品的所有權,而買主則變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轉售、抵押或讓它腐爛。生產資料是否適合於這個定義呢?顯然,是不適合的。第一,生產資料並不「出售」給任何買主,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而只是由國家分配給自己的企業。第二,生產資料所有者——國家,在把生產資料交給某一個企業時,絲毫不失去對它們的所有權,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權的。第三,企業的經理,從國家手中取得了生產資料之後,不但不變成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確認爲受蘇維埃國家的委任,依照國家所交下的計劃,來使用這些生產資料的。
由此可見,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國制度下的生產資料列入商品範疇中。
那末,爲什麽又講生產資料的價值,講它們的成本,講它們的價格等等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這是爲了估價、爲了核算、爲了計算企業的盈虧、爲了檢查和監督企業所必需的。但這只是事情的形式的一面。
第二,這是爲了在對外貿易上便於把生產資料出售給外國所必需的。這裡,在對外貿易領域內,並且僅僅是在這個領域內,我們的生產資料才確實是商品,才確實被出售(不是加引號的出售)。
這樣看來,在對外貿易流通領域內,我國企業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無論在實質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特性,可是在國內經濟流通領域內,生產資料却失去商品的特性,不再是商品,並且超出價値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之外,僅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估價等等)。
這種特殊情况究竟怎樣解釋呢?
問題在於: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並不是以變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漸改變的方式進行的,舊的東西並不是簡單地被廢除乾淨,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變得與新的東西相適應,僅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於新的東西也不是簡單地消滅舊的東西、而是滲到舊的東西裡面去,改變舊東西的本性和機能,並不破壞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來發展新的東西。在我國的經濟流通中,不僅商品是這樣,而且貨幣也是這樣,連銀行也是這樣,銀行失去自己舊的機能並取得了新的機能,同時保持着舊的形式而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利用。
如果從形式上的觀點,從現象表面過程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就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彷佛資本主義的範疇在我國經濟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看待問題,即把經濟過程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把深處的發展過程和表面現象嚴格地區別開來,那就可以得出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即資本主義的舊範疇在我國保留下來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實質上這些範疇在我國已經根本改變得與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相適合了。
關於第四點。
你斷定說,價値法則對於在農業中所出產的、依照採購價格出售給國家的「生產資料」的價格,發生着調節的影響。你在這裡所指的是例如棉花這種原料的「生產資料」。在這裡你還可以再加上亞麻、羊毛及其他農業原料。
應該首先指出,在這種情形下,農業所生產的並不是「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產資料」這個術語。當馬克思主義者說生產資料的生產時,首先是指生產工具的生產,——馬克思把這叫做「機械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爲生產的骨骼和筋肉的系統」,這個系統組成「社會生產一定時代的作為特徵的標誌」。把一部分生產資料(原料)和包括生產工具的整個生產資料等量齊觀,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因爲馬克思主義認爲,和其他一切生產資料來比,生產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誰都知道,原料本身不能生產生產工具,雖然某幾種原料也是生產生產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沒有生產工具是不能生產任何原料的。
其次,價値法則對農業中所生產的原料的價格的影響,是否像你諾特京同志所斷言的那樣,是具有調節作用的呢?如果我國存在着農業原料價格的「自由」漲跌,如果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在我國發生作用,如果我國沒有計劃經濟,如果原料的生產不是由計劃來調節的,那末,價値法則的影響就會是有調節作用的了。但是,因為在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並沒有這些「如果」,所以價値法則對於農業原料價格的影響無論如何不會是有調節作用的。第一,我國農業原料的價格是固定的,由計劃規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農業原料的生產規模並不是由自發的力量、不是由什麽偶然的因素來决定,而是由計劃來决定的。第三,爲生產農業原料所必需的生產工具,不是集中在個別人或個別集團手中,而是集中在國家手中。既然這樣,還有什麽價値法則的調節作用呢?結果,價值法則本身也是由社會主義生產所特有的上述事實來調節的。
因此,不能否認,價值法則是影響農業原料價格的形成的,它是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認,這種影響並不起調節作用,也不可能起調節作用。
關於第五點。
說到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贏利,我在「意見」中曾反駁某些同志,這些同志肯定說,既然我國計劃性的國民經濟不大重視贏利的企業,並且容許不贏利的企業也和這些企業並存,彷彿計劃性的國民經濟抹煞經濟中的贏利性這個原則本身。在「意見」中說,個別企業□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是决不能和社會主義生產所給予我們的那個高級形式的贏利相比的,因爲社會主義生產使我們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並保證我們的生產不斷提高。
但是,如果從此得出結論說,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是沒有特別價值的,所以不値得加以重視,那就不對了。這當然是不對的。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從發展我國生產的觀點來說,是有巨大意義的。無論在計劃建設或計劃生產時,這都是應該注意到的。這是我國現今發展階段上經濟活動方面的起碼知識。
關於第六點。
不知道應該怎樣了解你這個關於資本主義的說法:「形式大大改變了的擴大的生產」。應該說,這樣的而且還是擴大的生產,是世界—所沒有的。
顯然,在世界市場已經分裂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攫取世界資源的範圍開始縮小了的時候,資本主義發展的循環性質——生產的增長和減縮——一定還會存在。不過,這些國家生產的增長將在縮小的基礎上進行,因爲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將要減縮。
關於第七點。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蘇聯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開始的。這是總危機的第一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的各人民民主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展開了總危機的第二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第一次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第二次危機,應該看做不是個別的、彼此隔離的獨立危機,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發展的兩個階段。
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否僅僅是政治的或僅僅是經濟的危機呢?旣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旣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總的卽全面的危機。同時也就很清楚,這種危機的基礎,一方面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瓦解現象日益加劇,另一方面是脫離資本主義的各國——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實力日益增長。
約·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關於□·□·雅羅申柯同志的錯誤
今年三月二十日,雅羅申柯同志寫了一封信分送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說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討論會上所討論過的幾個經濟問題。他在這封信中申訴說,在討論會的一些總結性的主要文件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的「意見」中,雅羅中柯同志的「觀點沒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在這封短信中還有雅羅申柯同志的建議:請准許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內編寫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並給他兩個助手來作這一工作。
我以爲,必須從本質上來考察雅羅申柯同志的申訴和他的建議。
我們先從他的申訴開始。
究竟在上述文件中沒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羅中柯同志的「觀點」,是什麽呢?
一、雅羅申柯同志的主要錯誤
如果用一兩句話來評定雅羅申柯同志的觀點,那就應該說,他的觀點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因而是極端錯誤的。
雅羅中柯同志的主要錯誤是,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過分誇大了生產力的作用,同樣也就過分縮小了生產關係的作用,竟至宣佈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的一部分。
雅羅申柯同志同意承認生產關係在「對抗的階級矛盾」條件下有某種作用,因爲在那裡,生產關係「是與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這種作用限制爲消極的作用,限制爲阻礙生產力發展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的作用。生產關係的其他機能、任何積極的機能,雅羅中柯同志是沒有看到的。
至於說到已經沒有「對抗的階級矛盾」而且生產關係「再也不與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社會主義制度時,雅羅申柯同志便認爲,在這裡,生產關係的任何獨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產關係不再是發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產力所吞沒,猶如部分被整體吞沒一樣。雅羅申柯同志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的生產關系包括在生產力的組織中,作為這種組織的一個手段、一個成分。」(見雅羅申柯同志給中央政治局的信)
這樣一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又是什麽呢?雅羅中柯同志囘答說:「所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不在於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生產關係,而在於制定和發揮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組織的科學理論、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化的理論。」(見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 這的確也就說明,雅羅申柯同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這些經濟問題,如我國經濟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等,並不感到興趣,認爲這都只能引起煩瑣學派式的爭論的次要問題。他公然宣稱,在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某些範疇——價値、商品、貨幣、信貸等等——的作用的爭論,卽在我國常常帶着煩瑣學派式的性質的爭論,將用關於社會生產中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健全議論以及這種組織的科學論證來代替。」(見雅羅申柯同志在分組討論會上的講話)
這樣,就是沒有經濟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了。
雅羅申柯同志以爲,只要安排好「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難地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了。他認爲,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已經十分够了。他公然宣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爭取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鬥爭,是歸結爲在社會生產中正確組織生產力和合理使用生產力的鬥爭。」(見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雅羅中柯同志鄭重宣稱:「共產主義——這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
這樣,「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就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了。
雅羅申柯同志從這一切便作出結論說,對於一切社會形態,不可能有統一的政治經濟學,而應該有兩種政治經濟學:一種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以前各種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其對象是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另一種是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其對象應當不是研究生產關係卽經濟關係,而是研究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
雅羅中柯同志的觀點就是這樣。
對於這種觀點可以講些什麽呢?
第一,說生產關係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只限於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這是不對的。當馬克思主義者講到生產關係的阻礙作用時,他們所指的並不是任何生產關係,而只是已經不能適合生產力發展、因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係。但是,除了舊生產關係以外,大家知道,還有代替舊生產關係的新生產關係。可不可以說,新生產關係的作用歸結為阻礙生產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產關係是這樣一種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它眞正决定生產力進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發展,沒有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就注定要萎靡下去,如像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一樣。
誰也不能否認,我們蘇聯工業的生產力在幾個五年計劃中,有巨大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用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沒有我國生產關係卽經濟關係中的這種變革,我國的生產力就會萎靡下去,如像它現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萎靡的情形一樣。
誰也不能否認,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在最近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中,有巨大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在三十年代沒有用新的集體化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農村中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沒有這種生產的變革,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就會萎靡下去,如像它現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萎靡的情形一樣。
當然,新的生產關係不能永遠是新的,而且也不永遠是新的,它開始變舊,並與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而開始失去其爲生產力的主要推進者的作用,並變成生產力的阻礙者。那時候,就出現新生產關係來代替這種已經變舊了的生產關係,新生產關係的作用就是充當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推進者。
生產關係從生產力阻礙者的作用發展到生產力主要推進者的作用,以及從生產力主要推進者的作用發展到生產力阻礙者的作用,——這樣一種發展的特性,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是現在一切初學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的。原來雅羅申柯同志却不知道這一點。
第二,說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的獨立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在消失,說生產關係是在被生產力吞沒着,說社會生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歸結爲生產力的組織,這是不對的。馬克思主義是把社會生產看作一個整體,它具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社會生產力(社會對自然力的關係,社會在與自然力作鬥爭中來取得必要的物質資料)和生產關係(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這是社會生產的兩個不同的方面,雖然它們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繫着的。正因為它們是社會生產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所以它們能够互相影響。硬說這兩個方面中有一個可以被另一個吞沒而變成它的組成部分,就是極嚴重地違反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聯合起來進行共同活動並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便不能從事生產。爲了從事生產,人們就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而且只有通過這些社會聯系和關係,才有人們對自然的關係,才有生產。」(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可見,社會生產是由兩個方面組成,這兩個方面雖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系着,但却反映兩種不同的關係,即人們對自然的關係(生產力)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生產關係)。只有具備生產的這兩方面,才能有社會生產,——不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或其他社會形態下都是一樣。
大概,雅羅申柯同志是不十分同意馬克思的。他認為馬克思的這個原理是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歸結為合理組織生產力的問題,而拋開了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並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脫節。
這樣,在雅羅申柯同志那裡,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波格丹諾夫的「普遍組織科學」之類的東西了。
這樣,雅羅申柯同志在採納了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力量這個正確思想以後,却把這個思想弄到了荒謬的地步,竟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卽經濟關係的作用;而且,本來是生氣蓬勃的社會生產,他却弄成了片面的和空洞的生產工藝學,卽布哈林的「社會組織技術」之類的東西了。
馬克思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卽在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中——斯大林註),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要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則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藉以建立起來,而且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這就是說,每個社會形態,連社會主義社會也在內,都有自己的由人們生產關係的總和所構成的經濟基礎。於是發生一個問題:在雅羅申柯同志那裡,究竟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怎樣的呢?大家知道,雅羅中柯同志已經消滅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這個多少帶獨立性的領域,而把生產關係剩下的一點殘餘歸併到生產力組織之內。試問,社會主義制度有沒有它自己的經濟基礎呢?看起來,旣然生產關係這一多少獨立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消失,那末社會主義制度只好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了。
這樣,就是沒有自己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相當可笑的事情……
一般講來,沒有自己經濟基礎的社會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大槪,雅羅申柯同志認爲是可能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却認爲,這樣的社會制度在世界上是沒有的。
最後,說共產主義是生產力的合理組織,說生產力的合理組織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了,說只要合理地組織生產力,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難地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不對的。在我國的文獻中,有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定義、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公式、卽列甯的公式:「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看起來,雅羅中柯同志不喜歡列甯的公式,於是用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產主義——這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來代替列甯的公式。
第一,誰也不明白,雅羅申柯同志所吹噓的這個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或「合理」組織是什麼?這組織的具體內容是什麽?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和分組討論會上的講話中,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幾十次重複這個神話般的公式,然而他無論在那一個地方,都沒有試圖用片言隻字來說明這個彷彿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的生產力的「合理組織」,究竟應該怎樣來了解。
第二,如果對這兩個公式加以選擇的話,那末應該拋棄的,就不是唯一正確的列甯的公式,而是雅羅中柯同志的所謂公式,他這公式顯然是臆造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是從波格丹諾夫的武器庫——「普遍組織科學」中拿來的東西。
雅羅申柯同志以爲,只要做到合理地組織生產力,就能獲得豐富的產品並過渡到共產主義,就能從「按勞取酬」的公式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這是大錯特錯的,這暴露了他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法則一竅不通。雅羅中柯同志過於簡單地、小孩般簡單地想像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雅羅申柯同志不了解,如果讓集體農莊集團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經濟事實仍然存在,那就旣不能獲得能滿足社會一切需要的豐富產品,也不能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雅羅申柯同志不了解:在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前,社會必須經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造和文化改造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勞動將在社會成員面前從僅僅維持生活的手段變成爲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將變成爲社會存在的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基礎。
爲了準備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宣言上過渡到共產主義,至少必須實現三個基本的先决條件。
第一,必須切實加以保證的,不是神話般的生產力的「合理組織」,而是全部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而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佔優先地位。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之所以必須佔優先地位,不僅是因爲這種生產應當保證自己的企業以及國民經濟其他一切部門的企業所需要的裝備,而且是因爲沒有這種生產就根本不可能實現擴大再生產。
第二,必須用實行起來有利於集體農莊因而也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逐漸過渡的辦法,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並且也用逐漸過渡的辦法使產品交換制來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權或其他某個社會經濟中心能够爲了社會福利來掌握社會生產的全部產品。
雅羅申柯同志斷定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沒有任何矛盾。這是錯誤的。當然,我國現今的生產關係是處在這樣一個時期,它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增長,一日千里地把生產力向前推進。但是,如果以此自滿,以爲在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確了。因爲生產關係的發展是落後於並且將來也會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在領導機關的正確政策下,這些矛盾就不會變對立,而這樣也就不會弄到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如果我們執行類似雅羅申柯同志所推薦的不正確的政策,那就會是另一種情形了。在這種場合下,衝突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的生產關係可能變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極嚴重的阻礙者。
因此,領導機關的任務在於及時地看出日益增長的矛盾,並及時地採取辦法,使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的增長,來克服這種矛盾。這首先是與集體農莊集團所有制、商品流通這種經濟現象有關的。當然,目前這些現象是在被我們有成效地利用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而且它們也在給我國社會帶來毫無疑問的利益。無疑地,它們在最近的將來也將帶來利益。但同時這些現象已在開始阻礙我國生產力的强大發展,因爲它們正在阻礙這種由國家計劃化來完全包括全部國民經濟、特別是包括農業的事業,如果看不出這點,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這些現象就會愈加阻礙我國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所以,任務就在於要逐漸把集體農莊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以及也是逐漸用產品交換制代替商品流通,這樣來消滅這些矛盾。
第三,必須使社會達到這樣高度的文化發展,保證社會一切成員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使社會成員能獲得足以成爲社會發展的積極活動家的敎育,能自由地選擇職業,而不致由於現存的勞動分工而終身束縛於某一種職業。
為了做到這點,究竟需要什麽呢?
如果認爲用不着大大改變現今的勞動狀況,便可以達到社會成員的這種强大的文化高漲,那就不正確了。爲了做到這點,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勞動時間至少縮短到六小時,然後再縮短到五小時。這是使社會成員有充分的自由時間來獲得全面敎育所必需的。其次,爲了做到這點,需要實行普及義務的綜合技術敎育,這是使社會成員有可能自由選擇職業而不致終身束縛於某一種職業所必需的。再次,為了做到這點,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條件,把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至少提高一倍,也許還要更多,辦法是不僅直接提高貨幣工資,而且特別重要的,是繼續不斷地降低日用品價格。
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就是這樣。
只有把這一切先決條件全部實現之後,才可以希望,勞動將在社會成員面前,從累贅變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馬克思),「勞動從沉重的負担變成愉快」(恩格斯),公有制將被社會全體成員看作是社會存在的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基礎。
只有把這一切先决條件全部實現之後,才可以從社會主義的公式「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公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將是從一種經濟卽社會主義經濟到另一種更高的經濟即共產主義經濟的根本過渡。
可見,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事業,並不像雅羅申柯同志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企圖把這全部複雜的和多樣性的事業、需要有極重大經濟變更的事業歸結爲「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像雅羅中柯同志所做的那樣,就等於以波格丹諾夫謬論來偷換馬克思主義。
二、雅羅申柯同志的其他錯誤
一、雅羅申柯同志從自己不正確的觀點出發,作出了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對象的不正確的結論。
雅羅申柯同志認爲每一社會形態有它自己的獨特的經濟法則。他從這點出發,就否認有論述一切社會形態的統一的政治經濟學的必要。但他是完全不對的,他在這裡是與恩格斯、列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背道而馳了。
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各種不同社會中藉以進行生產和交換,及與此相適應,藉以經常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反杜林論」)。因此,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種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法則,而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法則。
大家知道,列甯是十分同意這點的,他在批判布哈林的小冊子「過渡時期的經濟」時說,布哈林把政治經濟學的作用範圍局限於商品生產,首先是局限於資本主義生產,這是不對的;他同時指出,在這裡,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後退了一步」。
政治經濟學敎科書未定稿中所提供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是與此十分符合的。在這未定稿中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法則」的科學。
這是很明白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在它的經濟發展中,不僅服從自己特有的經濟法則,而且還服從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法則,例如,在單一的社會生產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的法則,在一切社會形態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關係法則。所以,各個社會形態不僅以自己特有的法則互相分開着,而且以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法則互相聯繫着。
恩格斯說得完全對:「要全面地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這個批判,只認識生產、交換和分配的資本主義形式是不够的。還必須——那怕是大體上——研究和比較資本主義形式以前的各種形式或較爲不發達的國家中與資本主義形式並存的各種式。」(「反杜林論」)
看起來,在這裡,在這個問題上,雅羅中柯同志是與布哈林互相呼應起來了。
其次,雅羅申柯同志斷定說:在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政治經濟學的各個範疇——價値、商品、貨幣、信貸等等——將用關於社會生產中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健全議論來代替」;因而這種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不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是「制定和發揮生產力組織的科學理論、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理論等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喪失着自己獨立的作用,並被生產力吞沒着而成爲它的組成部分。
(下轉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必須說,在我們這裡還沒有一個發了瘋的「馬克思主義者」講過這種胡說八道的話。要知道,沒有經濟問題卽生產問題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什麽意思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嗎?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用生產力組織問題來代替經濟問題,這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雅羅申柯同志正好是這樣作的,——他在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裡,他是與布哈林完全結合起來了。布哈林說過,資本主義消滅時,政治經濟學也必定隨着消滅。雅羅申柯同志沒有這樣說,却是這樣作,作這種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事情。誠然,他同時裝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樣子,但這是詭計,而且是不值一文的詭計。事實上,他作的就是布哈林所鼓吹而爲列甯所反對的這件事。雅羅申柯同志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羅申柯同志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歸結爲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歸結爲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問題等等。但是他大錯特錯了。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問題等等,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而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這是兩種不同的領域,不能混爲一談。雅羅申柯同志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法則。經濟政策是由此作出實際結論,把它們具體化,在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經濟政策的問題堆壓在政治經濟學上,就是戕害這門科學。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這裡包括:(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丙)完全以生產關係爲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這個定義中缺少恩格斯定義內的「交換」這個術語。其所以缺少,是因爲「交換」通常被許多人了解爲不是一切社會形態而只是某些社會形態所特有的商品交換,這有時候就會引起誤會,雖然恩格斯所說的「交換」這個術語不僅是指商品交換。但是,恩格斯用「交換」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顯然已包含在上述定義中,作爲其組成部分。因而,就其內容講來,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這個定義是與恩格斯的定義完全相符合的。
二、當人們談到某一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法則時,他們通常是從下列這點出發的:社會形態不能有幾個基本經濟法則,它只能有某一個基本經濟法則來作爲基本法則。要不然的話,每個社會形態就會有幾個基本經濟法則,這就與基本法則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然而,雅羅申柯同志並不同意這點。他認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可以不是一個,而是幾個。這是難於相信的,但這是事實。他在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中說:
「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總量的多少和對比,是由被吸引到社會生產中的勞動力增長的事實和前途來决定的。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法則,它制約着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結構。」
這是他的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基本經濟法則。
雅羅中柯同志在同一講話中宣稱:
「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對比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由生產資料生產的需要所制約的,這種生產的規模是由被吸引到社會生產中的一切能勞動的人口的多少來决定。這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同時這是我國憲法從蘇聯人的勞動權引伸出的要求。」
這是所謂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基本經濟法則。
最後,雅羅申柯同志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宣稱:
「從這點出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特點和要求,在我看來,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生產之不斷增長和日益完善。」
這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第三個基本經濟法則了。
這一切法則都□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呢,或者僅僅它們中間的一個才是呢?如果是它們中間的一個,那末究竟是那一個呢?對於這些問題,雅羅中柯同志在最後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並沒有給予囘答。他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表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時,想必他「忘記了」在三個月前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中他已經表述過社會主義的其他兩個基本經濟法則,大概他以爲別人不會注意這個很不高明的手法。但他的打算顯然是落空了。
我們就假定,雅羅中柯同志所表述的前兩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羅申柯同志現在認為在他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所述明的第三個公式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我們來看一看雅羅申柯同志的這封信吧。
雅羅申柯同志在這封信中說,他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在「意見」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定義。他說:
「在這個定義中主要的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在這裡,表明生產是達到這個主要目的、卽滿足需要的手段。這個定義使人有根據認為,你所表述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不是從生產佔首要地位出發,而是從消費佔首要地位出發。」
顯然,雅羅申柯同志完全沒有了解問題的本質,並且看不見,消費或者是生產佔首要地位的議論是與問題無關的。當人們講到某種社會過程對其他過程佔首要地位時,他們的出發點通常是:這兩種過程多少是同一類的。可以而且必須說,生產資料的生產對消費資料的生產佔首要地位,因爲在這兩種場合下,我們所說的都是生產,因而它們多少是同一類的。但决不能說消費對生產佔首要地位或生產對消費佔首要地位,如果這樣說,那就是不正確的。因爲生產和消費是兩個全不相同的領域,誠然,這是兩個互相聯系着、但畢竟各不相同的領域。雅羅中柯同志顯然不了解,這裡所說的不是消費或生產佔首要地位,而是社會給社會生產定出什麽目的,它使社會生產——比方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服從於什麽任務。因此,雅羅申柯同志關於「生產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基礎,猶如是其他任何社會的生活基礎一樣」的說法,也是與問題完全無關的。雅羅中柯同志忘記了,人們不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是爲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他忘記了,跟滿足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
可不可以一般地講社會主義生產或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一般地講資本主義生產或社會主義生產所服從的任務呢?我以為是可以而且應當的。
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生產商品,而是生產剩餘價値或在發展形式下的利潤,不是生產產品,而是生產剩餘產品。從這個觀點看來,勞動本身只是在它給資本創造利潤或剩餘產品的情形下,才是生產的勞動。只要工人不創造這種東西,他的勞動就是不生產的勞動。因而,被使用的生產勞動量,只是在由於有這勞動量——或相當於這勞動量——而剩餘勞動量得以增長的情形下,才使資本感到興趣;只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叫做必要的勞動時間才是必要的東西。只要勞動不產生這樣的成果,那它就是多餘的,就是應當被停止的。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始終是以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來創造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値或最大限度的剩餘產品;旣然這種結果不能由工人的過度勞動來獲得,資本就產生這樣的傾向,即力求以儘最少的費用來生產該產品,——力求節省勞動力和費用……
「從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實際地位來了解,工人本身只是生產的資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產的目的。」(見「剩餘價值論」,第二卷,第二部)
馬克思這些話之特別卓越,不僅一方面簡要而精確地判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另一方面指出了應當向社會主義生產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務。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取得利潤,至於消費,只有在保證完成取得利潤這一任務的情形下,才對於資本主義是需要的。在這以外,消費問題對於資本主義就失去意義。人及其需要就從視野中消逝。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什麽呢?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應當服從的主要任務又是什麽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利潤,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如在斯大林同志「意見」中所說的那樣,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雅羅申柯同志以為這裡所說的是消費對生產「佔首要地位」。這當然是糊塗想法。其實,我們這裡的問題不是消費佔首要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生產服從於它的主要目的——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就是如此。
雅羅中柯同志想保持生產對消費的所謂「佔首要地位」,於是斷定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就是「社會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的生產不斷增長和日益完善」。這是完全不對的。雅羅申柯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和損害了斯大林同志「意見」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羅申柯同志那裡,却把生產從手段變成了目的,而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則被取消了。結果弄成生產增長是為了生產增長,生產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從雅羅中柯同志的視野裡消失了。
所以,作爲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人消失,雅羅中柯同志「概念」裡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殘餘也隨之消失,這是毫不奇怪的。
這樣,在雅羅中柯同志那裡,就弄成了不是生產對消費「佔首要地位」,而好像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佔首要地位」這類的東西了。
三、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問題是要單獨談一談的。雅羅申柯同志斷定說,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僅僅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它不包含對於其他社會形態——其中也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能發生效力的什麽東西。他說:
「把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經濟制定的再生產公式搬到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上來,是對馬克思學說作敎條主義理解的結果,而且是與他的學說的本質相矛盾的。」(見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講話)
其次,他斷定說:「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不能作為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基礎。」(同上)
講到馬克思在其中規定了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一部類)和消費資料的生產(第二部類)之間的一定對比關係的簡單再生產理論時,雅羅中柯同志說:
「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對比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是由馬克思的『第一部類的V+M和第二部類的C」這個公式所制約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上述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在發展中的相互聯系是不應當存在的。」(同上)
他斷定說:「馬克思所制定的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間的對比關係的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能適用的,因爲馬克思這個理論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經濟及其法則。」(見雅羅申柯同志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
雅羅申柯同志就是這樣斥責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
當然,馬克思由於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結果而制定出來的再生產理論,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自然也就具有資本主義商品價値關係的形式。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中,如果僅僅看到這個形式,而看不出它的基礎,看不出它那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生效力的基本內容,就是一點也不懂得這個理論。假如雅羅申柯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麽理解的話,那末他也就會懂得這個顯而易見的眞理: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决不只限於反映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它同時還包含有對於一切社會形態——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發生效力的許多關於再生產的基本原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些基本原理,類如關於社會生產之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的原理;關於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佔優先地位的原理;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對比關係的原理;關於剩餘產品是積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關於社會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關於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唯一源泉的原理,——所有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一切基本原理,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在計劃國民經濟時,不運用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羅申柯同志本人雖然如此高傲地蔑視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但他在討論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時卻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於這些公式。
列甯、馬克思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列甯批判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意見,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些意見中,大家知道,列甯承認,馬克思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對比關係的公式,也就是雅羅中柯同志所極力反對的公式,不論對於社會主義或「純粹共產主義」、即共產主義第二階段,都是有效的。
至於馬克思,那末大家知道,他不喜歡離開對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資本論」中,並沒有研究過他的再生產公式是否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問題。然而,他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十章「第一部類的不變資本」這一節中,論述第一部類的產品在這一部類內部的交換時,曾順便指出,這一部類的產品的交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像在資本主義生產下那樣不斷地進行。馬克思說:
「如果生產是社會公有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那末很明顯,第一部類的產品,爲了再生產的目的,將作爲生產資料同樣不斷地重新分配於這一部類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一部分直接留在生產它自己的生產部門,另一部分則轉到另一些生產部門,於是在這一部類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建立起不斷對流的運動。」(見馬克思「資本論」,俄文本,第八版,第二卷,第三〇七頁)
因此,雖然馬克思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法則,但他决不認爲他的再生產理論僅僅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顯然認為他的再生產理論對於社會主義生產也能是有效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在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和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經濟時,是從他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出發的,顯然他認為這些基本原理對於共產主義制度是一定適用的。
□應該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的「社會制度」和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時,也是從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出發的,認爲這些基本原理對於共產主義制度是一定適用的。
事實就是如此。
結果,在這裡,在再生產問題上,雅羅申柯同志雖然對於馬克思的「公式」發出放肆的議論,却又碰了壁。
四、雅羅申柯同志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的末尾,建議委託他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寫道:
「根據我在全體討論會和分組討論會上以及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定義,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我能在一年內,至多一年半,在兩個人的幫助下,從理論上來解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基本問題,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列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這個理論定會把這一科學變成人民爲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認,雅羅申柯同志所犯的毛病並不是謙虛。甚至,使用某些文學家的筆法,可以說:「而是恰恰相反。」
上面已經講過,雅羅申柯同志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領導機關的經濟政策混為一談。他所認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對象——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國民經濟的計劃化、社會基金的形成等等——並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而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
我已不必說,雅羅中柯同志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他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使我們不能給予他這樣的委託。
結論:
(一)雅羅申柯同志對討論會領導人的控訴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討論會領導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不能在自己總結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羅申柯同志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二)對於雅羅申柯同志請委託他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請求,不能認爲是鄭重的,至少是因爲他這請求中充滿着赫列斯達可夫(註)的氣味。
約·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註)赫列斯達可夫是果戈理著名喜劇「巡按」中的主角。他是一個招搖撞騙、虛僞
輕浮、厚顏無恥的典型人物。——譯者答薩寧娜和溫什爾兩同志
我收到了你們的信。可以看出,你們是在深刻地認眞地研究我國的經濟問題。信中有不少正確的說法和有意思的見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嚴重的理論上的錯誤。在這封囘信中,我想只來談談這些錯誤。
一、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斷定說:「僅僅由於從事物質生產的蘇聯人的自覺行動,才產生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這一論點是完全不正確的。
是不是在我們身外客觀地存在着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爲轉移的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呢?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是存在於我們身外的客觀規律性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但是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公式對這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這就是說,這兩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確理論的觀點上,這理論斷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的法則是由社會領導機關所「創造」、「改造」的。換句話說,他們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主觀唯心論的道路。
當然,人們能發現這些客觀的規律性,認識它們,並且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但是人們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造」它們。
假定說,我們暫且採取不正確理論的觀點,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生活中有客觀規律性的存在,並宣吿可能「創造」經濟法則,「改造」經濟法則。結果會怎麽樣呢?這就會使我們陷身在混亂和偶然性的王國,使我們處在奴隸似地依賴於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們不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簡直會在這偶然性的混亂中瞎摸。
這就會使我們取消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因爲不承認客觀的規律性,不研究這些規律性,科學是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取消了科學,我們就沒有可能預見國內經濟生活中事變的進程,卽沒有可能把那怕是最起碼的經濟領導工作做好。
歸根到底,我們就會受那班决心「消滅」經濟發展法則、不理解和不考慮客觀規律性而來「創造」新法則的「經濟」冒險主義者任意擺佈。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裡所提供的馬克思主義對這問題的經典說法:
「社會的力量如同自然力一樣,在我們沒有認識它們和重視它們以前,發生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壞的作用。可是我們一經認識了它們,研究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末,我們就能完全作主,使它們愈來愈多地服從我們的意志,並藉助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特別是指現代强大的生產力。在我們還執拗地拒絕了解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的時候——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維護者是反對這種了解的,——生產力總是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它總是支配着我們,正像在上面詳細敍述過的那樣。可是,當生產力的本性一被了解之後,它就會在聯合起來了的生產者手中,由惡魔似的支配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差別,正像雷電中帶破壞性的電力與電報機上和弧光燈中馴服的電力之間的差別一樣,也正像火災的火與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差別一樣。當人們能按照現代生產力的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處理它的時候,生產中的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便會由生產中的社會的有計劃調節來代替,這種生產是爲了滿足整個社會以及社會中每個成員的需要的。那時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將由新的佔存方式來代替。在資本主義佔有方式中,產品開始是奴役生產者,以後又奴役佔有者,而新的佔有方式則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爲根據的:一方面是社會直接佔有作爲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的產品,另一方面是個人直接佔有作爲生活和享樂的資料的產品。」
二、關於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
水平的辦法問題
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這當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國民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須採取些什麽辦法呢?
有些同志以爲,應該依照從前處理資本主義財產的例子乾脆把集體農莊財產收歸國有,宣佈它是全民的財產。這個建議是完全不正確的,是絕對不能採納的。集體農莊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財產,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像處理資本主義財產那樣來處理它。無論如何不能因爲集體農莊的財產不是全民的財產,就說集體農莊的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的財產。
這些同志以為,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財產轉歸國家所有,是唯一的或無論如何是最好的國有化(註)形式。這是不對的。事實上,轉歸國家所有,這並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國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國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裡關於這點所正確說過的那樣。當國家還存在的時候,轉歸國家所有,無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國有化形式。但國家並不是永世長存的。隨著社會主義的活動範圍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的擴大,國家將日漸消亡,因而把個別人的財產和個別集團的財產轉歸國家所有的問題當然也就會消失。國家一定消亡,而社會是一定留存下來的。因此,作為全民財產的承繼人的,已經不是將要消亡的國家,而是以中央經濟領導機構爲代表的社會本身。
那末,爲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應該採取什麽辦法呢?
作爲這樣來提高集體農莊所有制的基本辦法,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提議:把集中在農業機器站的基本生產工具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這樣來解除國家對農業作基本投資的負担,並達到使集體農莊自己來担負維持和發展農業機器站的費用。他們說:
「如果以爲集體農莊的投資應該主要用在集體農村的文化需要上,而對於農業生產的需要,仍舊應該由國家進行基本的大批投資,那就不正確了。因為集體農莊已有充分能力把這一負担完全承當起來,而使國家解除這一負担,豈不是更加正確些嗎?爲了在國內製造出豐富的消費品,國家在自己的投資方面還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爲了論證這一建議,建議人提出了幾個論據:
第一,援引斯大林所說生產資料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的這句話,建議人懷疑斯大林的這一論點,宣稱國家畢竟在出售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如像大鐮刀、小鐮刀之類的小農具以及小發動機等等生產資料。他們認爲,旣然國家把這些生産資料出售給集體農莊,那末國家也可以把農業機器站的機器之類的一切其他生產資料出售給集體農莊。
這一論據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國家是把小農具出售給集體農莊的,依照農業勞動組合章程和憲法,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農具和像農業機器站的機器那樣的農業基本生產資料,或者,例如,像那也是農業基本生產資料之一的土地相提並論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爲小農具絲毫也决定不了集體農莊生產的命運,可是像農業機器站的機器以及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料,在我國當前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農業的命運的。
不難理解,當斯大林說生產資料不出售給集體農莊的時候,他所指的不是小農具,而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即農業機器站的機器、土地。建議人玩弄「生產資料」這字眼,把兩種不同的東西混爲一談,他們不知不覺地碰了壁。
第二,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又引證說,在羣眾性的集體農莊運動開始的時期——一九二九年末和一九三〇年初,聯共(布)中央自己曾主張把農業機器站轉歸集體農莊所有,同時要求集體農莊在三年內償淸農業機器站的價值。他們認爲,雖然這事情當時「因為」集體農莊「貧窮」而□□了,但是現在,當集體農莊已經富裕的時候,可以囘頭來採取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的政策。
這一論據也是不能成立的。在一九三〇年初,聯共(布)中央確實决定過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當時是按照一部分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的建議,作爲試驗、作爲嘗試而通過這個决定的。爲的要在不久之後囘到這個問題上來加以審查。但頭一次檢查就表明這一决定是不妥當的。過了幾個月,卽在一九三〇年末,就把這個决定取消了。
後來集體農莊運動進一步的增長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發展,使集體農莊莊員以及領導工作人員都最後地確信,把農業的基本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中,集中在農業機器站手中,是保證集體農莊生產高速度增長的唯一方法。
我們大家都慶幸我國農業生產的巨大增長,穀物、棉花、亞麻、糖蘿蔔等等生產的增長。這種增長的源泉是什麽呢?這種增長的源泉就是現代技術,就是許許多多為這一切生產部門服務的現代化機器。這裡的問題,不僅在於一般的技術,而在於技術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須繼續日新月異地改進,舊的技術必須作廢,代之以新技術,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這樣做,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突飛猛進就是不可思議的,無論豐富的收穫,無論豐足的農產品,也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要把幾十萬架車輪式的拖拉機作廢、代之以履帶式的拖拉機,把幾萬架陳舊了的聯合機作廢,代之以新的聯合機,以及例如,爲技術作物製造新的機器,這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說,要負担幾十億的支出,這些支出非經過六年到八年之後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國的集體農莊是百萬富翁,它們負担得了這樣大的支出嗎?不,負担不了,因爲它們沒有力量負担要在六年至八年之後才能完全收囘的幾十億的費用。這種支出只有國家才負担得了,因為國家,並且只有國家才負担得起用新機器去更換舊機器所受到的這種損失,因為國家,並且只有國家才承担得起因在六年到八年之後才能收囘這筆費用而受到的這種損失。
明白這一切之後,那末要求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說,使集體農莊遭受巨大損失,使集體農莊破產,破壞農業的機械化,減低集體農莊生產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結論說,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建議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就是向落後方面退後一步,就是企圖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
就暫且假定一下,我們接受了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建議,並着手把基本生產工具、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這會得到什麽結果呢?
第—,結果就會是集體農莊成了基本生產工具的所有者,換句話說,它們就會處於我國無論那一個企業都沒有的特殊地位,因爲大家知道,在我國,甚至國有化的企業也並不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麽理由來作爲集體農莊的這種特殊地位的根據呢,用什麽進步的、前進的理由來作爲根據呢?可不可以說,這樣的地位就會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會加快我們的社會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呢?如果說這樣的地位只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離開全民所有制更遠,不是使得接近共產主義,反而是使得遠離共產主義,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第二,結果就會是擴大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因爲巨量的農業生產工具會投進商品流通的範圍。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能不能使得我們向共產主義推進呢?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以爲如何?說它只會阻滯我們向共產主義前進,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基本錯誤,是在於他們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作用和意義,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槪他們以爲,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商品流通是不會妨礙這個事業的。這是由於不了解馬克思主義而犯的嚴重錯誤。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裡批評杜林主張的在商品流通條件下活動的「經濟公社」時,確鑿證明商品流通的□在必然要使杜林的所謂「經濟公社」去復活資本主義。大概,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是不同意這一點的。那末,他們就更站不住脚了。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從這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依照需要來分配產品的共產主義原則,是擯斥任何商品交換的,因而也擯斥把產品轉化爲商品,同時也就是把產品轉化爲價值的。
關於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建議和論據的情形,就是如此。
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歸根到底應該採取什麽步驟呢?
集體農莊不是普通的企業。集體農莊耕種的土地早已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而是全民的財產。因而,集體農莊並不是它所耕種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體農莊藉以進行工作的基本生產工具,並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而是全民的財產。因而,集體農莊不是基本生產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體農莊是合作企業,它使用自己莊員的勞動,按照勞動日把收入分配給莊員,而且集體農莊□自己年年更換的、用於生產的種籽。
試問,集體農莊究竟佔有一些什麽,它可以隨心所欲、完全自由支配的集體農莊財產是什麽?這種財產就是集體農莊的產品、集體農莊生產的產品,即穀物、肉類、油類、蔬菜、棉花、糖蘿蔔、亞麻等等,而建築物和集體農莊莊員園地中的個人副業不計在內。問題在於,這種產品的大部分、卽集體農莊生產的剩餘品,進入市場,從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統中。正是這種情況現在阻礙着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應該從這一方面展開工作,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爲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須將集體農莊生產的剩餘品從商品流通系統中排除出去,把它們列入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間的產品交換系統中。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
我們還沒有發達的產品交換制度,但是有以「換貨」為形式的農產品產品交換的萌芽。
大家知道,對植棉、種蔴、種糖蘿蔔和其他的集體農莊的產品早已實行「換貨」了。誠然,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換貨」,但總算是在「換貨」了。要順便指出:「換貨」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應該用「產品交換」來代替它。任務是在於,要使農業的一切部門中都培植這些產品交換的萌芽,並把它們發展成為產品交換的廣大系統,以便集體農莊在交出自己的產品時不僅取得貨幣,而主要是取得必要的製成品。這樣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農村的產品,所以,推行這種制度無需特別急忙,要隨着城市製成品積累的程度而定。但是應該一往直前、毫不猶豫地推行這種制度,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活動範圍。
這樣的制度旣縮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就使社會主義易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此外,它使我們有可能把集體農莊的基本財產、集體農莊生產的產品包括進全民計劃化的總的系統中。
爲了在我國現今條件下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這將是實際的和有决定意義的辦法。
這樣的制度對於集體農莊的農民是否有利呢?無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爲集體農莊農民從國家手中獲得的產品,將比在商品流通中獲得的要多得多,價錢也便宜得多。大家知道,與政府訂有產品交換(「換貨」)合同的集體農莊所獲得的利益,較之沒有訂立這種合同的集體農莊,要多得無比。如果產品交換制度推廣到全國所有的集體農莊,那末這些利益就要成為我國全體集體農莊農民都能享受的了。
約·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九月廿八日
(註)在這裡,國有化是指歸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是指歸國家政權所有。——譯者
我沒有急於囘信,因為你所提出的問題,我認爲並不是緊急的。加之還有別的帶緊急性的問題,自然,就把對你的來信的注意力轉移了。
我來逐點囘答。
關於第一點。
在我的「意見」中有一個大家知道的原理:社會在科學法則面前並不是無能爲力的,人們認識了經濟法則,就能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你斷定說,這一原理不能適用於其他社會形態,它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有效,比方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過程的自發性質,就不會使社會有可能利用經濟法則來為社會謀福利。
這是不對的。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例如,在法國,資產階級就曾利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大家知道的法則來反對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新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並且使這種生產關係和在封建制度內部生長起來的生產力的性質相適合。資產階級做到了這件事,並不是由於它的特殊本領,而是因爲它對於這件事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封建主反抗這件事,並不是由於他們的愚鈍,而是由於他們有切身的利害關係,要來阻撓這一法則的實現。
關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應該這樣說。工人階級利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並且使這種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性質相適合。工人階級能够做到了這件事,並不是由於它的特殊本領,而是因爲它對於這件事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已從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的先進力量變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資產階級,曾經竭力反抗這一法則的實現,——它之所以反抗,並不是由於它沒有組織性,也不是因爲經濟過程的自發性質推動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於它有切身的利害關係,要來反對這一法則的實現。
由此可見:
一、在某種程度內利用經濟過程、經濟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這樣的事情也不僅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發生,而且在其他社會形態下也發生。
二、在階級社會裡利用經濟法則無論何時何地都有階級背景,而且利用經濟法則爲社會謀福利的旗手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先進階級,而衰朽的階級則反抗這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無產階級與其他曾在歷史上完成過生產關係變革的階級間的差別就在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和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是消滅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剝削,而是消滅任何剝削;至於其他階級的革命,却只是消滅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剝削,而爲它們與社會絕大多數人利益相矛盾的狹隘階級利益所限制。
在「意見」中說到利用經濟法則為社會謀福利這件事的階級背景。那裡說:「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和應用新的法則是或多或少順利地進行的;與此相反,在經濟學領域中,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則,却要遇到這些力量極强烈的反抗。」但是你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關於第二點。
你斷定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達到使生產關係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而在其他社會形態下,只能實現不完全的適合。
這是不對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當資產階級破壞了封建的生產關係、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的時代,無疑地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否則,資本主義就不會像它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那樣迅速地發展了。
其次,「完全適合」這種說法是不能在絕對的意義上來理解的。不能把這種說法理解爲彷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决沒有生產關係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的現象。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無可爭辯地是走在生產關係前面的。生產關係只是經過一些時候,才會被改造得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
那末,「完全適合」這種說法該怎樣來理解呢?應該理解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後了的生產關係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做到這點,是因爲在這社會的成份中沒有那些能够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當然,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有落後的惰性的力量,它們不了解生產關係有改變的必要,但是這種力量,當然不難克服,而不致把事情弄到衝突的地步。
關於第三點。
從你的議論中可以看出,你把我們國有化企業所生產的生產資料,首先是生產工具,看做是商品。
可不可以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資料看做是商品呢?據我看來,無論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這樣的一種產品,它可以出售給任何買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後,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對商品的所有權,而買主則變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轉售、抵押或讓它腐爛。生產資料是否適合於這個定義呢?顯然,是不適合的。第一,生產資料並不「出售」給任何買主,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而只是由國家分配給自己的企業。第二,生產資料所有者——國家,在把生產資料交給某一個企業時,絲毫不失去對它們的所有權,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權的。第三,企業的經理,從國家手中取得了生產資料之後,不但不變成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確認爲受蘇維埃國家的委任,依照國家所交下的計劃,來使用這些生產資料的。
由此可見,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國制度下的生產資料列入商品範疇中。
那末,爲什麽又講生產資料的價值,講它們的成本,講它們的價格等等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這是爲了估價、爲了核算、爲了計算企業的盈虧、爲了檢查和監督企業所必需的。但這只是事情的形式的一面。
第二,這是爲了在對外貿易上便於把生產資料出售給外國所必需的。這裡,在對外貿易領域內,並且僅僅是在這個領域內,我們的生產資料才確實是商品,才確實被出售(不是加引號的出售)。
這樣看來,在對外貿易流通領域內,我國企業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無論在實質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特性,可是在國內經濟流通領域內,生產資料却失去商品的特性,不再是商品,並且超出價値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之外,僅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估價等等)。
這種特殊情况究竟怎樣解釋呢?
問題在於: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並不是以變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漸改變的方式進行的,舊的東西並不是簡單地被廢除乾淨,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變得與新的東西相適應,僅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於新的東西也不是簡單地消滅舊的東西、而是滲到舊的東西裡面去,改變舊東西的本性和機能,並不破壞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來發展新的東西。在我國的經濟流通中,不僅商品是這樣,而且貨幣也是這樣,連銀行也是這樣,銀行失去自己舊的機能並取得了新的機能,同時保持着舊的形式而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利用。
如果從形式上的觀點,從現象表面過程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就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彷佛資本主義的範疇在我國經濟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看待問題,即把經濟過程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把深處的發展過程和表面現象嚴格地區別開來,那就可以得出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即資本主義的舊範疇在我國保留下來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實質上這些範疇在我國已經根本改變得與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相適合了。
關於第四點。
你斷定說,價値法則對於在農業中所出產的、依照採購價格出售給國家的「生產資料」的價格,發生着調節的影響。你在這裡所指的是例如棉花這種原料的「生產資料」。在這裡你還可以再加上亞麻、羊毛及其他農業原料。
應該首先指出,在這種情形下,農業所生產的並不是「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產資料」這個術語。當馬克思主義者說生產資料的生產時,首先是指生產工具的生產,——馬克思把這叫做「機械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爲生產的骨骼和筋肉的系統」,這個系統組成「社會生產一定時代的作為特徵的標誌」。把一部分生產資料(原料)和包括生產工具的整個生產資料等量齊觀,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因爲馬克思主義認爲,和其他一切生產資料來比,生產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誰都知道,原料本身不能生產生產工具,雖然某幾種原料也是生產生產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沒有生產工具是不能生產任何原料的。
其次,價値法則對農業中所生產的原料的價格的影響,是否像你諾特京同志所斷言的那樣,是具有調節作用的呢?如果我國存在着農業原料價格的「自由」漲跌,如果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在我國發生作用,如果我國沒有計劃經濟,如果原料的生產不是由計劃來調節的,那末,價値法則的影響就會是有調節作用的了。但是,因為在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並沒有這些「如果」,所以價値法則對於農業原料價格的影響無論如何不會是有調節作用的。第一,我國農業原料的價格是固定的,由計劃規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農業原料的生產規模並不是由自發的力量、不是由什麽偶然的因素來决定,而是由計劃來决定的。第三,爲生產農業原料所必需的生產工具,不是集中在個別人或個別集團手中,而是集中在國家手中。既然這樣,還有什麽價値法則的調節作用呢?結果,價值法則本身也是由社會主義生產所特有的上述事實來調節的。
因此,不能否認,價值法則是影響農業原料價格的形成的,它是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認,這種影響並不起調節作用,也不可能起調節作用。
關於第五點。
說到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贏利,我在「意見」中曾反駁某些同志,這些同志肯定說,既然我國計劃性的國民經濟不大重視贏利的企業,並且容許不贏利的企業也和這些企業並存,彷彿計劃性的國民經濟抹煞經濟中的贏利性這個原則本身。在「意見」中說,個別企業□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是决不能和社會主義生產所給予我們的那個高級形式的贏利相比的,因爲社會主義生產使我們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並保證我們的生產不斷提高。
但是,如果從此得出結論說,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是沒有特別價值的,所以不値得加以重視,那就不對了。這當然是不對的。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從發展我國生產的觀點來說,是有巨大意義的。無論在計劃建設或計劃生產時,這都是應該注意到的。這是我國現今發展階段上經濟活動方面的起碼知識。
關於第六點。
不知道應該怎樣了解你這個關於資本主義的說法:「形式大大改變了的擴大的生產」。應該說,這樣的而且還是擴大的生產,是世界—所沒有的。
顯然,在世界市場已經分裂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攫取世界資源的範圍開始縮小了的時候,資本主義發展的循環性質——生產的增長和減縮——一定還會存在。不過,這些國家生產的增長將在縮小的基礎上進行,因爲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將要減縮。
關於第七點。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蘇聯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開始的。這是總危機的第一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的各人民民主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展開了總危機的第二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第一次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第二次危機,應該看做不是個別的、彼此隔離的獨立危機,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發展的兩個階段。
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否僅僅是政治的或僅僅是經濟的危機呢?旣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旣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總的卽全面的危機。同時也就很清楚,這種危機的基礎,一方面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瓦解現象日益加劇,另一方面是脫離資本主義的各國——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實力日益增長。
約·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關於□·□·雅羅申柯同志的錯誤
今年三月二十日,雅羅申柯同志寫了一封信分送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說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討論會上所討論過的幾個經濟問題。他在這封信中申訴說,在討論會的一些總結性的主要文件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的「意見」中,雅羅中柯同志的「觀點沒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在這封短信中還有雅羅申柯同志的建議:請准許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內編寫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並給他兩個助手來作這一工作。
我以爲,必須從本質上來考察雅羅申柯同志的申訴和他的建議。
我們先從他的申訴開始。
究竟在上述文件中沒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羅中柯同志的「觀點」,是什麽呢?
一、雅羅申柯同志的主要錯誤
如果用一兩句話來評定雅羅申柯同志的觀點,那就應該說,他的觀點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因而是極端錯誤的。
雅羅中柯同志的主要錯誤是,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過分誇大了生產力的作用,同樣也就過分縮小了生產關係的作用,竟至宣佈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的一部分。
雅羅申柯同志同意承認生產關係在「對抗的階級矛盾」條件下有某種作用,因爲在那裡,生產關係「是與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這種作用限制爲消極的作用,限制爲阻礙生產力發展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的作用。生產關係的其他機能、任何積極的機能,雅羅中柯同志是沒有看到的。
至於說到已經沒有「對抗的階級矛盾」而且生產關係「再也不與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社會主義制度時,雅羅申柯同志便認爲,在這裡,生產關係的任何獨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產關係不再是發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產力所吞沒,猶如部分被整體吞沒一樣。雅羅申柯同志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的生產關系包括在生產力的組織中,作為這種組織的一個手段、一個成分。」(見雅羅申柯同志給中央政治局的信)
這樣一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又是什麽呢?雅羅中柯同志囘答說:「所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不在於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生產關係,而在於制定和發揮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組織的科學理論、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化的理論。」(見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 這的確也就說明,雅羅申柯同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這些經濟問題,如我國經濟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等,並不感到興趣,認爲這都只能引起煩瑣學派式的爭論的次要問題。他公然宣稱,在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某些範疇——價値、商品、貨幣、信貸等等——的作用的爭論,卽在我國常常帶着煩瑣學派式的性質的爭論,將用關於社會生產中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健全議論以及這種組織的科學論證來代替。」(見雅羅申柯同志在分組討論會上的講話)
這樣,就是沒有經濟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了。
雅羅申柯同志以爲,只要安排好「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難地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了。他認爲,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已經十分够了。他公然宣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爭取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鬥爭,是歸結爲在社會生產中正確組織生產力和合理使用生產力的鬥爭。」(見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雅羅中柯同志鄭重宣稱:「共產主義——這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
這樣,「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就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了。
雅羅申柯同志從這一切便作出結論說,對於一切社會形態,不可能有統一的政治經濟學,而應該有兩種政治經濟學:一種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以前各種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其對象是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另一種是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其對象應當不是研究生產關係卽經濟關係,而是研究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
雅羅中柯同志的觀點就是這樣。
對於這種觀點可以講些什麽呢?
第一,說生產關係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只限於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這是不對的。當馬克思主義者講到生產關係的阻礙作用時,他們所指的並不是任何生產關係,而只是已經不能適合生產力發展、因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係。但是,除了舊生產關係以外,大家知道,還有代替舊生產關係的新生產關係。可不可以說,新生產關係的作用歸結為阻礙生產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產關係是這樣一種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它眞正决定生產力進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發展,沒有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就注定要萎靡下去,如像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一樣。
誰也不能否認,我們蘇聯工業的生產力在幾個五年計劃中,有巨大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用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沒有我國生產關係卽經濟關係中的這種變革,我國的生產力就會萎靡下去,如像它現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萎靡的情形一樣。
誰也不能否認,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在最近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中,有巨大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在三十年代沒有用新的集體化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農村中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沒有這種生產的變革,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就會萎靡下去,如像它現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萎靡的情形一樣。
當然,新的生產關係不能永遠是新的,而且也不永遠是新的,它開始變舊,並與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而開始失去其爲生產力的主要推進者的作用,並變成生產力的阻礙者。那時候,就出現新生產關係來代替這種已經變舊了的生產關係,新生產關係的作用就是充當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推進者。
生產關係從生產力阻礙者的作用發展到生產力主要推進者的作用,以及從生產力主要推進者的作用發展到生產力阻礙者的作用,——這樣一種發展的特性,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是現在一切初學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的。原來雅羅申柯同志却不知道這一點。
第二,說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的獨立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在消失,說生產關係是在被生產力吞沒着,說社會生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歸結爲生產力的組織,這是不對的。馬克思主義是把社會生產看作一個整體,它具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社會生產力(社會對自然力的關係,社會在與自然力作鬥爭中來取得必要的物質資料)和生產關係(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這是社會生產的兩個不同的方面,雖然它們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繫着的。正因為它們是社會生產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所以它們能够互相影響。硬說這兩個方面中有一個可以被另一個吞沒而變成它的組成部分,就是極嚴重地違反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聯合起來進行共同活動並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便不能從事生產。爲了從事生產,人們就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而且只有通過這些社會聯系和關係,才有人們對自然的關係,才有生產。」(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可見,社會生產是由兩個方面組成,這兩個方面雖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系着,但却反映兩種不同的關係,即人們對自然的關係(生產力)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生產關係)。只有具備生產的這兩方面,才能有社會生產,——不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或其他社會形態下都是一樣。
大概,雅羅申柯同志是不十分同意馬克思的。他認為馬克思的這個原理是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歸結為合理組織生產力的問題,而拋開了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並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脫節。
這樣,在雅羅申柯同志那裡,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波格丹諾夫的「普遍組織科學」之類的東西了。
這樣,雅羅申柯同志在採納了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力量這個正確思想以後,却把這個思想弄到了荒謬的地步,竟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卽經濟關係的作用;而且,本來是生氣蓬勃的社會生產,他却弄成了片面的和空洞的生產工藝學,卽布哈林的「社會組織技術」之類的東西了。
馬克思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卽在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中——斯大林註),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要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則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藉以建立起來,而且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這就是說,每個社會形態,連社會主義社會也在內,都有自己的由人們生產關係的總和所構成的經濟基礎。於是發生一個問題:在雅羅申柯同志那裡,究竟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怎樣的呢?大家知道,雅羅中柯同志已經消滅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這個多少帶獨立性的領域,而把生產關係剩下的一點殘餘歸併到生產力組織之內。試問,社會主義制度有沒有它自己的經濟基礎呢?看起來,旣然生產關係這一多少獨立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消失,那末社會主義制度只好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了。
這樣,就是沒有自己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相當可笑的事情……
一般講來,沒有自己經濟基礎的社會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大槪,雅羅申柯同志認爲是可能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却認爲,這樣的社會制度在世界上是沒有的。
最後,說共產主義是生產力的合理組織,說生產力的合理組織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了,說只要合理地組織生產力,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難地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不對的。在我國的文獻中,有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定義、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公式、卽列甯的公式:「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看起來,雅羅中柯同志不喜歡列甯的公式,於是用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產主義——這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來代替列甯的公式。
第一,誰也不明白,雅羅申柯同志所吹噓的這個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或「合理」組織是什麼?這組織的具體內容是什麽?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和分組討論會上的講話中,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幾十次重複這個神話般的公式,然而他無論在那一個地方,都沒有試圖用片言隻字來說明這個彷彿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的生產力的「合理組織」,究竟應該怎樣來了解。
第二,如果對這兩個公式加以選擇的話,那末應該拋棄的,就不是唯一正確的列甯的公式,而是雅羅中柯同志的所謂公式,他這公式顯然是臆造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是從波格丹諾夫的武器庫——「普遍組織科學」中拿來的東西。
雅羅申柯同志以爲,只要做到合理地組織生產力,就能獲得豐富的產品並過渡到共產主義,就能從「按勞取酬」的公式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這是大錯特錯的,這暴露了他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法則一竅不通。雅羅中柯同志過於簡單地、小孩般簡單地想像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雅羅申柯同志不了解,如果讓集體農莊集團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經濟事實仍然存在,那就旣不能獲得能滿足社會一切需要的豐富產品,也不能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雅羅申柯同志不了解:在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前,社會必須經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造和文化改造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勞動將在社會成員面前從僅僅維持生活的手段變成爲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將變成爲社會存在的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基礎。
爲了準備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宣言上過渡到共產主義,至少必須實現三個基本的先决條件。
第一,必須切實加以保證的,不是神話般的生產力的「合理組織」,而是全部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而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佔優先地位。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之所以必須佔優先地位,不僅是因爲這種生產應當保證自己的企業以及國民經濟其他一切部門的企業所需要的裝備,而且是因爲沒有這種生產就根本不可能實現擴大再生產。
第二,必須用實行起來有利於集體農莊因而也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逐漸過渡的辦法,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並且也用逐漸過渡的辦法使產品交換制來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權或其他某個社會經濟中心能够爲了社會福利來掌握社會生產的全部產品。
雅羅申柯同志斷定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沒有任何矛盾。這是錯誤的。當然,我國現今的生產關係是處在這樣一個時期,它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增長,一日千里地把生產力向前推進。但是,如果以此自滿,以爲在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確了。因爲生產關係的發展是落後於並且將來也會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在領導機關的正確政策下,這些矛盾就不會變對立,而這樣也就不會弄到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如果我們執行類似雅羅申柯同志所推薦的不正確的政策,那就會是另一種情形了。在這種場合下,衝突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的生產關係可能變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極嚴重的阻礙者。
因此,領導機關的任務在於及時地看出日益增長的矛盾,並及時地採取辦法,使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的增長,來克服這種矛盾。這首先是與集體農莊集團所有制、商品流通這種經濟現象有關的。當然,目前這些現象是在被我們有成效地利用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而且它們也在給我國社會帶來毫無疑問的利益。無疑地,它們在最近的將來也將帶來利益。但同時這些現象已在開始阻礙我國生產力的强大發展,因爲它們正在阻礙這種由國家計劃化來完全包括全部國民經濟、特別是包括農業的事業,如果看不出這點,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這些現象就會愈加阻礙我國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所以,任務就在於要逐漸把集體農莊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以及也是逐漸用產品交換制代替商品流通,這樣來消滅這些矛盾。
第三,必須使社會達到這樣高度的文化發展,保證社會一切成員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使社會成員能獲得足以成爲社會發展的積極活動家的敎育,能自由地選擇職業,而不致由於現存的勞動分工而終身束縛於某一種職業。
為了做到這點,究竟需要什麽呢?
如果認爲用不着大大改變現今的勞動狀況,便可以達到社會成員的這種强大的文化高漲,那就不正確了。爲了做到這點,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勞動時間至少縮短到六小時,然後再縮短到五小時。這是使社會成員有充分的自由時間來獲得全面敎育所必需的。其次,爲了做到這點,需要實行普及義務的綜合技術敎育,這是使社會成員有可能自由選擇職業而不致終身束縛於某一種職業所必需的。再次,為了做到這點,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條件,把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至少提高一倍,也許還要更多,辦法是不僅直接提高貨幣工資,而且特別重要的,是繼續不斷地降低日用品價格。
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就是這樣。
只有把這一切先決條件全部實現之後,才可以希望,勞動將在社會成員面前,從累贅變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馬克思),「勞動從沉重的負担變成愉快」(恩格斯),公有制將被社會全體成員看作是社會存在的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基礎。
只有把這一切先决條件全部實現之後,才可以從社會主義的公式「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公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將是從一種經濟卽社會主義經濟到另一種更高的經濟即共產主義經濟的根本過渡。
可見,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事業,並不像雅羅申柯同志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企圖把這全部複雜的和多樣性的事業、需要有極重大經濟變更的事業歸結爲「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像雅羅中柯同志所做的那樣,就等於以波格丹諾夫謬論來偷換馬克思主義。
二、雅羅申柯同志的其他錯誤
一、雅羅申柯同志從自己不正確的觀點出發,作出了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對象的不正確的結論。
雅羅申柯同志認爲每一社會形態有它自己的獨特的經濟法則。他從這點出發,就否認有論述一切社會形態的統一的政治經濟學的必要。但他是完全不對的,他在這裡是與恩格斯、列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背道而馳了。
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各種不同社會中藉以進行生產和交換,及與此相適應,藉以經常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反杜林論」)。因此,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種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法則,而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法則。
大家知道,列甯是十分同意這點的,他在批判布哈林的小冊子「過渡時期的經濟」時說,布哈林把政治經濟學的作用範圍局限於商品生產,首先是局限於資本主義生產,這是不對的;他同時指出,在這裡,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後退了一步」。
政治經濟學敎科書未定稿中所提供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是與此十分符合的。在這未定稿中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法則」的科學。
這是很明白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在它的經濟發展中,不僅服從自己特有的經濟法則,而且還服從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法則,例如,在單一的社會生產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的法則,在一切社會形態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關係法則。所以,各個社會形態不僅以自己特有的法則互相分開着,而且以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法則互相聯繫着。
恩格斯說得完全對:「要全面地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這個批判,只認識生產、交換和分配的資本主義形式是不够的。還必須——那怕是大體上——研究和比較資本主義形式以前的各種形式或較爲不發達的國家中與資本主義形式並存的各種式。」(「反杜林論」)
看起來,在這裡,在這個問題上,雅羅中柯同志是與布哈林互相呼應起來了。
其次,雅羅申柯同志斷定說:在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政治經濟學的各個範疇——價値、商品、貨幣、信貸等等——將用關於社會生產中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健全議論來代替」;因而這種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不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是「制定和發揮生產力組織的科學理論、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理論等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喪失着自己獨立的作用,並被生產力吞沒着而成爲它的組成部分。
(下轉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必須說,在我們這裡還沒有一個發了瘋的「馬克思主義者」講過這種胡說八道的話。要知道,沒有經濟問題卽生產問題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什麽意思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嗎?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用生產力組織問題來代替經濟問題,這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雅羅申柯同志正好是這樣作的,——他在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裡,他是與布哈林完全結合起來了。布哈林說過,資本主義消滅時,政治經濟學也必定隨着消滅。雅羅申柯同志沒有這樣說,却是這樣作,作這種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事情。誠然,他同時裝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樣子,但這是詭計,而且是不值一文的詭計。事實上,他作的就是布哈林所鼓吹而爲列甯所反對的這件事。雅羅申柯同志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羅申柯同志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歸結爲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歸結爲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問題等等。但是他大錯特錯了。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問題等等,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而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這是兩種不同的領域,不能混爲一談。雅羅申柯同志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法則。經濟政策是由此作出實際結論,把它們具體化,在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經濟政策的問題堆壓在政治經濟學上,就是戕害這門科學。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這裡包括:(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丙)完全以生產關係爲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這個定義中缺少恩格斯定義內的「交換」這個術語。其所以缺少,是因爲「交換」通常被許多人了解爲不是一切社會形態而只是某些社會形態所特有的商品交換,這有時候就會引起誤會,雖然恩格斯所說的「交換」這個術語不僅是指商品交換。但是,恩格斯用「交換」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顯然已包含在上述定義中,作爲其組成部分。因而,就其內容講來,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這個定義是與恩格斯的定義完全相符合的。
二、當人們談到某一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法則時,他們通常是從下列這點出發的:社會形態不能有幾個基本經濟法則,它只能有某一個基本經濟法則來作爲基本法則。要不然的話,每個社會形態就會有幾個基本經濟法則,這就與基本法則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然而,雅羅申柯同志並不同意這點。他認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可以不是一個,而是幾個。這是難於相信的,但這是事實。他在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中說:
「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總量的多少和對比,是由被吸引到社會生產中的勞動力增長的事實和前途來决定的。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法則,它制約着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結構。」
這是他的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基本經濟法則。
雅羅中柯同志在同一講話中宣稱:
「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對比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由生產資料生產的需要所制約的,這種生產的規模是由被吸引到社會生產中的一切能勞動的人口的多少來决定。這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同時這是我國憲法從蘇聯人的勞動權引伸出的要求。」
這是所謂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基本經濟法則。
最後,雅羅申柯同志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宣稱:
「從這點出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特點和要求,在我看來,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生產之不斷增長和日益完善。」
這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第三個基本經濟法則了。
這一切法則都□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呢,或者僅僅它們中間的一個才是呢?如果是它們中間的一個,那末究竟是那一個呢?對於這些問題,雅羅中柯同志在最後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並沒有給予囘答。他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表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時,想必他「忘記了」在三個月前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中他已經表述過社會主義的其他兩個基本經濟法則,大概他以爲別人不會注意這個很不高明的手法。但他的打算顯然是落空了。
我們就假定,雅羅中柯同志所表述的前兩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羅申柯同志現在認為在他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所述明的第三個公式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我們來看一看雅羅申柯同志的這封信吧。
雅羅申柯同志在這封信中說,他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在「意見」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定義。他說:
「在這個定義中主要的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在這裡,表明生產是達到這個主要目的、卽滿足需要的手段。這個定義使人有根據認為,你所表述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不是從生產佔首要地位出發,而是從消費佔首要地位出發。」
顯然,雅羅申柯同志完全沒有了解問題的本質,並且看不見,消費或者是生產佔首要地位的議論是與問題無關的。當人們講到某種社會過程對其他過程佔首要地位時,他們的出發點通常是:這兩種過程多少是同一類的。可以而且必須說,生產資料的生產對消費資料的生產佔首要地位,因爲在這兩種場合下,我們所說的都是生產,因而它們多少是同一類的。但决不能說消費對生產佔首要地位或生產對消費佔首要地位,如果這樣說,那就是不正確的。因爲生產和消費是兩個全不相同的領域,誠然,這是兩個互相聯系着、但畢竟各不相同的領域。雅羅中柯同志顯然不了解,這裡所說的不是消費或生產佔首要地位,而是社會給社會生產定出什麽目的,它使社會生產——比方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服從於什麽任務。因此,雅羅申柯同志關於「生產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基礎,猶如是其他任何社會的生活基礎一樣」的說法,也是與問題完全無關的。雅羅中柯同志忘記了,人們不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是爲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他忘記了,跟滿足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
可不可以一般地講社會主義生產或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一般地講資本主義生產或社會主義生產所服從的任務呢?我以為是可以而且應當的。
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生產商品,而是生產剩餘價値或在發展形式下的利潤,不是生產產品,而是生產剩餘產品。從這個觀點看來,勞動本身只是在它給資本創造利潤或剩餘產品的情形下,才是生產的勞動。只要工人不創造這種東西,他的勞動就是不生產的勞動。因而,被使用的生產勞動量,只是在由於有這勞動量——或相當於這勞動量——而剩餘勞動量得以增長的情形下,才使資本感到興趣;只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叫做必要的勞動時間才是必要的東西。只要勞動不產生這樣的成果,那它就是多餘的,就是應當被停止的。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始終是以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來創造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値或最大限度的剩餘產品;旣然這種結果不能由工人的過度勞動來獲得,資本就產生這樣的傾向,即力求以儘最少的費用來生產該產品,——力求節省勞動力和費用……
「從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實際地位來了解,工人本身只是生產的資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產的目的。」(見「剩餘價值論」,第二卷,第二部)
馬克思這些話之特別卓越,不僅一方面簡要而精確地判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另一方面指出了應當向社會主義生產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務。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取得利潤,至於消費,只有在保證完成取得利潤這一任務的情形下,才對於資本主義是需要的。在這以外,消費問題對於資本主義就失去意義。人及其需要就從視野中消逝。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什麽呢?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應當服從的主要任務又是什麽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利潤,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如在斯大林同志「意見」中所說的那樣,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雅羅申柯同志以為這裡所說的是消費對生產「佔首要地位」。這當然是糊塗想法。其實,我們這裡的問題不是消費佔首要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生產服從於它的主要目的——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就是如此。
雅羅中柯同志想保持生產對消費的所謂「佔首要地位」,於是斷定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就是「社會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的生產不斷增長和日益完善」。這是完全不對的。雅羅申柯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和損害了斯大林同志「意見」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羅申柯同志那裡,却把生產從手段變成了目的,而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則被取消了。結果弄成生產增長是為了生產增長,生產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從雅羅中柯同志的視野裡消失了。
所以,作爲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人消失,雅羅中柯同志「概念」裡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殘餘也隨之消失,這是毫不奇怪的。
這樣,在雅羅中柯同志那裡,就弄成了不是生產對消費「佔首要地位」,而好像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佔首要地位」這類的東西了。
三、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問題是要單獨談一談的。雅羅申柯同志斷定說,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僅僅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它不包含對於其他社會形態——其中也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能發生效力的什麽東西。他說:
「把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經濟制定的再生產公式搬到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上來,是對馬克思學說作敎條主義理解的結果,而且是與他的學說的本質相矛盾的。」(見雅羅中柯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講話)
其次,他斷定說:「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不能作為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基礎。」(同上)
講到馬克思在其中規定了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一部類)和消費資料的生產(第二部類)之間的一定對比關係的簡單再生產理論時,雅羅中柯同志說:
「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對比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是由馬克思的『第一部類的V+M和第二部類的C」這個公式所制約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上述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在發展中的相互聯系是不應當存在的。」(同上)
他斷定說:「馬克思所制定的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間的對比關係的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能適用的,因爲馬克思這個理論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經濟及其法則。」(見雅羅申柯同志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
雅羅申柯同志就是這樣斥責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
當然,馬克思由於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結果而制定出來的再生產理論,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自然也就具有資本主義商品價値關係的形式。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中,如果僅僅看到這個形式,而看不出它的基礎,看不出它那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生效力的基本內容,就是一點也不懂得這個理論。假如雅羅申柯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麽理解的話,那末他也就會懂得這個顯而易見的眞理: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决不只限於反映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它同時還包含有對於一切社會形態——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發生效力的許多關於再生產的基本原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些基本原理,類如關於社會生產之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的原理;關於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佔優先地位的原理;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對比關係的原理;關於剩餘產品是積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關於社會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關於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唯一源泉的原理,——所有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一切基本原理,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在計劃國民經濟時,不運用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羅申柯同志本人雖然如此高傲地蔑視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但他在討論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時卻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於這些公式。
列甯、馬克思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列甯批判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意見,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些意見中,大家知道,列甯承認,馬克思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對比關係的公式,也就是雅羅中柯同志所極力反對的公式,不論對於社會主義或「純粹共產主義」、即共產主義第二階段,都是有效的。
至於馬克思,那末大家知道,他不喜歡離開對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資本論」中,並沒有研究過他的再生產公式是否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問題。然而,他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十章「第一部類的不變資本」這一節中,論述第一部類的產品在這一部類內部的交換時,曾順便指出,這一部類的產品的交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像在資本主義生產下那樣不斷地進行。馬克思說:
「如果生產是社會公有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那末很明顯,第一部類的產品,爲了再生產的目的,將作爲生產資料同樣不斷地重新分配於這一部類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一部分直接留在生產它自己的生產部門,另一部分則轉到另一些生產部門,於是在這一部類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建立起不斷對流的運動。」(見馬克思「資本論」,俄文本,第八版,第二卷,第三〇七頁)
因此,雖然馬克思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法則,但他决不認爲他的再生產理論僅僅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顯然認為他的再生產理論對於社會主義生產也能是有效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在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和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經濟時,是從他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出發的,顯然他認為這些基本原理對於共產主義制度是一定適用的。
□應該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的「社會制度」和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時,也是從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出發的,認爲這些基本原理對於共產主義制度是一定適用的。
事實就是如此。
結果,在這裡,在再生產問題上,雅羅申柯同志雖然對於馬克思的「公式」發出放肆的議論,却又碰了壁。
四、雅羅申柯同志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的末尾,建議委託他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寫道:
「根據我在全體討論會和分組討論會上以及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定義,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我能在一年內,至多一年半,在兩個人的幫助下,從理論上來解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基本問題,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列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這個理論定會把這一科學變成人民爲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認,雅羅申柯同志所犯的毛病並不是謙虛。甚至,使用某些文學家的筆法,可以說:「而是恰恰相反。」
上面已經講過,雅羅申柯同志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領導機關的經濟政策混為一談。他所認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對象——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國民經濟的計劃化、社會基金的形成等等——並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而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
我已不必說,雅羅中柯同志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他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使我們不能給予他這樣的委託。
結論:
(一)雅羅申柯同志對討論會領導人的控訴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討論會領導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不能在自己總結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羅申柯同志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二)對於雅羅申柯同志請委託他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請求,不能認爲是鄭重的,至少是因爲他這請求中充滿着赫列斯達可夫(註)的氣味。
約·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註)赫列斯達可夫是果戈理著名喜劇「巡按」中的主角。他是一個招搖撞騙、虛僞
輕浮、厚顏無恥的典型人物。——譯者答薩寧娜和溫什爾兩同志
我收到了你們的信。可以看出,你們是在深刻地認眞地研究我國的經濟問題。信中有不少正確的說法和有意思的見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嚴重的理論上的錯誤。在這封囘信中,我想只來談談這些錯誤。
一、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斷定說:「僅僅由於從事物質生產的蘇聯人的自覺行動,才產生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這一論點是完全不正確的。
是不是在我們身外客觀地存在着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爲轉移的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呢?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是存在於我們身外的客觀規律性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但是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公式對這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這就是說,這兩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確理論的觀點上,這理論斷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的法則是由社會領導機關所「創造」、「改造」的。換句話說,他們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主觀唯心論的道路。
當然,人們能發現這些客觀的規律性,認識它們,並且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但是人們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造」它們。
假定說,我們暫且採取不正確理論的觀點,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生活中有客觀規律性的存在,並宣吿可能「創造」經濟法則,「改造」經濟法則。結果會怎麽樣呢?這就會使我們陷身在混亂和偶然性的王國,使我們處在奴隸似地依賴於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們不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簡直會在這偶然性的混亂中瞎摸。
這就會使我們取消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因爲不承認客觀的規律性,不研究這些規律性,科學是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取消了科學,我們就沒有可能預見國內經濟生活中事變的進程,卽沒有可能把那怕是最起碼的經濟領導工作做好。
歸根到底,我們就會受那班决心「消滅」經濟發展法則、不理解和不考慮客觀規律性而來「創造」新法則的「經濟」冒險主義者任意擺佈。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裡所提供的馬克思主義對這問題的經典說法:
「社會的力量如同自然力一樣,在我們沒有認識它們和重視它們以前,發生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壞的作用。可是我們一經認識了它們,研究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末,我們就能完全作主,使它們愈來愈多地服從我們的意志,並藉助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特別是指現代强大的生產力。在我們還執拗地拒絕了解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的時候——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維護者是反對這種了解的,——生產力總是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它總是支配着我們,正像在上面詳細敍述過的那樣。可是,當生產力的本性一被了解之後,它就會在聯合起來了的生產者手中,由惡魔似的支配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差別,正像雷電中帶破壞性的電力與電報機上和弧光燈中馴服的電力之間的差別一樣,也正像火災的火與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差別一樣。當人們能按照現代生產力的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處理它的時候,生產中的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便會由生產中的社會的有計劃調節來代替,這種生產是爲了滿足整個社會以及社會中每個成員的需要的。那時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將由新的佔存方式來代替。在資本主義佔有方式中,產品開始是奴役生產者,以後又奴役佔有者,而新的佔有方式則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爲根據的:一方面是社會直接佔有作爲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的產品,另一方面是個人直接佔有作爲生活和享樂的資料的產品。」
二、關於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
水平的辦法問題
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這當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國民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須採取些什麽辦法呢?
有些同志以爲,應該依照從前處理資本主義財產的例子乾脆把集體農莊財產收歸國有,宣佈它是全民的財產。這個建議是完全不正確的,是絕對不能採納的。集體農莊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財產,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像處理資本主義財產那樣來處理它。無論如何不能因爲集體農莊的財產不是全民的財產,就說集體農莊的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的財產。
這些同志以為,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財產轉歸國家所有,是唯一的或無論如何是最好的國有化(註)形式。這是不對的。事實上,轉歸國家所有,這並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國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國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裡關於這點所正確說過的那樣。當國家還存在的時候,轉歸國家所有,無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國有化形式。但國家並不是永世長存的。隨著社會主義的活動範圍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的擴大,國家將日漸消亡,因而把個別人的財產和個別集團的財產轉歸國家所有的問題當然也就會消失。國家一定消亡,而社會是一定留存下來的。因此,作為全民財產的承繼人的,已經不是將要消亡的國家,而是以中央經濟領導機構爲代表的社會本身。
那末,爲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應該採取什麽辦法呢?
作爲這樣來提高集體農莊所有制的基本辦法,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提議:把集中在農業機器站的基本生產工具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這樣來解除國家對農業作基本投資的負担,並達到使集體農莊自己來担負維持和發展農業機器站的費用。他們說:
「如果以爲集體農莊的投資應該主要用在集體農村的文化需要上,而對於農業生產的需要,仍舊應該由國家進行基本的大批投資,那就不正確了。因為集體農莊已有充分能力把這一負担完全承當起來,而使國家解除這一負担,豈不是更加正確些嗎?爲了在國內製造出豐富的消費品,國家在自己的投資方面還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爲了論證這一建議,建議人提出了幾個論據:
第一,援引斯大林所說生產資料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的這句話,建議人懷疑斯大林的這一論點,宣稱國家畢竟在出售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如像大鐮刀、小鐮刀之類的小農具以及小發動機等等生產資料。他們認爲,旣然國家把這些生産資料出售給集體農莊,那末國家也可以把農業機器站的機器之類的一切其他生產資料出售給集體農莊。
這一論據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國家是把小農具出售給集體農莊的,依照農業勞動組合章程和憲法,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農具和像農業機器站的機器那樣的農業基本生產資料,或者,例如,像那也是農業基本生產資料之一的土地相提並論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爲小農具絲毫也决定不了集體農莊生產的命運,可是像農業機器站的機器以及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料,在我國當前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農業的命運的。
不難理解,當斯大林說生產資料不出售給集體農莊的時候,他所指的不是小農具,而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即農業機器站的機器、土地。建議人玩弄「生產資料」這字眼,把兩種不同的東西混爲一談,他們不知不覺地碰了壁。
第二,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又引證說,在羣眾性的集體農莊運動開始的時期——一九二九年末和一九三〇年初,聯共(布)中央自己曾主張把農業機器站轉歸集體農莊所有,同時要求集體農莊在三年內償淸農業機器站的價值。他們認爲,雖然這事情當時「因為」集體農莊「貧窮」而□□了,但是現在,當集體農莊已經富裕的時候,可以囘頭來採取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的政策。
這一論據也是不能成立的。在一九三〇年初,聯共(布)中央確實决定過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當時是按照一部分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的建議,作爲試驗、作爲嘗試而通過這個决定的。爲的要在不久之後囘到這個問題上來加以審查。但頭一次檢查就表明這一决定是不妥當的。過了幾個月,卽在一九三〇年末,就把這個决定取消了。
後來集體農莊運動進一步的增長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發展,使集體農莊莊員以及領導工作人員都最後地確信,把農業的基本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中,集中在農業機器站手中,是保證集體農莊生產高速度增長的唯一方法。
我們大家都慶幸我國農業生產的巨大增長,穀物、棉花、亞麻、糖蘿蔔等等生產的增長。這種增長的源泉是什麽呢?這種增長的源泉就是現代技術,就是許許多多為這一切生產部門服務的現代化機器。這裡的問題,不僅在於一般的技術,而在於技術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須繼續日新月異地改進,舊的技術必須作廢,代之以新技術,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這樣做,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突飛猛進就是不可思議的,無論豐富的收穫,無論豐足的農產品,也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要把幾十萬架車輪式的拖拉機作廢、代之以履帶式的拖拉機,把幾萬架陳舊了的聯合機作廢,代之以新的聯合機,以及例如,爲技術作物製造新的機器,這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說,要負担幾十億的支出,這些支出非經過六年到八年之後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國的集體農莊是百萬富翁,它們負担得了這樣大的支出嗎?不,負担不了,因爲它們沒有力量負担要在六年至八年之後才能完全收囘的幾十億的費用。這種支出只有國家才負担得了,因為國家,並且只有國家才負担得起用新機器去更換舊機器所受到的這種損失,因為國家,並且只有國家才承担得起因在六年到八年之後才能收囘這筆費用而受到的這種損失。
明白這一切之後,那末要求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說,使集體農莊遭受巨大損失,使集體農莊破產,破壞農業的機械化,減低集體農莊生產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結論說,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建議把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就是向落後方面退後一步,就是企圖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
就暫且假定一下,我們接受了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建議,並着手把基本生產工具、農業機器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這會得到什麽結果呢?
第—,結果就會是集體農莊成了基本生產工具的所有者,換句話說,它們就會處於我國無論那一個企業都沒有的特殊地位,因爲大家知道,在我國,甚至國有化的企業也並不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麽理由來作爲集體農莊的這種特殊地位的根據呢,用什麽進步的、前進的理由來作爲根據呢?可不可以說,這樣的地位就會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會加快我們的社會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呢?如果說這樣的地位只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離開全民所有制更遠,不是使得接近共產主義,反而是使得遠離共產主義,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第二,結果就會是擴大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因爲巨量的農業生產工具會投進商品流通的範圍。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能不能使得我們向共產主義推進呢?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以爲如何?說它只會阻滯我們向共產主義前進,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基本錯誤,是在於他們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作用和意義,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槪他們以爲,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商品流通是不會妨礙這個事業的。這是由於不了解馬克思主義而犯的嚴重錯誤。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裡批評杜林主張的在商品流通條件下活動的「經濟公社」時,確鑿證明商品流通的□在必然要使杜林的所謂「經濟公社」去復活資本主義。大概,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是不同意這一點的。那末,他們就更站不住脚了。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從這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依照需要來分配產品的共產主義原則,是擯斥任何商品交換的,因而也擯斥把產品轉化爲商品,同時也就是把產品轉化爲價值的。
關於薩甯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建議和論據的情形,就是如此。
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歸根到底應該採取什麽步驟呢?
集體農莊不是普通的企業。集體農莊耕種的土地早已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而是全民的財產。因而,集體農莊並不是它所耕種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體農莊藉以進行工作的基本生產工具,並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而是全民的財產。因而,集體農莊不是基本生產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體農莊是合作企業,它使用自己莊員的勞動,按照勞動日把收入分配給莊員,而且集體農莊□自己年年更換的、用於生產的種籽。
試問,集體農莊究竟佔有一些什麽,它可以隨心所欲、完全自由支配的集體農莊財產是什麽?這種財產就是集體農莊的產品、集體農莊生產的產品,即穀物、肉類、油類、蔬菜、棉花、糖蘿蔔、亞麻等等,而建築物和集體農莊莊員園地中的個人副業不計在內。問題在於,這種產品的大部分、卽集體農莊生產的剩餘品,進入市場,從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統中。正是這種情況現在阻礙着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應該從這一方面展開工作,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爲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須將集體農莊生產的剩餘品從商品流通系統中排除出去,把它們列入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間的產品交換系統中。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
我們還沒有發達的產品交換制度,但是有以「換貨」為形式的農產品產品交換的萌芽。
大家知道,對植棉、種蔴、種糖蘿蔔和其他的集體農莊的產品早已實行「換貨」了。誠然,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換貨」,但總算是在「換貨」了。要順便指出:「換貨」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應該用「產品交換」來代替它。任務是在於,要使農業的一切部門中都培植這些產品交換的萌芽,並把它們發展成為產品交換的廣大系統,以便集體農莊在交出自己的產品時不僅取得貨幣,而主要是取得必要的製成品。這樣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農村的產品,所以,推行這種制度無需特別急忙,要隨着城市製成品積累的程度而定。但是應該一往直前、毫不猶豫地推行這種制度,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活動範圍。
這樣的制度旣縮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就使社會主義易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此外,它使我們有可能把集體農莊的基本財產、集體農莊生產的產品包括進全民計劃化的總的系統中。
爲了在我國現今條件下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這將是實際的和有决定意義的辦法。
這樣的制度對於集體農莊的農民是否有利呢?無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爲集體農莊農民從國家手中獲得的產品,將比在商品流通中獲得的要多得多,價錢也便宜得多。大家知道,與政府訂有產品交換(「換貨」)合同的集體農莊所獲得的利益,較之沒有訂立這種合同的集體農莊,要多得無比。如果產品交換制度推廣到全國所有的集體農莊,那末這些利益就要成為我國全體集體農莊農民都能享受的了。
約·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九月廿八日
(註)在這裡,國有化是指歸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是指歸國家政權所有。——譯者
相关人物
斯大林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