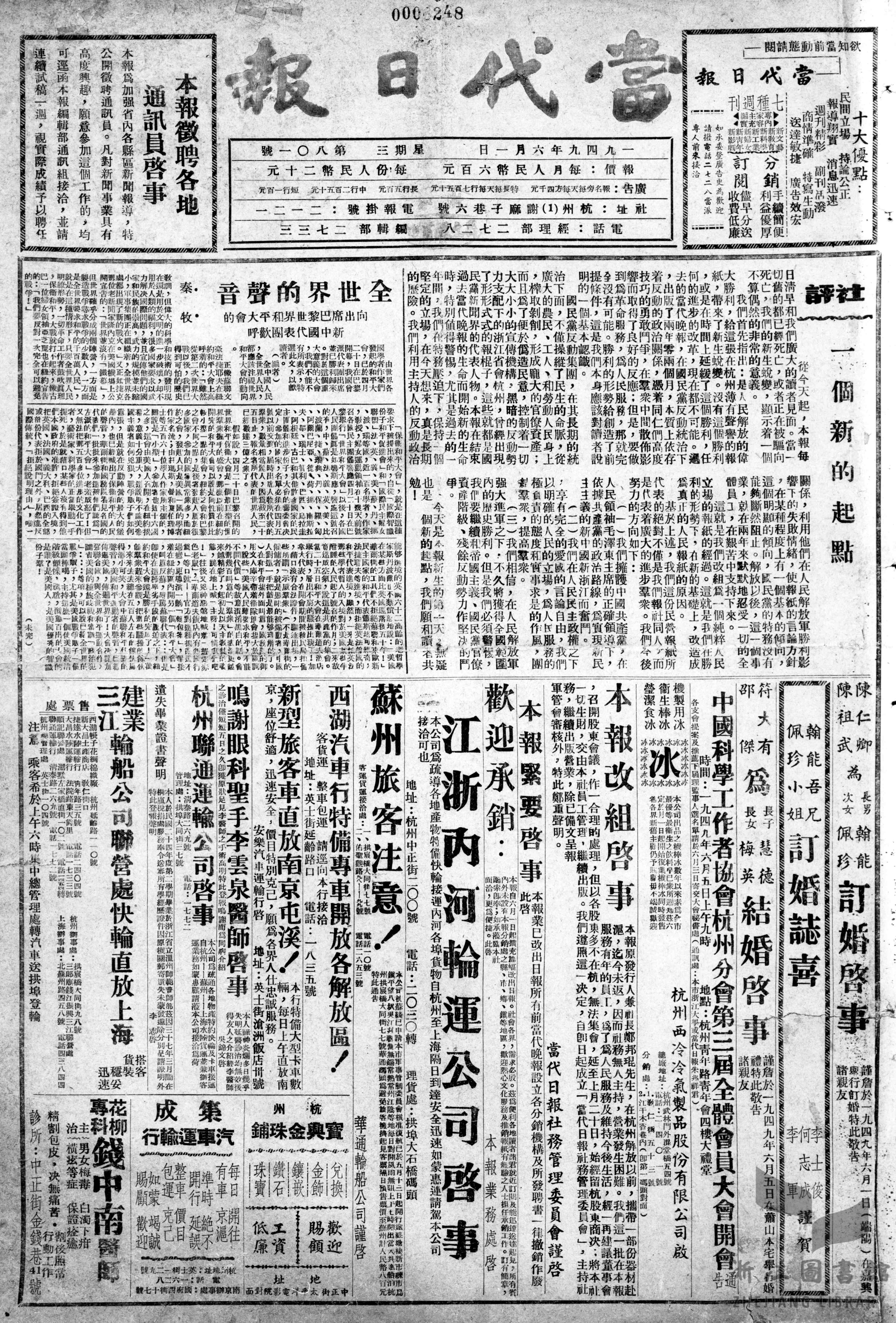内容
(續昨)
叛變了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沒有也不可能解决造成中國革命的任何問題。相反,由於比以前的反動統治者更加澈底地依靠帝國主義和更加殘酷地鎭壓革命人民,蔣介石和國民黨就使中國的民族危機更加深重了。帝國主義者對蔣介石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讓步(例如放棄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因爲他們知道把這些放在蔣介石手中和留在自己手中並無分別,但是在實質上,他們對於中國的侵略更加深入。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的上升,尤其顯著。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支配下,國民黨新軍閥的內戰和以前一樣地循環不息。工人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比以前更爲嚴重,尤其在城市中,國民黨的統治比舊軍閥的統治兇惡得多。蔣介石在叛變革命以後,已經不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了。蔣介石發展了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壟斷資本主義,即後來人們所說的官僚資本主義。所以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民族資產階級也比以前受了更多的壓迫。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八年總結當時的情勢說:「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够存在?」)這種情况,正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敢於以武力大規模進攻中國的根本原因。
蔣介石的統治雖然比以前的軍閥統治更加兇惡,但也有它的弱點。蔣介石統治的根本弱點,就在它的脫離人民和它的內部衝突。爲了鎭壓人民,蔣介石的反動國家機器是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它的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城市中,因而使城市的人民鬥爭不容易有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蔣介石不可能在全國極為廣大的農村中普遍建立强有力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各派軍閥的不斷混戰,加重了蔣介石在這
一方面的困難。尤其是在受過革命影響的農村中,農民有强烈的土地要求和組織起來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經驗,這是有利於革命而不利於反革命的。如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因爲沒有正確地領導農民解决土地問題而失敗,那麽,正確地完成前一個時期所沒有完成的農民土地鬥爭的任務,就是復興革命運動的希望所在。
在革命已經失敗,蔣介石已經建立了他的澈底反動的統治的情况下,黨的任務,就是要向人民指出繼續革命鬥爭的必要,指出恢復革命鬥爭的方法,並且領導人民加以實現。而為了這樣,黨就需要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糾正黨的領導的錯誤,並且迅速收集革命的力量,在敵人的進攻面前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和防禦。這就是說,需要將黨的組織一部分轉入反革命比較薄弱而革命比較有基礎的農村,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和游擊戰爭;一部分繼續留在城市而轉入地下,進行隱敝的活動,以便保存幹部和黨的組織,保存和積蓄羣衆的革命力量;然後,配合這兩支隊伍的鬥爭,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和弱點,爭取革命運動的復興。
黨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反共以後,緊接着就在八月七日召集緊急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澈底地糾正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並撤換了陳獨秀的領導。一九二八年七月召集的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更詳細地檢討了陳獨秀的錯誤。陳獨秀並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陳獨秀分子在此時宣稱: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由資產階級的勝利而終結,資產階級已經建立了並將鞏固它的統治,中國無產階級應當放棄革命鬥爭,轉入合法運動,以待將來舉行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分子由此走上了與托洛茨基分子結合進行反黨活動的反革命道路,因此黨就在一九二九年驅逐他們出黨。
黨在八月七日的會議上爲了挽救革命,曾號召農民進行秋收起義。毛澤東同志在會議之後就到江西西部和湖南東部一帶地區領導湖南江西的農民、工人和北伐軍各一部舉行了起義,在湖南江西邊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與敵人作戰。此外,黨還在中國的中部、南部以及其他地方組織了許多起義,包括著名的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起義。這些起義本身都失敗了,但沒有完全失敗,在起義中所組織起來的武裝部隊還留下一部分。凡是對於這一部分武裝部隊實行了正確領導的地方,那裏的革命武裝鬥爭就得到了發展。因此,在黨領導之下的革命武裝,就在幾個地方逐步地發展了起來。從此,就開始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這些部隊,就構成了後來的中國工農紅軍即現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初的來源。
但是在革命失敗的形勢下,整個黨的組織需要的是正確的退却,而不是繼續進攻;局部的武裝鬥爭,暫時也只能成爲一種特殊形式的防禦。因爲錯誤地估計當時的形勢爲革命仍在繼續高漲,拒絕承認革命的失敗,黨在瞿秋白同志的領導下,在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曾陷入「左」傾盲動主義,反對退却,要求繼續進攻,因而使保留下來的革命力量繼續受到了不少的損失。
一九二八年七月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清算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同時,也批判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第六次大會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民主革命,總的任務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農民主專政,並且規定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各項綱領。大會提出了建立紅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分配土地的任務。大會指出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但又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羣衆。這些都是第六次大會的功績。第六次大會的缺點是對於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中間階級的作用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少正確的估計;而對於黨的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別是需要將黨的工作的重點由敵人力量比較强大的城市轉移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農村這個關鍵問題,也沒有必要的認識。黨的領導工作,仍然掌握在「左」傾分子手中。第六次大會的這些缺點,曾經妨礙了黨內「左」傾錯誤的澈底糾正。
毛澤東同志沒有出席黨的第六次大會。在第六次大會上,毛澤東同志被選爲黨的中央委員。
第六次大會所沒有正確解决的問題,隨後就由毛澤東同志在實際上和理論上解决了。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領新成立的一支工農革命軍退到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井崗山區域,在那裏成立了湘贛邊區工農政府,並且着手領導農民分配土地。隨後,朱德、陳毅、林彪等同志又由廣東率領南昌起義的一支部隊,經過江西轉入湖南南部,領導當地農民的革命游擊戰爭,擴大了部隊,並在一九二八年四月與井崗山的部隊相會合,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與敵人的鬥爭中進行了多次的勝利鬥爭,以及由彭德懷同志率領的在平江起義的部隊前來會合以後,以井崗山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逐步擴大和鞏固了起來。在這個期間,黨所領導的江西、湖南、湖北、廣西等地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鬥爭,也有了發展,陸續成立了幾支紅軍和幾處革命根據地。一九二九年,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所領導的紅軍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進發,並以江西瑞金爲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開始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和他所領導進行的革命戰爭,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區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和他們所領導進行的革命戰爭,成了新時期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內容,成了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勢力,成了蔣介石反革命統治的最大威脅和全國勞動人民的最大希望。
紅軍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爲什麽是可能的呢?爲什麽是當時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内容呢?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所寫的「中國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够存在?」和一九三〇年一月所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兩篇論文中,給了理論上的答覆。在第一篇論文中,毛澤東同志指出:當時紅色政權能够存在的主要條件是五個:第一,中國的特點,即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這造成了反動統治的縫隙,給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機;第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影響的遺留;第三,全國革命形勢的繼續向前發展;第四,紅軍的存在;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確。在第二篇論文裏,毛澤東同志詳細地估計了中國紅軍戰爭的意義。毛澤東同志指出:紅軍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是「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農民鬥爭必然走向的形式」,是「半殖民地無產階級鬥爭最重要的同盟力量」和「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毛澤東同志認定:必須放手發展紅軍戰爭、發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權,「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甚大之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眞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找出了中國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敵人擊敗,暫時無法在城市中取得勝利的條件下唯一正確的發展規律,即以武裝革命的農村包圍並且最後奪取反革命佔據的城市。中國革命在後來二十年間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預見。
在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不但製定了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發展的總軌道,而且在各項具體政策方面,例如在土地革命的政策方面,在對待中間階級的政策方面,在戰勝優勢敵人的軍事戰略戰術和部隊工作方面,在農村環境和軍事環境下的黨的建設工作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創造。鑒於貧農和雇農是農村中最革命的力量,中農是堅决擁護革命的重要力量,富農的經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仍然需要保存,中小工商業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需要保護和發展,因此,毛澤東同志正確地規定了和堅决地實行了依靠貧農履農,聯合中農,保護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而僅僅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路綫。鑒於戰爭和軍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又鑒於當時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是敵强我弱,敵大我小,和敵之脫離羣衆我之聯系羣衆,因此,毛澤東同志正確地規定了紅軍必須是黨、人民政權、土地改革和其他一切地方工作的宣傳者和組織者,規定了紅軍必須在部隊中建立強大的政治工作和嚴格的羣眾紀律,規定了紅軍必須實行依靠羣衆的人民戰爭,以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作爲當時的主要戰爭形式,規定了紅軍必須實行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决戰,平時分兵以發動羣衆,戰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包圍迂迴和殲滅敵人,而這些基本原則和其他軍事原則就構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軍事路綫。由於這一切,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這個中國革命困難時期的工作,已經奠定了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主要基礎。
到一九三〇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約六萬人,江西中央區的紅軍已有三萬幾千人。在一九三〇年和稍後的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範圍已發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和廣東的海南島。紅軍的迅速發展引起蔣介石的極大的震動。一九三〇年底,蔣介石派了七個師共約十萬人圍攻中央區紅軍,結果被紅軍消滅一個整師和另半個師,蔣軍前敵總指揮被俘,一九三一年五月,蔣介石又派兵二十萬人由何應欽為總司令向中央紅軍舉行第二次圍攻,結果又被粉碎,被俘三萬多人,繳槍二萬多支。同年七月,蔣介石又發起第三次圍攻,自任總司令,隨帶英日德軍事顧問,率兵三十萬人,分三路深入中央紅軍根據地,但是結果仍然被粉碎。與此同時,在徐向前同志領導之下的先在鄂豫皖根據地後來轉移到川北根據地的紅軍,和在賀龍同志領導之下的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也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勝利。在紅軍勝利的影響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領導下,在江西寧都起義加入了紅軍。經過這些勝利,紅軍的力量就繼續發展,而新的革命形勢,也就逐漸地接近於成熟了。
正在這時,發生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開始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東北的大舉進攻。從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起就决心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看到一九二九年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以來英美等國忙於內部事務,無暇與日本爭奪中國,又看到蔣介石政府完全投降帝國主義,並依賴英美帝國主義的援助去進行反革命內部的內戰和反對工農紅軍的內戰,不敢抵抗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因此就決定首先侵略東北,然後逐步向中國本部擴張其侵略。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內迅速佔領東北全境,並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進入上海,一九三三年佔領熱河和察哈爾的北部,一九三五年佔領河北的東部。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根本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狀况。抵抗日本的進攻成爲全國人民緊急的任務和普遍的要求。工人、農民、學生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各地高漲起來。在一九二七年退出革命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時也改變了他們的政治態度,開始在政治上活躍起來,要求蔣介石政府改變政策。蔣介石政府則堅持他的對日不抵抗、對內加緊「剿共」、加緊法西斯恐怖的政策。但是甚至在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中間,也開始發生了政治上的分化。一九三二年一月國民黨的第十九路軍在上海人民反日運動的影響下,向進攻上海的日本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這個軍隊的領導者及其他一些國民黨人又在福建成立反蔣聯共的人民政府。馮玉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也與共產黨人合作在察哈爾的張家口組織民衆抗日同盟軍。
在日本進攻面前;中國共產黨首先主張武裝抵抗,並且領導了或積極參加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和東北人民的抗日游擊戰爭。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國工農紅軍宣言願在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人民民主權利和武裝民衆的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停戰議和,以便共同抗日。但是雖然如此,黨的領導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却因爲陷入了新的嚴重的「左」傾錯誤,以至不但沒有能够在日本進攻、紅軍勝利、人民抗日反蔣的有利形勢下將革命推向前進,反而使革命受到了新的挫折。
雖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及其以後種種事變的教訓,在黨的第六次大會以後,黨的領導機關仍然設在反革命中心的上海,黨的領導仍然沒有以紅軍戰爭爲中心,仍然沒有以毛澤東同志爲中心。抱着小資產階級急躁情緒、不了解紅軍戰爭的意義和規律,幻想着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舉行城市起義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繼續佔據着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至十月間,黨中央以李立三同志為首,曾經要求組織全國中心城市的總起義和全國紅軍向中心城市的總進攻。這個錯誤計劃曾經引起國民黨統治區黨的祕密組織的嚴重損失,但是在紅軍中却因受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堅决抵抗,沒有發生大的影響。一九三〇年十月,李立三同志的錯誤受到了黨的六届三中全會的糾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兩同志為首的以敎條主義為特徵的一個新的「左」傾派別,又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外衣,起來攻擊三中全會沒有糾正「立三路線」的「右傾」,並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以王明、博古為首的新的「左」傾派別,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認爲國民黨各派和各中間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進攻都是一致的,要求黨向他們一律進行「决死鬥爭」。這個「左」傾派別在紅軍戰爭的問題上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游擊戰運動戰的思想,繼續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在國民黨區城市工作的問題上,反對劉少奇同志所堅持的關於利用合法、積蓄力量的思想,繼續實行脫離多數羣衆的冒險政策。在這個錯誤的領導下,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壞,由「左」傾分子所組織的臨時中央也在一九三三年搬入中央紅軍根據地。臨時中央到達紅軍根據地後,雖然已與在紅軍中及革命根據地工作的中央委員如毛澤東同志等相匯合,組成了正式的中央機關,但是排擠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對於紅軍的領導。這樣,由紅軍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羣眾運動高漲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的復興,就被破壞了。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剛剛出賣了上海抗日戰爭的蔣介石,又以九十個師五十萬兵力組織了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第四次全面圍攻。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戰略,紅軍在這次反圍攻的戰爭中又得到了巨大的勝利。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又以一百萬兵力,舉行對紅軍的第五次圍攻,並以五十萬兵力進攻中央紅軍。在這次戰役中,紅軍因爲黨的中央實行了完全錯誤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綫和其他錯誤政策,沒有能擊破敵人的圍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退出江西根據地,進行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征。在此期間,全國其他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也遭受了「左」傾分子同樣的損害。各地紅軍,除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所領導的陝甘紅軍外,都先後退出了原来的根據地,進行了長征。
在中國紅軍長征中,黨的中央在軍事上繼續發生錯誤,使在敵人前堵後追中的紅軍數次陷入危險境地並受到極大的損失。爲了挽救在危險中的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於毛澤東同志及其他同志堅决的鬥爭,在貴州遵義舉行了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就一直在這位傑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而這就使革命的勝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證。
一九三五年十月,即在長征開始的一年以後,中央紅軍終於以超乎尋常的毅力,戰勝了軍事上的、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無數艱險,經歷了二萬五千華里的征途,越過了人跡罕到的雪山草地,達到陝西北部,與陝甘紅軍部隊相會合。任弼時、賀龍兩同志所領導的紅軍,和徐向前同志所領導的紅軍,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與中央紅軍在陝甘地區相會合。在徐向前同志所領導的紅軍中工作的張國燾,由於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曾經進行分裂和背叛黨的活動,拒絕與中央紅軍一同由川西北北上,反而强迫部隊向西康方面退縮,並非法地組織了在張國燾領導之下的另一個中央。由於毛澤東同志所採取的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由於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同志的堅忍努力,叛徒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很快地就完全失敗了,但是紅軍却因此受到了另一次很大的損失。在國民黨第五次圍攻以前,紅軍曾發展到三十萬人,但是由於黨內錯誤的領導,受到了許多的挫折,到陜北會合之後,總共已不到三萬人。但這是紅軍和黨的極可寶貴的精華。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爲安的關鍵。它使全國人民對於革命前途有了希望。它使全中國全世界相信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相信了爲着戰勝當時在中國得寸進尺的日本帝國主義,非要依靠中國共產黨不可,非要停止反共的內戰不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紅軍、陝北紅軍和由鄂豫皖北上的紅軍緊接在會合以後,就共同地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攻,大大地鞏固了陝甘革命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的聲勢。隨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向華北的進攻,由北京學生在十二月九日舉行的抗日救國大示威而開始的「一二九」運動,在全國發展起來了,廣大的人民在運動中一致地提出了黨所擬定的「停止內戰、一起抗日」的口號。革命重新走上高潮。在這個時候,需要對日本進攻中國以來的國內形勢作一次正確的分析,决定黨的政策,糾正在黨內濃厚存在着的「左」傾關門主義。這個工作,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黨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所决定的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的幫助之下,黨在八月一日所發表的號召統一戰線的宣言,特別是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陝北的會議所通過的决議,以及毛澤東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滿足了這個要求。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有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指出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可能參加抗日鬥爭而其他部份可能由動搖而中立,指出了國民黨營壘可能破裂和其中英美買辦集團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轉而被迫參加抗日,指出了長征的偉大意義以後,總結黨的任務說:「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綫。」毛澤東同志痛駁了黨內「左」傾分子提出來的反對統一戰綫的一切論據。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以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並且規定了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毛澤東同志指出: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對於不贊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資本家和他們所經營的工商業是保護的,它以工人農民爲主體,但又代表着反帝反封建的各階層人民的利益。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個統一戰線與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統一戰線的區別,是在有無堅強的共產黨和革命軍隊參加。毛澤東同志在比較兩個時期的不同時說:「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强的共產黨和堅强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據地。他們不但充當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爲堅强的台柱子,使日本人和蔣介石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台政策,或失敗主義,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這樣,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就不但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預見了中國政治的後來的發展,而且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本經驗,規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
中共中央的正確的政治路綫,迅速地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並迅速地促成了抗日戰爭的實現。紅軍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東征進入山西,在取得許多勝利以後,在五月間,向國民黨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並與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等首先實現了停戰。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劉少奇同志正確指導下,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是蔣介石仍然堅持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反動政策,繼續向紅軍進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要求聯共抗日的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迫使他停止亡國的反共內戰。中國共產黨認爲在當時的條件下,爲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應使西安事變和平解决,因此蔣介石被釋放了,國內和平乃得實現。爲了便於保持國內和平,並爲了爭取地主階級共同抗日,黨在西安事變和平解决後決定暫時停止沒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由於國內和平實現,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藉口蘆溝橋事變對中國實行新的進攻時,中國軍隊包括蔣介石的軍隊在內對於日本的進攻就實行了抵抗,全國規模的抗日戰爭就爆發了。由於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及其以後的各項正確的主張和努力,促成了國內和平和抗日戰爭的實現,就極大地提高了黨在全國人民羣衆中的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黨中央召集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討論和批准了黨在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政治路綫,並爲抗日戰爭作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
在革命脫離了危險而走向新的高漲的年份,爲了總結經驗,訓練幹部,毛澤東同志曾以極大的努力從事理論工作。在一九三六年秋,毛澤東同志寫了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總結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戰爭的經驗,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有系統地批判了「左」傾分子和右傾分子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優秀的馬克思列寧的軍事著作之一。但是這部書的意義遠超於單純的軍事問題以外。它實際上是深刻地分析了中國革命本身的規律。並且,由於它對於戰爭的勝利和失敗的根源,對於戰爭規律的認識過程和學習過程,以及戰爭的各種辯證規律,都作了根本性質的解剖,它就成了一部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在一九三七年夏,毛澤東同志又寫了他的著名的哲學的著作「實踐論」。毛澤東同志在這部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而又通俗地解說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同志這部著作在中國思想史和黨的思想工作上有極重要的價値。它是敎育人們如何正確地思想、正確地行動和正確地學習的最好的教科書。它分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爭論的哲學性質,根據無可辯駁的唯物論原理,揭露了「左」傾分子和右傾分于在認識方法上的敎條主義錯誤和經驗主義錯誤。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著作,不但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敎育的基礎,而且對於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寶庫,也作了光輝的貢獻。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黨在極端困難條件下達到政治上的成熟和推動革命的新高漲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主要地依靠毛澤東同志的努力,黨深刻地認識了軍事工作和農村工作的重要性,創造了革命軍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學會了領導革命戰爭、土地改革和各種政權工作。在這個時期,黨認識了自己的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者毛澤東同志,同時也認識了各種「左」傾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危害,並在與各種錯誤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中,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的領導。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國共合作中的右傾是主要的危害相反,在這個時期黨的領導機關所犯的主要錯誤是「左」傾;「左」傾的錯誤曾使黨和紅軍遭遇了嚴重的挫折,因而推遲了革命的新的高漲。但是無論如何,經過了各種艱難曲折鍛鍊出來並取得了豐富經驗的黨和軍隊,却構成了後來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主幹。由於上述一切,可以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對於中國革命的今天的勝利,是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準備和幹部準備。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黨渡過了極端嚴重的反動時期。在這個時期內,一方面,敵人企圖完全消滅我們黨,我們黨和敵人進行了極端艱苦、複雜和英勇的鬥爭;另一方面,黨在克服了右傾的陳獨秀機會主義之後,又受到「左」傾機會主義的幾次侵襲,使黨處於極端的危險之中。但是由於毛澤東同志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和他的異於尋常的忍耐性與遵守紀律的精神,充分圓滿地克服了黨內機會主義的錯誤,把黨從極端危險的情况中挽救出來。這樣,就使黨在渡過了十年的反動時期以後,在內外敵人的侵襲和打擊之下,在全國範圍內用革命精神教育了廣大的人民羣衆,在人民羣衆中保存了黨的革命旗幟,並保存了紅軍的基幹和一部分革命根據地,保存了黨的大批的優秀幹部和數萬黨員,積蓄了大量的革命經驗,特別是關於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經驗,用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全國規模的抗日愛國戰爭和新的國共合作。(本節完,全文未完)
叛變了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沒有也不可能解决造成中國革命的任何問題。相反,由於比以前的反動統治者更加澈底地依靠帝國主義和更加殘酷地鎭壓革命人民,蔣介石和國民黨就使中國的民族危機更加深重了。帝國主義者對蔣介石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讓步(例如放棄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因爲他們知道把這些放在蔣介石手中和留在自己手中並無分別,但是在實質上,他們對於中國的侵略更加深入。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的上升,尤其顯著。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支配下,國民黨新軍閥的內戰和以前一樣地循環不息。工人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比以前更爲嚴重,尤其在城市中,國民黨的統治比舊軍閥的統治兇惡得多。蔣介石在叛變革命以後,已經不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了。蔣介石發展了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壟斷資本主義,即後來人們所說的官僚資本主義。所以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民族資產階級也比以前受了更多的壓迫。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八年總結當時的情勢說:「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够存在?」)這種情况,正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敢於以武力大規模進攻中國的根本原因。
蔣介石的統治雖然比以前的軍閥統治更加兇惡,但也有它的弱點。蔣介石統治的根本弱點,就在它的脫離人民和它的內部衝突。爲了鎭壓人民,蔣介石的反動國家機器是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它的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城市中,因而使城市的人民鬥爭不容易有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蔣介石不可能在全國極為廣大的農村中普遍建立强有力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各派軍閥的不斷混戰,加重了蔣介石在這
一方面的困難。尤其是在受過革命影響的農村中,農民有强烈的土地要求和組織起來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經驗,這是有利於革命而不利於反革命的。如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因爲沒有正確地領導農民解决土地問題而失敗,那麽,正確地完成前一個時期所沒有完成的農民土地鬥爭的任務,就是復興革命運動的希望所在。
在革命已經失敗,蔣介石已經建立了他的澈底反動的統治的情况下,黨的任務,就是要向人民指出繼續革命鬥爭的必要,指出恢復革命鬥爭的方法,並且領導人民加以實現。而為了這樣,黨就需要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糾正黨的領導的錯誤,並且迅速收集革命的力量,在敵人的進攻面前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和防禦。這就是說,需要將黨的組織一部分轉入反革命比較薄弱而革命比較有基礎的農村,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和游擊戰爭;一部分繼續留在城市而轉入地下,進行隱敝的活動,以便保存幹部和黨的組織,保存和積蓄羣衆的革命力量;然後,配合這兩支隊伍的鬥爭,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和弱點,爭取革命運動的復興。
黨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反共以後,緊接着就在八月七日召集緊急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澈底地糾正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並撤換了陳獨秀的領導。一九二八年七月召集的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更詳細地檢討了陳獨秀的錯誤。陳獨秀並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陳獨秀分子在此時宣稱: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由資產階級的勝利而終結,資產階級已經建立了並將鞏固它的統治,中國無產階級應當放棄革命鬥爭,轉入合法運動,以待將來舉行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分子由此走上了與托洛茨基分子結合進行反黨活動的反革命道路,因此黨就在一九二九年驅逐他們出黨。
黨在八月七日的會議上爲了挽救革命,曾號召農民進行秋收起義。毛澤東同志在會議之後就到江西西部和湖南東部一帶地區領導湖南江西的農民、工人和北伐軍各一部舉行了起義,在湖南江西邊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與敵人作戰。此外,黨還在中國的中部、南部以及其他地方組織了許多起義,包括著名的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起義。這些起義本身都失敗了,但沒有完全失敗,在起義中所組織起來的武裝部隊還留下一部分。凡是對於這一部分武裝部隊實行了正確領導的地方,那裏的革命武裝鬥爭就得到了發展。因此,在黨領導之下的革命武裝,就在幾個地方逐步地發展了起來。從此,就開始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這些部隊,就構成了後來的中國工農紅軍即現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初的來源。
但是在革命失敗的形勢下,整個黨的組織需要的是正確的退却,而不是繼續進攻;局部的武裝鬥爭,暫時也只能成爲一種特殊形式的防禦。因爲錯誤地估計當時的形勢爲革命仍在繼續高漲,拒絕承認革命的失敗,黨在瞿秋白同志的領導下,在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曾陷入「左」傾盲動主義,反對退却,要求繼續進攻,因而使保留下來的革命力量繼續受到了不少的損失。
一九二八年七月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清算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同時,也批判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第六次大會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民主革命,總的任務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農民主專政,並且規定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各項綱領。大會提出了建立紅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分配土地的任務。大會指出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但又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羣衆。這些都是第六次大會的功績。第六次大會的缺點是對於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中間階級的作用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少正確的估計;而對於黨的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別是需要將黨的工作的重點由敵人力量比較强大的城市轉移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農村這個關鍵問題,也沒有必要的認識。黨的領導工作,仍然掌握在「左」傾分子手中。第六次大會的這些缺點,曾經妨礙了黨內「左」傾錯誤的澈底糾正。
毛澤東同志沒有出席黨的第六次大會。在第六次大會上,毛澤東同志被選爲黨的中央委員。
第六次大會所沒有正確解决的問題,隨後就由毛澤東同志在實際上和理論上解决了。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領新成立的一支工農革命軍退到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井崗山區域,在那裏成立了湘贛邊區工農政府,並且着手領導農民分配土地。隨後,朱德、陳毅、林彪等同志又由廣東率領南昌起義的一支部隊,經過江西轉入湖南南部,領導當地農民的革命游擊戰爭,擴大了部隊,並在一九二八年四月與井崗山的部隊相會合,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與敵人的鬥爭中進行了多次的勝利鬥爭,以及由彭德懷同志率領的在平江起義的部隊前來會合以後,以井崗山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逐步擴大和鞏固了起來。在這個期間,黨所領導的江西、湖南、湖北、廣西等地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鬥爭,也有了發展,陸續成立了幾支紅軍和幾處革命根據地。一九二九年,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所領導的紅軍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進發,並以江西瑞金爲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開始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和他所領導進行的革命戰爭,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區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和他們所領導進行的革命戰爭,成了新時期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內容,成了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勢力,成了蔣介石反革命統治的最大威脅和全國勞動人民的最大希望。
紅軍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爲什麽是可能的呢?爲什麽是當時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内容呢?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所寫的「中國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够存在?」和一九三〇年一月所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兩篇論文中,給了理論上的答覆。在第一篇論文中,毛澤東同志指出:當時紅色政權能够存在的主要條件是五個:第一,中國的特點,即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這造成了反動統治的縫隙,給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機;第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影響的遺留;第三,全國革命形勢的繼續向前發展;第四,紅軍的存在;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確。在第二篇論文裏,毛澤東同志詳細地估計了中國紅軍戰爭的意義。毛澤東同志指出:紅軍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是「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農民鬥爭必然走向的形式」,是「半殖民地無產階級鬥爭最重要的同盟力量」和「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毛澤東同志認定:必須放手發展紅軍戰爭、發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權,「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甚大之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眞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找出了中國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敵人擊敗,暫時無法在城市中取得勝利的條件下唯一正確的發展規律,即以武裝革命的農村包圍並且最後奪取反革命佔據的城市。中國革命在後來二十年間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預見。
在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不但製定了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發展的總軌道,而且在各項具體政策方面,例如在土地革命的政策方面,在對待中間階級的政策方面,在戰勝優勢敵人的軍事戰略戰術和部隊工作方面,在農村環境和軍事環境下的黨的建設工作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創造。鑒於貧農和雇農是農村中最革命的力量,中農是堅决擁護革命的重要力量,富農的經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仍然需要保存,中小工商業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需要保護和發展,因此,毛澤東同志正確地規定了和堅决地實行了依靠貧農履農,聯合中農,保護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而僅僅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路綫。鑒於戰爭和軍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又鑒於當時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是敵强我弱,敵大我小,和敵之脫離羣衆我之聯系羣衆,因此,毛澤東同志正確地規定了紅軍必須是黨、人民政權、土地改革和其他一切地方工作的宣傳者和組織者,規定了紅軍必須在部隊中建立強大的政治工作和嚴格的羣眾紀律,規定了紅軍必須實行依靠羣衆的人民戰爭,以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作爲當時的主要戰爭形式,規定了紅軍必須實行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决戰,平時分兵以發動羣衆,戰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包圍迂迴和殲滅敵人,而這些基本原則和其他軍事原則就構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軍事路綫。由於這一切,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這個中國革命困難時期的工作,已經奠定了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主要基礎。
到一九三〇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約六萬人,江西中央區的紅軍已有三萬幾千人。在一九三〇年和稍後的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範圍已發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和廣東的海南島。紅軍的迅速發展引起蔣介石的極大的震動。一九三〇年底,蔣介石派了七個師共約十萬人圍攻中央區紅軍,結果被紅軍消滅一個整師和另半個師,蔣軍前敵總指揮被俘,一九三一年五月,蔣介石又派兵二十萬人由何應欽為總司令向中央紅軍舉行第二次圍攻,結果又被粉碎,被俘三萬多人,繳槍二萬多支。同年七月,蔣介石又發起第三次圍攻,自任總司令,隨帶英日德軍事顧問,率兵三十萬人,分三路深入中央紅軍根據地,但是結果仍然被粉碎。與此同時,在徐向前同志領導之下的先在鄂豫皖根據地後來轉移到川北根據地的紅軍,和在賀龍同志領導之下的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也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勝利。在紅軍勝利的影響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領導下,在江西寧都起義加入了紅軍。經過這些勝利,紅軍的力量就繼續發展,而新的革命形勢,也就逐漸地接近於成熟了。
正在這時,發生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開始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東北的大舉進攻。從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起就决心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看到一九二九年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以來英美等國忙於內部事務,無暇與日本爭奪中國,又看到蔣介石政府完全投降帝國主義,並依賴英美帝國主義的援助去進行反革命內部的內戰和反對工農紅軍的內戰,不敢抵抗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因此就決定首先侵略東北,然後逐步向中國本部擴張其侵略。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內迅速佔領東北全境,並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進入上海,一九三三年佔領熱河和察哈爾的北部,一九三五年佔領河北的東部。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根本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狀况。抵抗日本的進攻成爲全國人民緊急的任務和普遍的要求。工人、農民、學生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各地高漲起來。在一九二七年退出革命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時也改變了他們的政治態度,開始在政治上活躍起來,要求蔣介石政府改變政策。蔣介石政府則堅持他的對日不抵抗、對內加緊「剿共」、加緊法西斯恐怖的政策。但是甚至在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中間,也開始發生了政治上的分化。一九三二年一月國民黨的第十九路軍在上海人民反日運動的影響下,向進攻上海的日本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這個軍隊的領導者及其他一些國民黨人又在福建成立反蔣聯共的人民政府。馮玉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也與共產黨人合作在察哈爾的張家口組織民衆抗日同盟軍。
在日本進攻面前;中國共產黨首先主張武裝抵抗,並且領導了或積極參加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和東北人民的抗日游擊戰爭。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國工農紅軍宣言願在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人民民主權利和武裝民衆的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停戰議和,以便共同抗日。但是雖然如此,黨的領導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却因爲陷入了新的嚴重的「左」傾錯誤,以至不但沒有能够在日本進攻、紅軍勝利、人民抗日反蔣的有利形勢下將革命推向前進,反而使革命受到了新的挫折。
雖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及其以後種種事變的教訓,在黨的第六次大會以後,黨的領導機關仍然設在反革命中心的上海,黨的領導仍然沒有以紅軍戰爭爲中心,仍然沒有以毛澤東同志爲中心。抱着小資產階級急躁情緒、不了解紅軍戰爭的意義和規律,幻想着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舉行城市起義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繼續佔據着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至十月間,黨中央以李立三同志為首,曾經要求組織全國中心城市的總起義和全國紅軍向中心城市的總進攻。這個錯誤計劃曾經引起國民黨統治區黨的祕密組織的嚴重損失,但是在紅軍中却因受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堅决抵抗,沒有發生大的影響。一九三〇年十月,李立三同志的錯誤受到了黨的六届三中全會的糾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兩同志為首的以敎條主義為特徵的一個新的「左」傾派別,又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外衣,起來攻擊三中全會沒有糾正「立三路線」的「右傾」,並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以王明、博古為首的新的「左」傾派別,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認爲國民黨各派和各中間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進攻都是一致的,要求黨向他們一律進行「决死鬥爭」。這個「左」傾派別在紅軍戰爭的問題上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游擊戰運動戰的思想,繼續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在國民黨區城市工作的問題上,反對劉少奇同志所堅持的關於利用合法、積蓄力量的思想,繼續實行脫離多數羣衆的冒險政策。在這個錯誤的領導下,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壞,由「左」傾分子所組織的臨時中央也在一九三三年搬入中央紅軍根據地。臨時中央到達紅軍根據地後,雖然已與在紅軍中及革命根據地工作的中央委員如毛澤東同志等相匯合,組成了正式的中央機關,但是排擠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對於紅軍的領導。這樣,由紅軍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羣眾運動高漲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的復興,就被破壞了。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剛剛出賣了上海抗日戰爭的蔣介石,又以九十個師五十萬兵力組織了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第四次全面圍攻。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戰略,紅軍在這次反圍攻的戰爭中又得到了巨大的勝利。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又以一百萬兵力,舉行對紅軍的第五次圍攻,並以五十萬兵力進攻中央紅軍。在這次戰役中,紅軍因爲黨的中央實行了完全錯誤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綫和其他錯誤政策,沒有能擊破敵人的圍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退出江西根據地,進行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征。在此期間,全國其他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也遭受了「左」傾分子同樣的損害。各地紅軍,除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所領導的陝甘紅軍外,都先後退出了原来的根據地,進行了長征。
在中國紅軍長征中,黨的中央在軍事上繼續發生錯誤,使在敵人前堵後追中的紅軍數次陷入危險境地並受到極大的損失。爲了挽救在危險中的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於毛澤東同志及其他同志堅决的鬥爭,在貴州遵義舉行了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就一直在這位傑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而這就使革命的勝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證。
一九三五年十月,即在長征開始的一年以後,中央紅軍終於以超乎尋常的毅力,戰勝了軍事上的、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無數艱險,經歷了二萬五千華里的征途,越過了人跡罕到的雪山草地,達到陝西北部,與陝甘紅軍部隊相會合。任弼時、賀龍兩同志所領導的紅軍,和徐向前同志所領導的紅軍,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與中央紅軍在陝甘地區相會合。在徐向前同志所領導的紅軍中工作的張國燾,由於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曾經進行分裂和背叛黨的活動,拒絕與中央紅軍一同由川西北北上,反而强迫部隊向西康方面退縮,並非法地組織了在張國燾領導之下的另一個中央。由於毛澤東同志所採取的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由於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同志的堅忍努力,叛徒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很快地就完全失敗了,但是紅軍却因此受到了另一次很大的損失。在國民黨第五次圍攻以前,紅軍曾發展到三十萬人,但是由於黨內錯誤的領導,受到了許多的挫折,到陜北會合之後,總共已不到三萬人。但這是紅軍和黨的極可寶貴的精華。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爲安的關鍵。它使全國人民對於革命前途有了希望。它使全中國全世界相信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相信了爲着戰勝當時在中國得寸進尺的日本帝國主義,非要依靠中國共產黨不可,非要停止反共的內戰不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紅軍、陝北紅軍和由鄂豫皖北上的紅軍緊接在會合以後,就共同地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攻,大大地鞏固了陝甘革命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的聲勢。隨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向華北的進攻,由北京學生在十二月九日舉行的抗日救國大示威而開始的「一二九」運動,在全國發展起來了,廣大的人民在運動中一致地提出了黨所擬定的「停止內戰、一起抗日」的口號。革命重新走上高潮。在這個時候,需要對日本進攻中國以來的國內形勢作一次正確的分析,决定黨的政策,糾正在黨內濃厚存在着的「左」傾關門主義。這個工作,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黨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所决定的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的幫助之下,黨在八月一日所發表的號召統一戰線的宣言,特別是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陝北的會議所通過的决議,以及毛澤東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滿足了這個要求。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有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指出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可能參加抗日鬥爭而其他部份可能由動搖而中立,指出了國民黨營壘可能破裂和其中英美買辦集團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轉而被迫參加抗日,指出了長征的偉大意義以後,總結黨的任務說:「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綫。」毛澤東同志痛駁了黨內「左」傾分子提出來的反對統一戰綫的一切論據。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以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並且規定了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毛澤東同志指出: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對於不贊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資本家和他們所經營的工商業是保護的,它以工人農民爲主體,但又代表着反帝反封建的各階層人民的利益。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個統一戰線與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統一戰線的區別,是在有無堅強的共產黨和革命軍隊參加。毛澤東同志在比較兩個時期的不同時說:「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强的共產黨和堅强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據地。他們不但充當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爲堅强的台柱子,使日本人和蔣介石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台政策,或失敗主義,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這樣,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就不但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預見了中國政治的後來的發展,而且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本經驗,規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
中共中央的正確的政治路綫,迅速地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並迅速地促成了抗日戰爭的實現。紅軍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東征進入山西,在取得許多勝利以後,在五月間,向國民黨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並與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等首先實現了停戰。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劉少奇同志正確指導下,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是蔣介石仍然堅持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反動政策,繼續向紅軍進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要求聯共抗日的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迫使他停止亡國的反共內戰。中國共產黨認爲在當時的條件下,爲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應使西安事變和平解决,因此蔣介石被釋放了,國內和平乃得實現。爲了便於保持國內和平,並爲了爭取地主階級共同抗日,黨在西安事變和平解决後決定暫時停止沒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由於國內和平實現,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藉口蘆溝橋事變對中國實行新的進攻時,中國軍隊包括蔣介石的軍隊在內對於日本的進攻就實行了抵抗,全國規模的抗日戰爭就爆發了。由於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及其以後的各項正確的主張和努力,促成了國內和平和抗日戰爭的實現,就極大地提高了黨在全國人民羣衆中的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黨中央召集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討論和批准了黨在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政治路綫,並爲抗日戰爭作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
在革命脫離了危險而走向新的高漲的年份,爲了總結經驗,訓練幹部,毛澤東同志曾以極大的努力從事理論工作。在一九三六年秋,毛澤東同志寫了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總結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戰爭的經驗,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有系統地批判了「左」傾分子和右傾分子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優秀的馬克思列寧的軍事著作之一。但是這部書的意義遠超於單純的軍事問題以外。它實際上是深刻地分析了中國革命本身的規律。並且,由於它對於戰爭的勝利和失敗的根源,對於戰爭規律的認識過程和學習過程,以及戰爭的各種辯證規律,都作了根本性質的解剖,它就成了一部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在一九三七年夏,毛澤東同志又寫了他的著名的哲學的著作「實踐論」。毛澤東同志在這部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而又通俗地解說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同志這部著作在中國思想史和黨的思想工作上有極重要的價値。它是敎育人們如何正確地思想、正確地行動和正確地學習的最好的教科書。它分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爭論的哲學性質,根據無可辯駁的唯物論原理,揭露了「左」傾分子和右傾分于在認識方法上的敎條主義錯誤和經驗主義錯誤。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著作,不但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敎育的基礎,而且對於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寶庫,也作了光輝的貢獻。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黨在極端困難條件下達到政治上的成熟和推動革命的新高漲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主要地依靠毛澤東同志的努力,黨深刻地認識了軍事工作和農村工作的重要性,創造了革命軍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學會了領導革命戰爭、土地改革和各種政權工作。在這個時期,黨認識了自己的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者毛澤東同志,同時也認識了各種「左」傾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危害,並在與各種錯誤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中,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的領導。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國共合作中的右傾是主要的危害相反,在這個時期黨的領導機關所犯的主要錯誤是「左」傾;「左」傾的錯誤曾使黨和紅軍遭遇了嚴重的挫折,因而推遲了革命的新的高漲。但是無論如何,經過了各種艱難曲折鍛鍊出來並取得了豐富經驗的黨和軍隊,却構成了後來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主幹。由於上述一切,可以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對於中國革命的今天的勝利,是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準備和幹部準備。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黨渡過了極端嚴重的反動時期。在這個時期內,一方面,敵人企圖完全消滅我們黨,我們黨和敵人進行了極端艱苦、複雜和英勇的鬥爭;另一方面,黨在克服了右傾的陳獨秀機會主義之後,又受到「左」傾機會主義的幾次侵襲,使黨處於極端的危險之中。但是由於毛澤東同志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和他的異於尋常的忍耐性與遵守紀律的精神,充分圓滿地克服了黨內機會主義的錯誤,把黨從極端危險的情况中挽救出來。這樣,就使黨在渡過了十年的反動時期以後,在內外敵人的侵襲和打擊之下,在全國範圍內用革命精神教育了廣大的人民羣衆,在人民羣衆中保存了黨的革命旗幟,並保存了紅軍的基幹和一部分革命根據地,保存了黨的大批的優秀幹部和數萬黨員,積蓄了大量的革命經驗,特別是關於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經驗,用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全國規模的抗日愛國戰爭和新的國共合作。(本節完,全文未完)
相关机构
中国共产党
相关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