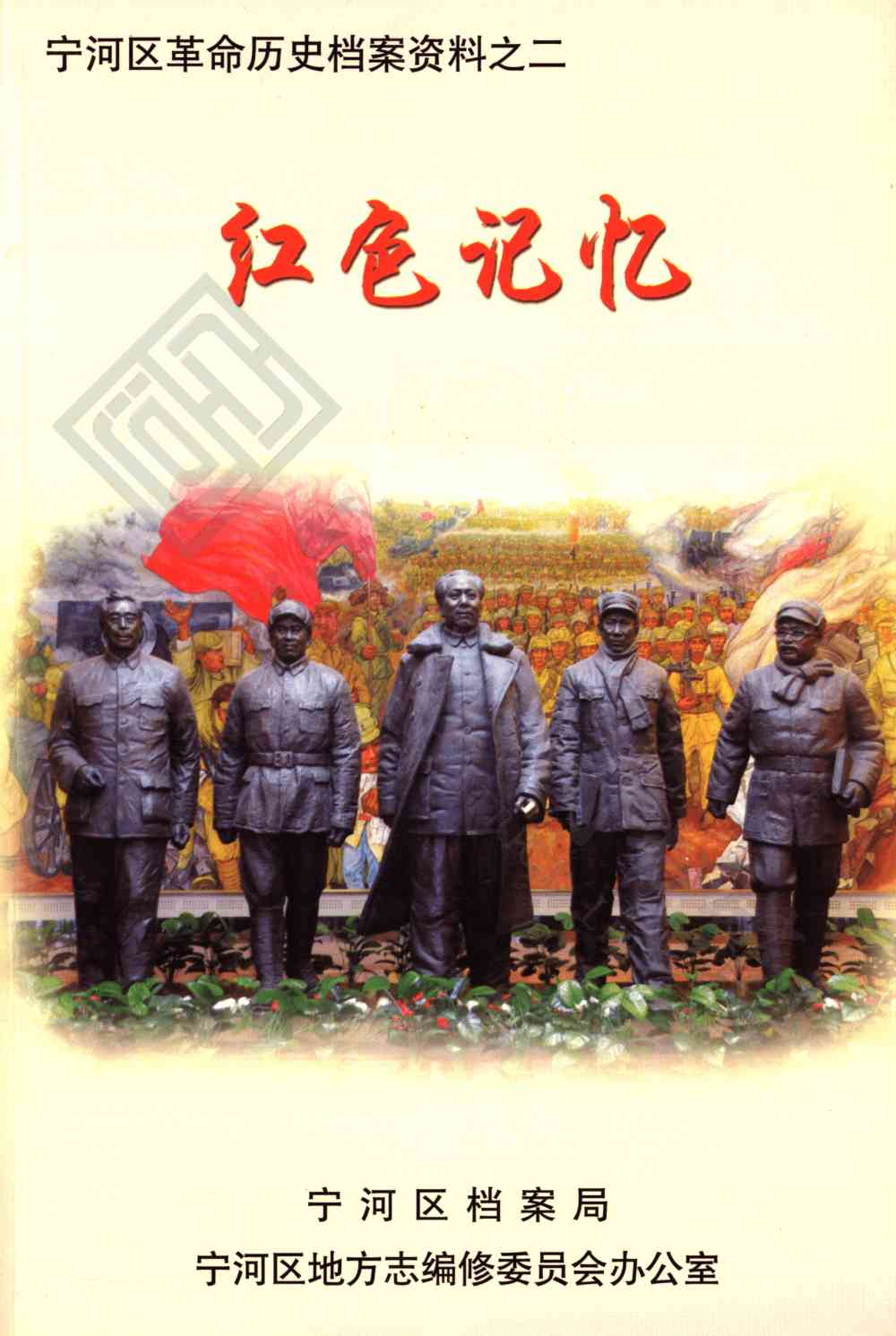内容
1952年1月,即军教导团学习结束一月之后,新兵到达丹东,兵源主要来自四川。我带着战士们从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境内。此时,每个战士的冬装已配发到位,除枪支弹药外,一人一件雨衣,一床被子,携带7天的干粮。入朝以后,为防止敌机袭击,我们白天宿营,晚上行军,不仅如此,从国内入朝的运输车队也是昼伏夜行,即使夜间行车也不准开灯,实在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也只能在没有敌机的时候迅速打开车灯照一下立即关闭,实际上基本是在摸黑行驶。从鸭绿江到“三八线”,无论白天黑夜,经常会出现敌机投弹、扫射,晚上则是先投照明弹,天空亮的如同白天,然后向发现的目标投弹、射击,一路上到处可见被炸毁的车辆和翻下山沟的汽车。为及早发现来袭的敌机,除了有专门的雷达监测外,在我们部队行军的沿途每个山头都设有防空哨,一旦发现敌机,迅速鸣枪报警,一层一层往下传,告知行军的部队和运输车队隐蔽,躲避敌机的袭击。
从进入朝鲜的第一天起,天天晚上下雨,战士们的行李也完全浸湿,行走起来更加困难,黑夜中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还要跑步跟上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和新兵战士到达前线,团里派我到五连任排长。乘着天黑,我冒着炮火进人五连阵地后才知道,连里刚刚打了一场恶仗,伤亡极大,连长、指导员流着泪向我诉说战斗的激烈和朝夕相处战友的牺牲经过。我看到坑道里到处是烈士的遗体和伤病员,枪支和手榴弹挂在石壁上,被鲜血浸染的痕迹历历在目,可见战斗是多么的惨烈悲壮。由于伤亡惨重,几天后,我连撤出阵地补充兵员、休整、练兵,阵地由其他部队接防。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部队进行了5次战役,共歼敌24万多,将防线牢牢地控制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1951年6月,我部奉命开赴开城板门店的余龙里接收防务。撤下的友邻部队将阵地移交我们时,各种基础设施基本俱备,各班排住的山洞、连部、伙房都已掏好,我们按连排班建制对应接防。不久上级任命我为八连副指导员,我自知自己文化水平低,担任副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难于胜任,于是反复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想法,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后,尊重了我本人的意见,不久让我改任八连副连长。此时的“三八线”白天炮弹轰炸不断,我们就在山洞里躲炮火,猛烈的炮火震得山洞内的石子哗哗往下掉。天一下雨,山洞里还渗漏雨,只好用雨布遮盖。晚上出去挖掘、修整工事,我们挖,对面山上的敌人也在挖,相互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有时双方还互相喊话,搞政治攻势,要对方投降,旨在瓦解、动摇对方军心。由于敌人喊的是外语,我们又听不懂,只好由他们去白费劲,而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对面的敌人也搞不清歌词的含义就跟着瞎唱。从我们接防板门店余龙里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中朝军队按照“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以阵地战为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配合停战谈判,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整体性攻防战役很少发生。
1951年下半年,我军主要是在“三八线”附近,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韩军队的局部进攻。为配合停战谈判,我部对开城附近的红山包实施过3次攻击,敌我双方反复争夺,互有伤亡。那时,我们都知道,双方谈判的条件取决于战场实力的较量,我们在战场上打得好,谈判桌上就有了主动、有了资格,因此,每次双方谈判的情况,上级都及时向我们基层部队传达,以鼓舞战士们不怕敌人、勇猛作战的信心和士气。
坚守坑道。1952年春,“联合国军”对中朝提出的中朝战俘全部遣返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迫使停战谈判陷人僵局。对此,毛主席讲我们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打持久战。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进行以坑道工事为主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战式防御体系建设,具体说就是全军挖坑道,有的驻防部队甚至把整个山都挖空了。
当时的朝鲜战场,挖坑道则是相当艰苦的工程。首先是用钢钎在岩石上打洞装炸药实施爆破,而钢钎头部磨秃之后需要在钢錾上用铁锤再打尖锐,铁锤和钢钎都从国内运来,但钢錾却极少,许多战士便去找敌人投掷的臭弹,然后卸下弹头做錾子使用,在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将臭弹引爆,有些战士因此而牺牲。为此上级专门下达命令,任何单位都不准再找敌人的臭弹,不能为了赶进度而让战士付出生命代价。我连因为这种情况牺牲了一名战士,团领导多次在营连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连长和指导员,要求各单位干部带头,全力爱护战士的生命,两位连首长反复检讨才过关。以后我们虽然也为坑道进度下指标、提要求,但在操作技术和方法上却慎重了许多。团首长批评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各连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部队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志愿军各部都在抢挖坑道,做长期作战的准备,因此,每个部队的师团营连排班都有掘进任务,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互相展开坑道掘进竞赛,因为有了坑道,就有了长期作战的基础。坑道既能屯兵,又能储存弹药和其他物资,遇到敌机投弹或敌人炮击时,战士们就可以躲进坑道,敌机走了,炮击停了,战士们则可以出来进入工事,打击敌人。这种作战模式有效地扼制了敌人大规模的进攻,保存了我军的实力,避免了因敌机轰炸和炮击造成的兵员伤亡。以坑道为依托,志愿军不断组织小规模的攻击战,夺取敌军阵地,歼灭小股敌军,给美韩军队造成极大的消耗。有一次,团部下令抓几个俘虏,而且要求必须抓活的,接到任务后我们都非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不久,接到前位哨的电话说敌人来了,我们迅速派了支小股部队把敌人引入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地带,以两个排的兵力从两面迂回包抄实施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来不及逃跑的就躺在地上装死。连长起初感到很失望,以为都打死了,让我们把死的也都通通弄回来,结果一检查还真有几个活的,可把连长高兴坏了,全连战士更是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们把俘虏押送到团部,算是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种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停战协定签字。
中朝友谊。从入朝一开始,为了便于和朝鲜老百姓相互交流,增进感情,我们每人发一本汉朝对照的小册子,开始学说朝鲜话,至今仍然记得一些单词:同志叫“东木”,女同志叫“咬森东木”,头发叫“毛里”,爷爷叫“阿拉巴吉”,男孩叫“阿登”,烟叫“坦白”,男子称“阿巴吉”,年龄大些的妇女叫“阿妈妮”,年轻些的大嫂叫“阿斯妈妮”。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非常热情友好,往往冒着炮火头顶着各种水果到前线慰问我们。在驻地吃饭时候,老百姓都会用一只大铜碗给我们盛上朝鲜特有的酸辣菜。1953年春节,我们换防后住在西海岸,朝鲜当地政府和百姓请志愿军吃饭,每家去几个志愿军代表,大家一起包饺子、喝米酒、开座谈会、唱歌跳舞,还相互征求意见,气氛非常热闹融洽。志愿军则用祖国内地运来的花生、白酒和猪肉招待朝鲜同志和百姓。双方彼此尊重,坦诚相见,共商歼敌之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浓浓情意和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决心、信心。
业余生活。在朝鲜一年零七个月的日子里,和战友们经历了血与火、冰与雪、生与死的人生考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锻炼了不怕死的坚强意志,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中提升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培养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对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时的生活、战斗环境虽然贫乏而残酷,但战士们在精神上却异常的乐观。战斗之余,有些战士用罐头盒自制乐器,有些战士用弹壳自制工艺品,有的讲故事,有的写家信,有的相互交流作战经验,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做的事,业余生活虽然单一却不单调。对于每天在头顶出现的敌机,同志们也给它们各自取了幽默而易记的绰号。把携带重磅炸弹的轰炸机叫做“油条子”,把贼头鼠脑、出没无常的侦察机称作“老病号”,把时而降低、时而爬高的战斗机叫作“儿童机”,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面对艰苦的作战环境和疯狂的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停战前后。1953年7月27日,面对中朝军队的顽强抗击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协定正式生效之前,双方都尽最大能量将炮弹倾泻到对方阵地,真是炮火连天、震天动地,板门店附近的村庄漆黑一片。至夜晚12时,双方炮击戛然而止,一时间,夜晚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这种寂静只停留了几分钟后,双方阵地欢呼起来,周围村庄的灯瞬间也亮了起来,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载歌载舞跳起传统的民族舞蹈,我们大家全都涌出坑道,站在山坡上欢呼来之不易的胜利。停战后,开城南北出现大量部队,共同的任务是在各自防区修建简易飞机场,为双方谈判代表相互接触、及时谈判提供快捷通道。我们和朝鲜军民合作,在开城西南方用推土机将小山包推平,战士们每人用一个小筐盛土,抬到低处将稻田垫平,形成简易跑道。机场的停机坪、调度楼等地面建筑都是用国内运去的木板搭建的。由此可见,抗美援朝中,我们志愿军在前方打仗,祖国人民为保障前方物资供应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那时新中国才刚刚建立,各项事业都处在百废待兴状态,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机场修好之后,我们在朝鲜过了八月十五,我所在部队开始准备撤回国内。撤军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根据签署的协定,双方要将在朝参战部队和番号公布之后报对方监督撤军情况。可能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在公布范围,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麻烦,我部最早撤出朝鲜。我们是从朝鲜的西海岸坐闷罐车回国的,为了防止暴露目标,给对方以口舌,途中始终没有停车。列车进入国内后,沿途也没有组织群众欢迎,个别停车点只有地方党政军领导上车表达慰问,我们乘坐的火车直接到达柴沟堡。对于凯旋的志愿军,全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热情,各省市纷纷组织慰问团,带着本省市最好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到部队驻地开展慰问活动。从回国之日起,几乎每天都有慰问团前来慰问,放电影、唱戏曲、耍杂技、演歌舞,慰问活动丰富多彩,演出的节目都是最高水平、最吸引人的。那些日子我们天天晚上看电影、看节目,慰问活动一直持续到当年的深秋,由于部队冬装还未配发,战士们穿的是夏装,晚上天气又冷,大家虽然十分喜欢晚上看电影、看节目,但饱了眼福,身体却冷的受不了。部队首长考虑到战士们的实际情况,经反复说明,婉言谢绝了一些慰问团和慰问活动,慰问活动才逐渐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对“最可爱的人”的巨大热情。抗美援朝结束后,我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臣奖章,祖国为我颁发和平纪念章一枚。
从进入朝鲜的第一天起,天天晚上下雨,战士们的行李也完全浸湿,行走起来更加困难,黑夜中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还要跑步跟上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和新兵战士到达前线,团里派我到五连任排长。乘着天黑,我冒着炮火进人五连阵地后才知道,连里刚刚打了一场恶仗,伤亡极大,连长、指导员流着泪向我诉说战斗的激烈和朝夕相处战友的牺牲经过。我看到坑道里到处是烈士的遗体和伤病员,枪支和手榴弹挂在石壁上,被鲜血浸染的痕迹历历在目,可见战斗是多么的惨烈悲壮。由于伤亡惨重,几天后,我连撤出阵地补充兵员、休整、练兵,阵地由其他部队接防。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部队进行了5次战役,共歼敌24万多,将防线牢牢地控制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1951年6月,我部奉命开赴开城板门店的余龙里接收防务。撤下的友邻部队将阵地移交我们时,各种基础设施基本俱备,各班排住的山洞、连部、伙房都已掏好,我们按连排班建制对应接防。不久上级任命我为八连副指导员,我自知自己文化水平低,担任副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难于胜任,于是反复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想法,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后,尊重了我本人的意见,不久让我改任八连副连长。此时的“三八线”白天炮弹轰炸不断,我们就在山洞里躲炮火,猛烈的炮火震得山洞内的石子哗哗往下掉。天一下雨,山洞里还渗漏雨,只好用雨布遮盖。晚上出去挖掘、修整工事,我们挖,对面山上的敌人也在挖,相互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有时双方还互相喊话,搞政治攻势,要对方投降,旨在瓦解、动摇对方军心。由于敌人喊的是外语,我们又听不懂,只好由他们去白费劲,而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对面的敌人也搞不清歌词的含义就跟着瞎唱。从我们接防板门店余龙里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中朝军队按照“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以阵地战为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配合停战谈判,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整体性攻防战役很少发生。
1951年下半年,我军主要是在“三八线”附近,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韩军队的局部进攻。为配合停战谈判,我部对开城附近的红山包实施过3次攻击,敌我双方反复争夺,互有伤亡。那时,我们都知道,双方谈判的条件取决于战场实力的较量,我们在战场上打得好,谈判桌上就有了主动、有了资格,因此,每次双方谈判的情况,上级都及时向我们基层部队传达,以鼓舞战士们不怕敌人、勇猛作战的信心和士气。
坚守坑道。1952年春,“联合国军”对中朝提出的中朝战俘全部遣返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迫使停战谈判陷人僵局。对此,毛主席讲我们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打持久战。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进行以坑道工事为主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战式防御体系建设,具体说就是全军挖坑道,有的驻防部队甚至把整个山都挖空了。
当时的朝鲜战场,挖坑道则是相当艰苦的工程。首先是用钢钎在岩石上打洞装炸药实施爆破,而钢钎头部磨秃之后需要在钢錾上用铁锤再打尖锐,铁锤和钢钎都从国内运来,但钢錾却极少,许多战士便去找敌人投掷的臭弹,然后卸下弹头做錾子使用,在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将臭弹引爆,有些战士因此而牺牲。为此上级专门下达命令,任何单位都不准再找敌人的臭弹,不能为了赶进度而让战士付出生命代价。我连因为这种情况牺牲了一名战士,团领导多次在营连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连长和指导员,要求各单位干部带头,全力爱护战士的生命,两位连首长反复检讨才过关。以后我们虽然也为坑道进度下指标、提要求,但在操作技术和方法上却慎重了许多。团首长批评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各连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部队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志愿军各部都在抢挖坑道,做长期作战的准备,因此,每个部队的师团营连排班都有掘进任务,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互相展开坑道掘进竞赛,因为有了坑道,就有了长期作战的基础。坑道既能屯兵,又能储存弹药和其他物资,遇到敌机投弹或敌人炮击时,战士们就可以躲进坑道,敌机走了,炮击停了,战士们则可以出来进入工事,打击敌人。这种作战模式有效地扼制了敌人大规模的进攻,保存了我军的实力,避免了因敌机轰炸和炮击造成的兵员伤亡。以坑道为依托,志愿军不断组织小规模的攻击战,夺取敌军阵地,歼灭小股敌军,给美韩军队造成极大的消耗。有一次,团部下令抓几个俘虏,而且要求必须抓活的,接到任务后我们都非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不久,接到前位哨的电话说敌人来了,我们迅速派了支小股部队把敌人引入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地带,以两个排的兵力从两面迂回包抄实施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来不及逃跑的就躺在地上装死。连长起初感到很失望,以为都打死了,让我们把死的也都通通弄回来,结果一检查还真有几个活的,可把连长高兴坏了,全连战士更是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们把俘虏押送到团部,算是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种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停战协定签字。
中朝友谊。从入朝一开始,为了便于和朝鲜老百姓相互交流,增进感情,我们每人发一本汉朝对照的小册子,开始学说朝鲜话,至今仍然记得一些单词:同志叫“东木”,女同志叫“咬森东木”,头发叫“毛里”,爷爷叫“阿拉巴吉”,男孩叫“阿登”,烟叫“坦白”,男子称“阿巴吉”,年龄大些的妇女叫“阿妈妮”,年轻些的大嫂叫“阿斯妈妮”。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非常热情友好,往往冒着炮火头顶着各种水果到前线慰问我们。在驻地吃饭时候,老百姓都会用一只大铜碗给我们盛上朝鲜特有的酸辣菜。1953年春节,我们换防后住在西海岸,朝鲜当地政府和百姓请志愿军吃饭,每家去几个志愿军代表,大家一起包饺子、喝米酒、开座谈会、唱歌跳舞,还相互征求意见,气氛非常热闹融洽。志愿军则用祖国内地运来的花生、白酒和猪肉招待朝鲜同志和百姓。双方彼此尊重,坦诚相见,共商歼敌之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浓浓情意和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决心、信心。
业余生活。在朝鲜一年零七个月的日子里,和战友们经历了血与火、冰与雪、生与死的人生考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锻炼了不怕死的坚强意志,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中提升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培养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对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时的生活、战斗环境虽然贫乏而残酷,但战士们在精神上却异常的乐观。战斗之余,有些战士用罐头盒自制乐器,有些战士用弹壳自制工艺品,有的讲故事,有的写家信,有的相互交流作战经验,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做的事,业余生活虽然单一却不单调。对于每天在头顶出现的敌机,同志们也给它们各自取了幽默而易记的绰号。把携带重磅炸弹的轰炸机叫做“油条子”,把贼头鼠脑、出没无常的侦察机称作“老病号”,把时而降低、时而爬高的战斗机叫作“儿童机”,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面对艰苦的作战环境和疯狂的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停战前后。1953年7月27日,面对中朝军队的顽强抗击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协定正式生效之前,双方都尽最大能量将炮弹倾泻到对方阵地,真是炮火连天、震天动地,板门店附近的村庄漆黑一片。至夜晚12时,双方炮击戛然而止,一时间,夜晚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这种寂静只停留了几分钟后,双方阵地欢呼起来,周围村庄的灯瞬间也亮了起来,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载歌载舞跳起传统的民族舞蹈,我们大家全都涌出坑道,站在山坡上欢呼来之不易的胜利。停战后,开城南北出现大量部队,共同的任务是在各自防区修建简易飞机场,为双方谈判代表相互接触、及时谈判提供快捷通道。我们和朝鲜军民合作,在开城西南方用推土机将小山包推平,战士们每人用一个小筐盛土,抬到低处将稻田垫平,形成简易跑道。机场的停机坪、调度楼等地面建筑都是用国内运去的木板搭建的。由此可见,抗美援朝中,我们志愿军在前方打仗,祖国人民为保障前方物资供应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那时新中国才刚刚建立,各项事业都处在百废待兴状态,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机场修好之后,我们在朝鲜过了八月十五,我所在部队开始准备撤回国内。撤军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根据签署的协定,双方要将在朝参战部队和番号公布之后报对方监督撤军情况。可能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在公布范围,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麻烦,我部最早撤出朝鲜。我们是从朝鲜的西海岸坐闷罐车回国的,为了防止暴露目标,给对方以口舌,途中始终没有停车。列车进入国内后,沿途也没有组织群众欢迎,个别停车点只有地方党政军领导上车表达慰问,我们乘坐的火车直接到达柴沟堡。对于凯旋的志愿军,全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热情,各省市纷纷组织慰问团,带着本省市最好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到部队驻地开展慰问活动。从回国之日起,几乎每天都有慰问团前来慰问,放电影、唱戏曲、耍杂技、演歌舞,慰问活动丰富多彩,演出的节目都是最高水平、最吸引人的。那些日子我们天天晚上看电影、看节目,慰问活动一直持续到当年的深秋,由于部队冬装还未配发,战士们穿的是夏装,晚上天气又冷,大家虽然十分喜欢晚上看电影、看节目,但饱了眼福,身体却冷的受不了。部队首长考虑到战士们的实际情况,经反复说明,婉言谢绝了一些慰问团和慰问活动,慰问活动才逐渐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对“最可爱的人”的巨大热情。抗美援朝结束后,我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臣奖章,祖国为我颁发和平纪念章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