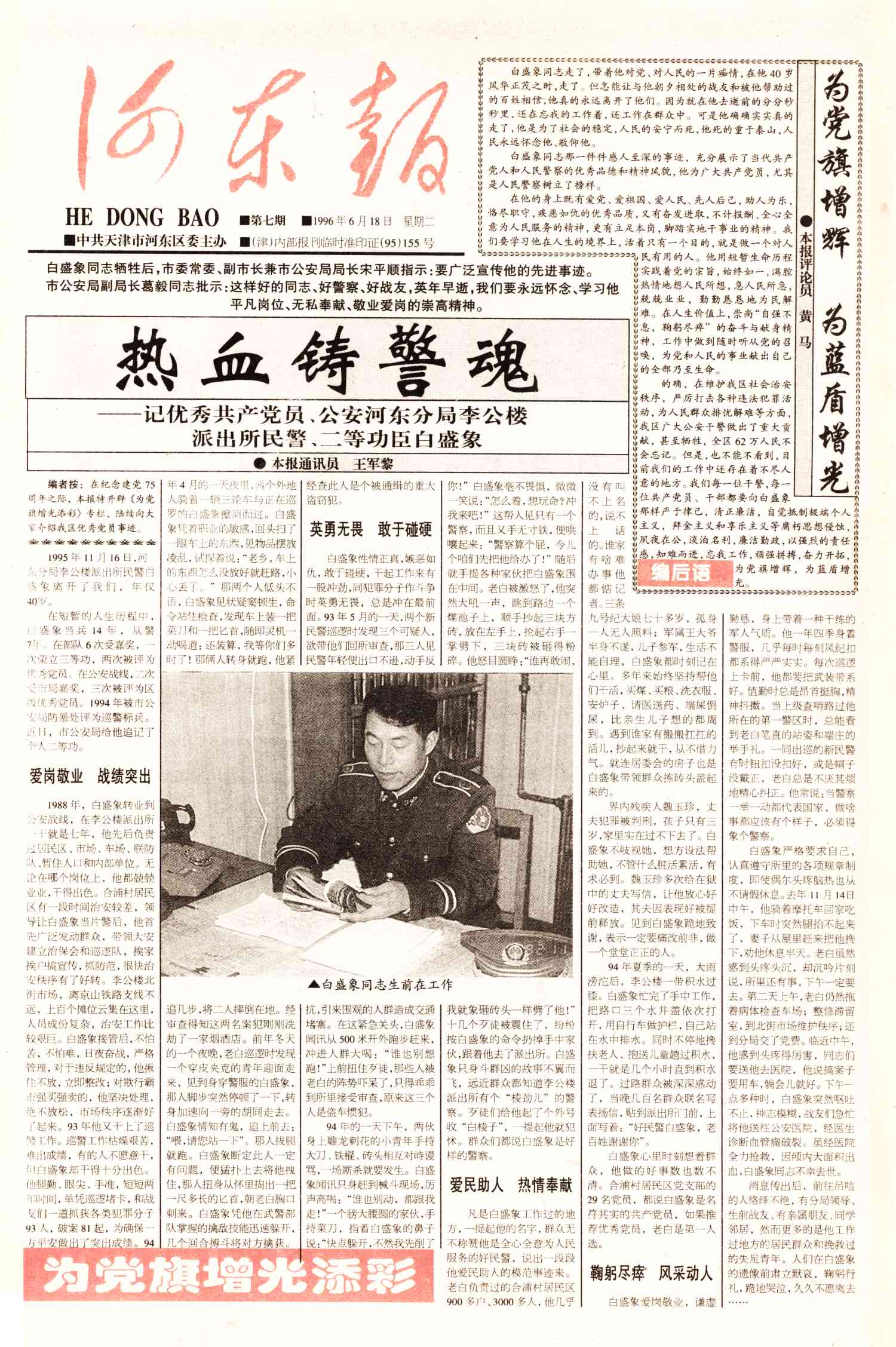内容
父亲去世后,在他的书柜中发现了一大叠照片,张张都比16开的纸还大,家人都很惊奇,不知父亲什么时候洗放了这么多大照片。我拿回了自己家中,觉得张张都好,以作永久的纪念。
近日我拿出父亲的照片再看时,萌生了一种想以照片为题写写父亲的念头。当一张张大相片摆在面前时,我却茫然了,后悔父亲在世时,没有问过他,这些照片是哪一年在哪儿拍的?但当我抱着侥幸的心理翻看那张相片的反面时,突然眼前一亮,在相背的右下脚一行小字赫然入目,上面写着拍照的时间和地点。再检查,果然张张背面都有!霍然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父亲是多么细心呀!留下的字迹又是多么弥足珍贵。
于是,那清晰的记录着一个老兵人生历程的照片摊开在我的案头——最久远的一张是父亲1953年夏天在朝鲜树林里拍的抗美援朝的留影。那是一张半身侧面照片,没有帽徽领章、志愿军的标志也不明显。可见军装的质地很粗糙,上衣的两个扣子颜色还不一样,有深有浅,身后的小树更是影影绰绰。父亲很瘦,面颊上颧骨毕露。想来战地生活一定很艰苦。
第二张是1954年夏天抗美援朝回国后在石家庄拍照的,这是一张标准的正面照片。虽没有戴帽子,但风纪口系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的双唇紧闭,浓密的黑发留着偏分头,显出风华正茂的年龄。左上方的口袋上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他的目光中透着一种凝重的沉思,或许是战火的洗礼使他过早的成熟,还是对身在异国他乡战友的深深怀念,那目光让人难忘。
第三张是1964年部队授衔后在邯郸拍的。父亲头上的黑发浓密直立,神采奕奕,充满刚毅果敢的神情,领章上两扛一星很醒目。不由使人想起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再就是1972年夏天,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留影。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父亲的军装上是红帽徽、红领章,胸前还佩带着毛泽东像章,身后是庄严的天安门城楼,照片的左前方有一支松柏在飘荡,显得庄重深沉。父亲的眼角已显出少许尾纹,看出岁月的沧桑在父亲的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记得那时的父亲只身一人在天津工作,我们兄妹跟母亲在邯郸生活。父亲差不多隔几个月才回家一趟,跟我们团聚。可从没听父亲抱怨过,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记得母亲生下大妹刚三天,部队有任务,父亲顾不上妻子女儿就赶回部队了。不巧大妹发烧,母亲只好抱着出生才几天的女儿去看病,被风吹的落下了常头疼的毛病。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母亲常有微词,而父亲则一声不吭,也不辩解。
后来父亲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地方,彩色照片开始一点点普及,然而在父亲的遗物中没有发现他洗放的一张大的便装彩照。由此我读出了父亲对部队生活的深深眷恋,因为他近三十年的青壮年时期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在心爱的军装中珍藏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有烽火连天的战斗年华,也有和平年代的富饶人生……
近日我拿出父亲的照片再看时,萌生了一种想以照片为题写写父亲的念头。当一张张大相片摆在面前时,我却茫然了,后悔父亲在世时,没有问过他,这些照片是哪一年在哪儿拍的?但当我抱着侥幸的心理翻看那张相片的反面时,突然眼前一亮,在相背的右下脚一行小字赫然入目,上面写着拍照的时间和地点。再检查,果然张张背面都有!霍然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父亲是多么细心呀!留下的字迹又是多么弥足珍贵。
于是,那清晰的记录着一个老兵人生历程的照片摊开在我的案头——最久远的一张是父亲1953年夏天在朝鲜树林里拍的抗美援朝的留影。那是一张半身侧面照片,没有帽徽领章、志愿军的标志也不明显。可见军装的质地很粗糙,上衣的两个扣子颜色还不一样,有深有浅,身后的小树更是影影绰绰。父亲很瘦,面颊上颧骨毕露。想来战地生活一定很艰苦。
第二张是1954年夏天抗美援朝回国后在石家庄拍照的,这是一张标准的正面照片。虽没有戴帽子,但风纪口系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的双唇紧闭,浓密的黑发留着偏分头,显出风华正茂的年龄。左上方的口袋上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他的目光中透着一种凝重的沉思,或许是战火的洗礼使他过早的成熟,还是对身在异国他乡战友的深深怀念,那目光让人难忘。
第三张是1964年部队授衔后在邯郸拍的。父亲头上的黑发浓密直立,神采奕奕,充满刚毅果敢的神情,领章上两扛一星很醒目。不由使人想起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再就是1972年夏天,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留影。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父亲的军装上是红帽徽、红领章,胸前还佩带着毛泽东像章,身后是庄严的天安门城楼,照片的左前方有一支松柏在飘荡,显得庄重深沉。父亲的眼角已显出少许尾纹,看出岁月的沧桑在父亲的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记得那时的父亲只身一人在天津工作,我们兄妹跟母亲在邯郸生活。父亲差不多隔几个月才回家一趟,跟我们团聚。可从没听父亲抱怨过,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记得母亲生下大妹刚三天,部队有任务,父亲顾不上妻子女儿就赶回部队了。不巧大妹发烧,母亲只好抱着出生才几天的女儿去看病,被风吹的落下了常头疼的毛病。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母亲常有微词,而父亲则一声不吭,也不辩解。
后来父亲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地方,彩色照片开始一点点普及,然而在父亲的遗物中没有发现他洗放的一张大的便装彩照。由此我读出了父亲对部队生活的深深眷恋,因为他近三十年的青壮年时期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在心爱的军装中珍藏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有烽火连天的战斗年华,也有和平年代的富饶人生……
相关人物
路超英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河东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