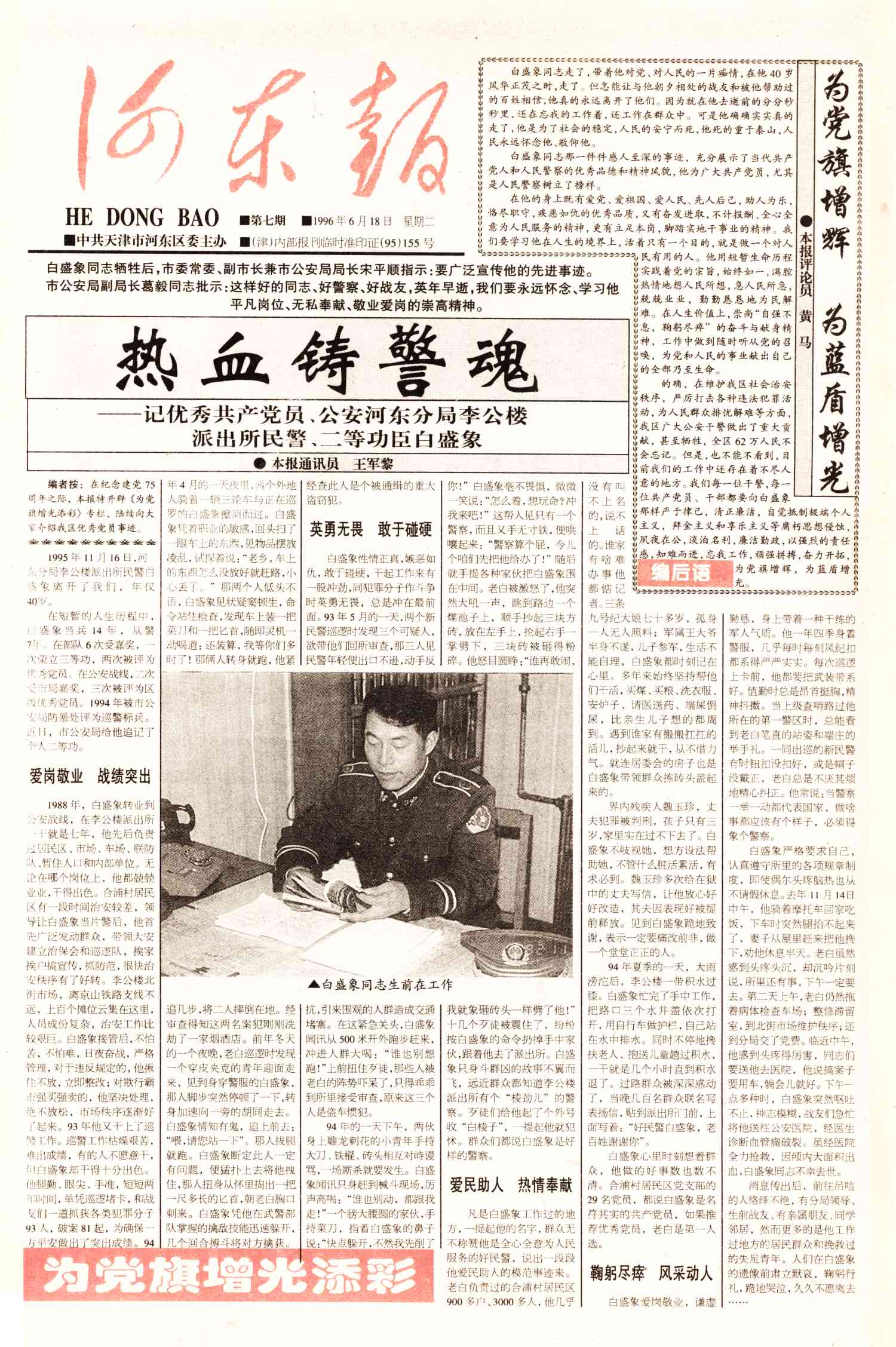内容
一
记得我5岁那年,一个盛夏的午后,比我大10多岁的姐姐带我去姑妈家。以前是不是去过,我不记得了;只是这一次留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深刻。姐姐告诉我得走着去,我问:“远吗?”她说:“远。”我又问:“我累了怎么办?”她又说:“背你。”那时,我们家住在李公楼官立胡同,走了老远,又过地道;走的都是土路,一会是上坡,一会是下岗,难走极了。她背了我两次,可我还是累。好不容易走到了姑妈家,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她说:“大直沽。”她笑了笑叮咛似地说:“记住了,这胡同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牌子,胡同口有个缝鞋的,常年在这里,人们都叫它‘修鞋胡同’,胖点人经过都不好错身,这是个死胡同,也就是实胡同,这头进得去,那头出不来。南侧仨门,尽头的瘪门就是姑妈家。以后自己来,别忘了!”
回家,听父亲说姑妈家住的地方是直沽街……大直沽早就有了,比天津卫还早呢!当时我听不明白。看着大直沽就觉着都是小破房子,道特别难走,路边稀稀啦啦有几棵小树,夹杂着摆小摊的,还有几家店铺,似乎比李公楼还穷。
自那以后,我就很少到大直沽去。
二
1969年5月,我骑车带着两个儿子从家里出来,顺着新开路,往唐家口方向走去。孩子问我:“爸爸到哪儿玩去?”“听说那边有个东风地道,没去过,咱们看看去。”
从唐家口拐向张贵庄路,径直到了东风地道。我们一起看了看,在东风地道上边,抓住过火车的时机,给两个孩子照了一张照片;又在铁道边草丛间各照了一张。过了地道往左拐,就到了大直沽的直沽街。说它是个街,可这里荒草杂生,且有个很大的脏水坑,臭气难闻。远处有几条小胡同,没什么人家,很僻静。在一个小胡同口,我打听一位摆糖摊的老人,“这附近有小花园吗?”那人说:“大直沽这片儿哪有花园呀?!但从这往东,有个第二工人文化宫,可以带孩子上那儿玩玩去!”无奈之下,去二宫玩了一会儿,人也不多,在大剧场前给孩子们照了相,然后就回家了。
三
1997年11月,危改春风吹到了李公楼,三个儿子分头去找房源,最后定下了汇贤里。孩子们开着车让我去看房,我问:“在什么地方?”小儿子说:“过了东风地道的直沽街就到了。”我一听,懵了,记忆里立刻就涌起了若干年前在这里的两次遭遇。
汽车驶过地道,还是往左一拐,咦!这里变样了,平坦的柏油路,两面楼群耸立,右侧是汇贤南里,左侧是汇贤里安教小区,再往里走就是万隆汇贤里。一大片楼房还没完工,选定之后就办了手续。1998年3月,我和老伴搬进了小区。看来,也算是缘分吧,我还是在直沽街买了房。新家,舒适的卧室,优雅的客厅,明亮的书斋,宽敞的厨房,入厕不出门,洗浴在家中,彻底改变了往日平房“一室多用”的老格局;每逢节日,一家三代十余口人在这里团聚,老年身在福中,圆了多年梦想。
岁月荏苒,转眼又是4年。居住环境洁净清幽,节日小区歌舞欢腾,早上晨练有小广场、小花园,有健身器材;出门汽车四通八达,商场超市就近购物,百姓生活需求足矣。
眼前的现实,涤荡了以往埋藏在心底对直沽街的茫然与无奈,我终于在这里安了家。真是“东风地道左邻处,一片荒芜都不见,换了人间。”
记得我5岁那年,一个盛夏的午后,比我大10多岁的姐姐带我去姑妈家。以前是不是去过,我不记得了;只是这一次留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深刻。姐姐告诉我得走着去,我问:“远吗?”她说:“远。”我又问:“我累了怎么办?”她又说:“背你。”那时,我们家住在李公楼官立胡同,走了老远,又过地道;走的都是土路,一会是上坡,一会是下岗,难走极了。她背了我两次,可我还是累。好不容易走到了姑妈家,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她说:“大直沽。”她笑了笑叮咛似地说:“记住了,这胡同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牌子,胡同口有个缝鞋的,常年在这里,人们都叫它‘修鞋胡同’,胖点人经过都不好错身,这是个死胡同,也就是实胡同,这头进得去,那头出不来。南侧仨门,尽头的瘪门就是姑妈家。以后自己来,别忘了!”
回家,听父亲说姑妈家住的地方是直沽街……大直沽早就有了,比天津卫还早呢!当时我听不明白。看着大直沽就觉着都是小破房子,道特别难走,路边稀稀啦啦有几棵小树,夹杂着摆小摊的,还有几家店铺,似乎比李公楼还穷。
自那以后,我就很少到大直沽去。
二
1969年5月,我骑车带着两个儿子从家里出来,顺着新开路,往唐家口方向走去。孩子问我:“爸爸到哪儿玩去?”“听说那边有个东风地道,没去过,咱们看看去。”
从唐家口拐向张贵庄路,径直到了东风地道。我们一起看了看,在东风地道上边,抓住过火车的时机,给两个孩子照了一张照片;又在铁道边草丛间各照了一张。过了地道往左拐,就到了大直沽的直沽街。说它是个街,可这里荒草杂生,且有个很大的脏水坑,臭气难闻。远处有几条小胡同,没什么人家,很僻静。在一个小胡同口,我打听一位摆糖摊的老人,“这附近有小花园吗?”那人说:“大直沽这片儿哪有花园呀?!但从这往东,有个第二工人文化宫,可以带孩子上那儿玩玩去!”无奈之下,去二宫玩了一会儿,人也不多,在大剧场前给孩子们照了相,然后就回家了。
三
1997年11月,危改春风吹到了李公楼,三个儿子分头去找房源,最后定下了汇贤里。孩子们开着车让我去看房,我问:“在什么地方?”小儿子说:“过了东风地道的直沽街就到了。”我一听,懵了,记忆里立刻就涌起了若干年前在这里的两次遭遇。
汽车驶过地道,还是往左一拐,咦!这里变样了,平坦的柏油路,两面楼群耸立,右侧是汇贤南里,左侧是汇贤里安教小区,再往里走就是万隆汇贤里。一大片楼房还没完工,选定之后就办了手续。1998年3月,我和老伴搬进了小区。看来,也算是缘分吧,我还是在直沽街买了房。新家,舒适的卧室,优雅的客厅,明亮的书斋,宽敞的厨房,入厕不出门,洗浴在家中,彻底改变了往日平房“一室多用”的老格局;每逢节日,一家三代十余口人在这里团聚,老年身在福中,圆了多年梦想。
岁月荏苒,转眼又是4年。居住环境洁净清幽,节日小区歌舞欢腾,早上晨练有小广场、小花园,有健身器材;出门汽车四通八达,商场超市就近购物,百姓生活需求足矣。
眼前的现实,涤荡了以往埋藏在心底对直沽街的茫然与无奈,我终于在这里安了家。真是“东风地道左邻处,一片荒芜都不见,换了人间。”
相关人物
汪宝树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河东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