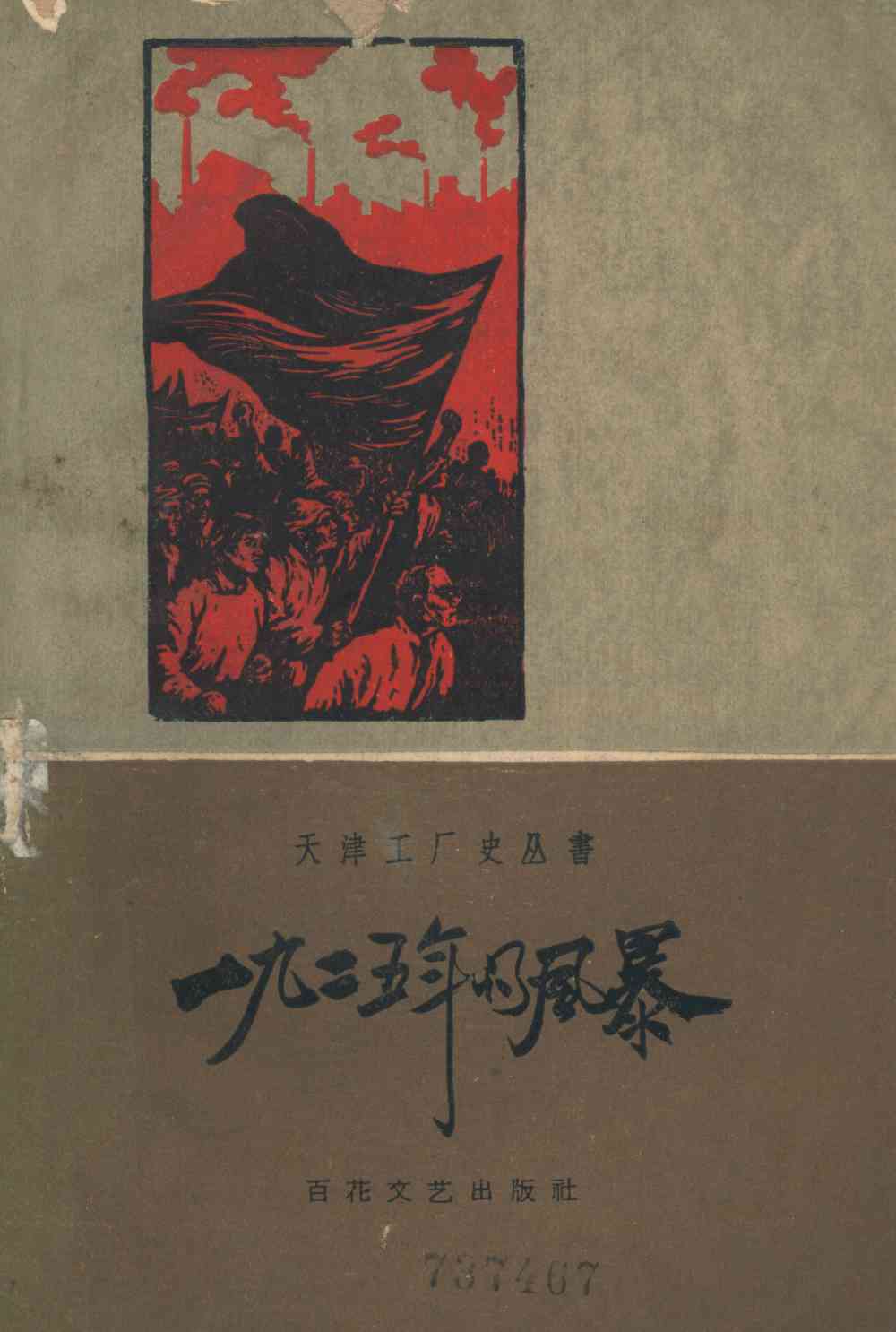我十一岁上工
内容
我十一岁那年的秋天,随着招工員蔣罗鍋,走进了黑暗无光的裕大紗厂的大門。因为家里事前給蔣罗鍋送过礼,驗工員幷沒有怎么难为我,开口就問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住在那?家里都有什么人?但我心里还是扑騰着,嗓音有点沙哑的一一作了回答。而后一个40来岁大个子山东人,讓我站在立尺上,量我的身高,我眞急了,怕嫌我长的个矮,我心里思量着,眼瞅着量我的大个子,我的脚底暗地使劲;我翹起了脚后根,身子、脖子使劲地往上挺着,再加上我在家已垫好在鞋底的破棉花,把自己身子拉长了估計高出五、六寸来。听那山东口音的大个子往里边說:身高4.5尺,我心里眞暗乐。又讓我站在磅秤上过我的体重,我恨从家里来时,家里沒有餑餑吃飽肚子算点重量,我站在磅秤上便使劲地往下压,想压重秤盤,但是我身子离开地已使不上劲了。但又听那大个子往里說:体重72磅。后来讓我看墙上挂着的考查眼睛的視力圖,只試了我一只眼,又听那人在里边說:視力0.9。这一番检查,把我紧张得汗順着后背直往下流。最后招工員拍着我的肩膀說:“这次行了!进工后好好的干活。”我答应:“是,謝謝您。”那个山东口音的大个子向我带有敎育的口气說:“我領你进厂,見了大头們、日本先生們要鞠躬,干活时要老老实实地干!”我答应:“是。”他带着我走进机器轟隆隆响的細紗車間,別人說什么我都听不見了,象是傻人一样。在細紗站着等了一回,从西边来了一个象狗熊的大高个,戴着綠色的“三道”帽子,穿着洋服,臉上嵌着兩只象牛蛋子一样的大眼,小肚子往外凸有半尺多高,兩只手往后背着。要是三岁的小孩子乍看見非得吓哭了不可。我总算大几岁,沒有被吓哭,但心里也确实有点害怕他。带我来的那个人,給我介紹說:“这是王大头王先生。”我沒有听淸楚他的話,也忘記了給大头鞠躬。那大头發起脾气来了,便对带我丞的那个大說:“你給我送这样的傻人来干嘛?”带我来的那个人急了,低头对我詭:“你怎么忘啦!你眞是記吃不記事的东西!快給王头鞠躬吧!”他随手按了我头一下,我給王头鞠了躬。带我来的那大个子把我交給王大头,回头就走了。現在我唯一認識的就是这怪家伙了。王大头交給我一把扫地的刷子,用手指了下說:“你就管这一塊地,要扫的净,要不就不要你!”我点了点头答应一声是。就这样,我当牛做馬的童工时代便开始了。
我抱着王大头交給我的扫地刷子干了約有兩个来月。这兩个来月的畫夜折磨,使我变成了小老头,失去了童年臉上的光彩,兩个眼珠子凹进眼眶,腮帮子也凹进去了,面黃飢瘦,夜晚讓电灯一照象死人一样,身上連一点劲都沒有。吃上窩头,便强支着担起比扫地更累的活“摆管”。王大头把我交給一个高个子有点駝背外号叫“难揍”的搖把(落紗长),他交給我一个三个轱轆的推管小車,吿訴我:“你管这一塊!”我点了点头,推着小車跟着推紗工去下收管去了。合絲的紗管都是用筐盛着,由于我个子矮小和吃不飽肚子身上沒有劲,搬不动一整筐紗管,只好一拤一拤地往車里头放,裝滿車推到楼上,再往細紗的管斗内摆。因为車高,我个矮,每逢到車底时我的手够不着車底的紗管,为了拤車底下的紗管,我要肚子压在車帮上伸手去够,一不小心常把头碰在車帮上,碰个大疙疸或碰破流血。就这样也避免不了王大头和搖把“难揍”的拳打、脚踢。
我記得有一次上班,我实在太累了,就和一个叫小黃的扫地工更換了工作,后被至大头知道了;他找着我不問靑紅皂白,上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子,底下跟着就是一脚,打完了以后問我:“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工厂!不是在你們家!你要不願意干你就家走吧!”我忍受着疼痛,含着眼泪,压住心里的憤怒,央求他道:“王先生留下我吧。”但是我說什么也不頂事了。只好眼里含着泪水,拿着被开除的条子,走出了厂門口。回家后見了亲人,心里一酸放声哭出来了。我哭着把厂里的經过吿訴了母亲,我的母亲又是疼儿又是顧全家里的生活,带有責备的口气說了我几句。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还得忍气呑声地去托人說情,給王大头送礼。就这样过了兩天我又回到細紗上工了。
这次上工后仍是干摆管的活,但是王大头对我更加刻薄了,他在我的身上吃慣了开除送礼的甜头,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和干活的劳累,再加上生活上的困难,我的身体更加干癟起来,同时得了严重的胃病,每逢上夜班吃不下从家带去的窩头咸罗卜,但是肚子餓的慌,还是用白弁水送下去,到过半夜时嘴里往外流酸水;自己也沒有錢治病,厂里更不用提了。日子长了我的身体眞是骨瘦如柴,每天听到上班的汽笛响,特別是夜班,吓的我就趴在炕上大哭,眞比进屠宰場还害怕。
每天上工以后,不知那儿不順大头或小头的眼,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这是当时童工的家常便飯。我記得夏季的一个夜班,我去楼下合絲(工序的名称)推管,到那一看紗管沒有下来;又看四周沒有日本人和大头們,于是便手拉了一筐紗坐在那儿等着,因为累和餓不多时就睡着了,幷且做起吃飽肚子不受气,和早晨背着書包上学校念書的美梦来。突然一只沉重的脚落在我后背上,美梦被脚踹散了。我急忙起来一看是王大头,吓的我魂不附体。我連忙弯下腰把紗管倒在車里头,王大头看我这样更急了,“叭”的一声一大巴掌落在我的臉上。我的耳朵里响起了嗡嗡的叫声,我用手擦了擦眼泪,睜开眼往車内一看,才知道不是紗管而是管紗。我急忙往外收,但是王大头的嘴和手也沒沒閑着,嘴里駡着,手照着我的后背象擂鼓一样一連就是几下子,当我把紗收出来以后,王大头的食指又落在我腦門子上,戳了儿下說:“你他媽这孩子眞混蛋,你不知道干什么来的嗎?要睡覚,家里去睡!”我只好含着眼泪忍着哭声,裝滿了一車紗管,推到楼上,当我到楼上时,那个外号叫“难揍”的搖把等的急紅了眼,不問靑紅皂白地奔着我的腰部就是一脚,把我連人带車踢在南墙上,我的臉和半边身子被碰破流出了鮮紅的血。我眞急了,俗語說:“人急了上房,狗急了跳墙!”心里想我跟他拼了!我照着他冲去,揚手抓住了他的裆部,使劲地拉,而他的拳头就在我后心叭叭的乱打,我究竟是人小力薄,讓他这頓拳头打的趴在地上。后来被我們共患难的大姐們給說情,才不打我了。在旧社会的工人,特別是我們那一代的童工,身受的压迫眞是說不尽,写不完。
那时候,童工不光要受头們的欺負,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大孩子常常欺負小孩子。
我記得靠着茅房的北面,有一个小伙子,比我們大几岁,胖胖的,园园臉,胳膊根很粗,腰里扎着“腰里硬”,說着滿口的天津話,他幷沒有靠山,仗着身强力壮,把我們都唬住了,对我們說話就象軍队發命令一样,誰敢道半个不字,就是一陣拳打脚踢。可是他在那些大、小工头的眼前,也是跟我們一样受气。
那时我們誰拾着女工丟的梳子或別人掉的錢,都得如数地交給他,否則他就打你一頓,这样日子长了,他就給我們立下一項規矩:不管誰拾到什么,都得归他。
有一天,胖子拾到半截鋼鋸条,便到修理場磨出了刀刃,然后再用石头磨快,用紗拈了根绳子纏好了刀把,象是卖罗卜的刀子一样,他跟我們說:“我这刀子飞快,可以給你們剃头,准保不疼。”当时叫我和小黃等三个人:“走,咱到茅房試試去!”我們問:“你会剃嗎?”他說:“不会剃咱学呀!”我們跟他到了茅房,他拉着我的胳膊說:“先給你剃!”我因为沒尝过他剃头疼的滋味,心里幷不害怕。胖子把茅房的水龙头开开,給我来了个凉水澆头,洗完以后,他脚蹬着洋灰台,讓我橫着趴在他的大腿上,他的左手拤住我的头皮,右手上去就是一刀子,这一刀子下去鋸鋸拉拉地剃下一条子头髮来,疼的我直出汗,可是胖子哈哈地大乐起来。在旁边站着的小黃他們还捧胖子說:“胖子,眞有兩下子!”胖子同意地問我:“不太疼吧?”我咬着牙回答:“不太疼,就是有点热燒火燎的。”胖子就这样按着我的腦袋一刀子一刀子地剃,下班前总算腦袋剃完了,又用水給我冲,这一冲可眞够我嗆,疼的鑽心。我讓小黃給我看看,小黄数了数說:“才拉了四五个口子。”胖子在旁边說:“那沒有关系,过几天就好啦!”这一天只給我一个人剃的。从此,胖子上了剃头的癮,第二天,到快要下班完活时,又把小黃他們叫去剃了。开始时他一天只能剃一个,沒有一个星期的工夫,胖子的剃头手艺練熟了,把我們的头也差不多都給剃剃完了,再剃就得从头来了。
我眞尝够了他給剃头的苦头,但是胖子癮头正大,你不願剃,他就打你,我也不敢說不剃,只好硬着美皮讓他剃那沒有长出来的头發。在他最火热的时候,我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剃兩次头。
直到胖子这股癮过去,我們的腦袋才算熬出来了。
我抱着王大头交給我的扫地刷子干了約有兩个来月。这兩个来月的畫夜折磨,使我变成了小老头,失去了童年臉上的光彩,兩个眼珠子凹进眼眶,腮帮子也凹进去了,面黃飢瘦,夜晚讓电灯一照象死人一样,身上連一点劲都沒有。吃上窩头,便强支着担起比扫地更累的活“摆管”。王大头把我交給一个高个子有点駝背外号叫“难揍”的搖把(落紗长),他交給我一个三个轱轆的推管小車,吿訴我:“你管这一塊!”我点了点头,推着小車跟着推紗工去下收管去了。合絲的紗管都是用筐盛着,由于我个子矮小和吃不飽肚子身上沒有劲,搬不动一整筐紗管,只好一拤一拤地往車里头放,裝滿車推到楼上,再往細紗的管斗内摆。因为車高,我个矮,每逢到車底时我的手够不着車底的紗管,为了拤車底下的紗管,我要肚子压在車帮上伸手去够,一不小心常把头碰在車帮上,碰个大疙疸或碰破流血。就这样也避免不了王大头和搖把“难揍”的拳打、脚踢。
我記得有一次上班,我实在太累了,就和一个叫小黃的扫地工更換了工作,后被至大头知道了;他找着我不問靑紅皂白,上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子,底下跟着就是一脚,打完了以后問我:“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工厂!不是在你們家!你要不願意干你就家走吧!”我忍受着疼痛,含着眼泪,压住心里的憤怒,央求他道:“王先生留下我吧。”但是我說什么也不頂事了。只好眼里含着泪水,拿着被开除的条子,走出了厂門口。回家后見了亲人,心里一酸放声哭出来了。我哭着把厂里的經过吿訴了母亲,我的母亲又是疼儿又是顧全家里的生活,带有責备的口气說了我几句。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还得忍气呑声地去托人說情,給王大头送礼。就这样过了兩天我又回到細紗上工了。
这次上工后仍是干摆管的活,但是王大头对我更加刻薄了,他在我的身上吃慣了开除送礼的甜头,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和干活的劳累,再加上生活上的困难,我的身体更加干癟起来,同时得了严重的胃病,每逢上夜班吃不下从家带去的窩头咸罗卜,但是肚子餓的慌,还是用白弁水送下去,到过半夜时嘴里往外流酸水;自己也沒有錢治病,厂里更不用提了。日子长了我的身体眞是骨瘦如柴,每天听到上班的汽笛响,特別是夜班,吓的我就趴在炕上大哭,眞比进屠宰場还害怕。
每天上工以后,不知那儿不順大头或小头的眼,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这是当时童工的家常便飯。我記得夏季的一个夜班,我去楼下合絲(工序的名称)推管,到那一看紗管沒有下来;又看四周沒有日本人和大头們,于是便手拉了一筐紗坐在那儿等着,因为累和餓不多时就睡着了,幷且做起吃飽肚子不受气,和早晨背着書包上学校念書的美梦来。突然一只沉重的脚落在我后背上,美梦被脚踹散了。我急忙起来一看是王大头,吓的我魂不附体。我連忙弯下腰把紗管倒在車里头,王大头看我这样更急了,“叭”的一声一大巴掌落在我的臉上。我的耳朵里响起了嗡嗡的叫声,我用手擦了擦眼泪,睜开眼往車内一看,才知道不是紗管而是管紗。我急忙往外收,但是王大头的嘴和手也沒沒閑着,嘴里駡着,手照着我的后背象擂鼓一样一連就是几下子,当我把紗收出来以后,王大头的食指又落在我腦門子上,戳了儿下說:“你他媽这孩子眞混蛋,你不知道干什么来的嗎?要睡覚,家里去睡!”我只好含着眼泪忍着哭声,裝滿了一車紗管,推到楼上,当我到楼上时,那个外号叫“难揍”的搖把等的急紅了眼,不問靑紅皂白地奔着我的腰部就是一脚,把我連人带車踢在南墙上,我的臉和半边身子被碰破流出了鮮紅的血。我眞急了,俗語說:“人急了上房,狗急了跳墙!”心里想我跟他拼了!我照着他冲去,揚手抓住了他的裆部,使劲地拉,而他的拳头就在我后心叭叭的乱打,我究竟是人小力薄,讓他这頓拳头打的趴在地上。后来被我們共患难的大姐們給說情,才不打我了。在旧社会的工人,特別是我們那一代的童工,身受的压迫眞是說不尽,写不完。
那时候,童工不光要受头們的欺負,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大孩子常常欺負小孩子。
我記得靠着茅房的北面,有一个小伙子,比我們大几岁,胖胖的,园园臉,胳膊根很粗,腰里扎着“腰里硬”,說着滿口的天津話,他幷沒有靠山,仗着身强力壮,把我們都唬住了,对我們說話就象軍队發命令一样,誰敢道半个不字,就是一陣拳打脚踢。可是他在那些大、小工头的眼前,也是跟我們一样受气。
那时我們誰拾着女工丟的梳子或別人掉的錢,都得如数地交給他,否則他就打你一頓,这样日子长了,他就給我們立下一項規矩:不管誰拾到什么,都得归他。
有一天,胖子拾到半截鋼鋸条,便到修理場磨出了刀刃,然后再用石头磨快,用紗拈了根绳子纏好了刀把,象是卖罗卜的刀子一样,他跟我們說:“我这刀子飞快,可以給你們剃头,准保不疼。”当时叫我和小黃等三个人:“走,咱到茅房試試去!”我們問:“你会剃嗎?”他說:“不会剃咱学呀!”我們跟他到了茅房,他拉着我的胳膊說:“先給你剃!”我因为沒尝过他剃头疼的滋味,心里幷不害怕。胖子把茅房的水龙头开开,給我来了个凉水澆头,洗完以后,他脚蹬着洋灰台,讓我橫着趴在他的大腿上,他的左手拤住我的头皮,右手上去就是一刀子,这一刀子下去鋸鋸拉拉地剃下一条子头髮来,疼的我直出汗,可是胖子哈哈地大乐起来。在旁边站着的小黃他們还捧胖子說:“胖子,眞有兩下子!”胖子同意地問我:“不太疼吧?”我咬着牙回答:“不太疼,就是有点热燒火燎的。”胖子就这样按着我的腦袋一刀子一刀子地剃,下班前总算腦袋剃完了,又用水給我冲,这一冲可眞够我嗆,疼的鑽心。我讓小黃給我看看,小黄数了数說:“才拉了四五个口子。”胖子在旁边說:“那沒有关系,过几天就好啦!”这一天只給我一个人剃的。从此,胖子上了剃头的癮,第二天,到快要下班完活时,又把小黃他們叫去剃了。开始时他一天只能剃一个,沒有一个星期的工夫,胖子的剃头手艺練熟了,把我們的头也差不多都給剃剃完了,再剃就得从头来了。
我眞尝够了他給剃头的苦头,但是胖子癮头正大,你不願剃,他就打你,我也不敢說不剃,只好硬着美皮讓他剃那沒有长出来的头發。在他最火热的时候,我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剃兩次头。
直到胖子这股癮过去,我們的腦袋才算熬出来了。
相关机构
天津市裕大紗厂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