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抓路线学大寨 农业生产迈大步
| 内容出处: | 《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经验汇编》 图书 |
| 唯一号: | 020020020230024668 |
| 颗粒名称: | 狠抓路线学大寨 农业生产迈大步 |
| 分类号: | F327.21 |
| 页数: | 12 |
| 页码: | 79-9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天津市西郊区张窝公社房庄子大队在学大寨过程中,通过抓路线,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摆正农业与工副业关系,实现农业高产和集体经济发展。 |
| 关键词: | 西郊区 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生产 |
内容
我们房庄子大队是个小村,只有一百三十六户,六百八十八人,土地七百九十三亩六,粮田六百八十六亩。地势低洼,土质盐碱,历史上是佃户村。解放前,这里流传着“穷房庄,苦房庄,春天盐碱白茫茫,夏季沥涝水汪汪,播下五升种,打回二斗粮,穷人没法活,卖儿卖女去逃荒”。解放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广。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学大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整风以来,路线斗争年年搞,精神面貌年年变,粮食产量年年增。从一九六七年以来,两年上《纲要》;三年跨“黄河”;去年大旱跨“长江”;今年粮食总产达到六十二万零一百一十二斤,平均亩产九百五十二斤,跟一九六四年比,总产和单产增加九倍。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连续九年,年年卖余粮,共六十二万多斤,其中今年交售余粮十六万斤。集体储备越来越厚,公共积累已达四十多万元,除固定财产占压外,还存现金七万多元;储备粮十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多斤。机械化从无到有,现有拖拉机两台,电动机、打井机、柴油机、扬场机、脱粒机、变压器、水泵等各种大型农机具九十八台,打机井八眼,打场、耕地、播种、脱粒、扬场、灌溉、饲料和粮食加工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也逐步改善。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批林整风的丰硕成果,是农业学大寨的结果。我们的体会是:
学大寨,首先抓路线,摆正农业与工副业的关系
学大寨千条万条,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重要。这是我们的切身体会。十几年来,我们在学大寨的路程上,经历着激烈的、反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农为主,还是以副为主;是以粮为纲,还是以钱为纲;这实质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斗争,决定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单干黑风的袭击下,“大队裱佛像,小队开香坊,全村变成了迷信品加工厂”,那年才收了两万斤粮食,单产才二十斤,吃粮靠国家,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够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苦头。
一九六四年,经过伟大的“四清”运动,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改选了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一年时间,扭转了局面,面貌大变,到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达到二十三万斤,开始向国家交售粮食一万二千斤。贫下中农尝到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头,学大寨的劲头更足了,大干的场面更大了,粮食增长的幅度更快了。到一九六七年,粮食上了《纲要》。社员口粮也提高了,户里有了余粮。这时抓钱的苗头又出现了,有人说什么“搞工副业是吹糠见米,来钱容易。粮食够吃了,该抓钱了”。我们意识到这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表现,于是就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联系我们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批判了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使大家认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进一步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干部、群众一心扑在生产上。
但是,我们当时对农业和工副业的关系认识并不完全清楚,曾笼统地认为搞副业就是资本主义倾向,主张不搞工副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慢慢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从一九六七年粮食上了《纲要》后,我们就想过“长江”。喊了两三年,总停在五百多斤,没有上去。主要是资金不足,没有钱买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影响农业大上。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三年之内,我们大队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包括城市下乡插队落户人口),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由于挖河修路,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每人平均土地由一亩六下降到一亩一。为了早日跨“长江”,地越种越细,农业生产费用越来越大,化肥、农药、水电费的开支较过去成倍地增长。一九七〇年农业生产费用为三万三千五百多元,较一九六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一九七〇年虽然取得了农业大丰收,秋后一决算,来了个增产减收。
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呢?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回忆了走过来的道路,这才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重副轻农、重钱轻粮是资本主义倾向,任何时候也是错误的。它腐蚀人的思想,损害农业这个基础,必须坚决批判;但是,只抓农业,忽视了多种经营,对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不利的。
一九七一年,我们办起了工副业,为发展农业生产积累了资金。如何摆正农业和工副业的关系呢?我们支部坚持以农为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以副养机,以机促农的方针。去年天大旱,我们决心以大寨为榜样,战天斗地夺高产,党支部决定暂停了工副业,全力以赴抗旱点种,抗旱保苗。有人就出来算开帐了,说工副业停一天就少收入千八百块,种一亩棒子收一千斤,满打满算不才百十块吗?这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只抓抗旱,必须抓路线。这笔帐不算清楚,就不能战胜干旱夺丰收。于是我们就组织社员批判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我们组织社员算了这样一笔帐:咱们国家有多少人口,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全年得需要多少?我们种地的不打粮食,粮食从哪来呢?靠进口,那是苏修的路!我们搞马列主义,就得自力更生。不能算小帐,要算大帐。这一算,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没词了,结果工副业停了二十一天,集中力量抗旱,夺得了大旱之年过“长江”。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时刻不忘党的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于资本主义倾向天天斗,时时斗。我们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三看三不忘”的处理农副业关系的标准。三看就是:一看领导主要精力放在哪里;二看主要劳力用在哪里;三看工副业收入花在哪里。三不忘是:不忘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不忘多打粮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本分;不忘国家建设、保卫祖国、支援世界革命需要更多的粮食。
第一,领导精力必须主要用在农业上。“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路线偏不偏,干部是关键。我们大队党支部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全部抓农业。从一九七一年办起了铸件厂,除一名支委抓副业外,其他四名支委全部抓农业;抓副业的支委也是干着副业,想着农业,想方设法支援农业。这样就保证了在领导农业生产上精力集中,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党支部抓路线,抓思想,抓关键措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带领着社员群众艰苦奋斗,大办农业。
第二,劳力主要用在农业上。不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上有足够的劳动力,要搞好农业生产就是一句空话。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以农为主,还是以副为主;是先考虑农业,还是先考虑副业;是农业人力有了多余再搞副业,还是主要劳力搞副业挤了农业,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劳力是这样安排的: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我们队共增加劳动力一百零五人,用于工副业四十二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占这三年中增加劳力的百分之四十。当农、副业发生了争劳力的矛盾时,我们就坚决为农业让路。去年抗旱,工副业停了二十一天,今年三夏三秋,工副业停了四十多天。这几年劳力使用的基本情况是:用于改土、积肥、农田管理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副业占百分之十左右,这样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第一线上有足够的劳动力。
第三,搞副业为了什么?增加了收入干什么?是为了分呢,还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支持粮食夺丰收呢?这是检验我们搞副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这几年有了工副业的收入,不仅及时购买了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及时支持了农业大上,而且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保证了农业大上。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和今年,从工副业积累四十多万元,除购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打井机、水泵、牲畜、大车、打机井、拉电缆等花了二十多万,还存现金十多万元,达到了以副养农,以机促农的目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路线正,粮食增;路线偏,粮食减。如果领导不能集中抓农业,劳力不能集中搞农业,副业不支持农业,工副业生产连年翻番,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这就是错误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倾向。但是,如果只抓粮,丢掉全面发展,从而集体收入少,生产资金困难,农业生产也不能迈大步。只有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农业和工副业关系上实行以农为主,以副养机,以机促农,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方针。
学大寨,艰苦奋斗,苦干大干
路线、方向正了,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领导必须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吃大苦,流大汗,在改变生产条件上下功夫。一九六四年以前,在刘少奇“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经过“四清”运动,改选了党支部,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是个什么情况呢?大队有半瓶墨水,存折上有一角八分钱,队的牲口是老牛、小驴、疙瘩套。社员生活也很困难,吃着低指标,瓜菜代,连打油买盐也困难。再看看土地呢?白花花的盐碱地,没沟没埝,高洼不平,真是“阴天一片黑,晴天一片白”。面对着这个乱摊子怎么办?房庄子贫穷落后的面貌能不能改变?怎样改变?干部在天天想,群众在天天想,议论纷纷,其说不一。就在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决心立大寨志,走大寨路,向大寨贫下中农学习。学大寨,见行动,在盐碱地上闹革命。就在这年冬天,改土治碱的战斗打响了。当时寒风刺骨,飞沙打脸,地冻得梆梆硬。社员们在大寨精神鼓舞下,吃着山芋干,改造盐碱滩。广大贫下中农说:“地再硬,没有我们的骨头硬,天再冷也动摇不了我们改天换地的决心!”“现在吃点苦,是为了子孙后代得幸福。”经过一个冬春的艰苦奋斗,当年取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增加了将近三倍。就这样,年年坚持改土,粮食产量年年增加,到一九六八年用了五年的工夫,把全部土地改造了一遍,粮食单产也由一九六四年的一百零一斤,达到了五百一十七斤,过了“黄河”。可是刚改造完,再看看开头改造过的地,经过几年冬天冻,春天化,风吹雨打水刷,沟渠有的淤了一半,有的淤得象个碟子,渗透力降低,有碱洗不下去,盐碱又托上来了。如果不继续改造,不仅影响粮食继续上升,还可能降下来。我们分析了这种情况,认识到土地改造没有头,生产潜力没挖尽,要想产量继续高,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停。于是党支部领导社员继续革命,重新改造土地,向高标准进军。从此,又开新沟,填老沟,改大撇为小撇,块块见方,方方有畦,土地平整,做到了咸淡分家,排灌分流。为了适应机井灌溉的需要,去年秋冬又平整、改造了二百多亩。到今年为止,又用了四年时间,把六百多亩粮田重新改造了一遍,全部实现了畦田化。改土用工六万多个,共动土十五万多方。
改土是费力、出汗、吃苦的活。说着好说,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艰苦奋斗,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当懦夫懒汉?是坚持高标准,彻底革命,还是修修补补,凑凑合合?这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看起来是个改土问题,实质是个路线问题。社会主义是斗出来的。我们学大寨就得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斗,同各种错误思想斗,时时斗,天天斗,年年斗。不能风平浪静地学,不能舒舒服服地学,学大寨必须下苦功夫,下硬功夫。
改造土地不光是挖沟治碱的问题,还有个改良土壤的问题。三分改,七分养。这就需要多上农家肥。只有不断提高地力,才能逐渐改变土质结构,逐渐改良土壤。“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是我们庄稼人千百辈实践的经验。可要抓到肥,用上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年使把劲抓上去了,明年一松手又下来了,非得年年使劲,年年抓,才能年年多施肥。一九六四年前,我们的地绝大部分是不上肥的“卫生田”。到一九六四年,施肥面积只占三分之一;到一九六八年,达到三分之二;从一九六九年以来全部施了肥。施肥数量也不断增加,每亩施肥由两千斤增到一万多斤,今年全年每亩施肥有一万五千多斤。我们的肥源主要靠养猪积肥,几年来坚持队繁户养,养猪年年增加,今年已达到三百二十头,每户平均两头半,上了《纲要》。猪多肥也多,今年光社员投肥就达到二百一十七万斤。猪多、肥多、粮多,反过来粮多、猪多、肥多,是辩证关系,互相促进。再一个肥源是在保证社员烧柴的前提下,搞了一部分秸秆还田。除此以外,就是长年固定挖污泥,每年都能挖一二百万斤。怎么运回来?除了大车、拖拉机,主要靠全队社员用小拉车拉运。一小车只能装八、九百斤,来回好几十里路,不仅男社员干,青年妇女干,家庭妇女照样干,拉着小车来回跑。今年我们学习了平谷三种三收的经验,这是夺高产的好办法,但是办法多好如果没有肥也不行。今年的丰收,肥料充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水利建设也是一样。前几年我们村没有水源,从一九六九年挖了新丰产河,就在我们村边、地边,觉得这下子用水算没问题了。那知道这二年天一旱,河干了,没水了。这一下子,我们对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教导加深了理解,认识到前几年没象抓命脉那样抓地下水,单纯靠河水,吃了苦头。从去年开始,抓了打井,经过二年的努力,实现了井网化,不但粮食亩产过了“长江”,也解决了人、畜用水的大困难。社员们说,多亏听了毛主席的话,走自力更生道路打了井。
随着土、肥、水条件的改善,复种面积不断扩大。一九六四年,夏种面积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一九六九年,达到百分之七十八;一九七二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今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七〇年以来,又狠抓了科学种田,培育良种,改革耕作制度,实行合理密植等。去年战胜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干旱,跨过了“长江”。今年又战胜了春旱秋涝和严重虫灾夺得了大丰收。这些,绝不仅仅光是由于今年的努力,如果没有前几年的改土、积肥、科学种田等方面的努力,今年的大丰收是不可能的。
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我们还狠抓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落实,实行了定额管理和责任制。去年天大旱,我们实行了三定三保的责任制,就是按作业组定地块、定任务、定时间;保浇、保活、保全苗。这个办法,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家干了三十八天,挖土井,担了三十多万挑水,实现了大旱大干大增产。今年钻心虫特别严重,在治虫时,我们统一质量标准,要求虫子死亡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按组搞了定额。男女社员认真负责,一棵棵地打药、灌药。那时候天闷地潮,玉米地里热得喘不上气来,一进去就是一身汗,还得弄一身药;但我们硬是把全部庄稼一棵一棵地治了五、六遍,有的治了七遍,终于战胜了虫害,没有造成损失。今年秋收种麦,三天两头下雨,大车、拖拉机进不了地,给秋收种麦带来很大困难,男女社员硬是把几十万斤粮食从地里背出来,四百万斤肥料用双肩挑进地里,大干了二十多天,及时种了五百多亩小麦,全是秋分麦,长势比那年都好。
陈永贵同志说得好:“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修修补补改变不了面貌。”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不在土地改造、水利建设和积肥上下苦功夫,不改变基本生产条件,要想把粮食搞上去,是办不到的。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居于“八字宪法”的首位;水是农业的命脉;肥是粮食的粮食。对土地改造,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就低产;种上收不收,水利是命脉;高产不高产,肥料是保证;粮食要过“长江”,科学种田是桥梁。
几年学大寨,回头看,有进步;看形势,鼓干劲。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步子不大。今后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快马加鞭,跟上发展的大好形势。明年我们计划夏收一季亩产六百斤,全年突破千斤关,保证一千一,力争一千二,实现一人一猪,多打粮,多贡献,以实际行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贡献!
学大寨,首先抓路线,摆正农业与工副业的关系
学大寨千条万条,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重要。这是我们的切身体会。十几年来,我们在学大寨的路程上,经历着激烈的、反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农为主,还是以副为主;是以粮为纲,还是以钱为纲;这实质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斗争,决定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单干黑风的袭击下,“大队裱佛像,小队开香坊,全村变成了迷信品加工厂”,那年才收了两万斤粮食,单产才二十斤,吃粮靠国家,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够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苦头。
一九六四年,经过伟大的“四清”运动,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改选了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一年时间,扭转了局面,面貌大变,到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达到二十三万斤,开始向国家交售粮食一万二千斤。贫下中农尝到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头,学大寨的劲头更足了,大干的场面更大了,粮食增长的幅度更快了。到一九六七年,粮食上了《纲要》。社员口粮也提高了,户里有了余粮。这时抓钱的苗头又出现了,有人说什么“搞工副业是吹糠见米,来钱容易。粮食够吃了,该抓钱了”。我们意识到这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表现,于是就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联系我们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批判了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使大家认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进一步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干部、群众一心扑在生产上。
但是,我们当时对农业和工副业的关系认识并不完全清楚,曾笼统地认为搞副业就是资本主义倾向,主张不搞工副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慢慢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从一九六七年粮食上了《纲要》后,我们就想过“长江”。喊了两三年,总停在五百多斤,没有上去。主要是资金不足,没有钱买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影响农业大上。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三年之内,我们大队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包括城市下乡插队落户人口),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由于挖河修路,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每人平均土地由一亩六下降到一亩一。为了早日跨“长江”,地越种越细,农业生产费用越来越大,化肥、农药、水电费的开支较过去成倍地增长。一九七〇年农业生产费用为三万三千五百多元,较一九六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一九七〇年虽然取得了农业大丰收,秋后一决算,来了个增产减收。
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呢?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回忆了走过来的道路,这才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重副轻农、重钱轻粮是资本主义倾向,任何时候也是错误的。它腐蚀人的思想,损害农业这个基础,必须坚决批判;但是,只抓农业,忽视了多种经营,对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不利的。
一九七一年,我们办起了工副业,为发展农业生产积累了资金。如何摆正农业和工副业的关系呢?我们支部坚持以农为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以副养机,以机促农的方针。去年天大旱,我们决心以大寨为榜样,战天斗地夺高产,党支部决定暂停了工副业,全力以赴抗旱点种,抗旱保苗。有人就出来算开帐了,说工副业停一天就少收入千八百块,种一亩棒子收一千斤,满打满算不才百十块吗?这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只抓抗旱,必须抓路线。这笔帐不算清楚,就不能战胜干旱夺丰收。于是我们就组织社员批判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我们组织社员算了这样一笔帐:咱们国家有多少人口,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全年得需要多少?我们种地的不打粮食,粮食从哪来呢?靠进口,那是苏修的路!我们搞马列主义,就得自力更生。不能算小帐,要算大帐。这一算,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没词了,结果工副业停了二十一天,集中力量抗旱,夺得了大旱之年过“长江”。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时刻不忘党的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于资本主义倾向天天斗,时时斗。我们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三看三不忘”的处理农副业关系的标准。三看就是:一看领导主要精力放在哪里;二看主要劳力用在哪里;三看工副业收入花在哪里。三不忘是:不忘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不忘多打粮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本分;不忘国家建设、保卫祖国、支援世界革命需要更多的粮食。
第一,领导精力必须主要用在农业上。“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路线偏不偏,干部是关键。我们大队党支部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全部抓农业。从一九七一年办起了铸件厂,除一名支委抓副业外,其他四名支委全部抓农业;抓副业的支委也是干着副业,想着农业,想方设法支援农业。这样就保证了在领导农业生产上精力集中,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党支部抓路线,抓思想,抓关键措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带领着社员群众艰苦奋斗,大办农业。
第二,劳力主要用在农业上。不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上有足够的劳动力,要搞好农业生产就是一句空话。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以农为主,还是以副为主;是先考虑农业,还是先考虑副业;是农业人力有了多余再搞副业,还是主要劳力搞副业挤了农业,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劳力是这样安排的: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我们队共增加劳动力一百零五人,用于工副业四十二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占这三年中增加劳力的百分之四十。当农、副业发生了争劳力的矛盾时,我们就坚决为农业让路。去年抗旱,工副业停了二十一天,今年三夏三秋,工副业停了四十多天。这几年劳力使用的基本情况是:用于改土、积肥、农田管理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副业占百分之十左右,这样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第一线上有足够的劳动力。
第三,搞副业为了什么?增加了收入干什么?是为了分呢,还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支持粮食夺丰收呢?这是检验我们搞副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这几年有了工副业的收入,不仅及时购买了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及时支持了农业大上,而且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保证了农业大上。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和今年,从工副业积累四十多万元,除购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打井机、水泵、牲畜、大车、打机井、拉电缆等花了二十多万,还存现金十多万元,达到了以副养农,以机促农的目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路线正,粮食增;路线偏,粮食减。如果领导不能集中抓农业,劳力不能集中搞农业,副业不支持农业,工副业生产连年翻番,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这就是错误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倾向。但是,如果只抓粮,丢掉全面发展,从而集体收入少,生产资金困难,农业生产也不能迈大步。只有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农业和工副业关系上实行以农为主,以副养机,以机促农,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方针。
学大寨,艰苦奋斗,苦干大干
路线、方向正了,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领导必须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吃大苦,流大汗,在改变生产条件上下功夫。一九六四年以前,在刘少奇“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经过“四清”运动,改选了党支部,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是个什么情况呢?大队有半瓶墨水,存折上有一角八分钱,队的牲口是老牛、小驴、疙瘩套。社员生活也很困难,吃着低指标,瓜菜代,连打油买盐也困难。再看看土地呢?白花花的盐碱地,没沟没埝,高洼不平,真是“阴天一片黑,晴天一片白”。面对着这个乱摊子怎么办?房庄子贫穷落后的面貌能不能改变?怎样改变?干部在天天想,群众在天天想,议论纷纷,其说不一。就在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决心立大寨志,走大寨路,向大寨贫下中农学习。学大寨,见行动,在盐碱地上闹革命。就在这年冬天,改土治碱的战斗打响了。当时寒风刺骨,飞沙打脸,地冻得梆梆硬。社员们在大寨精神鼓舞下,吃着山芋干,改造盐碱滩。广大贫下中农说:“地再硬,没有我们的骨头硬,天再冷也动摇不了我们改天换地的决心!”“现在吃点苦,是为了子孙后代得幸福。”经过一个冬春的艰苦奋斗,当年取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增加了将近三倍。就这样,年年坚持改土,粮食产量年年增加,到一九六八年用了五年的工夫,把全部土地改造了一遍,粮食单产也由一九六四年的一百零一斤,达到了五百一十七斤,过了“黄河”。可是刚改造完,再看看开头改造过的地,经过几年冬天冻,春天化,风吹雨打水刷,沟渠有的淤了一半,有的淤得象个碟子,渗透力降低,有碱洗不下去,盐碱又托上来了。如果不继续改造,不仅影响粮食继续上升,还可能降下来。我们分析了这种情况,认识到土地改造没有头,生产潜力没挖尽,要想产量继续高,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停。于是党支部领导社员继续革命,重新改造土地,向高标准进军。从此,又开新沟,填老沟,改大撇为小撇,块块见方,方方有畦,土地平整,做到了咸淡分家,排灌分流。为了适应机井灌溉的需要,去年秋冬又平整、改造了二百多亩。到今年为止,又用了四年时间,把六百多亩粮田重新改造了一遍,全部实现了畦田化。改土用工六万多个,共动土十五万多方。
改土是费力、出汗、吃苦的活。说着好说,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艰苦奋斗,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当懦夫懒汉?是坚持高标准,彻底革命,还是修修补补,凑凑合合?这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看起来是个改土问题,实质是个路线问题。社会主义是斗出来的。我们学大寨就得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斗,同各种错误思想斗,时时斗,天天斗,年年斗。不能风平浪静地学,不能舒舒服服地学,学大寨必须下苦功夫,下硬功夫。
改造土地不光是挖沟治碱的问题,还有个改良土壤的问题。三分改,七分养。这就需要多上农家肥。只有不断提高地力,才能逐渐改变土质结构,逐渐改良土壤。“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是我们庄稼人千百辈实践的经验。可要抓到肥,用上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年使把劲抓上去了,明年一松手又下来了,非得年年使劲,年年抓,才能年年多施肥。一九六四年前,我们的地绝大部分是不上肥的“卫生田”。到一九六四年,施肥面积只占三分之一;到一九六八年,达到三分之二;从一九六九年以来全部施了肥。施肥数量也不断增加,每亩施肥由两千斤增到一万多斤,今年全年每亩施肥有一万五千多斤。我们的肥源主要靠养猪积肥,几年来坚持队繁户养,养猪年年增加,今年已达到三百二十头,每户平均两头半,上了《纲要》。猪多肥也多,今年光社员投肥就达到二百一十七万斤。猪多、肥多、粮多,反过来粮多、猪多、肥多,是辩证关系,互相促进。再一个肥源是在保证社员烧柴的前提下,搞了一部分秸秆还田。除此以外,就是长年固定挖污泥,每年都能挖一二百万斤。怎么运回来?除了大车、拖拉机,主要靠全队社员用小拉车拉运。一小车只能装八、九百斤,来回好几十里路,不仅男社员干,青年妇女干,家庭妇女照样干,拉着小车来回跑。今年我们学习了平谷三种三收的经验,这是夺高产的好办法,但是办法多好如果没有肥也不行。今年的丰收,肥料充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水利建设也是一样。前几年我们村没有水源,从一九六九年挖了新丰产河,就在我们村边、地边,觉得这下子用水算没问题了。那知道这二年天一旱,河干了,没水了。这一下子,我们对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教导加深了理解,认识到前几年没象抓命脉那样抓地下水,单纯靠河水,吃了苦头。从去年开始,抓了打井,经过二年的努力,实现了井网化,不但粮食亩产过了“长江”,也解决了人、畜用水的大困难。社员们说,多亏听了毛主席的话,走自力更生道路打了井。
随着土、肥、水条件的改善,复种面积不断扩大。一九六四年,夏种面积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一九六九年,达到百分之七十八;一九七二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今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七〇年以来,又狠抓了科学种田,培育良种,改革耕作制度,实行合理密植等。去年战胜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干旱,跨过了“长江”。今年又战胜了春旱秋涝和严重虫灾夺得了大丰收。这些,绝不仅仅光是由于今年的努力,如果没有前几年的改土、积肥、科学种田等方面的努力,今年的大丰收是不可能的。
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我们还狠抓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落实,实行了定额管理和责任制。去年天大旱,我们实行了三定三保的责任制,就是按作业组定地块、定任务、定时间;保浇、保活、保全苗。这个办法,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家干了三十八天,挖土井,担了三十多万挑水,实现了大旱大干大增产。今年钻心虫特别严重,在治虫时,我们统一质量标准,要求虫子死亡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按组搞了定额。男女社员认真负责,一棵棵地打药、灌药。那时候天闷地潮,玉米地里热得喘不上气来,一进去就是一身汗,还得弄一身药;但我们硬是把全部庄稼一棵一棵地治了五、六遍,有的治了七遍,终于战胜了虫害,没有造成损失。今年秋收种麦,三天两头下雨,大车、拖拉机进不了地,给秋收种麦带来很大困难,男女社员硬是把几十万斤粮食从地里背出来,四百万斤肥料用双肩挑进地里,大干了二十多天,及时种了五百多亩小麦,全是秋分麦,长势比那年都好。
陈永贵同志说得好:“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修修补补改变不了面貌。”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不在土地改造、水利建设和积肥上下苦功夫,不改变基本生产条件,要想把粮食搞上去,是办不到的。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居于“八字宪法”的首位;水是农业的命脉;肥是粮食的粮食。对土地改造,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就低产;种上收不收,水利是命脉;高产不高产,肥料是保证;粮食要过“长江”,科学种田是桥梁。
几年学大寨,回头看,有进步;看形势,鼓干劲。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步子不大。今后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快马加鞭,跟上发展的大好形势。明年我们计划夏收一季亩产六百斤,全年突破千斤关,保证一千一,力争一千二,实现一人一猪,多打粮,多贡献,以实际行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贡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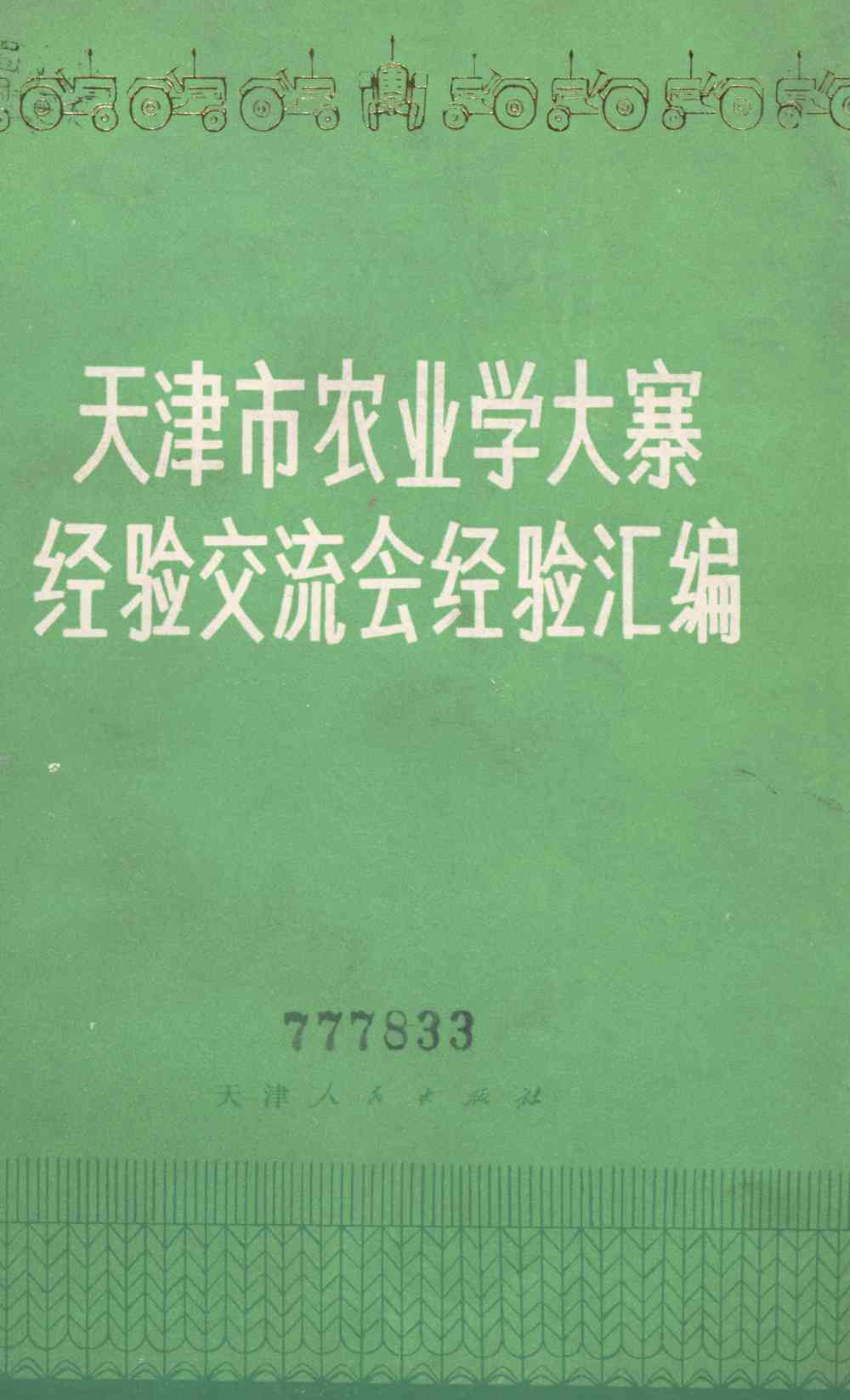
相关机构
西郊区张窝公社房庄子...
相关机构